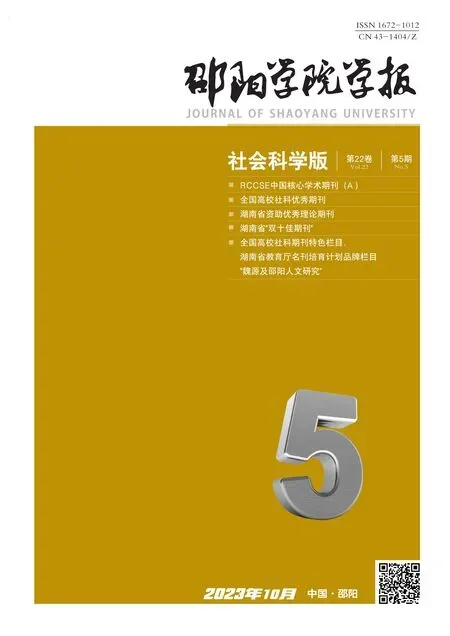清代宝卷与善书之比较
2023-03-11黄彦弘
黄彦弘
(邵阳学院 文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20世纪20年代初,顾颉刚先生注意到了散落在民间社会的孟姜女宝卷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并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和研究,从而揭开了宝卷研究的序幕;百年来,宝卷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随着宝卷研究的兴盛,除了集中研究宝卷本身外,学界还热衷于把宝卷和善书进行比较研究。尽管明知二者是不同的文体,但是在进行对比研究之际,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强调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有意识地忽略彼此之间的差异。比如,刘守华认为善书是宝卷的支系:“善书作为中国民间说唱艺术的重要品种之一,是人所公认的。但其历史源流尚需清理评说。我以为它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宝卷’的支系,乃至可以说就是‘宝卷’的别名或俗称。”[1]马紫晨甚至把宣讲宝卷和宣讲善书混为一体[2]291。不论是强调善书源自宝卷,抑或善书是宝卷的俗称,其实都是在有意识地强化二者之同;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明确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如游子安认为宝卷和善书有明显的区别:
前者是由教首编撰,是为了布教和宣传而制作,后者由士绅文人写成,主要是劝人修善止恶。在流通领域来看,善书是在一般的民间社会之间流行着,但宝卷却在下层社会或被认为是异端的社会之间流行。[3]51
宝卷源自佛教俗讲,到明代,宝卷成为民间教派宣扬教义的主要载体,而善书却是道教世俗化的结果。不论是宝卷还是善书,在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均呈现出阶段性的不同。大体上看,宝卷历经了“古宝卷时代”和嘉庆十年(1805)后“宣卷用、劝善用的”的“新宝卷时代”[4]34-36的阶段;至于善书,明末以前的善书是宗教性的,而明末及其之后的善书却是世俗化与儒学化的[5]。就游子安的论述来看,他所说的宝卷,应该指的是“古宝卷时代”中的教派宝卷;他所说的善书,大致可以理解为明末及其之后的善书。如果就教派宝卷与明末及其之后的善书的区别来看,游子安的理解是比较中肯的,但如果以此来笼统地区别宝卷和善书的不同,难免有以偏概全之感。
从来源与宗教的类别上看,宝卷和善书原本泾渭分明,清代以前很少混淆。到清代,随着世俗化和儒学化的不断推进,宝卷和善书呈现出来的社会功能高度趋同。尽管如此,清人对二者之间的界线还是相当明确的。
一、从清编善书集考察清人眼中的宝卷与善书
清代文人士绅热衷于编纂善书,故而善书在清代盛行。所谓善书,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曾指出:“就是这样一种书籍,即在儒、佛、道之三教合一的,或者是混合了民众宗教的意识下,劝说民众力行实践那些不仅超越了贵贱贫富,而且在普遍庶民的公共社会中广泛流传的道德规范。”[6]445通俗地讲,善书就是一种劝善去恶的通俗文本。不过,清人对善书似乎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定性,基本上持很开放的态度。比如,晚清郑观应在《训俗良规》序中云:“著述之最易感人者,莫如多著善书;善书之最著者,莫如《太上感应篇》《帝君阴骘文》《朱子格言》《颜氏家训》……”[7]1162在清人看来,诸如阴骘文、格言、家训、官箴和蒙学等,只要有助于劝善的文本,都可以视为善书。不仅如此,清人还把跟劝善没有直接关联的药方也纳入善书范畴,如乾隆年间刘山英编辑的《信心应验录》卷八辑录的“脱产要言”等药方。
尽管清人对善书持开放态度,但是,清代文人士绅几乎从来没有把宝卷纳入善书的范畴,这在清人汇编的善书集中可以得到证明。比如,乾隆年间刘山英编印的《信心应验录》是清代大型的善书总集,却并未引录一部宝卷;清吴引孙《有福读书堂丛刻》共辑善书25种,也没有宝卷入录;清吴思善辑《修省良规》8卷、清佚名辑《劝善书》等善书类编,都未曾辑录过任何宝卷。即使到20世纪30年代陕西贺箭村编辑的《古今善书大辞典》,分为上、中、下三册,共辑录善书169种,也没有辑录任何宝卷。
不难看出,在清代文人士绅的观念中,宝卷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善书之外的文本,与善书没有明显的交集。
二、清代宝卷与善书文本结构之比较
到清代,不论是宝卷还是善书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世俗化与儒学化,但即便如此,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明显的,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呈现出来。
(一)作者群体之比较
北宋时期出现的《太上感应篇》被公认为“善书之祖”,《太上感应篇》产生之后,稍后就有文人为之作注释,并增扩到30卷。南宋时期,真德秀、郑清之、陈奂子等文人士绅先后为之作序跋;明清时期,有朱珪、惠栋、俞樾等大儒为之作序作注。更重要的是,《太上感应篇》还得到了宋理宗、明世宗、清世宗等帝王的大力提倡。顺治帝《御制劝善要言序》云:“《感应篇》中要语皆已选入编内,而又命内院词臣翻译《感应篇》,引经征事,刊刻颁布。”[8]1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感应篇》和圣谕一样,都有助于教化。“‘宣讲圣谕’通行民间,在内容上就知书之士,多予附加民间流行善书,尤其故事性之短篇说唱,成为《圣谕》之外之附加品,并在民间兴盛流传。”[9]17《太上感应篇》产生后,仿此产生了一大批善书,且历代善书层出不穷。清代文人士绅大多热衷于编撰善书,在《明清善书知见录》中,张祎琛搜集发现各类善书达737种之多[10]135-313,且绝大多数善书都有文人士绅的署名。
不仅文人士绅积极参与编撰善书,而且刊印也是士绅富人所为。酒井忠夫曾根据《宣讲拾遗》的出版者及捐助者分析指出:“刊印《宣讲拾遗》、捐资捐书的集团,是陕西出身的乡绅(前湖北孔垅镇司巡检、闰灏)和众多的士人(生员)及因捐资捐书善行而被视为生员的民间人士;在民间人士当中,很明显也有山西、甘肃出身的富裕之人。这个集团是由乡绅、士人及工商富裕阶层组成的地域民间的宣讲共同体。”[6]523-524所以说,“清代善书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作为儒学者的乡绅、士人的力量”[6]530。
由此可见,从编撰到出版,《太上感应篇》等善书得到了统治者的倡导及文人士绅等上层势力的大力支持,走的完全是上层路线。
然而,清代的民间宝卷却完全不同,文人士绅几乎从未或者很少参与民间宝卷的编撰。郑振铎曾指出:“注意到‘宝卷’的文人极少。他们都把宝卷归到劝善书的一堆去了,没有人将它们看作文学作品的。且印宝卷的,也都是善书铺。”[11]307郑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了“注意到宝卷的文人极少”,但原因却并非他所说的“他们都把宝卷归到劝善书”里。宝卷之所以不被文人士绅关注,笔者以为,原因至少有二。
其一,在清代,民间宗教的盛行,轻则扰乱社会秩序,重则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与国家的安危,故而,清代统治者不仅把民间宗教定性为“邪教”,而且下令严格禁行。民间宗教被视为“邪教”,被清廷严厉打压,因而“邪教”所通用的教义经典,当然也就被视为“邪经”。由于明清各民间教派几乎都以宝卷作为教义的主要载体,宝卷无形中成为一切“邪经”的代名词。清代统治者不仅严厉打击“邪教”,还同时销毁“邪经”即宝卷。比如道光年间的地方官吏黄育楩《又续破邪详辩序》云:“今欲严禁邪教,必将邪经所说及近世邪教所说,一一辨明,俾愚民不被所惑,则邪教不能传徒,此拔本塞源,实禁邪之要务也。”[12]9因为统治者把“宝卷”视为“邪经”和“违禁品”,文人士绅当然不敢越雷池半步。
其二,宝卷的文字比较粗糙,上层文人士绅压根不屑于参与。如上所述,善书的作者大多署名,但宝卷的编撰者却不同,除了极少数外(1)比如,《醒心宝卷》序后署有“光绪岁次甲午春月之吉常郡蒋玉真撰,陈灿子书”。显然,该宝卷的作者无疑是蒋玉真。,基本上很少署名,即使署名,大多只是化名。比如清道光年间刊刻的《新锲韩祖成仙宝传》,序言有云:“佛祖现身说法,韩仙降传演经。将他修行故事,所托戊丁二人。述编二十四品,练就三八五行。节节事中藏道,篇篇情内隐真。”[13]106序言中所提及的“戊丁”二人,显系化名,至于具体姓名,已无从可考。尽管如此,根据一些蛛丝马迹,仍然能发现清代民间宝卷作者的身份特征。大体上看,清代民间宝卷的作者应该是那些读过圣贤书却科举失意没有取得任何功名资格的“准士”[14]31-34。比如《双钗记宝卷》有序云“余苦读家窗,翻出此书,改为宝卷”(2)转引自张颔:《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火花》1957年第3期。,虽然此宝卷并未署名,但从“苦读家窗”不难推测,该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屡试不中的“准士”。又如,一生未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清末塾师翁仕朝。“十九世纪大部分儒士出身官员,常不离《太上感应篇》及《文昌帝君阴骘文》等著名之因果报应书。而在翁氏竟无收存”。相反,翁氏“仅有《关帝明圣经》,光绪十七年香山张振南序,广州富文斋刻本;《宣化妙经》(即《观音菩萨经》),光绪二十四年,同诚信刻本,及《大圣末劫经》抄本数种”[9]50。翁氏没有收集《太上感应篇》等官方大力倡导的善书,却反而收存了不被官方认可的《关帝明圣经》和《观音菩萨经》等民间宝卷,显示出底层知识阶层与上层文人士绅的不同倾向。亦即,与文人士绅不同,清代的“准士”们似乎更热衷于编撰宝卷。实际上,从当代学者的实地调查结果中,也能得到部分印证。如在江苏靖江,“传说过去一个读书人科举失意,归而编写宝卷讲经”[15]283;在北方,“根据当地调查和许多北方民间宝卷抄本的记载,清嘉庆、道光以后,北方民间宝卷的传播,主要是一些民间的文化人(民间一般尊称他们是“老秀才”)和略识文字的人编写、抄传和‘念卷’”[15]254。可知,宝卷的编撰者基本上是下层文人,他们的总体文化水平可能远不及上层文人士绅,故而,宝卷的语言比较粗俗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同样都具有劝善功能的善书和宝卷,显示出底层知识分子即“准士”与一般文人士绅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线。相较于善书的行上层路径,清代民间宝卷走的完全是底层路线。到晚清时期,尽管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力明显松弛,但终清一代,宝卷从未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正名。
(二)受众对象之比较
由于善书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再加上文人士绅的参与,善书在社会广泛盛行,而民间宝卷的处境却不一样。善书与民间宝卷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因而他们的受众也不完全一样。“一般的善书是通过民间公共社会流传的,而宝卷则是以下层民众社会或者异端的社会阶层为背景而流传的,并经常对具有民众性的农民社会运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力。”[6]445善书的受众对象是“民间公共社会”的全体,可从颜茂猷的善书《迪吉录》得到更明确的了解。《迪吉录》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分8卷,即“一卷:官鉴一,多属卿相”,“心卷:官鉴二,多属侍从”,“普卷:官鉴三,多兵刑”,“度卷:官鉴四”,“兆卷:公鉴一,多家政”,“世卷:公鉴二,多道术交游”,“太卷:公鉴三,多济施”,“平卷:公鉴四,多杀业”[16]30-41。可知,善书《迪吉录》的受众对象既包括普通民众,也包括卿相在内的各级官吏,受众对象比较广泛,适应于全体大众。
而民间宝卷的受众对象则是比“一般的民间公共社会”更低的“下层民众社会”或“有异端背景的社会阶层”。相对善书而言,宝卷劝诫的对象倾向于更底层的民众,主要是指广大的从未受过学校教育的不识字的乡村社会中的“愚夫愚妇”。比如,光绪年间赵定邦序《立愿宝卷》云:“友人自吴门来,携有《立愿宝卷》一书,寓庄论于俚俗,得惩戒之真源,专为愚夫愚妇痛下针砭,而其中辨别隐微,剖析邪正,实与儒书相表里。”[17]441又如,《秀英宝卷》序云:“古人经典所载性与天道之说,文义甚奥,精理难明,即上智文墨之士,犹难一时领悟,况在中下愚人哉?……余受而阅之,见其言虽浅近,理实显明,赏善罚恶,报应昭彰,而破迷醒心一篇,尤足以唤醒痴愚。”[18]43不难看出,宝卷主要在乡村下层社会流传,受众对象主要定位于下层的“愚夫愚妇”,而其中又以生活在底层的女性为主。日本学者奥崎裕司曾指出,宝卷文学中的主人公多为女性,她们忍受一切苦难和迫害,终于成佛、成仙。因为前期宝卷的作者多为尼僧,宣讲宝卷的场所多为尼庵,故听众也以女性居多,甚至还有特别以娼妓为对象宣唱的宝卷。在悲惨命运中挣扎的妓女们通过听宝卷,总算可以找到憧憬来世安乐的一丝慰藉,因而,女性最爱听的就是宝卷[19]116。
(三)表达方式之比较
每一种文体都拥有各自独特的体式、风格与表达方式,宝卷和善书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体,故二者之间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
善书往往以格言的形式直接阐明观点,即使有叙述,也是开头即结尾,很少展开故事情节,故而长于说理,短小精悍。如清代“老名士”尤侗《戒赌文》云:
天下之恶,莫过于赌。牧猪奴戏,陶公所怒。一掷百万,刘毅何苦!今有甚焉,打马斗虎,群居终日,一班水浒,势如劫盗,术比贪贾,口哆目张,足蹈手舞,败固索然,胜亦何取?约有三费,未可枚举。[20]63
又如清人姚廷杰《戒淫录》之“黎民宝训”有云:“一有淫思,便多浪费。须知守分完粮,永远是太平百姓。”[20]75可知,善书言简意赅,但论理非常透彻;不过,这种格言式的说理,显得有点枯燥无味。清代的民间宝卷则不然,民间宝卷由先前的注重说理逐渐转向叙事,常常结合生动的故事形象来阐明道理。比如劝妇人要做“贤良节妇”,在《李宸妃冷宫受苦宝卷》中,是通过讲述李宸妃遭受诸多折磨后,最终被洗刷冤屈、尽享荣华的故事来进行说教。显然,宝卷故事情节极其曲折,感染力极强。尽管如此,该宝卷的目的却并非只是娱乐,其序有云“此种宝卷,皆是劝人为善,要做贤良节妇”[18]454,可谓一语中的。又如《孝心宝卷》,写的是孝子钱聚万割肝孝亲的故事,故事委婉曲折,生动感人,故而清人孙德真序《孝心宝卷》云:“孔君庆华持《孝心卷》示余,谓当翻刻行世。余披阅之。乃叙水渠孝子钱聚万颠末,其事为人所共知,其行为人所难及,前人取其实迹,编作白话,不明文义者,听之亦能了然于心,诚劝孝之善本也。”[21]527张颔曾指出:“‘宝卷’中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它是一种通俗的韵文,是一种讲唱文学,广大群众乐于接受,即便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念起‘卷’来无论十几岁的孩子或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会四座无言洗耳静听。我们小时候也曾听过‘念卷’,并且为‘宝卷’中的故事感动得流过眼泪。”[22]或许正是因为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宝卷赢得了底层民众的青睐。
从文本的角度看,不论是作者、受众对象还是表达方式等,清代宝卷与善书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界线;从史料上看,终清一代,清人基本上没有把宝卷纳入善书的范畴。可知,在清代,宝卷与善书即使都已世俗化与儒学化,二者之间还是没有多少交集,是彼此相对独立的文本。
三、清代宝卷与善书社会功能之比较
如前所述,在清代及以前,宝卷和善书之间的区别可以从多方面呈现出来;当然,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本,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有迹可循。不过,如果只是从源头上探讨宝卷与善书之间的联系,倘若没有足够的史料来加以佐证,所推演出来的结论恐怕很难令人信服。笔者以为,如果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考察二者之间的联系,或许更容易找到彼此间的契合点。实际上,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探讨宝卷和善书已然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重要发展趋势。
善书的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宝卷具有和善书一样的劝善功能。比如,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曾指出:“这些宝卷,从其在世间流行的历史性、社会性意义以及针对民众进行宣教与劝戒的内容来看,不仅具有与善书共同的社会意义,而且还包含了与善书中相同的庶民文化的重要要素。”[6]445不仅如此,在《中国善书研究》中,酒井忠夫还把宝卷列入善书的范畴,特意安排了两个章节(分别是上卷第七章、下卷第八章)进行研究。在《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中,游子安明确把宝卷纳入善书的范畴[3]19。
同样,宝卷的研究者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审视,认为宝卷确实足以比肩善书。比如,车锡伦在对比宣卷演唱的宝卷和宣讲的善书时,特别强调二者都是以“劝善”为宗旨的文本[15]559。陆永峰则认为:“差不多每一部宝卷,无论是佛教的,还是民间教派的,或世俗的,都会在卷中劝人行善修道,宣扬其教化主题。这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宝卷的常态与习惯。”[23]尚丽新强调:“宝卷含有极强的劝善思想,教化是其本质之一,也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24]103显然,宝卷和善书一样都具有较强的劝善功能,这已然成为学界的共识。
其实,早在清代,一些比较开明的士绅就已经意识到了宝卷中的劝善功能且有意加以倡导。比如,清王学仁序《孝心宝卷》云:“晚近风俗颓靡,人心浇漓,而于孝行尤薄,彼孝子虽未合圣贤守身事亲之道,而一片诚心,彼苍可格,洵难及也。予遂告诸里中善士,各出小资刊刻传送,公诸同好,俾阅之者,无论农工商贾,由是而皆知罔极之恩,所当竭力善恶之报,”[21]526又,自傭子《重刻孝心宝卷跋》云:“盖百善莫先于孝,一切劝善果报实录,胥以孝列首简,今是卷,文言道俗,确见孝子一念之诚,德无量而功可证。”[21]555在《孝心宝卷》中,钱聚万割肝孝亲的故事,原本惊天地泣鬼神,感人至深,然而,对于序跋者而言,他们关注的并非钱聚万感人的故事情节,而是不约而同地强调其中的孝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钱聚万实有其人,甚至是序者王学仁隔壁邻村之人,事迹班班可考,真人真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在当时风俗颓靡、人心浇漓的社会情境下,《孝心宝卷》实在是“劝孝之善本”[17]527。序跋者正是因为看中了《孝心宝卷》中劝善功能,才有意识地在序言中不遗余力地推广,以引导世人孝亲向善。
又如,《佛说金钱钥匙宝卷》序云:“凡妇人之能晓大体大礼者,十无一焉。有过而能速改者,亦十无一焉。大抵文过者多,故直言规诫,有时难以入心也。惟投其所好以悦之,假往事以讽之,似乎听也者。夫婢女虽属浅近,而烦琐亦难中听,宝卷之简捷俗便,易入妇人之耳矣。至其粗不文,难入识者之目,而讽刺规箴之深意,则有不可不传者,故钞之念之,使有心者听之,快孰甚焉。”(3)转引自于红:《明清时期晋商妇女的精神家园——评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晋图学刊》2011年第3期。不难看出,该序者原本打心底里瞧不起宝卷,认为其粗俗不堪、难以入目,但由于宝卷为妇人所好,且宝卷中含有讽刺规箴等劝善之深意,在宝卷宣讲的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教化和影响妇人,宝卷才得到了其认可。
尽管清人已经意识到了宝卷是以劝善为宗旨的文本,却始终未把宝卷纳入善书的范畴。笔者以为,关键原因在于,清代统治者把宝卷定性为“邪经”,亦即在清代社会,宝卷和善书完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文本,宝卷一直不被上层社会认可。有此污名,在清代的社会情境下,尽管宝卷蕴含有较强的劝善功能,也根本不可能改变其被歧视的状态。
四、结语
综上,清代宝卷和善书之间,不管是源流、编撰者的身份、受众对象,还是叙述方式以及清人对二者之间的态度等,彼此都相距甚远。不过,如果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进行审视,二者都是以劝善为宗旨的文本,彼此之间确实同向而行。宝卷的研究者们把宝卷和善书进行对比研究,且有意识地强化它们二者之间的同质性,尽管他们的研究方式值得商榷,但是,研究意图却很有意义。笔者以为,宝卷的研究者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宝卷具有和善书一样的社会功能,而宝卷却一直被“污名化”。作为宝卷的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说,难免会因此存有一种为宝卷鸣不平的心理,以及生发一种力图冲破二者界线以便提升宝卷地位的潜在意识。与此同时,清代的社会情境已不复存在,从社会功能的角度强化二者之间的联系也就成为可能,也更容易得到学界的认可与支持。如此,不仅有利于拓展善书的研究范畴,也有利于客观公允地看待宝卷在清代民间社会起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