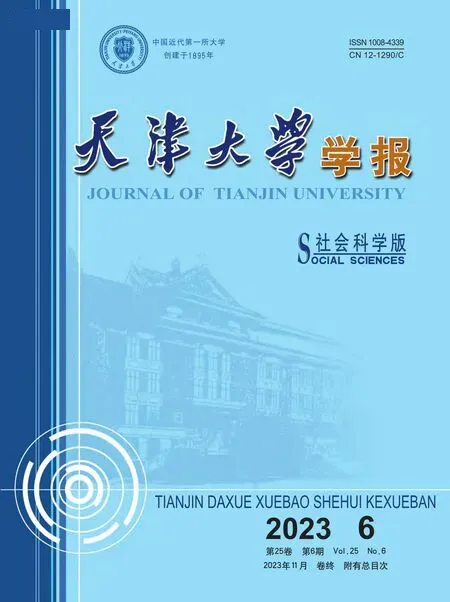柯莱特的“摩登金发”及其反种族主义内蕴
2023-03-10高飞
高 飞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20世纪初,柯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1873—1954)以细腻入微的文字和不受拘束的女性思想征服了法国文坛,但其对自身典型白人外貌的自豪,特别是在维希政府控制的反犹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行为,引发了种族主义批评。布鲁克·艾伦(Brooke Allen)[1]称柯莱特以平静的心态选择与最恶毒的期刊合作,足以表明她的种族态度与纳粹一致。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为其发声。赫伯特·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2]指出柯莱特所发内容不含任何恶意中伤或诽谤性言辞。伊丽莎白·布鲁纳兹(Elizabeth Brunazzi)[3]则认为是知名作家的头衔将柯莱特的“非政治”文本置于媒介宣传机构营造的高压政治环境中。对此,皮埃尔·R·勒克莱尔(Pierre-Robert Leclerq)[4]辩称,创作内容与政治时事分离意味着爱国情怀的缺失,柯莱特的种族态度便不言而喻了。然而笔者认为,正是柯莱特勾画的鸟语花香与锦衣玉食、随处可见的摩登女郎与英俊绅士,诸如此类远离战争硝烟的文字承载了其爱国主义精神。其中,金发书写就可以有力推翻那些只依据事件表象而草率为其种族倾向定论的不公正判断。从表面上看,热衷描写“摩登金发”似乎为其种族主义批评提供一种口实,因金发不仅代表着20世纪初的时尚,也暗含了种族主义色彩——希特勒鼓吹种族理论,昭告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雅利安人为最优人种。但柯莱特的“摩登金发”领异标新,不仅体现出个人对时代的反馈,并且在文本中发挥着颠覆性功能。本文通过对柯莱特的“摩登金发”系统深入地研究,以期寻绎它纷繁出现于作品中的复杂缘由,解析作家是如何借金发书写诠释出反种族主义的内蕴。
一、 摩登金发与混血身份
20世纪伊始,诸多领域相继掀起金发热潮,尤其是银幕中的金发女郎形象,引领了新世纪时尚。柯莱特作品中的金发主角颇多,貌似顺应了这股“摩登金发”潮流。加之其淡化自身黑人血统及当时歧视黑人的社会舆论,不免让人对其种族态度产生怀疑。但经过对柯莱特家族血统的考证和对其作品中黑人书写的分析可以明确,作家并非种族歧视者。
1. 金发热潮与金发书写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5]认为,19世纪浪漫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对庸常现实的否弃和对神秘远方的向往。我们从中发现,具有东方深发特征的女子通常被神话、高贵化为正面形象,而美丽性感的金发女郎却多为深发女主角的陪衬,或成为反派的代表[6]。如《基督山伯爵》中的黑发美人梅赛苔丝与金发女郎埃米娜的对比,前者为传统部落族裔,是贤妻良母的典型,在男性心中分量极高;后者出身巴黎显赫世家,却是一个不忠的妻子和失职的母亲,为男人发迹的工具。再如《交际花盛衰记》中,巴尔扎克将黑发犹太女主角塑造为忠贞无二的美好人物,而将接受良好教育的金发女郎边缘化为虚荣拜金、性情冲动的无名角色。20世纪初,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人类视野的开阔使异域情调的吸引力降低。此时美国电影业的蓬勃发展加强了时尚传播的速度与广度,好莱坞金发女郎的经典形象标榜着时代的审美潮流和时尚趋势。与之对应的文学创作也逆转了19世纪的文学主流,可以看到纪德、蒙泰朗等作家在作品中对金发之美大加赞誉,埃梅在《变貌记》中也高度赞扬了金发女秘书的机智勇敢,讽刺了黑发妇人出轨的可耻行为。
金发重新占领市场与20世纪帝国主义的强盛和西方中心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希特勒维护政治色彩浓烈的“种族纯洁”,金发碧眼则被愚蠢地认定为是衡量基因优劣最简单、直观的标志。这种通过颜色反差辨识人种贵贱的伪科学理论,同样使美国黑人遭受精神奴役之痛。莫里森的小说《最蓝的眼睛》再现了1941年前后贫苦黑人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转向白人普世价值观的悲哀情境,展现出帝国主义实行身体政治的恶果。书中的黑人女孩皮科拉将拥有白皮肤蓝眼睛视为改变厄运的希望;在其种族内部,肤色、发色相对较浅的黑人自认为优于深色同胞。这也解释了为何现实社会中存在一定比例深发色和深虹膜的白人,却将金发碧眼默认为白人的种族特性——因为金发碧眼通常与黄黑人种“绝缘”,并且颜色越浅差异越明显,乃至时至今日都洗脱不掉它的种族主义烙印。2017年12月,美国《信封》(The Envelope)杂志封面一组集聚六位金发女星的照片遭到网民质疑,指责统一的白人合照触犯了种族多元化大忌;一些媒体也常常聚焦英国王室成员的蓝眼睛和发色来做文章。
在柯莱特的写作中,金发人物具有高频性和高光性。不仅成名作《谢里宝贝》(Chéri,1920)中的蕾雅是金发、处女作《克劳汀在学校》(Claudine à l’école,1900)和风靡全球的电影同名小说《吉吉》(Gigi,1944)①的女主人公是金发、代表作《白日的诞生》(La Naissance du jour,1928)中年轻本分女子克莱芒也是金发,甚至一些配角及散文的中心人物都留着一头美丽的金发,并且多伴随着碧眼,常与褒义的视觉审美词汇搭配使用。柯莱特遗传了父母的金色系头发,在写作初期就彰显出金发的魅惑,这与其本人的主观审美相得益彰,也是社会客观现实的重现。自传性质小说《流浪女伶》(La Vagabonde,1910)中写道:“雅丹是个初入乐坛的小歌女,以至于还来不及用双氧水把她那棕栗色的头发洗淡。”[7]文中的画家把棕发饰以红里透金的光泽,把栗色的头发调到金黄的极限[7]26,极富戏剧性地揭露出20世纪初法国社会对金发时尚的狂热追捧,以及金发在两性间挥洒的魔力。
2. 血统之辩与黑人书写的复杂内涵
虽然柯莱特有着白色皮肤、金栗色头发和灰绿色眼眸,并且符合标准白人的五官和身材特征,但体内却流淌着其黑人祖先的血液。柯莱特公开承认其外祖父有1/4的黑人血统[1]。但有学者认为柯莱特故意将自身的黑人基因降低到1/16,以向纯正的法兰西人靠拢。艾伦就引用柯莱特女友娜塔丽·巴尼(Natalie Barney)戏虐年迈的作家重返舞台,描述其衰老容颜时脱口而出的“1/8混血儿(octoroon)”[8]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但巴尼这句无需承担责任的非官方话语并不具备公信力。克劳德·弗朗西斯(Claude Francis)和费尔南德·贡蒂尔(Fernande Gontie)则撰写了一篇名为《柯莱特的家族》的文章作为柯莱特传记的首章,用官印文件证实了其曾外祖父是一位来自马提尼克岛的黑白混血大富商,洗刷了作家淡化自身黑人血统的不实之词。然而矛盾似乎不能就此轻易化解,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在接任柯莱特成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的演讲中,为作家远离20世纪主流文学思潮做出这样的言说:“柯莱特女士是白人,她无需粉饰。她和印象派一样厌恶黑色,却从未加入其中,也许是对他们的研究不感兴趣,她(的写作风格)是独一无二的。”[9]
正如此番话对柯莱特种族态度造成的影响,其作品中对金发的崇尚以及对黑人情欲的描写,也仿佛为其歧视黑人增添了不利证据,但仅以此断定作家的种族倾向是否有所牵强?《谢里宝贝》中,金发的蕾雅把她理想的性伴侣假想为黑人[10];《母猫》(La Chatte,1933)中,金发的男主人公把性欲旺盛的女主人公当作黑人[11]。可见,柯莱特并不是蔑视黑人,其对黑人的书写不过是限于想象。约翰·P·拉什顿(Jhon Philippe Rushton)致力于种族研究,他认为黑人的相貌体征具有与热带生活相适应的诸多特点,其性活动或许相对其他种族更为频繁活跃[12]。由此可以推断,柯莱特的黑人书写可视为人类原初生命活力的体现,在某种程度上,点燃了现代性社会中人类的激情,根本不存在对黑人的诋毁。况且在柯莱特生活的法兰西学院时代,女性写作的道路本身就比男性作家艰难坎坷,柯莱特势必要对敏感问题把握好尺度。
二、 柯莱特是种族主义者吗?
1940年法国被纳粹德国占领,维希政府成为纳粹德国的傀儡。以艾伦为代表的学者对柯莱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为其扣上亲德反犹的帽子,不接受那些以“被动合作”为由的辩护。布鲁纳兹及其项目团队经过研究认为,相比有名望的男性合作主义作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有杰出女性作家存在通敌行为[3],并为柯莱特的被动合作做出精神分析,即延续了早年埋没自我,为第一任丈夫威利充当笔手的习惯[3]。可是这些只能说明柯莱特不存在与德军勾结的可能,没有对实质性问题进行有效回应。为了验证柯莱特的消极抗战,有人搬出其独生女不顾个人安危参加抵抗运动的事例以示不满[1]。而柯莱特与轴心国意大利首脑墨索里尼情妇玛格丽塔·萨尔法蒂(Margherita Sarfatti)“始于一战前的亲密友谊”[13],更令其陷入舆论漩涡——萨尔法蒂的经济资助和政治谋策,助攻了墨索里尼走向权力顶峰[14]。然而,以诸如此类不完整的陈述作为柯莱特政治和种族倾向的判定是失之偏颇的。要对具体事件及其前因后果进行剖析,且对柯莱特的生活境遇、人生理念进行考察,并通过还原“摩登金发”的社会语境,判断作家是否有亲德的政治思想和种族主义意象。
首先,1929年底欧美经济大萧条使柯莱特当时的伴侣莫里斯·古德凯(Maurice Goudeket)②的珠宝生意严重亏损,整个家庭重担落到作家一人肩上。与大资产阶级出身的普鲁斯特和书香门第的纪德不同,柯莱特家族并无能力为其提供援助,所以她不能心无杂念、无所顾忌地投身文学事业。1932年进军美容业的失败迫使近60岁的柯莱特重登舞台。1941年,德国纳粹为实现其在法国的文化霸权,仅在上半年就恢复出版并首发创办了数十份周报[3],并高薪邀请包含柯莱特在内的知名作家定期为其供稿。在丰厚稿酬的吸引下,不乏有影响力的法兰西学院和龚古尔学院要员与之“合作”。相比之下,柯莱特对报刊的贡献微不足道。生活所迫的柯莱特未能用行动支持女儿革命的一幕,真实映射出文学创作者委身于现实的无奈。
其次,柯莱特的第三任丈夫古德凯是一位犹太商人,在1941年底盖世太保授权的“知名人士围捕”行动中被捕[15]。柯莱特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也未曾与任何党派结盟,只得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用尽所有资源疏通关系,历经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才把丈夫从集中营解救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柯莱特对犹太人持接纳态度,并非有种族偏见。丈夫被囚禁的遭遇更是激发了柯莱特的人道主义情怀,她绝不可能对纳粹心怀同情或感激。如果柯莱特走合作主义道路,定会与古德凯保持距离,但丈夫重获自由后,二人携手度过了余生。选择在贝当主义刊物刊登文章其实是对丈夫变相的保护,在作品中将“摩登金发”伪装成种族色彩也是维护家庭完整的手段。毕竟这场浩劫使法国超过25%的犹太人失去生命。
再次,柯莱特的金发书写贯穿了其整个写作生涯,是她所擅长的时尚书写领域的一个分支。费里埃·卡维里维耶尔(Nicole Ferrier-Caverivière)[16]指出,柯莱特的作品通过时尚的纽带建立起与时代沟通的桥梁,实现与其所处社会的对话。其发表于时尚杂志的文章《首饰盒》(Le coffret à bijoux,1922)直言不讳地举证了不合时宜的时尚、过度利用时尚修饰功能的反作用;小说《谢里宝贝》则演绎出时尚自上流社会逐级推广到平民阶层的滴流效应,并渗透出对盲目追求时尚的否定。柯莱特用诙谐的言语抗击时尚的无序传播,笔锋深层指向集权者通过控制文化领导权以达政治和经济垄断的劣行[17],显然与德军的主导理念背道而驰。并且好友萨尔法蒂最终放弃了法西斯主义,柯莱特以包容的态度顶着纳粹的压力大胆迎接这位犹太女性流亡到法国。可以说柯莱特的社交网络单纯连接着女性间的情谊,突破了政治和种族的隔阂。
从次,柯莱特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授予国葬的女性。其对天主教的不敬,导致法国教会拒绝为其举行宗教葬礼。的确,柯莱特向来不受宗教礼数约束,离婚等离经叛道的行为无疑是对天主教的漠视。就无神论者柯莱特看来:“一切形而上学的理论和宗教的教条就本质而言都是可疑的,因为用有限的术语来阐释无限和不可全知的现实是不完善的。”[18]小说家马塞尔·茹昂多(Marcel Jouhandeau)的反犹主义就被认为可能与他保守的天主教背景相关[19]。因此,如果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分析,柯莱特不存在反犹动机。此外,柯莱特断然排斥激进主义思想,把爱国热情寄于微小而务实之事,其作品偏爱捕捉动乱时期人类的生存技能,从而带给黎民百姓生活的动力。这也是柯莱特笔下频繁出现精致、坚强女性的原因。
最后,柯莱特的母亲一生都是查尔斯·傅立叶哲学的信徒,这位无宗教信仰的母亲为柯莱特精神世界的建造奠定了基础。通过弗朗西斯和贡蒂尔对傅立叶主义的深度解读,可以对柯莱特文本中的政治和种族疑问一一作答。首先,柯莱特对黑人保留的性激情示意隐含了深刻意义。因为在傅立叶构造的乌托邦中,社会的不和谐源于被基督教压抑的激情和性,压抑使人类迸发出病态乃至犯罪[20]。这便是柯莱特文本中毫无掩饰的性心理描写的根源,并非一些评论家口中与世隔绝的闺房文学。再有,傅立叶以爱为核心构建了一个相互吸引并旨在促进健康、富裕、和平的社会体系[20]16。故此,在柯莱特的作品里几乎看不到阴谋与功利、战火与伤病、贫穷与低贱,却可以从事物的精心绘制与人类的细腻情感中呈现出社会的焦点。此外,傅立叶认为个人价值决定了个人地位,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是由性别或种族决定的,而是由个体差异决定的[20]17,这与希特勒奉行的种族理论是绝对相悖的。
三、 柯莱特作品中的反种族主义内蕴
从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谁不通敌?》一文中可以总结出部分法国知识分子在二战期间接受纳粹的几个主观原因:对犹太人的仇恨比对德国人的仇恨还要强烈;对共和派痛恨至极而渴望重建罗马天主教的权威;对政府无能、军队败落的国家失去信心[19]。柯莱特显然不在其中,另有皮埃尔·埃贝(Pierre Hebey)[21]认为,无论出版的方式或途径如何,这些被定义为合作主义者的文字可以在法国沦陷期间带给国民阅读乐趣,使沮丧之人得到鼓舞。不过,一旦脱离社会语境很难慷慨地对柯莱特敞开胸怀,尤其不能容忍“柯莱特与纳粹宣传员的文章在《镜报》(La Gerbe)上一起发表”[3],以及“小说《朱莉·德·卡内汉》(Julie de Carneilhan,1941)在法亚德(Fayard)出版时封底印有的希特勒著作宣传广告”[2]255。那么如果要进一步解除柯莱特背负的种族主义嫌疑,就务必返回文本内部。但柯莱特的作品大都以爱情为主题,鲜有涉及社会事实,更没有直接阐述政治观点,所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回到问题原点对金发人物进行归纳与解构,从而可以发现“摩登金发”的反讽效应,领悟到柯莱特对种族主义坚定不移的批判态度。
1. 面容消解因子
据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记载:“纳粹教师通过观察学生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测量头骨大小和鼻子长度,确定学生是否属于真正的雅利安人。”[22]柯莱特的“摩登金发”就是以细节制胜,为之搭配了与雅利安属性不和谐的面孔,有效消弭了金发的种族主义象征。小说《纯与不纯》(Le Pur et l’Impur,1941)的开场人物夏洛特是一位美丽的金发碧眼女郎,但在这标准的“雅利安颜色”下,柯莱特为她安置了一个违背纳粹严苛要求的鼻子:“短鼻子和肉嘟嘟的脸酷似雷诺阿最喜欢的模特”[23],“昏暗的灯光显示出她漂亮的短鼻子下面略微肥胖的下巴”[23]35等。并且在非异性爱恋遭受纳粹排挤和迫害的时期,柯莱特坚持出版这部带有萨福主义色彩的小说,足以视为其对维希政府的挑衅。另一部在二战期间连载于政治类报纸的小说《吉吉》,女主人公同样拥有淡黄色的头发和纯蓝的眼眸,但其长辈们不谋而合地惊叹她反祖式的塌鼻梁和短下巴,而这种俏皮可爱却俘获了实业家加斯东朝三暮四的心,吉吉因此收获了令人嫉羡的婚姻。值得注意的是,柯莱特很早就开始了对金发女郎的面容解构。1913年的《锁链》(L’Entrave)中,柯莱特创造了类似的人物枚,“一个生有洁净白皙皮肤的二十五岁的金发女郎,她长着一双印度式的、眼白很少的褐色大眼睛”[24]。如此,东方的五官消融了金黄发色所代表的西方相貌特征。而在《锁链》的前传《流浪女伶》中,作家悄无声息地运用宇宙奇妙的变幻来消解永恒的不变:“我只是在晚上见过您,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您会长着一对灰眼睛……您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这双眼睛看起来好像是棕色的。”[7]74幕前与幕后、黑夜与白昼分裂出真实与虚幻的两种色彩,时空的转换缩小着种族间的差异。在《谢里宝贝》的续书《谢里的结局》(La fin de Chéri,1926)中,柯莱特则以时间为终结让蕾雅一头卷曲的金发变成满头白发。
2. 行为消解因子
柯莱特对女性美貌的痴迷与审视不经意间联动着种族冲突,但也正是由于局部和微观上对面部细节的“挑剔”,使他人口中的柯莱特的种族主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解。相对于外貌的客观性,人物的主动性行为成为进一步消解种族主义的“武器”。散文集《葡萄卷须》(Les Vrilles de la vigne,1908)中有三篇文章都围绕叙事者的女性朋友瓦朗蒂娜展开。柯莱特这么描述她的外貌:“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人的头发像她这样金黄,皮肤像她这样白,像她这样打扮!她的头发,她的真头发跟别人的不同之处就是那颜色是介乎银白和金黄之间”[25],并且身材高挑。但在形容瓦朗蒂娜整体性行为时,柯莱特却给出了这样的综合评价:“她一点也没有瑞典金发的那种怪模怪样”[25]589。可以看到,在纳粹种族政策正式出台之前,柯莱特就不吝笔墨书写金发,但仅限于对美丽色彩的肯定。虽然文中没有详细解说瑞典金发女郎的怪异举止,但北欧人大都符合希特勒对雅利安人外貌的定义,流露出柯莱特对“雅利安人为优等人种”的质疑。短文《模仿游戏》(Jeux de miroirs,1924)中,柯莱特更是把对金发尤物的嘲讽升华到极致:“她的动作并没有为她增色。她像狗一样向前耷着下巴,像一只从水里出来的小海豹一样皱起鼻子。”[26]而当金发女子成功被陌生男子搭讪后,旁边动作优雅的棕发女子即刻“自行检讨”并模仿起金发女子愚蠢的表情及动作,无形中透露出作家对“摩登金发”背后审美意识形态的否定,以及对当权者营造病态审美的暗讽和谴责。于是在小说《雨月》(La Lune de pluie,1940)中,柯莱特将金发与黑发融入一个血缘。柯莱特剥夺了金发碧眼的姐姐的自信与魅力,让她成为一个相貌平庸、墨守陈规的老姑娘,而赋予黑发妹妹独特的处事风格和神秘的行为方式,使之成为焦点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种族间的二元对立,传递出种族融合的意象。
3. 心理消解因子
我们通过把分布在独立作品中金发人物的特质聚集起来,从面容和行为层面归纳出柯莱特笔下的金发群体五官特征异于标准雅利安人,行为表现落败于深发群体的共性。相对从个体中寻求共性,柯莱特更善于用个体来反映整体现象,其资深研究者唐娜·M·诺雷尔(Donna Marion Norell)就此解释道,“她想要窥视的整体是无精确限制的,不可胜言的,很难形成终极统一,只能反映在对个体的窥见中。”[18]鉴于此,探究单独作品中的金发个体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可以从最核心的心理层面消解金发所象征的由多重富贵阶层组成的繁杂社会整体。小说《朱莉·德·卡内汉》的同名女主人公朱莉和她的哥哥一样,继承了家族式的金发碧眼及完美的收紧式鼻孔。她出身名门但家道中落,却时刻以自己尊贵的姓氏为荣,看不起丈夫“穿袍贵族”的“新”头衔,离婚后,即使生活窘困仍坚守贵族生活方式,为此饱受身体和心理的摧残。柯莱特通过对朱莉一人扭曲心态的书写,辐射出对这一自视清高阶层的鄙夷。小说《母猫》则运用心理书写揭示出金发碧眼的丈夫对黑发黑眼的妻子所隐喻的不同种族和劳动阶层的歧视,形象地刻画出金发所象征的上流阶层对现代生活的不适,进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对母猫的疼爱和依恋远胜过妻子,并因排斥妻子而离婚。这种心理是丈夫惧怕被妻子超越、被社会淘汰的本能反应,归根结底是传统资产阶级顽固守旧、荒谬僵化的思维方式所致,暗示传统资产阶级如不醒悟最终将走向自我毁灭,这也从根本上瓦解了柯莱特写作中“摩登金发”的种族主义表征。而且,《母猫》的出版正值纳粹德国(1933—1945年)时期,柯莱特对徒有其表的金发碧眼进行赞美的糖衣下,埋藏着对种族神圣化的“轰炸”。按照时间线索回顾柯莱特作品的创作年代,不难发现其早期作品没有刻意强调金发与碧眼的结合,而20世纪30年代后的金发书写往往连带着碧眼,正中那些“合作期刊”所需,但作家的解构却随之渐入到心理的核心层面,使之内蕴更为明晰。
四、 结 语
柯莱特用时尚的笔锋、借助金发书写为我们营造了一个避开20世纪上半叶战火纷飞、看似歌舞升平的幻象,恰是这种非政治主题文本体现了其对当时高压政治环境的漠然。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虚拟写作中,柯莱特始终被花园、美食及时尚包围,充分展现了法式生活方式,故而形成法兰西民族在文化品位上对入侵者的抵抗,有助于民族自豪感和国民士气的重振。难能可贵的是,柯莱特能以这种不同寻常的表述方式揭示社会现况。实际上,也正如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女性天才3:柯莱特》里论述的那样,比起让老弱妇孺一起参与抵抗,柯莱特认为应该把自我保护放在首位,这也是法国人生性好客,总是以防御性的方式来应对周围变化的原因[27]。事实证明,经济的压力和犹太人家属的身份使柯莱特不能与当时政府公开为敌,但其人道主义和反极权主义思想表露出其对法西斯和纳粹的憎恨,而她的宗教观和哲学观更不可能令其成为种族主义者。可见,面对国仇家恨,柯莱特借用“摩登金发”洋溢的貌似种族主义的表象,隐藏自己没有实力直接表明的政治立场和种族态度,以顺利通过刊物的审查。但柯莱特利用精湛的写作手法巧妙地传递出反种族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其金发书写中体现得尤为深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