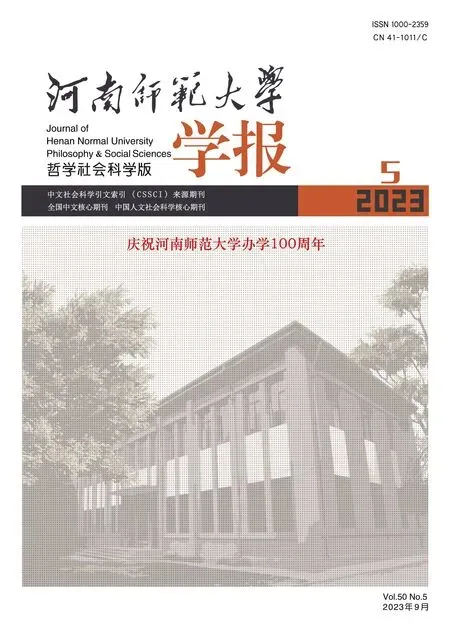第二人称叙事中的受述者
2023-03-09谭君强
谭 君 强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在叙事学研究中,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与受述者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二者相互关联,不可或缺。然而,与对应的叙述者相比,受述者所受到的关注与研究要少得多,至于第二人称叙事中的受述者问题,则更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实际上,相关问题在叙述交流研究的实践中虽然不是一个常常遇到的问题,但它们在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由其所辐射的一系列概念和有关问题涉及叙事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受述者及诸形态
叙事文本中的受述者(narratee)概念最早由普林斯提出(1)Gerald Prince.Notes towards a Preliminary Categorization of Fictional “Narratees” .Genre,4 (1971).。在叙事文本的叙述交流过程中,受述者是相对于叙述者而言的,它是叙述者讲述的接受者,也就是叙述者信息发送的对象。按照普林斯所言,在任何叙事文本中,“至少有一个(或多或少公开地表现出来的)受述者,处于叙述者向他或她讲述的同一叙事层次上”(2)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Revised Edi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p.57.。在叙事文本中,可以只有一个受述者,接受一个叙述者的讲述。但是,也可能出现几个不同的受述者,接受同一个叙述者或不同的叙述者的讲述(3)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Revised Edi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p.57.。在叙述交流的实践中,受述者既可以表现为“叙述者说话所面对的一个群体,也可以表现为单独的个体”(4)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页。。迄今为止,它已成为叙述交流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诸要素之一。
在叙事文本中,受述者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概而言之,受述者可以作为无声的叙述接受者,倾听叙述者的讲述;可以作为人格化的受述者,也就是作为一个具体人物,接受叙述者的讲述。受述者可以置身于故事之外,以不参与故事的故事外受述者呈现;也可以置身于故事之内,作为一个人物化的受述者,即受述者—人物活动于故事之中,既倾听叙述者的讲述,又作为一个人物而行动,与同一叙述层次的其他人物产生交流,如鲁迅小说《在酒楼上》接受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讲述、并作为受述者—人物与“我”产生互动的吕纬甫那样(5)谭君强:《从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看叙事本文的交流模式》,《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一般情况下,“受述者越被人物化,这一受述者在修辞交流中就越重要”(6)James Phelan.Somebody Telling Somebody Else:A Rhetorical Poetics of Narrative.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7.。受述者还可能被置于读者的地位,或者说与读者相耦合,接受作为作者的叙述者的讲述,如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叙述者常常直呼的“看官”“阅者”那样。有时,叙述者甚至可以直接面对作为受述者的读者,描述、推测其阅读故事之后所产生的反应,如巴尔扎克《高老头》开头部分所展现的那样:
你们读者大概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埋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想道:也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消遣一下。读完了高老头隐秘的痛史以后,你依旧胃口很好的用晚餐,把你的无动于衷推给作者负责,说作者夸张,渲染过分。殊不知这惨剧既非杜撰,亦非小说。一切都是真情实事,真实到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或心里发现剧中的要素。(7)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页。
上面所提及的均为叙事文本中所呈现的受述者。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建立在口头艺术基础上的、以表演或演示为中心的叙述交流中的受述者,因为“表演在本质上可被视为和界定为一种交流的方式”(8)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在表演和演示性的叙述交流场合中,受述者往往可以直接与读者(听众、观众)相认同,比如,在宋元以来说书人的故事讲述中,出现在勾栏瓦舍中的这些说话人,在说话的现场与其听众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就属于这样一种叙述交流状态。西方早期口耳相传的史诗朗诵或行吟诗人吟唱等场合,情况也大抵如此。与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同,它属于真实作者与作为受述者的真实读者(听众、观众)之间的直接交流与互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表演和演示对于表演者和读者(观众)都同样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说,作为一种语言交流的模式,表演存在于表演者对观众承担展示自己交流能力的责任,而从观众的角度来说,“表演者的表述行为由此成为品评的对象”,并引起“观众对表述行为和表演者予以特别强烈的关注”(9)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读者或观众的受述者与表演者(讲述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显得更为直接,其相互之间的互动显得更为强烈。
可以说,在叙事文本内外所包括的所有叙述交流场合中,都存在着相应的受述者,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和显现的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在虚构叙事的发展中,有一类叙事,即第二人称叙事,其叙述交流显得十分独特。但是,在这类叙事文本中,也同样存在着相应的受述者,此类受述者在叙述交流的过程中如何呈现及如何起作用,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二、第二人称叙事的叙述状况
第二人称叙事,即所谓“你—叙事”(you-narratives)或“你—文本”(you-texts)。与通常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相比,它是一类在叙事作品中出现得最晚的叙事模式。在欧洲文学中,尽管第二人称“你”叙事在17世纪、甚至15世纪的作品中便可发现个别的例证,但作为一种新的策略,主要是以后现代叙事技巧的面貌,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出现在数量日增的叙事作品中(10)Monika Fludernik.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Routledge, 2009, p.113.。在中国的传统叙事作品中,第二人称“你”叙事难觅踪迹,这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形成及其导致的叙述状况密切相关。可以看出,在中国,叙事文本中的第二人称叙事主要也是后现代先锋叙事的产物(11)谭君强:《第二人称叙述者如何叙述:论小说的第二人称叙事》,《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无论采取何种叙事方式,从叙事文本本身来说,其存在都离不开叙述者的话语构建,与此同时,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接受其话语讲述的受述者,这在第二人称叙事中同样不例外。让我们首先从具体的叙事作品入手,看看其中所呈现的叙述状况。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1979年出版并引起广泛关注的长篇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第二人称叙事作品,其开篇是这样的:
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先放松一下,然后集中注意力。抛掉一切无关的想法,让周围的世界隐去。最好关上门,隔壁老开着电视。立即告诉他们:“不,我不要看电视!”大声点,否则他们听不见。“我在看书!不要打扰我!”也许那边噪音太大,他们没听见你的话,你再大点声,怒吼道:“我要开始看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了!”你要是不愿意说,也可以不说;但愿他们不来干扰你。
找个最舒适的姿态吧:坐着、仰着、蜷着或者躺着。仰卧、侧卧或者俯卧。坐在安乐椅上、长沙发上、摇椅上、躺椅上、睡椅上。躺在吊床上,如果你有吊床的话。(12)伊塔洛·卡尔维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页。
一部叙事作品的开篇是呈现其叙述交流状况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引领读者进入故事世界的门槛,作品所表现的故事讲述方式可以从开篇看出端倪,而且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确定整部作品的叙述框架,因而具有明显的引领性,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卡尔维诺自己也谈到了他对包括《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在内的小说开篇的关注:“小说的开篇就像开始进攻那样,觉得有必要充分展现自己的能量……我在考虑写一本由故事开篇构成的小说时,就是从这种考虑出发的,这就是我后来写成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13)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的开篇确实十分富于冲击力,而且如作者所说,“小说的开头最终成为小说内容”(14)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从这一开篇的文本段落中,不仅可以一窥小说的内容,而且可以把握作品基本的讲述方式。我们从这一开篇中至少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你”,一个将要开始阅读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的人,不是这部作品的故事叙述者,而是叙事文本中被讲述出来的一个作为读者的人物。
第二,开篇的段落中隐含着一个向“你”进行讲述的主体,这一主体即叙述主体,也就是叙述者。这位叙述者并未直接露面,但是,所有的叙述声音都出自这位未露面的叙述者。
第三,开篇所呈现的既不是讲述过去的事,也不是讲述未来的事,而是讲述与讲述的此刻同时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它显现的叙述状况是同时叙述或同步叙述。
第四,与同时叙述相应的是,在讲述中未露面的叙述主体与接受其讲述的人物“你”处于同一叙述层,这一叙述主体在故事层次上与“你”产生接触,并且与“你”互动,如向“你”提出种种建议等。因此,这一叙述主体实际上也同时是一位参与故事的人物,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位人物——叙述者。
第五,故事与话语层次相互重合。“你”阅读一部小说以及阅读时周围的环境这一发生在故事层次的事件,被叙述者同时以话语表达出来,本应只出现在话语层的叙述者同时在故事层出现,本应仅承担讲述功能的叙述者同时作为与“你”互动的行动中的人物出现在故事层,故事与话语层次的界线从而被消解。
作为对照,让我们再看看另一部第二人称叙事作品——严歌苓的小说《扶桑》,这是一部有关19世纪北美移民浪潮中一位名叫扶桑的中国女子命运的史诗性作品。下面是《扶桑》开篇的段落:
这就是你。
这个款款从喃呢的竹床上站起,穿猩红大缎的就是你了。缎袄上有十斤重的刺绣,绣得最密的部位坚硬冰冷,如铮铮盔甲。我这个距你一百二十年的后人对如此绣工只能发出毫无见识的惊叹。
再稍抬高一点下颏,把你的嘴唇带到这点有限的光线里。好了,这就很好。这样就给我看清了你的整个脸蛋。
来,转一转身。就像每一次在拍卖场那样转一转。你见惯了拍卖:像你这样美丽的娼妓是从拍卖中逐步认清自己的身价的。(15)严歌苓:《扶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
看得出来,与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开篇的叙事方式相比,严歌苓《扶桑》的叙事方式显得大同小异,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与之相似的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篇同样直接出现了一个“你”,一个在叙述主体面前逐渐呈现的“你”,一个作为人物出现的“你”。
第二,与卡尔维诺小说开篇隐含的叙述主体不同,这里明确地出现了叙述主体“我”,所有的叙述声音均出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
第三,开篇段落中讲述的是120年前的往事,也就是说,讲述的是过去的事,但与此同时,却以一种跨越时代的“穿越”方式,将120年前的人与事与讲述的此刻连接起来,穿过厚厚的时间屏幕,叙述主体在叙说的同时,可以触摸120年前的人物,并与之产生交流和互动。
第四,通过采用“穿越”的方式,叙述主体不仅以故事讲述者,即叙述者的身份呈现出来,也以和“你”处于在同一叙述层次上的人物的身份呈现出来。
第五,故事与话语层次相互重合。在这里,客观现实与主观经验的界线被打破,120年前一位“美丽的娼妓”出现在眼下的“我”面前,举手投足,交流互动。通常在话语层次上发生的叙述变形直接呈现在故事层次上,只应出现在话语层的叙述者“我”同时在故事层行动,本应仅承担讲述功能的叙述者“我”同时与时隔120年的“你”互动的行动的人物出现在故事层,两个层次相互重合。
在对《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和《扶桑》两部叙事作品开篇段落所呈现的叙述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和归纳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同样采用第二人称叙事的两部作品在叙述方式上具有多方面的共同性。这些共同性明显表现出后现代小说或先锋小说的种种特征。比如,就其中所显示的同时叙述或同步叙述来说,它显然与经典叙事理论界定的围绕故事世界已然发生和完成的事展开的那种标准的、规范的或原型的叙事完全不同,而展现出一种新的姿态。同步叙述(现在时叙事)与被叙述事件同时进行,预示式叙述(未来时叙事)则展开对言说时尚未发生之事的叙说,诸如此类的叙述方式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在像法国“新小说”这样的后现代叙事作品中日益盛行。卡尔维诺对后现代叙事中一位重要代表博尔赫斯十分推崇,在作品的时间表现上他深受博尔赫斯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的影响,他将博尔赫斯这篇小说在时间表现上的特征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准确时间的想法,即主观的绝对的现在;二、由意愿确定时间的想法,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消除不了的;三、多样化的、分出许多枝杈的时间的观点,任何现在都分成两个未来,从而形成一个相互分离、相互交叉又相互平行且不断扩大的时间网(16)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与博尔赫斯十分近似的时间表现。经典叙事理论界定的围绕已发生和完成的事展开的叙事,其生命力在于其“确定性和事实性”,带有某种封闭性的特征,指向某个明确的结局;后者则带有更多的开放性、未定性,其中,“被叙述世界是一个形成过程,在被叙述的过程中逐渐显现,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体”(17)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0-100页。。用卡尔维诺的话来说,今天的长篇小说,即他所说的“超级小说”,“其结构是累计式的、模数式的、组合式的”,而“我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便是我努力创作的这种小说之一”(18)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第二人称叙事中的受述者,通常不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叙述者信息接收者的面目出现,而大多作为受述者——人物“你”或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出现,这在后现代叙事中是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
三、第二人称叙事的受述者及其与叙述者的相互关系
从前面两部小说的开篇,以及此后小说情节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受述者不论是作为一位读者的受述者(以后这位作为主人公的读者的受述者“又分成两个人,男读者和女读者”(19)伊塔洛·卡尔维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还是作为一位“美丽的娼妓”的受述者,都是作品中的人物,并且是作品的主人公。这是第二人称叙事中一种普遍存在的叙述状况,可以说是此类叙事的典型特征。
这两位作为受述者的主人公,其身份是如何确定的呢?回答是他们都是被讲述出来的。马克·柯里谈道,个人身份并不在其自身之内,而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要解释个人的身份,就必须指明个人与他人的差异”,考察建构个人的差别体现,而我们解释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能表现我们特性的事件,并按叙事的形式原则将它们组织起来”,从而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20)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而解释自身,自然是一种再贴切不过的方式。因而,在叙事文本中,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讲述自身的故事既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常见的叙说方式,成功的作品不胜枚举。但是,这种讲述也可以通过他人来进行,第三人称叙事,即通过所谓全知或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来讲述某个或某些特定人物的故事,也是我们常见的方式。人称叙事的第三种方式,即现在谈到的第二人称叙事,我们可以从前面对《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扶桑》这两部叙事作品开篇段落的考察中看出,透过其十分富于细节的描述,同样可以感受到两个具有自身独特身份的人物。也就是说,第二人称叙事同样可以将作为受述者的人物身份明确地描述出来。但是,这两个人物是如何讲述出来的呢?作为受述者——人物“你”、他或她是自己讲述自己,或者说“你”讲述“你”,还是被他人讲述出来的呢?
可以明确地回答,作为叙事文本中的受述者——人物“你”,他们是不可能像第一人称叙事中的叙述者“我”自己讲述自己的,因为受述者在这里只是叙述者信息发送的对象,是叙述者发送的信息的接受者,尽管叙述者可能和作为人物的受述者相互交流、产生互动,它毕竟不能改变受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事文本中的地位和功能。换句话说,受述者不能成为叙述者。因此,两部作品中的受述者——人物“你”,都不是自己讲述自己,而是被讲述出来的,是由其中的叙述者讲述出来的。尤里·马戈林对三类不同的人称叙事作了这样的区分:“在叙述者让其自身成为叙述施动者的情况下,他们参与了第一人称叙事;如果他们的叙述接受者充当叙述施动者的话,就产生第二人称叙事。而当叙述者话语中所指涉的实体并非当下交流情境的一部分,则产生第三人称叙事。”(21)Uri Margolin.Narrator. In Pater Hühn, Jan Christoph Meister et al (eds).Handbook of Narratology,2nd edition.De Gruyter,2014,Vol.2,p.659.在这里,马戈林所谈到的第二人称叙事的界定颇成问题。按照马戈林的说法,如果叙述接受者(addressee)充当叙述施动者(narrative agent)的话,那么就是第二人称叙事。问题在于,叙述接受者可以充当叙述施动者吗?
我们知道,在叙述交流中,发送者(addresser)向接受者(addressee)发送信息,接受者接受发送者发送的信息。在叙事文本中,这种信息采用双方都熟悉的符码形式,从而实现叙述交流的过程(22)Roman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homas A. Sebeok, ed.Style in Laguage,MIT Press ,1974, p.356.。在这里,接受者实际上是受述者的另一个表述,乔国强在《叙述学词典》中将addresser译为“讲述者”,将addressee译为“听者”(23)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修订版),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7页。,与这种叙述交流的实际状况比较切合。而所谓叙述施动者,是叙述中的“动原”,这一“动原”出自叙述者。与此同时,叙述者不可能同时作为受述者出现,除非这一叙述者是在向自身发送信息,进行内心的自我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与受述者可以合为一体,相互重合。而在上述两部作品中,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两部作品中的受述者——人物“你”都是由文本中的叙述者讲述出来的,并非“你”的自我叙述。
更进一步,两部作品中的叙述者不仅讲述出作为人物的受述者“你”,而且与之处于同一叙述层次上,与作为受述者的人物产生交流。尤里·马戈林以叙事系统作为出发点,谈及不同的人称叙事的差别,认为其主要区别在于:在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也参与到被叙述的事件中”,而在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不参与”被叙述的事件中(24)Uri Margolin.Narrator. In Pater Hühn,Jan Christoph Meister et al (eds).Handbook of Narratology,2nd edition. De Gruyter, 2014, Vol. 2, p.659.。马戈林所论述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并无问题。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者确实不参与所讲述的事件,而处于所讲述的故事之上,外在于所讲述的故事之上的叙述层次。而第一人称叙事中的叙述者“我”则常常作为人物参与到被叙述的事件中。但是,马戈林认为第二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不参与”被叙述的事件,则与我们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和《扶桑》这两部叙事作品中所看到的叙述状况并不一致。实际上,在第二人称叙事中,叙述者可以参与到所讲述的故事中,与所讲述的故事处于同一层次,并与故事中的受述者——人物“你”产生交流与互动。在这种情况下,它既表现出话语层次的讲述功能,也表现出故事层次的行动功能。从上面引用《扶桑》开篇中的段落,尤其是其中下面一段,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再稍抬高一点下颏,把你的嘴唇带到这点有限的光线里。好了,这就很好。这样就给我看清了你的整个脸蛋”。从前面的句子“好了,这就很好”来看,这是受述者——人物“你”对叙述者“再稍抬高一点下颏”的要求有了回应之后,叙述者对她的首肯。在这里,叙述者明显与受述者——人物“你”处于同一故事层,并参与到被叙述的事件中,与“你”产生了交流与互动。
再回到《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这部小说是在实时讲述人物自己的故事,包括受述者——人物的故事,以此不断“解释个人的身份”。小说中的故事层与话语层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作品中主人公自我叙说的过程、作者创作的过程、作为读者的受述者“你”在阅读中产生反应的过程都融合在一起。比如,在提及作品中一个让人关注的人物——马尔内大夫的前妻时,出现了这样的叙说:
你作为读者,现在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到这位妇女身上了。其实你在几页书之前就已经在她的周围转悠了;我,不,作者也早就开始围着这个人物转悠了。你早就希望这个幽灵能像其他小说中的幽灵一样渐渐现出人形,正是你的这种期望促使作者向她靠拢,也促使我(虽然我心里另有烦恼)走向她,与她交谈。(25)伊塔洛·卡尔维诺:《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这显然是叙述者与作为受述者的读者在同一叙述层次上的交流沟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叙事系统来说,在叙事文本的实践中,只有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不参与被叙述的事件。而第二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也如上述两部小说所显示的那样,可以参与被叙述的事件中,形成某种同步叙述行为,叙述行为与被叙述的情境和事件同步发生(26)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Revised Edi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p.89.。在这种故事与话语层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叙述者与受述者也在这两个层次中交相出现。因此,“叙述者不参与”被叙述的事件,不能成为第二人称叙事的依据。普林斯将第二人称叙事定义为“在故事中被讲述的他或她作为主人公的受述者的叙事”(27)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Revised Editi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p.86.,这个定义应该更为合理,也符合我们所看到的叙事文本的实际状况。
概而言之,当我们谈到“你—叙事”时,不是指第二人称叙述者“你”所进行的叙事,而是叙述关于人物——受述者“你”的叙事;在谈到“你—文本”时,也不是指第二人称叙述者“你”所叙述的文本,而是叙述关于人物——受述者“你”的文本。用弗卢德尼克的话来说,第二人称叙事是“讲述受述者的故事”(28)Monika Fludernik.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Routledge,2009,p.31.的叙事。“讲述受述者的故事”,不能由受述者自身来讲述,只能由叙述者讲述。叙述者与受述者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只有存在叙述者时,受述者才得以存在,只有当叙述者发送信息时,才存在接受这一信息的受述者。在第二人称叙事中,受述者——人物“你”始终是被叙述者讲述出来的,它永远不可能是受述者——人物“你”自我讲述的产物。
抽象地谈论“我”和“你”,或“我们”“你们”,以及诸如“他”“她”“他们”,本身并无意义,并不能指明具体的说话语境。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叙述交流语境中,方可显示他们各自在叙述交流中的位置及其被赋予的意义。在任何叙述交流语境中,都有叙述交流的主体,也都有叙述交流的对象。只要一开口说话,那就是“我”。同理,在叙事作品的讲述中,无论以什么方式讲述,都是“我”在讲述,用巴尔的话来说:“‘我’和‘他’都是‘我’。”(29)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谭君强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页。巴尔在这里谈的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在第二人称的“你—叙事”中,也同样如此。在言语交流中,“只有当讲话是指向第二人称时,语言才能够履行其交流使命”(30)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谭君强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页。。在第二人称叙事的言语交流中,这一情况也不例外,在这里,不可能出现一个交流的主体“你”向另一个交流对象“你”进行交流,而同样只能是一个“我”在向“你”讲述和交流。“你—叙事”中的叙述者与受述者——人物的关系再次得到确定。
当然,与在其他人称叙事的叙述状况中出现的情况一样,在一部第二人称叙事的作品中,未必自始至终都严格地维持这一叙述状况不变,而往往可能出现不同叙述状态的转换,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中,这种情况更为常见。在《扶桑》对受述者——人物“你”的描述中,此类叙述状况转换的情况往往不时出现。比如,在扶桑第一次与一个12岁的白人男孩克里斯见面时,在扶桑再次被拍卖等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叙述转换。以扶桑再次被拍卖为例,我们读到了如下段落:
这天扶桑被阿妈拿到拍卖场上。在这个阿妈卖她之前,她被其他阿妈卖过两次。之前的三天,扶桑不再挨鞭子。阿妈告诉她,这是留给她时间把皮肉养平整。(31)严歌苓:《扶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8页。
这是典型的第三人称叙事,由一位外在于故事的无所不知的叙述者讲述。《扶桑》的基本叙述框架是第二人称叙事,但诸如此类的不同叙述方式有可能交替出现。这就表明,尽管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们会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诸如第二人称叙事这种新的、不同一般的叙事模式,但不会刻意在一部作品中从头至尾维持一种固定的叙述方式。通常的原则是,什么样的叙述方式有利于刻画人物、展现场景,就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相对于置身故事之外的叙述者讲述的第三人称叙事来说,以直接面对受述者——人物“你”讲述的第二人称叙事明显拉近了与人物的距离,即使是时隔百年的人物,也可超越时空,拉到面前,娓娓而谈,显现出更多的情感色彩,带有更强的亲和力、感染力。在更具视觉力量的影视艺术中,类似的叙说方式也屡见不鲜。但是,第二人称叙事也会出现直接面对时无法观察到的死角,因为它既不像第三人称叙事那样无所不知,也不像第一人称叙事那样有明确的“限知”,即将视角限制在“我”所可感知的范围内,因而,第二人称叙事中往往更为频繁地出现叙述转换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以上结合两部对有代表性的第二人称叙事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伴随后现代小说的兴起而频繁出现的第二人称叙事或“你—叙事”,其中的受述者“你”与第一人称叙事或第三人称叙事中的受述者一样,在叙事文本中不是叙述施动者,而是叙述者信息发送的对象。这一对象同时成为叙事文本中的人物,甚至作品的主人公。从根本上说,受述者“你”不可能讲述,而是接受讲述。作为人物的受述者“你”,可以与叙述者处于同一叙述层次上,产生交流与互动,并成为具有独特意义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