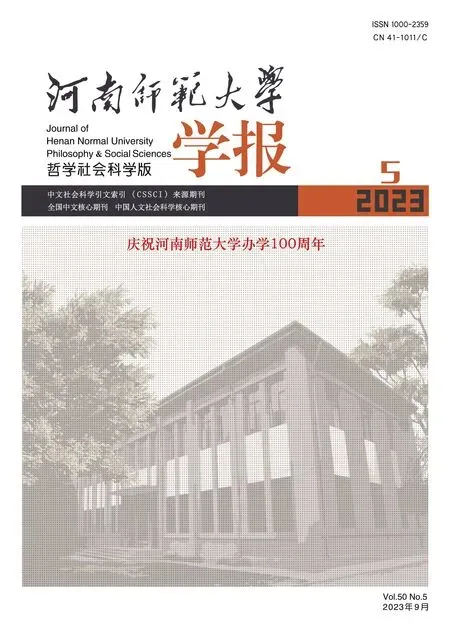近代报纸“附张”的时代价值
——基于《时报》与陈撷芬著译小说《人兽接脑记》的一次媒介考察
2023-03-09任春雨
刘 钊,任春雨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报刊的勃兴,除了数千种专门的文学期刊之外,由报纸所开办的文学副刊也发挥了重要的传播作用,有些副刊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正刊。“副刊”最初的名字叫做“附张”,以赠送的方式随报纸发行,国人自办的报纸“附张”始于《时报》。1904年,康有为、梁启超授意狄葆贤在国内创办《时报》。自1908年起,狄葆贤独立经营时报馆,并创办有正书局开展出版发行业务。除综合性报纸《时报》外,狄葆贤在辛亥革命前后陆续创办了《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等专门性杂志,在五四运动前夕又办《教育周刊》《妇女周刊》等系列“附张”,开创了中国报纸系列副刊的先河。作为《时报》附张之一,《妇女周刊》是国内综合性报纸创办的第一份妇女专刊,它通过刊载各种文体的文学作品以推崇女子教育、传播新的思想、普及科学知识、陶冶女性情操,等等,尤其是对张默君、陈撷芬、陈鸿璧等女权思想倡导者所著文学作品的刊发,更是发挥了文学、传播和市场需求联动的社会效应,引领了时代的潮头。
一、《时报》:近代通俗小说的发源地
《时报》在近代报界曾与《申报》《新闻报》占据三足鼎立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文学主张,并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推行他的小说观念与群治启蒙思想。1904年春,他不顾清廷的通缉,特意冒险来上海与罗孝高、狄葆贤密商办报一事。“时罗孝高、狄楚青方奉南海先生命在上海筹办时报馆,任公实亦暗中主持,乃日夕集商,其命名曰《时报》及发刊词与体例,皆任公撰定。”(1)罗孝高:《任公轶事》,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6月12日,《时报》第1号在上海出版发行,其中主笔是罗普,总主编是陈景韩,总负责人是狄葆贤。1908年后,狄葆贤独资办《时报》。此时的《时报》关注并迅速报道国际国内新闻,它在开辟“时评”栏目反映现实的同时,也设立“余兴”专栏以适合市民娱乐消遣的需要,颇受读者欢迎。1916年11月22日,《时报》在“余兴”专栏的基础上创办《小时报》文艺专刊,由包天笑、毕倚虹担任主编,此报可称为民国时期文艺副刊的雏形。
出于对新小说的一贯重视,梁启超对《时报》将要发表的小说文体类型不做任何限制:“本报每张附尽报刊之责以文字宣传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2)《时报发刊例》,《时报》,1904年6月12日。狄葆贤早年受梁启超“三界革命”文学观念的影响(3)胡全章:《“心存邦国”和“诗人之诗”:清末〈时报〉诗歌和“平等阁诗话”》,《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3期。,曾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文。尽管他一直保留着写作传统笔记小说的习惯,但是却能通过《时报》不遗余力地推动新小说的发展。主编陈景韩对于小说更是有独特的见解:“小说之能开通风气者有决不可少之原质二:其一曰有味;其一曰有益。”(4)冷:《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上),《时报》,1905年6月29日。1907年3月,《时报》在第一页“小说”栏目刊登了“小说大悬赏”的启事,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创作还是译作,都在悬赏之列。获奖作品均吻合了陈景韩的小说理论:第一等空缺,哀情小说《双泪碑》(南梦)获第二等,侦探小说《雌蝶影》(丹徒包柚斧)获第三等。被选中的这两部作品,或哀婉缠绵,或曲折离奇,在《时报》连载后颇受欢迎。
1921年,时报新馆落成,孙中山、蔡元培、杜威、胡适、张默君、朱胡彬夏等中外各界名流纷纷致信祝贺,赞赏《时报》的成就,其中,胡适的《十七年的回顾》一文影响力最大,讲述了《时报》对其人生成长和文学创作的影响:
我那年只有十四岁,求知的欲望正盛,又颇有一点文学的兴趣。因此,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当时把《时报》上的许多小说、诗话、笔记、长篇的专著,都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若有一天的报遗失了,我心里便不快乐,总想设法把它补回来。(5)胡适:《十七年的回顾》,《时报》,1921年10月10日。
胡适接触《时报》是在1904年离开家乡安徽绩溪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之后的事情。胡适认为其年少时“爱恋”《时报》,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每日由“冷”来做的短评是一种“创体”,“做的人聚精会神的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脑筋里发生有力影响”,他自然会从中受到思想启迪;第二,《时报》发表的由“冷”和“笑”翻译的白话小说,以及它所开辟的带文学兴趣的“附张”,均让胡适接受到了文学启蒙,“自从《时报》出世以来,这种文学附张的需要也渐渐的成为日报界公认的了”(6)胡适:《十七年的回顾》,《时报》,1921年10月10日。。胡适曾参加了1907年的小说悬赏征集活动,虽然没有中奖,但这件事与他后来对文学改良主张的提出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时报》大力推动新小说理念和新小说创作,抓住了“小说”与“妇女”这两个近代的热门话题。在《时报》小说专栏之外,狄葆贤还先后创办了《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两份杂志,开辟了小说的新阵地。《小说时报》创刊于1909年9月,由于代表新倾向的“四大小说杂志”(7)“四大小说杂志”包括:《新小说》(梁启超,1902-1906,日本横滨)《绣像小说》(李伯元,1903-1906年,上海)《月月小说》(吴沃尧、周桂笙,1906-1909,上海)《小说林》(黄摩西,1907-1908,上海),最早见阿英:《清末小说杂志略》,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103-110页。后来常以“晚清四大小说杂志”指称上述四种小说杂志,参见王燕:《近代科学小说论略》,《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已先后停刊,而《小说月报》尚未出刊,所以,《小说时报》的出版正可谓恰逢其时。1911年6月,有正书局又独立发行《妇女时报》,创下了商办妇女报刊的先河。三年之后,国内出版界掀起妇女报刊热潮,均与此有很大关系。《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以及《时报》小说专栏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小说家和编辑家,以周瘦鹃为例,“在《礼拜六》创刊前,据不完全统计周瘦鹃在刊物上发表了58篇文章。其中刊登在《妇女时报》上的为37篇,在《小说时报》上发表的为11篇,他在《时报》系统发文总计48篇;只有10篇文章发表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和《中华小说界》等也是很有影响的刊物上”(8)范伯群:《周瘦鹃论》,《周瘦鹃文集》,文汇出版社,2015年,第9页。。1917年,《小说时报》《妇女时报》这两份杂志同时停刊,原因不详。
1921年,时报新馆落成之后,狄葆贤将《时报》卖给了黄伯惠。至于他转卖报馆的原因,学界有多种猜测,或曰因其扩大经营、囤纸失策,以及不计成本等管理问题所致;或曰因其爱子夭折、妻子离世等家庭变故所致;或曰因其笃信佛教、心系佛缘而弃绝红尘所致,等等。1914年,陈景韩、包天笑、徐卓呆、毕倚虹、周瘦鹃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小说家们创办《礼拜六》杂志,并很快掀起休闲小说创作的高潮。应该说,《礼拜六》的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时报》系统的小说创作力量,而上述作家在移师《礼拜六》的同时,也带走了一部分读者群体,这些都直接对《时报》的销量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之,《时报》的兴衰与通俗小说的发生、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从1904年至1939年,《时报》历时35年,共出版发行12547号(周刊单记号的不在此数)。狄葆贤虽然执掌《时报》不到20年,但是由他所竭力推动的新小说创作却在近代小说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人兽接脑记》:陈撷芬著译的科学小说
“科学小说”是science fiction的直译,是“一些根据科学知识原理创作的小说”,包含有“超自然幻想”和“科学”两种因素(9)黄禄善:《是“科幻小说”,还是“科学小说”?》,《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4期。。它与如今常用的“科幻小说”概念不同,是近代中国“人们出于普及科学知识的需要,更多地借助科学小说来宣传化学、物理、医学、天文等各方面的知识”(10)康文:《略论中国近代科学小说》,《东岳论丛》,2003年第3期。,而不是具有科学性的幻想小说。由于20世纪初期国人对于科学缺少充分的认识,外国科学小说的译介工作因此也经历了概念模糊、文体特征混乱的过程,如1902年《新小说》第1号载《世界末日记》,编者将其称为“哲理科学小说”,意欲“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11)王燕:《近代科学小说论略》,《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作为新生事物,不仅“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积极译介科学小说,《时报》系统的《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也不甘落后,以科学小说寄托宣传科学、格致救国的理想。《妇女周刊》坚持《时报》最初对于小说的主张,在“新小说”专栏里发表或写或译的小说作品,主要有家庭、平等、性别等与妇女主题关系密切的文学作品,如法国小说《颈环》《女小说家斯吐活小传》等,著译小说则有陈撷芬的《人兽接脑记》。
陈撷芬是近代报刊史上由女性独自创办革命女报的第一人。她家学渊源深厚,从小随父亲陈范读书,后投在潘兰史门下学习诗词,十余岁便在《清议报》上发表《戊戌政变感赋》等诗作。包天笑回忆说,“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台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1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这里的“她”指的就是陈范的长女陈撷芬。1899年,她创办《女报》,后因稿源不足而停办。1902年5月8日,《女报》在上海派克路复刊。1903年2月27日,《女报》更名为《女学报》,并在创刊号上标“第二年第一期”,以示与《女报》的接续关系,栏目设有论说、演说、尺素、女界近史、译件、专件、谐铎、杂俎等,每期约60页。
1902年,蔡元培、章炳麟等人组织中国教育会,陈范是其中的成员,陈撷芬不仅随之参加了中国教育会的爱国女社,而且参加了蓄积反清力量的爱国行动。1904年,秋瑾到日本后,联合林宗素、陈撷芬等10余位留日女学生,于11月间重组共爱会,更名为实行共爱会,重新制订章程,陈撷芬被推为会长并任女子雄辩会会长,组织女留学生开展推翻清政府的演说活动(13)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第283页。。柳亚子曾提及她留日后的去向,“撷芬,十年前,创《女学报》,名闻海内外,适重庆杨俊,并留学美洲,毕业后,返国……”(14)柳弃疾:《陈蜕庵先生传》,卞老营,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49页。。张默君的《哀吾友陈撷芬君》一文,较为详细地记述了陈撷芬的性格、品质及婚后生活,是难得一见的关于陈撷芬生活的文献史料。陈撷芬与杨希仲在日本留学时相识,成婚后随其远赴美国。“辛亥义起,君偕杨氏浩然归,主持杨氏所办依仁中学于渝中,男女学子数百人”(15)张默君:《哀吾友陈撷芬君》,《时报》,1923年8月20日。。1912年2月,陈撷芬从美国归来,参加过张默君组织的“神州女界协济社”,同年秋天随丈夫离沪赴川。杨希仲在美国留学肄业,回到重庆后筹划创办银行。“在重庆,杨希仲夫妇共同倡办依仁学校,广收杨氏子弟、姻娅后生及邻里童稚入学。陈撷芬任校长,并亲自授外语。不数年该校即成为重庆著名学校之一。后来杨氏企业中的骨干人员,幼时大多就读于依仁学校,由壮及老,言及希仲夫妇,犹多怀念不已。”(16)戴元康:《杨希仲与川省外贸业务的开拓》,寿充一:《近代中国工商人物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54页。1920年春天,陈撷芬因心脏病多次危及生命,幸亏回沪救治及时方得以痊愈。她将自己的书稿交给张默君,“出所译著书数巨帙,畀予謄为校正。予受而读之,佩其有可取法,笔亦清畅”(17)张默君:《哀吾友陈撷芬君》,《时报》,1923年8月20日。,《人兽接脑记》便是其中的书稿之一。
《人兽接脑记》是一部短篇小说。小说叙事在结构上有三个层次:第一层,开篇与结尾相呼应,简要说明这是“余”写给“泰卷白蜡大学教师惠林·奇勃勒福吾友”的一封信;第二层,叙述者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三年前“余”与朋友福兰明汉在圆明山上的故事,并介绍了这座火山的自然环境。这里沉积着煤炭,留下了许多古动植物标本。圆明山的山顶有一个因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奇湖”,好似从地球内部冲出来的大喷水井,“余”来火山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它是否通向地球中心。第三层的叙述是小说的核心内容,即“余”在山上记载下来的关于“人兽接脑”的科学实验过程。
小说中的日记起始于1896年4月29日,终稿于1897年6月30日,记录了“余”与友人福兰明汉在圆明山做实验时与一个壮硕可怖的“大怪物”意外相遇之后所发生的离奇故事。怪物体壮且生命力强大,它的头在被斩断之后不仅没有死去,它的伤口还能奇迹般地自愈。福兰明汉当时正承受着因胃病而来的巨大痛苦,这不禁使他产生了人兽换脑的想法:“嗟乎!使余有此怪之精力,则余何致有此萎弱之病。此怪生活性之绵长迥异寻常动物,虽失脑而不受影响,若有人能换去余体之弱,补以此怪几何之精力,则欣幸何如哉?”(18)陈撷芬:《人兽接脑记》,《时报》,1920年11月17日。“余”也认为,如果脑筋敏捷的人能拥有此怪物的强健身体,的确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昔年医学协会曾断言曰,他日接脑之术必见成效。然何以至今尚未发明乎,只缘未经实验耳”。福兰明汉终因病痛难忍而自断其首,“余则不暇择他种精锐器械,遂执代木刀将福脑盖剖开,取出脑髓,幸完整未伤。盖其时余倘稍形鲁莽,或过于迟缓从事,则此生人之髓,均难免不为之伤及也。于是余又继续将怪物之创口剖开,以福脑置入,为之裹创敷药。一切妥帖,急回石屋将所贮备药尽数取出,再与敷治”(19)陈撷芬:《人兽接脑记》,《时报》,1920年11月24日。。复杂的脑部移植手术在没有精密的医学仪器设备和高超的医学技术的前提下施行,离不开小说家离奇、夸张的叙述,所以,这本身就是一场虚构,但是它的根本意旨却是对科学精神的探究。
这篇小说关注的核心始终是人,是从人的个体生命出发而达到的人类终极命运,其借助科学实验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此巨大之怪体,果具有君之智脑,不诚将成何种奇物也?”(20)陈撷芬:《人兽接脑记》,《时报》,1920年11月17日。作者认为先进之人脑与怪物之强壮体魄相结合,可以杂交出基因优质的物种,可以让人类在自身不足的前提下获得“物竞天择”的优势,并且,“余”还寄望于它能成为“世界新历史”的开创者。在一个凉爽的天气里,怪物在被接脑之后的创口自然痊愈,离奇的换脑术竟然大获成功。福兰明汉不仅借助怪物的躯体得以存活下来,而且逐渐能够说话和唱歌,进而恢复了人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但是,他害怕孤独,担心“余”丢下他而离开这里;他渴望自由,担心自己被捉住送到博物馆去展览,或成为科学家们实验的对象。所以,当一位科学青年发现他,并欲撒网捕捉他时,“福兰明汉忽喷出蒸汽,一若琴声,高歌希腊名人所著《何处为汝帽》之歌,举其粗而且黑之颈,大口全张,露出锋利似锯之牙,势欲噬人”(21)陈撷芬:《人兽接脑记》,《时报》,1920年12月8日。,他其实是在以死来保护他的自由。然而,一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余”在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六月三十日记录了人兽接脑的结局。“兽体克福人脑乎,良知为强蛮兽力消夺乎”,福兰明汉“柔弱优雅之脑力为彼兽体汩没殆尽,换以至粗极暴之怪脑矣”,他之所以言语陈腐,凶暴加剧,恐怕是“人类之脑,不敌猛兽体力之墙,而人类之智,久之将渐为兽体所化”(22)陈撷芬:《人兽接脑记》,《时报》,1920年11月24日。的原因所造成的吧。“余”由此终止了在湖边的探险事业,也失去了对科学进行研究的兴味。当然,小说的叙述重点不在于“余”的科研实验的失败与否,而在于作者所期望的科学理想最终破灭了。
《人兽接脑记》发表时署名“陈撷芬译”,但是没有标注这篇小说的原作者与国别,这给人们以此去和原著进行对比核实的工作带来了难度。虽然小说中的日记标有明确的时间,但并不能据此断定它的创作时间或翻译时间。大体来说,该作应为陈撷芬在重庆时期的译作。其原因是,20世纪初,中国的近代女性就对翻译小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00年,近代第一部由女性翻译的科学小说,即是薛绍徽采取“林译式”翻译的法国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因广受读者欢迎,1905年,这篇小说被更名为《寰球旅行记》,并在《时报》上面连载(1905年12月20日至1906年1月28日),1906年,小说林社和有正书局又分别以《寰球旅行记》的名字再出单行本(23)郭延礼:《女性在20世纪初期的文学翻译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在20世纪初期留学日本东京的三十多名中国女性中,陈撷芬是“长于英文者”(24)《记事外国》,《女子世界》,1905年第3期。。她先后流居于日本和美国,具有翻译英语和日语小说的能力,却未有作品呈现,从而与“中国近代女性翻译文学家群体”的名号失之交臂。在1910年赴美之前,陈撷芬在女界声名显赫,不至于在翻译了小说之后却不去发表。同时,由于没有发现原作,陈撷芬采取了何种方式翻译该作也就变得无从考证。郭延礼认为,近代女性经历了一个“以译代作”的小说创作准备阶段,随着女子教育发展和女留学生的增多,20世纪第二个十年(1910-1919)能阅读西方小说原文的人愈来愈多,同时对外国小说的兴趣也愈来愈浓。“许多女作家已着意模仿西方小说的写作模式,她们通过对源语文本的‘置换’和改造,作出新的解读,并融入了她们的审美理想,而又以创作小说的面貌出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译代作’”(25)郭延礼,郭蓁:《中国女性文学研究(1900-1919)》,山东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28页。。陈撷芬的《人兽接脑记》极有可能也是一篇“以译代作”的小说。事实上,陈撷芬在重庆的生活并不安顺,她的夫家虽然豪华至极,但是她坚持独立,不依靠他人,衣食出行十分简朴。她原本与丈夫感情笃深,信奉一夫一妻制,却因未育而受到家族的歧视。丈夫为续子嗣而纳妾,她因此患上脑疾,回沪之前又患心脏病,几次濒于绝命。她所承受的巨大的精神折磨和身体病痛,与小说中陷入疾病困境的人物经历颇为相似。她不满于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这与小说中人兽接脑失败后的结局几乎一致。至少可以说,陈撷芬或译或著的这篇小说当中是融入了她自己的切身感受的。
《人兽换脑记》涉及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诸多科学领域,其中的科学实验有更为深刻的关于人类进步的思考。当然,在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和故事情节的悬疑色彩上,这部小说都不能说是当时通俗小说的上乘之作,但这恰恰反映了陈撷芬与他人不同的旨趣。《人兽接脑记》选用了日记体和书信体双重的小说叙事结构,这在新文学初期还是比较少见的。它采用了“同故事叙述人”即“余”是情节中人的日记体小说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摆脱了传统小说“说书人”不参与情节设置的叙述传统,是女性小说叙述模式现代转换的较早尝试。
三、《妇女周刊》:传播新思想的“附张”
陈撷芬著译的这篇令人“不可思议”的科学小说之所以能发表在《时报》上,主要是因为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思想与《时报》“独创体裁,不随流俗”(2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的办刊理念有密切的关联。从1919年起,《时报》进入了积极的拓展时期,专题性系列附张的增加即是其显著表现之一。1919年2月24日,中国报业的第一份专刊即《时报》的“附张”《教育周刊》问世,9天之后,即3月6日,《时报》的第二份“附张”《妇女周刊》也以随报奉赠的方式问世。最初的《妇女周刊》每号有4张,较多版面的增加显然是为了迎合更广大妇女阅读群体的需要而考虑的。随后,《学术周刊》《图书周刊》等一系列附张在“吐故纳新”的目标下相继创刊,它们一起打造出了《时报》系列“附张”正派、严肃、高雅的报刊风格。
就《妇女周刊》而言,它的编辑主任是女界精英张默君。1920年1月1日,《妇女周刊》新年号上发表张默君的文章《民国九年对于女教育家新希望》,并同时附载了她的侧面半身像,以及“本周刊编辑主任张默君女士”的字样,标明此时的她已经正式出任《妇女周刊》主编的职务。自1920年1月15日开始,张默君在“新调查”栏目中连载《欧美女子教育考察录》一文,虽然这是一篇未完稿,但是就已经发表的文字来看,它已经对于近代的女子教育有了较大的影响。
1921年1月5日,《妇女周刊》(第92号)一改以“新思想”为统摄的标题栏目,除了“新论坛”之外,周刊里一系列的“新”字号栏目均变成了“小”字号的栏目,如小谈话、小发明、小笔记、小纪载、小博物、小书丛等,与此同时,周报的版面也缩减为两张。3月2日,《妇女周刊》不再独立发行,其内容全部被挪移到《时报》的第四张上面。此时的《周报》在整体的版面设计上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字号栏目已彻底消失,“新论坛”栏目被“社言”所取代,一些新的栏目如“小工艺”“家庭常识”“文艺”“讨论”“丛谈”和“小说”等开始出现。可以看到,改版之后的《周报》选取了更加平易的语言风格,这似乎也在表明它的受众选择开始向知识层次一般的妇女倾斜。改版之后的《妇女周刊》“以促进女界文化如目的”为总纲,“餐花”《今后之妇女周刊》指出:“今后之妇女周刊,其进行将如下所陈:(一)言论方面,以提高妇女界之知识为主旨,旁及破除迷信改良恶习。(二)事实方面,妇女界最近之进行,供参考及砥砺之资。”(27)餐花:《今后之妇女周刊》,《时报》,1921年3月2日。3月9日,“餐花”《妇女周刊第一百期感言》,对创刊一载有余(周刊中间偶有间断,从时间延续上实际已达两年)的百期《妇女周刊》进行了总结:“女界最可喜之现象,厥惟文化方面,较前为进步,是即为女界日缉熙于光明之征,安得不为我璀璨之女界颂且祷乎。至若干报之增刊妇女周刊,原欲为女界稍效绵薄,今已刊至百期,于女界果有所贡献与否,所不克知。惟有自今伊始,竭其驽骀,以扶助女界之向上而已。”(28)餐花:《妇女周刊第一百期感言》,《时报》,1921年3月9日。同期,《本周刊征稿条例》云:“(一)本周刊欢迎女界之著作,及男子对于女界之贡献。(二)投稿经本周刊后,酌给筹资或书券。(三)投稿之文学,以明白浅显为主。(四)凡关于女界之各项消息及各种摄影,投稿本周刊,最为欢迎,惟以未见报纸及杂志者为限。”(29)《本周刊征稿条例》,《时报》,1921年3月9日。由上述编辑策划可见,“餐花”所主编的周刊一方面坚守报刊的女权立场,另一方面则开设“常识”“消息”“世界妇女消息”“杂载”等通俗平易的栏目,大有重振旗鼓之势。遗憾的是,如此局面仅仅维系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妇女周报》在6月29日出版了第114期之后便停刊了。
由张默君担任编辑主任时期的《妇女周刊》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的《妇女周刊》每号有4张,其中两张登载广告,另外两个专张以“新妇女”和“妇女俱乐部”为标题,呈现出一种“求新”的风格。“新妇女”字样兼有英文标题:“THE EASTERN TIMES LADIES’ SUPPLEMENT”,“新妇女”专页下分设“新论坛”“新文艺”“新家庭”和“新彤史”等不固定的栏目,这些栏目内容的主旨上承清末“女国民”思想,下启新文化运动需求,显示出了办刊人与国际报刊接轨的视野,也体现出了他们致力于求新、时尚的时代性。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在世界大战的风云中,妇女们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活动能力,包括军事能力,证明了她们不仅能在家里料理日常生活,还能与男人一起承担民族国家危难之时的责任,妇女的社会地位由此在战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昔蒙古、斯巴达雄视一世,得力于妇女者尤多。美利坚妇人愿力之宏夙著称于当世。战期中效果如何,即未身亲目睹,亦可相喻于不言中也”(30)怿志:《妇女周刊导言》,《时报》,1919年3月6日。。“妇女俱乐部”报头下面也设有一系列“新”字头栏目,如“女界新消息”“新流行”“新游戏”等,大致包含有妇女的游戏、服饰、时尚和健康等内容,如第3号“新流行”名目下《缠胸》一文,倡导女子健康的观念,反映了对世俗中妇女生活的关心。
陈撷芬的著译小说《人兽接脑记》发表在张默君主编的《妇女周刊》上并不意外。“新思想”“新著述”等栏目的宗旨正是要以发表翻译作品的方式来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近代女翻译家陈鸿璧早年曾与张默君合作翻译过两部小说(31)李想,刘钊:《陈鸿璧与张昭汉关系考》,《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即Orison Swett Marden的两部著作《思想之伟力》(1920年1月29日至12月1日)和《妇女与家庭》(1920年12月29日至1921年4月27日),均连载于《妇女周刊》。那时,狄葆贤已在艰难地维持《时报》的正常运行,陈鸿璧的翻译之作应是对其办刊观念的勉强支撑。陈撷芬与陈鸿璧一样,也是张默君早年志同道合的女友。陈撷芬早年追求女性人格独立,但是当她弃别夫家重回其早年办报的上海时,却已是遍体鳞伤。张默君自然希望陈撷芬振作起来,并像陈鸿璧那样和她一起坚守《妇女周刊》这块新思想阵地,遗憾的是,身心俱损的陈撷芬因不堪其夫家习俗传统的折磨而过早地结束了生命。陈撷芬早年办报时曾经创作过诗词、论说、演说、传记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唯独不见小说。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她有机会在《时报》上发表小说应该说是一种幸运,但是她的生命晚期与狄葆贤时代的《时报》末期“遭逢”,则又注定了这部作品的不幸命运,以至于它被埋没在尘埃之中而不被人们所重视。
综上所述,作为清末民初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人,狄葆贤赞同“小说界革命”的文学主张,积极推动新小说创作。在陈景韩、包天笑等人的协助下,他使《时报》及其系列杂志、报纸附张成为新小说的阵地,更为近代报纸培养出了现代的小说阅读群体。《时报》采取集团系统化的经营模式,在思想上求新,在管理上求变,为《妇女周刊》的发展提供了通道。它不鼓动激进的西方式女权运动,侧重于女子教育、家庭建设、改良风气和道德重建。它发表陈撷芬著译的科学小说《人兽接脑记》,体现了近代知识者在崇尚科学、追求自由的现代转型之际,对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内在矛盾的认知与困惑。从这层意义上说,《时报》及其系列“附张”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媒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