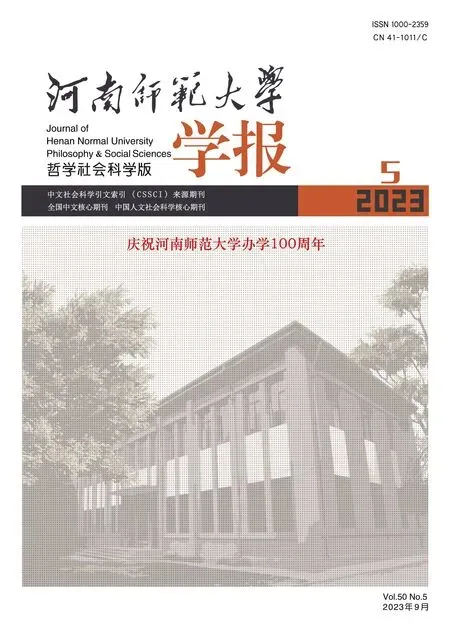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的南明史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2023-03-09谢盛
谢 盛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治学严谨,论著颇丰。其一生跌宕起伏,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诸多艰难时刻。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翦伯赞从正在钻研的史前史、殷周史和秦汉史领域暂时抽离,开展与抗战有关的历史研究。他于1940年起开始探研南明史,如此学术转向,实则蕴含丰富的现实意义。对此,尚未见有专门的学术成果发表。本文将从翦伯赞南明史研究的背景、内容、主旨逐一进行探讨,揭示翦伯赞南明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翦伯赞南明史研究的背景
翦伯赞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钻研南明史,这并非兴趣使然。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的军事侵略激发了中国学者以学识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情怀。作为中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翦伯赞于1938年3月在长沙《中苏半月刊》发表了《抗战的过去及其前途》,将治史领域由注重史料和考据的中古史,转移到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主题上来。同年8月,其《历史哲学教程》在长沙生活书店出版,翦伯赞在序中写道:“在我的主观上,这本书,正是为了配合这一伟大斗争的现实行动而写的。”他希望“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1)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2页、第8页。。然而,翦伯赞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被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所浇灭。同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作为中共党员,1940年2月13日,翦伯赞按照党的指示前往重庆,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副主编。在此期间,翦伯赞的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除了鼓呼抗战,还开始广泛阅读南明史料,并撰写相关论著,试图通过抨击南明政府的昏聩,影射偏安西南一隅的国民党当局的政治黑暗。
由于时局与南明颇为相似,因此引起了国人的“南明”情结,并形成了深厚的“南明”语境(2)谢贵安:《抗战时期“南明”语境的形成与史学表达》,《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南明史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相论争的焦点。翦伯赞研究南明史的学术环境相当艰难,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如翦伯赞撰写的第一篇南明史研究论文《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便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所扣压,未能发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机关的御用文人,亦以南明史为题,与支持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针锋相对,对翦伯赞、郭沫若等人进行文化围剿。1943年,蒋介石发表实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指责李自成灭掉明朝,导致亡国,清朝入主中原,使得中国的民族思想渐至消亡。1944年3月19日,正值明亡三百年纪念日,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予以回击,引起学界和政界的巨大反响。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阵营的口诛笔伐。1944年3月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便发表陶希圣主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指责郭沫若“为匪张目”,“将明之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3)《纠正一种思想》,《中央日报》,1944年3月24日,社论。。随后,《商务日报》发表社论,称《甲申三百年祭》是“时代错误的结晶,放任这种文章在社会传播,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事情”(4)《论赫尔的名言》,《商务日报》,1944年4月1日,社论。。4月13日,《中央日报》再次抨击《甲申三百年祭》“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5)《论责任心》,《中央日报》,1944年4月13日,社论。。4月20日,叶青发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一文,响应《中央日报》的社论,指责郭沫若文中蕴含“反对政府,歌颂流寇,大有希望今年为三百年前的甲申之再现的意思”,“是适合共产党需要的一篇时髦文章”(6)叶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评议》,《时代青年》,1944年4月20日;收入叶青主编《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独立出版社,1944年,第3、5页。。
面对如此严峻的学术环境,翦伯赞依然笔耕不辍,以史学作为斗争的武器,对郭沫若等同仁进行声援。面对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文化围剿,翦伯赞有理有据地撰写了诸多掷地有声的佳篇。
二、翦伯赞南明史研究的内容
1940年3月22日,翦伯赞撰写了《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该文的研究对象为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永历王朝。文章开篇介绍了永历政权所处的时代背景,认为无论是统治地域还是物质资源抑或是军事实力,都不可与南明前两个政权(弘光、隆武)同日而语。但弘光、隆武政权不过一年时间便相继覆亡,而永历政权却坚持了十六年之久,这并非“天时”,亦非“地利”,而在于“人和”。翦伯赞先是分析了永历政权的社会矛盾,随后阐述了永历政府的阶级性质,指出第三政府的本质已经改变,成为“当时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众之政府”。在这个“人民大众”政府里,既有缙绅又有寒士,既有元老重臣又有叛将贼众,是一个联合政府。翦伯赞认为,第三政府虽为联合政府,但以实力支持这个政府的却是寒士。永历时代,先后与清朝斗争者,为“人民义勇军”“反正之伪军”“闯贼余部”。正因为有这些以广大人民为基础的抗清力量,该政权才得以长期存在。随后,翦伯赞详述了永历政权从抗争到覆灭的历史过程,并在文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闯贼余部”的重要作用。翦伯赞用李成栋攻桂林,孔有德下全州、围桂林,清军陷桂林、入柳州、进攻贵阳、大举入滇、入缅等具体历史事件来说明,“抗战到底者,并非南明的缙绅,而实‘天人公愤’之‘闯贼’余孽”(7)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该文旗帜鲜明地同情支持“人民义勇军”,触碰到国民党逆鳞,因此遭到审查机关的扣压,未能发表。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后,翦伯赞发表了他的第二篇南明史研究论文《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该文探讨了南明第二个政权隆武朝的兴衰。首先,该文简述了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失败的经过,对弘光政府与农民起义军在民族危亡之际未能同心抵御外敌入侵表达了惋惜。随后,翦伯赞全面剖析了南明第二个政府,对其仍重蹈弘光覆辙表达了不满。他认为隆武政权虽然看似在军事实力和反抗意志上大不如前朝,但依然拥有抵抗清朝的物质基础和能力,再加上“江南人民义勇军”的兴起和李自成残部与政府军的合流,不至于不堪一击。紧接着,翦伯赞对当时多个社会力量进行探讨,分析了张献忠与隆武政权之间、隆武政权与鲁王政权之间、隆武朝廷中汉奸与正义之士之间的矛盾,并对这些内部矛盾未能转化为共御外侮的民族矛盾而感到遗憾。最后,翦伯赞对“人民义勇军”最终失败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指出义勇军缺乏政府支持、彼此割裂、战略战术不成熟等,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该文中,翦伯赞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内部的矛盾,不设法克服,而欲在抵抗外敌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是绝对不可能的。”(8)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苏文化杂志》,1941年第8卷第1期。
1947年,翦伯赞的《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在《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发表,但据他在该书《序》中指出,文章写于1943—1945年间。此文分为八个部分,叙述了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从建立到覆灭的过程。第一、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的经过,并对弘光朝的政权性质进行分析,认为该朝小人当道、排除忠贞、阉党再起。第三部分阐述了把持朝纲的马士英、阮大铖对清采取妥协政策,派人北上乞和却被拒绝。而清政府对弘光忠臣史可法进行诱降亦遭到拒绝。第四、五、六部分,揭示了弘光政权在马、阮等人把持下,文恬武嬉、贪污腐化、党狱繁兴的政治局面。第七部分讲述了福王政权爆发内战,左良玉起兵“清君侧”的史事。第八部分讲述了清军趁南明内讧之际,击溃李自成农民军,并挥师南下,导致弘光政权覆灭。该文揭露了南明政府抗清意志不坚定,时刻准备妥协的立场;揭露南明弘光政府大兴党狱,制造内讧,导致“内战爆发”的政治黑暗。最后,翦伯赞站在农民起义军的立场上,热情讴歌他们的爱国之心,字里行间蕴含着对弘光王朝覆灭的惋惜和愤懑。至此,翦伯赞将南明三个政权的历史皆进行了探讨,打通了南明全史。
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随后,翦伯赞发表《桃花扇底看南朝》一文予以响应。该文所指南朝实为南明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朝。与《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相比,该文研究的时间跨度更长,从崇祯十六年(1643)的南都,写到弘光朝的覆灭。全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孔尚任的生平和创作《桃花扇》的背景。第二部分分析了《桃花扇》的全剧结构和作者的写作动机。第三部分通过对《桃花扇》内容的解读,批判了明朝末年南京的纸醉金迷。第四部分仍通过对《桃花扇》文句的分析,讲述了崇祯败亡、弘光新创、朝廷被奸党把持的史事。第五部分讲述了弘光统治集团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第六部分描写清军夺取南京、弘光帝被俘“北狩”的情景。此文以孔尚任的《桃花扇》为文本,对其进行逐句分析,并结合史实和作者意图进行解读,这与其前三篇论文直接叙述南明政权兴衰史的研究理路有较大的区别。
1945年,翦伯赞又发表了《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该文叙述了清朝入侵中原的情形:“一六四六年(顺治三年)中国的历史,走进了一个空前的危急时代。当此之时,清朝侵略者,已经奠定河北,削平中原,西入陇蜀,南下闽浙。并且继续利用中国的人力与物力,驱使中国的汉奸与败类,以压倒之势,长驱而入西南。企图一举而下荆楚,再击而践粤桂,三击而入黔滇,以完成其对中国之最后的征服。”意指如今日本侵华的态势有如南明时代的“历史再现”。该文还对南明政府中的上层分子的腐败及军队的无能和骄横进行了批判,指出“桂王一行,用现代语说,也算是一个‘流亡政府’,因为他们还保持着政治的组织,而且缅甸政府,也是把他们当作一个政治团体接待的。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已经忘记了他的任务,他们简直没有想到怎样打回祖国这件事情。而这就表现他们拒绝与李定国等的抗清军继续斗争”(9)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945年第1011期。。
以上诸篇论文便是翦伯赞在抗战期间的南明史研究成果。在政局不稳、资料匮乏的特殊时期,能有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这些论著不仅探寻了南明史事,更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主旨。
三、翦伯赞南明史研究的主旨
翦伯赞的南明史研究,以治史方法而论属于史观派。他不同于柳亚子等人以搜集南明史料、编撰南明史书为首务,而是利用唯物史观分析南明历史,用阶级分析法探讨南明的社会阶层,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10)谢贵安:《抗战时期“南明”语境的形成与史学表达》,《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翦伯赞讨论南明史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南明时期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旗帜鲜明地肯定下层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功绩,指出南明的成功和坚持是由于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军余部的作用,猛烈批判了南明政府的腐朽,将南明的失败和覆亡归咎于南明帝王、官僚和将军的无能。具体来说,翦伯赞南明史研究的主旨有如下几点:
第一,歌颂农民起义军英勇坚定的抗清斗志和爱国精神。翦伯赞在南明史系列论文中对农民军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首先,讴歌农民军坚持抗清的斗志。翦伯赞站在农民起义军的立场上,热情讴歌农民军坚持抗清的斗志和决心,将农民起义军亲切地称为“人民义勇军”,所谓“广东人民义勇军”“江西人民义勇军”,他们“是何等的不顾身家性命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他赞扬农民军抗清的坚定和果决,认为“这些忠实又英勇的爱国人民”,在国家危难之际,以生命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生为忠义之士,死为壮烈之鬼”。他们“或‘倚山结寨’,或‘入海招兵’,或新起草茅,而聚众抗清,或旧为盗贼而反戈向敌,或连族而起,保卫家乡,或孤军奋战,攻陷城邑,或父母妻子,惨遭杀戮,或祖宗邱墓,横被发掘”。这种不畏牺牲的悲壮情怀,与官僚士大夫的懦弱行为“岂可同日语哉”!所以翦伯赞强调:“明末中国人民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南明史上,却留下不朽的一页。”(11)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945年第1011期。其次,对出身农民起义军的南明将领也予以肯定。譬如“清肃王又致书高杰诱降,但因高杰出身‘流寇’,富有爱国之心,终不为动”(12)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281页。。翦伯赞承认李自成和张献忠余部归顺南明政府的爱国目的。他指出在清军南下时,李自成部将李锦归附隆武政权“是为的大敌当前的原故。不仅如此,而且在归附以后,他们确能忠勇为国,效命前驱”(13)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苏文化杂志》,1941年第8卷第1期。。翦伯赞还为张献忠余部孙可望以武力挟制永历朝廷以“自重”的行为作了辩解,认为当时孙可望雄据滇黔,遥控川湘,地方数千里,甲兵数十万,他既可以继续割据一方,亦可以自立为王,还可以举滇黔土地而降清,又何必劫王自重呢?“这就证明了不是为了自重,而是为了要继承这一个没有希望了的民族。”(14)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945年第1011期。他特别叙述了孙可望归顺南明后指挥东路军李定国、北路军刘文秀收复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大片土地的战绩,“像这样一个惊人的胜利,就证明了中国人民并不是没有抵抗满清侵略的力量,以前的失败,只是为没有把这一部分力量运用起来。自从李定国把中国人民最后的旗帜举起来以后,满清侵略者也就惊惶失措了”(15)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945年第1011期。。他热情赞扬联明抗清的农民起义军余部抗战的决心和意志,指出当永历政权灭亡之后,不愿投降、坚持作战的,并非南明之缙绅,而是“闯贼余孽”李定国;当李定国战死后,继续抗清十四年之久的,依旧是李自成的余部李来亨、郝永忠、刘体淳等人(16)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他援引孙中山的话说:“民族精神不宝藏于士大夫,而宝藏于下层社会之会党!”(17)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由于这些观点触犯国民党的禁忌,因此遭到封杀。翦伯赞借桃源逸史在《永历实录》后的跋语,评价道:“余读史至此,不觉慨然而叹曰:嗟夫!夫果谁为顺而谁为逆,谁为忠而谁为奸,又谁为孤臣孽子而谁为盗贼流寇也。”(18)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945年第1011期。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意识。
第二,揭露南明政府政治黑暗、生活腐化、对外妥协。首先,翦伯赞批判了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内除忠臣、外谋妥协,以求“偏安江左”的政策。指出他们将“一切中兴大计,皆置之度外,而日以排除异己,援引私党为务”(19)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281页。。揭露南明热衷内战,对外投降的策略:马士英等制造内讧,导致“内战爆发”,左良玉以“奉太子诏”清君侧为名,率军直捣南京。他死后,“儿子左梦庚还是继续挥(叛)军东下”(20)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第290页;又载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270页。。南明撤掉防清之军以抗左,结果清军乘势南下,南明福王政权最终覆灭。其次,揭露了南明政府奢靡腐化的生活。翦伯赞以南明弘光政权为例,指出皇帝朱由崧采选美女、寻找壮阳之药,已属恬不知耻,但“福王还感到声色不足以恣其淫乐”(21)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286页。,真是无可救药。他称南明政府的“贪污腐化、荒淫无耻”和百姓的“饥寒交迫、流离死亡”,“这正是明代亡国前夕的社会之一里一面”(22)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第287页;又载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262页。。
第三,分析南明成败的原因。翦伯赞认为,南明成功的原因,在于坚持团结各阶层力量,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他指出,在清朝大军压境的情形之下,“摆在新政府之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政府军力,团结全国人民,组织统一政府,执行全国抗战尤其是克服内在的矛盾,以迎击共同的敌人”(23)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苏文化杂志》,1941年第8卷第1期。。南明政权是在人民特别是“闯贼”余部的支持下,才支撑下去的。翦伯赞以永历政权为例,指出该政府虽然是缙绅与寒士的“混合政府”,但支撑这个政权的是寒士而非缙绅,在与清军作战的过程中,先后奋起斗争的分别是“人民义勇军”“反正之伪军”和“‘闯贼’残部”。翦伯赞认为,永历政权能坚持斗争十六年,是“建筑在广大的人民的基础之上”(24)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是团结各阶层人民的结果,“我以为桂王政府在更恶劣的客观条件下而能支持较长的时期,既非天命未绝,亦非地理保镖,而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不协调的因素之消解,与各阶层的人民最后大团结之结果”。翦伯赞还将永历与弘光、隆武两个政权相比较,指出由于弘光、隆武两朝未将政权建立在广大人民基础之上,因此在当时虽有诸如史可法、张煌言这样的名臣辅佐朝政,却依然敌不住马士英、阮大铖这一类卖国求荣的大汉奸。而永历政府与前两个政权不同,它是由社会各阶层所组成的“人民之混合政府”。因此,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士大夫金堡看来,简直就是‘匪人’的政府。即因桂王政府变质为混合政府,所以他才能在极恶劣的客观环境中,支持十六年之久”(25)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945年第1011期。。同时,翦伯赞认为,统治者内部的不团结导致了南明的失败。他强调:“统治者内部不能团结统一,共抗满清,使满清得以乘间抵隙挥游刃于矛盾集结之处,以戳其要害,这是以前两个政府,尤其是第二个政府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不幸第三个政府成立之初,首先又重复这个错误。”(26)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他在《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具体分析了永历政权败亡的原因,指出李定国与孙可望被南明政府分化后,“一个统一的力量,分化为两个对立的力量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孙李的火并。在火并战争中,孙可望被迫投降了满清。孙可望离开了民族斗争的战线,这是失败主义者的胜利。同时,亦即满清侵略者的胜利”(27)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945年第1011期。,并进一步阐发道:“桂王政府可以说是以内战揭幕,而且几乎以内战结束。但是这残酷的历史教训,并不能使他警惕,不久在四川发动了内战。”(28)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1945年第1011期。
第四,分析了清朝入主中原的策略。翦伯赞认为,清朝入主中原的策略是制造南明各政治力量的分裂,然后各个击破。“拉拢一个中国势力,打到另一个中国势力,阻止中国的民族战线之形成,以达到其各个击破的阴谋,便是满清入关以后征服中国的一贯政略。”南明第一政府灭亡后,翦伯赞指出,清朝对唐王朱聿键建立的“第二政府”采取的手段就是制造分裂,各个击破。“所以满清政府,在攻陷南京以后,便利用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进行政治进攻与军事进攻之平行政策,他一方面乘着第一政府的新溃,人心动摇之际,派遣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汉奸洪承畴,诏抚江南,以图缓和或软化中国人民反对外族的斗争,施行其‘以华制华’的毒计;另一方面,他利用中国政府与‘闯贼’的对立,一面由南京趋浙江,由九江入江西,以进攻中国的政府军;一面分兵武汉趋湘北,扫荡‘闯贼’李自成的残部,由汉中趋川北,进击张献忠的大本营,以推行其各个击破的战略。”(29)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苏文化杂志》,1941年第8卷第1期。
四、翦伯赞南明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翦伯赞的南明史研究不囿于史事的钩沉,而是立足当下,借古喻今。他的论文并未按南明三个政权的更替顺序展开研究,而是从第三个政权(永历)写起,继而写到第二个政权(隆武),再到第一个政权(弘光),最后又回到第三政权(永历)。如此写作顺序,实与当时政治背景紧密相连。1940年,日本分化中国政府的企图取得部分效果,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给抗战前景蒙上浓重阴影。1940年3月22日,翦伯赞发表了第一篇南明史论文《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因为第三个政府永历政权存在了十六年,是南明持续最久的政权,因此他写这篇论文意在强调,只要像南明永历王朝一样,广泛团结农民军余部和缙绅、寒士、元老、重臣等社会各阶层,就能与日军持久抗战。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后,《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问世,字里行间表达出对南明隆武政权与张献忠所率农民起义军之间、隆武政权与鲁王政权之间“相煎何急”的痛惜,告诫人们内斗只会产生内耗,进而被异族灭亡。1944年,在明亡三百年之际,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引起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猛烈攻击,于是翦伯赞发表《桃花扇底看南朝》,论述弘光政权的腐败和南明政府不足恃的观点,对郭沫若进行声援。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对于中国未来的命运,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表达反对一党独裁、呼吁各派联合的政治诉求。同年,翦伯赞发表《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指出永历政权是由社会各阶层人民组成的“混合政府”(30)翦伯赞:《南明史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8页。,以作响应。此外,翦伯赞南明史论著中的术语,如“伪军”“义勇军”等,亦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颇为切合。《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所提及的挽救局势的新兴力量“江南人民义勇军”,更是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江南抗日义勇军”(即“江抗”)几乎同名。不仅如此,诸如“民族的统一战线”“联合政府”“以华制华”等词,皆反映出翦伯赞南明史研究具有当代隐喻的特征。
翦伯赞曾坦率承认,在革命年代,史学应成为斗争的工具,“一切历史家描写及批判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历史作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工具”(31)翦伯赞:《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文汇报·史地周刊》(香港),第7期,1948年11月12日。。当翦伯赞及其同仁看到如今偏安一隅的重庆国民政府与南明王朝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时,他们便投身南明史研究,在论著中激烈地批判南明政府的腐朽昏庸,旗帜鲜明地赞美和支持农民起义军,其寓意不言自明。
第一,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政治黑暗。翦伯赞通过论述南明统治者的纸醉金迷、不思进取,来影射重庆国民政府的腐败堕落。在《桃花扇底看南朝》一文中,翦伯赞指出,在满清的军队已迫近山海关,农民的起义已由西北扩大到西南及中原一带,“当时的南京,却是一座纸醉金迷的城市”(32)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第286页;又载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260页。。借南明政权的骄奢淫逸讽刺大后方重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局面。翦伯赞还借晚明“兴党狱,收捕复社诸生,摧毁文化,箝制舆论”(33)翦伯赞:《桃花扇底看南朝》,《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第289页;又载氏著《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268页。,批判国民党政治黑暗,大兴党狱,钳制言论。
第二,讽刺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无能。翦伯赞论南明的文章中,对南明三个政府的军事溃败着墨尤多。如《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一文,在叙述清军南下进攻江苏镇江时写道:“当时福王方面守镇江的是郑鸿逵的闽军。当清军逼迫镇江北岸时,郑鸿逵并无丝毫防御,每天只是捕杀从江北溃退下来的自己的败兵,一共杀了一万多人,杀得以后败兵不敢南渡,大部分都投降了清朝。”(34)翦伯赞:《南明史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7页。作者对这种荒谬场景的铺叙,实则是讽刺蒋介石在对日作战上的节节败退,并暗讽了蒋介石执行军事上认敌作友、以友为敌的投降主义政策。
第三,抨击国民党的内讧与内战,揭露日本分裂图谋。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人调整策略,对国民党当局“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国民党随之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翦伯赞通过论述南明各政权分裂、内讧、火并的史实,抨击国民党大搞分裂、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他借南明弘光政府的行径,揭露国民政府假抗日真反共的目的:“马士英等阉党,正玩弄妥协的阴谋,他们特别强调,国家的仇敌,不是清兵,而是‘流寇’,企图以此缓和清兵之进攻。”(35)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282页。同时,他借清朝揭露日本的阴谋,“想诱降一个,打击一个”,并直白地宣告:“站在清政府的立场,福王政府与李自成,同为明朝人,亦即同为他的仇敌,固无所谓谁为正谁为逆也……他对于福王政府与李自成,盖一视同仁,并无亲疏厚薄之分,同在剿灭的预算之内。”(36)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二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第280页。翦伯赞的意图,在于借古讽今,警告国民政府不要被日本人制造分裂,像南明那样产生内讧,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战胜日本。
第四,赞美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坚定性、不妥协性。翦伯赞在文章中多次论述李自成和张献忠余部的历史功绩,认为是他们力撑危局,才极大延缓了南明灭亡的速度。赞美“当时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众之政府”的坚韧(37)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这实则是对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冠以“匪军”“流寇”等蔑称的回应,赞扬以农民起义军为历史镜像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强大外敌入侵,顾全大局、顽强抵抗、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第五,为毛泽东的联合政府主张进行历史论证。翦伯赞指出,永历政权为何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十六年之久,是因为这个政权是由社会各阶层人民组成的“混合政府”(38)翦伯赞:《南明史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8页。。这无疑是对当时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的积极响应。翦伯赞强调,永历“混合政府”中的阶级成分是下层民众,这也符合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立场。
以现今的学术标准来看,翦伯赞南明史研究的论著或许“史料显得贫乏,有些还免不了有强加于历史的见解和不恰当的比附”(39)田余庆:《历史主义无罪:为纪念翦伯赞教授而作》,载《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6—77页。。对此,治学严谨的翦伯赞事后也作出了检讨,他于1952年说道:“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40)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9月号。
尽管如此,翦伯赞南明史研究仍旧瑕不掩瑜。他在极其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始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阶级分析法剖析历史现象和社会阶层,巧妙地借古喻今,深刻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衬托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与坚韧精神,将史学的现实功用发挥到了极致。在民族危机深重,阶级斗争激烈,政治压力巨大的年代,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充满着创造力和学术活力。他们身为儒雅文人,却活跃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化手中的笔杆为长枪,把历史文章作炮弹,“尽可能大的打击敌人的威力”,“千方百计地把历史同政治斗争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41)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页。。这是其迫切的历史使命感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翦伯赞的南明史研究注定因其强烈的现实意义,而成为独特的史学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