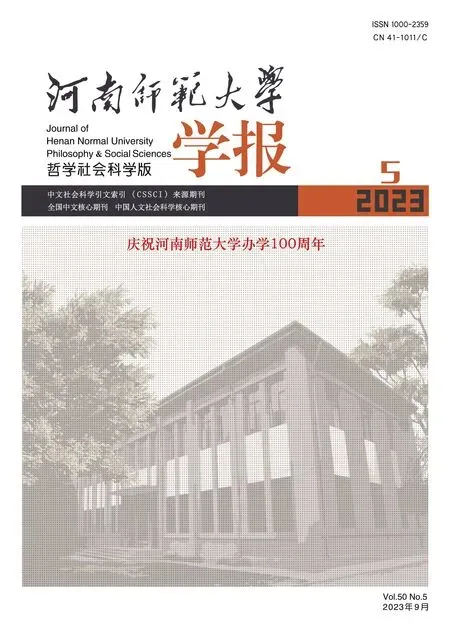“以类取,以类予”是归纳和演绎吗?
2023-03-09李亚乔
李 亚 乔
(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7)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在《周易》等古代典籍中就有体现,并于先秦论辩背景下达到顶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哲学思想的传播特别是西方传统逻辑体系的引入,国内掀起了重新审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热潮,伴随而来的是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累累硕果。针对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既难免受西方传统逻辑体系思维方法的影响,又亟须重塑中国古代逻辑推理的内涵特征。研究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过程既要权衡两种逻辑思想的特征又不失本土思想的特殊性。因此,找到能够突显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本质的思想理论并加以研究是必要且有效的着眼点。
“类”范畴一直是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类取,以类予”是“类”范畴研究中的关键性命题。近代以来,针对这一命题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尽相同,但多数学者认为其中体现出演绎和归纳的西方传统逻辑推理思想。比较一般的观点是,“以类取”表示从具体到一般的归纳推理,“以类予”表示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推理。我们认为,在对“以类取,以类予”古代汉语意义进行考辨,并完成对《墨子》文献资料的考察后,可以得出其本身并未包含任何归纳和演绎内涵的结论。
一、“以类取,以类予”“归纳”“演绎”说的由来
明确提出“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的归纳或演绎推理的观点较早出现于梁启超等学者的文献中。梁启超在《墨子学案》(1921年)中分析“夫辩者”一段时认为:“‘以类取’二句,是归纳法的要件。”(1)梁启超:《墨子学案》,中华书局,1938年,第96页。后又在讲到“推”式推理时说:“此条便是上文总论所讲的‘以类取,以类予’,是讲归纳法。”(2)梁启超:《墨子学案》,中华书局,1938年,第124页。在介绍了西方传统逻辑归纳法之后,他又借助例证对“以类取,以类予”进行分析:“取是举例,予是断定。何谓以类取?看见玻璃杯在这种条件之下结露,玻璃窗、墨盒、树叶都是在这种条件下结露,凡属同条件的都引来做例证,便是‘以类取’。何谓以类予?把同类的现象总括起来,下一个断案,说道‘凡传热难散热易,本体比周围空气较冷的东西和那含水分太多遇冷物变成液体的空气相接触一定要结露’,便是‘以类予’。”(3)梁启超:《墨子学案》,中华书局,1938年,第140-141页。由上述举例可见,梁启超认为“以类取,以类予”就是“推”式推理,并把归纳推理分为例证与断定两个部分,“以类取”是取证的部分,而“以类予”是把前一步的例证进行总结,两者合二为一组成一个完整的归纳推理。
胡适的相关研究比梁启超稍早一些,胡适在《墨子新诂》(1917年)中认为:“名实合而成辞,合辞而成辩说。其综合之法,要不外乎‘以类取,以类予’而已。《大取篇》云,‘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即此意。有所选择之谓取,有所是可之谓予。于动物之中择牛马,是以类取也。曰,‘牛马,皆四足兽也。’是以类予也。”(4)胡适:《胡适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64页。由上述引文我们可以知道,胡适认为“以类取,以类予”是辩说的重要法则,“以类取”如同在动物之中选择牛和马,“以类予”是把牛和马断定为四足兽。在同时期的著作《墨家哲学》(1918-1919年)中,胡适又对“以类取,以类予”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取是‘举例’,予是‘断定’。凡一切推论的举例合断语,却(都)把一个‘类’字作根本。……在万物中单举‘瓶’和‘声’相比,这是‘以类取’。”(5)胡适:《胡适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5页。上述两段话中,胡适没有明确指出“以类取,以类予”的具体推理性质,但从其所举例证来看,他与梁启超的解释基本一致,即从“举例”和“断语”两方面展开分析,以说明“以类取,以类予”具有归纳性质。
郭湛波的看法与梁启超基本相同,他认为:“‘以类取,以类予’。这是论理学所谓归纳的方法。亦即墨辩所谓‘推’的方法。”他接着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他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这就是归纳的方法。”(6)郭湛波:《先秦辩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03-104页。可见,郭湛波认为,“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推”,与归纳的方法一致。
上引三位学者都认为“以类取,以类予”指的是归纳,不过,也有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杜国庠在分析《小取》篇“夫辩者”一段时,认为其“规定了概念(‘以名举实’)、判断(‘以辞抒意’)和推理(‘以说出故’)的意义,有演绎也有归纳(‘以类取,以类予’)”(7)杜国庠:《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553页。。伍非百认为,“以类取,以类予”代表了“类行”的两个原则,“类”指的就是“类同”。“‘类取’,谓就其有以同者而取之也。‘类予’,谓就其有以同者而予之也。例如就‘白人’‘白马’‘白羽’‘白雪’而取其‘白’之一点,是‘类取’也。就‘凡白者必白’一例,而以‘在外者之色若是其色’,而因谓之白,是‘类予’也。”(8)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5页。由此可见,在“类行”原则的支撑下,“以类取”是演绎,“以类予”是归纳。
周云之的分析更加突出类比推理的作用,他认为:“‘以类取’可以理解为‘以类取其同’的意思,即从类的观点进行归纳以取其同(共同特征或本质),它反映了由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所以,把‘以类取’理解为墨家有关归纳逻辑(方法)的思想,是符合墨家逻辑的思想体系的。”“‘以类予’就是同类相推或同类推其同。这种方法相近于普通逻辑中的类比推理,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墨辩的‘以类予’则是已知甲乙属同类(具有作为类同的共同属性)进而由甲真推知乙真,由甲假推知乙假。因此这种推论在逻辑上则往往具有必然性。所以‘以类予’的方法带有很大的演绎性质。”(9)周云之:《论墨家“以类取”和“以类予”的推理性质和推理形式》,《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6期。因此,在周云之看来,“以类取”是归纳而“以类予”是具有演绎性质的类比。
综上所述,自梁启超在《墨子学案》中认为“以类取,以类予”是归纳推理之后,许多学者的观点与之一脉相承,或是认为归纳或是认为归纳、演绎并用。他们按照形式逻辑的推理方式进行解析,并通过举例证明其结论。这些分析有益于西方逻辑在中国的深入传播,也使中国传统逻辑思想被更多外国学者知晓。但其是否符合墨家逻辑的原貌,能否体现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维精髓,需要进一步论证。
在前文梁启超的相关论述之前,他细致描述了归纳逻辑的推理原理,以此作为背景来探讨“推”,使用完全符合归纳逻辑特征的推理例证进行解释。他所举的“玻璃结冰”的例子完全在归纳推理的形式下展开,分为举例和总结两部分。他着重强调“以类取,以类予”与归纳推理原理的相似性,最终确定“以类取,以类予”的归纳推理性质。整个讨论预设了其为归纳推理的前提,推论过程与“以类取,以类予”的直接关系不够清晰,不能准确表达“以类取,以类予”的实际所指。这种分析形式是西方传统逻辑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学者思维过程形成影响的直接产物,是“西学东渐”之后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渗透的具体表现。这种渗透的结果通常表现为,以西方思想为蓝本,对照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有与之相似的部分。比较外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的相似性是一种外来思想在传入时期的必要研究方法,它能使该思想更易于被理解被接受。但随着研究深入,只注重相似性而忽略特殊性的比较往往使本土思想的本质被隐蔽。在此背景下对《墨辩》研究的热潮中,墨家思想中的诸多要素及内容都留下了与西方传统逻辑对比的痕迹。“以类取,以类予”作为墨辩思想的重要命题,也成为众多学者对比的对象,认为其为归纳、演绎推理的各种讨论逐渐隐藏了该命题的本来面貌。这种借助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思想的做法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更要从利弊中总结得失,为新时期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提供坚固的理论基石。
二、“以类取,以类予”的文字考辨
梁启超等学者的相关讨论,没有以古汉语为背景对“以类取,以类予”进行详细的文字考辨,有些解释很大程度上受到现代汉语的影响。这种方式对于研究逻辑史来说是不够严谨的,所作出的断定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如何在古代汉语的语言背景下分析该命题是至关重要的。“类”在该命题中的使用基本没有引起太多异议,关键在于对“取”“予”二字的准确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更符合“以类取,以类予”本意的结论。
《说文解字》:“取,捕取也。”段玉裁注:“捕罪人也。”“取”的原始涵义主要有抓、抓取的意思。它可以单指“抓”的动作,但更主要的是强调“抓”的结果。《汉书·贾谊传》:“为主人计者,莫如先审取舍。”颜师古注曰:“取,谓所择用也。”“择用”显示了“取”字目的性与动作性相结合的特点。《墨子·经下》云:“知其所知、不知,说在以名取。”“名”在这里指的是概念。人的一生中总有自己知道的知识和不知道的知识。这是把概念的“知”运用到实践中,把概念作为媒介进行断定,究竟哪些是自己知的、哪些是不知的。《墨子·贵义》中还有一例:“子墨子曰:‘今瞽曰:钜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黑白,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此段文献中,墨子认为盲人是能说出什么是黑或白的,但把黑与白的东西混在一起让他判断时,他无法作出正确的选择。以此来说明:有些时候知道了“名”却无法“以其取”,即无法作出断定。分析上述与“取”有关文献之后,我们认为,“以类取”较为精确的涵义应该是,用“类”作基础,进行选取并作出断定或证明。
《说文解字》:“予,推予也。”段玉裁注:“象以手推物而付之。”可见“予”从动作方向来说与“取”正好相反,是从己到外的过程。而强调的结果是把己方想要达到的目的“付”之对方。《小取》曰:“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这段话点明了“取”的断定意义,同时强调了“予”是我方对敌方的反驳。《墨子·尚贤中》:“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这里“予”明显是给予、授予的意思,突出动作由我方到他方的方向性。《墨子·鲁问》中还有一段话中涉及“予”:“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墨子对公输子说:我没见您的时候,您想得到宋国,自从我见到您之后,我以不义的方式给您宋国,您不要,这就是我给了您宋国了。您追求道义,我还要给予您整个天下。针对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以类予”是对“以类取”的反面说明,即把以“类”为基础作出的断定给予对方,可以是说明己方观点也可以是反驳对方的观点,但在实际论辩中更突显反驳的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从古汉语考辨的角度,“以类取,以类予”表达的是以“类”为基础,从己方角度作出判断,同时把该判断用陈述或反驳的方式传达给对方。可以看到,其中并没有显示其包含了与传统逻辑的归纳和演绎等推理形式相近的内容。
三、“以类取,以类予”的文献解析
以文字考辨为基础的文献解析是思想史研究过程中的基础与根本。现当代一些学者意识到,一味寻找与西方传统逻辑相似性的研究方法存在弊端,开始回归文献本身,把重心转向彰显中国本土逻辑思想独特性的研究中。在这个过程中,多数论述在分析《墨经》原文的基础上展开,围绕墨辩思想的论辩环境阐述推理。比如章士钊认为“以类取,以类予”就是推类,他说:“推类者,原语为class-inclusion。此义如其文,率以谓词为一类名,主词属焉。《小取篇》曰:‘以类取,以类予。’即指是。”(10)章士钊:《章士钊全集》,第7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404页。可见,章士钊认为《小取篇》此二句就是推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谭戒甫也认为“以类取,以类予”表达了依“类”而推的方法。他在《墨辩发微》中说道:“例如《经上》第五条:‘知,接也。’《说》云:‘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此之论‘知’取‘若见’以为譬者,以‘见’‘知’皆具有‘过物能貌’之一法;则‘知’与‘见’为同类,故取‘见’以喻‘知’:此即谓之‘以类取’。又‘见’既有‘过物能貌’之性,则‘见’者‘接’也;因而推得‘知’亦有‘过物能貌’之性,则‘知’亦‘接’也:此即谓‘以类予’。”也就是说,若甲与乙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甲与乙同类,这是“以类取”;因为甲与乙同类,那么甲具有的另一个性质,乙也应该具有,这就是“以类予”。章士钊与谭戒甫都认为“以类取,以类予”指依“类”进行推论,这种分析显示出“类”范畴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核心,符合该命题的理论环境。基于思维的逻辑工具与语言密切联系的原因,温公颐曾认为:“墨辩的‘类取’和‘类予’虽是演绎和归纳并用,但它并不依于三段论或归纳五法进行。”(11)温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6页。他虽没有对“类取”和“类予”作进一步说明,但仍指出探索墨家逻辑思想不能依附于西方形式逻辑。
汪奠基更直接指出,把“以类取”理解为归纳、“以类予”理解为演绎是一种仅供参考的理解方式,而另一种理解方式为:“一方面取同观异、求同异的辩证理由,是为类取;另一方面,依类为推,过物,则予以断定,是为类予。”(12)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9页。也就是说,“以类取”是辨别事物同异的支撑,而“以类予”是以明晰类同、类异为核心的断定。这种分析反映了国内学界思考方式的复杂性,既无法抗拒西方逻辑思想的影响,又要考虑彰显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应有的地位。此后,一些学者提出更加鲜明的观点,比如孙中原在论及墨家讨论思维形式和规律时认为“以类取,以类予”是证明与反驳所要遵守的原则。他说:“《小取》说‘以类取,以类予’,即‘取’例证明和‘予’例反驳都应遵守同类相推的原则,不然会引起矛盾。这是形式逻辑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应用。”(13)孙中原:《中国逻辑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5页。刘培育也持相似的观点:“‘以类取’是证明,‘以类予’是反驳。‘取’是自己主张的或所同意的观点,‘予’是自己所不同意的观点和主张。”(14)张家龙:《逻辑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这些主张的本质是从墨家思想的实践性出发,充分考虑论证在论辩环境中呈现的两种形式,即证明与反驳。
上述学者的观点几乎都认为:“以类取,以类予”是运用到推理实践中,以强调通过“类”进行论断和证明的总则。具体说来,第一,这些观点都显示出了“类”在推理中的重要地位;第二,这些观点围绕“类”范畴进行分析并展示,“以类取,以类予”是依类而推的宏观说明;第三,“以类取,以类予”是运用到论证实践中的一条原则,是适用于证明和反驳的思维准则。这种分析合乎墨辩“以类行”的规定,契合墨辩逻辑以“辩”为核心的中心思想,也接近“以类取,以类予”的本质。
这些贴近墨家思想本质的讨论有助于我们使用更加清晰的思路来重新审视“以类取,以类予”所在的《墨子》文献。墨家的逻辑思想在近代以来的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墨辩”,而墨辩思想以“辩”为核心,强调立、敌双方进行争论以获得对方认可的过程。对范畴等诸要素的分析都应该以论辩为背景。既然是论辩环境下的研究,就必然会产生证明与反驳、立论与驳论的问题。“以类取”是以“类”的原则进行断定和证明,“以类予”是以“类”的原则进行反驳。可以说,“以类取,以类予”是墨家辩说的两种基本方式,这两种基本方式因其本质而成为约束辩说的一条原则。我们认同用“推类”或者“类推”理论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代表,这一研究已有较多成果,不再赘述。 “以类取,以类予”突出了“类”范畴的重要性,是推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总之,“以类取,以类予”既是论辩实践中应该充分强调的一条原则,也凸显了“类”范畴在推类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墨辩·小取》云:“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此段为《小取》篇的开篇之语,内容十分丰富且为《小取》篇的精华。“夫辩者”意在强调该论述是围绕论辩实践而展开,这是我们讨论的前提。接下来六句讲的是“辩”的目的,“摹略”二句指的是“辩”的准备工作,之后三句是“辩”的构成部分或环节,最后四句则是讲“辩”的要求。“以类取,以类予”所在四句强调在“辩”的过程中要遵守的规则。其中后两句“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是从道德角度来约束,旨在强调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以类取,以类予”是论辩推理可以顺利进行的规则保证,也就是要用“类”为根据作出判定,同样以“类”为根据对对方进行反驳并使其明白我方观点。众所周知,印度因明思想也体现在论辩实践中,“自悟”与“悟他”是因明“两益”,表明在因明思想中让自己明白、觉悟与使对方明白、觉悟一样重要。“以类取,以类予”这个命题前半句强调首先要自己明白,后半句强调让对方明白,它不仅体现了“自悟”与“悟他”在论辩中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突出了“类”范畴在推理实践中的核心作用。此处,显示了两个东方文明古国的思维契合之处。总之,能够代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推类理论是受“以类取,以类予”影响的,“以类取,以类予”因其强调“类”的重要作用而精确表达了中国古代推类理论的精髓。
四、“以类取,以类予”的例证与应用
我们从《墨子》文献的角度分析了“以类取,以类予”的理论意义及其与推类理论的相关性。下面我们将从具体论式的角度,用《墨子》文献中的具体例证来展现“以类取,以类予”是如何贯通墨辩思想的。墨辩主要推理方式有“效”“辟”“援”“侔”“推”“止”“或”等,这几种论式的具体使用都受到“以类取,以类予”这一论说方式的影响。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推理论式进行分析更有助于探究该命题在具体论辩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与价值。
效:“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效”是按照法则去做,若辩论的论题与法则相符合,那就是“中效”,为“是”,否则就是“不中效”,为“非”。这里,“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是“以类取”,意为我方针对一个命题是否“中效”有所判断;“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是“以类予”,意为若对方的命题是“中效”则我方无需进行反驳,若对方的命题不“中效”就要反驳其论点。《墨子·公孟》记载了墨子与程子的对话: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儒固无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程子无辞而出。
上述例子中:
“类同”原则:若A不是B,而我说A是B,这就是“毁”;若A是B,而我说A是B,这就是“非毁”。
我方断定:儒是有此四政的,而我说儒有此四政,这是“非毁”。
我方反驳:你认为的“儒是有此四政,而我说儒有此四政,这是‘毁’”,是错误的。
此例证很好地展示出“效”式论式对“以类取,以类予”的贯彻。对于该种论式的性质,詹剑峰从三段论的角度把“效”者作为小词、“所效”者作为大词进行分析,认为“效”具有演绎性质(15)詹剑峰:《墨子及墨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说效式推论的中效式是传统逻辑三段论第一格,不中效式是三段论第二格,这是缺乏理论根据的”(16)董志铁:《名辨艺术与思维逻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第202页。。
“援”在《墨子·小取》中的定义是:“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意思是,我方认为:你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也就是说,引用对方赞成的观点,证明其与我方的观点是同类,以此论证我方观点的正确性。这种推理论式显然是以类同相推为核心的。《墨子·公孟》还有一例: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日之丧亦为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日之丧,是犹裸谓撅者不恭也。”
在上例中从公孟子的角度:
“类同”原则:若A与B同属于时间,A之丧为非,那么B之丧为非。
我方断定:你认为三年之丧为非,那么你也应认为三日之丧为非。
我方反驳:你不认为“三日之丧为非”,是错误的。
这是“援”式的运用,也体现了“以类取,以类予”的推理方式。后面墨子又使用辟式推论进行反驳,认为对方以“三年”反驳“三日”犹如“裸身”反驳“掀起衣角”一样不合适。刘培育认为:“援式推论是以类同为前提,从个别推出个别的类比推理。”(17)张家龙:《逻辑学思想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9页。援式推论是一种类比推理得到了学界的基本认同。
“推”通常用于反驳对方的论点。《墨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这里是说,选择一个与对方论点同类的而对方又否定的观点,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而否认其论点。此论式是一种以“类同”为基础进行推理的或然推理,是与传统逻辑的类比推理所不同的类比推理形式。同样在《墨子·公孟》中有一段对话:
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在上引辩论中:
“类同”原则:无鬼而学祭礼,无客而学客礼,无鱼而为鱼罟,这三种行为是同类。
我方断定:无鬼而学祭礼不能被接受是你否定的,无客而学客礼不能被接受是你肯定的,二者同类,所以你自相矛盾。
我方反驳:你认为“无鬼神而君子必学祭礼”,是错误的。
《墨子·天志下》中还有“推”的运用:
今有人于此,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必曰:“吾目乱,不知黑白之别”。……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杀人,其国家禁之,以斧钺有能杀其邻国之人,因以为大义也,此岂有异蕡白墨甘苦之别者哉?
上引例子中:
“类同”原则:“少示之黑谓黑,多示之黑谓白”与“杀一人被禁,杀邻国人为大义”是同类。
我方断定:你不认可“杀一人被禁,杀邻国人为大义”为乱,你认可“少示之黑谓黑,多示之黑谓白”为乱,而两者是同类,所以你自相矛盾。
我方反驳:你不认为“杀一人被禁,杀邻国人为大义”为乱,是错误的。
“止”也是一种反驳的推理方式。《墨子》书中是这么解释的:“止,因以别道。”“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止,类以行之,说在同。”“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止式推论一般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对方用简单枚举推理得出结论,那么我方可以通过一个与之同类的例子进行反驳。第二种,对方直接使用一个全称肯定判断,那么我方可以用特称否定判断进行反驳。第一种形式是具有演绎性质的归纳推理,而第二种可以得出全称肯定的反面,是一种演绎推理。《经说下》云:
推:谓四足兽,牛与,马与,物不尽与,大小也。
此条《经说》为解释“推类之难”而举例。有人说:四足皆是兽。牛是,马是,但不是所有的四足动物都是兽,属于同类的事物范围有大有小。根据以上分析,在该例子中:
“类同”原则:牛、马以及其他某些动物(这里我们可以“兔子”为例)都是四足的。
我方断定:兔子是四足动物但不是兽,所以不是所有的四足动物都是兽。
我方反驳:你认为的“四足皆是兽”,是错误的。
可以看出此例证是“止”式第一种情况的应用。
上述几种典型论式的推理过程始终贯通“以类取,以类予”这一原则。其中,有些论式是归纳有些是演绎,有些复杂的论式需要分不同情况进行讨论。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第一,“以类取,以类予”本身不指示任何推理规则的具体内容,而是墨家辩学推论的两条基本方式或原则。在这条原则的引导下,先秦诸子的论辩思维更加有条理且更具规范性。第二,若是分析辩说的具体论式,因其具有不同的推理性质,所以无法概括地说是归纳还是演绎推理。所以,无论是从总体的角度来展示“类”的应用,还是具体到文献中描述的论辩实例,都无法简单、直接地得出“以类取,以类予”指的是归纳和演绎的结论。总之,对“以类取,以类予”的理解绝不能脱离先秦逻辑思想所处的诸子论辩背景,而要置于先秦诸子双方论辩对立的情景之中,感受先秦诸子论辩的智慧和立论、驳论的逻辑思维体系。
五、结论
中国古代的推理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它是以“类同”思想为基础引导前提推出结论的过程,这种推类理论贯通了整个中国思想史。从孔子的“有教无类”到荀子的“类不悖,虽久同理”,从墨子的“察类明故”到后期墨家的“辞以类行”,从“推类之难”的研究到连珠体的盛行,等等,都展现出推类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影响的广泛性。以“类同”为基础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核心不同于西方形式逻辑有关“有效性”的研究。形式逻辑旨在研究真的前提得不出假的结论且符合绝对形式要求的推理体系,而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代表的墨家逻辑却深受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论辩的时代背景影响,既无法抛开论辩的整体环境,又要顾及百家思想的不同学术理念。因此,这种论辩并非对“真”与“不真”的争辩,而是对“当”与“不当”的考量。也就是说,论辩过程的合理开展离不开相关条件的规范性约束,当条件具备且符合双方论辩及学术背景时,所得出的结论才能被对方接受并信服。所以,离开先秦逻辑思想盛行的论辩大环境及诸子百家争论观点背后的真实内涵都无法真正理解中国逻辑思想产生的土壤及其发展的轨迹。
“以类取,以类予”因其明确地强调“类”的总纲意义,对中国思想史上“辩”的实践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类取,以类予”与“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一个从原则角度,一个从道德层面,约束了“辩”的构建,两者都以总则的形式呈现,从宏观上指导论辩的进行。“以类取,以类予”并不包含归纳和演绎这些推理形式的意义,而是推理过程中对“类”使用的总称,或者说是“推类”理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墨家辩学理论基本且重要的两种推理方式,支撑着“辩”的形成过程。这两句话如同因明中的“自悟”与“悟他”,不涉及具体的内容但体现了印度逻辑的思维核心。它如同一个标识,表明墨辩逻辑不同于其他逻辑形式的关键所在:只有在“辩”的环境下以“类”范畴为思维根基,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掌握墨家的逻辑思想,才能深达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