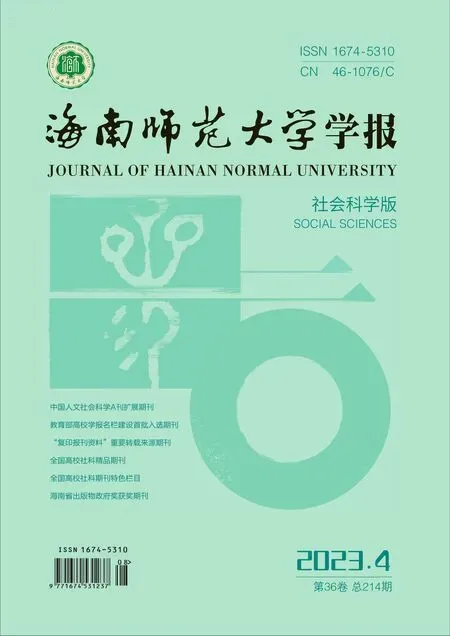欧阳江河1990年代诗歌的意义生成机制
2023-03-09范云晶
范云晶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谈论1990年代诗歌,特别是谈论语言的相关问题,欧阳江河是不能、也不应该绕过的重要诗人之一。这是因为他的诗歌和诗论都具有典型的“90年代性”——综合性、叙述、中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词语等等,不仅是打开欧阳江河诗歌的密钥,更是观照乃至重审90年代诗歌的关键词。①90年代诗歌中的许多关键词都与欧阳江河的诗论或诗作密切相关。参见陈均:《90年代部分诗学词语梳理》,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90年代备忘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95-404页。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些所谓关键词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研究者在重返“90年代诗歌”现场时,仍然要借助这些词汇。具体参见张桃洲:《重审1990年代诗歌的意识与观念》,《当代文坛》2022年第5期。在这些关键词中,与诗歌写作和诗歌本体关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词语”。它是欧氏诗歌表意范式生成的电码母本,研究者也多从“词语”入手,探究其90年代乃至整个诗歌的创作概貌。②较为典型的有毛靖宇、蓝棣之:《先锋诗歌“词语的诗学”研究——以欧阳江河为个案》,《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刘旭俊:《玻璃的诗学——欧阳江河诗歌中的“反词”修辞》,《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3期;敬文东:《词语:百年新诗的基本问题——以欧阳江河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上下篇),《东吴学术》2018年第3期、第4期;张清华:《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有一个引领者——欧阳江河印象》,《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等。当然,“词语”只是进入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场域的第一步,用这一有效工具撬起诗歌的内层肌理,进而挖掘隐在的深层诗学问题,似乎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欧阳江河,以及其所在场的90年代诗歌。
这里所说的深层诗学问题具体为:“词语”是如何成为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理解的钥匙”,诗人又是如何调度“词语”,如何建立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最终生成意义?深层诗学问题关乎由词语抵达意义的运作方式和词语生成意义的运用效果,也就是意义生成机制问题。只有充分理解这一问题,才能对欧阳江河诗歌中的词语,以及由此生出的“词语诗学”有着更为深入的认知。如欧阳江河90年代代表性诗集所命名的那样,需要“透过词语的玻璃”①欧阳江河:《透过词语的玻璃》,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具体到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创作而言,意义生成机制主要有“非诗”词语的跨语境运用、“物质性”对于语义的反哺与填充,以及“矛盾修辞法”。借助此三者,诗人完成了“词”与“物”的异质性碰撞与意义的多层叠加,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词汇的扩展”和意义复合度的生成,欧氏“词语诗学”也由此生成。
一、“非诗”词语的跨语境运用
如何圈定欧阳江河的90年代诗歌,是本文展开论析的起点。诗人自述其创作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4年《悬棺》开始一直持续到1993年去美国;第二阶段从1993年到1997年;第三阶段从2008年恢复诗歌写作开始。②欧阳江河:《消费时代的长诗写作》,《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结合诗人上述说法,本文论及的90年代诗歌创作应该包含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内。具体从90年代的哪一年算起,需要进一步辨析。因为在新近的访谈中欧阳江河这样说:“我的1980年代有一个延长期,一直延长到1993年。那一年,我离开中国去美国,这之前我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归并入1980年代。”③欧阳江河、何平:《个人与文学史的延长线 ——关于欧阳江河四十年诗歌写作的对谈》,《天涯》2021年第4期。按照诗人的上述说法,似乎1993年应该算作诗人90年代写作的真正开端。但是在2010年的另一访谈中,诗人又说:“《快餐馆》(引者注:此诗创作于1989年)就已经基本上具有我90年代写作的特征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开始更注重引入叙述性,但不是叙事,叙述不一定就必须要叙事”④张学昕、欧阳江河:《“诗,站在虚构这边”——诗人欧阳江河访谈录》,张学昕:《我们内心的精神结构》,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96页。。或者是由于诗人对自我创作认知的变化,或者是写作实践与写作观念之间的差异性,抑或看待问题角度的不同,诗人对其诗歌“90年代”属性的阐述前后存在矛盾。本文论及的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在兼顾断代史时间规定性的同时,更多是以诗歌本身精神内质和写作技艺具有的“90年代性”为依据。按照这一思路,《快餐馆》应当是观照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的恰切起点。
《快餐馆》是一首难以用几句话、几个关键词概括的诗。诗中一句话恰好能呈现全诗的“杂”与“乱”:“风中的快餐馆没有头绪被吹起”⑤欧阳江河:《如此博学的饥饿:欧阳江河集1983—2012》,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2页。以下所引此书诗句,不再另注,只在所引诗句后标注页码。。但是如果沉入文本,还是能够于零乱无序的意义线团中,拉拽出几根关键线头。诗歌以“近处的实在和实存空间”⑥笔者将1990年代诗歌“空间词”语义指向分为四种空间,近处的实在和实存空间是其中一种。具体参见范云晶:《词语作为开端——20世纪90年代诗歌表意方式之一》,《新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快餐馆为题,看似是从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的小空间生发的言说,实则因这一“空间词”具有“非确指特征”,以及时空延展所带来的开放性和多变性,而生出意义的多向度展开可能。⑦详细论述可参见范云晶:《词语作为开端——20世纪90年代诗歌表意方式之一》,《新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作为言说“开端”的“快餐馆”也必然会发酵出多种意义的益生菌。
《快餐馆》意义线头之一是作为“公共空间”的“餐馆”。其“公共空间”特质引发诗人对人际关系、众生百态的关注;其“餐馆”功能则导出诗人对“饱腹”和“饥饿”及引申问题的思考。比如“年龄透过裙子,轻轻提到腰际,/徐行或静坐时下垂,礼貌起了皱褶”(第53页),“饥饿疗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紧身之美”(第54页)。意义线头之二是以“快速”和“便捷”为主的“快餐”特征。诗人从此角度生发出对速度——生的缩短与死的加速度的理性思考。比如“把拿破仑和人头马搅混在杯中,/给乏味的午餐增添一点死亡的加速度”(第55页),“死从来是一种高傲,/正如我们无力抵达的老年”(第57页)。意义线头之三是“快餐馆”作为“现代空间”的“现代”特征,引发的是诗人对“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思考,以及对“当下”的现实本身与精神困境的省察。三个时间维度关乎传统与现代,更是与人的生命历程一致;“当下”则更多是对融汇了科技与进步、金钱与财富的所谓“文明”的理性审视,比如诗句“瞧那些代用品,那些进餐时闪闪发光的/假牙和餐刀,我们时代的局部骄傲”(第54页),“我们这一代/真的能抵达老年吗?真的那些维生素/能缓解时间,把高消费的夏季/变成慢动作的青春?”(第57页)意义线头之四是“快餐馆”作为诗歌写作和隐喻层面的空间。诗人更多表达的是对“快餐式”写作的警惕与省思:只追求速度、直接的快捷写作方式和思考方式,无法、也不可能真正触及“噬心的时代主题”(陈超语)。因为“对这一切的询问,仅有/松懈的句法,难以抵达诗歌”(第52页)。
上述论及的四条意义链杂糅、混合在一起,搅拌成“意义的浓汤”,凸显了该诗的“综合性”。以下诗句能够更鲜明地体现这种意义的综合:“文明的全部含义在于预制和搭配。/我们被告知饮食的死亡是预先的,/不可逆的,它支撑了生存/和时间。动词的时态掺和到食谱当中。/动物的内存,墨水的血,刀捅进语言的心脏时/身体的尖叫,蛋白和脂肪,所有这些/搭配在一起。遗忘和消化混而不分。”(第54-55页)这一“综合性”的获得,主要仰仗于诗人将“非诗”领域词语强行投入到诗歌之瓮中。比如“假牙”“牛排”“闪闪发光的餐具”“货币”“铸造金属”,再比如“动物的内存”“墨水的血”等等,这些看似都与诗歌没有直接关系。欧阳江河称其为“非诗性质的词汇”①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这些词汇本应在其应在的语境之中,比如货币、纸币、股票属于财经语汇,餐具、牛排属于餐饮语汇等等,但它们跨出了“舒适区”,挤入诗人为其量身打造的陌生环境之中。不同于天然带有诗意因子的词语②比如月亮、春天、雪花等等。,这些词语本身携带的异质性,必然会造成“诗”与“非诗”、“诗意”与“非诗意”的“对冲”与“耦合”,看似不谐和,却可以帮助诗人增加面对庞杂事境的言说的有效性。同时,表意效果方面也会形成对语义的偏离。③关于语义偏离问题,笔者有专门论述,具体可参见范云晶:《语义偏离——20世纪90年代诗歌表意方式之一》,《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偏离·繁复·精确——论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特质》,《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6期。关于这一点,诗人西川在论述欧阳江河时专门提及:“在英国反乌托邦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等人的启发下,他大胆闯入了从前诗歌的道德禁区和文化语汇的禁区,给诗歌注入了大量的非诗因素——权力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使其作品内部形成一种对于诗歌的偏离”④西川:《认识欧阳江河》,《让蒙面人说话》,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94-195页。。
不只是《快餐馆》,欧阳江河具有显豁“90年代特征”的很多诗歌文本皆是如此。比如《咖啡馆》《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另一个夏天》《纸币,硬币》《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饥饿》《雪》《时装街》等等。仅从上述诗歌题目上看,除了“雪”与“另一个夏天”是常规诗歌题目之外,似乎其他都是对“非诗”词语与事物的诗性言说。这里所说的“诗性言说”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借助浓烈抒情、美好意象等生成的诗意,而是指以诗歌的方式言说,这也是欧阳江河诗歌的典型特征。需要说明的是,欧阳江河具有鲜明“80年代性”的诗歌比如《玻璃工厂》等也存在“非诗性质词汇”的运用,但更像是将“诗”安插在“玻璃工厂”之中,而不是“玻璃工厂”被移植到了“诗”中。而且,从意义的复杂程度和跨语境的综合性角度看,与90年代诗歌相比还有很大的不同。
“非诗”词语的跨语境运用大致通过两个步骤来完成。一是,将“非诗”领域的词语移植到诗歌领域。比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饥饿”“睡眠”“晚间新闻”等等,这些原本无法被诗意言说的语汇,在诗人的悉心调教下,拥有了诗意言说的超常本领。“非诗”领域的词语不是表演独角戏,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展言说的广度与深度,诗人还会将诗歌语汇与非诗语汇、同一领域非诗语汇、不同领域非诗语汇加以勾连,营造出释放意义的最佳语境,从而将意义引向更为广博的空间。二是,将这些“非诗”领域词语所可能涵括的意义向度,同步移植并填充到诗歌之中。与第一步的复杂性一样,意义的移植同样不是同一领域、单个词语的单一意义的移植,而是不同领域、不同词语的意义多维度扩展。被强行塞入诗歌的物象和事象自身可能隐藏的意义向度,与诗人在诗歌中呈现的对其他问题的言说,形成一种互文性:谈论A就是在谈论B,反过来亦是如此。比如在诗歌《马》和《雪》中,诗人是在谈论“马”和“雪”,亦是在谈论语言观念。当然,欧阳江河的诗更多是物象和事象本身隐含的多重意义向度的互文,上述所列举的《快餐馆》至少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便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不妨简要分析《雪》一诗来深入理解此问题。该诗以“雪”自身所携带的时间感和寒冷感,以及诗人因身处异域而生出的空间感和孤独感为言说基点,看似是基于“雪”本身,却又远远超出于此。在诗歌的开头,超过作为现实之物的“雪”的意义延展可能就已经呈现:“雪深深落下。/雪落下因为到达了某个平面:不仅在纸上。/一些消除了见解的神秘读音萦绕不散,/词与事物的接触立即融化了。//这些害羞的点滴,没有从乡愁溢出。/器皿对器皿是多么软弱,词也是软弱的。/眼前这片景色像桌布一样抖动”(第149页)。这首诗从作为物质的雪起笔,第二句就转向了非物质意义上的雪。从整首诗看,“雪”至少延展出以下意义向度:对时空的体认,比如“雪将以夏天的样子被记住。/中年:一条终于松开的绳子,/双手从长满皮毛的事实缩了回来”(第158页)以及“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擦身而过”(第156页);词与物的关系,“词与物的片刻接触产生了分离的正面”(第155页)和“事实变轻了,词却取得了重量”(159页);人对物的强势命名现状以及对色彩的辩证性认知,“墨水在乌鸦身上站着,放弃了公众的雪/而更多的蝴蝶被强加给一只蝴蝶”(第157页);对语言的地方性的思考,“事物的公正性深深植根于本地口音”(第157页);还有乡愁以及语言观念等等。从上述尚未完全列举的意义向度可以看出,除了“乡愁”具有诗歌母题特征之外,大部分意义走向都属于非诗的范畴。而在诗人刻意塞入多重意义过程中,原本天然携带诗意因子的“雪”,已经远非诗意所能涵盖。其意义的涵容,早已溢出了词典意义的“雪”与诗歌中习见的“雪”的边界。
“非诗”词语跨语境运用生成的意义主要通过“叙述”这一行为来实现。“叙述”是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最显豁也是最重要的表意手法,侧重于“说的过程”的呈示,更具有敞开性,其诗歌的综合性、意义的多元扩展很大程度上都是仰仗于此。经由“叙述”,欧阳江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词汇的扩展、意义的变奏,以便实现意义领地的扩张。当然,因“非诗”语汇大量涌入诗歌所造成的“非诗性”问题,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存在。钟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直接逼近社会命题和哲学确实是他特色之一,但也正因为如此,知识层面所服从的罗各斯与同一性也就势在必行。道理很简单,现代思维的直观性和逻辑性支配着我们。如果,诗歌要非诗的知识入伙,那就得带入非诗知识的规律。”①钟鸣:《旁观者》第2册,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910页。
二、“物质性”对语义的反哺与填充
一般而言,词语的意义大致由词典意义(系统意义)和外指意义两部分组成。这其中,词典意义相对恒定,外指意义则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就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而言,外指意义的扩容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曰词与词的勾连,即由不同词语之间勾连而生出新的意义,A词与B词的意义彼此进入,互相填充,意义均得到扩展;二曰词与物的勾连,可能是A词所指的A物的意义进入A词,也可能是A词所指的A物的意义进入B词,词语的意义得以丰富。抛开因语境变化所可能生出的外指意义不谈,两种意义扩容方式的区别在于:作为能指的词的内涵相对固定,且相对抽象,具有限定性和规定性。而作为词的所指的物则因其具有形象性和具象性等特征,更易于被感知,也就更易于激发人们对其的敞开性想象,从而获得丰富的意义。比如,作为词的玫瑰特指花的一个品种,作为物的玫瑰则因有其颜色、形态、味道、数量和功能等方面的差异,而引发人们对作为“物”的玫瑰的多种想象。因此,相对于词而言,物对于语义的反哺作用更大。
物具有的、对词义反哺与填充的特质,可以称作“物质性”。关于“物质性”,欧阳江河有自己的解释:“90年代以后,尤其是我出国到了美国以后,我的语言处境发生了变化,我说的是中文,说不了英文,我说的中文,当地美国人又听不懂。我说出的话只剩下了声音,剩下了物质性,意义不在了。我在说,可声音却像鸟儿或动物的声音,谁都听不出什么意思。听见了声音,却听不出意义,声音作为物质的、让人听见的性质还存在,但不可能有意义了”②欧阳江河、王辰龙:《消费时代的诗人与他的抱负——欧阳江河访谈录》,《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欧阳江河在此处所论及的“物质性”,是指在非母语语境中,对话双方无法准确捕捉彼此语音背后的语义,语言本身只剩下表象为声音的物质性。因此,诗人强调的更多是“词的物质性”,即词作为具体物存在本身的特质。本文所说的“物质性”更侧重于“物的物质性”,更多指向“物”本身的复杂。欧阳江河对“物质”与诗歌关系的阐释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水是用来解渴的,火是用来驱寒的——这些都与诗无关,要进入时间就必须进入水自身的渴意和火自身的寒冷。”①欧阳江河:《作者的话》,唐晓渡、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
概言之,本文所说的“物质性”是指词与物勾连,或者词面向物敞开时,物本身的特性、功能以及其因自身性状可能暗含的复杂性,会让渡给词,词的意义因此变得繁杂与多元。这其中又包含两种情况,此词与此物的勾连,以及此词与彼物的勾连。或可称为“词物同向”与“词物异向”两种意义扩展方式。
“词物同向”是指词与其指称的物在基本意义向度和内涵上具有一致性。比如欧阳江河9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诗歌《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傍晚穿过广场》等,虽然会有溢出诗歌边界的词语和意义的大量闯入,但是其意义都与诗歌题目所呈现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广场”有关,或者是由上述词语进一步衍生出的意义。此处以《傍晚穿过广场》为例加以阐说。该诗是欧阳江河90年代最有分量的诗作,涵容丰富、寓意深邃、语调沉郁而内敛。“广场”是进入并剖析这首诗的关键。这里的“广场”首先是作为“词”的基本义存在,“指面积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地”②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88页。。作为“词”的广场有两个意义向度可供延展:由广场的城市属性可以延伸出其现代性特征;由面积广阔的特征可以看出其指称开放的公共空间。以作为词的广场的基本义继续深入和扩展,作为物的广场的意义向度也就生成:“广场”的最基本物质性在于公开空间。这一点和作为“词”的广场内涵一致,具有容纳性和敞开性,亦存在被改造(被改写)、被填充的可能。作为词的广场与作为物的广场意义叠加,作为隐喻空间的第三重内涵亦得以呈现:作为政治空间,暗含神圣、权威、理想、激情、狂欢等意义;作为文化空间,可能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勾连;作为娱乐消费空间,大众性和世俗性则会凸显。通过运用“昆德拉‘轻与重’的对称法”③钟鸣:《旁观者》第2册,第900页。,“广场”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矛盾特质,以及诗人通过赋魅与祛魅的方式,暗含的建构与解构意图也就暗藏其中。通过分析《傍晚穿过广场》可见,作为词与作为物的广场在相同的向度生成意义,然后再共同展开。尽管词与物的意义走向相同,但是这首诗所言说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广场”本身,繁复而驳杂。
“词物异向”是指此词与其所指称的物在基本意义向度和内涵上相异,包括相异,也包括相悖。也就是说,在一首诗中,诗人由A词切题,但是由于A词与B物(可能还有C物以及更多)的勾连,B物的意义进入A词之中,A词已经不再只是A词的能指,也不再是A词的所指,作为词和作为物的A的内质发生了较大变化。“现代诗歌包含了一种永远不能综合的内在歧异,它特别予以强调的是词与物的异质性,而不是一致性。”④欧阳江河:《〈谁去谁留〉自序》,《站在虚构这边》,第201页。词物相异的情况在诗歌《梨子》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词物相悖的情况从诗歌《春天》《雪》中可以看出。
在诗歌《梨子》中,诗人用“雪”将具象之物“梨子”“月亮”和抽象之物“爱情”串联在一起,让四者作为物的特征以及物的意义彼此进入。“梨子与山顶的月亮重叠在一起,/这天鹅绒似的昨夜之恋,/我从中看到了起了变化的物质的修辞”(第103页)。所谓“起了变化的物质的修辞”是指“梨子的长落就像爱情的转瞬即逝、雪的寒冷、月亮的圆满一样,瞬息万变,难以永恒。”⑤范云晶:《现代汉诗“词的歧义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35页。那么,同样可以说爱情的转瞬即逝,和梨子的长落、雪的寒冷、月亮的圆满一样。如此,作为词语的梨子以及所指称的物就具有了作为普通水果的梨子不具有的意义,比如寒冷、比如灼热、比如爱情等等。⑥具体论述可参见范云晶:《现代汉诗“词的歧义性”》,第234-235页。
与《梨子》的“词物相异”相比,诗歌《春天》更多呈现了“词物相悖”。该诗中的意义群主要由两个关键词“春天”和“爱情”组成。诗人首先借用“红色”“黑色”这些与喻指“春天”的“绿色”完全不同的色彩,以及“玫瑰”由最红到最黑,将意义引向了“是春天”与“不是春天”的交界地带——“因为紧握手中的并不是春天”⑦欧阳江河:《如此博学的饥饿:欧阳江河集1983-2012》,第70页。。接着,诗人在表述“爱情”时,用红色的火焰“在白色的恐惧中变得更白”,以及“在垂死者的眼珠里发绿”等不合常理的色彩,最后都指向了“爱情”(第70页)。“那像狼爪子一样陷在肉中的春天的爱情”(第70页)一句,将“春天”与“爱情”勾连在一起。两者更为紧密的关系在接下来的诗行中,经由“饿狼”和“毒蛇”,以及由这两者勾连的“玫瑰”和“火焰”得以建立。也就是说“饿狼”“毒蛇”“玫瑰”和“火焰”作为意义纽带,连接了处于左右两端的“春天”与“爱情”。无论是单独对“春天”与“爱情”的意义指向进行分析,还是将二者结合起来探究都会发现,由于诗人运用了非常规思路与可能走向意义歧境的四个“桥梁词”——其中,“玫瑰”与“火焰”被诗人用色彩变化进行了反向言说,同样有将意义引向歧境的可能——“春天”和“爱情”的意义都背离了自身,也背离了彼此。诗人笔下的“春天”与“爱情”在大致意义上指向了噬心与疼痛,这与原有的作为词与物的“春天”和“爱情”的喻指都相悖。饶有意味的是,两词与原有意义的相悖,又成就了两词在背离之后的意义的一致性,似乎又暗含着“词物同向”之可能。
通过上述对两种表意方法的简要论析可以看出,“词物同向”与“词物异向”并不能截然分开,欧阳江河90年代的诗歌,更多是上述两种方法的混用,比如《快餐馆》《咖啡馆》等等,即使上述论及的两首诗歌亦是如此。词与物的彼此进入、甚至是融合,“它(语言)被置于世上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既是因为物本身像语言一样隐藏和宣明了自己的谜,又是因为词把自己提供给人,恰如物被人辨认一样”①[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7页。。
“物质性”对于语义的反哺,使得“物质的特性返回到语言,就变成了语言的一部分了”②张学昕、欧阳江河:《“诗,站在虚构这边——诗人欧阳江河访谈录”》,张学昕:《话语生活中的真相》,第297页。。反哺的方式可能只是在原有词自带意义基础上的填充,可能是掏空自带意义,赋予其新的意义,这一全新的意义或者是填充的意义,“极好地抑制了汉语的肉体性”③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下篇),《东吴学术》2018年第4期。,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诗人的创造潜能,“诗人可以基于词的立场——发明或虚构的立场——去制作,评论及命名自己的作品,并且,文本的意义可以衍生自写作本身,而不必在‘预设的现实’中去寻找资源”④欧阳江河:《90年代的诗歌写作:认同什么?》,《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当然,其意义走向也会变得多元与不确定,这对于理解与阐释而言,无疑会加大难度。
三、矛盾修辞法
“矛盾修辞法”是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意义生成机制的第三个方法。很多研究者都关注到了此,但将之作为问题,单独探讨得不多。有学者在论及此时,更多使用“诡辩式语言”或者“悖论式语言”。例如,陈超曾经对“矛盾修辞”作如下界定:“诗中将相互矛盾的概念或感觉扭结一体的修辞手法,又称‘浓缩的悖论’。这种修辞有助于造成诗语的复杂性、体验的深邃感”⑤陈超:《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7页。。同时,陈超也对“悖论”作了较为精准的诠释,所谓悖论是指“诗人将互否的义项、不协调的品质综合展现,看似违反‘常识’,实则深切揭示了生存和生命的两难困境,捍卫了世界以‘问题’、‘难题’的形式存在,防止其被廉价的历史决定论、独断论所简化抹平”⑥陈超:《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下),第1263-1264页。。欧阳江河本人更认同“悖论式语言”或“矛盾修辞法”这样的说法。其实,“矛盾”“悖论”或者“诡辩”的内涵大体一致,其最终意义指向都是悖论。
对于现代诗而言,悖论是不言自明的“金科玉律”,是它的特质甚至是优势,在1980年代以降的现代汉语诗歌中也特别常见,比如张枣、昌耀、海子等人的诗歌中都有鲜明的体现。这才有了布鲁克斯(Brooks.C.)“悖论适合于诗歌,并且是其无法规避的语言”⑦[美]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页。的判断。也就是说,“矛盾修辞法”并非欧阳江河诗作所独有,但是就认知与运用的自觉程度和创造性来说,欧阳江河却是最鲜明、最具代表性的,特别是他90年代的诗歌。最能代表这种自觉性探索的是,他提出与重点阐释的“反词”概念,以及极具方法论意义的诗歌《马》。
在名篇《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中,欧阳江河提出了“反词”的概念,并明确了其功能和意义。“反词是体现特定文本作者用意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将词的意义公设与词的不可识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精心设计为一连串的语码替换、语义校正以及话语场所的转折,由此唤起词的字面意思、衍生歧义、修辞用法等对比性要素的相互交涉,由于它们都只是作为对应语境的一部分起临时的、不带权威性的作用,所以彼此之间仅仅是保持接触(这种接触有时达到迷宫般错综复杂的程度)而既不强求一致,也不对差异性要素中的任何一方给予特殊强调或加以掩饰。”①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站在虚构这边》,第21-22页。这是诗人为了防止词义的固定化与类型化,甚至被无限升华可能,而提出的一种表意方法。在肯定“反词”的价值的基础上,欧阳江河颇有创见性地亮明了个人的词语观念,即“从反词去理解词”②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站在虚构这边》,第9页。。他认为:“词的意义寄生在反词上面。先有了反词,然后词才被唤起,被催生,被重新编码。”③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站在虚构这边》,第11页。
乍看“反词”,“意义相反”可能是最先、也是最容易被捕捉到的意义,但其实它有着更丰富的内蕴。在近几年的创作谈中,诗人对“反词”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我把诗歌中的声音命名为‘反词’关系——不是反义词,也不是反对的意思,是一个形态”④欧阳江河:《反词·开耳·形态 谈诗歌的记忆与形式》,《上海文化》2019年第5期。。“反词”至少可以从词语本身、意义、声音以及异质混成等角度等去理解。比如欧阳江河认为“原子弹、无人机、艾滋病、病毒,这些都是世纪‘大反词’”⑤欧阳江河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词’能单方面加以命名的时代,必须借助‘反词’、借助词与反词的合力,才能对时代作出复调的‘新命名’。”参见欧阳江河、何平:《个人与文学史的延长线 ——关于欧阳江河四十年诗歌写作的对谈》,《天涯》2021年第4期。的观念,更多是从语境方面的考量。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反词”不能等同于“矛盾修辞法”,但“矛盾修辞法”与“反词”的主张又存在必然的联系。“矛盾修辞法”是诗人践行“反词”观念的有效表意方法之一,“它们往往会扩展为欧阳江河诗歌的逻辑结构;而这种逻辑结构,又跟这个时代的种种现实有着对称、错位、反转等等复杂的关系”⑥陈东东:《可能性的欧阳江河》,《收获》2018年第2期。。
就诗歌创作而言,90年代的诗作《马》,能够鲜明体现欧阳江河的写作观和方法论,也是运用“矛盾修辞法”的典型文本。诗人以“马”为题,由“马”切题,借助“马”放纵、奔跑的天性,挖出“马”之内心试图超越人类对其命名、规约的限定,以及自我超越的可能性。诗歌的意义走向也由“说马”转向与“马”有关的言说,完成了第一次意义向度的转移:
厌倦了赞颂和到达,厌倦了自身的不朽,/渴望消逝,渴望事物的短暂性。/马在白昼以弓形显现黑夜,在黑夜/离开黑夜,在狂奔中离开骑手。/马,它的颠覆,它的空茫,/深入到自然的神秘运转,深入到天与地的/飘忽直角,它的一跃陷入肉身。/骑手坠马而亡,/马眼睛在伤口里合拢,成为人的故乡。(第63页)
在接下来的诗行中,意义的展开不再只局限于“马”本身,而是可能与“奔跑”有关,再由“奔跑”牵扯出“根”的悖论——马的狂奔是为了吸入根须,同时马的狂奔又恰好是无根的表征,扎根与无法扎根构成了反题,而奔跑本身的意义与无意义也就构成了悖论。“马”也不再局限于实存的“马”,而可能是想象中的“天马行空”,也可能是由马蹄践踏延伸出的秋夜古战场与异域的战争场景,更可能是人之苦难(“乌云”“风暴”意象)。无论是由奔跑引出的“根”及“漂泊”的主题,还是由奔跑速度的“迅疾”和“缓慢”引出的短暂与永生的思考,都指向了超出“马”之言说范围的“人”。整个诗歌意义的走向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由“马”到“非马”:
马如此优美而危险的躯体/需要另一个躯体来保持/和背叛。马和马的替身/双双在大地上奔驰。(第66页)
借助“马”,诗歌大致呈现出这样的意义轨迹:说“马”—有关“马”—“非马”。在诗歌结尾,诗人亮明了真实的言说意图——“马之不朽有赖于非马”(第67页),完成了对“马”的背叛与超越。
《马》中的“矛盾修辞法”至少有两种:一是“马”作为此词与此物本身生出的悖论,比如有关“扎根”与“无法扎根”的悖论,与“马”善于奔跑的特质有关,是“奔跑”自身生出的悖论;二是矛盾并不直接由作为此物的“马”生出,而是需要通过对此物的“背叛”来生成。此诗最终的意义指向点明了这一方法——“马之不朽有赖于非马”。不妨将以上两种“矛盾修辞法”称为“自反”和“它反”。“自反”是指由此词自身所生出的悖论。这种悖论的生成未必只依靠直线方式,可能要借助另一个(些)词与物的意义联结才可以实现,比如《马》中扎根与无法扎根的悖论并不是由“马”直接生出,需要借助“奔跑”的语义方可实现。“它反”是指悖论不是由此词生出,可能是其他词,还可能借助生出悖论的关联词,以及同一意义向度词语的重复出现等表意手段,生成或语义或逻辑上的悖论。“自反”和“它反”通常“联袂”表意,除了《马》,欧阳江河90年代的其他诗歌也有显豁表现,比如以下的诗句:
有时短短十秒钟的对视/会使一个人突然老去十年,使另一个人/像一盒录像带快速地倒退回去,……(《咖啡馆》,第73页)
看到/生命的每一瞬间都被无穷小的零/放大了一百万倍的/朝菌般生生死死的世代。(《咖啡馆》,第78页)
许多年后,/一个人在一杯咖啡里寻找另一杯咖啡。(《咖啡馆》,第79页))
你首先是灰烬,/然后仍旧是灰烬。(《风筝火鸟》,第135页)
……
结合“自反”与“它反”的具体表意方式,欧阳江河大致在两个层面建构了“矛盾修辞学”。一个层面是语义悖论,即将语义矛盾或者相悖的词语并置,具有哲理思辨特征,传达对复杂事境的独到看法,也可称为显在悖论。除了上述列举的典型诗句,以下诗句同样存在语义悖论:
真正可怕的是:一个人死了还在成长。(《纸币,硬币》,第126页)
请想象一个人失去双腿之后/仍然在奔跑。(《去雅典的鞋子》,第133页)
手铐将会铐上两次,/一次作为零,一次作为无穷多。(《感恩节》,第136页)
夜晚你吃惊地看到/蜡烛的被吹灭的衣裳穿在月光女士身上/像飞蛾一样看不见。穿,比不穿还要少。(《时装街》,第167页)
另一个层面是语境悖论,即悖论不是由词语表面语义直接构成,而更多依靠一个诗句或一首诗的内在意义,可视为潜在悖论。①此处借用布鲁克斯的说法,具体参见[美]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第6页。在谈到“反词”时,诗人约略谈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所说的反词,不应该被狭义地界定为词与词之间自行产生的语义对立,而是应该从广义上被理解为文本内部的对应语境”②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站在虚构这边》,第21页。。比如《星期日的钥匙》,题目本身就暗含矛盾:钥匙的功能并不应该由时间决定,诗人却偏偏这样理解,在诗歌的最后,“钥匙”并没有起到开锁的作用,昭示了其本身的无效。“现在是星期日。所有房间/全部神秘地敞开。我扔掉钥匙。/走进任何一间房屋都用不着敲门。/世界如此拥挤,屋里却空无一人。”(第96页)诗歌也由语境的悖论走向了关乎钥匙的语义的悖论。
《晚餐》运用了三个“不会再有早晨了”,似乎是在强化“晚餐”的永恒性,但在最后一句,诗歌走向了“晚餐”中“晚”的反义——“不会再有早晨了,也不会/再有夜晚”(第102页)。语境悖论的生成往往需要借助表示转折、递进、重复的关联词来实现。《去雅典的鞋子》中,诗人连续使用了六次表示否定之意的“未必”“不会”,所谓“雅典的鞋子”未必适合去雅典(第132-133页);《歌剧》呈现的是有耳朵不想听,想听没耳朵的悖论(第140-141页);《毕加索画牛》传达的是“少”与“多”的辩证(第168-169页)……
无论是“自反”和“它反”这两种具体表意方式,还是“语义悖论”和“语境悖论”这两个表意层次,在面对复杂而难解的现实时,无疑能够增强言说效力。关于这一点,敬文东看得非常清楚:“以背反的言辞对付魔幻而背反的现实,很可能奇兵般地收到奇效”③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下篇),《东吴学术》2018年第4期。。但同时,其也存在无法避免的问题,正如布鲁克斯所说:“悖论是一种诡辩难当、巧妙机智的语言;它成不了心灵之言(the language of the soul)”①[美]布鲁克斯:《精致的瓮:诗歌结构研究》,郭乙瑶等译,第5页。。如果“矛盾修辞法”只剩下作为写作技巧存在的“修辞”意图与目的,就需要诗人警惕。
四、结 语
“非诗”词语的跨语境运用、“物质性”对语义的反哺与填充,以及“矛盾修辞法”这三种意义生成机制,构成了欧阳江河“90年代诗歌”的典型样态,同时也彰显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难度,增强了语言面对现实的言说效力,实现了语义的繁复与多元。
欧阳江河之所以如此费心地“发明”诗歌的写作方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语义的无限升华危险与“词生词”的问题。这是欧阳江河对现代汉语诗歌文体发展较为自觉而有价值的认识,也是他的诗论名篇《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最核心的论题。他说:“我的诗要保持一种狠劲儿,它要触及真实,触及现实,触及物象——词象得触及物象,否则就变成词生词的一个互动了。”②欧阳江河、顾超:《诗歌要保持一种狠劲儿——欧阳江河访谈录》,《天涯》2016年第6期。这样的努力,诗人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提及。具体参见欧阳江河:《电子碎片时代的诗歌写作》,《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参阅欧阳江河:《消费时代的长诗写作》,《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参见欧阳江河、李德武:《嵌入我们额头的广场——关于〈旁晚穿过广场〉的交谈》,《诗林》2007年第4期等。颇为吊诡的是,欧阳江河“发明”了上述表意方式来抵抗现代汉语诗歌可能出现的问题,然而他的诗歌却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即“词生词”——这似乎也可看作是对以“悖论”为主要特征的“矛盾修辞法”最有意味的诠释。很多学者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冷霜看到了“词语马赛克”③冷霜、姜涛、张洁宇等:《对话:胡续冬与“九十年代诗歌”》,《当代文坛》2022年第4期。,敬文东概括了“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④具体参见敬文东:《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欧阳江河与新诗的词语问题》(上下篇),《东吴学术》2018年第3期、第4期。,还有钟鸣的精辟见解:“词对于他(欧阳江河——引者注),像是一种装配零件……但他控制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用来寻找一种说法……他过分强调了写作的技术性,表现出一种永远把自己排斥在外的冷智”⑤钟鸣:《旁观者》第2册,第904、909页。。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欧阳江河表意意图与表意效果存在裂隙。即诗人意图表达的效果和实际表达效果并不对称,这可能也是现代诗人在面对语言,或者词面对物时,不可避免的难题;二是由于表达的惯性,诗人慢慢滑向了“失心的写作”的泥淖。关于这一点,耿占春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无论是语言的可能性还是言语活动的自由处置,都不能借助纯粹的技术与游戏来实现,根据最不可思议的法则,言语活动的自由与意义的无限性,总是由那些将言语活动以某种秘密的方式融入个人生命与痛苦之中的人来实现的”⑥耿占春:《退藏于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1页。。假如没有内心作为根基,词语要么变得空心,要么失真成为假词,要么丧失完整性成为语词的碎片。
理想的语词至少具有如下特征:有伸缩性和张力,能够深入底部,触及生存本身,又能向上拉伸,有更高大的升华空间;更重要的是在文体规则内,葆有深入骨血的本真性以及自我坚守、自我突破和自我反抗的勇气。“词语呈现出的每一个姿势,每一个偏旁,每一个内部的拐弯处,都经过内心力量的赋予、浸染,这个时候出现的诗句一定是不纯的,但也才显得更有力量。”⑦敬文东:《颂歌、我—你关系、知音及其他——关于吉狄马加诗歌的演讲》,《当代文坛》2016年第4期。这,可能是欧阳江河和当下其他汉语诗人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