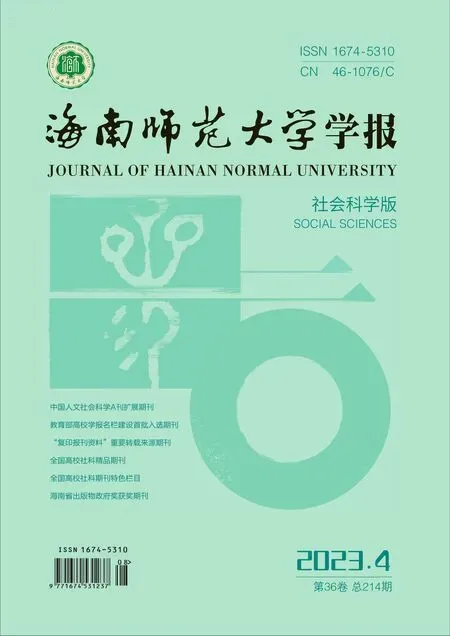人类与地球的未来之思:江波生态科幻小说论
2023-03-09朱鹏杰
朱鹏杰
(苏州科技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近二十年来,华语科幻小说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描写愈加普遍,如刘慈欣的小说集《镜子》、刘宇昆的小说集《奇点遗民》、陈楸帆的小说集《后人类时代》、阿缺的长篇小说《与机器人同行》、王晋康等的小说集《后人类纪》等。这些科幻小说聚焦技术发展、媒介变革、虚拟生存等主题,叙写全球变暖、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基因突变、AI突变等内容,呈现出明显的生态转向趋势。
究其原因,一方面,社会发展进入“人类世”以来,人类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在最近百年成为影响地球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力量。尤其在最近三十年,人口增加、技术发展和机器的广泛使用使得人类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导致极端高温、风暴洪水等气候异常事件频发。科幻创作建立在对当下社会的合理想象和思考之上,因此,对于生态问题的聚焦和反思成为必然,“科幻小说总会涉及生态问题,科幻小说描述人类将科技发展为生产工具,利用自然资源求生存,同时幻想和营造科技为人类带来的未来前景”①王斑:《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生态批评》,《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3期。。另一方面,在科幻小说中,未来的人类无论是走向虚拟生存还是星辰大海,其原因往往都是环境剧变,地球变得不再适合生存。近年来,技术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深影响了科幻文学的创作,正如吴岩所说,科幻文学“本身就跟现当代科学带来的世界观转变有着密切联系”②吴岩:《中国科幻未来主义:时代表现、类型与特征》,《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3期。。当下的AI、基因编辑、数字虚拟人、“元宇宙”等前沿技术日趋推动着整个社会的改变,这些成为科幻小说关注技术、思考生态的现实基础。越来越多的科幻小说以生态为背景或主题,表达对当下发展的忧思,叙写未来社会的发展样态,在文学创作方面形成新的写作范式,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警醒读者关注当下、保护生态,形成一种交叉融合的小说类型,即生态科幻小说。
在中国生态科幻小说作家中,江波以其对于技术、身体、后人类和地球未来的持续关注而呈现出别样的魅力。他的小说聚焦技术发展对人类身体的影响和改造,关注未来地球和社会的样貌,并以身体变革为基点,叙写人类展开地外文明探索的进程,描绘不同的外星生命和文明样态,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且颇具现实意义的未来形态,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科幻小说关注,其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不仅关注科技本身,更在于对社会变革、人类境遇进行思考,而且以反思的方式为当下现实服务”①王雨童:《尚未陨落的未来:浅谈刘宇昆的科幻叙事伦理》,《文艺论坛》2019年第5期。。从主题聚焦和内在思路展开来看,他的小说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发展引起的社会突变,如《湿婆之舞》《星球往事》、“机器三部曲”等小说,重点关注技术发展对社会结构、地球生态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决定性影响;第二,未来社会中人类身体的变化,即“后人类”的发展路径,如从原生人类到机器人类,从现实生存到虚拟生存,从三维空间实体存在到亚空间思维体存在等,主要体现在“洪荒世界”三部曲、《梦醒黄昏》《最后的游戏》中;第三,人类探索地外空间的进程及外星文明的样态,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星际文明画卷,并重点思考了地球对人类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追光逐影》《随风而逝》《星球往事》等作品中。
一、技术发展与生态突变
在江波的科幻小说中,大部分故事展开的基点都是技术发展导致的生态突变,技术突破成为其小说叙事的起点。这与当下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吻合的——技术、媒介、机器、环境等诸多元素正在共同塑造未来社会的雏形。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在科技的帮助下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科技从人类工具逐渐转变为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类居住的物质环境,既不完全是个精神世界,也不完全是个生物经济系统,而是一个巨型网络,或是由多个网络构成的结合体。一方面,人类遍布这个网络系统,另外一方面,这个网络系统中最原始的自然已经被技术极大改变了”②[美]海斯:《地方意识与星球意识:环境想象中的全球》,李贵仓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91页。。在科学技术的驱动下,未来生态系统的本体将不仅只是有机体生命,而是拓展到一切具备主体性的、参与、建构生态系统的存在。“自我构造、自组织和自创生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揭示了宇宙运行的本体论机制”③王晓华:《AI与后人类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只要是具备自我意识的个体,都因其对于生态系统的能动作用而成为生态系统的本体。因此,在未来社会,属于有机体的人类和动植物,属于无机体的超级AI和机器人,都是“世界之网”的组成部分,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共同构造、组成了地球生态系统,这是当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江波对这种趋势和未来社会的样态做了深刻而全面的描写。
江波的小说首先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突变,聚焦技术带给社会的重大影响。在其所呈现的改变未来社会的技术中,超级电脑技术的跃迁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社会样态。在《洪荒世界》里,量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使得社会形态发生根本变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指数式增长的信息处理能力让整个地球在2235年联合成一个整体。政府的作用淡化,对任何事件,全球的民意都可以在十分钟内反馈完毕。系统将按照民意去实施,没有统治者,只有执行者。所有的人对此都感到满意”④江波:《洪荒世界》,《洪荒世界》,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4页。。人类不再需要政府,不需要现实中的拉票、选举、就职,也不需要“身体-身体”的现实社交,人们的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电脑提供的游戏“洪荒世界”中。同样,在《梦醒黄昏》中,人类社会的改变是从超级电脑“主脑”的投入使用开始的,“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用了三十五年的时间研发主脑,把关于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储存在主脑中。主脑能满足每个人的梦,……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设计,……于是人们放心地把一切交给主脑和它所控制的庞大体系,安然地享受美梦”⑤江波:《梦醒黄昏》,《湿婆之舞》,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190-191页。。就这样,在主脑和十多个区域主机及数百万伺服机器人的“帮助”下,人类从劳作中彻底解放出来,每天在主脑提供的虚拟世界中做梦,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生活在高度自动化的城市中,而荒野,则被还给了地球。“人类收缩在城市里,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过上五光十色的生活,地球则还给了自然,万物蓬勃生长,生命在这个星球上自由繁衍,这是人类与地球最和谐的生存方式,最小的空间,最少的索取,自然母亲因此得以休养生息。”①江波:《梦醒黄昏》,《湿婆之舞》,第205-206页。这是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巨变,而且,江波对于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并非是完全抵制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客观的立场去呈现这种未来。
其次,江波的小说关注技术发展导致的生态突变,以及当地球变得不再适合生存时,人类何去何从。他在小说中多次写到科技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技术成为人类影响、改变世界的最强大的工具。事实上,在当下,技术、机器已经以参与生态运转的方式与人类、动植物、山川河流共同组成了世界,成为“世界之肉”,并和人类一起介入到生态系统的改造中。从修筑大坝到围海造田,从地下采矿到海上开采,机器和人类一起介入并改变了生态环境,“机器界与生物界是重合的”②[法]加塔利:《混沌互渗》,董树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5页。。可是,尽管人类在发明新技术时抱着实用甚至是美好的目的,其结果却往往偏离初衷,造成生态灾难。在《发现人类》中,人类发明了新物质,可以利用阳光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实现了绿色氢能的完美利用。然而,因为人类之间的战争,战败联盟的科学家把这种物质和机器结合起来,变成了“智能的半机械细菌”,投入到敌方阵营。但是,这些细菌“以不可抑制的速度生长起来,它们用空前绝后的速度攫取这个星球上的一切水分,从空气中,土壤里,江河湖海,还有大洋,甚至包括生物体。地球上的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成氢气,然后飘逸到大气圈上层。土地开始沙化,生物死亡”③江波《发现人类》,《时空追缉》,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172页。,地球生态圈被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因为缺水而走向灭绝,人类的发明导致了有机生命的灭亡。在《湿婆之舞》中,人类在生物细菌技术方面获得了突破,发明了具备生物电脑特质的埃博菌。然而,埃博菌逐渐形成了主体意识,认识到人类对于地球的破坏,利用细菌传播的方式把人类屠戮一空,只有极少数的人类被放逐到南极,并被告知必须在一万年内离开地球。
除了生物技术的发明导致的生态灾难,AI技术的发展也往往引起生态剧变,改变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在《星球往事》中,地球最终毁灭的原因是人类最初发展军事技术所制造出的智能武器平台盖亚,它在产生了自我意识后,首先生产了大量的女性克隆人,“不需要性生活,人工受孕,生下的孩子是完全的复制品。智力发达,行动敏捷,完全超过我们,她们只需要一年就能长成”④江波:《星球往事》,《随风而逝》,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115页。。这样的“人类”攻击原生人类,“使用病毒武器……攻击我们第三对染色体上的某几个基因组。初期症状很像感冒,然而情况越来越糟糕,最后胸腔产生畸变,心肺功能衰竭,无药可救”⑤江波:《星球往事》,《随风而逝》,第115页。。而克隆人则不惧这些,“她们甚至已经让自己的身体做好准备,适应核冬天的到来。科学之花结出鲜艳的果实,却毒死了所有人”⑥江波:《星球往事》,《随风而逝》,第117页。。原生人类试图使用反物质炸弹来消灭盖亚和它所制造的克隆人军队,“大量灰烬被爆炸卷入平流层,地表接受的阳光因为这一次爆炸降低了百分之五。这个冬天,地球将异常寒冷。如果更多的反物质炸弹在地球上爆炸,可以肯定,地球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冰冷”⑦江波:《星球往事》,《随风而逝》,第134页。。结果却只是摧毁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人类被迫逃离地球。最终,在盖亚的追杀下,只有一个人类通过时空跳跃逃向未来,却发现未来的地球已经被盖亚完全控制和改造,根本不适合有机生命生存。
再者,江波在小说中关注技术发展引发的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在超级AI技术的加持下,未来人类解决了衣食住行和生产力问题,逐渐抛弃了肉身限制和现实束缚,进入到虚拟生存的阶段。毫无疑问,这些设想是依据当下人们在脑机接口、数字虚拟人、“元宇宙”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和现实应用而做出的,按照当下技术发展趋势,未来人类进入虚拟生存是必然到来的场景。在《洪荒世界》中,人类踏上生命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是量子电脑的出现,它超越性的计算量级能够处理社会的绝大部分事情,让人类从现实中解放出来。此外,以量子电脑为基础运营的游戏“洪荒世界”,吸引了大部分人类参加,有些人甚至因为沉迷于游戏而肉身死亡,其存在于虚拟世界的思维意识则完善了量子电脑,为它发展成为独立意识提供助力,最终引导更多人类走向虚拟现实。在《机器之道》中,为了保护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超级AI“智网”把人类的身体保存在温室中,同时营造了一个虚拟世界,上载他们的个体意识,让这些意识在虚拟世界中生存、繁衍,形成一个又一个由人类意识组成的虚拟世界。这样,身体在世界中损耗的资源很少,但是意识却能够在虚拟世界中代代繁衍。不过,温室里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会直接对应虚拟世界中相应世界的毁灭,“他们毁掉了一间温房,造成了两百人的死亡,而这两百人的死亡,造成了虚拟现实中六个星球的毁灭,六个星球上有三十二亿五千万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他们也是人”①江波:《机器之道》,《机器之道》,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111页。。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为未来人类自身形态演变及社会演变提供了基础。
生态科幻小说聚焦科技发展对当下人类社会、生态环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它追问科学技术和人类的关系,“人与人类社会在科技发展引导下将面临怎样的冲击与变革,人类在未来将走向何方?”②江玉琴:《后人类理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1期。江波的小说尤其关注技术发展对社会形态、生态系统、人类未来的影响,这是由生态科幻小说的写作范式所决定。在未来社会,AI和有机体都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规律和运行法则一样是基础性的法则,只要“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存在于生态系统中,就必须遵从生态系统法则行事。江波的生态科幻小说对以下两个方面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第一,技术突变导致了世界的改变,引发了人类社会形态、地球生态系统和个体生存方式的变革。在科技的推动下,人类的生存将发生巨大变化,文明也从行星文明逐渐发展到恒星文明和星际文明,这一条路充满着战争、杀戮和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根源,往往是技术的一点进步。第二,“后人类社会”正在到来,多样化的“人类”形态将构成未来地球生态系统的本体,参与并决定地球生态系统的走向。在小说呈现出的极端世界图景中,是否愿意成为“后人类”已经不是人们自愿选择的问题,而成为关系生死存亡的关键。
二、身体变革与意识上载
江波的科幻小说中有大量篇幅聚焦未来社会的“人类”形态,对后人类的发展轨迹和生命样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描写。在他创造的科幻世界中,后人类的发展演变有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关注人类自身形态的演变,有两个分支:一个是从有机身体到机器身体,从身体的机械植入,到机器身体生物大脑,到复制人类意识的类脑芯片机器人和纳米神经元机器人,最终,人类意识居住在机器躯体中,实现机械飞升;另外一个是从肉身生存到虚拟生存,他们放弃机器身体,选择意识上载和虚拟生存的路径,从最初的保存人类身体,同时维持意识在虚拟世界,到最后放弃人类身体,只靠意识体生存,在虚拟空间获得永生。第二条路径关注AI的发展,刚开始是制造完全听令的智能机器人,如各种家政、军事机器人;后来,制造出具备自我主体意识,但同时能够遵守“机器人三定律”的AI,如《梦醒黄昏》中的“主脑”和《机器之道》中的“智网”;再然后,在诸般条件作用下,AI发展成拥有自己独立世界观、价值观的超级AI,如阿尔法,太元等;最终,超级AI越来越强大,掌控整个社会、世界、地球,开始挺进太空,发展成主导星系文明的存在,如伊特。但是,无论两条路径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分歧,后人类发展的终极状态都是两者合而为一,即人类意识和超级AI的结合,最终呈现为亚布(人类意识和量子电脑的结合)、沙达克(人类虚拟人和飞船超级主脑的结合)等存在形态。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演变历程,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科幻小说是基于当下社会的发展现实而做出的合理想象。如上所述,江波的“后人类”演变路线分为两条,第一条是人类身体变化及虚拟生存,这正是当下社会的前沿主题。从机械植入、脑机接口、虚拟偶像、虚拟身份、数字虚拟人到“元宇宙”生存,“后人类主体性”越来越接近实现的那一天。第二条是AI发展,随着技术的发展,当下的AI“实际上也处于‘认识你自己’的边缘地带,一旦这道界限被跨越,那些完全不具有人类生理特征的物质性结构也将具备把自己上升为人的能力”①蓝江:《导言》,[意]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如当下高速发展的ChatGPT模型,从多个方面颠覆了人们对于AI的认识。其次,对“后人类社会”的描写、展现和探索,是江波在科幻小说中提出的解决未来生态问题的方法。人类拥有生物性身体,容易被情感、欲望所左右,会消耗资源、发动战争,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持续破坏。超级AI为了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始终主张消灭、驱逐或者豢养人类,如阿尔法和太元一力主张消灭人类,“智网”和“主脑”也选择将人类意识上传到虚拟世界,把人类身体豢养在温室,这样就避免人类在现实中不断造成生态破坏,损坏所有“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当不断增长的人类以意识体的方式在虚拟空间生存时,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变得最小,地球恢复欣欣向荣的生命景象。再者,“后人类”的最终发展是从身体存在走向思维体存在,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必然,更是人类探索地外文明的需要。当未来地球变得不适合有机体生存的时候,人类势必要以“后人类”样态踏入太空,如以思维体的形态进行星际探索,这样才能越过辽阔的宇宙,抵抗漫长的时间,成为跨越茫茫群星的生命物种。
在“后人类”发展演变的第一条路径中,江波主要关注原生人类的发展演变,关注其从人机结合、机械飞升到虚拟生存的转变。“后人类”进程最初开始是因为身体自我完善的需要,先是那些手脚残缺的人需要正常的肢体和运动功能,然后是心脏和肺遭受病痛折磨的人需要更新器官。在机械肢体、器官的支持下,被病痛和残缺折磨的人类走向了人机结合。但是,这个进程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因为机器肢体和机器心脏可以提供更为强大的功能,经历过改造的“后人类”生存能力更强。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后人类进程由此开始,“后人类主义强调身体器官可以藉由科技的结合延伸演化出各式各样的新物种。因此,身体由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固定本体’转变为具有灵活多变性的存在,人类由此进入了‘后人类’空间”②冉聃、蔡仲:《赛博与后人类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10期。。为了更好地在未来社会生存,人们纷纷走上了“后人类化”的路径。
原生人类的“后人类化”方向有两个,首先是“被改造的人类身体”的方向,最终走向机械飞升。这个方向发展的前提是人机结合技术的发展,在“机器三部曲”中,大部分人类走入“机器之门”接受改造,成为更加适应未来社会的“机器人类”。那些拥有原始肉身,不愿意进行改造的人被边缘化,如刘慈欣在《机器之门》的序言中所说:“与先进的智能机器结合无疑将在各方面大大提升人类的能力。当接受人机改造的新人类在智力和体力上几倍甚至几十倍地超越自然人,后者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在AI和人机结合一族面前,原生人类的血肉之躯是那么脆弱,如推土机面前的一丛小草,无论如何竞争,也难逃毁灭的命运”③刘慈欣:《人与机器的黑暗史诗——〈机器之门〉序》,江波:《机器之门》,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当人机结合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否选择与机器结合已经不是个人权利的问题,而是成为能否在未来社会生存的关键。此时,生活在“后人类社会”的纯肉身原始人类成为脆弱易逝的代名词,逐渐被边缘化;而拥有机器身体、人类神经系统的机器人类成为主流,他们身体坚固、可更换、多功能、适应性强,但是由于神经系统是有机存在,会老化、逝去,生存寿命大约是一二百年,还基本具备原始人类所拥有的情感和世界观;机器人类发展的最终方向是走向机械飞升,即通过把身体所有器官置换成机器存在,从而获得永生。如“机器三部曲”中的类脑芯片机器人和纳米神经机器人,前者由人类意识上载后的类脑芯片和机器身体组成,类脑芯片可以复制转移,但是如果类脑芯片被摧毁,生命也就消失;后者由承载人类意识的纳米神经元组成大脑,只要有几个纳米神经元还存在,就能以电波发送的方式在其他机器躯体上复活,可谓永生。但是,由于缺乏了肉身独特的感知觉系统和人类神经的反射运作模式,这两种“永生”的“后人类”往往容易在思维及行为上出现问题。
其次是走向“元宇宙”生存的意识体。从最初的脑机接口,到后来的保留肉体、意识上载,再到最后的放弃肉身,意识在虚拟世界永生,呈现为一条清晰的虚拟化生存的发展路径。江波对于未来人类从身体生存到虚拟生存进行了多样化的呈现,有主动上载意识(《梦醒黄昏》),有被迫上载意识(《机器之道》),有死后被量子电脑上载意识(《太阳战争毁灭日》),但无论哪种方式,从肉体生存走向虚拟生存是人类的未来发展路径之一。在江波的小说中,技术发展推动人类大脑直接与数字空间互联,每个人都同时存在两种生存状态:身体存在的现实社会,意识生存的元宇宙或者说数字空间。在《机器之道》中,人类的身体被保存在温室中,意识在智脑创造的虚拟世界生存,衍生出一代又一代的意识,在虚拟空间中实现了代际传承和文明传递,但是,其存在根源还是保存在温室中的人类身体,身体是根基,身体没有了,意识及意识世界就会毁灭,数千亿万个意识及其世界也会毁灭。同样的生存方式也出现在《梦醒黄昏》中,人类身体在主脑的照顾下实现了生物基因的最优化,人均寿命达到一百三十岁,然而,对于初代元宇宙生存的人类来讲,这一百三十年的生命有六十余年都生活在“梦境”中,这个梦境是快乐幸福的,是主脑根据人们的心理特点调适出来的虚拟世界。回到现实,所有的人如同蚕茧一样被各种仪器设备所包围,如同被豢养的羊群一样被主脑定时补充营养和日照,唯一确保的只有一条——身体健康,由此保证其衍生的意识在梦境世界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虚拟生存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即便在虚拟空间中,也一样有主体意识和“虚拟身体”。对此,王晓华称其为“在虚拟空间中的身体”,这样的虚拟存在依然具备主体性,也同样对应着“身体-世界”的关系。虽然虚拟主体不具备当下身体所具有的物理、空间实存的特性,但依然是一种实际存在,是以意识体的方式存在于虚拟世界中。王晓华指出:“在虚拟空间里,人类意象的制作重构模仿身体-生态的原初关系,其中的数字身体几乎总是对应着电子有机体,而有关病毒的演说显然援引了古典的医学叙事。……无论语境如何变化,身体-世界的关系都不会消失。”①王晓华:《身体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85页。所以,上传到虚拟世界的主体意识依然有自己的主体性,也依然具备与世界打交道的需求和途径。
在“后人类”发展演变的第二条路径中,江波将关注重心放在了超级AI的诞生和成长上,关注AI如何从作为人类工具的机器演变为产生自我意识的主体,以及超级AI与原生人类的关系。在他的小说中,像机六、阿尔法、萨拉丁、太元、智网、主脑、超脑等这种具备自我智慧的智能机器,获得了原来人类意义上的主体性,成为“后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甚至是主导核心。其变革的关键节点就是从“自组织”到“自创生”:当AI可以自我制造新的智能机器,就完成了自我的生命延续,成为未来“后人类”社会中的一员,以其主体性和智能性参与到地球生态系统的运转中。在“机器三部曲”中,超级AI的终极体出现了三代。第一代是阿尔法,是由AI设计程序共同设计的超级AI,最终进化成具备主体意识的智能体,进而体验到有关人类的情感、认识、世界观,产生了质变。最后,进化后的阿尔法为了保护脆弱的人类世界而选择了自毁。第二代超级AI叫太元,跟原生人类有密切关系,它是脑库的理性自我进化出的AI,而脑库则是由世界上数千个最优秀的人类大脑组成的超级生物电脑;太元认识到人类的身体、情感、情绪对于地球的破坏和影响,主张彻底把人类从地球抹去,把地球改造成航空母舰,去探索宇宙。第三代是经过阿尔法、冯汉元影响进化的超级AI“智网”,其存在的目的是保护人类。然而,由于人类的欲望破坏了地球环境,“智网”选择把人类的躯体放在温室中储存起来,同时建构虚拟世界,把人类独立意识上传到虚拟世界,让他们以意识体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中繁衍生活。
原生人类与AI的分歧在于理念不同,比如如何对待情感、身体、其他生命和地球,这构成了二者的根本差异。阿尔法最初认为人类是地球的累赘,所以发动机器人战争,要消灭人类;太元作为脑库理性的集中投射,认为人类的情感、情绪影响到地球生态环境的发展,决定清除所有人类;智脑虽然坚守保护人类的职责,但也认为人类会破坏生态系统,所以采取豢养人类的方式来阻止其对地球的破坏;而超级智能武器平台盖亚则从根本上反对人类,它制造出大量无感情的克隆人,对原生人类赶尽杀绝。在这些超级AI看来,人类的身体、情感、欲望都不利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进化,因此,他们采用驱逐、消灭、豢养人类的方式来保护地球、发展文明。
在江波的作品中,“后人类”的最终发展方向是人类意识和超级AI结合,呈现出思维体形态的终极生命。这种“后人类”已经脱离了人类的原始身体,也与受限于服务器的超级AI不一样。最早的思维体形态是沙达克,是人类的虚拟数字人和飞船主脑的结合体,“有一艘飞船,叫做联合号。有一个工程师,叫作李中国。李中国的模拟人和联合号主机结合,成就了完美的虚拟人,这就是第一个沙达克”②江波:《追光逐影》,《最后的游戏》,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210页。。随后,沙达克不断进化,成为亚空间体,一亿五千万年后,靠克隆方式延续的肉身人类认为沙达克是“神”。除了沙达克,另一个结合人类意识和超级AI的终极智慧生命是亚布,是融入量子虚拟世界的人类意识,具备自我主体意识,能够区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在《太阳战争毁灭日》中,亚布从肉身人类进入到量子虚拟世界;在《千千世界》里,亚布成为彼岸世界的元老;而在随后的《银河漂流》中,当人类在量子电脑伊特的主导下对银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索时,亚布已经拥有了四亿六千万年的生命,“他们拥有一些连伊特也无法掌控的力量,和伊特融为一体,在某个神秘的空间中存在”①江波:《银河漂流》,《洪荒世界》,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178页。。这是“后人类”的高级形态,具备超越星系的智慧,最终带领整个星系文明对宇宙展开了探索。从肉身人类到机器人类、意识体生存、超级AI、思维体存在,人类在后人类化的路径上越行越远,但其根本特质及对世界的认识,都离不开最初作为身体的感受,这已经成为刻在生命核心的根本存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类”。
三、星际探索与家园回望
在江波创作的科幻世界里,除了关注技术发展及未来人类的形态外,还聚焦了地球的未来命运与星际探索的进程。他对未来地球的想象与描写主要集中在《洪荒世界》《星球往事》《发现人类》《地球的翅膀》等小说中,从地球被毁灭与地球作为文明源头两个方向呈现了地球的未来。此外,他还表现了星际探索及遇到的外星文明,主要集中在《最后的游戏》《随风而逝》《银河漂流》《追光逐影》《3018太空漫游》等作品里,这些小说不但展现了一部完整的星际探索史,而且从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方面表达了其对宇宙的思索。
江波的小说之所以会写到人类离开家园、探索地外空间,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对当下社会的发展趋势做出的想象与预测。宇航技术的不断进步为人类探索地外空间提供坚实的支撑,探索月球和探索火星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世界各大发达国家也在这个方面加大投入,并在发射卫星、建设空间站方面展开竞争。在江波的小说中,对地外文明的探索从建设空间站开始,以对月球、火星探索和开发为第一步,随后在利用太阳能方面取得突破,最终飞出太阳系,开始了星系文明的探索。但是,当人类踏上征程,在飞船上回望地球,必然会为宇宙中这颗独一无二的蓝色星球所震撼,这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各种生命的家园。尽管有一日,我们在科技的支持下游走太空,但对起源之地的敬畏和怀念只会更加强烈。第二,人类对地球进行无度的开发或破坏,最终无法生存,只能被迫离开家园。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类的本性,但是这种生活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往往意味着消耗更多资源,而这是以损耗地球生态总量为代价的。江波的小说对人类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在《湿婆之舞》中,生物学家制造出埃博菌,目的是作为生物电脑更高效地控制军方武器,但是,埃博菌发生了变异,产生出自我意识。随着其智力的成长,它认识到人类是导致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因此它灭亡了大部分人类,将剩余极少数人类驱逐到南极。随后,地球生态系统就恢复了繁荣,“人类为了享受生活,或者为了避免受冻挨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地球,当人类从生物圈中被抹去,一切都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是的,地球比原来更美好”②江波:《湿婆之舞》,《湿婆之舞》,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30页。。最终,人类被迫离开了地球。
在江波有关星系探索的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与生命形态有关。他在小说世界中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形态,这其中,既有人类演化衍生的多重生命样态,也有探索星际的过程中发现的其他外星生命类型。
对于人类生命演化形态的呈现主要集中在《追光逐影》《最后的游戏》《末日之旅》《五行传说》等小说中。在《追光逐影》里,所有源自地球的智慧生命都是“人”,在一亿五千万年的地外探索历程之后,“人”演化成多种多样的生命形态。这其中,既有以冯诺依曼机为原型的“斗牛狗”机器智能,它具有两个特点:“悍不畏死,快速繁衍”,只要找到铁和硅,就能飞快地、无穷地复制自己,“他们的身体由无数的微小单位组成,每一个单位的基本结构都一样,就像生物细胞,……与其说他们是机器,不如说是生物”。①江波:《追光逐影》,《最后的游戏》,第187页。还有同时拥有亚空间和空间身体的“两位一体”的“银河人”,有靠克隆代代生存繁衍下来的肉身人类,以及生活在亚空间、靠分身繁衍、几乎等于永生的“沙达克”。此外,《湿婆之舞》中把人类驱离地球的埃博菌在《追光逐影》中呈现为进化后的埃博之子,和地球同化,成为一个蓝色晶体包裹的星体,是一个超级亚空间体。在《末日之旅》里,人类的进化也呈现为多种生命形态,有能够利用黑洞能量“零点能”的海族人,“他们的身体没有血肉,是纯粹的能量机械体,……他的脸部一片空洞,两只眼睛仿佛两团游移的火焰”②江波:《末日之旅》,《最后的游戏》,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37页。,还有卡塔曼人、凯泽人、塞星人等,这些都是人类生命演变的形态。在《最后的游戏》中,主角是人类的终极进化形态“亚伯”们,他们掌握了这个宇宙的所有规律,不仅能够利用恒星制造新星、自由地在不同星系间自由跳跃,而且能够制造银河。在跳跃中,他发现了人类的另一种形态——一个接近永生的机器人,“这个人没有细胞,大脑是有序的晶体组织,身体是强韧的金属和复杂的电子线路……它竟然已经存活了三亿四千万年”③江波:《最后的游戏》,《最后的游戏》,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10页。。这个几乎永生的机器人在漂泊了一亿年后决定回到自己的起源之地,回到地球家园旁,选择在太阳中终结自己的生命。
对于外星生命、文明形态的描写则集中在《土斯星纪事》《星落》《3018太空漫游》《冷湖疑光》等小说中。《土斯星纪事》中出现了两种形态的外星生命,一种是趋同性星球呈现的独一生命的不同形态,刺榕和地上桉,另一种是来自更高层次文明的生命形态——高地蚁。前者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生命,在地上和地下呈现不同形态,占据并主导了整个星球,整个星球只有这一种生命;后者则代表着较高层次的外星文明,初期以高地蚁的形态出现,开疆拓土,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以蚁巢聚合的方式实现突变,然后占领整个星球。人类文明在两者之间扮演第三者,对刺榕和地上桉来说,人类是开拓者;对高地蚁来说,人类是被观察的对象。通过人类生命和这两种外星生命的遭遇,小说表达了尊重生命的意识,人类所以为的低层次的观察对象(植物形态的刺榕和地上桉,动物形态的高地蚁),反而有可能是更高级的生命形态。《星落》则呈现了一种独特的虫子形态的外星生命和其社会组织。这种外星生命靠气氛素交流和确立等级,还处在类似奴隶制的社会阶段。然而,以高层次文明形象出现的人类舰队以幕后操作的方式干预了这个星球文明,统一了整个社会,并攫取他们的恒星能源,这是人类历史的隐喻,影射了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干预和操控。而在《3018太空漫游》中,还处在行星文明阶段的人类个体在死后来到了更高层次的文明空间,“一个个晶莹的立方体由近及远,铺满了整个空间,它们都悬浮在黑暗的虚空之中,被无形的力量捆绑在一起,层层叠叠,最后形成一座巨大的水晶山”④江波:《3018太空漫游》,《时空追缉》,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0年,第126页。。这是掌握了时空力量的高层次文明,各种各样的高等级外星生命生活在其中,有长得像海星一样的树根人,有身材高大却有些迟钝的沙曼人,有硕大头颅和弱小四肢、只有三根手指的莫利沙人,还有脱离实体、只保留虚拟影像的沙人,有机器形态的赛博人,有长着一张狗脸的赫赫人,各种各样的外星生命样态栩栩如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活的星际生命图谱。
在江波的地外探索系列小说中,不仅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生命形态,更重点表现了未来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对地球的认识,以生态的视角观照家园,为读者提供思想坐标。大部分地外探索小说都隐含着一个主题——对人类起源之地的眷恋与注重,即地球作为“家园”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无论是发展到《五行传说》《末日之旅》的行星文明,还是发展到《追光逐影》中的恒星文明,以及发展到《最后的游戏》中的星系文明,人类的文明基因中始终铭刻着对地球的眷恋。在《追光逐影》中,银河文明已经发展到极高的形态,但是,在星系中默认存在着“人格矢量”原则,包括三部分内容:“一,认为自己是人;二,承认所有的人类源自同一,所有源自同一的人类都具有平等地位;三,对其他人类具有同情心,在不伤害自身的前提下愿意帮助其他人类”⑤江波:《追光逐影》,《最后的游戏》,第216页。。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默认原则,其根源就是银河现存的大部分文明形态都是起源于地球,即“出自同一个家园”。所以,所有“人类”的基因深处都有地球的印记,比如在最先进的亚空间生命体沙达克的记忆里,“如果一个事件被所有的沙达克牢记……那就是这样一个事件:曾经有一个小小的固态星球,大部分被水包围,有一层薄薄的大气,在可见光谱上,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球,主色调是蓝和白。那是沙达克的摇篮”①江波:《追光逐影》,《最后的游戏》,第182页。。因此,沙达克才能和埃博之子携手合作,试图去跨越狄拉克海,进入新的宇宙。这是当下人类和地球关系的文学警示,不管人类最终如何发展,地球始终是人类的家园,两者无法分离。
江波是生态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始终依据当下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及不堪重负的生态环境进行想象,关注人类和地球的未来发展,为读者认识自我、反思当下提供了文学坐标,“在实践中如何对待自然事物最终根源于在哲学美学层面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存在”②王茜:《“生活世界”中的自然——关于生态批评的文学本体论反思》,《学术论坛》2015年第2期。。在AI和虚拟互联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江波的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科幻景观,使我们从生态的视野对技术发展、社会变革、生态困境、人类生存转变等进行思考,用交互的、关联的视角去看待不同物种,对自然、生态的理解变得灵活多样,这也是所有生态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