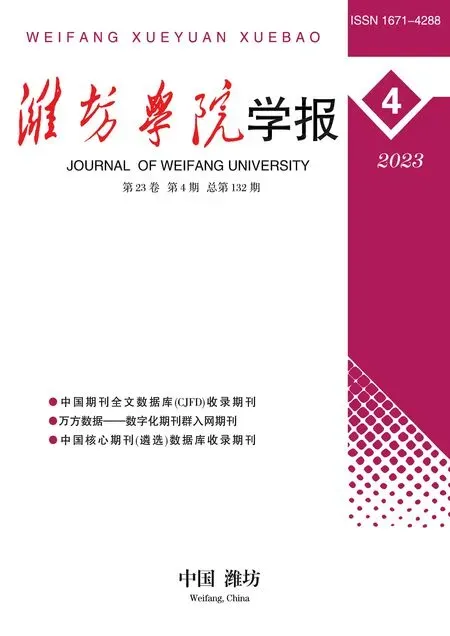论作者身份与署名
2023-03-07薛惊天
薛惊天
(武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0)
一、引言
作者身份不正当(impropriety of authorship),在国内通常表现为在文章上挂名(titular)。许多人早已注意到在文章上挂名的学术不端行为,并对其进行批评,包括新闻文章挂名[1][2]、政绩文章挂名[3]、科技文章挂名[4][5][6]、法学文章挂名[7]。能在知网检索到的第一篇批评文章于1995 年发表[1],最新的文章则由“解剖学研究”期刊编辑部于2022 年发表[8]。国内在文章上挂名的学术不端行为,既是普遍的,也是长期的。如今某些期刊杂志公然要求作者将对创作文章没有实质贡献的导师挂名为文章第一作者,而且,即便期刊杂志不要求挂名,文章挂名的行为也是常见的,以至于出现“学术妲己”等事件。此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将对创作文章没有实质贡献的人挂名为文章作者显然是违法行为。既然如此,为何在文章上挂名仍层出不穷?学术道德和操守的腐败固然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通过查考相关法规可以发现也有模糊之处。
国内关于“署名权”是否可以转让的问题,有许多争论。杨信等人[9]认为“署名权”可以转让;唐冰洁[10]认为委托作品的“署名权”可以转让;柳励和[11][12]、秦昉新[13]、马珂[14]认为“署名权”可以转让;但要在一定条件下,并且要受到一定限制;孙琳[15]、齐晓丽[16][17]认为“署名权”不可以转让;董葆莉[18]、陈宇佳[19]、林萌[20]、马立等人[21]认为委托作品的“署名权”不可以转让。支持“署名权”可以转让的主要理由是:在一定条件下,“署名权”的转让不会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反对“署名权”可以转让的理由主要是:“署名权”是作者的权利,并且为“著作人身权”,属于不可转让的“人格权”。此外,争论的双方都认为,“作者身份权”不可转让。这些争论都围绕着“署名权”,也认为“署名权”与“作者身份权”具有密切关系。然而,由于不清楚“作者身份权”与“署名权”以及二者的关系,所以,正反双方僵持不下,均难以理服人。
孟德斯鸠曾说:“有两种腐败:其一是,人们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他们为法律所腐败;后者是不可治愈的痼疾,因为它就存在于疗法本身。”[22]为了避免“疗法”被腐败,进而通过法律整治“腐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有必要厘清《著作权法》中的相关概念:“作者身份权”与“署名权”,以及二者的关系。由于中国是《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著作权法》受其影响,所以,以下将先分析《伯尔尼公约》中“作者身份”概念,随后在此基础之上阐述《著作权法》及相关法规中的“作者身份”,并探讨“作者身份”与“署名/签名”的关系,最后提出对《著作权法》中的“署名权”的修改建议。
二、《伯尔尼公约》中的“作者有权利主张/要求作品的作者身份”
《伯尔尼公约》在其开篇以及第一条开宗明义:“为保护作者对其……作品的权利(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uthors in their ……works)”[23],由此可见,《伯尔尼公约》所保护的乃是“作者对其作品的权利”,而不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第六条之二“精神权利(Moral Rights)”提到了“作者身份(authorship)”:“独立于作者的经济权利之外,即使在转让上述权利之后,作者有权利主张(claim)作品的作者身份,并反对一切会对其荣誉和声望有损害的任何对上述作品的歪曲、毁损、修改以及其它相关不敬行为。”[23]《伯尔尼公约》在此表明,“作者‘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的权利”乃是独立于“作者的经济权利(author's economic rights)”的,亦即,“作者‘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的权利”不是一项“作者的经济权利”,即使在“作者的经济权利”被转让之后,“作者‘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的权利”仍独立受到保护。
“作者有权利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the auth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 of the work)”中的“作者(author)”乃是对其“作品(work)”具有“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主体,“作者‘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的权利”乃是基于“‘作者’对其‘作品’具有‘作者身份’”这一事实(fact)。至于如何判断此事实,《伯尔尼公约》未加限定,而是留给其成员国。
“作者有权利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指的是作者的“主张的权利(the right to claim)”,并且是作者“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claim authorship of the work)”的权利,而且权利的主体乃是“作者”。此处的“主张”其英文是“claim”,此词确实具有“表明”的意思,但其法律意思乃是“要求当得或被认为当得之物(如金钱)(a demand for something (as money) due or believed to be due)”[25],在当前语境,将“claim”译为“主张”或“要求”更合适。
上述作者所有的“权利”还包括:“反对一切会对其荣誉和声望有损害的任何对上述作品的歪曲、毁损、修改以及其它相关不敬行为。”[23]对“作品的歪曲、毁损、修改以及其它相关不敬行为”可以说是对“作品”的“不正当使用”,甚至“滥用”。也就是说,“作者”有权利反对会损害其荣誉和声望的“不正当使用”,甚至“滥用”其“作品”的不敬行为。不难看出,此处所述作者的权利乃是基于“作者对其作品具有作者身份”的事实。
三、《著作权法》中的“作者身份权”与“作者”
目前是全球化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规约被承认。尽管有少数国家尚未加入《伯尔尼公约》,但《伯尔尼公约》在保护著作权方面已是国际规约。中国于1992 年成为《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另一方面,中国的法规也有面向国际的英文版。
(一)“作者身份权”
国内较少将《伯尔尼公约》中的“作者有权利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the auth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 of the work)”称为“作者身份权”[24],其更常见的名称是“署名权”。《著作权法》第十条界定了术语“著作权(copyright)”包括“位格权利(personality rights)”和“财产权利(property rights)”[26],通常称为“人格权”或“人身权”与“财产权”[27]。其中“位格权利”包括了:“(2)作者身份权,即,主张(claim)相关作品的作者身份,并拥有作者之名义而被提及的权利”[26]《著作权法》此处通过援引《伯尔尼公约》中的“主张作者身份的权利(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来定义“作者身份权(right of authorship)”。不难看出,此处的“作者身份权”就是“主张作者身份权”或“要求作者身份权”。中文的说法却是“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27]。《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以下简称:《著作权法释义》)也说“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是署名权的应有之义”[28]。然而,上文已经论及,“claim”的基本意思是“尤其是作为一项权利而要求(to ask for especially as a right)”[25]。故此,将“right of authorship”说成是“署名权”,将“claim”说成是“表明”并不准确,已经引起误解,造成争论。
《著作权法》第十条进一步说明:“著作权所有者可授权他人行使前述(5)至(17)项的权利,并依据协议或此法接受报酬。著作权所有者可让出前述(5)至(17)项的权利中的部分或全部,并依据协议或此法接受报酬”[26]第(2)项的“作者身份权”既不属于“可授权他人行使”的权利,也不属于“可让出”的权利。此外,《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指出:“作者的作者身份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无时间限制。”[26]并且《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26][27]指出:在自然人作者死后,作品的著作权属于自然人的,其著作财产权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将被依法转让。《著作权法》未表示作者的作者身份权可以被转让。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29]指出,作者死亡之后,其作者身份权仍受保护。作者死亡之后,该作者已不能继续主张或要求作者身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却指出已故作者的作者身份权仍受保护,其意义何在?当一部作品的作者死亡,非作者是否有权利主张或要求那部作品的作者身份?基于上文的论述,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事实上,非作者不是那部作品的作者。《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正是基于事实。
(二)“作者”
《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作品的作者乃是创作该作品的自然人。当作品是在主办之下,按照意图并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之下创作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被视为作者。”[26][27]第十条对“‘作者’对其‘作品’具有‘作者身份’”的事实基础予以说明,只是未在此定义“创作”。《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对“创作”予以定义:“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29]并且指出:“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作。”[29]依据《著作权法》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作者’对其‘作品’具有‘作者身份’”乃是基于“作者‘创作’作品”的事实,从而为《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提供了基础。
四、作为作者署名或签名
作者署名或签名对于保护著作权的主体以及追究责任、确认作者身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确定了作品的作者身份,就确定了著作权的主体,作者可对侵权行为者发起诉讼;而当作品损害他人权益时,也可追究作者的责任。关于如何确定作者身份则是“推定(presume)作者”的问题。一般依据作品上的署名/签名来推定作者,除非有相反证明表示署名/签名不是作者。
(一)《伯尔尼公约》中的推定作者
依据《伯尔尼公约》“主张作者身份权”或“要求作者身份权”的主体乃是“作者”,“非作者”无权对“作品”“主张作者身份权”或“要求作者身份权”。《伯尔尼公约》第十五条提到了四种情况:一、以作者名字或毫无疑问的笔名(pseudonym)标示作者身份的情况;二、关于电影作品(cinematographic works);三、匿名(anonymous)或使用笔名的作品;四、未知的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未发表作品。《伯尔尼公约》随即做出更具体的规定。《伯尔尼公约》指出:
“为使文学或艺术作品的作者受此公约保护,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他当被视为作者,并有资格在同盟的成员国发起侵权诉讼,他的名字以通常方式出现在作品上乃是充分的。即便此名是笔名,在作者采用的笔名能毫无疑问地确认其身份的情况下,本段也是适用的。”[23]
作者“有资格在同盟的成员国发起侵权诉讼”;“名字以通常方式出现在作品上”即被推定为作者,除非有相反证明。以通常方式出现在作品上的名字有可能并非真名,而是笔名,甚至有的作品上没有签名/署名,可能出现暂时无法推定真实作者身份的情况,对此,《伯尔尼公约》指出:
“对于匿名作品和前段所述情况以外的笔名作品,若发表者(publisher)的名字出现在作品上,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就被视为(be deemed)作者的代表(represent),并且,在此地位上有资格维护和行使作者的权利(author's rights)。当作者揭示其身份并证实其作品之作者身份(authorship)的主张(claim)时,此段规定即停止适用。”[23]
“对于匿名作品和前段所述情况以外的笔名作品”都是指暂时无法推定作者身份的作品,所以是未知作者的作品。尽管这样的作品被发表,发表者的名字出现在作品上,发表者被视为作者的代表,但并不被视为真实作者,因为发表者不一定是作者。发表者在作者的地位上,有资格维护和行使作者的权利;而当真实作者揭示其作者身份并得以证实,发表者就不再被视为作者的代表。只有在无法推定“作者”的情况下,才有“作者的代表”,一旦真实作者被证实,就没有“作者的代表”了,“作者的代表”所代为维护和行使的作者的权利,将由真实作者维护和行使。
“对于匿名作品和前段所述情况以外的笔名作品”,无论发表者是否担任“作者的代表”,都没有“主张作者身份的权利”,有资格行使“主张作者身份权”或“要求作者身份权”的只有作者。“发表者的名字出现在作品上”,是“以作品的发表者之名义”出现,不可是“以作品的作者之名义”出现。假设“对于匿名作品和前段所述情况以外的笔名作品”,“发表者的名字以作品的作者之名义出现在作品上”,那么,发表者就是在“主张作者身份”,应当推定发表者为作者,作品就不是“匿名作品”或不知真实作者身份的“笔名作品”,而这是和前提相矛盾的。因此,“对于匿名作品和前段所述情况以外的笔名作品”,“发表者的名字出现在作品上”不可是“以作品的作者之名义”出现。
(二)《著作权法》中的推定作者
上文业已提及《著作权法》第十条关于“作者身份权”的界定:“(2)作者身份权,即,主张(claim)相关作品的作者身份,并拥有作者之名义而被提及的权利”[26]其中“拥有作者之名义而被提及”的常见方式就是作为作者的“署名/ 签名(signature)”,所以,在作品上“署名/签名为作者”乃是“作者”对其“主张作者身份权”或“要求作者身份权”的行使。《著作权法》第十二条指出:“在作品上签名的(signed)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即为作者,并有依作品而来的相应权利,除非有相反证明。”[26]由此可见,作品的作者乃是通过作品上的签名/署名推定的。“除非有相反证明”表示,仅当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才可否认通过作品上的签名/署名所进行的推定。此处与《伯尔尼公约》第十五条一致。
关于“雇佣作品”即所谓的“职务作品”[29],《著作权法》第十八条指出:
“由自然人完成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指派给他的任务所创作的作品,被视为(be deemed)雇佣(employment)过程中的作品。如此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有此条第二段规定的除外……
有任何以下情形,在雇佣过程中被创作的作品的作者享有作者身份权(the right of authorship),著作权的其它权利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享有,并奖励作者:……”[26]
由此可见,雇佣作品的作者身份权属于作者;雇佣方并不享有作者身份权,无权主张或要求作者身份。也就是说,雇佣方无权“以作品的作者之名义”在作品上签名/署名。
至于“委托作品”,《著作权法》第十九条指出:“委托作品(commissioned work)著作权的所属,由委托方和受托方之间的合同约定。没有合同或合同未做明确约定,著作权属于受托方(commissioned party)。”[26]此处并未对委托作品的著作权予以更详细的说明,所谓“著作权的所属”是否包括“作者身份权”?若包括“作者身份权”,则获取作者身份权的一方就拥有署名/签名为作者以及相关的权利;若不包括“作者身份权”,则获取其它著作权的一方就有除作者身份权以外的其它权利,但无权署名/签名为作者。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著作权法》第十九条所说的“著作权”是否包括《著作权法》第十条的“作者身份权”?《著作权法》第十条在规定可转让的著作权时,并未将作者身份权归为可转让的;第(2)项的“作者身份权”既不属于“可授权他人行使”的权利,也不属于“可让出”的权利。《著作权法释义》指出“财产权转让后,作者仍有人身权。受转让的著作权人一般只有财产权而无人身权”,并且“在作品著作权转让后,必要时作者仍有权①此处字体为笔者所加粗。声明自己是作品的作者”[28]。因此,《著作权法》第十九条关于“委托作品”的著作权的所有权并不包括“作者身份权”,“作者身份权”属于作者且不可转让。
五、关于《著作权法》中“署名权”的修改建议
陶鑫良在其“论‘署名权’应改为‘保护作者身份权’”一文敏锐地指出了《著作权法》中的“署名权”概念的模糊,认为署名权与其它著作人身权并不是同一层次的法律概念。他将《伯尔尼公约》中的“作者有权利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the auth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 of the work)”称为“保护作者身份权”,认为“作者身份权”是“保护作者身份权”的简称,提出“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表明作者身份权又是保护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将“保护作者身份权”“表明作者身份权”“署名权”分别定义为“主张作者身份与反对损害作者身份的权利”“是否在作品上表明身份与如何在作品上表明身份的权利”“是否在作品上署名与如何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30]。陶鑫良关于“保护作者身份权”“表明作者身份权”“署名权”的定义和层次关系的论述有一定道理。然而,陶鑫良将《伯尔尼公约》中的“作者有权利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the auth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 of the work)”[23]称为“保护作者身份权”有待商榷。第一,《伯尔尼公约》此处并未提到“保护”“作者身份”一词;第二,《伯尔尼公约》此处所说的是“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而不是“保护”“作品的作者身份”;第三,《伯尔尼公约》开篇即表明了保护作者对其作品的权利的宗旨,换言之,整个《伯尔尼公约》都是要“保护”作者对其作品的权利,其中包括了“主张作者身份”或“要求作者身份”的权利;第四,“保护”的前提基础是拥有正当“权利”,保护正当权利即“维权”,“保护作者身份权”的说法预设了“作者身份权”,“保护作者身份权”与“作者身份权”并非同一层次的法律概念;第五,定义“主张作者身份与反对损害作者身份的权利”中的“反对损害作者身份的权利”对应“保护作者身份权”,而“主张作者身份……的权利”与“保护作者身份权”似乎无关;第六,“保护作者身份权”“表明作者身份权”“署名权”三个法律概念的英文表述可能会重叠。因此,笔者不同意陶鑫良关于《著作权法》中的“署名权”应改为“保护作者身份权”的论点。《伯尔尼公约》中的“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是“主张作者身份权”或“要求作者身份权”,但是,“主张作者身份权”或“要求作者身份权”的说法太抽象。所以,不同成员国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
(一)德国、法国、韩国、日本、俄罗斯著作权法中的相关规定
中国的著作权法接近大陆法系,韩国、日本、俄罗斯与中国在地域上相近,在文化上也互相影响,考察这些国家的著作权法中的相关规定有助于理解《伯尔尼公约》中的“the auth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 of the work”。
德国的著作权法使用了“作者身份识别”(Recognition of authorship[31]/Anerkennung der Urheberschaft[32])的概念,其定义为“作者有权利被确认为作品的作者。作者可以限定作品是否会有作者身份的名称,以及哪个名称会被使用。”[31]法国的《知识产权法典》将“作者权的本性”(Nature du droit d'auteur) 定义为:“精神作品(oeuvre de l'esprit)的作者,单单因为创作此作品,就享有一项排他的并且可对抗所有人的无形产权”,而且“作品的完整性和父亲身份(la paternité)不得受到任何侵害”[33]由此可见,作者仅仅由于创作精神作品的事实,就对该作品具有作者权、父亲身份。作者对其作品具有“父亲身份”,并非只有法国的著作权法这样说。韩国著作权法也有类似说法,该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为“父亲身份权”(Right of Paternity),在韩文版里则是“姓名标示权”()[35]。日本著作权法采用的是“归因权”(Right of Attribution)[36],日文版里也是“姓名标示权”(氏名表示権)[37]。这些国家的著作权法中的用语与《伯尔尼公约》中的“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不同。比较接近《伯尔尼公约》用语的是《俄罗斯联邦公民法典》(Civil Cod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其中第1228 条关于“理智活动成果的作者”(The Author of the Result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提到“理智活动成果的作者是通过其创作劳动使该成果被创作出来的公民”[38],并且,“理智活动成果的作者持有归因权(right of attribution),并在本法典所规定的情形下,享有提名权(right to the name)和其他位格非财产权利。作者身份权(right of authorship)、作者的提名权和其他位格非财产权利都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对这些权利的放弃乃是无效的。作者身份权和作者的提名权受永久保护。”[38]其中也使用了“归因权”。第1265 条规定:“归因权,即被识别(recognised)为作品的作者的权利,以及,提某人自己名字的权利,即以作者之名、笔名或没有标示名字(即,匿名),使用或允许使用作品的权利,乃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如,作品的专有权利被指派给他人或转让给他人,使用作品的权利被授予他人。对这些权利的放弃被视为无效。”[38]
综合上述国家著作权法中有关《伯尔尼公约》的“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的相关规定,德国和俄罗斯的法规共同提到了“识别”作者身份的权利,法国和韩国的法规共同提到了“父亲身份”的权利,韩国和日本的法规共同提到了“姓名标示权”,日本和俄罗斯的法规共同提到“归因权”,其中俄罗斯的相关法规最详细。
(二)应将“署名权”改为“作者身份权”
英文《著作权法》 的用词是“right of authorship”[26],中文的用词却是“署名权”[27],但是二者并不对等。陶鑫良分析了“署名权”作为著作位格权的不当之处[30],采用了郑成思提到的“保护作者身份权”[39],但是,并没有直接解释《伯尔尼公约》的“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
“作者身份”不应当与“作者”相割裂,作者具有对其作品的作者身份,作者身份基于作者创作了作品的事实。作者与其作品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法国和韩国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条甚至采用了“父亲身份”的说法。在中国文化中,主张作者身份或要求作者身份的常见方式就是署名或签名,所以,中文《著作权法》使用的“署名权”有一定道理。然而,在中国文化中,主张作者身份或要求作者身份还有其它常见方式,比如,印章、纹印等,署名或签名的说法不足以涵盖这些方式;另一方面,署名或签名的说法的主要意思是行动,由于如今需要署名或签名的场合较以往更多,该说法容易让人忽略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创作者和被创作者的关系。与中国文化具有相似性的韩国和日本,在使用本国文字的著作权法中都使用了“姓名标示权”。在这些文化中,冠以“姓氏”乃是建立在紧密关系的基础上的,例如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就此而言,“姓名标示权”的说法比“署名权”的说法更好。而且,署名或签名无法标示作品来源于作者的因果次序,就此而言,“署名权”不如“归因权”。此外,无论采用哪种“……权”来表示主张作者身份或要求作者身份的权利,该权利都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不可放弃的,正如《俄罗斯公民法典》所指出的那样[38]。
将“署名权”改为“作者提名权”(right to the name)或“作者签名权”(right of author's signature)更准确;考虑到因果关系,改为“归因权”(right of attribution)更合适;考虑到作者和作品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中国文化特点,改为“父亲身份权”(Right of Paternity)更合适。定义需要考虑《伯尔尼公约》中的“作者有权利主张作品的作者身份(the autho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 of the work)”,即“主张作者身份的权利”或“要求作者身份的权利”。综合考虑,应将“署名权”改为“作者身份权”(right of authorship),定义为“即主张或要求相关作品的作者身份,并拥有作者之名义而被提及的权利。该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对此权利的放弃乃是无效的”(that is, the right to claim authorship and to have the author’s name mention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k.This right is unalienable and unassignable. A waiver of this right shall be deemed null and void.)。
六、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作者创作作品的事实,作者对其作品具有作者身份,此身份乃是紧密的,以致于可以用社会生活中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来描述。所以,作者有权利主张或要求作者身份,包括作为作者在作品上署名或签名、在作品上冠以姓名,并有权利反对非作者充当作者在作品上署名或签名、在作品上冠以姓名等,该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不可放弃的。倘若某作品侵害他人权益,需要承担责任的正是该作品的作者。在文章上挂名、期刊杂志社要求挂名都属于作者身份不正当。当作者身份可以被剥夺、转让、放弃,出现学术腐败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