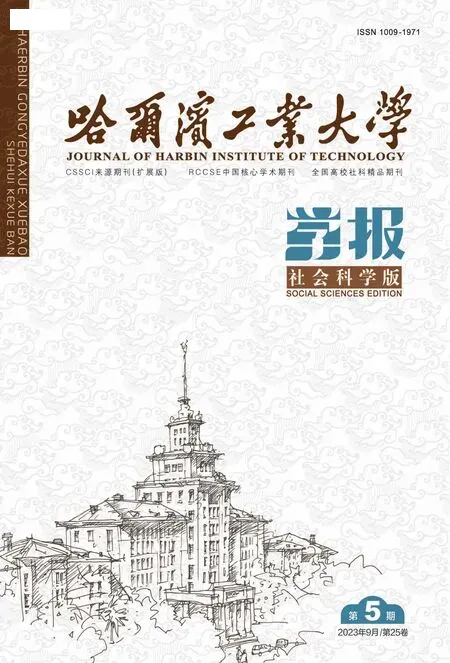袁枚与浙派的诗学关系考论
2023-03-07梁结玲
梁结玲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漳州 363000)
清诗研究里的 “浙派” 是一个意指含混、莫衷一是的概念,从清代乾嘉时期至当代,学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内涵不尽相同。 广义的浙派是指清代以来主要由浙籍人构成的以宗宋为价值取向的诗派,狭义的浙派是指以厉鹗为代表的康雍乾时期由浙籍人构成的宗宋诗派。 追溯源起,最早用 “浙派” 一词的当属袁枚,袁枚所指称的 “浙派” 指的是狭义的浙派。 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是清代乾嘉时期影响最广泛的诗歌流派,在性灵派之前,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也曾风靡一时。 文学流派的消长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对于乾嘉时期风行一时的性灵派而言,浙派是一个前导性的存在,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既是乾嘉诗坛的遗产,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门槛。 浙派的活动中心是杭州,袁枚的青少年是在这一带度过的,他与浙派中人物过往甚密,《随园诗话》屡屡谈及浙派诗。 当前关于袁枚与浙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袁枚与浙派个别成员交游的考证上,研究比较零碎,对两者的关系缺乏全面、深入的探析。
一、袁枚首提 “浙派” 的诗学史意义
在袁枚之前,多用 “浙中诗派” 指称浙江籍的诗人,全祖望说道: “浙之诗人,首朱先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汤先生西厓,实鼎足,至今浙中诗派不出此三家。”[1]864-865沈德潜说道: “浙中诗派,前推竹垞,后推西崖。 竹垞学博,每能变化,西崖才大,每能恢张,变化者较耐寻味也。”[2]475《四库全书总目》在总结清初至雍正期间的浙江诗坛时说道: “论者称浙中诗派,前推竹垞,后推西崖,两家之间,莫有能越之者。”[3]作为一个诗学流派,浙派有浓重的宗宋色彩,朱彝尊对宋诗怀有强烈的不满,全祖望、沈德潜等人的 “浙中诗派” 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并不具有诗学流派的内涵。 全祖望、沈德潜与厉鹗都有不浅的交往,他们在谈及 “浙中诗派” 代表人物时并没有将厉鹗列入其中。 最早用 “浙派” 一词的当属袁枚,他多次提及 “浙派” ,他所指称的 “浙派” 有明确的含义。 “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4]347“吾乡厉太鸿与沈归愚,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 余道:厉公七古气弱,非其所长,然近体清妙,至今为浙派者,谁能及之?”[5]892“小雅才兼大雅才,僧虔用典出新裁。 幽怀妙笔风人旨,浙派如何学得来!”[6]645清初至雍乾,浙江影响最大的诗人是朱彝尊、查慎行和汤佑曾,袁枚将厉鹗视为 “浙派” 的代表性诗人,与此前的 “浙中诗派”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袁枚的 “浙派” 兼有地域和创作倾向两层内涵,这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流派是很接近了。 雍乾之际,诗学内部争论不断,袁枚从文学流派的角度提出 “浙派” ,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诗学史的意义,这一点并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
厉鹗并非浙籍诗人的代表,袁枚从流派的角度标示 “浙派” ,这与 “浙派” 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诗学主张有关。 王士祯是康熙年间的诗坛盟主,被视为 “一代正宗” ,他论诗虽有三变,但仍以唐音为旨归。 王士祯去世后,宗唐余响仍在。 厉鹗对宗唐一派有所不满, “有明中叶,李、何扬波于前,王、李承流于后,动以派别概天下之才俊,噉名者靡然从之,七子、五子,叠床架屋。 本朝诗教极盛,英杰挺生,缀学之徒,名心未忘,或祖北地、济南之余论,以锢其神明;或袭一二矩公之遗貌,而未开生面。 篇什虽繁,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7]735厉鹗批评了明七子和清初宗唐的王士祯,认为宗唐一派 “供人研玩者正自有限” ,他别立新风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杭世骏说道: “(厉鹗)为诗精深华妙,截断众流,乡前辈汤少宰西厓最所激赏。 自新城、长水盛行时,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灵于两家。太鸿独矫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征材尤博,吾乡称诗于宋、元之后,未之过也。”[8]475厉鹗标举宋诗,这本身就具有与宗唐时贤对抗之意。 在批评盲目宗唐的同时,厉鹗将学宋推演到了极致。 “(厉鹗) 间客游扬州,马嶰谷员外、半查征士兄弟延主其家。 马氏储书甲江浙,先生学殖本富,又得诸未见之遗文秘牒,朝夕渔猎,故其发为诗文,削肤存液,辞必己出,以清和为声响,以恬澹为神味,考据故实之作,搜瑕剔隐,仍寓正论于叙事中,读者咸敛手慑服。”[7]703厉鹗宗宋的思潮在当时曾风动一时,汪沆说道: “吾师樊榭厉先生以诗古文名东南者垂四十年。 ……忆前此十余年,大江南北,所至多争设坛坫,皆以先生为主盟,一时往来通缟纻而联车笠,韩江之雅集,沽上之题襟,虽合群雅之长,而总持风雅,实先生为之倡率也。”[7]703-704厉鹗去世后,全祖望感慨道: “风雅道散,方赖樊榭以主持之,今而后,江、淮之吟事衰矣。”[1]365浙派的兴起表明诗坛已发生了变化,袁枚把握住了诗坛的动向并总结浙派的风格: “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 宋人如:‘水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不过一蟹一鹧鸪耳。‘岁暮苍官能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 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不过松、霜、水、柳四物而已。 廋词谜语,了无余味。 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类《庶物异名疏》《清异录》二种。 董竹枝云:‘偷将冷字骗商人。’责之是也。”[4]347-348宋人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诗歌创作好用典故、替代,厉鹗将这一作法推到了极致,袁枚捏出 “浙派” 是事出有因的。
袁枚对 “浙派” 的理论总结影响了后代的诗论,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评厉鹗时说道: “诗品清高,五言在刘杳虚、常建之间。 今浙西谈艺家专以饤饾挦扯为樊榭流派,失樊榭之真矣。”[2]719张云璈有诗: “吾浙诗有派,每怪积习狃。 色或事铅泽,工亦喜饤饾。 乡之诸先辈,未易除沟犹。 一变怀清雄(汤西侍郎),再变道古茂(杭堇浦太史)。 近时惟随园(袁简斋先生),生气充宇宙。矫然君出尘,一一撤垣囿。”[9]陈衍《石遗室诗话》评浙派: “浙派诗喜用新僻小典,妆点极工致,其贻讥饾饤即在此。”[10]袁枚有意总结浙派,这为后人留下了口实,浙派的名声也由此而传播开来。
除了有鲜明的创作风格,厉鹗与沈德潜的唐宋之争是袁枚提出 “浙派” 的又一事实基础。 在厉鹗推崇宋诗之际,沈德潜却积极宣扬唐诗, “德潜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 迄今几三十年,风气骎上,学者知唐为正轨矣。”[11]沈德潜以唐风自勉,对宋诗颇有不满,他曾以王士祯的垂问感到自豪,袁枚说他 “先生最尊阮亭” 是很有道理的。 厉鹗诗论有明显的宗宋倾向,他推扬宋诗显然不合时调。 果然,厉鹗与沈德潜发生了争论。 袁枚说道: “吾乡厉太鸿与沈归愚,同在浙江志馆,而诗派不合。”[5]592袁枚与浙派成员关系密切,与沈德潜曾三度同年(博学鸿词、会试、殿试),对于诗派之间的争论,袁枚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在与沈德潜的辩论里,袁枚谈及了厉鹗与沈德潜的诗风之争。 “先生诮浙诗,谓沿宋习、败唐风者,自樊榭为厉阶。 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诗。 樊榭短于七古,凡集中此体,数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气,先生非之甚当。 然其近体清妙,于近今少偶。”[12]321厉鹗与沈德潜都通过选诗、作诗宣扬自己的诗学观点,两人曾同时参与《浙江通志》编撰,争论是在所难免了。 沈德潜 “诮浙诗” 在厉鹗的文集里也可以找到影子。 在《樊榭山房续集自序》里,厉鹗自叙: “幸生盛际,懒迂多疾,无所托以自见,惟此区区有韵之语,曾缪役心脾。 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或位置仆于诗人之末,不识为仆之桓谭者谁乎?”[7]951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以格调甲乙当代诗人,将厉鹗置于卷末,沈德潜对厉鹗的评价并不高。 沈德潜和厉鹗虽然并没有因为诗学观点的差异而交恶,但两人诗学思想的差异已为诗坛所认知。 袁枚对沈德潜 “诮浙诗” 的批评引起了浙派的共鸣,施兰垞主动致信袁枚,希望袁枚能够与浙派共倡宋诗。雍乾之际,厉鹗与沈德潜的争论是诗坛的一则公案,这一争论成为乾嘉诗坛的遗产。
经过厉鹗与沈德潜、袁枚与沈德潜的争论,雍乾诗坛的分化日趋明显。 王昶是沈德潜弟子,他与厉鹗为忘年交,他在《蒲褐山房诗话》中评厉鹗的诗: “幽新隽妙,刻琢研炼,五言尤胜,大抵取法陶、谢及王、孟、韦、柳,而别有自得之趣,莹然而清,窅然而邃,撷宋诗之精诣而去其疏芜。 时沈文悫方以汉、魏、盛唐倡于吴下,莫能相掩也。”[13]王昶委婉的表述里其实也蕴含了厉、沈二人的诗学之争。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摩》云: “新城王渔洋力宗唐音,范围一世,学之者几无以自见性情。钱塘厉樊榭出,乃主张宋诗为教,以救渔洋末流之弊,后人因以浙派尊之。”[14]李慈铭站在宗唐的立场评论两人的论论: “(厉鹗)诗词皆穷力追新,字必独造,遂开浙西纤哇割缀之习。 世之讲求气格者颇诋諆之,以为浙派之坏,实其作俑。”[15]厉、沈二人的争辩是袁枚提出 “浙派” 的又一事实依据,袁枚对浙派和格调派的双向批评推动了诗歌的发展。 乾隆年间,沈德潜和袁枚相继成为诗坛盟主,浙派的争论成为乾隆诗坛的前奏,其诗学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袁枚与浙派诗人的交谊
袁枚的少年、青年都是在家乡钱塘渡过的,定居随园后,他仍然频频回乡。 袁枚是个有浓重乡土情怀的人,怀乡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情结。 “飞鸟犹知恋故都,我来心欲别西湖。 ……且将满目河山意,偏访黄公旧酒垆。 ……此会自然非偶尔,他生还要遇诸公。 三千世界花同落,十二因缘事未终。 天意亦怜垂老别,连宵不起挂帆风。”[16]817袁枚不信佛,论及乡土他却用 “他生” “因缘” ,乡土的情意可想而知。 回杭州成了袁枚经常性的活动,每次回杭州,除了叙情游旧,他还与浙江诗人诗文唱和。 “满耳乡音听未终,东关行李又匆匆。 ……此日花间送残客,明朝天外望诸公。 回头多少酣嬉事,交与湖楼一夜风! 巾车踏遍九州尘,到底吾乡意气真。 入郡未为投刺客,敲门先有送诗人。 ……招饮一宵三四处,拟分身醉武林春。”[6]606“余每下苏、杭,必采诗归,以壮行色;性之所耽,老而愈笃。”[5]724袁枚与浙江诗坛的联系是全面的,他既与浙派骨干成员如杭世骏、金农、钱载、吴锡麟、金志章、胡天游、万光泰、陈兆仑、吴城等有不浅的交往,又与浙派继承者保持良好的关系,乡土的情怀与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与浙派保持联系的精神纽带。
袁枚与浙派诗人的全面接触始于乾隆元年在京师举行试博学鸿词考试。 这一次考试浙籍文人众多,有严遂成、厉鹗、周玉章、杭世骏、齐召南、张懋建、周长发、汪沆、周琰、周大枢、万光泰、陈士璠、邵昂霄、程川、孙诒年、李宗潮、钱载、全祖望、申甫、周大枢、胡天游等,浙派重要的诗人几乎都参加了这一次考试。 袁枚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这次考试使他与浙派成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是年,袁枚年仅20 岁,声名未起,而厉鹗、杭世骏等人已名满浙江诗坛。 袁枚能参加这一次考试,是广西中丞金鉷举荐,他也是由广西赴京参加考试。虽然不是由浙江官员举荐,但这并不妨碍袁枚与浙派诗人的交往。 将袁枚推荐给浙派诗人的是胡天游,袁枚回忆起那一次相见: “吾与稚威同荐鸿词。 初见,谓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 年少修业而息之,他日为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车行,称余于前辈齐次风、商宝意、杭堇浦、王次山诸先生,而劝之来交。”[12]265胡天游性豪爽,在浙派中人际关系好,经由他的推荐,浙派诗人开始与袁枚交往。 “丁巳春,予与元木、循初同在稚威寓中,夜眠听雨。 元木见赠一篇云:‘文章之家无不有,袁郎二十胆如斗。’诗甚奇诡,不能备录。 壬申岁,余起病至长安,元木再赠七古。 起句云:‘忆昔相见长安邸,志气如虹挂千里。 狂飞大句风雨来,头没酒杯笑不已。’真乃替余少时写照。” “元木诗最坚瘦,独咏《桃花》颇婉丽。”[17]233年轻的袁枚胆大气盛,并不为乡人所重, “余少时气盛跳荡,为吾乡名宿所排。”[4]442乾隆元年的这一次考试袁枚年龄最小,周大枢(元木)的赞赏让他倍受鼓舞。 万光泰(循初)对袁枚也很推崇,袁枚在《鱼门极爱万柘坡遗集余读之中有与袁子才听雨之作怆然感旧为题》一诗回忆了这一友情: “偶翻亡友《栾于集》,中有同吟我姓名。 二十年前春雨夜,九重天外化人城。 ……难得心香最供奉,未曾倾尽一程生。”[18]同乡诗人的推许让袁枚终身难忘,也使他倍受鼓舞,年仅二十的袁枚与浙派诗人由此结下了终身难忘的友谊。 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考试之后,袁枚与浙派诗人保持着联系,两者的关系不断加深。
杭世骏与厉鹗是浙派的核心人物,两人交往密切,是浙江诗坛的领袖,号称 “厉杭” 。 经胡天游的推荐,杭世骏认识了袁枚,杭、袁枚二人从此成为忘年交。 杭世骏在《词科掌录》中评袁枚: “仁和袁子才廪生,奉天金公有国士之目,力荐于朝,在诸征士中最为年少,兼有美才,一时名满日下。”[8]597《词科掌录》收录了袁枚不少诗歌,袁枚晚年整理诗集时从《词科掌录》中补辑了少青年时的作品。 乾隆四年,袁枚考取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当时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两人往来更加频繁。 同年,袁枚乞假归娶,杭世骏通书天津友人查宣门, 查宣门 “命其子俭堂礼登船厚赆”[17]143,可见杭世骏是很看重袁枚的。 由杭返京后,袁枚看望了杭世骏,两人相聚甚欢。 乾隆七年,庶吉士散馆,袁枚外调江南任知县,杭世骏写下《送袁子才之江南序》,对袁枚豁达的胸怀表示赞赏。 乾隆二十四年,杭世骏将自己的诗集《岭南集》寄给袁枚,袁枚看后赞赏不已,认为这是杭世骏最具代表性的诗集。 杭世骏去世后,袁枚尤为感伤,对杭世骏的学问、诗歌给予了高度评价, “伤心此日风流尽,江左灵光半夜台。”[6]579杭世骏论诗重学问,与厉鹗很接近, “余特以学之一字立诗之干,而正天下言诗者之趋,而世莫宗也。”[19]杭世骏与袁枚相差20 岁,两人论诗每每相左,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交谊,也没有影响袁枚对杭世骏的积极评价。 “杭堇浦诗云:‘千林乌桕都离壳,便作梅花一路看。’是此景被人说矣。 晚年好游,所到黄山、白岳、罗浮、匡庐、天台、雁宕、南岳、桂林、武夷、丹霞,觉山水各自争奇,无重复者。”[17]262-263“堇浦先生诗,以《岭南集》为生平极盛之作。 《题陈元孝遗像》云:‘南村晋处士,汐社宋遗民。 湖海归来客,乾坤定后身。 竹堂吟暮雨,山鬼哭萧晨。 莫向厓门去,霜风正扑人。’……此种诗, 悲凉雄壮, 恐又非樊榭、 宝意所能矣。”[4]526-527《随园诗话》摘引杭世骏的诗也不少,诗学主张不同,但袁枚并无批评之意。
商盘也是与厉鹗并称的浙派诗人,他与袁枚情投意合,关系极为融洽。 经胡天游介绍认识后,商盘与袁枚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 乾隆四年,袁枚考取进士,乞假归娶,道经润州,商盘留宿三天,命其子陪游,袁枚在润州极尽欢乐。 乾隆九年,商盘与外调做官的袁枚相会于江南,袁枚赋诗《与商宝意司马宿王禹言太史斋中临别奉赠》: “莺飘凤泊一千年,流水行云意洒然。 但使人间唤生佛,胜教天上作顽仙。 乌衣巷里解鸣珂,月下弹筝灯下歌。 半榻梅花同日别,一官偏恼两人多。 ……为我当年惆怅事,自敲檀板拨琵琶。 蓬海升沉话寂寥,江州司马莫萧骚。 诗人都到青云顶,谁领湖山访六朝?”[20]与袁枚同科的士子如沈德潜、裘曰修等都步入 “青云” ,而袁枚却还是落落不如意,商盘为袁枚未能留职京师而鸣不平,可谓是袁枚的知心人。 乾隆十三年,袁枚购得随园,商盘以 “随园体” 诗向袁枚道贺,谐趣与诗意并存,两人的友谊不言而喻。 乾隆十九年,袁枚与商盘相遇于淮上,两人相聚甚欢。 乾隆三十二年,商盘死于云南军中,袁枚无限感伤,写下了哀词,叙述两人的情谊。
钱载是秀水派的代表诗人,乾隆元年,他与袁枚同试博学鸿词,两人也是那次博学鸿词最后仅剩的两位文人,袁枚和钱载都非常珍重同征的情谊。 乾隆三十年,钱载任江南乡试副考官,公事毕,专程访问袁枚,不巧的是,袁枚此时正送尹继善、钱陈群北上,钱载失意而归。 乾隆四十五年,钱载再度造访随园,袁枚极其高兴,叙述对钱载的思念之情: “同征四十六年前,殿上挥毫事宛然。每忆云仙看碧落,忽持玉尺下江天。 须眉换尽清谈在,桃李栽还旧雨怜。 正拟寻公呼蜡屐,八驺先已唱门边。 爱我山庄处处幽,一丘一壑总勾留。卿云气暖花争迎,老鹤情深语未休。 难得相逢刚九日,自怜此会亦千秋。 知公写赠孤松意,朝野于今两白头。”[6]625两人情深义重,袁枚此诗既道出彼此的交情,也写出了两人相互倾仰之意。 钱载在题《随园雅集图》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从这首诗上看,他在随园的这九天应该是兴致已极。此后,袁枚与钱载相互造访,每次相会,两人皆兴致不已。 钱载去世后,袁枚甚为神伤,他在《哭钱萚石先生二首》中写道: “词科同日赋《长杨》,甲子迢迢六十霜。 陶令山中琴早挂,郗诜殿上桂初芳。 屡操文柄无遗彦,曾祭尧陵有奏章。 四十二人《征人颂》,伯恭此日倍神伤。 前岁扁舟访病身,病中能坐板輿迎。 虽枯半体神犹旺,听说三朝语更清。 岂料别来成永诀,但留诗在即长生。 临风一奠君知否? 彼此都应老泪倾。”[16]923风烛残年,两位老诗人互珍互重,情义非同寻常。
厉鹗与袁枚虽为博学鸿词同年,但目前并没有见到两人直接交往的记录,这可能与两人在年龄、影响、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袁枚21 岁,厉鹗已44 岁,当时厉鹗已名噪诗坛,而袁枚声名未起,无法与厉鹗比肩。 袁枚虽然没有与厉鹗有直接的交往,但这并不影响袁枚对这位乡贤的崇敬之意,在《随园诗话》里他每每赞叹厉鹗的诗歌。 “黄星岩《随园偶成》云:‘山如屏立当窗见,路似蛇旋隔竹看。’厉樊榭咏《崇先寺》云:‘花明正要微阴衬,路转多从隔竹看。’二人不谋而合。 然黄不如厉者,以‘如’字与‘似’字犯重。”[17]153-154“佳句有无心而相同者……厉樊榭《游智果寺》云:‘竹阴入寺绿无暑,荷叶绕门香胜花。’”[17]239-240“厉樊榭诗云:‘蛾眉前后皆奇绝,莫怪群公欠致身。’较梅庚‘蘼芜诗句横波墨,都是尚书传里人’之句,更觉蕴藉。”[17]245“‘身披絮帽寒犹薄,才上篮舆趣便生。’‘压枝梅子多难数,过雨杨花贴地飞。’‘白日如年娱我老,绿阴似水送春归。’《入都会试途中除夕》云:‘荒村已是裁春帖,茅店还闻索酒钱。’‘烛为留人迟见跋,鸡防失旦故争先。’皆绝调也。”[5]892《仿元遗山论诗》中,袁枚评厉鹗: “小雅才兼大雅才,僧虔用典出新裁。 幽怀妙笔风人旨, 浙派如何学得来!”[6]645厉鹗是浙派的代表人物,袁枚不仅充分肯定的他的才华,而且对他用典出新意也表示肯定。 厉鹗的 “幽怀” 与 “妙笔” 具有《诗经》的旨趣,袁枚认为浙派的这种境界是常人难以做到的,袁枚对厉鹗及浙派评价之高由此可见。 沈德潜论诗与厉鹗不合,袁枚处处维护厉鹗,可见他对浙派大体是持肯定态度的。
浙派诗人中,袁枚最推崇的是胡天游,《随园诗话》不仅选摘了胡天游大量的诗作,而且还叙述了胡天游不少异事。 “山阴胡天游稚威,以旷代才,受知于大宗伯任香谷先生。 其待之之厚,不亚于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 馆于其家。 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葡萄曰:‘彼实垂垂矣。 若能以‘侪’、‘淮’险韵,刻划其状,当令某伶进酒为欢。’稚威刻烛二寸,成四十韵。 其警句云……”[17]14“本朝诗家,序事学古乐府《孔雀东南飞》而绝妙者,如……胡稚威之《孝女李三行》,皆古藻淋漓。惜篇页繁重,不能尽录。”[17]101胡天游才气纵横,袁枚将之视为 “奇才” ,在著作中多次提及胡天游的诗风。 胡天游英年早逝,他的著作在逝后被儿子烧毁。 袁枚对此其为痛惜,《随园诗话》为此收录了不少胡天游的诗文,这算是对亡友最好的纪念了。
其他同征诗人,袁枚的评价也不低。 评金志章: “金江声观察,名志章,在吾乡与杭、厉齐名。……尤爱其《过冷水铺》云:‘白鸥傍桨自双浴,黄蝶逆风还倒飞。’《宿灵隐》云:‘窗虚暗觉云生壁,夜静时闻雨滴阶。’”[4]361-362评陈兆仑: “吾乡陈星斋先生《题画》云:‘秋似美人无碍瘦,山如好友不嫌多。’江阴翁征士朗夫《尚湖晚步》云:‘友如作画须求淡, 山似论文不喜平。’ 二语同一风调。”[17]26评严遂成: “海珊(严遂成)自负咏古为第一,余读之果然。 《三垂冈》云:‘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赤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17]65袁枚从诗友的角度对浙派同征诗人进行评述,推崇之意甚明。 金农、周大枢、吴锡麟、钱竹初、周长发等人也都与袁枚有不浅的交往,袁枚编的《续同人集》保留了他们与袁枚交往的文字,袁枚在诗集、文集、诗话等著述中也都提及彼此的交往。 简而言之,袁枚与浙派诗人的交往既广泛,又深入,两者的关系是我们考察浙派和性灵派不可或缺的视角。
三、试图修正浙派
清诗学问化倾向很明显,这也是清诗的一大特色。 乾嘉考据学兴盛,肌理派以翁方纲为代表以考据入诗,形成了一股诗风。 肌理派与浙派都有宗宋的倾向,都是学问诗,虽则如此,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肌理派将诗歌作为考据表达的工具,主旨在考据而非诗,浙派以僻典、僻字入诗,追求生僻的诗风,使诗歌在陌生化、学问化的处理中呈现新的审美境界,其主旨仍在诗。 浙派借学问另辟诗歌途径,考据诗用诗歌的形式铺叙学问,一重在诗,一重在学问,两者并不一样。 袁枚对考据诗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 何必借诗为卖弄? ……近见作诗者,全仗糟粕,琐碎零星,如剃僧发,如拆袜线,句句加注,是将诗当考据作矣。 虑吾说之害之也,故续元遗山《论诗》,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 抄到钟嵘《诗品》 日,该他知道性灵时。’”[17]158以僻典入诗,追求生僻风格尚为诗中一格,诗尚有些韵味,用诗作为考据的工具,那诗的审美本性就丧失无遗了。 袁枚认为考据诗不是诗, “天涯有客号詅痴” 其实就是指翁方纲。 在对待考据诗和浙派上,袁枚能够辨析两者的差异,他对两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学界目前对此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
浙派诗人在学问中讨生活,他们的诗歌缺乏健实的社会内容,正因如此,僻典、好用替代字成为他们的嗜好。 袁枚其实并不反对诗歌的学问化: “诗用经书成语,有对仗极妙者。 前辈卢玉岩云……皆用经书、乐府成语也。 余戏集乐府云:‘背画天图, 子星历历; 东升日影, 鸡黄团团。’”[17]110“用巧无斧凿痕,用典无填砌痕,此是晚年成就之事。 若初学者,正要他肯雕刻,方去费心;肯用典,方去读书。”[17]189袁枚对浙派的学问诗也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学人之诗,吾乡除诸襄七、汪韩门二公而外,有翟进士讳灏、字晴江者,《咏烟草五十韵》警句云……典雅出色,在韩慕庐先生《烟草》诗之上。”[4]321“严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后花如许,记得来时路也无?’暗中用典,真乃绝世聪明。”[17]78可见,袁枚对诗歌的学问化是持肯定态度的。 在学问与诗歌的关系上,袁枚还是能够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他告诫友人: “世人所以不如古人者,为其胸中书太少。 我辈所以不如古人者,为其胸中书太多。 昌黎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亦即此意。 东坡云:‘孟襄阳诗非不佳,可惜作料少。’施愚山驳之云:‘东坡诗非不佳,可惜作料多。 诗如人之眸子,一道灵光,此中着不得金屑。 作料岂可在诗中求乎?’予颇是其言。 或问:‘诗不贵典,何以少陵有读破万卷之说?’不知‘破’字与‘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读书作文之法。 盖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囵用其糟粕也。 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 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4]499学问也是诗料,灵活运用能使诗歌有生气,囫囵吞枣,恰得其反,袁枚对学问的看法是很辩证的。 朱则杰认为 “浙派诗人共同的创作倾向,大抵是善写景,主空灵;宗宋诗,重学问,真正将‘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而为一。 清初黄宗羲最早提出这种创作主张并付诸实践;稍后,出现了两个大大家朱彝尊和查慎行,予以发扬光大;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派生出厉鹗、胡天游、袁枚、钱载四支,各有发展”[21]。 将袁枚视为 “诗人之诗” 与 “学人之诗” 的代表,是浙派的发展,这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这一论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袁枚对浙派不满之处主要在浙派的过度学问化,认为过度学问化偏离了普通人的认知,使得诗歌失去了应有的审美性。
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 宋人如: “水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 不过一蟹一鹧鸪耳。 “岁暮苍官能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 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 不过松、霜、水、柳四物而已。 廋词谜语,了无余味。 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类《庶物异名疏》、《清异录》二种。 董竹枝云: “偷将冷字骗商人。” 责之是也。[4]347-348
浙派诗人通过对文字的陌生化处理以追求诗歌的审美趣味,这是为文造情而不是为情造文。用僻典、野乘、冷僻字固然能够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但这也让诗歌远离了日常的情感,袁枚对这种为文造情的倾向感到不满。 在诗歌中,学问与生活本来并不矛盾,浙派诗人沉湎于学问而不能自拔,这造成了诗歌的学问化。 厉鹗说道: “少陵之自述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诗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处,乃在读万卷书,且读而能破致之,盖即陆天随所云‘輘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造平澹而后已’者,前后作者,若出一揆。 故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吾于徐君柳樊之诗尤信。”[7]742-743杜甫强调读书,并没有局限于学问,厉鹗过度强调了学问的重要,将学问置于诗学的首要地位,这就难免滑入冷僻一路了,袁枚认为这并不是诗学大道。 朱庭珍评论浙派时也说道: “不惟采冷峭字面及掇拾小有风趣谐语入诗,即一切别名、小名、替代字、方音、土谚之类,无不倚为词料。 意谓另开蹊径,色泽新异别致,生趣姿态,并不犹人也。 殊不知大方家数非不能用此种故实字样,大方手笔非不能为此种姿态风趣,乃不屑用,并不屑为,不肯自贬气格,自抑骨力,遁入此种冷径别调耳。 是小家卖弄狡绘伎俩,非名家之品也。”[22]故意造生僻,这只能使诗歌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属品,很难赢得诗坛的广泛认可。 洪亮吉批评厉鹗: “樊榭气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为诗坛初祖。”[23]这也是比较中肯的。 浙派成员普遍都存在用替代字、僻典、野乘等特点,袁枚对此多有批评:
亡友万柘坡……近体索索,殊少真气,说者谓为宋人所累。 余按宋名家绝无此种。 考厥滥觞,始于吾乡辁材讽说之徒,专屏彩色声音,钩考隐僻,以震耀流俗,号为浙派。 一时贤者,亦附下风。 不知明七子貌袭盛唐,而若辈乃皮傅残宋,弃鱼菽而啖稀苓,尤无谓也。孙伯符诮公路云: “恨不及其生时与共辨论。” 柘坡与余总角之交,九原有知,必喜闻过。 而余亦深悔当年不早进规语,致留才人未竟之憾。 逝者已矣,来者未已。 为抉其瑕以见其平生所误者止于是也,而大美以益彰。且以严诗之防,而谨其所趋。 否则,文章公器,目论者谓竟可以好尚异也,其不然矣。[24]
袁枚从诗歌 “公器” 的眼光来看待浙派,认为以一己之 “好尚” 来改变诗歌正常的轨迹并不可取。 袁枚批评厉鹗等人开启了这种诗风,认为这样的诗作 “专屏彩色声音,钩考隐僻,以震耀流俗” ,误导了贤者。 万光泰与袁枚有总角之谊,袁枚在早期就认识到浙派的弊病,《随园诗话》卷一就批评了这种倾向, “同征友万柘坡光泰,精于五、七古。 程鱼门读之,五体投地。 近体学宋人,有晦涩之病。”[17]26万光泰晚年自订其集,袁枚的跋是万光泰去世后写的,袁枚以不能及时规劝为恨, “逝者已矣,来者未已” ,他希望浙派能够改变这一不良的创作倾向。
袁枚在与沈德潜的辩论中极力维护浙派,浙派的施兰垞将袁枚视为同调, “欲相与昌宋诗以立教”[12]324,袁枚对此颇为不满,极力劝阻。 “唐诗之弊,子既知之矣。 宋诗之弊,而子亦知之乎?不依永,故律亡;不润色,故彩晦。 又往往叠韵如蝦蟆繁声,无理取闹。 或使事太僻,如生客阑入,举座寡欢。 其他禅障理障,廋词替语,皆日远夫性情。 病此者,近今吾浙为尤。 虽瑜瑕不掩,有可传者存。 然西施之颦,伯牛之癞,固不可如其勿颦勿癞也。 况非西施与伯牛乎?”[12]326浙派刻意追宋,人为地造成了唐宋的分裂,这是袁枚最不满意之处, “夫诗,无所谓唐、宋也。 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 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异也。 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12]325施兰垞与袁枚同出杨绳武门下,袁枚对他的苦劝是希望浙派能够回归诗歌正道,不偏执于一隅。
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和以翁方纲为代表的肌理派是清代学问诗的代表,袁枚否定了后者,辩证分析了前者,从诗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袁枚的诗论是学人诗论发展的正道。 在对待浙派上,袁枚既有乡情、友情的推扬,又能够深入诗学的内核辩证分析,这样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