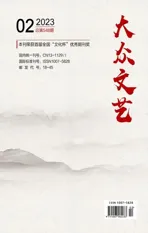包世杰与觉悟社的交往及其学术思想研究
2023-03-06陈皓
陈 皓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00;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上海 200000)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各类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其中诞生于天津的觉悟社就是其中之一。觉悟社由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发起,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分子组成,并于1920年出版社刊《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觉悟社一经成立,即广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名家前来讲座。讲座的内容从文学诗歌到救亡图存等,其中胡适、钱玄同等名家的演讲主题主要是文学艺术等纯粹的学术领域,而李大钊、徐谦、包世杰的演讲则是紧扣时代救国图强的主题。据《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所述,包世杰在1919年11月1日和同月15日两次赴觉悟社演讲,是唯一一位曾两次前来演讲的当时名士,与觉悟社的交往相比其他名人更胜一筹。然而目前对包世杰的研究最为薄弱,仅可见地方志中有包世杰的生平简介。本文探讨包世杰与觉悟社的交往,并力图对包世杰现存著述中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
一、包世杰的生平
据地方志记载:“包世杰,原名永江,字志拯,奉城人(今上海市奉贤区人)。早年求学于上海澄衷中学,与胡适之同学。后南洋公学肄业。民国3年去日本留学,获明治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天津当律师,与陈友仁、郭增凯等办《益世报》《民报》,任编辑。十月革命后,以外交部长王正廷秘书身份,在广州见到孙中山,服膺三民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任鲁案督办王正廷秘书,为青岛归还祖国出了力。袁世凯死后,应召去冯玉祥部,授中将参议、宣传处长等职,任驻察哈尔交涉使。孙中山逝世后,合同广东军政府代表孔祥熙说服冯玉祥与南方携手。军政府迁至武汉时,被外交部长陈友仁委为沙宜交涉使。未及就任,汪蒋叛变,遂蛰居上海,彷徨观望。后因去电南京政府,希望容纳异己、迎接宋庆龄共商国是而触怒蒋介石,遭拘禁。民国24年(1935年)释出,受孔祥熙之聘为南京中央银行专员。三年后因患心脏病而殁。”关于包世杰的法学教育背景,另有日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的提法。另有记载包世杰与孔祥熙关系密切,曾任孔祥熙私人秘书。
二、包世杰与觉悟社的交往
觉悟社成立之时,包世杰正在《益世报》工作。包世杰对于觉悟社的活动是予以支持和肯定的,不仅体现在其两次赴觉悟社演讲,也体现在《益世报》给予觉悟社的诸多关照之上。
(一)两次赴觉悟社演讲
1919年11月1日,包世杰和徐谦一起赴觉悟社演讲。徐谦与包世杰一同在《益世报》工作,担任主编。二人演讲的主题是“救国问题”。对于演讲的具体内容,目前未见有具体的记录。根据李震瀛(化名二八)所著《三个半月的“觉悟”社》:“十一月一日,有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同本社会员谈话,研究‘白话文学’,又有徐季龙同包世杰两先生畅论救国问题。当天的感触是:社员间彼此感情尚不能贯通,彼此思想尚不能了解,所以就感想到个人谈话同分组讨论的必要。”参考1919年9月17日徐谦曾经在上海为青年会做演讲,主题是“公理何在”。结合徐谦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这次“救国问题”的演讲应当也与巴黎和会有关。
1919年11月15日,包世杰第二次前来觉悟社演讲,这次是独自前来。据《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记载:“11月15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会议的时候有包世杰先生来参观,作一个很长的谈话,所说的是‘对新思潮流的感想’。”值得注意的是,当日除了聆听包世杰的演讲,觉悟社还举行特别会议,总结工作经验,明确努力方向,提出觉悟社要加强建设,“做引导社会的先锋”,成为一个“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和“作战的‘大本营’”。李震瀛回忆“我们那一次会,感触到时间大步敷用,就延长时间到晚上,以十二点钟为止……经过这次会议后,社员的团结又增进一层,社中的精神又猛进一步。”包世杰此次所讲的具体内容并未找到明确记载,但有记载同月26日包世杰赴上海青年会演说“新思潮与北方”,两次活动之间仅间隔数日,均为面向青年群体的演说,内容很有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二)益世报给予觉悟社和进步青年的关照
包世杰与觉悟社的交往绝不止于两次演讲。包世杰任《益世报》编辑的时间段与觉悟社的活跃时期较为重合。《益世报》是报道觉悟社成员领导和参加的斗争的主要报纸,且对于学生运动报以赞扬的态度,而包世杰担任《益世报》编辑,其对于报道内容的选择也自然体现出其对于觉悟社的态度。
《益世报》敢于报道学生请愿活动,对天津学生赴京请愿多有报道,如《各省又派代表背上拟作第二次之请愿》《各地请愿代表在京研究请愿事项》《各徐世昌拒见请愿代表》等。1919年10月12日,《益世报》刊发号外,详述学生游行被军警阻拦殴打的事件。同月13日,《益世报》刊载周恩来起草的《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同月19日,《益世报》又刊载《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学生联合会发布文告严斥杨以德无理攻击学生运动》等。可以肯定的是,觉悟社成员如周恩来等可以通过《益世报》号召学生运动和传播先进思想,《益世报》也由此成为学生运动的宣传平台。
除了报道觉悟社成员的学生运动外,《益世报》也帮助觉悟社成员自行办报。1919年7月21日,周恩来任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以下简称《学联报》)创刊,影响日益扩大,北洋政府便向印刷厂施压,还派出军警武力逼迫印刷厂不准承印《学联报》。1919年9月22日,《学联报》被迫停刊。周恩来为《学联报》停刊所写的紧要启示,发表在当日的《益世报》上。在危难关头,《益世报》不避嫌疑,毅然出面代印,解决了周恩来的燃眉之急。据《学联报》“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记载,“‘几经曲折’,现在蒙‘益世报馆’慨然允许,拨出百忙的人工,承印本报。本报实在感激的。”
1920年1月29日,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员被捕直至7月才被放出。在社员们被捕后不久,《益世报》即刊登《南开教职员敬告各界书》,“学生之运动出于爱国,纵有偏激,犹宜曲谅,而况未有过分之举,何至视之如仇,临之如敌。”翌日刊载《天津学联上书北京政府》,要求“请速回复本埠各界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并释放被拘代表及学生也。”“被拘代表及学生惨遭凌虐,尤属非法。”
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后,仍然与《益世报》保持紧密的联系,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在《益世报》上发表的文章约35万字(另有说法是25万余字)。仅《勤工俭学生在法国最后之命运》这一篇文章长达三万余字,分18天在《益世报》上连续刊出。由此可见,周恩来与《益世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益世报》所支付的稿费也成为周恩来在欧洲的留学和革命活动的资金的主要来源。在周恩来等人赴欧留学之后,觉悟社的活动趋于沉寂。
由此可见,觉悟社的活动背后,《益世报》一直在给予帮助。结合包世杰与觉悟社的交往情况,作为《益世报》的重要人物,包世杰对觉悟社应当持有肯定和认可的态度,并通过《益世报》这一平台对觉悟社活动和学生运动给予支持。觉悟社的多位成员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三、包世杰的学术思想
(一)法学相关著述
包世杰接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虽然主要在报界和政界工作,但其仍然不吝于阐述自己关于宪法和法律观点。笔者对包世杰的传世法学著述进行了粗略的梳理,读者可以由此略知包世杰的法律思想。《驳政治救济法律之谬说》是包世杰在《益世报》上发表的社论,文中包世杰驳斥了“政治救济法律”的理论,指出“救济法律之道”唯有遵从立法,在法律允许的途径内制定良法、废除恶法,绝不能另辟蹊径以“政治救济法律”的名义妄造法律,所谓“国会不良”“宪法不良”“法律不良”的问题,皆是假借之辞。
《王瑚与苏议会》一文是一篇随感,是包世杰对家乡政治有感而发,发表在《市民公报》。1921年6月,王瑚被任命为江苏省长,采取一系列措施缓和当时省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对立的状况,包世杰对此深表赞同。包世杰在文中指出:“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论,实是一种错误,英伦政治从来行政立法打通一起,多数党为少数党所监督,而实受国民之裁判,若行政不得民心,则多数党变为少数党,而归失败。”“天下从未有立法专掣行政之肘,亦从未有立法专为行政之走狗也”。包世杰敢于对孟德斯鸠的观点提出质疑,显示出其不盲从于西方法学理论的学术品格。
《独任制与合议制》是包世杰为湖南省宪运动而作,发表在《市民公报》。20世纪20年代初,面对军阀混战,中国许多省份出现自治倾向,湖南省就是其中最为典型代表。1920年7月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宣布湖南自治,还请梁启超代拟一湖南自治法大纲寄至湖南,该年11月湖南正式宣告自治,此后先后设立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和省宪起草委员会进行制宪活动。湖南省宪运动在当时颇具影响,例如毛泽东也提出了“湖南人民自决”的主张。湖南省宪运动的成果之一就是《湖南省宪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宪法文本。包世杰也参加到这一讨论中来,其关注点是《湖南省宪法草案》中的行政权行使采用独任制还是合议制的问题。包世杰在文中首先指出要准确界分独任制、合议制与委员制的含义,并指出许多人没有区分合议制与委员制的问题。包世杰明确指出独任制并不是独断,与是否推行民主并不相干;对于合议制,要留意不要变成绅董包办;对于委员制,要留意不要变成职阀包办。包世杰还进一步介绍了苏维埃劳农委员会制已把私产制度打破,实行了共产主义,所以根本不会有职阀的产生。包世杰提出,如果我国要实行俄罗斯式的委员制,那么实行共产主义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最后,包世杰认为,设立省长是必要的,可以确保省行政的稳固。通过此文不难看出,包世杰不仅通晓美国、英国、瑞士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制度,其对于苏维埃制度颇为推崇,且对彼时刚成立的“远东共和国”的宪法制度也十分熟悉,显然是对十月革命后新兴的苏俄制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论市政之重要》同样是为湖南省宪运动而作,发表在《市民公报》。此文围绕“注重市之独立”展开,指出:“(一)唯市政府为国民利害关系最亲切之政府,如果市政府不良,所谓国民已经失去要有国家之目的亦无不可;(二)唯市政府为国民最容易监督之政府,故全民政治、直接民权之理想,皆可于市政府为最良试验场所;(三)唯市为人才财富集中之地,故上足以防止省集权之流弊,下可为乡镇之模范,故自治之中枢实在于市;(四)如果市政独立,则一切重大政潮,如果为市民所不喜,皆可无从波及;(五)市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最容易实施之地;(六)市政独立可使人才各有相当发展,谋地方实际之繁荣,减少因省级政权集中行使权力不当而引发政潮的风险;(七)训练国民政治常识,市为最易实习之地;(八)理想的国家制度,都可以在市政中有容易实现的希望。”包世杰主张给予市级政府充分的自主权,只受省级立法之监督,不受省级行政之监督。文中列举了英国伦敦市、美国纽约市、波士顿市的自治制度作为参照,显示出包世杰对英美宪法相当熟悉。
《致山东省议员讨论青岛市政书》是包世杰跟随王正廷处理鲁案善后适宜时所著,收录在《鲁案善后月报》。所谓“鲁案”就是指巴黎和会未能解决的“山东问题”。1922年4月中日两国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鲁案善后”是指中日两国对条约具体事宜的交涉与执行。包世杰在鲁案督办公署中承担《青岛市暂行条例》的起草。此时包世杰已经参与过“湖南省宪”“浙江省宪”的起草工作,有一定的立法经验,但是《青岛市暂行条例》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地方立法,“其手续尚需经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然后再由理事会决定”。在此文中,包世杰进一步重申了《论市政之重要》中的观点,并对“监督”一词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所谓监督者,不过监督而已非干涉之别名,亦非染指之美词……中国自来政象只有二端,即干涉与放任是焉,遇事于己有利者无不干涉之,于己无利者无不放任之,从来不识有正当之监督者也”,随着立法经验的积累,包世杰逐步认识到法律条文背后的法律文化问题。法律条文的制定相对简单,但条文背后经过历史积淀的法律文化确较难改变,包世杰已经意识到中国法律文化中缺少“监督”的文化传统,认为国人需要正确认识监督权、正确行使监督权,改变要么过度干涉,要么放任不管的极端做法。
(二)其他作品
除了宪法、法律相关论著外,包世杰亦有许多关于宗教和时事的文章。《基督教问题》一文载于《新青年》杂志,是包世杰与陈独秀关于基督教问题的通信,包世杰对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表示赞同,包世杰指出,“要改造中国的文化,要对旧道德、旧思想、旧伦理,一切所谓‘天经地义’的,重新来评价一遍新价值”。包世杰呼应陈独秀的观点,认为基督教问题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应该用心研究;提倡耶稣的人格,承认信与爱;应当攻击“吃教者”和利用基督教的政客。
《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系根据包世杰亲身经历,并采撷报刊及时人记载编撰而成,收录于《近代史资料第七十一册》。《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以日志形式叙述了1924年11月初孙中山应邀北上商定国是,至1925年3月病逝北平期间的活动,对孙中山逝世前病情的发现、发展及诊治过程和逝世后治丧、停灵西山的全部过程的记述颇为详细。
《国共合作前之一页重要史料》系列是包世杰在《晶报》上发表的一系列回忆类文章,分为“辛亥革命以后之北方革命线”“孔庸之与德甫金氏之会见”“谈话之后果”等共八期在报纸上连载,主要讲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一些往事,主要事1923年9月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员与苏联外交官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磋商经过。此文虽然写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但也表露出包世杰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欣喜态度,“然当初吾人之心,革命为吾人唯一目的,分党分派,自成系统,非吾人所有之目的也”。此文发表后不久,《晶报》即刊载了包世杰因病去世的消息。
结语
包世杰是受过良好法学教育的法律专家,也是五四运动时期活跃的报界人士,曾先后在王正廷的外交团队、冯玉祥的军事团队和孔祥熙的经济团队工作,也曾两度为觉悟社的先进青年演讲,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学生运动领导人有着非同一般的交往。尽管包世杰去世时年仅48岁,但他的一生无疑是丰富而精彩的一生。关于包世杰的生平和著述的研究仍有许多值得深入的地方,需要学术界给予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