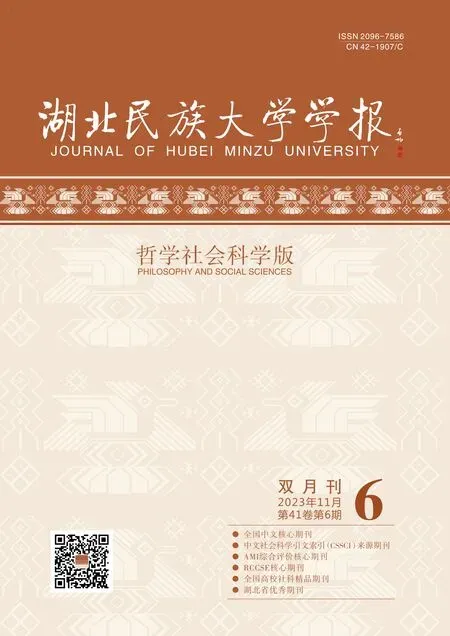短视频生产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研究
2023-03-02李静
李 静
民族团结进步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多次强调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界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下简称各民族“三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关于各民族“三交”的概念内涵(1)金炳镐、肖锐、毕跃光:《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6-69页;王希恩:《民族的融合、交融及互嵌》,《学术界》2016年第4期,第33-35页。、中国各民族“三交”的历史(2)杨须爱:《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1-13页;王文光、孙雨蒙:《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维度研究述论》,《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30-36页。、促进各民族“三交”的实践路径、影响机制等物理空间中的族际互动(3)赵月梅:《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呼伦贝尔地区的实践与启示》,《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第13-24页;艾斌:《民族交融的影响机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基于2018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第16-31页。,对于线上网络空间的各民族“三交”关注较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2版。网络空间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途径(5)王延中、章昌平:《新时代民族工作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5-27页。,尤其是短视频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迅速崛起的新媒介,广泛地影响着各族人民互动的模式,各族群众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场域也随之改变。因而,本文关注在新时代背景下短视频内容生产与互动生产中的族际互动实践,总结民族“三交”在短视频等线上空间中所呈现的特征与动力因素,试图回答在短视频这样的数字化场域中促进民族交融何以可能。
一、短视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场域
新媒体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传播与使用,改变了全球范围内人际互动的模式(6)Dhir, A., Kaur, P., Chen, S., &Pallesen, S.,“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edia Fati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vol.48, no.5, 2019, pp.193-202.,其中也包括各民族间的互动交往。互联网打破了面对面族际交往的地理障碍、心理焦虑、语言沟通等问题,使得网络中的族际交往更易于发生。(7)尕藏草:《互联网场域的族际交往》,《青年研究》2014年第3期,第27-35页。而在当前的数字技术时代,短视频因其制作门槛低、传播即时性、内容多元化等特点而成为最具热度和吸引力的新媒体之一。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短视频用户规模约为10.26亿人,占整体网民数量95.2%。可以说,短视频已成为当前社会存在和文化实践的一种结构性条件。(8)朱天、齐向楠:《媒介化视野下短视频的概念想象、逻辑延伸与价值审视》,《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年第6期,第37-45页。
一些研究关注到了短视频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赋能(9)王晓敏、李晗:《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策略探究——以“互联网+”为视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年第2期,第88-93页。和短视频传播实践过程中对于民族形象的生产与认同建构(10)江凌、严雯嘉:《以文化展演践行少数民族青年文化自觉——以凉山“悬崖村”彝族青年手机直播及短视频为例》,《传媒》2020年第1期,第55-58页。,但是各民族群众在短视频场域中的互动交流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与关注。各民族短视频用户,尤其是民族地区主播所生产的短视频不仅增进民族信息的交流,还推动各民族群众间的线上互动交流。短视频逐渐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
场域是由布迪厄所提出的概念,具体指在各个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短视频不仅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兴媒介,也是其内部各行动者之间实践、互动所形成的媒介场域。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一个场域内部往往由多个子场域构成。民族地区主播所生产的短视频场域便是从属于短视频场域中的子场域,因而,其既有类似于短视频场域的逻辑、规则,也具有作为子场域独特的属性、特点。
民族地区主播生产的短视频场域与其他短视频场域的相似性在于,同样具有数字化和临场感的特点。数字化是指该短视频场域中的主体、客体与媒介都是数字化的。具体而言,短视频技术使各民族群众成为了短视频平台中的数字用户,民族地区主播以虚拟数字化形式的叙事形态呈现其短视频,各族粉丝用户通过各类数字化符号的“评论”“弹幕”在短视频平台中进行表达、互动,同时各族粉丝用户通过“关注”“点赞”“加群”等功能建立数字化的社交关系。以抖音中的“爱心”图像符号为例,各族粉丝用户在赞赏、喜爱某民族地区主播的短视频或某用户的评论时可以点按“爱心”,当不喜欢某评论时可点击“心碎”图标点踩该条评论。因而,各族群众在短视频场域中的数字化“在场”与“互动”,是基于短视频技术发展出的虚拟数字交往形态。
民族地区主播生产的短视频内容丰富多样且短小精悍,在感官上营造出一种社会临场感。社会临场感概念是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主要是指在虚拟沟通情境中个体对其他在线参与者即时即刻的感知,以及互动双方的亲密程度。(12)童清艳、迟金宝:《微信实时传播的社会临场感影响因子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微信使用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68-76页。短视频展演化、场景化的画面呈现让各族粉丝用户具有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各族用户时空的距离感,而让各族粉丝用户从感官上产生一定的社会临场感。同时,短视频中的群聊、评论与私信消息等技术设置也让各族粉丝用户产生了情感的社会临场感。例如,短视频的“信息”栏中,既有基于某个短视频内容交流而可被各族粉丝用户自由获取的公共信息,也有各族用户个人之间互动私聊的私人信息。
民族地区主播生产的短视频场域不同于其他短视频场域的地方,在于短视频内容由民族地区主播制作、各族粉丝用户参与其中。举例来说,截至2023年2月8日,快手平台中以“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风情”及“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等为话题的短视频总播放量近75亿次,而抖音平台上仅以“少数民族风情”为话题的短视频播放量就高达289.8亿次,网友的点赞数、转发数与评论数更是累计超亿次。抖音平台中少数民族用户活跃度和话题热度远高于其他短视频平台。(13)《2022年Q3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发展总结》,https://www.questmobile.com.cn/research/report/1595862859576872962,2023年2月1日。根据QuestMobile公布的数据显示,抖音、抖音极速版月活跃用户数为9.31亿,用户月使用总时长为239.74亿小时。因此,本研究以抖音平台为例,从2022年11月至2023年2月持续关注跟踪30位抖音平台中粉丝在数百万以上的民族地区短视频网红主播,分析这些短视频生产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
短视频场域虽然属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但各族用户们通过互动交往所建立的情感并不是虚假的。社交情感交流也许更容易通过面对面来实现,但在数字媒体中也同样常见和有效。(14)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董晨宇、唐悦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6页。线下各民族群众间的互动交往关系正逐渐迁移至短视频场域中。民族地区主播生产的短视频除了短视频内容生产本身以外,还生产抽象的族际关系和社会意义。总之,可以说,短视频加强了各族用户之间的互动连接性,已经成为各族用户交往交流交融不可忽视的媒介场域。在此场域中各族用户基于数字化、符号化的技术形式,获得多维度的社会临场感体验。短视频作为新的族际互动场域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开辟了新空间、注入了新动能。
二、时空与主体:短视频内容生产的多重维度
短视频作为“内容社交新媒体”,在其场域中的族际互动除了具有社交功能(如评论、点赞)外,比起一般的社交媒介更注重民族信息的内容生产。毫不夸张地说,内容生产是短视频的灵魂和核心环节(15)吕永峰、何志武:《逻辑、困境及其消解:移动短视频生产的空间实践》,《编辑之友》2019年第2期,第86-90页。,也是短视频场域中民族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动力因素。根据本研究关注的主播,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包括时间、空间与主体等多重纬度的叙事。
(一)短视频内容中时间节奏的控制
短视频内容按照时间维度进行分类,可分为日常生活时间与民族仪式时间。民族地区主播生产的短视频中日常生活时间打破了线下日常生活时间的连续性和模糊性,呈现的日常生活时间是中断式、碎片化的,同时又是清晰确定的。举例来说,“新疆优素福”将自家熏牛肉的过程分成了准备熏牛肉、熏牛肉以及燎牛头三个短视频;“迷藏卓玛”将去亲戚家帮忙盖房的事情分成与妹妹一起挖土以及集体协作搬石头两个视频。这些短视频中民族地区主播通过短视频技术将原本线性流动勾连的日常生活时间切分、嫁接成具有边界且清晰的短视频日常生活时间。
中国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仪式,相较于日常生活时间的开放与含混,仪式时间是封闭完整且秩序井然的。仪式时间在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的选择控制下呈现零散、碎片化的特点,但不同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对短视频中的仪式时间控制形式不同,其呈现的仪式时间特点也不同。比如“苗妹杨沐贤”近50个短视频呈现的是苗族每隔13年举办传统祭祖仪式“鼓藏节”(16)“苗妹杨沐贤”在其短视频标题内容中写道:“鼓藏节是远古苗民祖先流传下来的一种古老祭祖礼仪,每隔13年举办一次,寓意来年风调雨顺、怀念祖先、富裕安康的生活。”中的饮酒宴席、跳芦笙等无序片段;“吾买尔大叔”关于孙子摇篮仪式的短视频内容主要是准备抓饭、招待客人就餐以及摇篮仪式等部分片段;“西藏兄妹(索珍&加措)”根据藏历新年线性时间顺序包括“制作切玛”“初一接水”“做人参果饭”“吃切玛”等有序的仪式时间。
(二)短视频内容中空间意义的生产
根据短视频内容中民族地区主播与其所在空间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中性背景的空间与意义生产的空间。大多数短视频内容中的“空间”构建了短视频意义的完整性,这既来自于各族用户视觉上的物质空间完整性,也包括了该空间在短视频内容中民族符号叙事及意义生产的完整性。与抖音平台中其他类型的主播相比,大多数民族地区主播的短视频内容生产中所呈现的日常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例如,被网友称为苗族李子柒的“苗家阿美”,其视频内容空间主要是湘西苗族特色村寨、苗族传统的住宅内部;“那曲拉姆”视频内容的空间多在藏区高海拔的山坡、藏式民居内;“牧民达西”视频内容的空间主要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蒙古包内。在这些短视频内容中民族地区主播不仅“在空间”中实践,还“与空间”进行了互动,因而构建出具有诗性意义和民族风情的空间叙事。
还有一些民族地区主播的短视频内容生产中“空间”作为中性的背景,在视觉秩序上与主播处于同构关系中。比如“欧可爱”“嘉曦(2月26日生日)”及“布依姐”等主播的大部分短视频内容中空间都只是客观的背景形态,并不生产意义。但从空间与主体的关系角度而言,这些短视频内容中的无意义空间本身也是在生产意义,表达了空间的从属与边缘意义。
(三)短视频内容中的主体呈现
第一,各族用户的主位表达。在短视频内容生产中,各族用户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位”表达者,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进行本土文化的叙事。(17)朱靖江:《村落影像志:从乡愁标本到乡建助力》,《民族艺术》2020年第4期,第89-95页。一方面,短视频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带动更多普通少数民族用户通过短视频内容生产进行自我表达;另一方面,短视频在传播过程中普通少数民族用户获得流量后成为网红主播,又带来了短视频中心化、圈层化的传播模式。相较于普通的少数民族用户,民族地区主播的主位表达意识更强。本研究关注的民族地区主播超过一半以少数民族生活或文化为短视频内容生产的主题,其中有7名在个人简介中明确提出要展现、宣传自己民族的文化,比如“苗族阿美”在简介中写自己是“苗族文化传播者”,并且所有短视频都带有“还原苗族生活本色”的标签。这也促使短视频内容生产相对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而言,更具异质性、流变性以及多元性。
第二,各族用户主体间“米姆”式内容生产。“米姆”(meme)(18)该词也译为“模因”,于由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1976)一书中引入,其相应词根源自希腊语“mimeme”。是“一个可以用来描述模仿行为的文化单位”(19)理查德·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短视频“米姆”式传播指的是通过对源自短视频或其他媒介形式的原生“米姆”的继承、扩展或修改而进行的短视频衍生化内容生产与传播。(20)奚路阳、程明:《短视频米姆式传播:行动逻辑与社会文化意涵》,《传媒观察》2022年第7期,第65-72页。有许多受欢迎的短视频内容在各族用户的二次创作下形成了大量衍生的“米姆”式短视频。“云南傈僳族小伙——蔡总”翻唱《我是云南的》引起短视频场域的“米姆”式传播。在抖音被命名为“全国各地来上分了”话题,在该话题下各族用户用各族语言或地方方言进行了“米姆”式内容生产,话题播放量累计110亿次。还有视觉化“米姆”式传播的短视频。比如,民族服饰落手秀是近年非常热门的“米姆”式短视频,抖音平台中“落手秀民族服饰”相关话题就有超38亿次的播放量。各族用户通过“米姆”式的短视频内容生产进行叙事表达和自我呈现,同时也促使民族团结的意义在各族用户主体之间传播。
第三,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的身体形象构建。首先,短视频内容中的民族特色服饰展示是一种场域内的身体实践。服饰和装饰作为身份的一种视觉隐喻与身体处于互构关系中(21)Davis, Fred, Fash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13.,成为短视频内容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例举的民族服饰落手秀就是对少数民族服饰配饰的视觉化展演,民族地区主播伴随着音乐,在抬手与落手间从普通甚至邋遢的日常装扮转变成精美的民族装扮。例如,“琪琪琪有此理”“阿靖zi”和“鸟木”等民族地区主播的短视频内容大部分都是类似的变装秀。在民族服饰变装秀的内容生产中,民族地区主播的身体成为各族符号的表达,也是中国民族文化丰富多元性的化身。
其次,短视频内容中身体意象的媒介呈现。短视频场域中的身体意象指民族地区主播“对于自己身体外形的感知和态度”(22)Mills, Jennifer S., Amy Shannon, and Jacqueline Hogue, “Beauty, Body Image, and the Media”, Martha Levine, eds., Perception of Beauty, London:InTech, 2017, pp.145-157.。大部分短视频内容中民族地区主播身体形象是自然、淳朴的风格,有一些民族地区主播如“布依姐”“苗妹杨沐贤”“月野兔是苗族小姐姐“等会使用滤镜和美颜来修饰自己的身体形象。无论是否使用滤镜,短视频内容都反映了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的身体意象。因为身体把自身借给了图像,图像才将“自身”构造为身体的镜像。(23)周午鹏:《技术与身体:对“技术具身”的现象学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98-105页。不使用滤镜的民族地区主播常常以“原生态”标签来进行身体形象的建构,而使用滤镜的民族地区主播身体意象反映了其对完美身体的想象。本质而言两者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只是后者身体形象失真致使各族用户对其短视频内容的怀疑,比如“嘉曦”在其短视频中就使用美颜效果导致背景扭曲失真被粉丝用户发现后质疑。
总之,民族地区主播从短视频的符号世界内部去思考、感知、演说或表征物质世界(24)林文刚:《媒介环境学》,何道宽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年,第28页。,因而其在短视频内容中“展演”既是一种对外的时空微观叙事,也是属于其自身生活中创造意义的实践。由此,短视频内容的生产不是静态复合体,而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集合结构。
三、具身认知:短视频内容生产中各族用户主体间性的呈现
短视频作为新兴技术改变了各族用户知觉的形式以及经验世界的方式,各族用户通过肉眼观看和以短视频技术为中介观看到的差异,正如唐·伊德话语体系中“人—世界”的关系与“人—技术—世界”的关系之间的差异。(25)王颖吉、楼程莉:《技术与科学视角主义的建构——浅析唐·伊德的视觉媒介技术观》,蒋原伦、张柠主编:《媒介批评·第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3页。具身关系构成了所有“人—技术”领域中的一种生存形式(26)唐·伊德:《技术现象学》,韩连庆、吴国盛编译,吴国盛编著:《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0页。,是指人借助技术来感知并由此转化成人的知觉和身体的感觉。(27)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8页。伊德受梅洛—庞蒂现象学身体的启发,以眼镜为例说明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当人戴眼镜后,原来作为技术中介的眼镜就成为了人的身体延伸,人并不会意识到眼镜的存在,这时人与眼镜就形成了具身关系。(28)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基于当下手机触屏与短视频技术具有高灵敏度、反应迅速准确等使用体验感,短视频已不只是简单的再现客体,而成了各族用户在短视频场域中产生互动的身体延伸,各族用户也“用整个身体来知觉”(29)唐伊德:《技术现象学》,韩连庆、吴国盛编译,吴国盛编著:《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7页。短视频内容。因而在短视频场域中,各族用户与短视频技术之间的关系亦包含具身关系结构。伊德将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图示化为“(人—技术)→世界”。民族地区主播生产的短视频场域之具身结构则为“(各族用户—短视频技术)→短视频内容”。但各族用户与短视频技术之间的具身关系结构并不是一致的,除了各族用户的个体差异以外,民族地区主播在短视频内容生产中采用的视角也会影响各族用户的具身认知。需要强调的是,有一些民族地区主播主要采用其中一种内容生产视角,但多数民族地区主播在短视频内容生产中混合使用多种视角。
第一人称视角,即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的主观视角。一些民族地区主播从自己的视角拍摄短视频,例如“草原乌音嘎”拍摄自己大年初一喝蒙式奶茶过程;“新疆优素福”从第一人称的视角与家人日常互动;“洛桑和小志玛”拍摄在山上采摘各式野生蘑菇的过程。此时主播的拍摄镜头就成了各族用户身体的延伸——眼睛,短视频的内容也就成了其目力所及的内容,视听知觉在民族信息环境中得到扩展。各族用户在观看第一人称视角的短视频时,能即时性、沉浸式地代入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的主观视角与其所处的环境交互,去知觉短视频内容,而这些知觉体验也转换为各族粉丝用户身体经验的一部分。
第二人称视角,即各族粉丝用户的主观视角。这种视角的短视频内容生产基于民族地区主播与各族粉丝用户对话交流,因而短视频内容中最常用的称谓是第二人称“你”“你们”“家人们”等。例如“金花阿妈妮”“宝鲁日”“西藏兄妹(索珍&加措)”等主播的短视频内容中多数是自己一边做着民族特色美食,一边与屏幕另一端的粉丝用户或讲解美食做法或调侃闲聊。在此类短视频中,短视频技术“准透明性”(30)吴宁宁:《对伊德“人—技术关系现象学”的辨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5第3期,第145-151页。更为凸显,各族粉丝用户从“身体—主体”出发与民族地区主播身体进行交互,具身性地融入短视频内容去认知。
第三人称视角,即短视频内容生产的客观视角。此类短视频内容主要以旁观者的视角呈现。如“洛桑和小志玛”呈现藏族汉子洛桑或带女儿志玛到山上识别传统草药或为女儿做各色美食;“旅途(宁夏牧飒)”的短视频主要是西北少数民族家庭成员温馨互动日常;“馕饼妹”的短视频以维吾尔族家庭的搞笑段子为主。不同于前两种视角的短视频通过扩展身体与虚拟情境以及加大主体间的交互性,让各族粉丝用户具身化地知觉短视频内容。第三人称视角的短视频内容的画面艺术感、故事趣味性以及情绪感染力等更强,给各族粉丝用户带来极强的临场感和沉浸身体体验。
短视频作为具身的视听技术有“放大—缩减”效应(31)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0页。,放大了各族用户对民族文化信息的视听知觉,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身体的其他知觉。以火把节为例,抖音平台中“甘孜文旅局局长刘洪”“彝之微爱 甲古阿支”等主播有关火把节的短视频主要是藏彝火把节中的服饰、舞蹈或热闹场面等视觉化的内容展示。各族用户在评论中也多是“民族服装太美了”“局长好适合彝族服装”“这个配乐绝了”等。而在现实物理空间中观看火把节(32)周晓钟:《走进白马藏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4页。周贤中(笔名周晓钟)记录自己1983年参与白马山寨火把节的知觉感受:“寨坝中的篝火燃起来了,呼呲呲地跳动着熊熊的火苗,在暮色的雪海中特别耀眼。节日的夜晚,空气中弥漫着腊肠熏肉和青稞酒的浓厚香气。‘啊——火火,开始啰!’”虽然也属于视觉实践,但是其调动的知觉更为复杂丰富。可以说,各族用户在短视频场域中的知觉体验中,视觉存在被强化甚至过度强调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而言,在短视频技术的“放大—缩减”效应中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各族用户抽象、简化地感知为少数民族装饰文化。
总之,短视频能让各族用户的视觉、听觉在“数字化”的作用下进入虚拟的短视频场域,构建各族用户身体觉知与短视频场域交互的认知图景从而产生沉浸性、临场感的具身性体验。但由于短视频技术对各族用户视觉的强调和放大,各族粉丝用户知觉短视频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缩小了。唐·伊德只考虑到人与技术的二元关系,而没有注意到在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对于技术的影响。各族用户在短视频场域中的具身体验进一步说明人与技术不是唐·伊德的二元关系,而是“人和非人组成的链”(33)Latour, Bruno,“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8, no.1,1990, pp.103-131.。
四、情感共鸣:短视频互动生产中族际生态的构建
短视频不仅是“内容生产”的技术,还是连结人与人关系的“连接性媒体”。(34)Van Dijck, J., &Poell, T.,“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Logic,”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1, no.1, 2013, pp.2-14.短视频除了为各族用户提供了文化自我表达和意义生产的窗口,更重要的是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搭建了一个新的桥梁。
(一)短视频场域中族际交往的特点
各族用户围绕民族地区主播生产的短视频场域进行的互动实践,包括观看、点赞、评论、关注、私信等。与传统面对面的线下族际交往,以及其他社交媒体中的族际交往相比,在短视频场域中族际交往所呈现出的特点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短视频场域中的族际互动以民族地方知识的内容生产为互动核心。如前文所述,内容生产是短视频的核心,与其他媒介的族际交往不同,短视频场域中的族际互动围绕着内容而发展。本研究跟踪民族地区主播发现,其短视频中涉及民族“地方知识”的短视频获得的有效评论数通常要高于其商品植入的短视频。这里的有效评论是指民族地区主播与各族用户以及各族用户之间的互动评论,在很多时候呈现的是“地方知识”的传播。例如:“西藏兄妹(索珍&加措)”关于2023年藏历新年一系列的短视频评论区中各族用户交流讨论汉族新年、藏历新年的日子,“都灵城上望明月”评论道“问下,他们不是过藏历新年么???也过春节??”“玉树小小罗”回复“我是青海玉树藏族,我们既过春节,也过藏历新年”;“一米阳光”也问道“藏历新年是每年的二月二十一,还是每年都不一样的啊”“西柚莫名”回复“按藏历走的,藏历的1月1号就是藏历新年,每年的公历时间不一样。跟汉族的农历差不多”;“奢侈”问道“今天是你们当地过年?”“安静”回复“林芝的年是工布年,这是前藏的年吧?”这几句各族用户的评论互动虽只是藏族地方知识双向传播的小片段,借此亦可一窥短视频场域中族际交往的深入与密切。
第二,在短视频场域中的族际互动以符号为互动载体。人是符号的动物(35)恩斯特·卡西尔:《哲人哲语:符号形式的哲学》,赵海萍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261页。,因而短视频场域中各族用户之间的互动,也属于一种符号互动。短视频场域中各族用户除了以文字符号、表情符号及图像符号等进行社交媒体中的常规互动以外,还会以少数民族特色符号进行互动。短视频场域中族际互动常用的少数民族特色符号主要包括少数民族音乐、虚拟民族符号特效。各族用户在自己的短视频内容生产中多偏好使用民族特色音乐作为背景音乐。以虚拟民族符号来说,抖音平台中有“蒙古姑娘”“彝族姑娘”“民族姑娘”等虚拟的民族装扮符号特效吸引了大批女性用户在短视频内容生产中使用。多个民族用户使用同样的民族特色符号进行微观实践也是各民族群众在短视频场域中虚拟交互的具体体现。图像符号与评论区的表情符号、文字等作为各族用户互动的表现形态和意义载体,建构了丰盈复杂的族际关系网络。短视频场域中的族际交往不仅建构多层次的符号互动,也是一个各族群众间情感意义共享的过程。
第三,短视频场域中各族用户通过具身的实践方式进行互动。具身是各族用户在现实与虚拟、主体与客体的重叠结合中相互影响的复杂身体处境。具体来说,表面看起来各民族用户在短视频场域的族际互动中是缺场的“肉身”,在场的“化身”。然而,在短视频场域中各族用户被重构为交往中的身体—主体(36)孙玮:《传播再造身体》,《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11期,第5-11页。,使用短视频进行族际交往的过程在手机屏幕中呈现的是“虚拟身体”,但各族用户都是从身体—主体出发去知觉、互动。当各族用户在观看民族地区主播的短视频时,通过向上向下滑动屏幕的手指姿势和打字的手指运动模式,进行短视频的即时点赞、评论以及讨论。各族用户正是在使用部分身体(手指)进行即时互动的过程中也逐渐熟悉这种具身互动的形式,并将之内化为身体的知觉体验,同时短视频场域中互动的身体感知体验被“融入于”新形态的族际关系中。因此,在短视频场域中的族际交往是各族用户作为身体—主体的具身交互实践,其具身关系不仅包括各族用户与短视频技术的具身关系,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各族用户间的具身互动。本研究通过探索身体是“活生生”的动态生产性过程,提出短视频场域中各族用户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是具身的,以驳斥社会建构主义将身体视为社会文化结构的被动建构客体。
第四,短视频场域中族际互动呈现动态开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指各族用户在此场域中的交往对象来源更为多元、异质,从而使得各族用户社交关系的建立也更为开放。线下的族际交往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大多数社交媒介(微信、QQ)等中的族际交往模式主要是基于原有社会关系的更新。而短视频场域中的族际交往包括了基于各族用户对民族地区主播短视频内容的喜好而建立起的趣缘关系。比如“金花阿妈妮”“新疆味道”等主播吸引了许多爱好民族美食的各族粉丝用户,在短视频评论区或粉丝群内交流民族美食的制作方法与品尝民族美食的店铺等。此外,短视频“同城互动”功能设置下的地缘关系,以及“关注”功能中连接用户通讯录的血缘、业缘关系等。因此,短视频场域中的族际互动不仅打破了各民族群众线下交往的物理空间范围,更突破QQ、微信等互联网社交媒介基于熟人关系的半封闭互动形式,呈现围绕短视频内容生产而不断聚合又散开的动态开放特点。
(二)短视频场域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构建
从理论内涵来看,各民族“三交”是一个层级递进的关系结构(37)王延中、章昌平:《新时代民族工作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5-27页。、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民族交融是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的本质要求(38)金炳镐、肖锐、毕跃光:《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6-69页。,是指民族之间相互接纳、吸收、包容和认同(39)罗彩娟、蓝尉铭:《以节为媒: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机制——以广西布努瑶祝著节为例》,《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44-153页。。在数字化时代,短视频中的族际互动是各民族“三交”中不可忽视的新形态。短视频场域中的族际互动突破了传统线下族际交往中面对面的互动方式,缩短了各民族群众交往的物理空间距离,提高了各民族群众互动交往的频率,拓宽了族际交往的渠道和交往方式。
短视频不仅是生产、传播民族信息的中介,其内容生产涵盖丰富多元的民族地方知识,同时还是各族用户具身认知民族文化的场域,让各族用户了解彼此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此外,各族用户围绕短视频内容生产而展开的评论与讨论,促进了用户间的互相尊重与欣赏,他们在此场域中互动交流、包容差异,继而激发出各民族用户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内生动力。因此,短视频场域也成为了增进各族用户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场域。
本研究认为,短视频场域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指,各族群众虚拟化为短视频用户,通过虚拟的文字影像符号进行微观叙事及具身互动,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更为坚固的情感联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据短视频场域中族际互动的特点,本研究试图提出促进各族用户交往交流交融的可能路径。
其一,从族际互动的核心维度,鼓励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进行民族地方知识的生产。短视频之所以在当下如此盛行,与其多元化的内容生产有直接关系,短视频内容生产的丰富性也决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效果。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可以依托民族地方知识的传播,增强其内容的丰富性。正如格尔兹所说的,“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地方知识,我们更需要一种方式来把各式各样的地方知识转变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评注”(40)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杨德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66页。,短视频的生产恰是可行的方式。
对地方知识的呈现形式很大程度上又影响族际交流交融效果。举例来说,“苗妹杨沐贤”有期短视频是介绍贵州苗族招待客人的特色食物——凉拌生猪血,该期视频点赞量最高的评论是用户“今生随缘”:“生猪血,恶心,就是血流出来凝固了(震惊表情)”。另一主播“耶叔,一个人吃饭”同样介绍苗族凉拌血旺时介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该菜肴的大致历史渊源,其粉丝用户的评论不像“苗妹杨沐贤”短视频粉丝用户的评论,主要是对该菜的吐槽和反感,而更多是对该饮食习俗的尊重以及讨论民族习俗文化等有效互动。因而,短视频内容生产可以鼓励民族地区主播针对不同民族地方知识的丰富内涵,促进短视频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传播,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其二,从族际互动的互动载体维度来说,通过讲好民族符号故事,增强各族用户对其他民族的认知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承德考察时指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在短视频场域中讲好民族符号的故事才能更好提高各族用户的参与感与互动性。比如,“阿靖zi”和“鸟木”的短视频内容都是民族服饰变装秀,但不同的是前者呈现的是她在变装前参与该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各族用户围绕“鸟木”短视频的讨论也多如“很帅”的评论,而“阿靖zi”的互动中更多是“果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噢麦嘎嘎)、“……多为民族代言,展现大美中国”(阳光晒满人间)的评论。可见,讲好民族符号故事的短视频能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民族的互动与交融,并在此过程中强化各族用户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民族地区主播为了获取流量而将民族符号狭隘化甚至丑化。比如“布依姐”“嘉曦”等主播的短视频内容主要是穿着民族服饰对口型唱歌,丰富的民族符号在其短视频呈现出扁平化、狭隘化倾向。“云南佤族黑妹”常特意穿比自己身材稍小码的民族服饰唱歌,通过呈现不符合大众审美的臃肿邋遢形象与其高亢明亮的歌喉制造反差感而吸引流量。虽然这些民族地区主播获取了一定的流量,但是在其内容生产中民族符号更多只是无意义的流量工具,无益于民族间的交流交融,甚至可能导致各族用户形成对该民族的刻板印象。
其三,根据民族互动中的具身性、开放性特点,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与平台应注重以民族团结为前提培育各族用户民族互动行为,促使各族用户在互动中建立起情感体验。对于民族地区主播而言,可以通过“吸粉”“固粉”等行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其短视频中多使用“少数民族风情”“少数民族生活”等标签,以吸引那些对少数民族风土人情感兴趣的各族用户关注他(她),与各族用户建立弱连接。(41)本研究认为在短视频场域中族际互动可以按照大致的互动频率与熟悉程度等分为强连接、次强连接与弱连接。强连接用户主要指在评论区、粉丝群与民族地区主播保持长期互动并对其非常熟悉的各族用户“铁粉”;次强连接用户主要指关注了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并偶尔在评论区或粉丝群与其互动的各族用户;弱连接用户主要指观看民族地区主播短视频并点赞的各族用户。同时,通过生产更多讲好民族符号故事的高质量短视频与交互式短视频,提高各族用户具身体验,与弱连接以上的各族粉丝用户保持有效互动,从而建立坚固的情感联结,实现民族间更深层的交融。
对于短视频平台而言,首先将民族团结议题相关的短视频内容与各族用户的习惯、需求匹配,进行更为高效且精准的投送。借助用户画像、推荐算法技术手段把优质的短视频推送给更多可能感兴趣的各族用户,并鼓励各族用户生产关于“民族团结”议题的内容。其次,围绕短视频内容生产场景进一步加强社交互动功能设计,提高各族用户在内容互动中的临场感与参与感,促使各族用户建立积极的身体感知和具身体验。此外,推进短视频平台与其他社交媒介平台的通联系统,构建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全媒介平台,实现民族地区主播优质短视频的广泛传播及其在社交圈层的裂变,从而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42)《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2021年9月26日,https://news.cctv.com/2021/09/26/ARTIK9bDsxG8RDkpuGoey5sG210926.shtml?spm=C94212.PirFnyxHi2TB.S16152.1,2023年8月14日。。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族际互动的形态发生了新的转变,短视频已经成为各族用户交往交流交融不可忽视的媒介场域。短视频作为“内容生产的新媒体”,民族地区短视频主播的多元化“内容生产”既是其构建自身生活的意义实践,也是其对外交流的微观叙事。同时短视频作为“关系生产的新媒体”,各族用户在短视频场域中具身地认知与互动,不仅加强了民族文化信息的传播与交流,也使得各民族处于一种相互交织、嵌入的互动连结状态,并在此状态中逐渐建立情感。而本研究根据短视频场域中族际互动呈现动态开放的表现形式,具有以民族地方知识生产为互动核心、以符号为互动载体、以具身实践为互动方式等特点,试图提出在短视频生产过程中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可能路径,从而促使各族用户形成更为坚固的情感联结,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