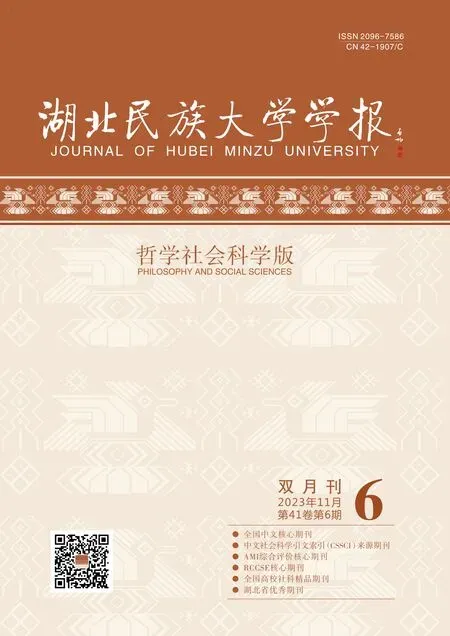现代“民族”概念的中国本土化及其“多元一体”特征
2023-03-02胡兆义
胡兆义 曾 嘉
中文“民族”一词的来源及其定义一直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学术界对该词的来源众说纷纭,其界定也比较模糊,外延比较宽泛,使用不够严谨,这导致中国民族研究的诸多困惑和分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国内外发展大势,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勇担民族工作面临的新时代历史任务,创新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理念,推动其写入党章,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第4-35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我们分析民族的概念提供了价值指引和全新思路。2023年2月,中央统战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深化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概念内涵外延的研究。”(2)《中央统战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国民族》2023年第2期,第4-5页。在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中,概念界定具有基础性,没有统一的概念就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因此,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重新审视和理解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透过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而探索其本质及特征,对于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民族概念的产生及内涵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建立和民族主义传播,“民族”一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具有了多元含义,具备国家形式的人群与具有共同历史文化或血缘联系却不具备国家形式的人群都用民族来指称,且同时出现于各种民族理论之中用于解释各种形式人群的产生、发展及相互关系,由此造成民族概念使用的混乱。但是,查阅已有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在民族概念指称的所有群体中,本源性的是指最早形成并随着民族国家构建而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深远地影响着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形成。(3)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79-98页。这类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诸多学者将之称为“国族”,以指代国民共同体,并与英文nation相对应。
Nation作为现代政治范畴,作为国族意义上的民族,首先出现于西欧。5世纪下半叶,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步入中世纪时代,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以封建割据为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罗马教皇成为整个西欧社会的最高权威。9世纪,几乎覆盖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查理曼帝国在外族入侵下崩溃,一些强大的封建王国在英格兰、法兰克等地区诞生。11世纪至13世纪,欧洲的农业增长,商业逐渐繁荣,城镇发展,人口增加,教权和皇权都得以巩固;另一方面,英国和法国发展成为中央集权国家,两国的国王对国家的控制逐渐加强,并发展出英国的议会和法国的三级会议这种由被统治者来限制王权的制度。(4)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杨宁、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14世纪和15世纪,君主们在与教皇及领土上的贵族进行斗争中逐渐胜出,教皇权力被大幅削弱,英格兰、法国、西班牙、俄国各自建立了稳定的中央集权政府,开始走向主权国家的道路。在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与世俗王权相结盟,既摧毁了罗马教廷的神圣权威,也消灭了割据的地方领主,并建立了绝对主义的君主国家,进而使“国王”和“王权”取代了原有的“上帝”和“神意”,人文主义思潮也相伴而生。(5)周传斌:《概念与范式:中国民族理论一百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31页。在教权和皇权同时存在并相互争斗的过程中,王权逐步加强,而民众的自我意识尤其是权利意识也在城市工商业及其促成的市民阶级兴起的基础上逐渐觉醒,文艺复兴中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的传播更是起到了促进作用,国民整体的民族意识觉醒和增强,之后,资产阶级革命将国家由“王有”转为“民有”,使“君主之国”成为“民族之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国家形态最终形成(如英国和法国),如此一来,国家具有了民族的内涵,得到一个有组织的国民群体的支撑,而民族也有了国家的形式,并获得了制度性的确认和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即国族。(6)参见周平:《现代国家基础性的社会政治机制——基于国族的分析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79-98页;周平:《中国何以须要一个国族?》,《思想战线》2020年第1期,第106-114页。
Nation虽然是一个现代政治术语,但其具体定义一直含糊不清。厄内斯特·勒南将nation视为“一个灵魂、一种精神原则”,认为nation的存在“就是日复一日的公民投票。”(7)厄内斯特·勒南、陈玉瑶:《国族是什么?》,《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第59-69页。安东尼·D.史密斯将政治、法律、领土、历史文化、经济等要素都包含在nation之中,并强调“某种政治共同体意识”是其含义中不可或缺的因素。(8)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15-21页。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nation的出现与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息息相关,是一项相当晚近的人类发明,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9)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0页。德拉诺瓦也认为nation与明确的疆域概念和严格的主权概念相关,是现代建构与历史演变结合的产物。(10)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2-58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直接指明,nation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并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7页。由此可知,无论西方学者是否将nation这样的“民族”群体与历史文化或血缘相联系,都无法脱离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因素,它是在人类社会漫长历史发展中已经具备了某些要素和基础,并在16世纪后随着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新教、资本主义经济等现代性元素出现,在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权发生利益冲突、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民族国家的情况下而产生,与现代国家(state)紧密结合,用于指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国民共同体,是拥有现代国家疆域、享有国家主权并具有高度国家认同感的人们共同体。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所追求的“一国一族”“一族一国”,本质上是建立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nation就是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即国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nation这一层次的民族是指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实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成的命运共同体,是支撑中国民族国家制度的国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各族群众必须牢固树立中华民族认同,并自觉承担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应尽义务。
二、现代“民族”概念的中国本土化
中国的民族概念到底是舶来品还是本土产生,学术界看法不一,并由此形成外来说和本土说两类观点。外来说认为,中文“民族”一词是近代由国外传入中国。林耀华早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汉语“民族”一词可能首先是从日文转借过来的,时间大约在辛亥革命前夕,章炳麟在《序种姓上》中的论述可能是最早有关“民族”一词记载之一。(12)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的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第171-190页。金天明、王庆仁认为,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出现“民族”一词的文献,是1899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且是直接引自日文。(13)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第89-94页。韩锦春、李毅夫指出,汉文中的“民族”一词是在中国近代才出现,很可能是从日本传入的,最早使用该词是见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载于《强学报》上题为《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的文章。(14)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第36-43页。吴仕民也认为现代“民族”一词始自1899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日本借用汉语“民”“族”两字翻译英文nation一词,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15)吴仕民:《民族问题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此外,还有学者虽然赞同“民族”一词的外来说,但认为其并非来自日本。1985年,彭英明撰文指出,“民族”一词是近代传入中国,但最早使用该词的是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撰写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且该词来源也不会引自日文,可能是来自英语。(16)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5-11页。
另一方面,本土说认为民族的概念是在中国本土产生,是中国固有之词汇。2001年,茹莹在其文中指出,汉语“民族”一词是中国本土词汇,最早出现于唐代李筌所著兵书《太白阴经》的序言中,它虽然不具备现代民族的内涵,可是汉语“民族”词汇绝非近代的“舶来品”。(17)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第1页。邸永君也一直坚持“民族”来源的本土说,认为《南齐书》卷54《高逸传·顾欢传》中“民族”一词的内涵与现在民族概念所指接近,并推测日本所用“民族”一词可能直接取自汉典。(18)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98-99页。郝时远对中文“民族”一词的源流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民族”是中国古代文献固有之名词,其含义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故“民族”一词由中国传入日本可能更符合事实,很可能是在19世纪70年代或之前传入日本,并在日译西书中对应了volk、nation、ethnos等名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19)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第60-69页。龚永辉也持此观点,认为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古籍中就有“民族”二字连用,汉文献中代代相传的汉语民族概念形成了一条古籍链,其用法与我们当下所用民族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通。(20)龚永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体系》,《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1-10页。
综合来看,无论是外来说还是本土说,学者们对“民族”一词的来源和出现虽然存在不同看法,但普遍认为“民族”一词被广泛使用及其与英文、俄文中有关“民族”的词汇相对应并具备现代民族的含义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在抵御外敌入侵、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社会背景下被普遍接受,成为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概念。20世纪初,随着“民族”一词的普遍使用,国人对其内涵进行了介绍和探讨。1903年,梁启超将政治学家布伦奇里的民族概念引入中国,指出民族最重要的特质有八个,即共同的地域、血缘、肢体形状、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生计等,并对这一概念进行提炼和改造,赋予其深厚的政治内涵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带有中华现代国家范畴的政治共同体意涵”(21)江也川:《从“种族”到“民族”:论梁启超民族思想的初步自觉》,《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43-57页。。1924年,孙中山在阐述三民主义时提到,民族是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五种巨大压力所造成。1938年,张仲实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译成汉语在中国出版。在这篇著名论文中,斯大林为民族(俄文为Нация)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斯大林卷》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2页。斯大林将这四个要素视为民族的一切特征,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个民族,并强调民族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而非普通的历史范畴。该定义将血缘联系排除在民族特征之外,进而将民族与种族、部落相区分,具有明显的现代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对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无论是梁启超、孙中山,还是斯大林,其所谓的“民族”均具有明显的政治实体含义,相当于英文的nation,无法准确描述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展开全面反思和修订,尤其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定义提供了崭新思路。随着源于西方的族群概念的传入和使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族群”与“民族”之争,民族概念的中国化探索更加深入。进入21世纪,为了准确分析中国民族现象,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05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一词进行了新界定:“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2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这一定义不同于之前国内外学界对民族的界定,对于中国复杂的民族现象具有很强适用性,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族及国情的准确把握和深入认识,从而能够辩证看待、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斯大林现代民族概念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24)杨须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概念及其语境考辨——兼论“民族”概念的汉译及中国化》,《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第1-16页。但是,该定义将民族内涵止于生物性和文化性的“族裔”或“族群”(ethnic),可以涵盖中国的56个民族,而无法包容具有现代国家或“国族”涵义的nation。(25)潘志平:《Nation及“国族一体”论》,《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61-69页。尽管这一定义有着非常中国化的色彩,但它更适用于族类共同体性质的民族(即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具有同一文化或血统的共同体,如国内的56个民族),而不适用于国家民族(即与现代国家一体两面的国民)。(26)《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与思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21年,第48页。因此,鉴于中国民族概念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一些学者放弃对其进行重新定义的尝试,而只是对其进行一些宽泛的描述。
三、中国特色民族概念的“多元一体”特征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多元一体是对中华民族结构的一种高度概括,但多元一体也体现着一种事物结构上的规律性,即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由不同元素紧密结合而成的整体。(27)参见王希恩:《再倡“多元一体主义”》,《学术界》2018年第8期,第86-93页;胡兆义:《多元一体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及特征》,《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46-56页。“民族”一词的中文含义十分复杂和难以界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本土性,体现出显著的“多元一体”特征。多元是指中国民族概念的思想来源具有多元性,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大一统”和“天下观”基础上形成的族类概念,又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借鉴了西方民族主义话语,更结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相关论述,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工作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一词。一体是指无论中国民族概念的思想来源多么复杂,无论其涵盖什么层次的人们共同体,都可以用中文“民族”一词来指称。
“民族”一词吸收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大一统”和“天下观”基础上形成的族类概念。中华大地自古就生活着众多族群,族际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间断,并对族际之间的特征差异有了直观感受和书面记载,形成了华夷五方格局。中国传统的族类概念历史久远,有人、民、族、种、类、部等多种表述,“民”一般是指民众或百姓,“族”用来指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宗族、氏族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虽然没有出现将“民”和“族”合在一起使用并与现代所谓的“民族”相对应的情况,但古代族类划分标准中实际上已经包括了语言、地域、经济、风俗等民族的要素。因此,中国古代虽未出现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概念,但是族类划分标准与现在的民族内涵大体一致,包含着民族的一些要素,其实质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民族概念。(28)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第5-11页。在古代中国,人们一方面以文化为标准形成“华夷之辨”的族群观,根据语言、风俗、礼仪等对人群进行划分,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华夷之辨产生于西周末叶至春秋中叶,在中原华夏与周边族群的交往中,面临“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形势,华夏诸族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孔子更是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另一方面,古人又提倡“夷夏一体”,认为华夷之间可以转化,如孔子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韩愈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至中国则中国之”。这表明华夷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传统中国这种兼容并包的族群观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传统族群观是在“大一统”格局中形成并为“大一统”基础上的“天下观”服务。“天子”在统治中原地区的同时,通过和亲、互市、征讨等多种途径向四周“蛮夷”施以“教化”,以维护自身“天朝上国”的地位和“天下”格局。(29)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156页。历代政权在逐鹿中原、实现一统的理念下形成以“天下观”为基础的国家观念,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海之内皆兄弟”,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直接说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以朕如父母”的名句。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将“大一统”作为最高政治目标,如汉朝主张“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隋朝提倡“协同内外,混一戎华”,元朝奉行“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清朝学者提出“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之人也”。传统的“族类”概念就是在“天下观”及“大一统”基础上形成并为这一理念服务。
“民族”一词借鉴了近代西方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民族”成分。民族(nation)概念的形成和广泛使用,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及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形成直接相关,中文“民族”一词的产生和广泛使用则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入有着紧密关联。虽然汉语古籍中早有“民族”字样的出现和使用,并在19世纪末期就与西方的nation一词有了对应关系,但并未受到社会重视,人们依然习惯用“蛮”“夷”“族类”“民”“种”“部”等称呼,如林则徐在谈到国外民族时用的是“部”“部落”“族”“类”等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将英文nation译成“民”,康有为、梁启超此时也多使用“种族”来指代与民族共同体相关的人群。进入20世纪之后,“民族”一词开始大量涌现,尤其是在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使用下,已经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汉语词汇。近代以来,中国不仅遭受清政府的残酷统治,更面临帝国主义入侵导致的亡国灭种危机,在此期间,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民族”一词随之成为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从而得以普遍传播和使用。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族实体在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逐渐从自在走向自觉,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成为与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等一样的民族,也就是与国家(state)结合在一起的民族(nation)。(30)周平:《再论中华民族建设》,《思想战线》2016年第1期,第1-8页。同一时期,西方社会的种族概念也传入中国,这一概念将民族视为在文化及血统或生物学上具有一致性的人群,于是导致中国产生两种民族主义思潮,即强调在现存国家领土范围内全体国民认同意识的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和强调汉族、满族、蒙古族等各自意识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面对这两种民族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革命排满”,而立宪派主张“满汉一体”,双方在彼此较量中逐步接近,共同创造了“五族共和”这一具有中华民族认同特征的新文本,之后又有顾颉刚、费孝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充分反映出中文民族概念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民族”一词结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的相关论述。马克思与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研究民族及民族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留下了大量关于民族的相关论述,并使用过4个不同的德文词汇来称呼“民族”,即Volk (Völker)、Völkerschaft(Völkchen)、Nation及Naitonalität,这些德文词一般都译为中文“民族”一词,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对民族的内涵进行界定,但却在不同文章中零散地提到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地域、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感情、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工业条件等特点。(31)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6页。列宁与斯大林在建立和建设苏联的斗争中继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在文章中使用过народ、наци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ость等俄文词汇,汉文一般都译为“民族”。列宁提出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套理论,将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强调必须使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抗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系统论述民族自决权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讨论民族主义问题。(32)周传斌:《概念与范式:中国民族理论一百年》,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49-50页。斯大林第一次完整阐述了民族(нация)的定义,总结了民族消亡的规律,分析了民族运动的性质、产生根源及发展方向,阐述了社会主义民族思想,并提出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政策及措施。(33)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不同地方使用不同词汇来指代民族及与其相关的群体,而中文翻译时多统一采用“民族”一词,没有根据具体语境做更细的区分,这就容易导致理解和认识上的不一致或错位,需要我们在阅读时联系上下文和具体语境来理解,从而避免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
“民族”一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工作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并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开创者,较早使用并系统论述了“中华民族”一词,认为中华民族不仅包括汉族,还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34)《毛泽东民族工作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7页。。面对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树立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以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对内团结各族人民消除内乱以实现国家统一与和平的目标,一方面强调整体层次的中华民族,提出“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观点(3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8页。,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3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8页。,这其实是将中华民族视为西方民族主义所宣称“一族一国”中的“一族”,以达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平等和团结为基本原则处理民族事务,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民族政策,确立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观和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制度,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支持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形成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民族间的共性不断增多,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更加巩固。进入新时代,面临国际国内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准确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国情,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整体性,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的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的观点结合起来(37)《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年,第46页。,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概念,与时俱进地推动了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理论上超越欧美“民族建国主义”的群体概念(38)马英杰:《中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语义逻辑》,《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61-73页。,使中文“民族”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中华民族整体性叙事更加突出。
多元一体的中国民族概念在外延上包罗了古今中外的各种人们共同体,具有极强的伸缩性和包容性:既可以指古代民族,也可以指近现代民族;既可以指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也可以指一国内部具有历史文化共性的群体;既可以指与国家政治性质相关的群体(资产阶级民族、社会主义民族等),也可以指与文明程度相关的群体,还可以指与经济生活方式相关的群体。这充分显示中文“民族”一词的复杂性,它既不完全是nation,也不等同于ethnic group,而是多元融为一体的中国本土化概念。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都是民族,但并不矛盾,二者处于不同层次,中华民族是高层,56个民族是基层,可以并行不悖。(39)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3页。中华民族中的“民族”是中国的国民共同体或国族,享有国家主权,相当于英文nation,而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及历史上不同时期活跃于中华大地的各类人群,则是具有共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共同体,而非国民共同体,相当于ethnic group。有学者认为,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自传入中国就与“国家”联结在一起,其概念至少包括两个层次,即具体民族、与国家合为一体的国家民族,对中国而言,前者指汉族、藏族、回族等56个民族,后者指与中国国民合为一体的中华民族。(40)王希恩:《20世纪的中国民族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使用“中华民族”这一重要概念时,尤其注重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叙事,“中华民族”已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全国各族群众”“全体中华儿女”“中国人民”等特定概念的价值引领,是新时代中国人政治认同、身份认同和目标认同的关键内核。(41)青觉:《做好做足中华民族这篇“大文章”》,《中国民族报》2020年10月13日,第5版。同时,新时代“中华民族”概念具有了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观的语义,嵌入了国家政治的话语表达体系,彻底扭转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战略方向,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升华至新的历史高度。(42)徐杰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内涵与学术支撑》,《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77-86页。
四、中国特色民族概念的英译问题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了让外部世界清晰地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政策,尤其是全面准确地在全球推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统一中文“民族”一词的英文翻译十分必要。中国特色民族概念包罗了各种历史形态和各种层次的人们共同体,我们无法在外文中找到完全与其内涵对应,能够准确反映中国人使用所指的词汇。马戎认为,为了建立一个超越各个族群、能够反映中国“多元一体”民族共同体的群体意识,我们可以从“国族”的新角度来使用“中华民族”这个习惯用语,同时保持56 个“民族”的称呼,或者保持“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nation相对应,而把56 个民族改称“族群”,以与英文的ethnic groups 相对应。(43)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32-143页。斯蒂文·郝瑞、石奕龙等人则认为,“民族”这个汉语术语与任何西方的范畴都不同,没有完全对应的名词来翻译,进而提出在国际交流时直接使用汉语拼音Minzu来表示该词。(44)参见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1-263页;石奕龙:《Ethnic Group不能作为“民族”的英文对译——与阮西湖先生商榷》,《世界民族》1999年第4期,第79页。此外,还有学者认为,nation, nationality, ethnic, ethnic group, Minzu等译法都不能全面、完整地表述中国的民族概念。(45)乌小花:《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12-16页。
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民族”一词的英文翻译已由nationality改为ethnic,很多学者在论及国内56个民族时也将其翻译为ethnic或ethnic group,并用Chinese nation来对应“中华民族”。同时,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大连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名称中“民族”一词的英文翻译,则由原来的nationality直接改为其汉语拼音Minzu。查阅近年来中国官方文件的英文译本及对外英文宣传报道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政府官方英文网站介绍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章程》,还是新华社英文官网报道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又或者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官方英文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官方英文译本、《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英文版,均将“中华民族”译为“Chinese nation”,而在提及“各民族”时,则将其译为“all ethnic groups”(46)叶江:《浅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英译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年第2期,第4-13页。。新华社英文官网在介绍保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将“保安族”译为“Bao’an ethnic”(47)《800-year-old Ethnic Broadsword Forging Craftsmanship in China》,2021年7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7/07/c_1310047854.htm, 2023年10月14日。,在报道贵州壮族人民庆祝传统的跳水节时,则将“壮族”译为“Zhuang ethnic group”(48)《People of Zhuang Ethnic Group Celebrate Traditional Diving Festival in Guizhou 》,2020年8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8/05/c_139266925.htm,2023年10月14日。。可见,无论学界还是官方的英文翻译,虽尚未形成统一的英译,但都注意使用不同英文词汇来对应不同层次的中文“民族”概念。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民族工作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是在“中华民族”层次上,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在“56个民族”层次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巩固民族团结。有鉴于此,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民族工作”“民族事务”“民族问题”“民族院校”时,可以使用汉语拼音Minzu作为“民族”一词的英文翻译,以便涵盖国家层次的中华民族和国内的56个民族,使用nation来特指中华民族这一国民共同体涵义上的“民族”,而在具体谈论56个民族或“民族干部”“民族区域自治”“民族优惠政策”时,则可以使用ethnic或ethnic group作为“民族”的英文译词。这样既尊重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民族概念的“多元一体”特征,至于有些学者认为改变会引起一定的混乱、不符合使用习惯等,大可不必过于担忧,毕竟现代民族概念在中国的使用也经历了一百多年历程且至今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任何新的事物或概念都有一个逐渐被认知和接受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习惯而放弃对事物新变化所做的创新和尝试。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49)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因此,中国民族学者要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主线,加强民族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适时地对中文“民族”一词的使用和外文翻译做出一些调整,以便在国际社会宣传展示我国民族理论政策,讲清楚、讲明白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显著优势,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我国发展争取好环境、赢得正能量。
五、结语
现代“民族”概念是在近代伴随民族主义思想而传入中国,并在国内形成国家民族层面的民族(nation)和民族单元层面的民族两个层次,为了弥合两个层次的实际与来自西方世界“nation”构想之间的张力,中华民族精英进行了持续探索和讨论,“民族”概念逐渐中国化,具有了显著的本土特色及“多元一体”特征。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50)费孝通:《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读书》1993年第11期,第3-8页。。因此,在使用中文“民族”一词并将其与外文相对应时,需要对其使用的中外文语境进行分析,不可盲目套用西方民族理论来解释中国民族现象、分析中国民族事务,而是要立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和现状,突显民族概念的中国特色,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以此来彰显民族事务治理的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新理念,为全面分析中国特色“民族”概念的内涵及特征提供了新思路,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原则和方向,有助于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从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