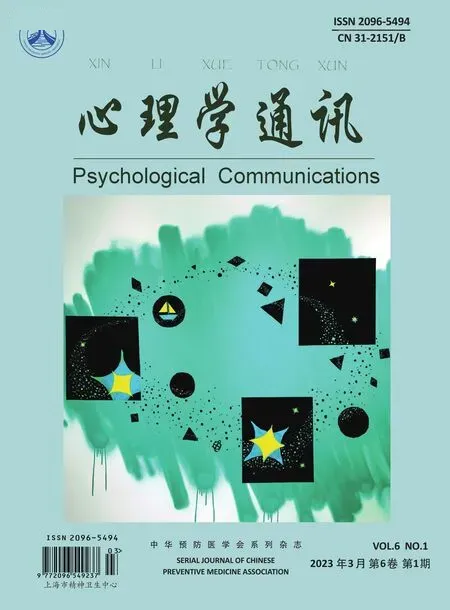失眠认知行为治疗中治疗联盟的影响因素与巩固策略综述
2023-03-01葛方梅苑成梅
葛方梅,苑成梅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上海 200030
2 上海市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 200065
1 前言
失眠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insomnia,CBT-I)是一种多成分的心理治疗方法,主要包括刺激控制、睡眠限制、睡眠卫生教育、认知矫正、放松训练等,是公认的慢性失眠障碍一线治疗方法(Edinger et al., 2021; Wilson et al., 2019)。其开展的形式有个体治疗、团体治疗、远程视频治疗以及基于网络的数字化治疗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失眠症状。但遗憾的是,在CBT-I 的临床应用中,普遍存在脱落率高的问题。CBT-I 的脱落率在个体治疗中为8%~20%(El-Solh et al., 2019; Garland et al., 2019),在团体治疗中为6%~27%(Dyrberg et al., 2022; Latocha et al.,2023),而在一项全自动化网络CBT-I 研究中,脱落率达到了38%(Hagatun et al., 2019)。心理治疗的有效性依赖于患者的参与,高脱落率则限制了CBT-I 的效用。
有多个因素影响CBT-I 的脱落率,如症状改善(Karlin et al., 2015)、存在慢性疼痛症状(Koffel et al., 2020)、存在抑郁焦虑症状(Cui& Fiske, 2020)、治疗内容缺乏针对性(Nagai et al., 2022)、治疗环境及治疗联盟(therapeutic alliance)的建立等。其中,治疗联盟的作用至关重要,对治疗联盟感知度低的患者更易脱落且对治疗满意度更低(Constantino et al., 2007; Karlin et al., 2015)。治疗联盟,又称工作联盟(working alliance)或助人联盟(helping alliance),是治疗师和患者间协作和情感的纽带,其核心特征是合作、齐心协力和互动性。治疗联盟是心理治疗中影响脱落的重要过程变量(Mallonee et al., 2022),对脱落具有跨治疗形式和跨疾病类型、稳定一致的负向预测力(何姣 等, 2020)。治疗联盟的形成、发展和维持受到治疗师、患者以及治疗双方相互作用等因素影响。治疗联盟在CBT-I 中体现在对患者的共情与支持、提供更符合患者实际的治疗方案、促进治疗依从性上。
因此,本文将就治疗联盟在不同形式CBT-I 中的作用和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并提出强化治疗联盟的建议,以期降低脱落率,更好地发挥CBT-I 的效用。
2 不同形式CBT-I 中的治疗联盟
2.1 个体CBT-I
CBT-I 最传统的应用形式是个体面对面治疗,即个体CBT-I(individual CBT-I),为治疗师与患者两个人在同一时空进行言语或非言语的即时互动,产生情感联结、建立治疗联盟。
研究表明,个体认知行为治疗中治疗联盟与治疗结果相互增益(Strappini et al., 2022; Wolf et al.,2022),高质量治疗联盟对降低失眠严重程度有预测作用,经过培训的非睡眠领域专家也能在个体面对面治疗中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治疗联盟(Karlin et al., 2015)。个体治疗相较于团体治疗能够建立良好治疗联盟,其优势在于:不受患者治疗前症状严重程度和人际关系问题等复杂状况的影响(McEvoy et al., 2014)。此外,治疗师真诚的态度以及对患者高敏感的同理心,尤其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患者的同理心,是建立良好治疗联盟的关键预测因子(Ullrich,2022),这提示治疗师的同理心和真诚是建立治疗联盟的重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在受教育水平低、治疗周期长以及住院环境下个体的治疗中,治疗联盟与脱落的相关性更强(Sharf et al., 2010)。高中及以上学历的被试占比每减少1%,脱落率与治疗联盟之间的关系效应量增加1.74 个单位,即患者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治疗联盟越弱,脱落率越高。与治疗周期为9 ~16 次的患者相比,治疗周期为16 ~40 次的患者治疗联盟更弱,脱落率更高,对应着0.42 个效应量单位的增加。相较于门诊和咨询中心的患者,住院患者的治疗联盟更弱,脱落率更高,分别对应增加了0.30 个和0.65 个单位的效应量。
个体CBT-I 所需投入的人力资源与时间成本最高,众多研究致力于找寻替代方案,如缩短治疗周期、开发简化版的CBT-I(Bramoweth et al., 2020)以及培养护士成为CBT-I 治疗师等(Nagai et al., 2022; Yamamoto et al., 2023)。
2.2 团体CBT-I
团体CBT-I(group CBT-I)的经典形式是建立由2 名治疗师领导的、4 ~6 名患者构成的小组,每周进行1次约75 min 的治疗。团体形式增强了治疗的可获得性,其治疗联盟不再局限于患者和治疗师2 个人,而是涉及患者系统与治疗师系统2 个系统,包含着患者与治疗师间、不同患者之间、团体本身与治疗师间的复杂关系。
研究表明,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中治疗联盟对治疗结果有预测作用(Bisseling et al., 2019)。团体治疗联盟是团体人际关系与治疗后症状改善等指标间重要的中介变量,高质量治疗联盟可以提高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对治疗效果的预期,并带来高治疗投入及症状改善(Vîslă et al., 2018)。这与Constantino 等人(2007)的研究一致:CBT-I 的团体治疗联盟对脱落率有预测作用,初始治疗效果预期低、感知到高质量治疗联盟的患者受益最多。这提示我们,建立治疗联盟及合理预期十分重要,比如使用成功案例来促进治疗联盟的建立、提前告知治疗过程以调整患者不合理的预期等,都能提高团体CBT-I 的疗效。
在团体治疗中,单个成员与治疗师的治疗联盟对建立团体成员间治疗联盟及群体氛围、凝聚力等有预测作用(Clough et al., 2022),这提示:采用在团体治疗前加入个体治疗等增进单个成员与治疗师的治疗联盟的方式,可能可以提高团体治疗联盟的质量。此外,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中,当面临的行为改变具有挑战时,成员间的相互支持可以增强患者改变的信心(Argiros et al., 2023),这也是团体CBT-I 有益的组成部分(Koffel et al., 2015)。目前,团体CBT-I 的研究与应用多聚焦于同质性较高的失眠亚群体,如绝经期女性(Farsani et al., 2021)、耳鸣患者(Marks et al.,2019)等。
2.3 远程CBT-I
远程CBT-I(telemedicine CBT-I)可灵活分配治疗资源,降低交通不便带来的治疗成本。其最常见的形式是治疗师通过视频与失眠患者进行个体或团体的实时治疗。它的治疗联盟与面对面治疗一致,是在患者与治疗师之间或患者系统与治疗师系统之间建立的。
Arnedt 等(2021)比较了远程CBT-I 与面对面个体CBT-I 的治疗联盟,结果显示两者无显著差异;目前,未见关于远程CBT-I 团体与面对面CBT-I 团体治疗联盟的对比研究。一项纳入40 个研究的系统综述显示,远程团体治疗联盟、团体凝聚力等过程变量相比于面对面治疗均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是:远程团体治疗的参与者对治疗师的信任度低(Gentry et al., 2019)。远程治疗技术中网络或信号的连接质量已被证明不是治疗联盟的关键影响因素,对治疗结果有预测作用的是治疗师的同理心(Sperandeo et al., 2021)。这提示,远程CBT-I 需要治疗师更多地表现出同理心,比如使用肢体语言等,以提高治疗联盟的质量。信息技术助力CBT-I 向数字化和患者自我管理等方向发展,但鉴于数字化治疗尚未纳入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远程视频、电话形式的CBT-I 仍然是最常见的节约时间和空间成本的治疗方式(Manber et al., 2023)。
2.4 网络CBT-I
网络CBT-I(internet-delivered CBT-I)或称数字化CBT-I,指将自我引导的CBT-I 干预方案通过网站或软件运行,使用既定的在线方案向患者传达治疗目标和治疗任务,并使用计算机程序与患者进行交互(Tong et al., 2022),有别于上文提到的需要真人治疗师实时参与的远程CBT-I。即使在有治疗师指导的网络CBT-I 中,患者与治疗师的沟通也多基于文本,缺乏即时性。
在网络治疗中,治疗联盟与治疗结果的相关性与面对面治疗相当(Flückiger et al., 2018),且与患者对治疗结果的满意度相关(Herrero et al., 2020)。患者与计算机程序间的治疗联盟在任务和目标维度可以达到与治疗师一致的水平,但情感维度差异较大(Tong et al., 2022)。有研究提示,尽管其治疗联盟在目标和任务维度有很高的评分,但与失眠严重指数的改善不相关,究其原因,真正影响治疗效果的是治疗联盟的情感维度(Heim et al., 2018)。Berger 等(2014)指出,治疗联盟在不同治疗条件下对治疗效果的预测作用并不相同,即在基于网络的标准化治疗中,治疗联盟对效果有预测作用,而在个体定制化方案中,对效果的预测作用并不显著。这提示治疗师的参与有利于增强网络治疗联盟对结果的预测作用,定制化方案可能利于在缺乏治疗师参与的情况下达成较好的治疗效果。
有研究提示,虚拟治疗师有利于网络CBT-I 中治疗联盟的建立,在治疗中使用虚拟治疗师头像有利于提高情感联结,且其治疗联盟的建立早于有真人治疗师指导的网络CBT-I。尽管如此,很多患者在治疗后的调查中表示更需要一个真人治疗师的参与(Heim et al.,2018),提示可以在网络CBT-I 中增加真人治疗师指导,以提高治疗联盟质量。
网络CBT-I 方兴未艾,其疗效及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均缺乏足够的研究;此外,还需探索出合适的人工干预节点及保证信息安全的方式等。
3 建立或巩固治疗联盟的策略
综上所述,治疗联盟受治疗师、患者、治疗形式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要加强治疗联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治疗师因素
治疗师因素主要包括治疗师的个人特征及其专业能力:即真诚、开放、自信、可靠的个人特征;以及良好的技能水平,如治疗师对相关情境变量的考虑和反应等。治疗师应侧重于促进患者的自我效能感,采用支持、理解、情感促进、准确合理的移情解释等治疗方式更有利于治疗联盟的构建和完善。特别是对文化背景存在差异、高敏感性和远程治疗的患者,治疗师需要通过更多的肢体语言和行动表达同理心。考虑到目前治疗形式的多元化发展,在网络CBT-I 方案的设计中,代替治疗师进行互动的网络虚拟程序的专业性及软件平台的安全性应进一步加强,以提高患者的信任度(唐瑀蓁 等, 2022)。
3.2 患者因素
患者较为强烈的积极期望、动机和态度,开放、宜人、外向的个人性格,良好的行为模式和安全型依恋关系都有助于建立牢固的治疗联盟。对于情绪障碍和失眠症状严重的患者,进入治疗前要进行筛选,并匹配合适的CBT-I 实施形式。如对情绪障碍明显的患者可先着重解决情绪问题再进入CBT-I;个体CBT-I 在疗效和建立治疗联盟方面存在优势,失眠症状严重、共病情绪障碍的患者可优先考虑个体CBT-I;团体CBT-I对患者的疾病同质性要求高,对进入团体的患者宜进行同质性筛选;此外,存在明显人际问题的患者亦不适用团体CBT-I;网络CBT-I 对于高龄和受教育水平低的患者来说适用性低。
3.3 治疗师与患者的互动因素
治疗联盟的实质是治疗师与患者的人际互动,其受双方情感、态度和反应的相互影响,需要治疗师和患者建立信任感,积极促进情感共情,共同拟定目标,完成相应任务。强化治疗联盟的方法有:在治疗中贯彻保密原则以建立信任感、建立治疗师与患者相互关心与共同关注的治疗关系、调整患者预期、使用定制化方案、明确治疗目标和进度,以及在团体、远程、网络形式的CBI-I 中适当增加面对面或个体治疗,在网络CBT-I 中加入虚拟治疗师、增加提醒功能、深化心理治疗数字化水平等。
4 结语
治疗联盟是CBT-I 中脱落及治疗效果的重要预测因子,在不同形式CBT-I 中的作用及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为强化治疗联盟,降低脱落率,应从治疗师因素、患者因素、治疗师与患者互动因素等多个方面创造适宜的治疗环境、选择恰当的治疗形式,并尽可能地增强情感联结。对治疗联盟的探究除了解决脱落率的问题,也为治疗提供了关系视角,后续CBT-I 相关技术的开发应更注重建立积极的治疗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