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还是制度: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瓶颈约束及路径创新
2023-02-28伍文中李静
伍文中 李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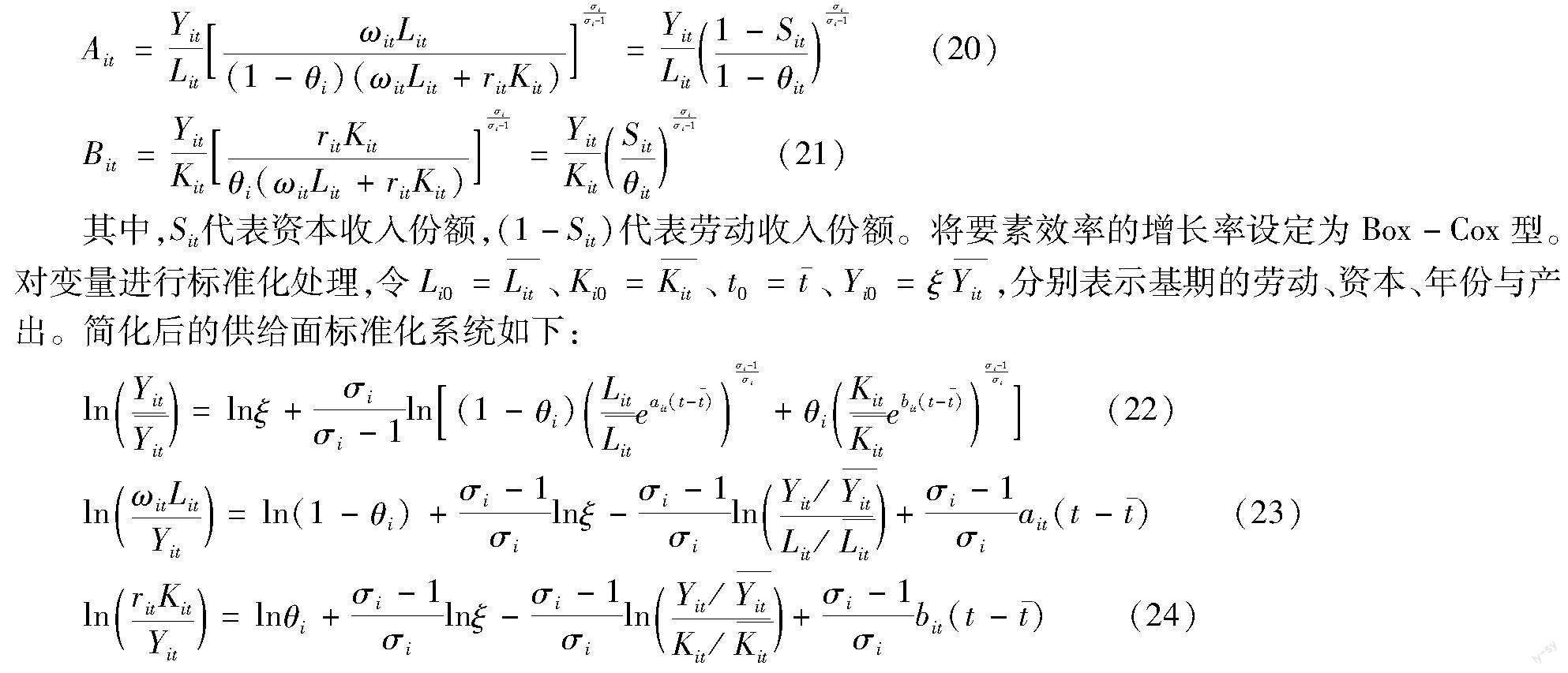

摘 要:公共服务合作有利于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民生福利,有利于大湾区持续高质量发展。由于技术及制度原因,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仍存障碍,迟滞了大湾区一体化深度发展进程。研究发现,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不足,既有制度方面的无形约束,也有技术方面的有形約束,其中制度创新不足是根源。粤港澳大湾区应以创新公共服务合作机制为突破口,提高湾区内公共治理的技术能力,主要包括:夯实国家认同的公共价值、完善配套制度对接、建立公共服务民主决策机制、统一公共服务合作技术标准、优化公共服务合作技术手段等方面。研究成果的边际贡献在于同时将制度和技术置于湾区公共服务合作过程中,在制度多样性前提下,解构了技术一体化路径,进而精准性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制度创新;技术创新
文章编号:2095-5960(2023)05-0022-09;中图分类号:F124.7;F812;文献标识码:A
邻近行政区围绕共同的战略目标走向一体化过程中,往往推动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供给。世界三大湾区成功经验显示,要想充分整合区域内外资源,必须实现公共服务合作供给。否则,会迟滞或阻碍区域一体化纵深发展进程。与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及东京湾区相比,甚或与国内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域”的特殊性。[1]三地政府各自形成迥异而独立的公共治理空间,其公共服务法理基础、公共治理价值、提供机制明显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富活力的区域,但与全球典型湾区相比,由于湾区内制度整体性、运行协同性、法律包容性有很大差距。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公共服务一体化供给瓶颈仍未突破,导致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粤港澳三地之间流动不畅,提升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2]基于此,站在国家战略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历史节点,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合作发展现状,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进行技术及制度的优化设计,高效推进三地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打造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提出
大量研究发现政府间财政合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援助之手”[3]。与税收合作不同,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打破行政区壁垒,为跨区域居民和流动要素提供无差别公共服务,通过整合公共管理能力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4]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围绕着“谁供给”“怎么供给”等问题不断创新发展。最初的重大突破就是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产品供给,以期克服政府失灵带来的低效率。[5]之后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在维持契约关系的前提下,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决策与生产,能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6]不可否认,多中心治理理论实质上是封闭辖区内的多中心治理,难以解决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问题。[7]现实表明,各辖区政府“自利化”倾向往往导致了整体非理性窘境,形成了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8]。这些问题的存在引致了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理论的发展。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公共需求跨界外延特征日益明显,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已经成为流行趋势。[9]其主要通过制度创新在不同政府主体间建立信任关系,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公共治理复杂性挑战,尤其是“棘手问题”[10]。有学者甚至认为,在竞争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合作本身就是公共需求的表达机制。[11]有研究认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往往以合同为主要合作形式,更加重视法制、平等、互惠等理念,本质上就是契约主义。[12]
一个隐含的问题是,什么是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驱动力?是技术还是制度?抑或是技术和制度共同作用?诸多研究表明,制度为政府间公共服务跨域合作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而技术则保证了公共服务跨域合作供给的现实可行性。客观地说,大数据信息技术参与到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合作才可能发生。[13]只有技术进步,才能整合公共服务供给的子系统,改变原有的碎片化供给格局。[14]技术进步最大的益处就是能从海量信息中解读跨区域居民的公共需求,也同时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信息反馈给跨域居民,能实现“威克塞尔——林达尔均衡”[15]。有学者据此提出了公共服务合作的网络治理模式,认为技术扩大了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的维度,加快了公共治理开放共享。[16]有研究发现,信息技术推动了公民参与进程,公共服务供给才可以由“制造逻辑”走向“公民逻辑”[17]。
必须辩证看待公共服务合作供给过程中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共生关系。没有制度保障,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无法启动;没有技术保障,公共服务合作将难以进行;既要通过制度创新“聚集信任”,又要通过技术创新“扩散桥接”[18]。当前关于公共服务合作过程中技术和制度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研究认为促成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的核心制度必然是公共价值,没有公共价值就没有政府间公共合作。[19]只有将创造公共价值、维护公共利益维系于合作行动之中,技术力量才能发挥作用。[20]第二个层面的研究认为必须完善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运行机制,形成强制力和约束力,并据此划分各公共服务参与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21]具体的运行制度应该包括合作组织体制、合作协调与激励机制。[22]第三个层面的研究认为合作过程既是成本分担过程,也是利益分配过程。公共服务合作治理失败往往源于利益失衡[23],必须完善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分享、利益补偿和利益冲突调解等制度。[24]
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具有紧迫性。张树剑、黄卫平借鉴新区域主义尝试性探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品合作供给路径,尤其提出了平行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跨境就业者的“社保可携性”难题。[25]当然,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具有其特殊性。陈剑认为公共规则差异性是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难点和理论困境。[26]宋雅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本质上就是“一国两制”的深度发展,建议将横琴、前海等地作为“深度合作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建设。 [27]也有学者对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的模式进行了有益探索,如赵辰霖、徐菁媛总结了三地政府之间通过常设协作机构、外部采购协议、联席会议等三种公共服务合作模式。[28]方木欢发现“分类对接”与“跨层协调”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有效的公共服务合作模式,避免了“竞争”与“合作”狭隘思维。[29]
既有研究鲜有基于对基本社会制度及其体制机制多元化、高度差异化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之间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制度和技术约束现状及未来耦合路径进行拓展性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的历史及现状,剖析其技术及制度障碍,进而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路径优化提供建议。
二、技术和制度:公共服务合作进程中两大驱动力
(一)区域公共服务合作进程中制度因素作用机理
区域公共服务合作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协商层面,第二是执行层面。协商层面主要确立合作的目的、公共价值、合作规则和合作秩序,甚至合作法律法规等。这些都是公共服务合作过程中的制度因素,最终为执行层面提供运行环境。其作用机理如下:
第一,构建集体行动规则。行政壁垒带来的制度鸿沟往往成为区域公共服务合作的最大障碍。制度制定过程其实就是通过协商制定一系列的协议、框架、备忘录等,能有效构建区域公共合作进程中集体行动的整体行为规则,更好地凝聚向心力。区域之间尤其是城市群之间公共服务合作的集体行动是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其往往承接了公共治理价值、结构和功能,有利于消除各治理层的无序状态和治理失灵。第二,确立多中心治理秩序。在公共服务合作过程中,制度具备统一性、融合性和协调性,才能保证多中心治理秩序的确立,维护区域间公共服务合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因为,多中心治理秩序的基本原理是权力共享,并以责任和义务为导向来实现公共物品供给,并最终形成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秩序。第三,整合协同发展导向。协同发展有正导向和负导向两种结果,即上升或沉沦。区域公共服务合作往往会打破旧有的行政区划和公共权力配置体系,如果制度建设滞后或偏离正确方向,区域合作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遭遇瓶颈,积累公共风险,并扭曲协同方向,最终导致合作破局。
(二)区域公共服务合作进程中技术作用机理
如果说,制度因素主要源于协商层面,那么技术因素则主要服务于执行层面。在区域公共服务合作进程中,技术因素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合作运行,使得集体行动和多中心治理从可能变为现实,并消除了诸如信息不对称等合作痼疾,从而提高合作效率。其作用机理如下:
第一,缓解了集体行动的成本约束。区域合作日益复杂,集体行动一个久为诟病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而效益的释放又具有滞后性。公共服务合作供给也遭遇这一难题。技术尤其是现代数字技术可用于整合区域集体行动的复杂信息和流程,便捷了交流和沟通,提高了公共服务合作效率,降低了合作生产的成本,集体行动的成本困境可能得到突破。第二,助力多中心治理中介效应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合作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公共服务能否主动供给、精确供给和个性化供给。最大的难题就是对跨域公众的需求进行准确捕捉和判断。现代网络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可以通过“人人互联,物物互联”,共享资源、信息、机会,使每个人都是信息链上的平等节点,实现去中心化和扁平化,并使得公共服务由“同质固化”向“情境适应”转变。第三,提高协同发展的系统性。协同发展的核心就是系统性和协调性。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其实就是一个个子系统耦合起来的大系统。在公共服务合作系统中,需要参与主体的互动来实现系统目标。其中,数字技术发展和网络运用日益改变着信息流通路径与交换方式,使公共服務合作系统能高效处理海量数据,变成越来越开放的信息流系统。各个子系统共同参与价值创造过程,形成协同合力。
(三)区域公共服务合作进程中制度和技术的耦合
制度和技术是公共服务合作进程中两大核心驱动力。前者确定了合作方向,后者保证了合作进程。但是,两者绝非孤立的,而是互相耦合的。且两者耦合的方向和程度,也决定着区域公共服务合作的成功与否。两者耦合的着力点或者耦合的桥梁在哪里?
实践一再证明,公共价值是制度和技术耦合的着力点和桥梁。现代公共服务合作进程中的要素流动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的物质流,包括物质和资金,比如区域帮扶过程中资金和物质援助;另一类则是隐性的价值流,尤其是合作双方都秉承的公共价值,比如区域帮扶救济过程中体现的民族大家庭温暖等。尤其是,技术进步推动着传统的“服务共享”向“价值共创”嬗变。
区域公共服务合作过程中的公共价值,应该源于区域共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公共需要。该公共需要可以体现区域发展方向、辖区居民的共同意志,抑或是区域公共权力机关共同恪守的政治意志,其具有个体差异性和动态演进性。
三、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现状分析
公共服务范围很宽泛。鉴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本文选取公共饮水、公共卫生、跨境养老、教育科技、环境保护等几类公共服务,梳理粤港澳三地之间公共服务合作的历程,为未来深入合作提供现实经验及借鉴。
(一)公共饮水合作现状
严格来说,饮水并不是纯粹的公共服务。但对于港澳特殊的地理环境而言,与广东合作供水确实是港澳居民非常刚性且无法替代的公共需求。60年前,在中央政府直接关怀下,广东省克服一切困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通过两条庞大的引水工程,为香港澳门同胞送去淡水。60年来,广东省累计向港澳供水约300亿立方米,满足了香港80%的用水需求,满足了澳门98%以上的用水需求①①人民网《为港澳安全供水提供坚实保障》,2022-03-25。。以香港供水合作为例。60多年来,广东向香港输送的淡水超半个三峡水库水量。香港利用内地丰沛的水资源,迅速发展经济。而广东为了保护水源质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说,广东宁可牺牲沿河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要把最好的水资源供给香港②②《广东水利年鉴》,2019年。。
(二)公共卫生合作现状
粤港澳三地之间同根同源,一方有难,三方同心。粤港澳三地之间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历史悠久。本文拟重点透析本轮新冠肺炎抗疫过程中的公共卫生合作。2020年广东疫情期间,澳门同胞在第一时间向珠海伸出援手。澳门特区政府第一时间捐赠几十万个医用外科口罩,紧急支援珠海定点医院。2022年2月以来,香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新冠阳性病例不断走高,从日增过百到日增破千,再到日增数万。多家医院病房入住率爆满,甚至超出110%使用率水平。危难时刻,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靠山。中央对此高度关注,迅速组织全国尤其是广东省政府全力驰援。2022年3月,广东先行向香港派出5000名防疫人员,协助香港进行病例排查和分析工作。其中,深圳向各省支援香港防疫人员提供后勤支援保障。至3月24日,广东省援建7个方舱医院全部竣工,共提供2万张床位。
(三)跨境养老合作现状
港澳都是长寿社会,人口老龄化指数不断上升,同时都面临土地空间狭窄、人工成本高企等约束条件。给港澳两地的社会保障、医疗养老带来巨大压力,亟须三地政府推进养老合作。广东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机遇,积极探索打造“跨境养老模式”。2019年,广东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港澳台居民养老保险措施的意见》,明确规定:在广东省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港澳同胞享受本地居民同等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小于15年,参照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补缴至满15年即可享受同等待遇;对可以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港澳同胞,享受广东省同等退休待遇;对持有港澳同胞居住证的未就业人员,可在广东省内居住地参加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财政补贴。与此同时,香港和澳门出台了 “广东计划”,鼓励老年人到内地养老。截至2022年2月28日,共有19533人通过“广东计划”在广州各地市领取现金津贴。
实践证明,由于三地政府积极合作,港澳同胞跨境养老规模越来越大。截至2021年底,港澳居民在广东省参加养老累计达2792万人次。仅在广州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港澳居民有15957人,参加失业保险8897人,参加工伤保险8751人③③中国青年网《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同心 破浪前行》,2022-06-21。。
(四)教育科技合作现状
大规模人口流动是城市兴旺发展的动力,也是城市竞争力的具体体现。人口流动涉及教育及科技随之流动等一系列机遇和问题。粤港澳大湾区多年来开展了教育和科技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30]
为贯彻落实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广东省积极推动来粤工作的港澳同胞随迁子女平等教育权利。目前,持居住证的港澳子女在广东省就读已实现各学段全覆盖。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港澳子女来广东就读,广东省按照“一视同仁、就近入学”的原则,享受与当地子女同等教育服务。同时,广东省支持港澳居民随迁子女在粤参加升学考试,同等学籍待遇,同等填报志愿,同等分数录取。广东省各市成立了“港澳子弟学校”,开创了港澳同胞子弟15年一贯制的培养模式,其他非港澳子弟学校也开设了“港澳子弟班”。据统计,在广东各市就读港生近3万人①①人民日报《粤港澳大湾區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2月19日。。
高等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全面推进,港澳高校纷纷入驻广东。深圳引来香港中文大学,珠海引来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入驻广州并正式招生。此外,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香港理工大学在佛山、香港都会大学在肇庆、香港大学在深圳、澳门科技大学在珠海等正在建设新校区。
湾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振兴和腾飞的承载空间,也是全球创新要素资源集聚的枢纽。世界上几个大湾区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无不是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城与港澳的经济合作必然带来科技合作,而科技合作又进一步推进经济深度合作。目前,大湾区中广东省9个城市高新技术企业很多,但基础研究薄弱;香港、澳门基础研究雄厚,而高科技企业不多。因此,三地之间的科技合作正在蓬勃兴起和渐次展开。[31,32]2021年,广东省向港澳两地大学和科研机构开放大型科学仪器200多台,港澳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标广东省各类财政科研资金26亿元,粤港澳三地通力合作初步投资200多亿新建30家联合实验室和科研中心,70余位港澳科学家到广东珠海、广州、佛山等高新技术企业联合研发[33],粤港澳大湾区必将成为世界级的产业湾区和科技湾区。
(五)环保合作现状
粤港澳三地环保合作早已展开。早在1981年12月,深圳市与港英政府就深圳河治理展开过合作;2000年共同制定《后海湾( 深圳湾) 水污染控制联合实施方案》;2002年4月,粤港两地共同发布《改善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素的联合声明(2002~2010)》。2007年订立深圳湾污染物减排目;2009年,完成粤港澳三地珠江口湿地生态保护工程,种植5万公顷的红树林,并抢救珠江口周围50万公顷湿地;2011年,粤港双方同意实施《粤港珠三角地区空气质素管理计划(2011~2020年)》。事实证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保护合作是卓有成效的,2006~2017年间,区域内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颗粒物PM10的年均值分别下降77%、26%和34%②②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建设美丽湾区 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2019-02-22。。
四、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障碍的技术和制度视角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有利于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民生福利,事关港澳大湾区的持续繁荣稳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合作可以带动港澳同胞对“一国两制”的认同,促进人心回归,最终实现“共赢”。就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而言,其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深厚的合作基础、叠加的政策支持、共同的利益目标等优势。但是,由于认识未统一、制度未统一、技术标准未统一等原因,导致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的核心公共价值彰显不足,最终迟滞了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
(一)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的技术阻力
第一,信息不对称约束。粤港澳三地尽管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但在公共服务合作进程中,三方信息并不充分对称。比如,在供水合作过程中,由于成本信息不对称导致合作梗阻时有发生。香港立法机构不知道供水的全部成本,而片面关注运营成本、汇率变动等技术成本,要求广东省“按实际供水数量支付”,不认可上游城市为保证东江水质而投入的巨大人力和财力。[28]
第二,资质标准及技术标准约束。主要表现如下:1.在医疗合作过程中,港澳沿用欧洲医疗执业资质标准,其保险机构不认可广东省医护人员的医疗资质,甚至在疫情期间拒绝广东省支援的医护人员。2.大湾区三地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评价标准和培训体系尚未统一,诸如养老医师执业、护理人员认定等资质标准也不统一。香港和澳门跨境养老热情高,但是信心不足,就主要源于不认可广东护理资质。3.在科技合作过程中,同样存在资质认定障碍。比如高科技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广东省以政府行政审核审批为主,而港澳则以行业自评为主,统一认证难度较大,增加了科技型企业和高层次专业人才跨境难度。④在环保合作过程中,也存在环保标准冲突,信息交流不健全等问题。2014年签署的《粤港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合作协议书》要求大湾区在防治空气污染方面合作,但三地政府现行的评价考核标准和评价方法差别很大。香港采用世界卫生组织“中期目标-2”的标准,而广东省则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中期目标-1”标准。香港每年均会发布污染物排放清单报告,广东方面的空气污染排放信息仅涉及污染物浓度,缺乏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源信息。
第三,规划衔接约束。作为中国目前唯一规划湾区,粤港澳三地之间理当在公共服务领域实现规划衔接,实现区域内各项规划的无缝对接。但目前规划设计在技术上尚未实现有机对接。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中存在各自为政现象,降低了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效率。最典型就是粤港澳大桥建设,广东省希望采取双Y方案将深圳及珠江东西岸规划在内,但香港方面规划未能通过,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单Y 方案。当前粤港澳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是各行其是,难以形成统一分工和协作。
(二)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的制度阻力分析
第一,国家认同感缺失。国家认同其实可以说是粤港澳三地公共服务合作的核心公共价值。国家认同不足增加了合作难度和合作成本,导致合作难以实质性进展。[34]在“一国两制”的制度背景下,港澳拥有高度自治权,大湾区三地的政策沟通与协调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本地主义治理倾向。主要表现如下:1.尽管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但相当一部分港澳年轻人缺乏对内地的正确认知,甚至还停留在“香港优先”等陈旧思维中,形成破坏湾区稳定的离心力。这在公共安全合作过程中尤为明显。2.在医疗防疫卫生合作过程中,缺乏全局观或国家整体利益观。香港医界甚至有一部分人担心与内地全面合作会失去医疗市场,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特区政府决策。
第二,公共管理制度差异瓶颈。因为多种原因,粤港澳三地公共管理模式及公共管理理念存在很大差别,制约着公共服务合作进程。其主要表现如下:1.公共安全合作存在诸多盲区和死角。香港用的是英国法律体系,澳门用是葡萄牙法律体系,在诸如犯罪等司法界定差别很大,难以共同行动。2.决策机制差异影响合作进度。广东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其财政预决算迅捷且能高度一致。而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财政预决算过程中议会作用很大,对政府形成了强力的牵制。尤其是香港前几任议会会员之中一些“港独”分子,对一些有利大湾区未来发展的项目建设人为阻拦,导致很多本该上马的项目无法对接。
第三,配套制度滞后且制度创新不足。尽管《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已经出台,但是由于种种问题,各项配套制度尚未跟进,导致制度协力不足。这在教育科技合作過程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情况如下:1.教育合作缺乏法律支持。比如,港澳高校到内地办学必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执行,将港澳高校视同外国教育机构,要求较高。再比如课程设置衔接问题。由于历史原因,粤港澳三地课程设置差异较大。广东省无论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有思政课,香港和澳门基本没有,其成绩如何认定也存在争议。2.科技合作过程中,人才流动存在社会保障、医疗、税收、专业资格互认等一系列身份差异带来的成本负担。比如三地个人所得税税制的差异,就是一堵多年来阻碍三地高素质人才流动的“玻璃墙”。3.制度创新不足。正由于创新不足才导致制度配套跟不上。比如,广东省对港澳供水这一公共服务合作主要采用长期合同外包模式,相同的还有大陆对港澳蔬菜供应和电力供应。这一方式从本质上应该由市场驱动,而不是政府。
(三)对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技术和制度问题的辩证认识
上述制度和技术问题的划分并不绝对。有的问题既是技术问题也是制度问题,技术问题累积起来能滋生制度问题,同样的制度问题累计也能引致技术失效。两者对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的进度、方式、效果影响各异。因此,应对两者关系进行辩证分析:
第一,制度问题是核心。也就是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的核心原因是制度障碍。从近几年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最新发展看,湾区深度合作已经触及核心领域。“一国两制”有制度优势,但也带来一定的法律、行政等领域合作交易成本。世界上其他湾区以及国内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都没有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治理结构如此复杂。其核心难点就是异质化的政府如何合作提供同质化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如何在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实行跨制度、跨区域的公共治理。
第二,技术也可以成为障碍。无论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经济技术等,粤港澳大湾区都走在全国乃至全球前列,完全能满足公共服务合作治理的需要。但是,如果不积极利用既有技术优势,其终将成为合作的障碍,并影响着制度深入创新。比如,香港和内地医疗资质认证、高层次人才认证、社保资质认证等问题,完全可以采取互通互认的技术转换。
第三,制度和技术瓶颈的症结在于改革迟滞。任何制度都必须根据形势进行因应性改革。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只有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的目标契合、价值契合、机制契合、策略契合。这就迫切需要推进制度创新,进而推动治理技术创新。建议在根本制度无法改革的情况下,对核心制度的实现机制、运行模式等适时创新和优化。否则,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最终受制于滞后的制度改革。
五、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路径创新探索
可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必将涉及各主体局部利益调整,大湾区三地政府只有坚持“制度突破、技术保证、先行先试”的原则,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才能实现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第一,夯实国家认同核心公共价值。无论经济圈、大湾区,还是城市群,其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增加信任的基础上实现其区域公共价值。粤港澳三地能够发起公共服务合作、能够维持公共服务合作,最核心的公共价值就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具体内容就是维护国家统一、维持社会稳定、促进湾区繁荣富强。强化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的核心价值取向,并将这一理念整体性融进公共服务合作过程每一环节之中,以国家认同来弥合公共治理技术上的差异和裂痕。
第二,完善配套制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是区域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合作过程无法绕开的制度分治造成了鸿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配套制度改革跟进。具体包括:①清理不利于大湾区公共服务合作的制度,建立负面制度清单。比如通关管理办法、跨境办校管理办法、科技交流管理办法等。②站在全局高度改革或重新设立相关制度。制度改革和重新设立背后也是利益的重新配置,粤港澳三地必须站在全局高度,根据比较优势选择更好的制度。比如养老培训及资质管理,广东必须向港澳学习;还有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广东也可以借鉴港澳做法,诸如蔬菜、自来水等外包管理,可以交给市场。世界一流湾区无不是市场和政府共同发力的结果。
第三,建立公共服务民主决策机制。粤港澳政府间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的实质就是满足三个辖区公民偏好进而实现湾区整体利益最大化,其最核心的问题包含两个方面:公共服务费用问题,尤其是跨区域公共服务成本分解;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问题,即需要提供什么种类的跨区域公共服务、跨区域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等。鉴于粤港澳三地公共决策机制的差异,为抚平三地公共服务决策纠纷,建议立足于民主决策机制基础上,整合三地公共需要,尝试性构建基于三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标准,提供基本同质的公共服务。
第四,优化技术手段。当前,既要利用大数据提升服务能力、改进服务质量,也要积极搭建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及服务支撑平台,推动三地电子政务系统整合,消除“信息孤岛”。为此,必须大力构建大湾区信息共享平台、区域公共事务在线服务等技术平台。比如跨境养老、子弟入学等信息可以充分共享,为大湾区居民提供快速精准服务。可以积极尝试区块链技术在大湾区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运用,该技术模式能够有效识别公众的需求,捕捉公众的真实愿望,其去中心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无缝合作的过程。
第五,统一技术标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具有特殊性。应该统一湾区公共服务技术标准和资质标准,缩小或拉近粤港澳三地之间的治理水平落差。统一标准过程必须坚持 “向先进标准靠拢”,不能囿于自我“一亩三分地”,更不能发生先进标准服从落后标准现象发生。比如护工资质、技术职称认定、环保标准等,通过先进标准的介入,更能促进落后地区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大湾区各地政府应该积极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机遇,包括先行立法权、变通规定权、试错免责权等。
参考文献:
[1]杨爱平,郑晓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非实体性治理单元及其运行机制[J].理论探讨,2022(4):75~82.
[2]霍祎黎,宋玉祥,刘亭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研究[J].经济纵横,2021(1):90~96.
[3]陈抗,Arye L.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经济学(季刊),2002(4):111~130.
[4]竺乾威.新公共治理:新的治理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16(7):132~139.
[5]Johannes Rincke. Yardstick competition and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J].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009,16(3):337~361.
[6]Osborne S P , Strokosch K , Radnor Z . Co-Production and the Co-Creation of Value in Public Services[M]. 2018.
[7]Brandsen T,Honingh M.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production:A Conceptu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6(3):427~435.
[8]辛沖冲,陈志勇.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8):1~16.
[9]张云翔.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文献综述及其启示[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5):31~45;126.
[10]郭佳良.应对“棘手问题”:公共价值管理范式的源起及其方法论特征[J].中国行政管理,2017(11):111~117.
[11]Emerson K,Nabatchi T . Evaluating the Productivit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gimes:A Performance Matrix[J].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2015(4):717~747.
[12]Alford John. Co-Production,Interdependence and Publicness:Extending Public Service Dominant Logic[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5(5):673~691.
[13]梁玉芳.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变革的四个维度[J].理论探索,2022(1):107~113.
[14]李春生.大数据驱动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问题面向、运行机制及其技术逻辑[J].湖北社会科学,2021(6):41~48.
[15]颜佳华,王张华.人工智能与公共管理者角色的重新定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6(6):76~82.
[16]唐秋伟,訾大丽.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网络建构[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30(1):121~127.
[17]张骞文,刘延海.基于SNA的公共服务供给中群团组织合作新模式[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3):64~71.
[18]李响,陈斌.“聚集信任”还是“扩散桥接”——基于长三角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动态演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20,13(4):69~89;206.
[19]MOORE M. Public Value Accounting: Establishing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4(4):465~477.
[20]王學军.合作生产中的公共价值失败及其治理[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7(4):78~86.
[21]刘丽杭,徐俊.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如何创造公共价值——以C市帮乐帮互助养老服务项目为例[J].求实,2021(6):54~70;109.
[22]余璐,戴祥玉.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合作共治与地方政府协同治理[J].湖北社会科学,2018(7):38~45.
[23]赵星,王林辉.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学家,2020(9):75~84.
[24]牟娟,齐英.政府协调合作与宏观经济振兴的内在关系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4):13~22.
[25]张树剑,黄卫平.新区域主义理论下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品供给的协同治理路径[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7(1):42~49.
[26]陈剑.基于国家主导的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治理融合:条件保障、现实困境与路径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21(1):18~24.
[27]宋雅楠.“双循环”新格局下“粤澳深度合作区”合作机制分析——以中葡平台为视角[J].港澳研究,2021(2):57~65;95.
[28]赵辰霖,徐菁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下的粤港协同治理——基于三种合作形式的案例比较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20,13(2):58~75;195~196.
[29]方木欢.分类对接与跨层协调: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治理的新模式[J].中国行政管理,2021(3):36~44.
[30]汤学兵,韦开成.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2(3):95~109.
[31]陈广汉,任晓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集聚变动的经济效应分析[J].亚太经济,2021(2):143~152.
[32]徐青.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发展研究[J].亚太经济,2021(3):147~152.
[33]伍文中,唐霏,李勤.从竞争走向合作:粤港澳大湾区财政行为的推进路径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4):24~32.
[34]李冬娜,关锋.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机制初探[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128~134.
Technology or system:bottleneck constraint and innovation path of 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 in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WU Wenzhong,LI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China)
Abstract: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and welfare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o th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Due to 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reasons, there are still obstacles in the 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which delays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integr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ack of 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results from both intangible constraints in the system and tangible constraints in the technology, among which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problem.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system breakthrough, technical assurance and first try”, and takes innovation of 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s a breakthrough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capacity of 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Bay Area. It mainly includes consolidating the public values recognized by the state,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levant supporting systems, establishing a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for 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 unifying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for 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 and optimizing the technical means for 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lies in placing both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 in the Bay Area. Under the premise of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the path of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is deconstructed, a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with precision.
Key words: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public service cooperation;system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