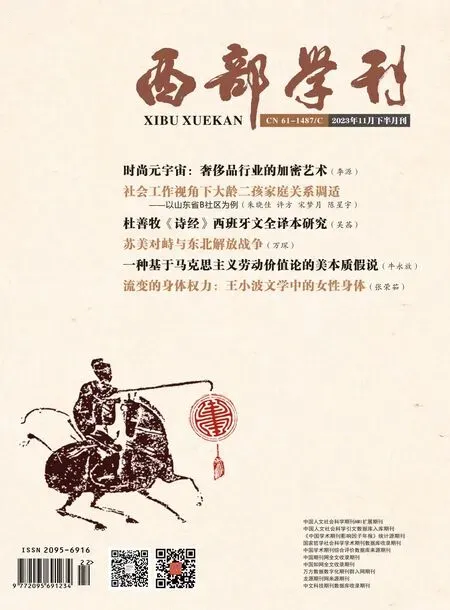空间视域下《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的身份建构
2023-02-26王壮壮刘少杰
王壮壮 刘少杰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西安 710100)
《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是新晋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的处女作。小说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获得美国亚马逊网站2014年度图书桂冠。该小说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跨族裔家庭在白人至上主义社会影响下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身份危机,以及最终导致女儿莉迪亚死亡的家庭悲剧。“《无声告白》与以往华裔文学中常见的文化冲突主题不同,作者更为关注种族、性别等社会压力对主体建构的影响,着重于展现外在压力在个人身份建构中的破坏性作用”[1]。小说中多次采用闪回与并置等空间叙事策略,打破了文本叙述的时间顺序,从不同家庭成员的角度分别叙述他们的精神困境,而莉迪亚的死则是彻底打破家庭表面和谐的导火索,将潜在的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作为“父母眼中的一朵娇花、掌上明珠、心肝宝贝、母亲心中永恒的唯一”[2]111的莉迪亚对于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无声告白》中人物的身份建构受着空间元素的重要影响。莉迪亚在学校受到排斥,在家庭中饱受压抑,面临身份危机;在经历母亲离家出走又重返后,在家庭中试图按照父母的意愿建构身份,在米德伍德湖象征重生的跳湖行为后重构身份。因此,本文采用加布里尔·佐伦的空间叙事理论,从空间叙事结构出发,回归小说真正的主角——也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莉迪亚的视角,试图揭示家庭与社会因素对其身份建构的影响。
一、地志层与身份危机
自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在《西旺尼评论》(Sewanee Review)上发表名为《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An essay in two parts),明确提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形式”问题以来,空间叙事问题就得到学者的广泛讨论。在20世纪末叶,学界经历的“空间转向”推动着空间问题与叙事学结合。“空间批评从文学文本作为‘社会参与者’的视界出发,赋予了‘文学性’新的诗学内涵”[3]。在此影响下,“加布里尔·佐伦(Gabriel Zoran)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一文中建构了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实用价值和理论高度的空间理论模型”[4]12。佐伦将空间划分为三个层级:地志层、时空体层以及文本层。对于地志层,佐伦将其定义为“通过直接描述来表现地形结构”[5]的地图,“这个地图是建立在一系列矛盾上的”[5]。在小说《无声告白》中,正是这些矛盾促使莉迪亚受到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迫,引发身份危机。
作为米德伍德小镇上唯一的华裔家庭成员,莉迪亚不仅遗传了父亲黄种人的外貌,更继承了母亲的蓝眼睛,这双代表西方人特征的蓝眼睛使得莉迪亚成为父母的宠儿,但同时也是莉迪亚不幸命运的开端。作者在书中将莉迪亚的死亡矛头直指家庭因素。“如同任何事一样,根源在父母,因为莉迪亚的父母,因为她父母的父母。”[2]26在家庭这个内部空间中,作为黄种人的父亲詹姆斯渴望融入人群,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他努力变得优秀,但最终没有能够获得来自哈佛大学的教职,因此詹姆斯将他的梦想寄托给最具有美国人特征的莉迪亚。母亲玛丽琳则希望与众不同,她渴望摆脱母亲对她的影响,并且希望通过做医生“与母亲的生活方式拉开距离”[2]31。但最终与詹姆斯的结合以及怀孕辍学使得玛丽琳被迫放弃自己的理想,转而一心培养女儿莉迪亚。莉迪亚带有西方人特征的华裔身份使得她承载了父亲的期待,她的女性身份也寄托了母亲对通过从事医生这一具有男性气质的职业战胜性别歧视。莉迪亚身份的混杂性以及作为父母梦想载体的二重性导致莉迪亚“被迫承载父母的梦想,压抑着心底不断涌起的苦涩泡沫”[2]156,但“她已经开始感觉到,继承父母的梦想是多么艰难,如此悲哀是多么令人窒息。”[2]271
而在学校这个外部空间里,莉迪亚显得形单影只,她的父亲一直在为莉迪亚是否能够融入人群而担心,就连送给莉迪亚的项链都是为了莉迪亚能够与人们相称而选择银色。这样的生日礼物在父亲的所谓教导“你会和每个人好好相处,朋友永远都不嫌多”[2]225的映衬下“如同一只冰环围绕着她的喉咙”[2]225。而母亲自离家出走又重新回家之后,莉迪亚所有在学校尝试交朋友的行为与思想全部都被害怕再次失去母亲的恐惧占据。在家庭中的身份危机已经成为影响莉迪亚在学校的身份建构,揭示出了空间的对立关系。
二、时空体层与身份建构
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将苏俄文艺评论家巴赫金引入文学批评的术语“时空体层”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时空体层“仅仅被定义为一种可以由作为运动与变化的空间和时间的整合范畴”[5],并划分出共时与历时关系,探讨这些关系在空间结构上的不同效果类型。《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的身份建构过程体现出明显的共时与历时关系,她在空间的迁移中初步建构了自己的身份。
佐伦将共时关系划分为运动状态和静止状态,“静止是一种必定会有一个特定的空间背景的情形,运动是将自身从空间背景上切断从而转换到不同的背景的能力。”[5]《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的身份建构过程历经自己的房间、米德伍德湖码头、杰克的车上等多个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动态特征,莉迪亚5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离家出走,想要继续完成学业。可在年幼的莉迪亚眼里,她却觉得“这是他们的错……他们没有满足她的期待”[2]133。因此,莉迪亚暗自承诺,如果母亲能够回来,“她要实现母亲的每一个意愿”[2]134。莉迪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那本代表着囚禁着母亲渴望自由的“红色封面的大烹饪书”[2]132藏到自己的房间,选择独自替母亲背负实现梦想。后来在米德伍德湖码头,哥哥内斯将莉迪亚推到湖中又将她救起这件事情促进了莉迪亚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此之前,大家都“会围着莉迪亚曾经存在过的空间旋转,最终卷入她留下的真空之中。”[2]150这种生活让莉迪亚觉得压抑,然而,就是在“当水面在她头顶闭合的时候,莉迪亚感到极大的解脱,她在呛咳中满足地叹息着……她迫切体会到,那些倾斜挤压在她身上的东西,她也不想要,它们太沉重了”[2]150。最终在杰克的车上,在与杰克的相处中,莉迪亚完成了自己的身份建构。杰克教会了她如何开车,还教会她如何撒谎,这些都是作为乖乖女的莉迪亚以往从未接触过的。莉迪亚决定“她再也不会假装成另一个人了。从现在开始,她要做她想做的事情”[2]272。莉迪亚在空间的迁移中逐渐找到真实的自我,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
佐伦认为历时关系有方向、轴和力量等因素的影响,“运动的实际方向是由时空结构所决定的;这样,一个地点被定为出发点,另一个作为目的地……如此,空间中的运动轴就被确定。”[5]从历时关系上来看,莉迪亚的身份建构过程具有明确的方向,以家庭为起点向外部世界不断延展的空间为运动轴,呈现出不断摆脱“他者化”命运的发展轨迹。起初,莉迪亚会认为“母亲的回归无异于奇迹”[2]142。即使母亲对于莉迪亚的期待已经远远超出对一个正常发展的孩子应有的期待,莉迪亚还是会全盘接受,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失去自我的“他者”。在学校里,由于有了哥哥内斯的陪伴,莉迪亚可以暂时逃避来自父母的期待和同学们的排斥,短暂地找回自我。作为“她生活的调剂”[2]102的内斯,可以在学校坐在她身旁,让她觉得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在家里,当莉迪亚面对父母的拷问时,内斯会适时转移话题。可是随着内斯即将去往大学,并且慢慢忽视莉迪亚之后,莉迪亚就开始被动地转变自己最初的身份,逐渐学会了拒绝,就算内斯主动示好,想为她拍照时,莉迪亚也只是“直视黑洞洞的镜头,拒绝微笑——哪怕是轻微地弯弯嘴角,甚至在听到快门声之后,她仍然保持着这副表情”[2]178。这种拒绝的举动显示出莉迪亚自我意识的被动觉醒。而莉迪亚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体现在学校外杰克带她逃课练车的行为中,在杰克的车里,莉迪亚满怀欣喜地想到“等获得驾照,她就能去任何地方……她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逃离”[2]217。之后莉迪亚来到码头,“在码头上许下新的承诺……她将重新开始”[2]271。至此,莉迪亚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摆脱了被完全他者化的命运。最终,她跃入湖水,以死亡换来了精神上的新生。
三、文本层与身份重构
作为“一个再现世界的组织结构”[5],佐伦认为文本层中“被构建的事物属于再现世界,但结构自身则通过文本的语言学性质影响事物。”也就是说作者在文本世界中构建的结构图式是通过文本来产生影响的。这些结构图式与文本层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语言的选择性”“文本的线性时序”以及“视角结构”。《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的身份重构受到“视角结构”的重要影响。
佐伦在视角结构中着重关注“此在(here)”与“彼在(there)”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以两种方式出现,其一是叙事空间与其背后真实世界的对立,此时“超越文本虚构空间的‘彼在’与囿于文本虚构空间的‘此在’会形成不同的关注点,两者在叙述过程中可以相互转化,但不同的聚焦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效果”[4]13。小说中莉迪亚生活的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正处在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下,对于移居美国的华裔移民,他们采取的态度是规训和排斥。他们提出所谓“模范族裔家庭”的概念,企图把他们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强加在这些华裔移民上,小说中莉迪亚的父亲詹姆斯就饱受白人至上主义的影响,无时无刻都在渴望美国化,他在同玛丽琳恋爱之后“觉得从容自信,这似乎是他人生中从未有过的体验”[2]41。在莉迪亚出生后,詹姆斯也试图将这种被内化过的价值观强加在莉迪亚身上,使得莉迪亚谈到美国华裔想到的都是“扛箱子的中国小工,戴着苦力帽,眼睛歪斜,牙齿突出,吃饭用筷子”[2]190。在父亲的影响下,她重构了自己属于美国公民的身份。
母亲玛丽琳面临的则是美国社会当时用性别劳动分工在经济方面禁锢了女性的潜在价值。在学校,老师和学生们强化性别对立,在家庭中,玛丽琳的母亲也告诫她上学的真正目的是“遇到很多优秀的哈佛男人”[2]31,这让渴望与众不同的玛丽琳希望以从事医生来与母亲的生活方式拉开距离。组建家庭后,莉迪亚自然而然地接过母亲这一沉甸甸的愿望。虽然玛丽琳告诉她“你的人生完全取决于你,你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2]220。但是“除了当医生,莉迪亚无法想象自己能够拥有别样的未来和不同的人生”[2]159。莉迪亚被迫依照母亲的意愿以及当时父权社会下的集体性压迫重构自己的女性身份。因此,文本中的“此在”世界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彼在”世界构成一种对比关系,体现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白人至上主义和父权社会的压迫成为影响少数族裔的主体身份建构的重要因素。
视角结构的第二种关系就是在文本层内部“一个特定时刻被感知为前景中的事物和被感知为在背景中的事物之间”[5]的对立关系,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能在文本中任何位置改变”。《无声告白》中莉迪亚的身份随着空间的置换而发生变化。从小说整体来看,小说用“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2]1作为开篇,叙述整个家庭在莉迪亚死后身份重构的过程和结果:父亲詹姆斯因无法接受打击选择出轨华裔助教路易莎,最后因对妻子、对家庭的爱和愧疚选择回归家庭,不再纠结于自己的华裔身份,而是“和玛丽琳说话时会选择真正能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措辞”[2]279;母亲玛丽琳一开始选择将自己封锁在莉迪亚的房间,纠结于莉迪亚的真正死因,后来她发现正是她对莉迪亚的过分要求使得莉迪亚不堪重负。最终玛丽琳决定放下过去,正确地爱自己的孩子,“她明白,他们没有别的去处,只能向前”[2]280;哥哥内斯作为最能对莉迪亚的遭遇感同身受的人,在考上哈佛大学之后却“忙于幻想自己的未来,没有再听见莉迪亚没说出口的话”[2]160。最后内斯通过跳入莉迪亚葬身的湖中,“想象着莉迪亚下沉的那一刻”[2]285来完成自己的精神救赎;妹妹汉娜则从一开始的懵懂无知,拥有的东西“都是别人不要或不再喜欢的”[2]205,被家庭边缘化的角色受到关注。莉迪亚作为背景人物,展示出在其影响下家庭其他成员身份重构的结果。
四、结束语
佐伦在空间叙事理论中将空间结构分为地志层、时空体层以及文本层。小说《无声告白》则在这三个层次下分别展现出小说主人公莉迪亚的身份危机,身份建构以及身份重构过程,并以此展示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大背景下,以莉迪亚为代表的美国华裔群体面临的身份焦虑以及生存困境。作者伍绮诗借这部小说表达她对族裔问题以及主体身份建构的思考:只有保持真正的自我,才能扭转美国社会对于华裔群体的看法,身份问题才能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