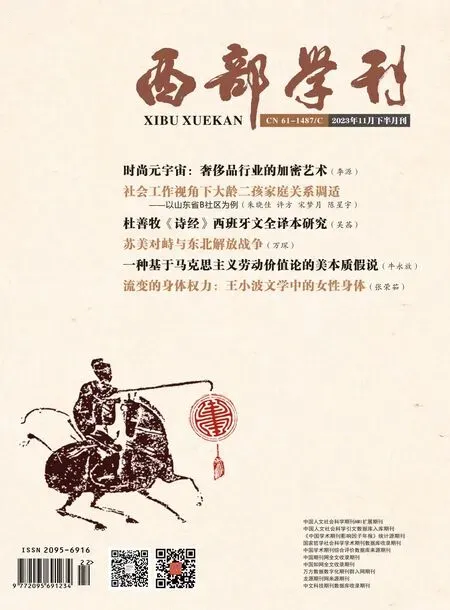杜善牧《诗经》西班牙文全译本研究
2023-02-26吴茜
吴 茜
(青岛大学 外语学院,青岛 266000)
作为中华文明的珍宝、全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诗经》自1626年由耶稣会士金尼阁翻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出版后,其西播途程已有四百余年。19世纪时,几乎主要的欧洲语言都有了相应的全译本,有的语言甚至有了多个译本。首部《诗经》德文全译本由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于1833年依据法国传教士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的拉丁文译本翻译而成;1871年,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完成了一部至今仍然广受欧美文学界赞誉的《诗经》英译本;1872年,首个《诗经》法文全译本诞生,由法国汉学家鲍狄埃(Guillaume Pauthier)执笔。当欧洲其它国家陆续出版相应语种的《诗经》全译本时,西班牙汉学发展却因种种政治、社会变动几乎停滞。18世纪爆发的王位继承战争以及19世纪初西班牙人民反抗法国侵略军的民族解放战争,造成了人民的劫难与国力的消耗。1898年美西战争中西班牙惨败,菲律宾、古巴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西班牙国力亏空,国际地位迅速下降,在本民族内忧外患、前途未知之时,自然很难关注到遥远的东方。1984年,《诗经》西班牙文全译本《中国歌谣集》(Romancero Chino)诞生,译者杜善牧首次将这部古老东方的璀璨文明完整地呈现在西语读者面前,这是西方《诗经》翻译史的一大进步。研究这部翻译经典,对中华典籍的西译、西方诗经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西班牙汉学发展背景下的《诗经》西译历程
《诗经》的西译与历史、政治因素影响下的西班牙汉学发展的兴衰密切相联。《诗经》首次出现在西班牙语世界是在20世纪上半叶。彼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与西班牙内战,中西两国人民本着反国际法西斯的一致目标,建立起相互支持、互相支援的友谊。最早西译《诗经》的为翻译家黄玛塞(Marcela de Juan,1905—1981),她选译了《静女》《日月》《将仲子》等十首诗,收录在她所著的《中国诗集选》(Breve 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china)中。该诗集包含了从公元前2000多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多首中文诗歌,于1948年出版。但战争还是大大阻碍了两国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加上二战后佛朗哥在西班牙国内实行反共产主义的制度,西班牙汉学研究仍然没有突破性进展。
20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西班牙亦开启了民主化进程,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逐渐改善,“西班牙出版社开始着手恢复佛朗哥统治时所破坏的文化,译入了大量的世界文学作品”[1]。此外,该时期中西外交关系也取得巨大进展,1973年中国与西班牙正式建交,1978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访华。两国人文交流日益频繁,西班牙汉学发展也更加活跃,中国文化在西班牙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多个《诗经》西译本相继诞生。1974年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翻译家及汉学家杜善牧(Carmelo Elorduy)的节译本《诗经选译》(Odas selectas del Romancero chino)付梓,由Monte ávila Editores出版社于加拉加斯出版,但因其为节译而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十年后,1984年杜善牧推出了历史上首个以中文原诗为母本的西班牙文《诗经》全译本《中国歌谣集》(Romancero Chino),至此西语读者才有机会完整品读这本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该译本至今被视为最早且最权威的西语翻译。凭借该翻译杜善牧于1986年获得了“西班牙国家翻译奖”的殊荣。
进入21世纪后,法籍华人高行健和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相继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使得国际社会愈发关注中国文学作品,在西班牙亦掀起一股译介中国经典文学的浪潮。2001年,由西籍华人、翻译家陈国坚执笔的《中国传统诗歌》(Poesía Clásica China)出版,其中收录了7首《诗经》的诗篇,分别是《蒹葭》《关雎》《湛露》《静女》《大车》《木瓜》与《将仲子》。2003年,Visor Libros出版社发表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Rafael Alberti,1902—1999)与玛利亚·特蕾莎(María Teresa León,1903—1988)合译的诗歌集《中国诗歌》(Poesía China),其中包含有《相鼠》《静女》《日月》与《将仲子》4首诗。但上述两部诗集都着墨于唐诗与宋词的翻译,《诗经》仅占极小的篇幅,这更加凸显了杜善牧《诗经》全译本的弥足珍贵。2013年,西班牙出版了第二部《诗经》全译本《诗歌之书》(Libro de los cantos),译者为格拉纳达大学中文教师、汉学家、翻译家加西亚·诺夫莱哈斯(Gabriel García-Noblejas)。他曾在采访中高度赞扬杜善牧译本并直言他在翻译时曾参考过杜氏的翻译。
二、杜善牧:传教士而来,翻译家而去
1926年,25岁的杜善牧首次来华开展耶稣会的传教工作。其间,杜善牧沿袭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所实行的文化适应策略,与中国民众密切交流,对中国的道德价值和一些礼仪实践保持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加之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热爱,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通晓中国语言文字的精妙,可以“研究中国文字复杂一字多义,及确认每一个中文用法的真正意涵及精确翻译”[2]。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共实行肃清外国在华文化势力的政策,加之健康原因,杜善牧于1959年返回西班牙。休养期间,他受到哥哥——著名哲学教授Eleuterio的鼓励,着手从事中国经典的译介,此时的杜善牧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已经积累了深厚的中华语言文化素养。1962年,他重返中国台湾后,便专注于中国经典的译介与研究工作,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的译介与研究。
根据在WorldCat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cional de Espaa)的检索数据,杜善牧共有九部重要译著。首部是中国经典《道德经》的译本《〈道德经〉中的道家智慧》(La gnosis taoísta del Tao Te Ching),于1961年在奥尼亚出版。在该译本中,杜神父结合自己对道家哲学思想的阐释,将其与西方哲学流派如斯多葛主义和诺斯底主义进行比较[3]。该书分别于1984年和1996年由Ediciones Orbis和Tecnos两家出版社再版,足见其价值与影响力。1967年,杜善牧译介了道家另一部经典《庄子》(Chuang-tzu.Literato,filósofo y místico taoísta),该书受到西班牙汉学界的高度评价,也为道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关于道家思想的六十四个概念》(Sesenta y cuatro conceptos de la ideología taoísta)等多部杜神父的著作相继问世,在西方学界引发强烈反响。晚年时期,他对《周易》《墨子》这两本传统经典产生了浓厚兴趣,虽然身体抱恙,但仍坚持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两部作品的西班牙语译介工作。
杜善牧将多部中国典籍直接从汉语译成西班牙语,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以往的西班牙译者大多缺乏直接阅读研究中国古文的能力,只能依赖于其他语言的间接翻译材料。而杜善牧不仅能够直接阅读原文,而且还力求全面完整地翻译原著,不做删减或选编。这些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在西班牙的传播,也为后来的汉学家提供了宝贵资料。正如加西亚·诺夫莱哈斯[4]所言,杜善牧可以算是最伟大的中西语翻译者之一,他是将中文译成西班牙文的翻译先锋和领路人。
作为传教士,他想通过译介寻找中国典籍中与基督教相通的思想和理念,如“天”“道”“仁”等,并试图借此宣扬基督教义,推动中西宗教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作为汉学家与翻译家,他希望通过译介向西语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精髓、艺术魅力、思想智慧和信仰体系,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三、杜善牧《诗经》西译本翻译策略
(一)副文本的丰厚性
杜善牧的《诗经》全译本《中国歌谣集》(Romancero Chino)共507页,由序言、诗歌正文,附录三部分组成。序言部分,杜氏用17页的篇幅概述了《诗经》的成书背景、内容结构、文化意义和历史影响。他从《风》《雅》《颂》三个部分入手,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和社会变迁,探讨了孔子对《诗经》的删选和运用,论述了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者的政治理念。杜善牧认为,《诗经》是一部智慧之书,对历史学和人类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之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如同《圣经》之于基督教徒。与此同时,杜译本对诗歌原文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共三类。第一类为字词注释,如第39页(1)文中译例均出自Elorduy C.Romancero Chino[M].Madrid:Editora Nacional,1984。通过脚注对“鲂”进行了描述。第二类文化注释旨在说明源语文本中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民俗风情等,如阐明《新台》为民众讽刺卫宣公劫夺儿媳宣姜的诗歌。第三类互文性注释用以指出不同诗篇在主题、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联系与差异。注释的丰厚性体现了杜译本的工具性特点,它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环境中,以弥补翻译过程中的文化缺失。书后附有汉语专有名词索引,方便西语读者欣赏汉字的美感。
(二)诗旨的严格考释
杜善牧对诗旨的阐释体现了他对传统经学观点的尊重。例如,杜氏认为《关雎》赞扬了周文王正妃太姒的品德,这与传统经学家的观点相同。他在字词考释上也遵从传统注释,如把“淑女”译为“端庄且品德好的少女”(doncella recatada y virtuosa)。再如,《螽斯》一诗,杜解释为预示后妃太姒子孙众多[5]33,承袭了毛诗和朱熹之说,虽指出了“对多子多孙的美好愿望”这一主旨,但引申出“后妃”使诗的内涵窄化和教条化。然而,杜善牧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传统的经学义理解释置于绝对权威的地位。比如,《女曰鸡鸣》一篇,杜善牧借鉴了现代学者的观点,认为诗歌表现了青年夫妇对和睦生活的赞美与向往,他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达诗歌中最朴素的生活气息。又如,《桑中》一首,他不同意传统经学家把它看作是揭露男女淫乱之作,而是赞同程俊英、余冠英等现代学者认为它描写了男女约会之情。他批评传统经学家“过度地强调了儒家的道德礼仪”,并表示外国学界“对于经学家把该诗与道德说教联系到一起而感到遗憾”[5]85。由此可见,杜善牧没有盲目追随经学家道德教化式的注释,而是带有批判性地引用,甚至可以说,这些传统经学观点本身也为杜善牧的研究内容。
(三)内容与形式的“忠”与“不忠”
1.对文化词汇的“忠”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了许多反映地域特色、民族色彩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词汇。杜译本充分参考了传统注释对字词的考释,力图保持原作的忠实性和准确性。例如,对于动植物类词汇“棘”,杜氏没有选择归化策略,将其译为“dátil”(西班牙人常食用的一种长椭圆形的椰枣),而是采用其准确的学名“azufaifos”,但该词在西语中为使用频率极低,因为这种小酸枣乃至国人喜食的红枣在西班牙并不常见。
杜善牧在翻译传统服饰、生活器皿、祭祀用具等文化词汇时大量使用描述性翻译技巧。例如,“衣锦褧衣”(《硕人》)一句中,他将“锦”(一般指较为华美锦织衣服)和“褧”(用麻类植物织成、穿在外面以避尘土的单罩衫)分别译为“绣花的华美长衫”(rica túnica bordada de flores)和“朴素绸缎外罩”(sencilla bata de seda)。再如,“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芄兰》)一句中“韘”的本义为男子射箭时套在右手大拇指上来钩弦的工具,后为贵族男子佩戴的饰品,是已成年的象征。其本义对于该诗并非必要信息,但杜氏选择在原句中将其译出,“用来发射弓箭的扳指”(dedal para el tiro del arco)。描述性翻译为读者提供了确切而有用的信息,但同时使整个译句过于冗长,与原作简洁、清新、自然的风格不符,造成了译文流畅度下降。
2.对原诗风格与叠词形式的“不忠”
《诗经》中诗歌多采用四言格,形式简练有力,韵律明快流畅。杜译本采用散文形式叙译,未保留原诗的风格特征。例如,“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杜善牧译为:“两只燕子一起飞,他们挥舞翅膀的方法不一样”[5]58;再如,“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野有蔓草》),杜氏译为:“我遇到了一个有着美丽的双眸和额头的人”[5]39。原诗浪漫唯美,女子目光温柔、清纯透彻。杜善牧的翻译虽然准确传达了原诗的含义,但平铺直叙的翻译却属实难以传递出原诗歌的美感与韵味。
《诗经》广泛运用叠词,赋予作品回环往复的韵律美和音乐美。而西班牙语是一门忌讳重复的语言,虽然也有类似的“词汇重复”(reduplicación léxica),但其使用频率和范围远不及叠词,二者在语义上也有明显差异[6]。也许正是出于该因素,杜善牧在多数情况下采用释义法来解释原词含义。例如,他将“桃之夭夭”译为“桃树闪耀着蓬勃的生机”;将“风雨潇潇”译为“猛烈的大风混合着雨发出嗡嗡声”;将“忧心悄悄”译为“忧伤吞噬了我的心”。虽然,杜译本未能再现原诗的音乐性和节奏感,这是重叠形式所具有的独特美学功能,但不能因此否定杜译本的美学价值,“闪耀”“吞噬”等词也能激发读者的审美体验。
杜译本对文化词汇考证精确,但在形式上有所偏离。这种翻译策略并非出于杜氏个人喜好,而是由译介目的与译介背景所致。当时西语世界还未有完整介绍《诗经》内容的译著,杜氏作为传教士兼汉学家,其主要译介目的为向来华传教士和西语世界详细介绍原作内容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因而更注重内容和意义上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从这个角度看,他对《诗经》形式上的偏离是一种合理的取舍。
(四)宗教及哲学词汇的运用
作为耶稣会士,杜善牧似乎难以摆脱传教布道的隐晦目的,在《诗经》译本中多次运用蕴含西方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术语,试图论证基督教信仰和中国古代文化的相似之处。他在序言中谈到中国古人对万物之主“上天”的崇敬时,用了大写的“Dios”来隐含基督教中至尊的上帝。在西班牙语中,“dios”是泛指神灵,而“Dios”是专指唯一的神,即上帝。杜善牧此举试图将中国人敬仰的“天”与基督教信奉的独一无二的真神相提并论。再如,《君子偕老》里的“帝”字,据学者李山[7]的阐释,其本义既可指“玉帝”又可指“帝女”,但考虑到诗歌中是将貌美、雍容华贵的宣姜与“帝”相媲美,第二种理解明显更为合理。在杜译本中,他没有使用“diosa”(女性的神),而是再次使用了大写的“Dios”来暗指上帝。此外,在序言谈及“道”时,杜善牧先用威妥玛式拼音法音译为“Tao”,然后括注西班牙文“Logos estoico”,将“道”比作古希腊哲学学派斯多葛主义(estoicismo)的逻各斯。杜善牧的这一翻译策略受其基督教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同时反映了他作为耶稣会士服务于传教事业的翻译宗旨。
四、结束语
杜善牧来到中国的最初目的是向东方宣扬耶稣会天主教教义,但他最终的影响力却远超传教的范畴。他对中国典籍的翻译涉面广、质量高,在西方读者与中国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其《诗经》西班文全译本在译介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让西语读者首次有机会完整品读到这部蕴含儒家文化精髓的作品。尽管其中多处可见传教士背景的痕迹,且他对诗歌内容的过度关注也使译文与原文文风有所差异,但其译风严谨,对字词的考释、诗句的理解与再现都力求精准,在诗义的诠释上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批判性。杜译本对于想探索中国哲学、历史、地理和民俗文化的西语读者极具参考价值,对《诗经》乃至中华文化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