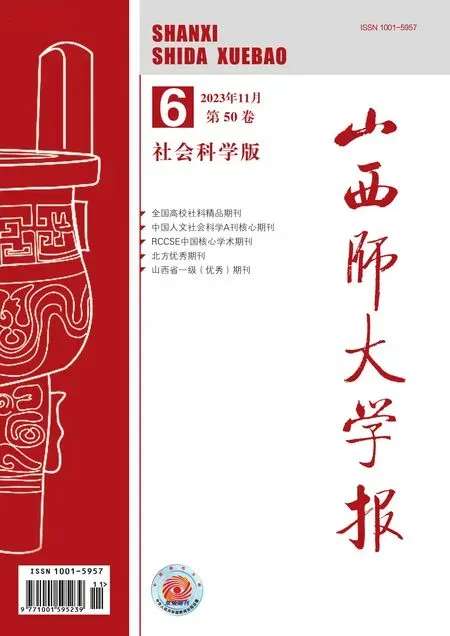美国跨境破产立法应用修正的普及主义对我国的启示
2023-02-26常柳溪
常 柳 溪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 北京102249)
一、问题的提出
修正的普及主义是现阶段最为学界推崇的跨境破产域外效力理论,它从纯粹的普及主义演变而来,但在纯粹的普及主义基础上做出了更加符合各国利益和更切合实际的改变。纯粹的普及主义制度推崇的是由一个法院根据其本国破产法所作出的破产宣告及于破产公司位于全球范围内的所有资产这一理念(1)刘敏敏:《破产宣告域外效力理论探析》,《现代经济信息》2017第12期。。虽然学界一致认为,普及主义是全球化市场下最理想的破产制度设计,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各个国家基于司法主权,并不愿让渡本国境内破产资产的管理权,因此该理论难以为跨国界的破产合作提供可实行的路径。而修正的普及主义并不像纯粹的普及主义一样要求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破产程序,它保留了普及主义制度中主/辅破产程序的部分,即破产公司的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法院可以指派一名破产代表人在该国提起一项主破产程序,同时其资产所在的其他国家的债权人也可同时提起一项辅助破产程序。修正的普及主义制度为了更大范围地保护公共利益、国家政策及母国债权人的利益不受侵害,赋予了主要破产程序所在国的司法机构对域外有违公正的辅助破产程序的法律效力予以否认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也被众多国家在制定跨境破产制度之时所采纳。
《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下称《示范法》)是联合国贸法会于1997年通过的法律,它普遍被学者们认为是修正的普及主义的具体制度体现。(2)Adrian Walters, Modified Universalisms &the Role of Local Legal 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aw, 93 AM.BANKR. L. J. 47 (2019).如今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53个国家(合计56个法域)均已采纳《示范法》(3)S. Guo &J. Su, “Chinese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aw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Review,1(2023),41—59.。《示范法》的范围仅包括跨境破产中程序方面的内容,目的在于融入一国国内破产法并作为其组成部分来予以适用,核心主题包括救济准入、认可和协助、合作和沟通、程序协调。(4)魏铭声、邱腾:《“一带一路”语境下中国应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之理由与风险应对》,《复旦大学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示范法》具有中立性和示范性,它的中立性为不同采纳国的法律文化以及或强或弱的修正普及主义形式提供了弹性空间,作为跨境破产领域的示范法,它允许采纳《示范法》的国家可自主决定改编或者拒绝接受其中的任何条款,体现了《示范法》背后理性利己主义的逻辑内涵(5)魏铭声、邱腾:《“一带一路”语境下中国应采纳〈跨境破产示范法〉之理由与风险应对》,《复旦大学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它的示范性为尚未在跨境破产领域取得全面成文立法的国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模板。
我国学界长久以来在是否加入《示范法》上颇有争议,回看我国的跨境破产立法,虽然在2007年生效的《企业破产法》第五条对于跨境破产进行了规定,但仍处于不成熟的原则性阐述阶段,《企业破产法》第五条中的互惠原则、公共政策原则均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而美国作为牵头制定《示范法》的国家,由最初的第304条对礼让原则、公共政策原则的模糊界定,到在其《破产法》第15章对《示范法》的细致采纳并投入运行,完成了从属地主义到普及主义再到修正的普及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顺应着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利益需求,同时也展现了全球的经济发展趋势——纵观整个国际社会,对于跨境破产问题的解决模式已经逐渐趋同,无论是从立法理念还是价值取向上来看,大多是以修正普及主义为理论基础,采纳可兼容多个破产程序的复合破产模式。正如新加坡等国家一样(6)龙光伟、王芳、叶浪花:《“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破产的发展路径选择——新加坡跨境破产发展历程的经验与启示》,《人民司法》2020年第1期。,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也更加倾向于属地主义,但随着我国资本输出国的角色愈发明显,在跨境破产上进行国际合作也愈发符合我国的利益需求。2007年《企业破产法》第五条的生效意味着我国放弃了破产属地主义的立场(7)张玲:《我国跨境破产法立法的完善:目标、框架与规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采取了修正普及主义的理念。但由于我国跨境破产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尚不充分,因此,厘清属地主义、普及主义以及修正普及主义的概念,研究美国的转变和采纳《示范法》的路径,对我们国家是否加入《示范法》以及加入《示范法》后的相应制度建设来说有着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二、从普及主义到修正的普及主义
(一)普及主义的源起与发展局限
普及主义是由以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JayWestbrook(8)Irit Mevorach, Modified Universalism a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96 Tex. L. Rev. 1403 (2018)为首的破产法学者提出并极力推崇的一种理论。学者们一致认为,普及主义的特点是由一个主要的法院适用单一的破产法来管理跨国破产,即在债务人的母国,或者说在债务人拥有其主要利益中心的国家启动单一的主要破产程序,其他地方的法院协助母国法院根据母国的破产法完成对全球财产的统一管理。从规范上讲,这种由主导法院和辅助法院组成的系统,植根于普遍性和服从性原则,它在跨国范围内复制国内破产制度的福利,用全球市场对称、价值最大化、降低成本的集体程序取代昂贵的、重复的、效率低下的单个程序,用其单一有效的债权解决程序,给予全世界情况类似的债权人平等的待遇。
到1990年左右,现代普及主义开始蓬勃发展,它具有两个鲜明特点。首先,它认为全球化是理所当然的,并相信如果国家之间能在法律范畴上尽可能地趋同和无摩擦,就能够极大地促进全球市场的形成。在普及主义的世界里,债权人的期待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在母国的利益,而是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其次,因其主要的拥护者是以JayWestbrook教授为首的美国破产法学者,因此它具有深刻的北美取向(9)Adrian Walters, Modified Universalisms &the Role of Local Legal 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aw, (93 AM.BANK R. L.J. 47 2019).,在JayWestbrook教授的理念中,普及主义相当于美国破产法的全球化版本——以清算或重组为目的,在美国各地根据多个主权国家的其他非破产法律进行破产宣告。
然而,在一个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中,普及主义所推崇的“纯粹的普遍性”(10)Adrian Walters, Modified Universalisms &the Role of Local Legal 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aw, (93 AM. BANKR. L.J. 472019).无疑是停留在理想层面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破产制度,有自己的原则和目标。普及主义的全球化、统一化范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立,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作为一个与自由国际主义紧密相连的理论,它需要在二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凋零的时代进行反思。无论如何,普及主义者早就承认,“理想仍然有一定的距离”(11)Westbrook, Global Solution, supra note 11, at 2277。目前,学者们开始对修正的普及主义抱有信心,认为它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性的解决方案,是通向普及主义道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它在主权主义上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对母国的债权人以及母国利益进行了保护。
(二)普及主义的可行替代物:修正的普及主义
当前,修正的普及主义是以国际法律发展当前阶段的实际情况为基础的普及主义。它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一个即使在没有公约的情况下也能复制普及主义的大部分好处的体系。如果通过国际合作鼓励法院在当地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产生与单一诉讼程序所产生的结果尽可能接近的结果,那么修正的普及主义将创造出一个可行的普及主义替代物。它保留了普及主义理想中的主/辅法院方面,但从实际出发,预计各国可能不愿意放弃对当地资产和债权人的管理主权,也不愿意容忍当地资产和债权按照主要利益中心法律的优先权规则而不是当地法律优先权规则进行管理所产生的结果差异。因此修改后的普及主义的主导思想,是让附属法院遵从主程序法院中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遵从并非自动的,而是可选择的——当母国政策与当地的基本政策相抵触或者严重侵犯当地债权人利益时,他们可以拒绝服从。根据这种观点,法院在决定如何或是否合作方面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修正的普及主义的一大优点就是它包含了普及主义的核心合作信念,它主张在一个国家的中心法院领导下进行国际协调,保持了当地法院在本国程序下的公平性,也保护了当地债权人利益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首要地位;它保留了普及主义中极具效率的部分,但也同时纳入了地域灵活性,尊重各国的法律和规定,减轻了那些担心放弃国家主权的人的恐惧(12)S. Edward Adams &Jason Fincke, Coordinating Cross-Border Bankruptcy: How Territorialism Saves Universalism, 15 Colum. J. Eur. L. 43 (2009),试图在普及主义和属地主义之间取得平衡(因为每个法域都保留了拒绝服从其他国家破产法的权力),以实现更高效和公平的跨国破产解决方案。
尽管修正的普及主义是在当前国际政策和法律土壤下汲取了普及主义的诸多优点生长而出,但现阶段的修正的普及主义制度中部分地利用了属地主义,是属地主义和普及主义的结合。
三、《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修正的普及主义的具体制度体现
学者们普遍认为,《示范法》是体现修正的普及主义的制度工具,是介于普及主义和属地主义两者之间的巧妙妥协。它包含这样一个概念,即主导的主要程序法院推定有权在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所在的法域管理债务人的全球范围内的破产债务,但考虑到当地的公共政策或相关利益者的担忧,也给予了接案国拒绝对该外国破产程序承认的权利。同时,亦允许平行辅助程序的同步进行。
对于那些认为修正的普及主义理应服从“主要利益中心原则(COMI)”的普及主义者来说,《示范法》真正的意义在于,它的承认和救济体系是以法院选择(Choice-of-forum)规则——主要利益中心原则(COMI)——为基础的。COMI原则是用于在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跨国破产案件中,提供一个统一、公平和可预测的方式来选择主要破产程序的司法管辖区。这种法院选择规则,即COMI原则,可以充当法律选择规则(Choice-of-law)。(13)法律选择规则(Choice-of-law):在选择适用法律时,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有权决定对涉及外国当事人、外国交易或若干外国因素的案件适用哪种法律。一般情况下,法院总是适用自己的法律,即法院地法(在拉丁语中称为lex fori)。也就是说,尽管《示范法》在法律选择方面所展示的态度是中立的,并没有在其条文中强制要求承认法院(recognizingcourt)适用主要程序地的破产法,但它采用主导/附属法院模式作为其核心,在理论上允许附属法院采取“普及主义”的行为——即给予他们自由裁量权去选择服从主要程序的破产法。这样,如果附属法院均选择服从主要程序的破产法,那么《示范法》颁布国的法院将有余地在可能的情况下接近普及主义的结果,从而完成修正的普及主义向普及主义的过渡。
因此,从理论上讲,《示范法》是普及主义的特洛伊木马(14)Adrian Walters, Modified Universalisms &the Role of Local Legal 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aw, (93 AM. BANKR. L.J. 47 2019).特洛伊木马在这里是指表面获取了胜利,但实际埋下了隐患,反向抑制了发展。。它的中立性应该使各国都能接受;采纳国之间的反复互动原本可以使得法院逐渐适应普及主义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利益中心法院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剩余资产管理和解决破产索赔的推定权利原本应使主要利益中心原则成为法律选择规则所应遵从的原则,为在现实世界中实现普及主义模式创造线性进展的条件。然而,由于《示范法》的中立性已经为附属法院提供了选择(附属法院可以选择主要利益中心法院的规则,或者不选,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极大地掩盖了法律选择规则的适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普及主义的实现。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国际法律发展形势来看,普及主义的实现几乎不可能。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文化背景、利益需求不同,在处理同一类法律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如果在一套规制跨国界商事行为的体系中,各个国家没有自由呼吸的空间,即没有足够的自由裁量权去做更加有利于本国利益的选择,那么这套体系将很难从文本走向现实。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示范法》的体制和程序结构创造的是一个跨国界“系统”,而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国际“标准”。(15)J. Westbrook, J. ,“Interpretation Internationale”,Temple Law Review, 4(2015),739—758.根据JayWestbrook教授的理念,体系文本建立了一个国际合作或执行体系,而标准文本则为国家或个人的国际行为创造了规范。标准文本的国际规则通常侧重于统一性,以便国家和个人行为者能够使其行为,特别是其跨境行为符合这些国际规范,并且各国能够一致地适用这些规范。相比之下,统一性却并非体系文本的主要目的,其目的应该是通过规则,使设想中的国际体系能够实现其目标。《示范法》作为一个体系文本,就是在试图构建一个跨国界的制度机制,为实现共同的合作目标而服务。在美国破产法第15章中规定,“在解释本章时,法院应考虑其国际渊源,以及促进本章的适用与外国司法机构通过的类似法规的适用相一致的必要性”(16)See 11 U.S.C. § 1508 (2012).。意味着美国在吸收引进《示范法》时,亦将《示范法》的性质全盘吸纳——采纳国适用规则时应考虑国际合作效率的最大化,而不仅是统一性。
四、美国跨境破产制度的建立路径
美国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破产事物的领导者,1978年的《破产法》第304至306条赋予破产法院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并与之合作的权力。随着1995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代表们就《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的案文达成一致,该法很快于2005年成为美国破产法的第15章。可以说,美国在跨境破产领域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采纳《示范法》前和采纳《示范法》后,美国的国内法破产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仅两个条款的原则性阐述到整个15章的建立,美国完成了较为成功的制度完善。目前,《企业破产法》修改已列入我国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2022年度立法工作计划(17)《全国人大财经委: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已形成》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211/fc9b2eb1a512487da4f1daf68a623c78.shtml,有代表提出的关于修改企业破产法的议案中就包括“跨境破产”这个专章。因此笔者认为,梳理美国的跨境破产制度,对于想要但尚未采纳《示范法》、抑或想要对本国跨境破产法进行修改的国家来说,将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前《示范法》时代”的美国跨境破产立法
在美国现行跨境破产法——美国《破产法》第15章颁布之前,美国跨境破产的早期立法路径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时期,1978年304条颁布前和1978年304条颁布后。
在1978年304条颁布以前,美国采取的还是严格的属地主义——在考虑是否服从外国破产法时,法院几乎总是着重于对美国债权人权利保障的分析。由于当地债权人的利益可能会因为其资产成为外国破产程序的一部分而受到损害,因此法院偏向于不采取普及主义的方法,即不采取国际义务和便利原则,不承认有效外国法律的原则。这意味着当时的美国法院更关注保护本国债权人的权益,而不倾向于支持外国破产程序或国际破产原则。这点也在美国1898年颁布的《破产法》(The Bankruptcy Act of 1898,也被称为“1898年法案”或“Nelson Act”)第119条中有所体现:“当破产人或针对破产人的清算或破产重整程序已在美国以外的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启动时,美国破产法院可在通知申请人或法院指示的其他人进行听证后,在考虑到当地债权人的权利和便利及其他相关情况后,根据适当的条款驳回案件或中止其中的程序。”
20世纪30年代,美国法院才逐渐停止了对国内债权人的偏袒,继而更加注重破产的国际合作——1978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美国统一联邦破产法》,第304条首次将普及主义原则正式纳入法律框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成文法确立外国债权人在美国境内资产分配权益的国家。第304条(a)款引入了辅助破产程序的概念,第304条(b)款详细列出了一旦辅助程序成立,美国法院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包括禁止任何人对债务人的财产提起诉讼或进行强制执行,要求将在美国境内的财产及其收益移交给外国代表以进行均等分配,并根据申请人的要求提供其他救济措施。第304条(c)款列出了在决定是否根据(b)部分授予救济时,法院应参考的因素。
第304条虽然蕴含了国际破产合作的理念,在其一出台之时也曾被认为是美国破产法取得的一项重大进步和突破,对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跨境破产立法均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它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尽管第304条中倡导修正的普及主义,但第304条(c)款中的六项因素之间的价值取向却并不十分统一——在第1、3、5项中暗含了与外国程序合作的意图和目标,而2、4项中却强调了保护国内债权人的利益(18)第304条(c)款具体规定如下:在决定是否根据(b)部分授予救济时,法院应以最经济最迅速的管理理念为指导,并符合以下要素:a.保证公平对待所有对该财产提出债权或权益主张的持有人;b.保护美国的债权人免受在外国程序中处理债权时的不利和不便之害;c.防止对该破产财产的优先或欺诈性处置;d.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规定的顺序分发破产财产的收益;e.遵循国际礼遇原则;f.在适当情况下,为外国程序所涉及的个人提供新起点的机会。。这两种不同的倾向,由于美国法院拥有较为广泛的决断权(19)季立刚、解正山:《美国跨国破产立法的最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致使其在决定是否给予外国救济时给出了不一样的解释,引发了不同的法官在普及主义和属地主义中的分化,造成了极大的司法不确定性,因此很快便被第15章所取代。
(二)“后《示范法》时代”——美国《破产法》第15章
美国于2006年加入《示范法》,并根据《示范法》制定修改了本国的跨境破产制度,体现在美国《破产法》第15章中。美国《破产法》第15章采用的《示范法》体现了修正的普及主义理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修正的普及主义运作方式如下:外国跨国债务人将在外国法院提起全面的破产程序。然后,破产债务人、受托人或其他指定的管理人(“外国代表”)将向美国破产法院提起第15章申请,以获得该法院对跨国债务人财产管理的协助。这种协助可能包括停止在美国的所有债权人的追债;要求移交美国境内的资产以便在外国破产案件中进行分配;或要求协助在美国境内进行调查,以便找到债务人的资产或探索潜在的诉讼理由。
第15章申请开启了一个两步走程序,法院将据此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与外国程序合作。第 15 章要求,如果该程序是在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提出的,那么法院应承认外国程序为“主要”程序;如果该程序是在债务人进行非临时性经济活动的地方提出的,那么则为“非主要”程序。这一承认步骤是非常典型的普及主义类型的跨国界破产办法,因为它几乎自动承认外国程序,从而创造了一种可选择机制。“几乎自动”(20)B. Andrew Dawson,“The Problem of Local Methods in Cross-Border Insolvencies”, 12 Berkeley Bus. L.J. 45 (2015)的意思是,在某些情况下,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可能仍需要司法确定。此外,如果“承认”明显违背了美国的公共政策,那么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一旦给予承认,法院就进入下一步——合作步骤,根据该步骤,它必须确定给予外国程序何种救济,以促进对债务人的管理。如果外国程序得到承认,则有权获得某些即时救济(如果是外国主要程序)和其他酌情救济(无论它是外国主要程序还是非主要程序)。虽然承认阶段反映了在程序层面上对普及主义的预先承诺,但合作阶段平衡了普及主义和属地主义。某些承认是自动给予外国主要程序的,反映了在不担心选择国际法院时对普及主义的偏爱。外国主要程序和非主要程序都可以获得额外的救济,但只有在法院确信这种合作不会对当地利益造成不适当的负担时,才可以进行。例如,在给予酌情救济时,法院必须确信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债务人)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示范法》第22条(《破产法》第1522条)反映了这样一种想法:尽可能地在“给予外国代表的救济”和“此种救济下所影响的其他人的利益”之间保持平衡。在许多情况下,受此种救济影响的债权人一般是当地债权人。
最后,属地主义保护见于《示范法》第6条(《破产法》第1506条)的公共政策例外:“如果本法规定的行为明显违背本国的公共政策,本法中的任何规定都不能阻止本国法院拒绝采取本法规定。”尽管公共政策的例外情况很少使用,但《示范法》依然保留了这一条——以公共政策为由,排除或限制有利于外国程序的任何行动的可能性,包括对该程序的承认。虽然从国际角度来看,这可能会给《示范法》的实施增加不确定因素,但是从国内角度而言,第6条增加了在国家内部适用法律的确定性。从第6条也不难看出,《示范法》中所体现的修正的普及主义,具备了普及主义中“法律选择规则”(Choice-of-law)的优点,同时也对国家主权进行了一定的保护,是属地主义和普及主义的巧妙结合。
美国《破产法》第15章致力于法院的程序规则选择,从而建立了法院间合作的根本基础,它构建了良好与稳定的法律环境,通过财产价值最大化为跨国公司的成功重组提供一套良好的法律机制。并且,第15章在第304条的基础上,强制性规范大幅度增加,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法院法律适用不一致的情况,极大地提高了司法确定性,有效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效率和增长。
五、我国跨境破产立法现状及美国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跨境破产立法的发展历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跨境破产的立法和实践上均缺乏理论基础和经验。1980年的香港妙丽集团破产案和1983年南洋纺织品商行破产案是我国跨境破产早期实践中的两个经典案例。在这两起案例中,当境外的破产代表要求接管我国境内的破产资产时,由于我国缺乏此方面立法和实践经验,均是通过行政权力的介入来最大限度地协助跨境破产程序,与此同时,由于政府的介入,也避免了对境外破产程序的效力问题的认定。紧接着,在1992年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深圳分行破产案中,尽管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均有破产资产和清算程序,但我国否认了境外破产程序的效力,体现了我国当时的属地主义倾向。当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急需引入外国投资进入中国,因此对本国资产利益进行保护是当时的本能诉求。正如前文所述,美国、英国等国家在处于相同发展时期时,为更好地吸引并留住外国资本在本国发展,亦采用属地主义立法价值取向。
随着我国的国力不断增强,经济飞速发展,在吸引境外投资的同时,我国资本输出国的角色也愈加明显,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国门到境外投资,以地域界定效力范围的属地保护面临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属地保护的地域局限与国际化的开放合作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21)曹启选、叶浪花:《我国跨境破产的实践发展和路径探索——以全国首例香港破产程序认可和协助案的审理为视角》,《法律适用》2022年第3期。在世纪之交的广国投案和2005年的法国百高洋行案等的催化下,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首次以人大立法的形式对跨境破产进行了规定,是我国跨境破产立法史上的重大突破。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条的规定,外国法院作出的破产裁决经我国法院审查后可以获得裁定承认与执行,确立了我国互惠原则之下的修正普及主义立法立场。但《企业破产法》虽然在跨境破产立法上实现了重要的突破,但是其对于跨境破产仅为原则性规定,而缺乏与之匹配的相应细致规定作为支撑,并未搭建起跨境破产法律制度的框架,且在原则性规定的设置上仍存在许多模糊地带。
(二)我国跨境破产立法的局限性
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仍有许多局限性。首先,对外国破产判决和裁定界定不明确,没有将破产宣告裁定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承认予以区分,因此在实践中对于承认的内容以及承认后与之匹配的救济措施仍没有明确的规定(22)张玲:《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破产司法合作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其次,我国《企业破产法》在立法技术上不够成熟,缺乏跨境破产法律所追求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比如,我国借用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诉讼中的互惠和公共政策理念,但却在破产法中对“互惠关系”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同时,破产案件中公共政策例外条款适用的情形也没有明确的指引。再次,在《企业破产法》第五条中规定,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应当以不损害我国债权人合法权益为基础。但是对于这一款中“合法权益”的限度,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解释和具体的尺度。从美国第304条被取代的经验来看,在针对本国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和外国破产程序合作的条款上,如果不加以细致和详细的规定,很容易在实践中产生对本国债权人的过度保护,或是法院基于自由裁量导致判决不确定性增大的结果,从而影响对相关国家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
(三)美国跨境破产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跨境破产法制度从第304条到第15章的变化,是从原则性规定到强制性规定增多的变化,也是美国法院的判例从法官自由裁量导致的在普及主义和地域主义之间争论不休的局面,演变为相对确定的修正普及主义制度的变化。美国跨境破产的立法研究在制度更迭中,正向跨境破产法律所追求的确定性逐步靠近,而这也与当时美国破产法学界针对普及主义和修正的普及主义的激烈讨论分不开,以JayWestbrook教授为首的破产法学者们在思维碰撞中所形成的理论观点为美国跨境破产立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同时,随着国际经济不断发展,境外投资不断增多,除美国之外的各个国家也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从属地主义到普及主义再到修正的普及主义的转变,如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国家新加坡亦选择加入《示范法》(23)龙光伟、王芳、叶浪花:《“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破产的发展路径选择——新加坡跨境破产发展历程的经验与启示》,《人民司法》2020年第1期。,完成了属地主义到修正的普及主义的转变。
在我国,虽然学者们在采纳《示范法》与否上仍争论不休,但在某种程度上,选择采纳《示范法》可以更好地让我国以清晰的制度载体去采纳修正的普及主义制度,从而更加完善我国的跨境破产制度。《示范法》作为一部中立性跨境破产制度,赋予了采纳国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作为采纳国可以选择部分或全部制度去应用。美国几乎全盘引入了《示范法》,第15章的生效以及其在实践中取得的成功已经说明了《示范法》的可取之处。美国虽国情与我国不同,但其《示范法》的采纳路径,以及从第304条到第15章制度更迭的背景、原因及历程,依然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首先,具体而言,“主要利益中心原则”是跨境破产制度的核心原则,正如前所述,它是修正的普及主义的灵魂体现。因此,笔者认为,在《企业破产法》修订的过程中,我国应对《示范法》中的核心制度“主要利益中心原则”予以采纳,并进行详细解读与细化,特别在其认定规则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的立场(24)黄圆圆:《“巴西电信案”对跨界破产主要利益中心规则的突破与发展》,《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年第4期。,以期获得更加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中外跨境破产合作。此外,作为平衡国家利益与跨境破产合作需求的核心条款(25)黄圆圆:《公共政策例外条款在跨界破产中的适用与启示》,《时代法学》2018年第4期。,在跨境破产合作中限制性解释“公共政策条款”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26)石静霞:《香港法院对内地破产程序的承认与协助——以华信破产案裁决为视角》,《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除美国外(27)美国《破产法》中关于公共政策例外的规定在第1506条。,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毛里求斯、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已经将《示范法》中的第6条完整纳入本国的跨境破产制度中。在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五条中规定:“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涉及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财产,申请或者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裁定承认和执行。”该条款虽然与公共政策例外有着相似的外观,但却缺乏更为详细的解释,如“不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的类似表达就出现在我国许多不同的部门法中,难以在跨境破产语境下产生具体的、特殊的释义。因此,在进行立法改革时,应着重对公共政策例外的内涵及适用提供详实的指导。
其次,我国应加强对普及主义和修正的普及主义等跨境破产基本理论的研究。目前我国对于该理论的研究依然停留在一般性阐述上,缺乏对它们最新发展的探索以及其在制度上影响的深刻认识。美国跨境破产立法的巨大进步,也是建立在学者们对理论的激烈讨论和深入研究之上。因此,想要构建既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又能协调国际破产合作的理论体系,想要在跨境破产立法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要深刻地认识跨境破产领域的基本理论,为立法、司法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