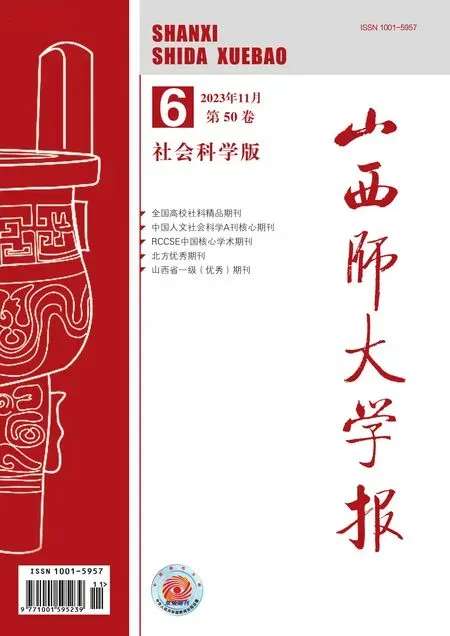“个体化时代”的生存困境与人的价值重建
——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公共性规制的努力
2023-02-26袁祖社
袁 祖 社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西安 710119)
“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是一种近代性或者现代性现象,它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的世俗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意味着个体对于自主性生存的权利的追求、捍卫,对于个人独立性价值、自由和解放的坚持。近代社会之前,个体所以可能的关系背景,是具有从属关系性质的阶层隶属、社区归属、宗族认同以及对相应的地方性的宗教信仰、约定俗成、道德规范的遵守。
针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历史性关系的存在情境,马克思表达了基于唯物史观立场的深刻识见:“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民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民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 页。也就是说,现代性社会生存情境中,所谓“个体化”,就其本质而言,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相互矛盾的结合体(2)Yauman Gygmunt,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Polity Prcss,2000),32.,个体一旦进入某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结构,就意味着必然接受其外在性的诸多规范的强制,依照社会所希望的方式选择一种不由自主式的生存和生活,并且为这种选择及其所可能导致的结果负责,以期在被动性意义上获得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3)Giddc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启蒙现代性自由主义“个体化生存”神话及其现实:理念、逻辑与话语的虚妄
自由主义的观念源远流长,尽管其涵义是“复杂的和有争议的,但人们一般都同意自由主义包含对以下四种主要价值或原则的信奉:个人的同等的道德价值(平等对待的原则是有争议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限政府,私有财产”(4)[英]乔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张小玲、杨立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主张和业已完全制度化的实践,被正确理解了的自由主义,原本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信念,“一种哲学和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社会体制构建和政策取向。它还是一种宽容异己、兼容并包的生活方式。它把自由当作政府的基本方法和政策,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人与社区的生活方式”(5)[英]乔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张小玲、杨立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已故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总结出了自由主义的六大基本原则:自觉、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多元主义、中立性、公共善的原则以及正当(权利)对善的有限性等。(6)参见顾肃:《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页。当然,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诸多内在困境。
“自由意志”“独立自我”“个体化持存”是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主张。滕尼斯指出:“进步的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和主要的运动是特殊化、分化和个体化的倾向,……它是指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及目的都要挣脱其束缚的共同体才可发展。”(7)[德]斐迪南·滕尼斯:《新时代的精神》,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页。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引起了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与转型,社会结构方面变革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由原本“同质化的统一”走向一种“异质化与分化”。在一种新的“契约式”法理性政治的、法权的国家共同体中,个体逐渐摆脱了对原初的自然共同体的依赖,被“抛入”一种“社会化了”的关系情境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同时又非常孤立的“原子化的自我”。在当代“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贝克看来:“个体化是指个体行为的框架以及制约条件的社会结构逐步松动,以致失效,个体从诸如阶级、阶层、性别、家庭的结构性束缚力量中相对解放出来。同时个体对传统的思想意识和传统的行为方式越来越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个体与传统共同体(主要是家庭和集体)关系的弱化的结果,也导致了由此种关系和环境所提供的相对牢固和稳定化的依附和庇护关系开始松懈。“在个体化社会中,社会对于个体来说已经是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不易辨识、难以捉摸的。”(9)[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0页。此种新诞生的个体“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势的特征”(10)[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81—182页。。社会存在、社会生化的日益个体化,客观上要求个体重新发现、寻找和确定个体何以如此、所以可能的新的构成性要素,这就是所谓非确定性的变动性最大的特定情景和惯习。这种流动性的背景导致了“安全感”与“确定感”的丧失,决定了个体对于确定性的自我的建构、认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个人越来越成为“孤岛”,社会化属性和能力不断丧失,“个体越来越孤独和原子化,更少地在帮助他人方面审视自己”(11)Simon Tormey,“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2(2003)。。如此以来,普遍性的焦虑和必要的归属感的获得,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以驾驭和自立推进性。”(12)[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7页。
就世界范围内现实的人类历史实践的结果来看,自由主义其实是人类理智的一个并不高明的发明。自由主义毫不掩饰人性的恶和无限贪婪、占有的欲望,意识到这是一个单靠有限的、非完全进化的有缺陷的人类智识,是根本不可能根除的先天性痼疾。因此,自由主义倾向于对非完满形态的“人性”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允许以类似自然科学的“实验”的方式,提供一种让人性之恶尽情展现的平台和场所。至于说这样一种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其对于人性自身、对于制度和文化,以及文明价值的损害究竟有多大,无法给出一个充分的预估。自由主义者相信,人类自身是有足够的对于究竟何为真正的善恶、正义等的明晰的辨别力的,也相信人类在经受了自由主义极端泛滥以后,会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反省意识,并随之采取必要的矫治行动的。因为,坦率地承认人性的自私曾经被公认为是一种“美德”。既然自有人类文明以来,尽管人类大多数情况下以“私且恶”的名义,理直气壮地干了许多违背、伤害天理、人性的事情。自由主义从来不愿意直面自身所深陷其中的深刻的迷误,它甚或不认为自由主义本身有什么错。自由主义天经地义地认为,就本质和应然态而言,人理应是自然、自在的,不应该被来自外部的一切所束缚。历史上和现实中,人之所以始终处于非自主、被奴役等身不由己的状态,那是由于人类理智还没有认识到整个对象世界的本质。一旦人类理智掌握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一切存在秘密,人类的自由就会变成现实。自由主义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都不是自洽的。因为单凭生存的自由逻辑,人类无法在整全性意义上成就一个人格圆融的自己。道理在于,自由之于人,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的价值。真正的、真实的自由,从来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制度的一个因素,相对自足性才是自由的真谛。那种试图绝对化自身的自由信念,无论伪装得多么巧妙,到头来都只是一种欺骗。
人类生存的自由主义逻辑之价值取向,是无休止的永远难以最终满足的欲望引导下赤裸裸的利己。自由主义的发明者、拥护者以及实践者们,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明确地洞悉了这一思想倾向所可能带来的许多恶果。不仅如此,自由主义在变成一种居于“正统”地位的理论形态、制度实践、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以及普遍的生活信念和理想以后,就变得更加精致、更为隐蔽。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为业已破绽百出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做着这样、那样的苍白辩护。自由主义者们所推崇的自由,就其基本涵义和意义而言,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其实始终是晦暗不明、充满暧昧的。其理由在于,现实的、真正的自由原本就是一种多维、多义的复杂。属人的或者人类的理论和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能够达到、所能够实现和体验的自由,始终只是作为人类意义总体的非常有限的一部分。真正的自由,永远在人类理智所不及处。在被不正确地理解和错误地实践了的自由主义的社会历史中,人类或许在短期内获得了财富、平等、地位……从而误以为自由主义就是人类的终极性真理。其实,这些财富、繁荣和享受的背后,则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究竟谁应为这些历史的负面清单买单,其实并没有引起人类理智足够的关注。着眼有关自由主义问题上历史主义和历史性的有机统一做系统观照,理论的审慎辨析和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和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即使在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体系、话语从一开始是非圆融态的,而是漏洞百出,面临着依靠自身难以解决的诸多困境。自由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框架中,抽象现代性启蒙的哲学理论和话语主张,依托技术理性、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实践,足够强势。自由主义文化、价值和制度实践标榜的所谓主流性、主题性话语——理性、主体、自由,从来都没有依照自己的逻辑顺利确立,而是充满着内在的悖谬,其对于人类历史进步的真实现实的解释方式漏洞百出,出现了“理性的工具性异化”“主体的非人化消匿与沉沦”以及“自由的非人道性背反”等现象,引发了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离心化以及精神生活的虚无化等严峻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在其“普世化”和“极端化”的历程中,在经济上强调最大限度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其结果,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度内部,是强势经济利益集团愈来愈丰厚的获利,而在国际社会,那些拥有明显的先天竞争优势的先发现代化国家则坐享其成。相反,对于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必须拥有强大的政府管理和财富再分配能力,否则,难免被强大的某个经济利益集团所绑架。在回答“为什么对自由主义的哲学辩护是重要的”这一尖锐问题时,克劳德著指出:“首先,即使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和制度已经在非自由主义的替代品的威胁面前安然无恙,活生生的问题依然存在,例如……自由主义的形式应当是自由放任的还是再分配的,多文化的还是单文化的?哲学是巨大的和复杂的问题,其意义远远不是单纯学术性的;它们深深地影响着千百万人的生活。……其次,自由主义的未来无论如何都远远不是很有保障的。单就知识层面来看,自由主义原则受到许多挑战,无论在西方思想传统之外(伊斯兰教和儒教),还是在内部(马克思主义、参与民主、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版本)都是如此。最后,自由主义自身的原则把注意力吸引到它的合法性的根据上。既然自由主义有对于道德价值的平等和个人自律的基本信条,它在每一步骤上都有责任追问,社会的制度和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对所有的公民实际上是所有通情达理的人都是有正当性的。”(13)[英]乔治·克劳德著:《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应奇、张小玲、杨立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29页。
启蒙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文化意识形态根基,是自由主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的制度实践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依托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几乎就是人类幸福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就人类社会、人类制度理性以及人类错综复杂的生存与生活现实而言,自由其实并不必然代表纯粹的狭隘的“私”,被正确理解和规制了的现实的自由(理念、主义、文化以及秩序性实践),其实是经过利益博弈后最后胜出的最大的“公”,其所彰显的,可能是人类的真精神。人类发展到当今,“私”的力量依然足够强大。如果说“公”是人类生存的未来之应然,那么,“私”则是人类社会的“实然”,人的生活基本上是自己无法真正掌控的私欲私利本位秩序和强制。生活的无忧无虑和自如如意,常常是一种奢望。常见的情形是,有人疯狂地、不择手段地追逐、攫取并贪婪地占有、挥霍金钱与财富,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证明自己是自由的。到头来却发现这种自由的获得,根本就是本末倒置。自由主义同样可以视为人对于自己行为的一种辩护方式。人需要自由,人也一直追求着自由,享受着用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一点点可怜的自由。人类的思想、理论、制度、价值观和生活形态,要么个体性自由,要么群体性公共。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作为对于“私”和“个人欲望”的社会性、制度性约制,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公共性福祉本位的“公共”性价值理论和实践,是一以贯之的当然的选择。
二、 现代性视域内“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迷思:埃利亚斯的识见及其启示
当代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1898—1990)关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依埃利亚斯之见:“这个由我们大家一起构成的‘社会’,它究竟是怎样的样子?我们大家彼此组成了它,但就它如今所成为的那个样子,却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人,甚至不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意愿、共同计划的结果;它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有众多的人现成在场;它之所以保持运转,仅仅是因为有众多的单个人有所意愿、有所行动。尽管如此,它的构造,它所经历的巨大的历史演变显然并不取决于单个个人的意志。”(14)[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页。在社会本质问题研究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将社会理解为某种具有超越性的“世界精神”,一种是将社会理解为“超然于个体心灵”的“集体灵魂”。对此,埃利亚斯明确指出,“不管从何处着眼,人们遭遇的都是类似的自相矛盾:对于我们自身作为单个个体之所是,我们抱着确定的传统观念。对我们在说‘社会’这个词时我们的意指,我们也同样抱有某种确定的观念。然而,这两种观念,一是我们将自己当做社会的那个意识,一是我们认为自己是个体的另一个意识,这两者从未能够彼此统一起来。与此同时,我们肯定也多少清楚地意识到,现实中并不存在那种分隔个体和社会的鸿沟。对个体组成社会和任何个体都是个体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人会产生怀疑。可是当我们试图把自己在现实中每日所经历的东西在思想中重构出来时,我们的思想链中那些不在这方面就在那方面总是一再出现的断裂和缺口便显示出来了。这就如同一种拼图游戏,把那些单个的组件拼接起来未必就是图案的整体。”(15)[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7页。埃利亚斯注意到,今天,在社会生活自身之中,我们不得不为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做不懈的努力:人们之间共同相处的秩序是如何可能以及是否可能的?这是一种能够促成以下两个方面更好地协调一致的秩序:一是所有个体的个人的需求和偏好;一是那些对个人提出的要求,如众人的携手合作、社会整体的维持和功能。“无疑,营造一种人类的共同生存,使不仅是少数几个人,而且是社会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有机会彼此协调一致,这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那个秩序,如果我们的这个愿望对现实状况拥有足够的影响力的话:只要我们冷静地想一想,那么很快就会发现,上述这两个方面其实只有联系在一起才是互为可能。”(16)[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9页。但是,现实的人类思想和现实的真实情境是,论及“整体”,我们一般的是将它想象为某种多少是和谐的东西。但人类的社会群体生存却充满了矛盾、敌对和冲突。上升变成衰落,和平时代战火绵延,经济发展中却危机不断。人类之共同生存全不是这般和谐。“即便不说它是否和谐——至少‘整体’这个词在我们心里唤起的是关于某种自成一起的东西的想象,是关于这样一种构造物的想象,它有着勾勒分明的轮廓,有着一种直接可见的形态和可触摸的、或多或少可直观到的结构。然而,社会并不具有这种可直观到的形态;它不具有能让我们直接在空间看到、听到或把捉到的结构。作为整体来看,社会向来或多或少是封闭的:不论人们从何处着手观察它们,它们在时间的视域内,即是说从过去到未来的限度上,始终是开放的。”(17)[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4页。道理在于,历史上和现实中,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是某种很独特的东西。它在存在的其他领域里没有一个类比项可寻。尽管这样,那些我们在观察其他领域内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时可获得的经验,应该能在这里的某一方面给我们提供帮助。(18)[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客观地讲,实际上现在还没有一种图式能充分传达出人们之间的关联性对单个人的特征形成的重要性,除非我们深入这些关联本身的本性和构造之中,否则就无法想象出人的功能的互渗关系是如何牢固地并在何种深度上将单个的人维系在一起的。总之,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我们就不能对诸个体相互整合形成社会的过程获得一个清晰的图像。“假如人类不是从本性上就在他们的行为驾驭方面比动物更具可塑性和变动性的话,那么,他们彼此就既不能组成一种自律的历史连续体,组成社会,又不能作为个体拥有某种个体性。动物群体除了具有‘自然进化史’,别无其他历史;……”(19)[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72页。“……单个人之所以能够说‘我’,是因为和似乎他同时也能够说‘我们’。甚至‘我在’这种思想尤其是‘我思’的思想,就已经预先设定了他人的存在与他人的共在——简言之,已预先设定了一个群体,一个社会。”(20)[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72页。“社会和社会的规制离开了个体就什么都不是;它绝不是与单个人‘对立’的一个‘客体’;它是被每个人叫做‘我们’的东西。但这个‘我们’的出现,不是许多称自己为‘我’的单个人事后聚在一起,并决定成立一个共同体的结果。人际功能和联系是相互依赖的,我们借助‘我’‘你’‘他’和‘她’,以及‘我们’‘你们’和‘他们’这样以下语法将它们再现出来。它们中没有哪一个能无需另一个而独自存在。”“每一个‘自我’都不能免于被统摄进一个‘我们’,这一点也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当一个个自‘我—们’的行动、计划和目的相互掺杂在一起时,总是不断地衍生出某种东西来,这种东西,就如它是其所是和成其所成为的那样,绝不是哪个个人所计划、所企图或者所创造的”。(21)[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风靡西方世界的以法国哲学家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关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理解和诠释,颇具启发性:“事情很简单:就是我和他人的关系首先并从根本上讲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而不是认识与认识的关系,如果唯我论应该有可能被摒弃的话。事实上,我们已看到胡塞尔的失败在于他在这个特殊的水平上以认识来衡量存在,而黑格尔的失败在于把认识和存在同一了。”(22)[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杜小真校,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328页。在这个基础上,萨特主张“他人不是对象。他在他与我的关系中保持为人的实在”,“我们的关系不是一种面对面的对立,而毋宁是一种肩并肩的相互依赖。”(23)[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杜小真校,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328页。因此,“别人和我的意识的原始关系不是你和我,而是我们”。(24)[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杜小真校,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328—329页。
三、 “共同体中的人”:以后现代文化—价值立场恢复、建立人与对象世界的真实性联系和关系
在《经济与社会》中,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首次提出“共同体化”这一论题。依韦伯之见,所谓 “‘共同体化’应该称之为一种社会关系,如果而且只有当社会行为的调节,在个别的情况或者一般的情况下或者纯粹的类型中——建立在主观感觉到参加者们(情绪上或者传统上)的共同属性上。”(2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0页。可见,“共同体”的获得,是基于特定的历史和生存情景中不同主体之间在共同活动之中的相互认知、相互影响而建立一种内在性关系场域的过程。在当代西方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鲍曼眼里,共同体是一个温暖、温馨、舒适、人人相互依靠的地方,是现实的主体基于特定目的自觉建构的结果。作为交往共同体、价值实现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但是在日益市场化、功利化的社会现实,此种并生、共在的主—主关系状态,已经被严重扭曲了。(26)[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序言,第1—8页。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进入全球化新的历史实践情境之中。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世界性历史以及个体存在的地域化色彩日益淡化的过程,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固有边界被逐渐打破的过程,是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多样化、多元化关系质态的形成和确立。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毋宁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不同存在方式间相互观照的场域。作为一种新的参照,曾经作为民族国家单元内相互独立和孤立化的个体,现在几乎同时被卷入了一种“一体化”的生存空间,被迫调整、改变自己的生存坐标。依埃利亚斯之见,就全球化层面而言,人类走向一体化的转变过程现在的确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但一种新型的世界意识的雏形,特别是人类间认同的进一步扩展,已经变得清楚明了了。许多迹象表明,已经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责任意识,来帮助改善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个人的命运,不管这些个人具有怎样的国家或部落归属,一句话,不论他们具有怎样的群体认同。“那种对目前被人们当做人权来理解的东西的倡导,其动力的一部分无疑来自大国之间相互斗争所要获得的政治利益。但只要人权精神今天被政治家狭隘地用来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把双刃剑就会反戈及己。只需明天,人权精神就会反诘那些今天用它来达到狭隘的国族目的的人。”(27)[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93页。“……现时代的一体化进程,除了上述所讲到的从部落到国家,从民族国家到洲级联合体那两个以外,还有第三个层级。只要做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在现时代,单个国家民众的利益,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已不再取决于这个国家——甚至是潜在的洲级国家联盟如欧洲——为其民众提供的保障了。即使在今天,维持生存的机运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层面上发生的事。全体人类才是今天具有最终决定性的生存单位。”(28)[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64—265页。“在过去两百年的时间历程中,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已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所有人类群体之间已经形成某种日益重要的依赖关系。人类之间不断增强的一体化好歹都显示出,它不仅是一种最广泛的,也是一种产生最大效应的整合层级。”(29)[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65页。
就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类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生存情境而言,全球范围内共同体的加速破坏和纽带的断裂,是先发现代化国家经济社会变迁实践中无法避免的宿命般的境遇。这种现象所以产生,与对于将增长等同于发展错误有关。“发展主义”是“二战”后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普遍遵循的现代性信念,其所表征的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抽象、片面的价值观主张。其核心要义,就是将“发展”等同于“增长”,将不断累积的社会“财富”视为“进步”的标志。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和现实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如其所愿的民众幸福感的同步增加,反而带来了以生态破坏、社会动荡以及以虚无主义等为代表的精神生活危机等负面后果。正是基于此种悖论性现实,全球范围内,发展理论的研究者们对上述发展观展开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与反思。从此以后,国际社会关于现代化与发展的论争进入到以强调“社会发展”“综合发展”以及“人文发展”等新的阶段,引起了发展观的新的变革,一定程度、一定意义上纠偏,矫正了社会现代化的航向。人们普遍认识到,将发展视为单一的经济增长,以财富多寡作为衡量进步和幸福的尺度的做法,是先发现代化国家的一厢情愿。如果一种发展没有将“大自然的生态财富和环境成本的核算”(生态—绿色GDP)等计算在内,那么,由这种模式的发展和现代化实践所带来的所谓“高水平、高质量的生活”就是有缺陷的,它不仅不能体现真正的经济发展程度,同时忽视或者排除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价值要素。真实的情形是,不仅先发现代化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始终遭遇着“发展悖论”: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发展并没有与此一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变革、文化水平提升和环境的改善同步增进的现象,相反,却出现了经济的通货膨胀、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生活中的贪污腐败所导致的政治动荡等。美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小约翰·科布认为:“当人类活动开始对人类环境造成全球性的威胁时,西方的想象是从理论上把自然削弱为人类经验的功能或一种静止的、对能动的人类活动来说没有内在价值的条件,分散了对自然的注意力。”(30)John B. Cobb Jr. &David Ray Griffin, Process Theology: An Introductore Exposition, (Westminster Press,1976),146—147.人类对待自然的征服和宰制态度不仅不会造福人类,而且其结果会毁灭人类。“整个自然都参与了我们,并且我们就在它当中。”(31)John B. Cobb Jr. &David Ray Griffin, Process Theology: An Introductore Exposition, (Westminster Press,1976),155.“未来是完全开放的。我们在我们的决定中创造未来。我们对未来负责。”(32)John B. Cobb Jr. &David Ray Griffin, Process Theology: An Introductore Exposition, (Westminster Press,1976),81.科布深刻批判现代经济理论有关“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实质及其危害。崇尚自我利益最大化为追求的结果,忽视了自然界的存在价值:“自然界被简单等视为单一物质,即被人类使用的客体。其中任何部分的价值都是由乐意为它们支付价格的人决定的。人类的享受在本质上是有价值的,而且整个系统都是为了支付和增进这种享受而建立的,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追求这个目的的工具罢了。”(33)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114.具体而言,经济人对于在社会中的地位是漠不关心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个体对于生活感受的满意度主要是随着个体与其他个体联结的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在其共同体中的相对位置。“……经济福利的绝对水平对个人的满意度贡献甚微,而社会给予的相对地位却做出了不小的贡献。”(34)John B. Cobb Jr. &Herman E. Daly,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ivonment,and a Sustainzble Future,(Beacon,1989):86—87.在此基础上,科布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的“后现代共同体”理论。依科布之见:“人是由他们与肉体和更广泛的自然界、特别是和他人的内在关系构成的。除了这些关系以外,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形成并成长于人类共同体中,正是在共同体中并通过共同体,他们达到了真正的个性和人格。”(35)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121.科布对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快速发展一定会同时带来每个个体幸福和福利的同步增进的论调持否定态度,因为经济增长指标只是积累了数据。尽管宏观总体上统计数据不断增加,但这种增加由于无法准确显示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因此根本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所有经济学家都假设国民生产总值对经济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大部分假设认为它与人民幸福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如此,“成功的经济发展就意味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令人满意的”(36)John B. Cobb Jr. &Herman E. Daly,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ivonment,and a Sustainzble Future,(Beacon,1989),63.。事实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与人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之间并不会同时发生:“国民生产总值所衡量的市场行为忽视了社会成本,并且国民生产总值也确实包含了为减少这些相同的社会成本的社会行为。显然,国民生产总值夸大了经济带来的福利。”(37)John B. Cobb Jr. &Herman E. Daly,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ivonment,and a Sustainzble Future,(Beacon,1989),64.1990年科布等人提出了ISEW(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即可持续经济中衡量人民幸福的指数。科布认为,ISEW比国民生产总值更能真实地反映真正的经济福利,因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同时ISEW不一定伴随增长。
科布据此对现代人类的生存价值目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为我们自己的享受而活着,而且也为了我们作为其部分的那个整体而活着。”(38)John B. Cobb Jr. &David Ray Griffin, Process Theology: An Introductore Exposition, (Westminster Press,1976),158.科布倾向于用“共同体”来表达人类群体,主张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在其所著的《后现代公共政策》中,科布指出:“人是由自身与肉体以及更广泛的自然界、特别是和他人的内在关系构成的,除了这些关系以外,他们就根本不存在。”(39)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 Polic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121.科布指出,德国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传统也许会引发不同的政治思潮,它可以使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具体化。……这确实猛烈地打破了个体主义,但是却没有打破实体论者的思维,它仅仅是将实体从个体转向国家或各个阶级。“对于所有的这一切,我现在要强调共同体的思想,这是实体主义思想忽视的地方。这是因为,实体主义思想认为,关联对被关联者来说是外在的事情。无论是单个的人还是单独的阶级,他们保持着独立。不论他们的关系是利他主义的还是相互竞争的,这一点都是千真万确的。”“当不存在共同体的概念的时候,共同体的福祉的概念也不可避免地无人谈起了。”“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共同体形而上学的概念。共同体与其他社会形式的区别在于进入到另一个人的生活的方式。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强健的共同体是核心家庭。”“……在共同体中,思维和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成员的思维模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认为共同体存在独立的个体的话,我们可能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责任。一个人类共同体如果不是一个人的共同体,那么它就什么也不是。但是同样地,离开共同体的人也不存在。”(40)John B. Cobb Jr.,The Common Good:Individual Rights and Community Responsility, (Ottawa: St.Paul's University Press, 2003).
立足共同体化生存的立场和人类公共福祉至上的信念,就现代发展哲学的理论视野及其终极价值预设和核心关切而言,发展在本质上最终要以人为中心,实现整个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体现并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论及社会现代化实践中人类的经济行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合理性”非常具有启发性意义。依韦伯之见,前者强调的是技术的或计算的合理性——工具合理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价值的或伦理的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其宗旨在于“要提出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并以此用价值合乎理性或者在实质上目的合乎理性的观点来衡量——哪怕形式上还是十分合理的即可以计算的——经济行为的结果”(41)[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页。。很显然,为现代社会所推崇的“实质合理性”构成经济行为合理性之最根本性内容,明确地凸显了特定经济行为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伦理行为意涵。也正是针对此一论题,德国当代著名伦理学家科斯洛夫斯基有关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人的经济行为动力结构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有重要借鉴性意义的答案。科斯洛夫斯基指出,通常认为,“最强的动力(指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最好的动力(指人对自我完善的追求)”是人类经济行为中最常见的两种类型,“人的最强的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42)[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页。。著名发展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当代美国学者古莱就明确指出:“发展乃是彻底的解放,这种解放的目的是要将人类从自然的枷锁中、从经济落后和压迫性的技术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不公正的阶级结构和政治剥削者、文化和心理异化中解放出来——总之,从一切非人性的生活中解放出来。”(43)[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页。同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们普遍认为,贫穷国家的贫穷主要是因为他们极端缺乏资本,而且,追加资本正是他们更迅速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我认为,仍然需要重视资本的特殊类型方能求得这种协调……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44)[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页。针对发展主义无视“内在关系”“主体能力的全面性”以及“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相协调”,武断地将不断升级的“需要”“欲望”“增长”和“财富占有”视为唯一价值尺度等的弊端,当代法国著名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表达了自己的深刻洞见:“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的……在原始交流中,每个关系都使得社会更加富有。而在我们这个‘区分性’的社会中,每个社会关系都增加着个体的不足,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与他人比较的时刻被相对化在原始交流中,它是通过与他人建立的关系本身才获得价值的。”(45)[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6—57页。印裔美籍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更是明确表示,自由应该是人的最高价值标准,“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46)[美]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 页。。
依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之见,社会的“现代化不仅仅导致中央化的国家力量、资本的集中、更紧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关系网络,以及流动性和大众消费的发展。它同样导致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脱离,即从历史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解放的维度);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祛魅的维度);以及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47)[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个体化之于个体自我确定和自我成就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在于,面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生存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个体对于包括道德规范等在内的自我何以可能的解释资源,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差异化的。现代性社会的制度规则更多保护个体而非群体,即使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但是个体之间无法实质性介入,个体对于社会、国家等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隔膜,根本无法找到交集,传统的同一与秩序已被颠覆,具有群体特征的“文化意义资源”日益萎缩。(48)[德]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李荣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6页。“人再也不能从一种能够为世界的统一意义提供依据的‘元话语’,如宗教信仰、政治理想或阶级意识中获得生活的目标、价值和意义。”(49)[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325页。个体化社会实践的现实化,是整个生活世界的“支离破碎”,是相对主义泛滥所导致的生存的荒诞感、无力感和无意义感。意味着现代性社会因文化与价值整合力的下降,找不到一种足以将孤立、分散的原子化个体连接起来的共同纽带。个体化社会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规范,在有效调整和规制个体与社会的权利边界,使得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但是,现实的情形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因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性分裂。整个社会和个体生存的“合理性”诉求成为一个难题。于是“眼前的一切,似乎与那些所谓的长远目标、一生的规划、持久的义务、永久的盟友、不变的认同等都已相去甚远,以至于一个人无法与人合伙筹划未来。家庭关系也是如此,在爱河交汇的时候,相互聚集在一起无非是为了各有所图,往往始于美丽的承诺而终于可怕的伤害,今天的亲密结合很有可能增添了明日的怨恨。”(50)[英]保罗·霍普:《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沈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现代个体追求不受限制的无限的自由、权利的结果,终至陷入可怕的极端个人主义,只强调权利优先,忽视或者放弃了对于他者和社会的责任。用桑内特的话说,这样的社会是“公共人已死,公共精神已凋零”,“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来说,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构成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之间,但对他们视若无睹;他触碰这些人,但对他们毫无感觉;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他的脑海里还有家庭的观念,也肯定已经不再有社会的观念。”(51)[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弱》,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扉页。
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实践的知识论智慧,一种较为合理的理解和界定毋宁是:特定时代、特定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本应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基于改变不合理的生存与生活现实、现状的历程中,努力谋求一种先进、合理的理念、主张和特定现实之间的一致与契合。此处所谓契合,最重要的涵义和指称在于,它对于人性的恶有约制和范导,对于制度的优良品质有增益,对于人类的生存境界和生活品质有引导和提升。历史上和现实中,理念契合现实其实是一件更复杂、更艰难的事情。不仅各种理念自身相互冲突和绞缠,达成一致和共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而且事实上由理念所建构的“现实”本身以及理念和现实之间相互契合的形式,更是一种充满非确定性的变数。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实践要求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历史使命和核心问题在于:在一个自由主义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我们需要站在人类文明新转型的历史转折点上审时度势,理智地明辨从根本上影响、左右当今以及未来一个长远历史时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之所在,明确人类前进的新的目标、方向等。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全球社会、国际知识界的认知、判断、理解其实从未达成实质性一致。一些天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家们坐在书斋里,提出了许多有关天下大事、文明大势等的带有前瞻性意味的“真知灼见”,但这些理念和主张也仅仅存在和传布于极其有限的学术圈内。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依然故我,根本不太理会学者们的理论、设想和建议。理论和现实之间,永远需要一种充分、自如的张力空间。但常见的情形是,某一种新的现实还没有发育成熟,尚处在萌芽或生成过程之中,另一种超前性的理念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其进行粉饰性的过度诠释了。其结果,是新概念、话语不断被制造,但是究竟哪一种概念和主张更贴近现实的真实,哪一种思想主张实质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人类文明的范式变革提供启示性的智慧并构成新智慧的有机元素,其实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