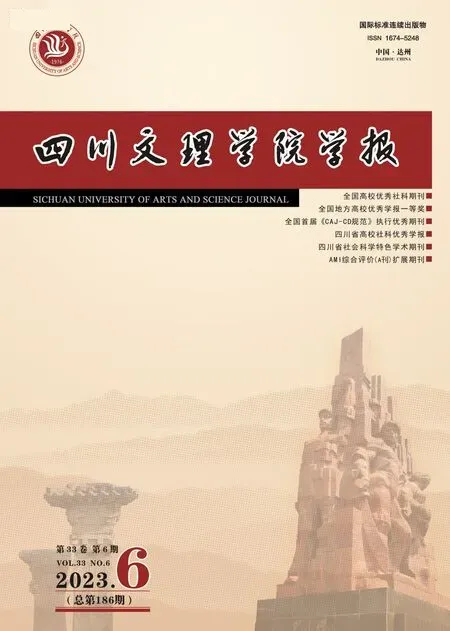从汉语史的建构体系说到宗廷虎的汉语修辞史研究
2023-02-24冯广艺
冯广艺,李 津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88)
进入21 世纪以来,汉语修辞史研究首屈一指的代表作是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1]这部著作从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演变史、篇章结构修辞史等五个方面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了汉语修辞的发展演变史,填补了在汉语史研究中不见修辞史的空白,具有极大的学术理论意义和学科应用价值,曾荣获教育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宗廷虎先生是这部著作的策划者、第一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参著者除陈光磊教授、李金苓教授外,均为宗先生的学生,也可以说这部著作体现了宗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科理念。本文讨论现行几本汉语史著作建构体系的情况,探讨汉语史著作中涉及修辞的相关内容,论述宗廷虎先生研究修辞史的理论基础、学术创新及其对完善汉语史学科建构的贡献。
一
汉语修辞史是汉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2]13应该从哪些方面认识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从几部汉语史权威著作看,都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大的方面着手的,但是对这三个方面的具体论述却是有很大差别的。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点:
第一,篇幅安排不同。以王力《汉语史稿》、向熹《简明汉语史》[3]5和张世禄《汉语史讲义》[4]为例。《汉语史稿》:全书约53 万字,语音约18 万字,占总字数的30.3%,词汇约11 万字,占20.2%,语法约24 万字,占49.5%;《简明汉语史》:全书约160 万字,语音约34 万字,占总字数的20.1%,词汇约44 万字,占27.5%,语法约82万字,占53.6%;《汉语史讲义》:全书约70 万字,语音约24 万字,占总字数的34%,词汇约38 万字,占54%,语法约8 万字,占12%。可以看到,王著语法所占篇幅大,语音次之,词汇所占篇幅小。向著语法所占篇幅大,词汇次之,语音所占篇幅小。张著词汇所占篇幅大,语音次之,语法所占篇幅小。三部著作中语音、词汇、语法的篇幅大小不同,详略不一,表明它们研究汉语史的重点和倾向有差别,也反映出建构汉语史的主观性、多样性和灵活性。
第二,内容叙述不同。王力《汉语史稿》“语音的发展”部分,论述语音、语法、词汇的关系,中古、上古的语音系统,由中古到现代的语音发展(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语法的发展”分“历史形态学”和“历史句法学”两个部分,“历史形态学”论述名词、单位词(量词)、数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的发展,“历史句法学”论述构词法、系词、词序、词在句中的临时职务、名词的关系位、句子的仂语化、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递系式的产生和发展,语气词的发展、省略法的演变、五四以后的新兴句法和句法的严密化等。向熹《简明汉语史》上编“汉语语音史”论述上古语音系统(声母系统、韵部系统、声调系统),中古语音系统、上古到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近代语音系统、中古到近代汉语声母系统的发展、阴声韵的发展、阳声韵的发展、入声韵的发展、声调系统的发展以及现代汉语标准音的形成等。中编“汉语词汇史”分三个部分论述:“上古汉语词汇的发展”论述从甲骨文看商代词汇、上古汉语单音词、复音词的发展、上古汉语词义的发展、同义词、成语和谚语的发展等。“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论述中古汉语单音词、复音词、词义的发展,外族文化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同义词的发展、成语和谚语的发展。“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论述近代新词的产生和蒙语、满语对汉语词汇的渗透、复音词和词义的发展、近代西方文化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同义词、成语和谚语的发展、五四以后汉语词汇的发展等。下编“汉语语法史”的“上古汉语语法的发展”部分主要论述从甲骨文看商代语法、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詞、量词的发展,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的发展,句法的发展。“中古汉语语法的发展”亦从这几个方面论述。“近代汉语语法的发展”除了从以上几个方面继续论述之外,还论述了五四以后汉语语法的发展等。张世禄《汉语史讲义》语音篇“上古汉语语音”部分除概述外,主要论述上古音的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问题。“中古汉语语音”主要论述中古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发展。“近代汉语语音”主要介绍《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韵母、声调以及从《中原音韵》到北京音系、现代汉语方言概况等。语法篇从词法和句法的角度展开论述,词法讲上古、中古、近代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及其发展。句法从词组、句子成分和句子结构、复句三个层面阐述,揭示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如“中古汉语语法”部分“句子成分和句子结构”中,不排列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定语、补语,主要讨论宾语、状语和合成谓语的产生和发展。“近代汉语语法”部分“句子成分和句子结构”中,主要论述把字句的普遍适用、定语的复杂化、状语的复杂化、新兴的成分共用法、新的插说法等。词汇篇分四编论述。“上古汉语词汇”主要讲先秦、秦汉时期词汇的时代特征、基本词汇、词义变化和词的结构、熟语、方言词、外来词、阶级同行语等。“中古汉语词汇”分别讲中古词汇的时代特征、外来词的大量输入、基本词汇的继承和发展、口语词汇的发展、词义的变化、熟语的继承和发展、词的结构等。“近代汉语词汇”分别讲这一时期词汇的时代特征、北方话词汇的发展、外来词的发展、词的构成、词的变化、熟语的引用与继承、基本词汇和阶级同行语等。第四编“汉语词汇发展简史”谈上古词汇的发展、中古词汇的发展、近代词汇的发展,内容上与前三编有重复。总的看来,三部汉语史著作,在内容的叙述上各有特色,大不相同。
第三,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王力《汉语史稿》在谈到“汉语史的研究方法”时提出了四个原则,即“注意语言发展的历史过程”“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重视语言各方面的联系”“辨认语言发展的方向”,主要论述了历史比较法的运用。[2]564向熹《简明汉语史》谈到了汉语史研究中的多种方法。如“归纳。就是从许多语言事实中概括出一般的原理。”“比较。就是比较某种语言现象,从而得出一定的结论。”“统计。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搜集、整理、计算,求得具体的数据,在定性的基础上进行定量的分析。”“探源。就是探求事物得名的理据或探明某种语言事实的起源及其演变,以便了解它的发展线索和规律。”“转换。......就是通过句型的变换来解释某一语言现象,包括同时代不同句型的转换、古今句型的转换以及可转换与不可转换的比较等。”“推演。就是利用一般存在的语言事实,推论出某种语言现象可能存在。”“系联。......主要用于声、云系统的研究。”[3]9张世禄《汉语史讲义》指出:“在研究汉语史中,必须运用那种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历史比较法。”注意“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共同语与方言的比较”“汉语与其他民族语的比较”等等。[4]913三部著作都讲到了“历史比较法”(具体含义不完全一样),这是共同点。向著论述的方法更多,其中“定性定量分析法”“转换分析法”等是较新的研究方法,也是另两部著作没有明确提出的研究方法,这可能跟这部著作出版的年代以及汉语史研究的发展背景等有关。
二
在汉语中,修辞和语音、词汇、语法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史的研究不可避免修辞方面的内容。在汉语史体系的建构中,三部著作或多或少涉及修辞方面的内容,也可以说,汉语史中也研究了修辞史的内容。如关于“成语和典故”,王力《汉语史稿》中说:“成语的作用之一是加强语言的稳固性,因此成语应该是一字不改的甚至字的次序也不能稍有更动。举例来说’兼容并包‘不能说成‘兼蓄并涵’之类,甚至不能说成‘兼包并容、并容兼包、并包兼容、兼并包容等。”[2]564“典故是把一段古代传说或历史故事压缩成为一个句子或词组,例如‘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7]564这里,从“作用”和“运用”的角度论述问题,即是典型的研究修辞的方式。无独有偶,向熹《简明汉语史》也用这种方法研究语言事实,如在论述“近代汉语成语和谚语的发展”时引用《红楼梦》第十六回的例子,指出:“‘指桑骂槐’比喻表面上骂这个人,实际上骂那个人,‘坐山观虎斗’比喻对双方的斗争采取旁观态度,等到两败俱伤,再从中渔利,......”[3]739这里,对成语和谚语的解读紧扣修辞(比喻),方便、实用。又如,该书从“内容上的发展”和“结构上的发展”两个方面论述成语的发展,“内容上的发展”从“描写人的外貌神态的”“描写人的举止行为的”“描写人的思想情绪的”“描写人言语谈吐的”“表扬人的优点的”“斥责人的恶行的”等六点论述,显然,这是从修辞功能上对成语的解释。而“结构上的发展”谈到“联合式成语特别丰富”主要是从修辞上进行分析的,因为联合式成语与音节对称、音韵和谐、对仗对比、反义映衬等有内在联系。张世禄《汉语史讲义》也是如此。如在谈到新成语的创造时,认为中古时期成语的创造“一是把历史故事的主要内容概括而成带有比喻色彩的成语”,如“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等,二是“把寓言概括而成为成语”,三是“从文人作品里选择精炼新鲜的字句充当成语或词组成成语。”[4]913这些都跟修辞有关。一方面,创造成语既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某一时期的修辞现象,是汉语修辞史研究的内容。另一方面,汉语词汇史中谈到的成语、谚语等产生和发展往往与修辞密切相关,从修辞史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成语、谚语等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途径。
对一些具体的词汇、语法现象,三部著作也常常从修辞、语用的角度阐释。如关于“省略法”,王力《汉语史稿》指出:“在先秦对话里,‘曰’字的主语往往承前而被省去,......省略是语言所必有的事;只要不妨碍了解,省略完全是可能。”[2]565我们理解所谓“不妨碍了解”就是一种修辞标准,也就是说,“省略”与否,是又修辞的需要而决定的。向熹《简明汉语史》在谈到“新的词序”时指出:“五四以后,形容词做定语、副词做状语,为了修辞的需要,有时也都可以位于中心语后面,通常用逗号隔开。”[3]817关于“新兴的成分共用法”,张世禄《汉语史讲义》认为:“成分共用是语言中一种经济的表达法;能够以少量的词句严密地表达较为复杂的意思,使得语言既精密又简练。”[4]428-429总之,这几部著作虽以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建构汉语史体系,但在具体语言事实的论述中,往往涉及修辞,也可以说,涉及修辞史的内容。
三
从跟汉语史密切相关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教材看,无一例外地都按照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建构教材体系。古代汉语方面,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四册)在“凡例”中指出:“通论大致包含六方面的知识”,即关于字典及古书注释的知识、关于词汇方面的知识、关于语法方面的知识、关于音韵方面的知识、关于修辞方面的知识、关于文体方面的知识。[5]9该书“通论”第28 讲“古汉语修辞”[5]1295讲了稽古、引经、代称、倒置、隐喻、迂迴、委婉、夸饰等八个方面的修辞内容,虽然篇幅不大,但至少表明编者重视古代汉语中的修辞问题。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三册)在下册中论述了古代汉语的九种修辞方式,即引用、譬喻、代称、互文、并提、夸饰、倒置、委婉、省略。[6]同样注意到了古代汉语中的修辞现象。现代汉语方面,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第五章修辞,分六节讲“修辞概述、词语的运用、词语的配合、句子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语体和风格”[7],不限于修辞方式,内容丰富多样。邢福义主编《现代汉语》第五章现代汉语修辞,分五节讲“概说、词语的选择、句式的选择、修辞方式、语体”[8],和胡裕树本有异曲同工之处。既然跟汉语史密切相关的《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无一例外地将修辞都纳入教材系统,且在《现代汉语》教材中还将修辞和语音、词汇、语法等作为平行内容安排,为什么汉语史的体系建构不能这样处理呢?
我们高兴地看到,刁晏斌的《现代汉语史》是一本在“史”的体系建构上富有创新特色的著作。该书既继承了汉语史体系建构紧扣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的传统,又注意增添体现时代性、发展性的研究内容,加入了修辞史的内容。该书第十一章“修辞”分五节分别讨论修辞与词义的发展、修辞造词、辞格的发展变化、新辞格的产生、现代汉语修辞发展的阶段性考察等问题[9],为汉语史包括汉语断代史的研究体系建构提供了参考依据。
四
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陈望道先生很注意从修辞史的角度观察修辞现象,他的修辞学著作中也融进了他的修辞史研究思想。如:陈望道先生认为:“修辞现象常有上落”。以辞格为例。陈先生说:辞格方面,也常有上落,有的是自然演进,有的是有意改动。像藏词由并用歇后藏头渐渐演进为专用歇后,又从凭借《诗经》《书经》等书上成语渐次演进为直用口头上的成语,又像复叠,从“灼灼”“依依”渐次演进为“随随便便”“不不少少”等叠字,都是不声不响地在那里进展。都可以看作自然演进。这种自然演进,在发动的个人想必也是有意的,不过它既不曾出名,我们也就难以考查它的经历罢了。只有几种积弊极重,改革也颇费力的,我们还能知道那是有意的改革。例如对偶。对偶本来不必排斥,假如事意有自然成对的,自然也可以用成对的语言去表达它。又如引用,引用本来也不必排斥,假如前人的成事成语真有足以补助或代替我们自己的说话的,引用也是不妨,甚至还是有益,但过去往往借用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来代话,又往往借用不全切或全不切的故事陈言来解话,有时晦涩费解,简直等于做谜猜谜。而刻削不自然的体态也往往教人看了生厌。……平常的用典虽然不至可笑如此,但使人感到不自然处,往往也和听彭书袋文不相上下。所以不久以前,也曾有过度激烈的反对运动。像这些都是有意的。有意的运动,自然效力更大,可以把平常看作当然的现象的缺点提到眼睛前头来,教人触目惊心。但这种运动大抵只是病象极重极显的时候才会发生,其余大都是不声不响地在那里进展改动。而那进展改动,往往也是竭力利用语言文字的各种可能性来应付各种不同的情境,有时反比有些纯凭主观、不顾实际的鼓吹还周到得多。如文法上语词的多音节化过去未见有谁提倡,早已逐渐加多,把“马”加上“儿”,叫做“马儿”,把“鸭”加上“子”,叫做“鸭子”,这是为的声音加多更容易听得清楚的缘故。而修辞上的节短,虽然曾经有人笼统排斥,却也仍在逐渐加多,例如把“五月四日”节做“五四”,把“左翼作家联盟”节做“左联”。这又是为了大家熟悉,无须繁说详举的缘故。......就像错综,是反排偶的最有效的手法,但在几次反排偶的运动中,都不曾有谁提挈它,把它看做可同对偶排比比并的辞格。而实例却早已存在。我们尚不注意实例,必致遗落了这种即可注意的修辞现象。[10]178
望道先生认为辞格的“上落”有“自然的演进”和“有意改动”两种情况,这对我们研究修辞史很有启发。
望道先生还特别指出:修辞现象也常有生灭。辞格的项目,也不是一定不易。现在有的或要消灭了,现在未有的也许要产生出来。就现有的例来说,如出奇的造作的回文便已经要消灭了,而藏词却是从汉代以后才产生的,如今也已消歇了一半,不过发达了一半……[10]180
他指出的这种修辞现象也是我们在研究修辞史的时候要时刻注意的。
宗廷虎先生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毕业于复旦大学,早年在陈望道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语法修辞研究室工作,专治修辞学至今。在宗先生的学术生涯里,研究修辞学史和修辞史占有重要的学术分量,可以说,宗先生的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研究成果,都是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的扛鼎之作。从20 世纪70 年代后期开始至今,宗先生的主要学术关注点是修辞学史和修辞史,可大致分两个阶段,以20 世纪和21 世纪的交界线为转折点,即1979-1999 年为前一阶段,宗先生重点研究修辞学史。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的“后记”中,宗先生说:“我是从1979 年开始探究修辞学史的。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可说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修辞学史领域却是一片荒芜,亟待开垦。”[11]这一指导思想促成宗先生取得一系列修辞学史研究成果,除了他个人的专著之外,他还和李金苓先生合著了《汉语修辞学史纲》、和袁晖先生共同主编了《汉语修辞学史》、和郑子瑜先生一起主编了《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这些著作同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周振甫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等,形成了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繁荣景象。在这片繁荣的景象中,宗先生的修辞学史研究璀璨夺目,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后一阶段:21 世纪开始至今,宗先生的修辞学研究重点转向了修辞史。
宗廷虎先生始终认为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理应双管齐下,并行不悖。随着宗先生的学术研究重心转移,修辞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宗廷虎、李金苓合著《修辞史和修辞学史阐释》一书充分体现出这一学术思想。该书分上下两编,分别阐述修辞史和修辞学史两个方面的理论。其中“修辞史阐释”又分五章,第一章是理论探索,其余四章分别论述“诗歌体中连珠格的历史演变”“顶真格连环体的历史演变”“药名嵌字格的历史演变”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引用辞格”等。可以看到,这部著作的修辞史内容,是研究具体修辞现象(辞格)的发展演变,既注重理论阐发,又联系修辞实例,深入、扎实。在修辞史理论探索上,该书继承了陈望道先生的学说,进一步澄清了修辞、修辞现象、修辞史几个概念,阐述了修辞史及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认为“修辞现象既然是修辞史的基本资料,修辞现象的范围自然也就成了修辞史研究的范围”[12]6汉语修辞史除了研究辞格发展史外,还应研究汉语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和篇章修辞史等内容。该书论证了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的密切关系,[12]7特别强调了研究修辞史的时代需求和学术需求,指出研究修辞史是“提高全民族语音修养和文化素质的需要,是中国语言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也是修辞学学科建设和新拓展的需要”。[12]8-12
应该看到,对中国修辞史的认识,学术界有一个较长的渐进的过程,在20 世纪出版的修辞学史的著作较多,可谓蔚为大观。修辞史著作直到21 世纪初,宗廷虎、陈光磊主编的《中国修辞史》(三卷本)才得以问世,显得修辞学史和修辞史著作很不对称。除了三卷本的皇皇大著《中国修辞史》之外,21 世纪以来,还有两本具有“修辞史”性质的著作值得一提。一是宗廷虎、李金苓先生的《中国集句史》,[13]这是一部研究“集句”发展史的著作,“集句”属于引用辞格的一个小类,是一种富有鲜明汉语特色的修辞现象,作者从“史”的角度勾勒了集句的发展脉络,认为春秋至魏晋是集句萌芽期,宋代是集句建立、发展期,金元代是集句的继承期,明代是集句的进一步发展期,清代是集句的繁荣期,近现代是集句在缓行中局部取得进展的时期,该书论述了集句作品源远流长、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动因,剖析了集句的能动创新特性及其抒情言志功能、记述历史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二是于广元的《汉语修辞格发展史》,[14]这是一部从修辞史的角度研究辞格发展史的专著,该著“绪论”中特别强调了“汉语修辞史研究”问题,认为不外乎传统语言学的影响、部分学者的一些观念和研究成果的基础等,于著选取修辞格的发展演变为研究的切入点,十分合理、恰切。“辞格是在言语活动中长期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符合特定类聚系统的模式”[15],在修辞史的研究中,辞格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它的结构特征、功能特征等十分鲜明,有些辞格的历史悠久,发展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值得深入探讨。于著研究了比喻、比拟、借代、示现、双关、对偶、夸张、引用、回环等常见辞格的发展及其动因和机制,是汉语修辞史的研究中的成功之作。真正从宏观上把控中国修辞学的发展走向,高屋建瓴地研究中国修辞学的学术课题,解决修辞学史和修辞史“二史”之间的“不平衡”问题、促使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并行不悖、共同发展繁荣的是宗廷虎先生,他前后两个阶段的“学术重心转移”恰好验证了这一点。
宗廷虎先生的汉语修辞史研究和修辞学史研究都代表了当代修辞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在修辞学领域真正做到了“二史”研究均衡发展、不断创新,由于修辞和语音、词汇、语法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修辞史理应和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一样,成为汉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宗廷虎先生为领头雁的一批学者汉语修辞史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为汉语修辞史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创造了较为坚实的学术基础,由此可见,宗廷虎先生的汉语修辞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极高学科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