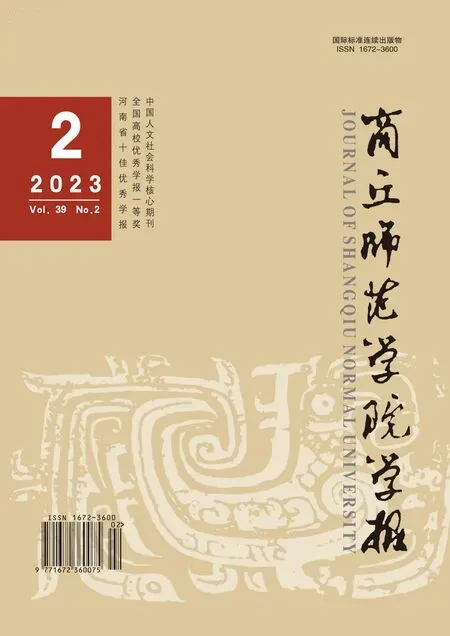《老子》作为一种共生哲学
——为共生而承认无知,为共生而承担柔软
2023-02-22赖锡三
赖 锡 三
(台湾中山大学 中文系,台湾 高雄)
缘起
老庄思想的背景,正是周文疲弊、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战乱时代。时值天下大一统政治秩序崩解的战乱之世,也是文化要求大规模重建的转型阶段。当周代统一天下的官方正典话语逐渐遭受挑战,终而土崩瓦解之际,政治、军事、文化等总体处境,都走向了离中心化、解辖域化的“大乱”状态。用当时的概念来说,“天下有道”堕入了“天下无道”,于是“天下大乱”。对于这种战乱苦难的惨状,《老子》曾述及:“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四十六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七十五章)。从这些只言片语的间接描述中,可以约略观察《老子》思想的时代背景:苛政猛虎般的横征暴敛(其上食税之多),饥荒连连(民之饥),生不如死(民不畏死),战争惨烈,连怀孕的母马都离不开战场(戎马生于郊)。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想见那是政治狂暴和兵凶战危的苦难时代。人活在“天下无道”的年代里,几乎无路可走,更无所逃于兵凶战危的集体动员之逼迫情况。甚至“不得已而用兵”之道,也吊诡地出现在《老子》这本“不争”“处卑”“慈柔”的无为之书中。可以说,《老子》不得已而谈兵的唯一关怀,只在复还“天下有道”,让百姓赶快回到有路可走的生活之道。《老子》从不歌颂战争英雄,主张以丧事面对胜利。出现在战国年代的《老子》,虽不能全逃于战乱兵事,关心所在却完全不在战事技术,而在于深思如何回归“天下有道”的共生之路。且在《老子》看来,“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祸咎秧苗虽可追溯多端,然而人心的“欲得”而“不知足”,自我“刚强”而争先恐后,欲望的贪求扩张与不知节制,恐怕已让冲突战端,在人性深处有了秧苗种子,不可不慎微。本文尝试拣择、疏解《老子》若干章句,阐发其以柔化刚、恬淡知足、无知无为的思想内涵,希望对人类难以止息的对立冲突,提供些许思考“共生”(co-existence,co-living,co-becoming)之道的哲思资粮(1)“共生”一概念,目前可采用co-existence,co-living,co-becoming这三种英译。而我根据“共生哲学”的前行者,日本东京大学中岛隆博的建议,根据不同脉络而有时用co-living,有时用co-becoming来呈现,前者为突显“共同生活”,后者为突显“生的动态性”。而根据道家“化”的哲学精神,我们尤其想强调co-becoming的变化历程性、万物之间的有机性、超人类中心性,甚至共同转化的创造性。有关co-becoming的英译与共生的汉语哲学潜力,可参见赖锡三、莫加南对中岛隆博教授的访问对谈《共生哲学对当前世界、两岸处境的迫切性——与中岛隆博教授的对谈》(《思想》2022年5月,第45期)。。
一、释“道”:“非常道”可解开意识形态斗争,提供思想共生的价值多元道路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1]1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庄子·齐物论》)[2]83
《老子》首章首句便表示出,与时俱变、化而不固的活动历程之“道”,虽可暂时性用某方式加以实践(例如行走出某条道路出来),但这种特定化的运用与呈现(“可道”),却不宜被恒久固定下来(“非常道”)。同理,与时俱变、化而不固的脉络运用之“名”,虽可暂时用来描述事物,但这种描述与分类的命名活动(“可名”),却不宜被偏执地一定永定(“非常名”)。老庄之“道”,既不像古希腊存有论那种不落入变化的形上实体(metaphysical substance),也不必是神秘不可名状的消言境界(mystical silence)。《老子》之“道”,最宜理解为不离变化历程、不离物化脉络的千变万化、并行不悖之道。朱谦之对此有一精准把握:
盖“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实则《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也。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也。自解《老》者偏于一面,以“常”为不变不易之谓,可道可名则有变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则无变无易(林希逸)……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故以此处世,则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四十九章)。以此应物,则“建之以常无有”(《庄子·天下篇》),言能常无、常有,不主故常也。不主故常,故曰非常……常即非常也……《庄子》所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若不可变、不可易,则安有所谓常者?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3]4
由上可见,“道”就在描述与时迁移、应物随化的活动历程,此活动历程自然在不同活动情境的差异脉络下,流行演绎出杂然万象。可以说,具体的变化之道属于“非同一性”的复数化运动,自然也要呈现“夫物芸芸”的万象多元性。“道”并非外于物而高高在上的大写之道、单一之道,“道”乃表现在千差万别又并行不悖的物化之道中。用道路的譬喻来说,《庄子·齐物论》所谓“道,行之而成”[2]69,既显示“道”是在“行”的活动中才不断践行出来,也暗示“道”具有种种践行可能性及道路的脉络性。例如,当人们行走在大地上时,会因应不同情况而摸索出不同道路途径出来,然而《老》《庄》提醒我们,这些暂时施行出来的道路途径(“可道”)和指示路标(“可名”),虽有其功能性、合理性的运用脉络,但不宜将特定脉络的“可道”与“可行”给予胶定下来,更不宜将它们封闭、执定成为“常道”“常名”。事实上,“道”和“名”具有转化变通和无穷运用的可能性,所以《老子》首章首句就提醒人们,在“可道”“可名”的权用过程中,务必透过“非”的除病、去执作用,来预防自我掉入“常道”“常名”的“固而不化”,如此才能善保“化则无常”的最大变通性(2)如《大宗师》篇:“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华正书局1999年版,第285页)。
从《老子》的立场来看,如有所谓的“道家”,则“道家”是最不固执于自家道路(非常道),最不胶定于自家之言(非常名)。没有一条固定、直线、不变化的恒常可行道路,才是道家所主张的“非常道”的“不道之道”。对于道家,“道,行之而成”,而行者在“行之”的过程中,走在永未完成的实验性道路上。如《老子》提醒“善行无辙迹”[1]70,善行者尽量不让过去行走的暂时路迹,一定永定地成为固定自己与后人的常道。又如《庄子·人间世》提醒:“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2]150因为“有”翼飞者,容易留下被模仿的恒定模式;而“无”翼飞者,则是透过“无”的去执作用,而无住于过往陈迹并敞开新道路。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可运用《庄子·齐物论》来相应诠解:“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老子》将“道”和“名”并举,《庄子》也将“道”和“言”并举。两者都忧心于“道”和“名”(道和言),在还没有“封”与“常”的未恒定状态,逐渐经由“可道”“可名”的“为是”过程中,不慎落入“(道)有封”“(言)有常”的僵硬畛域框架中,而逐渐遗忘了它的无穷可能性。顺此“为是而有畛也”,原本“未封之道”被封闭为“常道”,原本“未常之言”被固定为“常名”。于是在建构出(特定之“为”)一种特定道路或观点(特定之“是”)的同时,也把自己聚焦在特殊性的符应系统中,而遗忘了“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的并行不悖、多元共生的无穷可能性。
“道”,其实是先秦诸子普遍使用的概念,尤其在“天下大乱”的政治、文化危机背景下,先秦诸子都有救治天下、回复秩序的淑世关怀,如何使“天下无道”回复“天下有道”进而“道行天下”,便成为诸子百家的共同关怀与道德使命。如孔子有“就有道而正焉”的期许,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感叹(《论语·公冶长》)[4]86,孟子更有拒“邪说”、立“道统”的迫切需求(3)《孟子》虽没有统一思想与言论的主张,但它对所谓“邪说”的拒斥性,却极为强烈:“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朱熹《四书集注》,世界书局2014年版,第296页),而墨家也希望齐平差异、“一同天下”之道(4)《墨子》因为担忧“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的思想差异,将带来标准不一、规范秩序的紊乱,进而主张“一同天下之义”(或“同一天下之义”)。墨子为平齐差异观点,走向同一天下言论的尚同观点,可参见《墨子·尚同》篇(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98页)。。换言之,用“常道”来导正天下,用“一道”来恢复正途,用“正道”来建立正名,几乎是各家诸子自我许诺的共同心声。而先秦流派影响最大者就是《齐物论》所说“儒墨是非”的儒家之道与墨家之道。简言之,儒家认为自己的仁义之道、礼乐之道、正名之道等,才是救治天下的“常道”统绪,而墨家则认为自己的兼爱之道、非乐之道、节葬之道、非攻之道等,才是救治天下的“常道”统绪。或者也可以说,儒家会认为自家提出的名言主张,在百家言论中最具价值优位性;而墨家则会认为自家提出的名言主张,才是百家言论中最具殊胜性价值。
可以说,《齐物论》所反省的“儒墨是非”,不只是一般立场差异的是非观点,而是当两种“可道”“可名”的差异性观点,几乎被上升到两种“真理之道”、两种“救世之道”,甚至是两种“终极之道”、两种“唯一之道”的思想战争时,也就将两种“可道”与“可名”的双方差异,提升为两种“常道”与“常名”的唯一之战。如类比于武力战争,“儒墨是非”之争几乎可视为思想战争,这也是为何《孟子》不得不清除邪说而建立道统,因为建立思想道统可以清除思想异端,而清除思想异端才能落实道统思想,两者是“既庄严又焦虑”的二而一关系。如果用“共生哲学”的概念来说,不管是墨家的“尚同”主张,或者儒家的“道统”建立,两种“常道化”的“深度歧见”(5)“深度歧见”是邓育仁用来诊断当前民主政治的价值冲突难题的核心概念,笔者将之运用到解读先秦诸子的思想冲突,尤其《齐物论》所探讨的“儒墨是非”。例如《庄子·天下》篇谈及诸子思想各自停在“一察自好”“以自为方”的一曲状态,虽能各自提出治理时代之见解(一曲之见),也各有其特定意义(各有所明),但由于“成心自师”而未能自我反思,以容纳差异性观点并进行开放性交流对话(不能相通),在《庄子》看来,不是掉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偏蔽,就是掉入“知也者争之器”的“儒墨是非”之理论竞争(而有堕化为“意识型态之争”的危险)。换言之,“皆有所长,各有所用”的“一曲之士”,由于看事情过于自我中心(故不能该),又对自我知见以偏盖全(故不能遍),甚至把自己的“是”当成“全是”,把自己的“可道”当成“常道”,于是让立场差异的不同观看角度,堕化成为“自是非他”的深度歧见。有关“深度歧见”,参见邓育仁《公民哲学》(台大哲学出版中心2022年版)。参见拙文《公民道家与深度歧见——以〈庄子〉的〈齐物论〉和〈人间世〉为思考》,即将收录在《公民道家与公民哲学》一书。,几乎难以共在共生,因为两者皆坚持拥有超越他人的“大写之道”在自家手上,除非他家尚同在我墨家的“一同之道”之下,除非他家统绪在我儒家的“大写道统”之下,否则吾家之“常道”与“正名”就难以实现,那么天下也就难有“大行其道”(大行我道)的可能了。因此,墨家不得不发展出墨辩的种种思想利器,而孟子也不得不好辩以求破淫辞、破诐辞,由此“儒墨是非”不得不进行理论竞争乃至思想斗争,为求“大是大非”而“道行天下”,乃不得不进行思想战斗,以求思想与真理的大一统。
从上述背景,老庄对“道”与“名”(或者“道”与“言”)的反省,可以提供一个反讽的画面,因为老庄以“道家”为名,刚好因为道家走出“常道”、拥有“常名”的自我标榜与宣示,老庄谦卑柔软地知道自己从未拥有任何唯一的真理之道,也从未拥有绝对超然的真理之言,甚至认为“道之为道”“名之为名(言之为言)”,其本质就具有脉络性、方便性的“变化不定”特质,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唯一、恒常之道,可被占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唯一、恒常之名,可被据有。道家之所以为道家,反而在于它提醒我们:“未始有封”的“非常道”,“未始有常”的“非常名”的无限大空间,藉由“非常”“无常”的解蔽而开放心胸和想象,以容纳各种道路开辟的实验性尝试,容纳各种言论观点的尝试性提出,也就是说道家的“道”与“言”,永远保留容许歧路、容纳异议的“余地”。也是这种为另类道路、为另类思想,永保余地的自我虚位化态度,让道家哲学打开了最大的“共生”余地。
二、释“帝”:“象帝之先”的解实体化之道,可提供宗教和解的共生之道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1]10
对于“道”的理解,第四章通过“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这三项特性来描述。“冲”兮、“渊”兮、“湛”兮,皆具水意象的流变特性,据此可以推断“道”无法被实体对象化。耐人寻思的是,第四章以“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来总结“道”的描述,这又暗示我们无法再为“道”的变化流行去寻找外在性、位格性的实体来作为生因。综合上述两部分,大约可以这么说,《老子》是通过“冲、渊、湛”,这些暧昧不定修辞,来描述“道”的没有源头、若有若无、无始无终等“前对象化”的特质。“冲”“渊”“湛”,符合《老子》向来爱“以水喻道”的书写风格,不管是江、湖、海等水域系列隐喻,或者扩展到容纳百川的山谷、谿豁等隐喻,它们都具有“道”的隐喻群组之象征潜力。而关键就在于“水”的非实体、变化性、混融性、可静可动、就下性、润泽性,使得水意象群成为《老子》用来形容“道”与“德”的极佳象征(6)关于《老子》的“水”之道与“水”之德之多重象征意味,可参见拙文《从〈老子〉的道体隐喻到〈庄子〉的体道叙事》,收入《当代新道家》(五南出版2021年版,第287—336页)。。
为何用“冲”(虚也、无也、空也(7)朱谦之:“‘冲’,傅奕本作‘盅’,‘盅’即‘冲’之古文。《说文·皿部》:‘盅,器虚也。《老子》曰:“道盅而用之。”’……盖器中之虚曰盅,盅则容物,故《庄子·应帝王》篇曰:‘太盅莫胜。’”(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页)),来作为描述道的核心特质?这是为了强调,最好使用否定性表达来暗示“道”的非决定性(indeterminacy)。因为一旦把“道”设想成实体般的存在,也就会把“道”给对象化成存有物,或特定化为某实体物,就像西方哲学的形上实体或基督宗教的绝对存有者“上帝”。西方形上学设想“万有现象”背后,必须肯定更根本的“本体有”来作为第一生因或绝对实体,以之满足解释生命万象的充足理由。然而从《老子》看来,不管是信仰“吾乃自有永有者”的创造者上帝,或者哲学思辨所设立的第一因实体,它们都属于实体之有,而大不同于《老子》道“冲”的“解实体化”性格。“道冲”暗示“道”是无形相、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将其对象化,更不宜使用诸如“耶和华”(定名、真名)去给予对象化指涉(定形)。用《老子》第一章的概念来说,“耶和华”便是对“常道”化的上帝给予“常名”化。而“冲虚”则暗示出“道”的“无”之面向,以否定性修辞暗示“道”的不可实体对象化。可以说,道的“冲、虚、无”等特性,在表示人们若想要透过认识个体物、实体物的方式来掌握“道”,尤其用对象化的语言去对“道冲”进行“有封”“有常”的命名指涉,其结果便会“名以定形”地把“道”给对象化、固定化,从而遗忘“道”的“冲、虚、无”之未决定性。而“道”的“渊兮”性格,则象征着“道”具有幽玄、深邃、不可穷尽的性格,好像源源不绝的力量如深泉般涌现溢出,成为滋润万有生命的活水深渊,即所谓“渊兮似万物之宗”。但这里的“宗”,不宜依循西方形上学的思维方式,将“道”执着成为存在万象背后的先在性、实体性的本源。就像“冲”不离于“用”,“渊”与“宗”也不能离于“用”,只是“道冲”倾向描述“用”的“不满溢”,而“道渊”则倾向描述“用”的“不穷竭”。但无论“道冲”或“道渊”,都不宜将其中的“道”,执实为流行大用之外、之先的形上实体般的宗本(8)释德清:“道体渊深寂寞,其实能发育万物,而为万物所依归。但生而不有,为而不宰,故曰:似万物之宗。或似,皆不定之辞,老子恐人将言语为实,不肯离言体道,故以此等疑辞以遣其执耳。”释德清《老子道德经憨山注·庄子内篇憨山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56页。对于《老子》之道,不宜使用西方形上实体来理解,参见拙文《后牟宗三时代对〈老子〉形上学诠释的评论与重塑——朝向存有论、美学、神话学、冥契主义的四重道路》,《当代新道家》(五南出版2021年版,第1—90页)。。否则就难以和第四章的总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产生意义融贯的思想呼应。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其中的“不知”,既意味着人对自己“无知”的承认,也意味着找不到或者不宜强索力求;而“吾不知谁之子”则进一步表示无法在“道冲、道渊、道湛”的大用流行以外,再去寻找父母般的源头来作为奠基之因,然后再把大化流行之道当作被生产或被创造出来的结果(之子)。对于“道”的大用流行,人们不但“不知谁之子”,而且它还是“象帝之先”。“象帝之先”(或“帝象之先”)暗示我们:道的变化流行活动,超越了上帝位格或诸神形象那一类运用宗教信仰体系所建构出来的解释模型。因为上帝与诸神通常容易被想象成世界之外之先的神圣实体,再以其作为解释宇宙变化的奠基性源头。例如在创世神话叙事谱系里,第一个故事原型就是用创世神话来解释世界起源,例如泰初大神如何凿破混沌而开天辟地等创世情节。而《老子》不无反讽地说,“道冲、道渊、道湛”之大用流行,乃“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正是对人们将“道”给予位格化、实体化的对象化思维,做出“解-实体化”“解-奠基性”的反省转向。宗教信仰善于把无形力量给予实体位格化、特定焦点化,以作为祈求仪式的投射功能,启动人心的情感渴望和能动性想象。但宗教这种神圣化的药性,本身却也同时隐含着毒性,那就是让“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的“未封之道”“未常之名”,从“未封未常”的冲虚流行,堕化成为“有封有常”的位格性神祇与实体性存有(9)关于《老子》善用“大母神”神话意象,却又不落入神话隐喻的实体化限制,可参见拙文分析。《后牟宗三时代对〈老子〉形上学诠释的评论与重塑——朝向存有论、美学、神话学、冥契主义的四重道路》,《老庄的肉身之道与隐喻之道:神话·变形·冥契·隐喻》,《当代新道家》(五南出版2021年版,第1—90页、第247—286页)。。用《老子》的话说,“象帝”(或“帝象”)的常道化、常名化,也会造成人们的依赖与固执,进而可能产生“帝象”与“帝象”之间的争锋相对。
自有人类以来,冲突不间断,战争未曾歇。冲突与战争仿佛魔咒般,如影相随而挥之不去,在战祸绵绵无绝期的暴力历史中,野蛮与文明难分难解,人类写出来不怎么文明的文明史。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几乎就同时拥有了宗教诸神的庇佑,虽然宗教时常提供苦难世代以抚慰功能,诸神也时常扮演垂怜庇佑的神圣角色。但不必讳言,宗教从未抚平冲突,诸神也从未消弥战争。十分吊诡的是,有时宗教诸神还成为冲突与战争的起因,甚至是启动圣战的发动机,从古代部落与部落间的诸神之战,到现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真神之争,都再三告诉我们上帝与诸神也无法止息战争,“祂”或祂们的神圣性,甚至成为“发动圣战”的最强催化剂。可以说,诸神各为其部落选民而各显神通以庇佑其族群文化,同时打击异族群文化的竞争与冒犯,实乃人类宗教史上神圣暴力的阴影书写之另一实相。而且这种以神之名、以爱之名的神圣暴力,可能也是贯通古代、当今甚至未来的宗教、文明之普世现象(10)难怪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充满洞见又充满争议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出版),分析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将从意识型态转向几大宗教、文明区域的冲突,例如几大宗教文明区域(欧美基督教、中东伊斯兰、中国儒家)的竞争与冲突上。亨廷顿的观点曾引爆众多争论,但从当今国际局势来重新回顾他当年的分析与预料,文明与宗教的竞争与冲突,确实扮演着越来越显明、越强烈的因素。参见辛翠玲《美国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充满争议的经典之作——二十一世纪重读〈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收入萨谬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著,黄裕美译《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联经出版社2020年版)。。
若用老庄的观点来说,人类文明的各种冲突,不管是宗教之间、价值之间,还是主义与主义之间,包括神圣层面和世俗层面的各种冲突,可以透过老庄的“道”来加以“描述”,甚至加以“解构”。简单说,上述各种冲突的极端化都可被描述为“常道”与“常道”的冲突:基督教之道与伊斯兰教之道,儒家之道与墨家之道,民主党之道与共和党之道……当上述各种差异与认同之“道”,被上升为“大写的常道”“唯一的常道”时,那么各种“可道”“可名”的差异性立场,便会同时上升成为“常道”和“常名”的深度歧见与严重冲突。如此一来,双方的“文明冲突”,便可能极端化为“正/邪”之间,“对/错”之间,“正统/异端”之间,“神圣/魔鬼”之间的圣战了。严格讲,这种“唯一”与“唯一”的圣战冲突没有“之间”,因为双方只有争出“唯一”,才能止息这场“不两立”的冲突。于是“战争”甚至“圣战”的发动与讨伐,成为不得不兴的正当性“义战”。纵观人类文明的重大冲突,最初或许只是世俗利益的冲突、立场角度的冲突,但发展到最后,则经常诉诸真理、道德、正义之名,强化自身以神圣性,丑化对方以邪恶性。
用道家的最核心观念来说,人类的冲突乃至最暴力性的战争,都间接或直接涉及“大写之道”(帝象)的冲突。“大写”意味着“唯一”,而“大写之道”与“大写之道”的冲突,便意味着“唯一帝象”与“唯一帝象”的冲突,用老庄的概念来说,也就是“常道”(恒常之道)与“常名”(恒常之名)的永恒之争,或者“正道”与“正道”的唯一之争(11)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宏文《暴力与形上学》的概念来说,“大写存有”涉及形上学还原思维可能挟带的光之暴力、他者暴力。而从德希达看来,决定西方(形上)哲学旧瓶的整体性架构,在于三个核心概念架构:一是同一性的主宰。二是形上学的还原。三是伦理学的次级化(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著,张宁译《书写与差异》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而且极端危险的是,这种“大写对大写”“常道对常道”“正道对正道”“真理对真理”“神圣对神圣”“帝象对帝象”的“善-善”斗争,几乎难以避免将冲突上升到毁灭的圣战层次,也就是说,难以避免将“善-善冲突”转化为“善-恶冲突”,最后堕落为“恶-恶冲突”。也就是说,当两种文明之间不能有“共在共生”的可能性时,那么以战争来消灭邪恶,以获正义实现的终极解决方案,便成了必要甚至唯一选项。
所以对于老庄而言,和平共生与其诉诸宗教的“象帝”(实体化)思维,不如诉诸道家“象帝之先”的(非实体化)思维。原因无他,宗教思维几乎很难逃乎“大写存有”“大写之道”的形上实体思维,亦即宗教的神圣性与超越性设定,很少不把自己纵贯性地拉高到“绝对性高度”(天的高度,神的国度,彼岸的域外维度),以形成我族我文明的“刚性认同”,并由此俯视芸芸众生、芸芸他教、芸芸他义。大写的本体之道或帝象本体,将永远超然于小写现象或芸芸众生,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一统多”的形上思维,除非跟随唯一大写之道的召唤与垂怜,否则将永难获得眷顾垂怜。而这也是宗教思维几乎都会树立“正统”与“异端”、“内道”与“外道”的分界线。界线内属于“常道”而界线外属于“外道”,界线内属于“正道”而界线外属于“魔道”,界线内属于“我选民”而界线外属于“异教徒”,界线内“多吉祥”而界线外“多妖魔”。
上述“正道/邪道”的极端不两立,绝不仅止于宗教范畴与现象,事实上,把“立场和立场”之间“小写之道”的差异,上升成为“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的常道、常名之圣战,充斥在人类所谓文明的各种历史处境中,甚至变形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日常小道之中,也可经常看到为了日常小道而头破血流、惨不忍睹的准战争现象。从《老子》第四章来观察,因为大部分人都停留在“象帝”层次的对象化、实体化思维习惯,缺乏“象帝之先”的非对象化、非实体化的“柔性”思维。如果能对“道冲、道渊、道湛”的“未决定性”,保持“未知”甚至“无知”的开放性,就比较不会把我人我族我教的“一偏知见”和“成心自师”,当成普世性“常道”“常名”般的“神圣帝象”来加以“刚性认同”,甚至不惜为它发动圣战。可以说,“象帝之先”的柔性、敞开认同,能转化“象帝”的刚性、内聚认同,进而缓和文明与宗教的刚强冲突,打开柔软共生的调节机制。
三、释“一”:在关系性宇宙的互联网中,共生共荣共创命运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将恐蹶。(《老子》第三十九章)[1]105—106
“一”,也属于《老子》思想的关键性概念,“一”和“道”也具有概念位阶的家族类似性,可用来补充说明“道”。如《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17显示“道”在演化为“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的气化流行的过程时,“道”和“一”的亲密连续性。而《庄子·天下》篇在描述老聃的学术核心思想时,也涉及:“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2]1093可见“主之以太一”,也被视作老聃思想的核心标示。问题在于“一”该如何理解?它和共生思想有何关联?我们将通过第三十九章的“得一”思维,来加以阐述。
得了“一”,可说是得了“道”,也就是参与分享了“道”(12)《大宗师》底下一连串“得之”(得道)的描述,或可视为《老子》第三十九章“得一”的改写或翻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牺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太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庄子集释》,第246—247页)。正如前文所强调,老庄之道乃“无逃乎物”的“即物之道”“物化之道”,一切万化(包括天、地、人、神、物),可谓浸泡遍润在道化流行之中。因此所谓的“得道”“得一”,也可说是敞开于“道”的遍泛流行中,如《老子》三十四章的“大道汎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衣养万物而不为主”[1]85。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得一”?
“一”象征了整体性、连续性,暗示我们:“分别(个别)”不能独立孤离于“非分别(整体)”的关系互联网。《齐物论》有所谓“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2]66“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79,看似拥有个体性、分殊性的“我”甚至“一指”“一马”,实乃完全浑然中处于天地万物之间。“我”绝非外于“天地万物”,反而只有身处“天地万物之间”,并且与其“并生为一”,也就是存活在万有交织、缘构相生的关系互联网之中,“我”才能“在世存有”地拥有具体性的存活样态与存在内涵。反过来说,天地万有的互联网关系,也会具体而微地显现在任何一指一马之中。“一”既象征着万物关系连动的交换体系,而且也表现出“非均质”“非同一”的“夫物芸芸”。换言之,“一”同时体现出“万物并生”的多元现象。
而《老子》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则告诉我们,没有孤立的天与地,没有孤立的神与谷,也没有孤立的万物与侯王。一切一切的存在样态(如天、地、神、谷、人、万物,等等),只有当它们共在共生于“一”这个浩瀚网络,并发生亲密的分享关系时(所谓“得一”“致一”“抱一”(13)吴澄:“一者冲虚之德。上篇所谓抱一、所谓为一,后章所谓道生一,皆指此而言。庄子谓太一,又但谓之一,此乃自然之道所为,其用则虚而不盈、后而不先、柔而不刚、弱而不强。前章固屡言之,而此章尽发其蕴。得者,谓得此一以为德,以此故能若是,天地神谷四者名异实同。”吴澄《道德真经注(二)》卷3,收入严一萍选辑《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1967年版,第4页)。),才能生发丰沛的存在力量或朗现存在的充盈意义。反之,一旦存在事物自我封闭而孤立于情境,将与关系互联网络产生隔碍或疏离(“离一”或“失一”),就会因为离开活水源头而渐趋荒芜枯竭。如此一来,原来的天之清反转为“恐裂”,地之宁转为“恐废”,神之灵转为“恐歇”,谷之盈转为“恐竭”,万物之生转为“恐灭”,侯王之贞转为“恐蹶”。也就是说,包括天、地、人、神的任何事物,只要离开了“天地并生,万物为一”的这个一大共生网络,那么它的存活状态将难以为继。
用个比喻来说,万有的分殊性存在,就像分布海上岛屿,而岛屿生命万象所以能各畅其生、各尽风采,正因为岛屿底层与大海连通为一,一但岛屿孤立疏离,悬空无根而立,它就必然注定走向“裂、废、歇、竭、灭、蹶”的荒芜命运。正如《老子》三十六章所谓“鱼不可脱于渊”的道理,三十九章的“一”可相通于三十六章的“渊”、二十章的“母”、第八章的“水”,这些带有类似隐喻意涵的概念群组(“一”“渊”“母”“水”等),都共同涉及了变化联动、循环往复的关系性宇宙之隐喻。而一切存在物既不能离开此一大互联网,更因为彼此之间的不断交换,才能促成“并生为一”的共生演化。有关“关联性的宇宙”以及它所蕴含的共生(co-living),乃至共同创造(co-becoming)的丰厚意义,安乐哲(Roger T.Ames)曾给予很好的诠释:
道家的宇宙起源论并不担保某种极端的起始,那种起始与那些描述秩序(Order)凌驾于混沌(Chaos)之上的形而上的宇宙起源论有关……《道德经》中广为渗透的‘母亲’和‘出生’的比喻,不是要诉诸那种有关起始和独立的有效原因的语言,而是要在一种自生性的再生产(Autogenerative reproduction)的不断循环中来描述胎儿的诞生。[5]11—12
《道德经》中所体现的关联性宇宙论的四个预设:一、道家肯定构成我们经验世界的各种事件本身的实在性,认为并不存在‘多’背后的‘一’,且事件与时间不相分离。二、各种事物都是过程性的事件,一方面各有其特性,一方面又内在地彼此相关。每一事物都处在其他事物所构成的不断变化的脉络之中,并在这种动态的脉络中以共同创造的方式成就自身。三、生活是具体的经验场域,同时每一种具体的经验场域又总是具有整个宇宙的全息性。四、世界的创生性转化来自于构成世界的各种事物的回应性参与,在创生转化的不断过程中,事物不是被动的参与者,而是主动的共同创造者。[5]5(14)“一”不是万物背后的形上根源,而是描述万物并生为一的关联性变化历程。安乐哲对《老子》的“道”和“一”解读,具有强烈反西方形上学思维的批判特质。
“得一”也可呼应第二十二章“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抱一”。亦即圣人回应世界、回应事物的方式,在于他能柔软地怀抱着不断变化中的全息性关联宇宙。因为这种深切体认“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的“抱一”态度,最能将自己敞开于天地万物,并善于回应事物的交互作用、彼此连动的有机关系。凡是存在,就必然是全息关系性中的有机存在,没有任何存在可以长期维持自我中心、自我孤立而片面行事。任何一味的自我伸张、自我增强、自我扩大、自我高涨,早晚都要遭逢“裂、废、歇、竭、灭、蹶”的荒芜与破败。而圣人的“得一”“抱一”则要提醒我们,不可以自我刚强地想要支配一切关系,反而应该在关系连动的交互变化中,柔化自我来丰富彼此。而且这种柔化自我的回应模式,不只是纯然的被动性参与而已,也是迎向共同创造的主动回应性。
四、释“天之道”:损益均衡的两行调中,才能进行无限游戏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1]186
“天之道”有其维持不断趋衡的力量原理。《老子》透过张弓的力量均衡现象,比喻“天之道”就像张弓的力量运作,需要在“损与补”“有余与不足”之间,维持均匀的力量调节,既不能拉力太强而偏高(偏高之极而失衡),也不能拉力松弛而偏低(偏低之极而失衡),而是要能进行“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的“调中之和”活动(15)河上公章句:“天道暗昧,举物类以为喻也。言张弓和调之,如是乃可用耳,夫抑高举下,损强益弱,天之道也。天道损有余而益谦,常以中和为上。”(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94页)。“中和”是一种在异质性的力量“之间”,保持动态调节的精微转化。也就是为了在张与弛“之间”,有余与不足“之间”,往来调节出力量的“适中”,也就是“均匀”的合宜和谐状态。而“调中”与“适中”,是为了避免事物的力量运行,戏剧性地处在“过亢”与“过卑”的两极摆荡,而造成力量的失衡失谐与恶性摆荡。进一步说,更是为了促使“张中有弛,弛中有张”的“非同一性”力量,能“均匀”而“两行”地相互调节与谐和转化。《老子》就是透过张弓隐喻来比拟“天之道”,那种“两行调中”的互补互救,才能成就天道的长久运作。
相对于“天之道”总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着“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趋衡运作,《老子》则提醒我们“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亦即“人之道”经常由于人的“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自我扩张,将“天之道”的适中守衡之均匀运用,朝向不足者更不足、有余者更有余的极端化发展。而根据张弓的“损益均匀”的中和运作原理,这种“人之道”歧出于“天之道”的极端发展,必然会让原本可以良好运作的力量机制受到破坏,而导致运作的失效与停摆。亦即从《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来观之,“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是不可能行之久远的。就像张弓道理,力量偏向一端的一味增强,反而会加速自我折断与失败。
我们可尝试权用“有限游戏”(finite game)或“追逐垄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与“无限游戏”(infinite game)或“共创繁荣”(Perfect competition)这两概念,来方便说明“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损有余而补不足”(16)James P.Carse,Finite and Infinite Games:A Vision of Life as Play and Possbil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2011)。中文译本参见卡斯(James Carse)著,马小悟、余倩译《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一个哲学家眼中的竞技世界》(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有限游戏”可意指当某种物类过分伸展、过分独大的现象发生后,不久便会破坏生物链的交互关系与平衡共生,例如单一物类的短暂独赢(唯一寡头大富翁的Monopolistic winner),很快也会产生物链断裂的恶性发展,终而又返过来伤害自身所安身立命的共生链条。而《老子》要告诉我们的是,“天之道”属于“无限游戏”的大共生关系网络,万物之间所以能维持多元并生的繁荣生态(万物自在而共生的Multiple winners),就因为它自然而然地“损有余而补不足”。倘若某一种物类想要持续“损不足以奉有余”来让自己扩张独大,超过某个临界点,就会破坏“无限游戏”而堕化为“有限游戏”。而“无限游戏”才是形成多赢局面的共生系统,而《老子》正是以趋衡、适中、均匀的“天之道”,来比喻这种“天地并生,万物为一”的生态永续之共生网络。
若连结前面的“释一”,我们可以说,“天之道”实乃展现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一大共生关系网,其中“吾人”和“万物”,实乃共在共生于“天地”这一既广大又绵密的共生互联网。而“一”则是描述“生物以息相吹”“通天下一气耳”的生息与共、气化交感的“生命共同体”或“一大关系网”。换言之,“人”并非只与“物”发生外部性关系,在“人”的内部性之中早已通达于“物”。道家无意将“人”从万物中全然独立突显出来,更不希望“人之道”异化而歧出了“天之道”,成为万物的公害祸源,这也是为何《庄子·齐物论》要再三提醒,“人”莫硬将“自我观之”的“人道”之“正”,给强加在万物身上,以免造成“樊然淆乱”的伤害: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鰌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2]91—93
“人、鰌、猨猴”“人、麋鹿、蝍、鸱鸦”“人、猨猵、麋鹿、鰌鱼”,万物一起并生在天地之间,“人”有何特权而“自我观之”地成为万事万物的标准尺度?强行把自我的“同一性”标准的所谓“正处”“正味”“正色”之“正”,给强加在千百姿态的万物身上?《庄子》批判的正是“人之道”“自我观之”的中心主义和独断暴力,而它所带来的“是非之涂,樊然殽乱”,也就是“人之道”成为万物遭受苦难的来源。一旦人类只知扩张自我权力与欲望,遗忘“万物与我为一”的平等、共生的交互关系,那么人类终将成为《逍遥游》那种无尽掠夺其他生命的狸狌物种:“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2]40当人类一味把其他生命只当作资源物,欲望无尽地猎取万物时,这也意味着人自身也陷入了人道异化所编织出来的天罗地网。对于《庄子》而言,“人之道”必须体认物我平等、共在共生的“天之道”,人应尽量避免自身成为“物害”的苦难来源(害者)。
五、释“人之道”:自我刚强与不知足,成为共生的杀手
在释解“人之道”之前,可暂且对道家的“天人”关系,稍做简单的眉目梳理。“天”与“人”这组概念,也是老庄思想的核心概念,而且常以对比方式呈现张力。“天之道”和“人之道”的分途对比,经常出现在老庄思想的反省脉络,如上述《老子》七十七章便是典例,而《庄子》也时常出现“人小”而“天大”的“小大”之辩:“眇乎小哉,所以属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2]217“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2]273尽管老庄经常用“天之道”来反省“人之道”的歧出与异化,但道家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完全取消人的主体性(或人文创造性),而是在于强调人道对天道的体法参合,例如《老子》二十五章有所谓“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62—64。其中“人(王)”的大,绝不在孤立于天地之道而妄自尊大,而在于对天地之道的守护与参法。也只有“人”重新在“地大、天大、道大”之中来定位自己,“人”才能在“天人之际”的交会关系中,“知人”又“知天”地整全化自身,这也是《庄子·大宗师》所以要强调“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17)有关《庄子》“天人不相胜”的思维内涵,请参见拙文《〈庄子〉“天人不相胜”的自然观——神话与启蒙之间的跨文化对话》,《清华学报》(2016年09月,第405—456页)。。
问题在于,为何“人之道”歧出偏离于“天之道”?甚至极端化扭曲了天道的共生系统?这里便涉及了《老子》对于“人”的进一步诊断。直指核心而言,《老子》认为“人之道”未能体法“天之道”的关键,在于人形成了一连串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认知惯性和欲望推扩模式,正是这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让“人”形成人类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并由此遮蔽了“天地并生,万物为一”的共生之道,甚至恶化成为他人与万物的伤害之源。对于“人之道”背后的这种“自我”状态,可以《老子》二十四章和二十二章来观察分析: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二十四章)[1]60—61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第二十二章)[1]56
在《老子》看来,一般所谓“人”的自我状态,几乎难免于“四自”: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而这种自我的“日益”模式,倾向于《老子》第三十六章所谓“固张之、固强之、固兴之”(18)《老子》第三十六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8—89页)的增强、扩张,也就是自我的“顺向思维”或者自我的“刚强思维”。而二十四章的“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和二十二章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思想义理内涵相通,只是表述形式一正一反。对于“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一连串以“自”为中心的单边主义,二十四章善用譬喻来反讽这种自我状态:那就像翘着脚尖是站立不稳的(企者不立),跨步走路是行走不远的(跨者不行)。原因很简单,它们都是不合自然、不合实情的过分有为造作状态。二十四章更进一步反讽说,“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这种象是用脚尖站立、跳着步走路的夸张行动、造作行为,根本就象是:餐桌上的残食剩饭(余食)、身体上的多余肉瘤(赘形),那样令人嫌恶而不适然(物或恶之)(19)林希逸:“余食赘行,皆长物也。有道者无迹,有迹则为长物矣。曰余,曰赘,《庄子》骈拇枝指之意也。食之余弃,形之赘疣,人必恶之,此有道者所以不处也,言不以迹自累也。”林希逸《道德真经口义》,收入《道藏》第12册第2卷(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705页)。。而真正有道者的立身处事,要尽量避免这种自我膨胀、夸张造作的累赘行为(有道者不处)。
二十四章是从批判面来看“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四自”限制,它会造成“不明、不彰、无功、不长”等弊端。而二十二章则从修养“四自”而转化为“四不自”,来谈“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的效益,其益在于开启“(互)明、(互)彰、(互)功、(互)长”的双向成全。可以说,二十二章是从积极面来谈“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的开显性,二十四章是从消极面来谈“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遮蔽性。总言之,二十四章是从反思的角度,批判过于自我中心的观点、评价、行动、感知,容易导向“自我观之”的单边主义之扩张与膨胀,因而无法回应关系性中的多元差异之他者存在,所以也就无法走向双向照明、双向开显、双向促成、双向滋长的共生之道。
《庄子·天下》篇,曾经对惠施“自以为知盛”的人格特质和自我形象,很传神地用“自以为最贤”来概括(20)“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庄子集释》,第1111—1112页)。这种“自以为最贤”而“欲以胜人为名”的人格特征,《秋水》篇则以河水暴涨后自我过度膨胀的河伯形象来加以反讽:“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2]561惠施和河伯(也可说是人类自我的象征)这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自我”暴涨形象,就像横冲直撞的泥石流,无视于两边涯岸的共在关系,所到之处总是“与众不适”地泛滥成灾而破坏共生。对这种漠视共在关系的自我横行,自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的河伯,终于导致“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的相刃相糜。这也同时象征着人类中心的“自以为贤”、自我中心的“自以为美”,极容易导致权力扩张、欲望扩张,终而成为他人他物的害源。
六、释“损”:无知无我的减法修养,敞开与他者共生的余地
《老子》描述“道”时,总是带着虚位性的修辞,主要在于彰显“道”无为而让开,任让万物“自生自长”“自然而然”。不只对于“道”的表达倾向虚位、后退的虚损性格,对于真人的“自我”修养,也一样充满着柔性的虚位性修辞。如前所述,《老子》二十四章对“四自”(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批判反省以及二十二章对“四不自”(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的转化修养,可作为老庄共生思维的主体性修养基础,由此修养而将自我从“至坚”转化为“至柔”,进一步产生四十三章“至柔驰骋至坚”的共生效益。首先,《老子》二十二章对“四不自”的自我转化,不禁令人想起《庄子·齐物论》王倪曾经连番使用“吾恶乎知之”来回答啮缺(详见前文所引)。王倪连番几次承认“自我的无知”(“吾恶乎知之”),可谓间接呼应《老子》的“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的“四不自”,这样的态度提醒人们要松开“人类中心”和“自我中心”,并如实承认“无知”的重要性。而且只有柔化松解“以我观之”的“正”之标准(其实也是“正”之暴力),才能解放“是非之涂,樊然淆乱”的价值冲突与是非争辩的深度歧见,转而容纳不同事物的立场脉络、欣悦不同事物的存在方式。对于这种减损自我、承认无知、包容接纳的修养,涉及《老子》“为道日损”和“以柔化刚”的共生之道。下面先解释“为道日损”的自我转化之修养: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1]127—128
“为学”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为”积累,属于“日益”的增益模式。但《老子》对“为学日益”的反省,主要不是从经验知识的扩充来讲,而是从它的“自见、自是、自矜、自有功”的自我中心化的增强来反省。因为“自以为知”的争强好胜之刚强主体,最容易“自是非他”,而将立场差异导向恶性竞争,所以《老子》才会激进地(radically)反省自恃刚强、争胜扩张的危险性。《老子》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知识,而要反思“为学”背后的自我“日益”状态。并从“为道”的修养角度来看,反讽过分刚强的自我中心,就像二十四章所谓“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那样,宜舍而不宜久留。而“为道”的功夫修养,主要不在于否定知识,而在于要“日损”自以为是、自以为知的自我膨胀。也就是把“余食赘行”的过剩自我,给予“损之又损”。
从“为学”转向“为道”,关键在于如何从自我加法的“益之又益”,转向自我减法的“损之又损”。如前所述,《老子》的“道”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道”只是“不禁其性,不塞其源”地让开自身,给予万物自生自长的最大空间。不支配、不主宰的“无为”之道,“莫之命而常自然”地给予万物最大生机,正所谓“无为”却能成全“无不为”的妙用。所以《老子》四十八章强调“无为而无不为”,以“无为”(无事)来任让天下,而不是“有为”(有事)去宰制天下。最后需提醒的是,“取天下常以无事”的“取”,不是“藏天下于一己”的私藏私取,而是“藏天下于天下”的不藏不取。一旦违反“无为”“无事”而异化成为“有为”“有事”,那么“以无事取天下”,将堕化为有心有为的权谋之术。因此《老子》要再度强调“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七、释“柔”:为彼此的共生,而承担柔软
柔弱思维显示出自我“日损”“减法”的“逆向”模式,而且《老子》相信削减自我的减法模式,将可带出二十二章所谓“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的共生效果:自我能迂回曲折(曲),反而更能保全自身,乃至与他人的相互成全(成)。自我能低腰弯下(枉),反而更能带来重新的伸展,也给彼此保留更大空间(直)。自我能谦卑处下(洼),反而更能带来丰盈会聚,也能带出共存的更大余地(盈)。事物老旧坏空之时(弊),反而也是处处呈现事物更新的契机(新)。愈少去占有(少),反而愈不害怕失去而心安理得(得)。愈想要占有(多),反而会因为恐惧失去而忧心忡忡(惑)(21)河上公注《益谦第二十二》:“曲己从众,不自专,则全其身也。枉,屈己而申人,久久自得直也……地洼下,水流之,人谦下,德归之也……自受弊薄,后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自取少,则得多也。天道祐谦,神明托虚。财多者,惑于所守,学多者,惑于所闻。”参何上公《老子河上公注》,收入彭晓钰校《老子四种》(台大出版2016年版,第103页)。。我上述使用一连串的“反而”来诠解“则”(如“曲则成”的“则”),是为了突显逆转“顺向”、解构“刚强”的“反转”效果,也就是将自我的极端化扩张,给予逆转收回,而以柔软来成全共在共生。
《老子》的“逆向”“柔弱”“减法”“后退”等反向思维方式,不是建立在“手段-目的”的权术架构下的谋略运用,而是深刻体察到事物“相反相成”却又“一体连动”的存在道理。所以二十二章也强调“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其中的“抱一”意味着:生命没有独自存活这回事,存在必然要与万事万物彼此环抱、圆环共舞,相互构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老子》的“减法”或“后退”思维,其实是建立在“抱一”“体一”的一大关系网络中,以关系联动来思考处境中的伸缩之道、进退之道、损益之道。因而这样的活动,是迂回的柔软之道,而非自我尊大的刚强之道。而“柔软”并不是软弱或脆弱,而是为共生而承担柔软的实践修养。柔软才能保留余地给他人,同时也为自己留下余地。正是这种“保留转圜”的余地哲学,让《老子》提出了“逆向思维”和“柔弱思维”。这种“逆向”能让自我中心的单向道,被转化为关系性的两行之道;这种“柔弱”能让孤立性的独我增强,被转化为包容性的共生之道。这种“夫唯不争”的柔软,不以刚性思维的增强模式去“争胜”“争霸”,却反而实现了“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自然效益。对于《老子》来说,绝非因为我“刚强”才形成“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局面,而是因为我“柔软”而放下“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相争相强,反而才留给其他事物宽阔的余地,因而能够促成共生共长的最大繁盛。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老子》第四十三章)[1]120
四十三章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其中的“至柔”(或柔弱),对照于“至坚”(或刚强),主要是就人的主体或自我状态而为言。而“至坚”或“刚强”的自我,总是表现出“自见、自是、自伐、自矜、自有功”的刚强意志,也就是说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志状态,充斥着争胜、主宰、控制的强烈欲望。而“至柔”或“柔弱”的则是修养出“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自有功”的虚心怀柔,也就是转化“相争”为“共生”,转化了“控制”为“任让”。也就是说,“柔弱(至柔)”是把主宰意志给予虚心弱志,转而因循于彼此共在的关系脉络,以寻求共生之道。
《老子》所以强调“柔弱胜刚强”或“天下至柔驰骋天下至坚”,重点并不在于权谋地使用柔性策略来战胜强者,因为这种理解仍然陷入“柔”与“强”相争的输赢逻辑。究其实,《老子》不是要刻意要使用“柔弱”去打败“刚强”,而是因为“刚强”的“至坚”主体,源自主宰性意志或强制性的欲望,因此其自身终不可能长久而导致自败自散。在《老子》看来,没有任何个人意志可以控制一切,没有任何事物状态可以维持不变,自然总是依随情境转化而不断示现“非-常道”,这将使得人们依其“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主宰欲所想要勉强维持的“常道”,必遭“反讽”而自我解构,并且再度敞开于四通八达的无常、无封之道。可以说,想要终极解决一切、控制一切的(自我)“刚强”,反而会放大显示自身的脆弱和漏洞。只有因循变化而向各种可能性敞开的(无我)“柔软”,才能欣纳变化、随遇而安、调适共生。
而四十三章的“无有入有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这句话,或可相应于《养生主》的“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正是使用庖丁手上那把刀的“厚”与“薄”,来比喻自我状态的“实”(刚)与“虚”(柔)。而一个能让自我,由“厚”转“薄”,由“刚”转“柔”的庖丁,他才能柔软有韵地“依乎(牛之)天理”,从而处处发现人牛之间、物我之间的共生余地(刀牛之间的恢恢乎间隙)。这再度印证了“无为”,能转化“输/赢”(lose-win)的有限游戏,而打开“双赢”(win-win)的共生大益。这种“人之道”合于“天之道”而走向双赢共生的无限游戏,正是四十三章最后所以要强调的“不-言”之教(不偏执于己言),和“无-为”之益(不偏执于自为),才真是天下珍贵稀有的公共资产。所谓:“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八、释“反”:向对手学习,与敌人共生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1]24
《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的“反”,其实同时包含“相反”与“相返”之“玄同”义(22)陈鼓应指出:“反:通常有两种讲法:(一)相反:相对立。(二)返:如林希逸说:‘反者,复也,静也。’如高亨说:‘反,旋也,循环之义。’”参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3页)。陈先生则建议以“返”为从,而本文则更愿意保留“反”与“返”的辩证丰富性。另外,王淮亦认为反有二义:(一)反向运动:相对作用之意,以老子第七章、十三章、二十二章、四十一章、八十一章为义例。(二)反复运动:循环作用之意,以老子第九章、十六章、二十五章、五十二章等为义例。参王淮注释《老子探义》(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161—162页)。。而“相反”与“相返”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模式,而是同一运动中“既异又同”的吊诡玄同关系。对于老庄来说,世界所以能永续地生成变化而无所终穷地成就“道之动”,乃在于“有无玄同”“阴阳冲气”的“相反又相返”之玄妙运作。亦即“反者道之动”,既表示阴阳气化之间的“相反又相成”,也暗示有无之间的微妙玄通的可转换性。如前所言,“相反又相返”的力量运作模式,不只呈现在“天之道”这种宏观宇宙(遍化在万物中)的运作中,其实也呈现在“人之道”的微观自我的运作中。而它们共通的基本原理就在于:不要让相反的力量,各自往极端化一边去自我增益,而是应将外围境遇的差异性力量(包括不同方向甚至相反方向的力量),以适宜地方式将它们“冲气为和”地调节起来,以形成一种内部差异却多元并生的吊诡状态,也就是一种“两行调中”“均匀适中”的力量运作模式。
《老子》善于体察天道/人事之“均衡”消息与机微,事物一旦向极端化的一边摆动太过,则“物极必反”(反者道动),其中必同时隐含反向动势(以求重新趋衡)之机微在其中。但是一般人容易循着“自我”刚强的顺取习性,依循眼前“趋势”一味增强竞逐,如此一来,便容易盲目于:一味追求扩张而过分固执、上瘾于扩张(必固张之);一味追求增强而过分固执、上瘾于增强(必固强之);一味追求繁盛而过分固执、上瘾于繁盛(必固兴之);一味追求施加而过分固执、上瘾于施加(必固与之)。这种“固执一偏”的极端化发展,未能善加体察事物变化的隐微“内势”,其实隐藏着“反者道之动”的物极必反以回复均衡之天理。因为“扩张(张之)”的力量趋势,同时也隐含着“收敛(歙之)”的反作用力;“增强(强之)”的力量趋势,同时也隐含着“衰退(弱之)”的反作用力;“繁盛(兴之)”的力量趋势,同时必隐含着“没落(废之)”的反作用力;“施加(与之)”的力量趋势,必同时隐含着“收回(夺之)”的反作用力。对于《老子》而言,这些“物极必反”的众多现象,一再反映出“反者道之动”的吊诡运动与均衡之理。因而提醒我们,宜对事物活动所体现的反势运动(道之反动),保持着精微敏锐的觉察(微明)(23)如范应元指出:“张之、强之、兴之、与之之时,已有翕之、弱之、废之、取之之几,伏在其中矣。几虽幽微,而事已显明也。故曰:‘是谓微明’。或者以此数句为权谋之术,非也。圣人见造化消息盈虚之运如此,乃知常胜之道,是柔弱也。盖物至于壮则老矣。”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一)》,收入严一萍选辑《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1967年版,第72—73页)。。
“反者道之动”,并无任何神秘之处,绝非天道为了惩罚人们而刻意使强盛事物衰败,它只是天道变化(事物力量变化)自然而然之趋衡现象。一旦作用力朝向极端化发展而严重失衡时,反作用力就会戏剧性地增强它的拉回力道,以求再度趋衡。如此可见,天道中的事物变化的无限游戏,不在于一味增强与扩张,而在“负阴抱阳”“相反相成”的辩证转化与调衡运动。因此对《老子》来说,从“反者道之动”所释放出的共生思想,就是让不同存在事物之间保有互相转化的调节空间,千万不要迷信自我力量的一味增强,而导致力量之间的极端“相反”,而是给对方留下余地,因为留给别人余地和留给自己余地,也就是把“相反”的力量冲突,转化为“相返”的力量共生。这也是《老子》第九章所再三强调的: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棁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1]21
若再度使用“有限游戏”(finite game)与“无限游戏”(infinite game)这两个概念来比喻:“持而盈之”“揣而棁之”“金玉满堂”“富贵而骄”的行为与心态,就像是掉入一场“有限游戏”的竞赛,赢者通常会高举胜利姿态,自以为战胜了世界、征服了他人,这是属于赢者全拿的零和游戏。但《老子》告诉我们,自然天地之道原属于共生的循环法则,物类生态若要维持多元并生的繁荣演化,就不宜只让单种物类无穷扩张、过分独大,因为这将破坏生物链的交互关系与平衡共生,终而导致“物极必反”而“从独赢到全输”的反向效果、恶性竞争。而“无限游戏”则是转化“相反”为“相返”,如此可形成“双赢乃至全赢”,而正是这种多赢共生的无限游戏,才能让天地之道、自然生态朝向永续发展而无穷无尽。《老子》时常反讽人类以“有限游戏”的“人之道”,去干扰甚至破坏“无限游戏”的“天之道”,如此一来,人类将难以避免在高与下、有余与不足的两种极端化竞争,落入恶性循环的激烈摆荡。唯有当人能转化“有限游戏”的“两极对抗”,转而效法“无限游戏”的“两行调中”,人类或许才能稍微避免“物极必反”“亢龙有悔”的自我溃败与自取灭亡。
何谓“弱者道之用”?我们可先从对立面的“刚强”谈起。“刚强”通常预设主体中心的强悍夸大,是以“我”为中心的“自是”“自矜”“自伐”的有心有为状态。而“柔弱”并非与“刚强”二元对立下的另一端,而是转化成为“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的无我与虚待。“弱”也相通于《老子》的“慈”与“柔”,都是将人类自是、自见、自明的主体中心主义,逆转收回地转为“泰然任之”的包容与聆听,并能给予万物自生自长的最大共生空间。换言之,道的“弱”呈现出处下、处柔、处卑,不主不宰而让出“无用之大用”的最大余地给万物们。“柔弱胜刚强”的修养智慧,则建立在转化“自我中心”的刚强意志与主宰习性,并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相对反,转化为“相反又相返”力量共在状态,并互留余地以共生共化的天理游戏。显然,对应于“刚强”倾向“同一性”力量的单向强度支配,《老子》倡导的“柔弱”并非与刚强对立的软弱,“柔弱”的修养也绝不是无力的虚弱,而是在“非同一性”的力量之间,保持更好的调节敏觉。即《老子》的“柔弱”,是同时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相反”和“相返”都考虑在内,并思考两者“相反又相成”(不只是相反)的调节性。
对于人类习惯顺着“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所养成的自我状态,遭遇相对或者相反的理念、事物或力量,人们多少都会兴起本能性的排斥或厌恶,这是因为吾人已经习惯于从顺时钟方向去“日益”刚强的自我,因而对于阻碍甚至违逆我刚强壮大的逆时钟力道,都会感到阻涩而不适,进而想要消除这种“反向”的事物或力量。但《老子》四十章却提醒我们:“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简单地说,“反者”“弱者”,由于具有把“日益”的刚强自我,调节转化为“日损”的柔软自我,因此更能回应“反者道之动”的运作机微。如此一来,面对相对或相反的人、事、物、力,不要只是想要一味地去消除它们、抹杀它们,反而要想办法去消化它们、吸收它们,进而转变自我、演化自我,是《老子》要我们从“反”的角度,向对手学习,与敌人共生,把对立的力量转化成自身力量的一部分。换言之,共生不只是与“相生相益”的助力事物,共在共生;更深层的课题还在于如何与“眼前相伤相碍”的反力事物,共在共生。
另外可补充,《老子》书中充满着“正言若反”的思维方式。例如原本属合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正言”,由于世俗之人沉溺“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深陷自我刚强而积重难返,反而对柔软共生的“天之道”,觉得刺耳而不可思议,误认为“反言”。《老子》欲使人们逆转“人之道”重返“天之道”,以便将“人之道”的颠倒给再颠倒,将“人之道”的逆向给再逆向,如此“反反”期能“返正”,此乃“正言若反”之吊诡修养义。比如《老子》四十一章,一开头便带有这种“正言若反”的反讽味:“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1]111“下士”即一般沉溺“人之道”而习惯“自是、自见、自明”的“固我”之人,而“上士”乃能“不自是、不自见、不自明”而效法“天之道”的“无我”之人。然长久习惯于“人之道”的下士,乍闻“天之道”的言论观点(如“柔弱胜刚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等言论),反而会觉得“荒唐之言”“谬悠之说”那般可笑(大笑之)。但是《老子》不无讽刺地指出:在俗人愈觉得荒唐可笑的言论行为(反言,反行),反而才愈加显示这些言论的真实可贵(不笑不足以为道),它们在有道之士的眼光里,正是最可贵而值得立即践行的“正言”(勤而行之)。原因无它,因为“人之道”经常“反其道而行”,行之既久,便误以为刚强掠夺的“人之道”为正道。此时若有人告知,应该逆转“人之道”方能重返“天之道”的正道,此时久溺“人之道”的下士,便可能因为遭遇“反言”“反行”而不适不快。
然而《老子》要告诉我们,其实看似“反言”的话,有时才是货真价实的“正言”,它之所以让人有“若反”的感觉,完全是因为我们先行颠倒了正言、逆行了正道,并养成甚深习癖,因此才对真正的正道之言,反而觉得陌生不适。倘若我们能够转化“故我”与“固我”的习性,那么我们将能重新聆听“若反”之“反反之正”所开示的“反动之道”。由此可见,“正言若反”的“若反”,不是简单的“反”,而是带有“反反以归正”的辩证性格(否定之否定以回归肯定)。可以说,《老子》的“正言若反”,带有“将颠倒再颠倒”,以复归正言、正行、正位之旨趣(24)总体言之,《老子》的“反”,可能有几个意涵:一者,“反向”,带有“反向而行”的逆反意味;二者,“相互返回”,例如“负阴抱阳,冲气为和”,“反者道之动”,带有“相反相成”的调中意味;三者,“否定性创造”,例如透过“无”“非”“去”“不”的去执去病作用,以复归“非常道、非常名”的妙用状态。。要特别注意的是,“正言若反”的“正”,绝不再是固定标准、单一方向的“正”,反而是要“反”固定之正、反单一之正,以便让各种“恢恑谲怪”能够“各正其正”而“并行不悖”地被包容、被笑纳。如此一来,“正言若反”的“反”,具有反讽“常道”“常名”的正言性格,以逆返“不道之道”“不正之正”的吊诡之正言。
九、释“玄德”:知白守黑、和光同尘的共生伦理
《老子》喜欢用水的“处柔”“处下”“处卑”,谷的“处空”“处虚”“处中”,这些带有“否定性”意味的隐喻,来重新描述“道”与“德”。这种“否定性”的修养,将“自见,自是,自矜,自伐”的自我中心之主宰性与判断性,给予柔软松解,从而敞开涵容广大的“玄道”“玄德”空间,足以包容各种差异立场与事物,甚至两极对立的立场与事物。而这种将对立两极给予“玄同”的思想,彰显出《老子》最深刻的共生思想。《老子》首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已经显示出“玄”能将“无与有”(或无欲与有欲)这两端,给予“玄同”化,使其“差异中能和同,和同中有差异”。而这种“玄同”化思维,《老子》五十六章又以“和光同尘”这个隐喻来表示:“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可见,能让“光”(光明,价值)和“尘”(黑暗,反价值),这最远的两极,产生和解共生的“和同”关系,才能称之为“玄同”。“玄”之为“玄”,就是让“非同一”的张力状态(如“无与有”)或张力事物(如“光与尘”),能产生彼此往来、相互过渡的交织状态,才可谓之“玄”。其深刻在于,化冲突对立为两行共生。由此而可理解,《老子》的“道”与“德”,尝试“否定”单行道的“据道”与排他性的“据德”,并透过“不道之道”与“上德不德”,来开显更为广大包容的玄同之道(如《老子》第一章)、玄同之德(如《老子》第三十八章)。下面尝试言之。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1]136—137
“道”虽然生畜、长育、养覆万物,却要“莫宰其命”地化除自恃心态,又要“常任自然”地信任万物各随形势去展现自身。“道”对待万物的“玄德”方式,呈现出尊重、信任、放开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才真能呼应于道的宏大无私、阔然容纳之“玄德”。“玄德”也是有道者去自我、去中心、去偏私、去宰制的修养。正是“玄德”这种“道法自然”的“泰然任之”,让万物(含百姓)拥有千姿百态的差异之美,让万物自然而然地自发生长与多元发挥。如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1]90—91也就是说,道与万物最理想的状态乃是:道无为让开而万物自宾自化。也可说,道的莫宰莫命之“无为”玄德,最能“无不为”地任让出万物自宾自化、自然而然的生生景观。可见“玄德”的精神在于让万物皆能生机盎然地实现自身,而不是将世间万物收摄于统一之道而只彰显道的权柄。事实上,《老子》的“玄德”不是为了荣耀道的主宰性,而是为了荣耀万物的自发性。尤其在解构道的主宰性与控制性之后,反而才能让万物缤纷多彩地自宾自化。而人(侯王)最为可贵的“上德”态度,最宜效法大道玄德的“无为而无不为”,并将这种包容差异、欣赏多元的玄德伦理,运用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中。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老子》第三十八章)[1]93
相应于《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三十八章则强调“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并透过“不”的治疗除病作用,将自以为“据德(不失德)”的优位固我心态给予消除。首先,《老子》将“上德”和“下德”作对照,并透过否定性的“不德”(不据德),来辩证彰显它所要呈现的肯定性表达:“是以有德。”换言之,“是以有德”是透过对“不德”的除病或者对“下德”的治疗,来呈现其“有德”的宽容包含。“上德”的提出,代表《老子》的伦理关怀是批判后的辩证肯定,而不是单纯的直接肯定。一般“下德”的直接肯定(不失德)的思维模式,行事上断然表现出“为善去恶”的积极作为(为之),内心里又带着“择善固执”的强度意向性(有以为)。然而《老子》却批判这种“为之(外)”又“有以为(内)”的“据德”状态,并不是与他人兴发原初性伦理关系的最好方式。从《老子》看来,原初性伦理关系的“上德”(上善之德)实现方式,需要对主体的道德裁判(为之)和道德意志(有以为)之“前识”,给予“无为”和“无以为”的“双无”之转化修养。
三十八章所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意指“下德”乃不脱“为之”和“有以为”的“前识”做主,这是一种“以自为前、以自为识、以自为光”的自为之和自以为(25)河上公章句:“不知而言知为前识,此人失道之实,得道之华。言前识之人,愚暗之倡始也。”《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150页。林希逸:“前识者,多识前言往行也。以多识为智,则非道之实矣。华者,务外也。若以此为智,反以自愚,故曰愚之始。”(林希逸《道德真经口义》卷3,第710页)。而《老子》认为“前识”做主的道德优越感,凿破了原初素朴的伦理关系(道之华),反而走向了“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愚昩(愚之始)。《老子》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约可相应于《齐物论》的“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的成心自师[2]63。而“前识”(即“成心”),正是凿破浑沌、裁判是非的利刃,从此让“知白守黑”的“和光同尘”,变成善恶分明、是非两端。《齐物论》言:“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其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2]83显然《庄子》嘲讽的“八德”(左右,伦义,分辩,竞争),契近于《老子》所批判的“下德”(26)《庄子·齐物论》的“八德”之说,应是对“仁、义、礼、廉、勇、忠、信、孝”等用法的“反讽”。亦即道德条目在《庄子》看来,它反而属于“道封”“言常”的产物或标示。原本“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的状态,属于《老子》“道德”未失的原初状态。一旦“道有封”“言有常”,便堕化为“失道”“失德”而后的“仁、义、礼、廉、勇、忠、信、孝”等,具有明确条目性的价值判断与行为规范。对于这种定义相对明确、分辩相对清楚的儒式道德伦理,《齐物论》便以反讽口吻指出八德的核心本质不脱于:“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简言之,这种“有左有右,有伦有义”的规范秩序,它建立在“有分有辩”的名言分类与区辨的基础上,同时也脱不开“有竞有争”的价值竞争与排斥的命运。这就像《人间世》对“德”“知”“名”的反讽与反省:“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庄子集释》,第135页)。《庄子》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有左有右,有伦有义”的秩序规范,也要留心它带来“有分有辩、有竞有争”的“樊然淆乱”之后遗症,也就是类似《老子》三十八章所谓“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浅薄与混乱。
《老子》批判以自为前、以自为识、以自为光的“前识”,称这种自我笃定与自我优越的成见心态,其实是对于“道”的踵饰增华之“余食赘行”,所以才要有返朴归真的“不自”“去自”之修养功夫。而为了对治“余食赘行”“前识踵华”,则有二十九章的“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也就是将自我的“甚、奢、泰”,转化为“敦、俭、朴”的柔软平淡(27)林希逸:“甚、奢、泰三者,皆过当之名,亦前章余食赘行之意。圣人去之者,无心无累,无为无求也。此章结得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语,非唯是其鼓舞之笔,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道德真经口义》卷2,第707页)。
《庄子·齐物论》所嘲讽的“八德”,除了呼应《老子》三十八章的“下德”,进一步说,“八德”或“下德”都涉及了道德之光的暴力,尤其和语言概念的二分切割,密切相关。如《老子》二章所分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28)王弼注:“美者,人心之所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明数也。”(《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6页)因为语言的二元特性,使得人类经由命名、分类所建立的道德规范与伦理尺度,产生肯认中心而排斥边缘的现象。就像美、善的被高抬和丑、恶的被贱斥,是同时成立的。有/无、难/易、长/短、高/下,一连串对比概念,都不免于肯定与否定的“相较相成”。换言之,对正价值的追求与负价值的贱斥,属于“即肯定即否定”的一体两面。由此很容易造成肯定一边而牺牲另一边,如《齐物论》所分析的现象:“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2]70肯定这一边(成此一端)、否定那一边(毁彼一端)的道德裁判,在老庄看来,则属于“凿破浑沌”的下德处境。这种肯定部分生命、部分行为,排斥其他生命、其他行为的八德处境,使得原本“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的接纳差异而欣赏多元,堕化为“有分有辩,有竞有争”的特定追求而贱斥他者。
老庄除了批判“有分有辩,有竞有争”的二元性道德伦理乱象,《老子》也指出道德优位性的一偏之见,容易产生“光之暴力”,因而《老子》的玄同伦理则要以“袭明”来加以柔和,并走向“和光同尘”的宽容与谅解。此如《老子》五十六章“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老子》第二十七章)[1]70—71
在《老子》看来,一般意义的“善”透过与“不善”的对立来突显自己,例如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但是这种“善/恶”俨然分明的“一偏之善”,也容易留下后遗症:一者很容易产生自我确信的道德固执,二者容易产生贱斥他人的道德裁判。换言之,一般意义的“善”,可能会带来择善固执的不柔软与不宽容。所以二十七章要柔化一般善行容易产生的固执与对立,调节转化出“无弃人、无弃物”的柔软之德、宽容之善。
三十八章的“下德”之“善”,处于善与恶对抗的一偏之善,它只能位于跷跷板两端对立的其中一极。但二十七章的“善救人”“善救物”的“(上)善”,并非取一端、弃一端的“下德”模式,而是“无弃人”“无弃物”的广大包容之“上德”模式。这种能让两端和解、两行相化的“上德”之善,二十七章又将其称为“袭明”。何谓“袭明”?“袭”,具有含藏收敛、因循调节意味。也因为能含藏、节制自是自见的“明”,所以才能因循对方的脉络而“和光同尘”。透过“袭明”,才能“知白守黑”,才能够两行对话而调节极端,以防止掉入单边的道德裁判。简单说,“袭明”是为了转化同一视域的光之暴力,让不同视域所带出来的差异性明暗光谱,具有“黑白相守”“光尘和同”的交互对话性。
也由于具备“无弃人,无弃物”的“袭明”态度,它才可能让“善人”与“不善人”,从两极互斥的对立斗争,转化为“和光同尘”的两行对话,甚至变成“相师”“相资”的互助互化。所以二十七章总结“善与不善”的“互师”“互资”的共荣景观:“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所谓的“善人”与“不善人”,如果能暂时松开固定化的标签,转从故事化的脉络去尝试同情理解,那么它们便可能具有互照功能,可以成为提醒彼此的好教材,甚至成为双向学习、双向转化的共生资产。正是这种“善/不善”的“相师相资”,才真正显现了两行共生的玄同妙义(是谓要妙)。然而一旦只是一味地自是非他,一味地固执一边之见,那么我们将舍弃“相资相师”的大好学习机会(不贵其师),也遗忘了双向转化的互为资产(不爱其资)。然而这种自以为是的小聪明(虽智),其实是困在自我成心的迷宫中而出不来(大迷)。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第四十九章)[1]129
大体说来,《老子》的“常心”与“无常心”,相应于《庄子》的“成心”与“虚心”。而老庄的圣人希望转化“以我观之”的成心之见,松解“常心”的一偏之见与一端之执,以百姓的思考为思考、以百姓的需要为需要,这样才能容纳百姓的多元角度和众多意见(以百姓心为心)(29)朱谦之:“各本‘无’下均有‘常’字,敦煌本、顾欢本无……圣人不私心自用,唯以百姓之心为心而已。”朱谦之释,任继愈译《老子释证》(里仁书局1985年版,第194页)。。“无常心”的圣人,不高高树立自以为是的美善标准,不硬用善恶二元的价值体系来框限并裁判百姓。由于不轻易黏贴“善”与“不善”的价值标签,所以更能够聆听差异的众多声音(善者,不善者,皆能善之),也更能够接纳多元的不同故事(信者,不信者,皆能信之)。
一般人视为善恶对立的同一性价值标准范式,如今被转化为立场差异的价值多元之共生对话。对此,四十九章称呼这种非二元对立、非道德裁判为“上德之善”(玄德之善)与“上德之信”(玄德之信)。这也呼应了第三十八章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关键在于,“上德”不固执(无常心)于自以为是、自以为对的道德标准,因此才能如“上善若水”那般“善利万物而不争”。而“下德”太固执(有常心)于自是自见的道德框架,自以为能决断价值的主流方向,结果造成与万物争善,反而难以避免道德裁判的光之暴力。《老子》的“德善(得善)”与“德信(得信)”,提供了“和光同尘”“知白守黑”的包容力道,它让不同立场与脉络的百姓们,可以找到自然自在的生长空间(30)有些版本做“德善”与“德信”,但有些版本也做“得善”与“得信”,即“德”与“得”相互假借。焦竑引苏辙语:“无善不善,皆善之,无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尝渝也。可谓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之者未尝变也。可谓徳信矣。不然,善善而弃不善,信信而弃不信,岂所谓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哉?”焦竑《老子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焦竑引吕吉甫语:“犹之鉴也,无常形,以所应之形为形而已。圣人之视己心也如此,则其视百姓心亦若是而已,则善不善,信不信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无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亦无常,而以德信之故也。”(《老子翼》,第122页)。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老子》第二十八章)[1]73—74
二十八章主要由三个对应句子来构成,而且意义结构相一致。基本上这三个句子的意义相似,一开头都在描述不落入“雄/雌”“白/黑”“荣/辱”等二元对立的两端(但或可稍做细微区分,如“雄/雌”或涉及性别或动静的两端,“白/黑”或涉及“道德”与“非道德”的两端,“荣/辱”则涉及“声名”与“非声名”的两端)而超越“价值”与“非价值”的两端对立方式,乃在于回到“为天下谿”“为天下式”“为天下谷”的会聚之地。尤其“谿”“谷”更是表达道的负抱、容纳意象,如三十二章“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四十一章“上德若谷”、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显然“谿”“谷”的处下、容纳、不争,常被《老子》用来譬喻柔软包容的上德、广德、常德(31)《老子》经常交互使用“上德”“广德”“常德”“玄德”等概念,来对照于善恶对分的“下德”。基本上,它们都意味着超越二元对立的另类德行模式。这是因为老庄的“道”不固定、不占据某特定之道,因此其“德(上德不德)”也具有了包容差异的广纳特性。。
也唯有处卑、就下、不争、广纳的“常德”性情,能做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既能知道“价值(有用)”如何被焦点化地突显出来,也能守护未被焦点化而隐没在“非-价值(无-用)”的广大场域。亦即“谿谷”的“中央”之地、“浑沌”之玄德(常德、上德、广德),能促使原本对立的两极(“雄与雌”“动与静”“白与黑”“荣与辱”),重新遇合于“谿谷”(无极)之地,展开“即有用即无用”的相知相守之两行共生、平等对话(32)至于“为天下式”的“式”,除具有法式的模范意义外,它可能具有早先“式盘”所象征的“中心与四方”“天圆与地方”“中心与两行”的统合意味:它的天圆地方形象,圆的中心有一空洞,可悬挂而圆转不息,象征天行运动的周行不殆。放在本文的脉络乃涉及“负阴抱阳”的“冲和”意义,“式(盘)”的具象本身,就带有“雄雌负抱而不二”“黑白负抱而不二”的意味。有关“式盘”的考辨,可参看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章,第89—174页)。。《庄子·应帝王》的“中央”之地,呼应于《老子》的“谿谷”之地,都具有“中而空”“中而下”的虚位、谦下之意涵。而“浑沌”之善,则呼应于“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的“常德”之善。而复归“婴儿”(雄雌未对立)、复归“无极”(阴阳未两极)、复归“素朴”(原木未裁割),其中的婴儿、无极、素朴,这三者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脉络下,都具有“即有即无”“浑而为一”的二边交织而“中道不偏”特质。例如成玄英对《庄子·应帝王》“浑沌”中央帝的注解,便很能保握这种“即无即有”“非有非无”的调中特质:“南海是显明之方,故以儵为有。北海是幽暗之域,故以忽为无。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浑沌为非无非有者也。有无二心,会于非无非有之境,和二偏之心执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2]309—310
因此二十八章要提醒我们“朴散则为器”,并总结在“大制不割”。“朴散”意味一体流通、多元交流的浑沌、抱朴状态,现在被割裂成对立的两边,使得原先的浑朴被支离了,而“常德”也就被破坏了。原本可为天下范式(式)的“常德乃足”,现在被“朴散为器”的特定框架与硬性规范给取代了。因此《老子》要提醒我们,唯有重新“复归于朴”而善用“大制不割”的圣者,才能成为好官长。因为好的导引者要能实践“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的“常德”包容之道,而不是让百姓掉入“各得一偏”却“不能相通”的定用之器。
对于“不割”“抱朴”等状态,除了呼应谿谷的中空、处下的容纳特性,《老子》还运用了婴儿“专气致柔”的身心状态来比拟(“婴儿”是雄性与雌性气质,尚未单向固定化的原初可能性);也用了阴阳流转而两行无碍的无极来比拟(“无极”是“无偏于阳亦无滞于阴”的两行可能性);还用了树木尚未被制成特定器具前的原朴可能性来比拟(一旦凿成特定器物,可能性就被决定的现成性给代替了)。总之,“朴”乃处于暧昧两可、浑然为一的可能性,一旦进入“朴散为器”的割裂状态,人们就很难不掉入“雄/雌”“白/黑”“荣/辱”的有封、有常,并且由此产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对立斗争。所以好的带领者(官长),要能善于守护“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的“常德”“不割”之道。值得提醒的是,“不割”只是不决裂为绝对分离的两边(“于二而无二”),而不是全然无用的“纯粹同一”。亦即官长作为人类文明的守护者,不可能不适度“用器”而走向一定程度的“朴散”,但也要“知有守无”“知器守道”,才不会掉入“用器忘朴”的一边之见。当然,《老子》的还朴之道,也不是简单地回归“纯然无用之朴”的另一边见。而是“知其器守其朴”的“即器即朴”之中道调节,调节中道。
十、释“下”:以柔软谦下作为国际政治的共生原则
《老子》思想产生于春秋末期,当时邦国与邦国的国际关系,大都走向军事的富国强兵与政治的合纵连横,邦国与邦国走向力量与力量的兼并关系,彼此之间难有信任可言,甚至兵刃相对而战事连连。这种大邦国欲求扩大、小邦国欲求生存的冲突对立、互不信任,使得国际政治愈走愈极端,几乎把当时大小邦国都共同卷入国际战乱局势。可以说,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是离共生哲学最遥远的时代,但也可以说是最迫切需要共生哲学的时代。因此《老子》“反”其道而行,不管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上,都要逆反当时的刚强扩大之道,改采共生的柔软谦下之道。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1]159—160
大邦国最容易自恃力量的刚强,然而当它能做到虽强却不恃其强时,才能够收回强权给人的威胁压迫感,转而敞开春风化雨般的柔性力量,不使人因畏惧而远离,甚至自然而然让人自愿亲近。《老子》期许邦国之“大”,不在以“强”权来迫人屈服,而在于让出共生余地,如海纳百川般居下广纳,如磁铁效应般自然吸引,让小邦国人可亲而愿依。只有大邦国能将“争雄”的杀伐之气,转为“怀柔”的和平之气,才更能发挥“柔胜强”的吸纳效果。因此《老子》强调,这都是因为大邦国能效法雌性“处柔”(不恃强)“处静”(不妄作)“处下”(不争胜)的原故。一言以蔽之,大邦国的自居“下流”“以静为下”,而能体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处下”“不争”“不宰”等德性,小邦国才自然而然地愿亲近依偎。
对于《老子》,“下”其实是大邦、小邦和平共生的共通原理。《老子》提出“以下”作为大邦国、小邦国互留余地的共生之道:“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33)吴澄:“大国不恃其尊,谦降以下小国,则能致小国之乐附;小国甘处于卑,俯伏以下大国,则能得大国之见容。”(吴澄《道德真经注(二)》卷4,第3页)如张默生言:“或谦下以取得小国的信仰,或谦下而取得大国的信任。”[6]293换言之,大邦国与小邦国的互信互存与长治久安,绝对不单靠势力大小来进行强弱的力量主宰与单边支配,而是大邦国谦让怀柔(大国以下),而取得小邦国的敬重与信任(则取小国)。小邦国谦卑处柔(小国以下),而取得大邦国的尊重与见容(则取大国)。所谓“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前者(或下以取)是指大邦国取得小邦国的亲近,后者(或下而取)是指小邦国取得大邦国的容纳。大邦国和小邦国,皆因“以下”而能互信互取、共在共生。由此可见,双方的“以下”,才能获得双边的相互取信,以共创双赢的共生之道。
一般而言,大邦国的愿望在于兼容并畜(欲兼畜人),小邦国的愿望在于相亲无事(欲入事人)。然而两者的愿望要想能一同实现(夫两者各得所欲),《老子》则以“大者宜为下”做总结(34)王弼注:“小国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归之。大国修下,则天下归之。故曰‘各得其所欲,则大者宜为下’也。”(王弼《老子王弼注》,收入彭晓钰校《老子四种》,第54页)。换言之,虽然“以下”是大邦国和小邦国共生互信的共通原理,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大邦国还是应该领头做出“大者宜为下”的表率风范,毕竟军事与权力的强大,容易带来威胁的距离感与不信任感,因此大邦国宜先松解这种杀伐之气,以打开共生互信的第一步。可以说,《老子》强调大邦国最能够作为领头羊,最应率先“以下”“处柔”地引领大家,一起营造兼容并蓄、共生共荣的好气氛。
十一、释“兵”:战争是对共生之道最极端的伤害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老子》第三十章)[1]77—78
《老子》身处乱世,大国走向富国强兵以求扩张版图,小国被迫以军事防卫以求自我生存,在战国穷兵黩武、刚强争胜的年代,富国强兵几乎成为君王治国的首要目标。在集权又军权的时代氛围下,《老子》“政治不正确”地提出了它“反其道而行”的深沉呼吁:“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它要急踩刹车地劝戒君王、呼唤有士者:要以“道”来引导人主,而不是以“兵”来争强天下。《老子》的“道”,柔软无为、不争处下,要守护多元共生的最大余地;而“兵”,刚强争胜、杀伐征服,为求扩张版图而不留余地。
三十章沉痛地提醒我们:“以兵强天下”的军事行动,几乎难以避免两种恶性后果:一是“其事好还”,以军事武力毁人家园、取人性命者,必定种下长久的仇恨心理与血偿逻辑,也就是掉入仇恨滋生仇恨,血债报复血债的“好还”恶果。一旦开启战端就会导致接二连三的恶性循环,也就是战事很难摆脱仇恨心理带来的报复逻辑(35)成玄英:“还,返也,报也。言外用兵刃,即有怨敌之仇。”参强思齐编《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8,收入陆国强等编《道藏》第13册(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页)。朱谦之:“兵凶战危,反自为祸。”参考朱谦之释,任继愈译《老子释译》(里仁书局1985年版,第120页)。蒋锡昌:“此谓用兵之事,必有不良之报还。”蒋锡昌《老子校诂》(东升出版1980年版,第199页)。王淮引李息斋语:“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是谓好还。”(参王淮注释《老子探义》,第121页)。“其事好还”暗示我们,这种国仇家恨的心理情结,不但不会随着战事结束而结束,还会形成未来战端的甚深因子。二是“必有凶年”,随着武力杀伐之后,大量男丁的死亡带来的家庭破碎,而军事行动更造成土地荒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随着男丁缺乏、土地荒芜,接着就是经济破败与民不聊生(必有凶年)。因此对于《老子》来说,有识之士必须“以道佐人主”,尽最大可能避免“以兵强天下”的两大恶性循环。
无奈的是,当国与国已身陷“其事好还”的战乱时局,为保卫家园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有时也不免被迫用“兵”来抵御入侵或守护家园,对此《老子》三十章也慎重警惕人们,要戒慎恐惧地坚守“善有果而已”“果而不得已”的用兵态度。王弼解“果”为:“果犹济也。言善用师者,趣以济难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强于天下也。”[1]78“果而已”,表示绝不主动兴兵去争强争胜,而是在“济难”情况下,才“不得已”而用兵,一旦有了渡过难关的军事效果就应当适可而止,不可掉入穷兵黩武的“取天下”诱惑中(36)王弼云:“言用兵虽趣功济难,然时故不得已后用者,但当以除暴乱,不遂用果以为强。”(《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78页)。亦即,《老子》一者主张“用兵”在于“济难”而非“征服”,这是最小化的用兵原则。二者主张对于“用兵”之“果”,要适可而止地止于当止,不可被战“果”诱惑而掉入“其事好还”的仇恨逻辑。可以说,这是“不得已”“最少化”的用兵原则。因此三十章再三提醒人们:“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勿强”,否则就会违背“以道佐人主”的共生初衷,掉入“强取天下”而导致“其事好还”与“必有凶年”的恶性循环。三十章最后结尾在:“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凡事若只是一味增强、一味扩张(“物壮”),而不留给其他事物共生共存的余地,必然会背离了多元共生之道(是谓不道)。这在《老子》看来,违背共生之“道”,而一味争强好胜的“不道”结果,只会戏剧化地加速早夭早亡(不道早已)。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第三十一章)[1]81
看似光鲜亮丽的刀刃兵器(佳兵),却有着不祥征兆而充斥杀伐之气,令人焦虑不安而让人难以亲近(物或恶之)。因此有道者立身处事,要对它们保持抵抗的间距(有道者不处)。正常情况下,君子应该“以道”来敞开最大生机,“用兵”只在极“不得已”的“济难”情况下,才勉强权用。因此三十一章使用了古代行礼空间的左右方位来强调:“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贵左”与“贵右”的修辞,具有古礼方位的空间象征痕迹,如成玄英疏解:“左,阳也,主吉,主生。右,阴也,主凶,主杀。言君子平居之世,则贵左用文。荒乱之时,则贵右用武。喻行人实智,则贵长生。权智有时而杀。”[7]212由此隐喻可见,圣者与君子的治国处事之道,应以减少干预、减少伤害为最大原则,以此酝酿最大的生长空间与安稳的生存环境。《老子》利用空间在左位的“主阳、主吉、主生”之象征,和右位的“主阴、主凶、主杀”之象征,来对比性地比拟,君子应该尽最大可能使用“以道佐人主”的“贵左”方式,来让生机之道广布流行,而只有在遭逢济难的少数特殊情况下,才“不得已”权用武力来以战止战的“贵右”方式,以求早日恢复“贵左”的生活之道。
三十一章进而强调,在莫可奈何而“不得已”用兵的情况下,也要戒慎恐惧地保持“恬淡为上”。何谓以“恬淡”态度来“用兵”?吴澄指出:“恬者不欢愉,淡者不浓厚。谓非其心之所喜好也。”[8]18据此,“恬”是指心性上的绝不嗜杀,“淡”是指行事上的绝不黩武。“恬淡用兵”的肃穆与节制,对照的是“穷兵黩武”的好战与嗜杀。不仅如此,三十一章还提醒我们,绝不礼赞战事、绝不美化胜利(胜而不美)。一旦崇拜战争英雄、歌颂军国主义(美之者),就有可能掉入对暴力杀伐的病态嗜欲(是乐杀人)。对于“不得已”用兵所带来的胜利,非但不可“胜而美之”,三十一章最后甚至主张“以丧礼处之”“以悲哀泣之”。面对两边将士的大量伤亡(“杀人之众”),要以庄严哀伤的处丧心情来面对亡者,并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的丧礼仪式,愧责自己,抚慰将士(37)河上公章句:“偏将军卑而居阳者,以其不专杀也。上将军尊而居阴者,以其专主杀也。”(《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126—127页)另外成玄英贴切地诠释这样的处丧精神:“左是吉位,右是丧位。令偏小之将,居迟左边。上大将军,处其右者。欲明虽复专命,即以死丧之礼而安处之。兵戈行处,屠害必多。故上将悲哀,愍其伤害。既非用道,死滥无辜……伤己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无辜。则心为悲愍而泣之,明非所乐也。君子善人,贵能用道,事不获已,方动兵戈。虽战胜前敌,不以为善。故素服而哭,仍以丧礼葬之。”(成玄英《老子义疏》,广文书局1974年版,第214—216页)。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1]173
六十九章的“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其中的“为主”“进寸”,意指主动兴兵、积极行动的军事扩张之侵略逻辑,然而《老子》的“不得已”的用兵,几乎“反其道而行”:在于被动(为客)、防卫(退尺)的情况下,“迫而后动”的不得不然之回应而已。“不敢为主”“不敢进寸”的“不敢”,而是对生命可贵的最大敬重,也是对暴力杀伐的最大戒慎。而“为客”“退尺”,是想要尽最大可能保留“不战”的转圜余地,希望尽量降低伤害程度而留下最少后遗症。而且就算在“不得已”用兵的情况下,《老子》仍然大不同于好战者的强势态度,而是要出之以“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的“战而无战”之吊诡态度。此即王弼所谓:“言以谦退哀慈,不敢为物先。用战犹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也。言无有与之抗也。”[1]173也就是要以“无”的修养,来转化争强斗胜的相抗逻辑。
一般人都会直觉地以为力量与力量之间的斗争,尤其在军事战争的强取过程,只能是刚强与刚强之间的对决,以为只有使用比对手更强大的力量,才能击溃敌人、摧毁对手。然而《老子》的不得已而用兵,完全不走相互摧毁的力量逻辑,它要在两军交战的相抗逻辑中,永保“不战”或“止战”的余地与间隙。以便在力对力、刃对刃的战争逻辑之外,一者转化出更大的灵活性而让对手难以测定,二者在生杀输赢的相刃相靡之外,永保一线生机的转圜余地。
最后,《老子》提醒我们千万不可“轻敌”,“轻敌”容易傲慢或轻慢地“出兵”。这既违背“为客”(不敢为主)“退尺”(不敢进寸)的“不争”态度,也会让《老子》强调的宝贵态度(“慈”“哀”等肃穆精神),荡然无存。因为轻敌代表着对可贵士兵生命的“轻用”,不管是轻敌或是轻用,都是对不可被取代、不该被侵犯的苍生性命(“天下神器”)的亵渎与侵犯,因而丧失了最宝贵、最珍视的事物。所以六十九章总结:“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相信在两军势均力敌的态势中,能够保有慈悯、肃穆的那一方(38)陈鼓应:“哀:有‘慈’的意思。说文:‘哀,闵也。’”(《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第216页),才是真能提供共生机会的最后赢家。
十二、结论:无知与幽默,提供了平坦厚实的共生平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成语,来自《淮南子·人间训》的一则故事(39)“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版,第1256—1258页)。。这则故事的核心哲理在于“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故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显然故事背后的哲理,完全相映并改写自《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1]151—152
故事主角塞翁,面对眼前“一时失马”或“一时得马”,他的认知与情绪和一般人显然大异其趣。对一般人,眼前的“失马”是明显不过的“祸”,眼前的“得马”是明显不过的“福”。而且在一般的认知里,一件事的“福”与“祸”,既能够明确区分,也可以明确认定。然而从老庄的哲理看来,“福”与“祸”的明确二分与绝对定性,反映出人们沉迷已久的偏见,所谓“人之迷,其日固久”,正是对这种认定祸福之间有明确界线、有明确定性的“绝对标准”(所谓“正”),所给予的反讽。这种“反讽”表现在塞翁失马故事叙述里的有趣发展:“失了一匹马”的事件(祸),竟延伸连结到“得了一对骏马”的事件(祸转福,妖复善),而“得了一对骏马”的事件(因祸得福),竟又延伸连结到“失了一条腿”的事件(福又转祸,善又复妖),而“失了一条腿”的事件竟又再度连结延伸到“保了一条命”(祸又再转为福,妖又再复为善)……如此“相倚相伏”地相生相化。一事件连结延伸到其他另一事件,甚至我们可由此推演,事件与事件之间具有辗转相因又连环相扣的暧昧关系。眼前这一事件(event),绝不只是自我封闭的一件事,也绝不只是定格在眼前的一件事,而是“事件对事件开放”“事件连动事件”的“转而相生,其变难见”的未定过程。可以这么说,任何“事件”的内部都必然有待于外在的敞开与连结,或者说,任何的内在性都必然依待于外在他者性深藏其中。因此,当事件被放在时间历程和空间绵延的“化(事物不停转化)”的角度来观察时,身为极其有限的观测者“人”,对事件是祸、是福、是善、是夭的任何判断,都未免“太早计”“太武断”,太过认真地想要“统一”事件的“不一致性”,太过严肃地想要“终结”事件的“未完成性”(40)对于老庄的“物化”与“幽默”的关系,安乐哲(Roger T.Ames)有一洞见可以参考:“万物之转化蕴涵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总是有无数可以替代的心境,它们对一个人目前的心态的终结性构成了挑战;第二,经验的连续性保证一个人能够实际经历无数这样的心态。以哲人的姿态承认这一事实,是道家最高明的幽默的源泉。”《自我、幽默与物化》,彭国翔编译《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376—377页)。安乐哲的哲人承认姿态,呼应于本文所强调“承认无知”的姿态。。
正是这种如实面对事件“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转而相生,其变难见”的实情,使得《老子》(故事中的塞翁)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且不敢于遽下定论,更不敢于提出终极解决问题的绝对常道。《老子》这种“孰知其极”的承认“无-知”,与其说是一种“消极”立场,不如说是一种“幽默”态度。对每一件表面看似清晰、简单的事件或立场,都能够保持“化不可极,深不可测”的开放性,因此产生一种“永不遽下定论”的放松感与幽默感。因为每当遽下定论,没多久就会观察到“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福之为祸,祸之为福”的自我矛盾与反讽。用《庄子》的概念来说,刚刚定下解决是非问题的“有封”“有常”之道,很快就会遭逢到自己的“滑疑之耀”(自己滑走而跌了自己一跤)(41)“滑疑之耀”出自《庄子·齐物论》,它和“环中”“两行”,共同构成了《齐物论》对“儒墨是非”的转化之道。其实,“滑疑”通于“滑稽”,本就隐含有幽默意味。你的立场,你的自以为是,你自以为的仁义,都可能自我滑走甚至颠倒相反,这个时候自己会被自己给滑了一稽,自我会被自我给幽了一默。任博克曾对“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做出极具理趣的英译:“Thus the Radiance of Drift and Doubt is the sage’s only map.He deploys no single definition of what is right,but instead entrusts it to the everyday function of each thing.This is what was meant by ‘using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Obvious.’ ” Zhuangzi:The Complete Writings,p.16。另外也可参见任博克对“滑疑”的精采解读:“‘滑’就是不稳定,一直在变化,随时滑走到另一端;‘疑’就是随时不肯定,不‘为是’,不定义是非,不封彼是,不肯定其为谁何。又滑又疑,互立互破,因是因非,谓之两行,也谓之‘滑疑之耀’。”参见任博克、林明照、赖锡三《〈齐物论〉的儒墨是非与两行之道——吊诡、反讽、幽默的不道之道》(《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6页)。。
人们总是自以为“福是福”“祸是祸”,“朝三暮四”较好,或“朝四暮三”较好,这些看似明显不过的认知和喜怒,对于老庄而言,都不能免于“成心之知”和“前识之见”。“成心之知”不是一无所知,“前识之见”也不是一无所见,但它们也都不能免于一偏之知、一曲之见。而当人们习惯于“自是、自见、自矜、自伐”而“以偏概全”,通常就容易误以为自我拥有了“常道”“常名”,因此难以对他异之道、之名,有所宽容而如实对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吊诡观察,以及由此而来的“孰知其极”之承认无知,主要不是主张:所有事物都是相对而未定,因此所有行动都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这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理解,并未真正进入“化不可极,深不可测”的未决定性与不可测性。真正深入其中,会把“成心之知”和“前识之见”的单行道给予宽松,并对“事件”发展成为其他可能性,甚至自我相反性,既保持宽容又保持兴味,因为那些看似与我相异,甚至相反的观看视角,严格讲,都在自我立场成立的同时,已经被我的“内在待外性”或“内在他者性”给包其中了。用《齐物论》的话说,我的立场从来都无法孤立封闭在纯粹的“我是”之中,我的立场同时间和不同立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地“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地连环相抱在一起(42)“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庄子集释》,第66页)另外关于《齐物论》的“为是”与“因是”之重要差异,以及“因是”对“果是”之解构,可参见笔者《公民道家与深度歧见——以《庄子》的〈齐物论〉和〈人间世〉为思考》与《〈齐物论〉的天籁物化与吊诡两行》两文。。据此,无人可以超然决定是非之“正”而永远终结是非,人人都必须接受“孰知其极”的自我反讽与承认无知。
或者说,人人都无所逃于被自己幽了一默。原因无他,滑疑与幽默,来自于人人总是“成心自师”地被“前识之见”给严肃地拖着走(set up),但也都得面对“化不可极,深不可测”对“自以为知”的“我”给予打脸(punch line)。“成心”与“前识”总是对自己的“可道”“可名”十分慎重其事,严肃以对地将自我当成大写的“常道”“常名”,然而每一事件其实无所逃于“转而相生,其变难见”的“不知其极”。正是对这种“不知其极”的彻底“无-知”之领悟,能将“常道”“常名”的严肃性,给予回归“可道”“可名”的可笑性。也正是这种可笑,带来了严肃的释放,也正是这种释放严肃之病的幽默可笑,缓和了彼我歧见的敌意。
幽默跟共生如何连结?首先,“滑疑之耀”让所有事件和立场,都无法站住自身太久。其次,事事物物“转而相生”的结果,将促使立场与立场之间的互立互破。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气氛或转机?用《齐物论》的概念说,那就是你不再能够绝对确定、绝对坚持、绝对固执地认为自己拥有“果是”“果然”(43)“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庄子集释》,第108页)。虽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哲学(如形上学)、宗教(如唯一真神)会许诺类似“果是”“果然”的严肃之道,那就像《齐物论》所反讽的“儒墨是非”,儒墨两家也曾相信自己可以提供终极解决“天下大乱”的常道常名、果是果然,所以不能不对自己所认定的“常道”“果是”严肃以对,不能不对异端邪说的“外道”“果非”给予消除或同化。大异于此,《齐物论》的中空道枢,以运无穷,它虚化了任何大写常道,并让自己“虚而待物”地成为了众多可道可名的无穷通道之“枢”。“非-常道”的去形上学化、去严肃化,许诺了可无穷实验“行之而成”的方便之道。人们可不断尝试行走某条可行之道,但都无法一立永立、一定永定。相反地,任何观点与立场都可能随着新脉络而自我瓦解,使得原先自以为的“果是果然”遭受“滑疑之耀”的自我反讽。而这种瓦解、滑走或反讽,同时也是打开另一道方便法门的新开端。
《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与祸都不是一定永定的事件本质,两者都因循故事脉络而“滑疑”未定。祸福相依,彼是不定,这个时候的“无-知”,转化了自以为“知”的固定之福之祸之是之非的“定见”与“偏执”。这种“无-知”的领悟,会对人们所笃定的严肃之道,偏执的终极解决,给予极大的能量释放,提供宽广的共生平台。然而“幽默”虽然看似带有“宽容”味道,但宽容还是过于严肃,而且可能还以“我”作为能给予宽容的主体。而幽默则是先领悟自身的彻底“无-知”,先看到自己同样不能免于“朝四暮三,朝三暮四”的可笑与好笑,因此先释放了自我对事件的绝对裁判与严厉谴责,转而对自己和他人同样“无知却又自以为知”,保持着幽默以对的兴味与宽松(44)正如安乐哲所指出:“对于讲齐物的道家来说,在逗趣者与可笑的东西之间,没有根本的界限。幽默必须以同等为基础,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产生许多笑话。”《自我、幽默与物化》,《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374页)。。正是这种对自我与他人都平等地宽和以对、从容以待,能为人类搭起了一座最平坦、最厚实的共生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