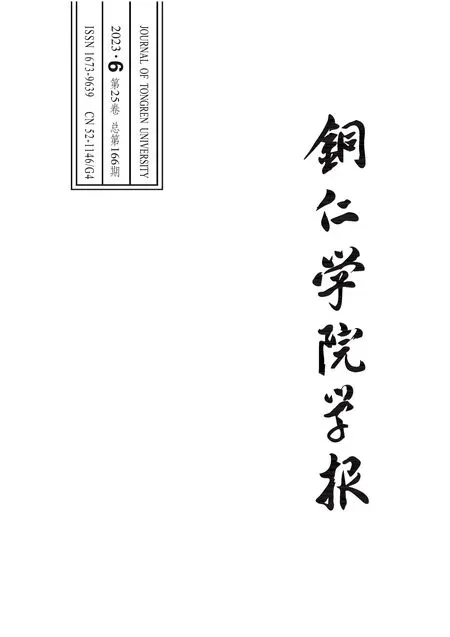《佩文韵府》的纂修与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建构
2023-02-20黄金灿
黄金灿
【梵净古典学】
《佩文韵府》的纂修与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建构
黄金灿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佩文韵府》的纂修为观照清代官方诗学话语建构的情形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场域。它在清初兴起的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下展开,既是这一浪潮的产物,又是对这一浪潮的强化。其展开过程也是多重诗学话语融通的过程,其中尤以康熙皇帝与查慎行的诗学话语融通最具代表性,表明即便是在清官方全程“干涉”的官修图籍范域,个体的文化活动仍然可以具有相当程度的主体性。而纂成的《佩文韵府》作为一个官方诗学话语的载体,颇为集中地体现了个体诗学话语的官方化,其刊刻与流传过程并没有太多官方权力的强制介入,反映了一种官方诗学话语发挥影响的积极模式。
清代; 诗学; 官方话语; 《佩文韵府》; 图书纂修
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最早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权力与话语的复杂关系经由福柯开创性的研究,一度成为备受热捧的文化观照新视角。当然,这一命题可以运用于文史领域来观照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致力于明清以降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王汎森先生就曾借助福柯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观念来研究清代的政治与文化,其《从曾静案看18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等文都是努力探究“权力在微小的、隐秘的空间中作用的状况”的力作。[1]9不无遗憾的是,虽然这些力作面对的文化现象相对于福柯著作而言是全新的,但因其理论取向的“福柯化”而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对官方价值的有意消解与对个人主体性的无形淡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文化无主体性”视作“传统中国的常态”。然而,官方话语果真只能带来“猜测”和“恐惧”吗?个人话语果真只能“毫无主体性”地“随幡而动”吗?[1]430事实上,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当权力话语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一致时,它也理当能产生某些积极作用,而且一旦深入到更为微观的层面就会发现,权力话语的施受关系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发生于康熙朝后期的《佩文韵府》纂修活动正好提供了一个权力话语运行的微观场域,加之《佩文韵府》与诗学具有天然的互动关系,故而对该场域的观照可以反映出清代官方诗学话语建构的诸多面相,藉此也可以窥见官方话语的某些积极因素以及个人维持自身主体性的努力。此举不是为了给清王朝的文化专制翻案,而是为了反思话语权力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有限性。
一、语境:知识的穷尽式集中浪潮
清代历史发展到康熙朝(1661—1722),文化界迎来了一场对文化知识进行大规模搜集整理的浪潮。由于这一浪潮中的诸多图书纂修活动都以对相关知识的穷尽式汇集为职志,故而不妨即以知识的穷尽式集中浪潮之名来指称之。《佩文韵府》就是在这一浪潮中纂成的一部具有穷尽式集中特征的大书。该书的纂修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成于康熙五十年(1711),全书四百四十三卷。书成数年之后,康熙五十五年(1716)又加以增修,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增修工作完成,由于原书已经雕成刊出,无法将增修成果添入已经成型的书版,故另成《佩文韵府拾遗》一部一百十二卷。《佩文韵府》与《拾遗》虽然在形式上是先后纂成的两部书,实际上是一个系列。可以说,《佩文韵府》的真正成书时间不是康熙五十年,而是康熙五十九年。五十九年,康熙朝即将进入最后阶段,《佩文韵府》在这个时段正式完工,暗示着康熙朝的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逐渐接近尾声,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康熙朝与诗学相关的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的最后一个波峰。
关于康熙朝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的具体情况,可以从官修书籍的命名方式中看出。例如《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大清会典》《朱子全书》《广群芳谱》《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分类字锦》《古文渊鉴》《全唐诗》《全金诗》《历代题画诗》等书题名中的“汇纂”“会”“全”“广”“府”“渊”“类”“历代”等字词,都指示出对相关专题内容穷尽式容括的宗旨。上述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编纂形式无论是题作敕撰、敕编还是敕刊,都是直接受命于康熙皇帝,属于名副其实的官修书籍。由于具体内容不同,编撰诸书的具体作用自然不同,但编撰诸书的终极目的却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力图通过穷尽式集中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思想、体量正大的官方权威版本。这一终极目的在诸书的序文中都有直接的披露。这些“宣言”主要反映出康熙朝知识穷尽式集中浪潮的三个基本面向:
第一,它们直接反映出康熙朝对知识“求全责备”的主观意图。散见于诸序中的“广大悉备”(书经传说汇纂序》)[2]6765、“无所不隶”(《大清会典序》)[2]6844、“攟摭荟萃”(《广群芳谱序》)[2]6897、“千有余年而集其大成”(《渊鉴类函序》)[2]6909、“蔚然萃群书之秀”(《骈字类编序》)[2]6910、“成册府之钜观,极图书之大备”(《古今图书集成序》)[2]6911等一众关键词汇或语句表明,康熙朝的确出现了一场知识的穷尽式集中浪潮,而且这一浪潮对雍正、乾隆这两位继承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仔细分析上述关键词汇或语句,能够发现它们都具有通观全局的眼界,单纯用封建帝王的好大喜功来解释之无疑会把问题简单化。
第二,它们表明康熙朝对知识的穷尽式集中并不是一般理解上的“寓目辄书”式的穷尽,而是有选择、有目的地进行穷尽。康熙朝对知识的穷尽式集中分两步:第一步是对某一领域或专题的知识进行全面调查;第二步是在尽可能全面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官方立场,只有符合官方立场的知识才会被真正地加以穷尽式集中。诸书序文中可以佐证上述“两步走”策略的关键词句有:“惟择其言之当于理者”(《春秋传说汇纂序》)[2]6784;“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广群芳谱序》)[2]6897;“增其所无,详其所略;参伍错综以摛其异,探赜索隐以约其同”(《渊鉴类函序》)[2]6907;“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历代诗余序》)[2]6959;等等。以上关键语句固然有提供文献学意义上的善本这一层含义,但对官方来说,真正的“善本”不仅不能于己有害,而且最好于己有利。所以,官修书籍命名时标举的“汇纂”“广”“渊”“历代”“全”等词汇,并不是单纯材料意义上的穷尽,而是对经过过滤后的“正确”内容的穷尽。换言之,“全”中隐含着“选”,求第一步的“全”,是为了在“选”中更好地实现第二步的“全”。
第三,它们显现出清代官方将知识进行穷尽式集中的终极目的。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官方”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对知识进行穷尽式的集中?如果从话语理论视角展开思考,对这一问题可以如是回答:谁穷尽式地掌握了知识话语,谁就能将话语权力最大化地集中于自己的手中。当然,清朝官方不会讲得如此显露,他们有一套话语来解释将知识进行穷尽式集中的终极目的。例如“尊崇经学、启牖万世”(《书经传说汇纂序》)[2]6765、“右文稽古,表章圣经”(《诗经传说汇纂序》)[2]6769、“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朱子全书序》)[2]6876、“贯三才之道而靡所不该,通万方之略而靡所不究”(《古今图书集成序》)[2]6911等等,都是这套话语中的典型表述。上述关键话语表明清代官方的文化行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其话语表达中所使用的启牖万世、通究万方等“大词”,直接表达了他们掌控并运用文化力量的终极意图。
一方面,启牖万世、通究万方等终极文化理想,并非个人凭一己之力能够实现。个人的能力必然会受到个体生命本身带有的局限性的限制,在时间、空间、物质条件等许多方面都不可能超过群体的力量。而能够充分调动各方面资源的官方则不同,往往能够相对轻松地克服物理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的视角而言,知识的穷尽式集中是学术研究一贯的目标,康熙朝的集中浪潮具有推进文化研究的正面价值。当然,清代官方不会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纯粹的学术探索,他们还有掌握文化话语权力的实际政治需要。即便康熙朝的官书修纂看似都是缘起于康熙皇帝的个人学术兴趣,但是当他一旦将纂书意图以“敕撰”的形式交付文官系统具体执行,那么他的个人兴趣就转化成了官方的集体行为,进而具有了官方效力。《佩文韵府》的纂修作为一个官方话语场域,不仅被清代官方文化建设的话语场域所涵盖,更被清朝统治权力合法性地巩固与维护的话语场域所涵盖。在这种逐渐放大的话语场域中观照《佩文韵府》的纂修,能得到的启发就不会仅限于这一图书修纂活动本身。
二、传统:个体诗学话语的官方化
清初思想文化界涌动着一场争夺文化话语权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双方代表分别是清朝官方与明朝遗民。顾炎武提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3]557之说,力倡“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558,显然是将矛头直指清朝入关之后对汉文化传统造成巨大冲击的现实。在文学思想上,他还明确主张文章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3]775他又呼吁汉族文士要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议之矣。”[3]777可见,他极力地提倡对文学伦理道德内容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文学直接介入现实的政治功利性的重视。
面对这样充满政治斗争意味与反抗民族压迫情感的话语,清朝官方必须有合适的应对之策。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当然是用粗暴的武力手段进行镇压,但是因剃发与反剃发而引起的屠杀与抗争已经证明,简单粗暴的武力手段并非上策,反而会加深民族矛盾与仇恨,破坏社会稳定,破坏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这种手段,在政权逐渐稳定,全社会都渴望和平环境的康熙朝更是不合时宜。在此背景中,最好的方式就是由皇帝亲自带领一批文人把代表正统的文化话语权夺过来。在这场斗争中,康熙皇帝想做的不是军事统帅而是文化统帅。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塑造成汉族文化的代言人,用汉族文化对抗汉族文人。大力提倡科举、广开博学鸿词科与频繁纂修各类大书都是重要的手段。在修书方面,清朝官方有着巨大的优势,无论是财富、人力还是藏书,都不是个人或某个群体能够对抗的。事实证明,康熙皇帝频繁地大规模组织人员纂修各种大书,不仅成功地抢夺了文化话语权,还在纂书过程中吸纳了大量有实力有影响的汉族文士,从内部瓦解了对手的阵营。
康熙皇帝对汉族传统文化话语的官方化是比较全面彻底的。首先,通过经学书籍的纂修,成功地将历代都具官方性质的经学话语进一步清朝化;其次,通过《明史》的纂修,将民间各种私修《明史》的行为官方化,同时也是对官方史学传统的清朝化;最后,通过多种文学总集、选集、工具书的纂修,对能够直接影响人心的文学进行官方化,当然这同时也是对文学的清朝化。清朝官方为什么会对字书、韵书、类书这样的工具书如此重视?主要是因为工具书是任何文化爱好者、工作者、考生都必须频繁使用的书籍。像《佩文韵府》这样的书籍,既有韵书功能又有类书功能,既能当作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工具书,又能当作考试的参考书,只要能够严格把关,过滤掉不利于统治的内容,注入有利于统治的内容,其影响范围与力度都将是相当巨大的。在康熙皇帝已经将各类大书修纂完备之后,他必然想将这些成果综合起来,而《佩文韵府》这样具有类书体例特征的书籍,也能部分满足这些方面的要求。因此,《佩文韵府》纂修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纂修这样一部大书来贯彻清朝官方的文学尤其是诗学话语。
康熙皇帝在《佩文韵府序》中说:“尝谓《韵府群玉》《五车韵瑞》诸书,事系于字,字统于韵,稽古者近而取之,约而能博,是书之作,诚不为无所见也。然其为书,简而不详,略而不备,且引据多误,朕每致意焉。”[4]从这段自述看来,《佩文韵府》的纂修似乎源于康熙皇帝的一时灵感迸发。事实上,此书的纂修却体现出清朝官方将传统个体诗学话语“官方化”的努力。《佩文韵府》在《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的基础上纂修而成,这一事实体现的不仅是康熙皇帝对这一两部书的态度,更是对悠久的韵书型类书编纂传统的靠拢。《五车韵瑞》是明代凌稚隆所编,而它是仿照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纂成。其实在它们之前,中国古代就出现了一系列类似体例的书籍,尤其是两宋时期,同类书籍的数量与规模已经蔚为壮观。
据笔者考察,两宋时期已出现的同类书籍有张孟《押韵》、刘羲叟《刘氏辑历南北史韵目》、杨咨《歌诗押韵》、袁毂《韵类题选》、李滨老《李杜韩柳押韵》、郑潾《经语韵对》、钱讽《回溪先生史韵》、王百禄增辑《书林事类韵会》、裴良甫《十二先生诗宗集韵》、楼君秉《三家诗押韵》等等。可见,中国古代编撰韵书型类书的传统并不始于元代阴时夫的《韵府群玉》,两宋时期已经有很多的同类著作,而且动辄数十百卷的大部头书籍已经出现,它们与《佩文韵府》一样,主要是为诗歌创作的押韵、用典与句法锤炼服务。虽然两宋时期出现的这些著作大多已久佚不存,但是它们却对后来的同类著作产生很大影响,是构成韵书型类书传统的重要一环。宋濂《韵府群玉后题》曰:“《韵府群玉》一书……乃因宋儒王百禄所增《书林事类韵会》、钱讽《史韵》等书,会粹而附益之,诚有便于检阅。”[5]①宋濂已看出宋代同类著作对阴时夫《韵府群玉》的纂修具有直接影响。但是,将这一传统上溯至两宋时期并未到达源头。
事实上,早在中唐时期,颜真卿就组织同道编纂了一部影响甚大的同类著作《韵海镜源》。《封氏闻见记》卷二述之甚详:“天宝末,平原太守颜真卿撰《韵海镜源》……解释既毕,征九经两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编入本韵,爰及诸书,皆仿此。自有声韵以来,其撰述该备,未有如颜公此书也。”[6]可见,以“撰述该备”著称的《韵海镜源》正是一部将众多书籍材料按韵编排的韵书型类书。甚至在比唐代更早的南北朝时期,就已出现《群玉典韵》等启发《韵海镜源》的书籍。《群玉典韵》五卷,撰人不详,姚振宗曰:“此则专为诗赋所须,与前《韵林》相似,亦如颜真卿《韵海镜源》之类。或谓排韵隶事始于《韵海》,窃谓始于是书。”[7]可见《群玉典韵》在当时的韵书中别出心裁、独树一帜,已经具备后世“韵藻”的内容,开始出现集韵书与类书于一体的特征。此书问世于唐前,远早于《韵海镜源》,其“专为诗赋所须”的“排韵隶事”之文学功能,更是对后世类书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可见,与《佩文韵府》性质相同的书籍编纂传统有着悠久而清晰的脉络,甚至一直可以上溯到韵学初创的南北朝时期。
康熙皇帝组织纂修的《佩文韵府》是历代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精密程度最高的,它标志着此类书籍以“私修”为主的传统彻底官方化。从此,这类书籍从原本用于表达个人诗学兴趣的载体成为表现官方诗学话语的载体。《佩文韵府》在康熙朝末期的纂成,标志着清朝官方在经学、史学、文学等各领域建构系统的文化话语权目标的全面实现。随着包括《佩文韵府》在内的一系列官修书籍的纂成,清朝官方的文化话语已经成为当时整个文化界的强音,遗民团体拯救文化之天下的目标随之失效。由于他们心系的文化传统不仅没有沦亡,反倒变得比历史上更加强劲,故而他们为自己塑造出的“文化遗民”形象已消失于无形。要而言之,《佩文韵府》的纂修对历代“韵书型类书”编写传统的整合、集成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三、实践:主要参纂者的诗学话语融通
《佩文韵府》作为一部韵书型类书,主要是为诗歌创作服务,故而它的编纂必然体现着某种诗学话语。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康熙皇帝的诗学观念,他的诗学观念作为官方诗学话语的代表,势必会灌注到纂修的各个环节,每一个参修人员都不得不执行他的指示,甚至会主动迎合、放大他的观念。与此同时,虽然康熙皇帝的诗学观念会以压倒性的强制力量影响其他纂修人员,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其他纂修人员也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们能够有资格进入纂修人员名单,本身就表明他们在诗歌创作或诗学研究领域有所造诣,并早已形成或基本形成自己的诗学观念。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纂修人员,忠于皇帝的意见是一个基本的客观要求,而具有自己的诗学观念又是一个必须具备的基本主观条件。如此一来,客观要求与主观条件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张力。在这种情况下,《佩文韵府》的纂修如果想要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理念,就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参纂者的诗学话语融通;换言之,《佩文韵府》纂修实践的展开过程,实际上就是包括康熙皇帝在内的全体参纂人员的诗学话语融通过程。
通过敕撰书籍的形式,帝王可以凭借独有的居高临下的势位自上而下地贯彻自己的文学观念,有顺风吹毛、乘高决水之势。当然,修书官并不只是机械地执行指令,他们的文学观念也会反过来影响皇帝,这种影响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的?可以查慎行为例探讨之。查慎行在《佩文韵府》纂修过程中的作用颇为关键。他是康熙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有很高的诗学造诣,诗歌创作深受康熙皇帝赏识。他不仅一度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官,在《佩文韵府》的编纂中,还担任“纂修兼校勘”的职责。可以说,无论在诗坛声望与诗学水平上,还是在实际的纂修工作中,他都堪为由数十人组成的纂修队伍的代表。
在《佩文韵府》的编纂过程中,查慎行作出了关键贡献。《查慎行文集》中收录了三篇文章——《武英书局报竣奏折》《佩文韵府告成公请御制序文奏折》《武英书局报竣回奏折子》,都是专门向皇帝汇报《佩文韵府》纂修事宜的专门公文,这三篇奏折都由查慎行撰写,充分反映了查慎行在纂修中的重要作用。《武英书局报竣奏折》:“《韵府》一书,尤宸衷所注意。钦颁体例,御定规模。……命查慎行、钱名世、汪灏住武英殿,分纂上、去、入三声(按:本奏折另载,平声全部至上声五尾已由孙致弥偕张元臣、赵晋等先期纂出),大约不过一半年间可以竣事。……臣慎行等三人凛遵圣训,将未经编辑自六语起至十七洽止,共七十一韵分为三股……。”[8]19-20康熙皇帝阅后派人传话:“这折内修书人员,谁修的多?谁修的少?走了几年?谁勤?谁惰?可令查慎行、钱名世、汪灏等查明,即注在名单之下,再奏。”[8]22对于康熙皇帝关心的问题,查慎行等人又回奏道:“臣慎行等三人,编辑既定,派令缮写,各限页数,每日交收……不容推避偷安,亦不令此多彼少。”[8]22-23在上述三篇奏折中,共有五次提到编纂负责人,都是以查慎行起首,可见查慎行确实是《佩文韵府》纂修的主要实际负责人。
虽然康熙皇帝对查慎行颇为赏识,查慎行本人在《佩文韵府》的纂修过程中也尽职尽责,并全力配合康熙皇帝的指挥,但是他们在诗学理念上其实是有冲突的。康熙皇帝非常推崇唐诗,不仅下令编纂了《全唐诗》,还组织人员编纂了一部体现自己唐诗品味的唐诗选本,即《御选唐诗》。然而对于宋诗,康熙皇帝并没有表现出这么大的热忱。在他敕撰的《御选四朝诗》中,只是将宋诗与金、元、明诗并列,虽然对宋诗的成就予以了肯定,但可以明显看出,在康熙皇帝看来,如果唐诗属于诗歌的第一等级,宋诗只能与金、元、明诗一起算作第二等级。查慎行则不然,他一向推崇宋诗。对于这些,清人已经形成了共识。例如,四库馆臣认为他的诗“核其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观其积一生之力,补注苏诗,其得力之处可见矣”[9];沈德潜认为他“所为诗得力于苏,意无弗申,辞无弗达”[10];等等。清人的这些论述无不是对查慎行诗歌得力于宋诗的强调。当然,查慎行推崇宋诗,但他也不主张只学宋,不学唐,而是主张“唐音宋派何须问,大抵诗情在寂寥”(《得川叠前韵从余问诗法戏答之》)[11]623,还曾告诫友人“知君力欲追正始,三唐两宋须互参”(《吴门喜晤梁药亭》)[11]85。前者意在强调不要强分什么“唐音宋派”的畛域,后者则明显将“三唐两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查慎行提倡“三唐两宋须互参”,与康熙皇帝的冲突在于,康熙皇帝虽然不排斥宋诗却将它放在第二等级,而查慎行却将它放在了与唐诗一样的第一等级。查慎行提倡唐宋诗互参的目的很明显,不是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对唐宋诗的同时提倡,其实主要是为了提高宋诗的地位。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查慎行确实也认为唐诗的地位非常高,事实也确是如此。他在《初白庵诗评》中评论宋诗名家的作品,经常将他们的诗法渊源上推至唐诗。这样一来,查慎行的诗学观念虽然与康熙皇帝有冲突,但是也有巨大的交集,他们的冲突不是“有唐诗无宋诗”或“有宋诗无唐诗”的绝对对立,而是对唐宋诗的重视程度问题。要而言之,有不同,是他们的诗学话语需要融通的原因;有重叠,是他们的诗学话语能够融通的前提。
从《佩文韵府》纂修项目成功结项,查慎行作为主要参与者收获的荣誉与物质等奖励的实际结果来看,查慎行与康熙皇帝的诗学观点事实上实现了融通。这在《佩文韵府》这部书里得到很好地体现。郑永晓先生用大数据思维对《佩文韵府》引用诗人诗作的研究表明:唐代诗人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杜甫,其次为白居易、韩愈、李白、元稹,宋代诗人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苏轼,其次为陆游、范成大、欧阳修、梅尧臣;被引用超过万次者,唐代三人,为杜甫、韩愈、李白,宋代一人,为苏轼;同时,唐宋诗的影响度也被计算出来,唐诗的影响度为宋诗的近2倍。[12]132郑永晓先生总结说:“唐诗优势明显。但是宋诗的个别作家如苏轼和陆游,在康熙时期的热度确实很高,尤其是苏轼的风头,甚至有比肩杜甫之势。”[12]132这样的结果表明,查慎行对宋诗,尤其是对苏轼、陆游诗歌的推崇,极有可能在《佩文韵府》的成书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一结果虽然远没有达到查慎行欲令唐宋诗齐头并进的理想状态,但是宋诗的地位已经得到明显提升。
尤其是陆游诗歌在这部地位尊崇的官方文本中能够获得仅次于苏轼的“出场率”,其背后所隐藏的诗歌文本接受性质的转化颇值得注意。蒋寅先生曾指出,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曾非常流行:“从天启到康熙末年整整一百年,陆游诗风都长盛不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13]并通过详实的考证,展示出其时陆游诗歌的流行已然达到“家置一编,奉为楷式”(李振裕语)与“人人案头无不有”(叶燮语)的具体情形。[13]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情形所反映的仍主要是诗学发展史内部的诗学走向问题,而《佩文韵府》的大规模收录却使这种原本流行于文学群体间的话语转化为强有力的官方话语。当然,这肯定与陆游诗歌的体量巨大有关,但他的出场率依旧没有超过苏轼,表明《佩文韵府》收录诗句并不是完全取决于诗人作品的数量。可以想见,查慎行虽然没有直接与康熙皇帝的诗学观念发生冲突,但是他在实际执行《佩文韵府》纂修工作的过程中,却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如此一来,推崇唐诗但不排斥宋诗的康熙皇帝的诗学话语就与推崇宋诗但又重视唐诗的查慎行的诗学话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通。一旦这两个关键人物的诗学话语被证明能够融通,那么其他参纂者的诗学话语即便有冲突,但基本也可以达成平衡。当然,这样的平衡过程肯定更复杂,值得继续深入细致的探索。
四、效果:官方诗学话语的积极模式
纵观有清一代,官方在文化领域施加影响的模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对有利于统治的文化话语进行推广,典型的手段是拉拢文士组织修书,这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影响模式;一种是对不利于统治的文化话语加以禁止,典型的手段是兴起“文字狱”并禁毁书籍,这则是一种消极的影响模式。《佩文韵府》的纂修是清代官方诗学话语的一次集中表达,也很好地体现了官方诗学话语的积极影响模式。根据现有材料来看,《佩文韵府》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发挥积极影响:第一,《佩文韵府》的纂修活动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它本身就是对官方诗学话语的有力宣传,参纂《佩文韵府》既被视为一种荣誉也被视为对参纂者能力的认可,清代有相当数量的诗歌、传记、墓志、地方志都对相关人员参与编纂《佩文韵府》的经历津津乐道。第二,康、雍、乾三朝,尤其是康熙朝为犒劳参纂者与乾隆朝为鼓励献书者而进行的赐书活动,也被视作一种荣誉为各种文献反复记载,这又是一种扩大《佩文韵府》影响的形式。第三,不少文献都记载了《佩文韵府》的刊刻、销售情况,而刊刻、销售使得官方诗学话语在《佩文韵府》的流通过程中逐渐产生影响,它是《佩文韵府》可能发挥广泛影响的最重要形式。
在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下精心刊刻的初印本,到乾隆中叶尚有大量库存。乾隆三十九年(1774),永珹等在一份关于内府藏书的清查报告中说:“惟预备查用陈设之书……现在存积甚多。又有自康熙年来臣工陆续奏进之书,向例不在通行之列。如《佩文韵府》,现存一千九十余部。”[14]191福隆安在另一份报告中又提到:“此项《佩文韵府》,原有一千九十六部。”[14]194可见此书虽然名噪一时,但由于种种原因,初刊本的流传并不算广。由于《佩文韵府》的初刊本流通并不顺利并导致大量的库存积压,乾隆皇帝遂有意进行细致的市场调查以便将这些书籍顺利出售。永珹等提议说:“臣等公同商酌,请将前项书籍,无分外进内刊,凡数至一千部以上者,拟留二百部……概予通行,俾海内有志购书之人,咸得善本。”[14]191但这样的大书造价既已不菲,售价当然不会太低,导致这批《佩文韵府》并没有出现海内有志购书之人争相购买的热潮:“再,查此书共计八百九十六部,自本年五月奏准发售之日起,迄今仅售去四十四部。”[14]196永珹的报告写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福隆安的报告写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相隔一个半月,共售出44部,福隆安用一个“仅”字暗示了这项生意的惨淡。
乾隆皇帝想把内府藏原刊本《佩文韵府》销售出去是后来的事,一开始还是以鼓励需要者自行印刷为主。据素尔讷《学政全书》卷四载:“乾隆三年奉上谕:从前颁发圣祖仁皇帝御纂经史诸书,交直省布政使敬谨刊刻,准人刷印,并听坊间刷卖。”[15]19可见乾隆皇帝非常鼓励民间自行刷印、翻刻。其中内府藏《佩文韵府》与《拾遗》也进行了重新刊刻,并且乾隆皇帝还命令将书版“存贮书局”:“至内廷书籍,外间士子无不群思观览。照从前颁发《御选语录》等书之例,将武英殿各种书籍,交与崇文门监督存贮书局,准令士子购觅,以广见闻。”[15]20另外,《学政全书》还载:“武英殿有存贮书籍十九种,俱系从前臣工遵旨刊刻之书。其书版存贮各省臣工之家,亦应开单行文各省督、抚,转行各该处,听坊贾人等广为刷印。并准其翻刻,以广流传。”[15]20以上种种推广、鼓励政策,可谓细密周祥。如此一来,民间所见《佩文韵府》的版本也就日益增多。
据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三记载,八千卷楼所藏《佩文韵府》有苏州刊本、广州刊本、石印本三种,《拾遗》有京板本、广东刊本、石印本三种。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五自叙购书经历时提到:“书凡五种……索白镪六十四金,急欲归之,而议价再三,牢不可破,卒以京板《佩文韵府》相易,贴银十四两,方得成此交易。”[16]从黄丕烈和丁仁的记载可知,《佩文韵府》和《拾遗》都有“京版”,这应该是指北京坊间印刷的版本,不是指内府初刊本,因为内府初刊本由于相对更加珍贵难得,清人提及时一般都会特意强调。
至于最早的广东刊本当是始于番禺人潘仕成,金武祥《粟香随笔》卷六载:“潘氏所刊有《佩文韵府》《海山仙馆丛书》,又石刻、碑帖百数十种,皆称于时。”[17]史澄《广州府志》亦载:“(潘氏)好刻书帖,尝翻刻《佩文韵府》一百四十卷,《拾遗》二十卷。”[18]邱炜萲也提及:“《番禺县志》称潘德畬方伯重刻《佩文韵府》,嘉惠士林,欲读中秘书者,皆得家置一编,洵巨观矣。亦其时沪上未传泰西照相石印法,故殿版大集,难于赀购,若今时之《佩文韵府》不过六十整册,藏之巾箱而已足矣。”[19]据上可知,潘仕成重刻的《佩文韵府》就是广州刊本,而所谓“石印本”乃是以“泰西照相石印法”印制的版本,这种方法印制的书籍更易携带、价格也更低廉。
石印本的出现使《佩文韵府》的流传更为方便。据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记载:“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陆续印岀……《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20]可以想见,近代石印本的出现非常有利于《佩文韵府》的传播。虽然后来《佩文韵府》的价格已经下降,但还是有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购买,例如战乱。据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五记载:“同治甲子春适贵阳,值黔中久乱,无人购求书籍。《佩文韵府》价祗十金,客无顾问者,以其艰于驮载耳。”[21]此例表明,由于战乱期间运输不便,导致《佩文韵府》这样的大书即便价格大降也无人愿意购买。
更重要的是,《佩文韵府》作为一部韵书型类书,它并不太受重视根柢之学的大学者青睐。例如曾国藩在与袁芳瑛的书信中说:“尊处广搜群籍,如遇有殿板诸善本及国朝名家所刊之书,凡初印者,概祈为我收买。惟《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等,向非所好,不必购之,此外殿板书初印者,多可取也。”[22]康、乾二帝非常重视的《佩文韵府》,一向谨慎的曾国藩却对其流露出轻蔑之意,主要是因为它属于与根柢之学相冲突的被视作“兔园册子”的类书。另外,《佩文韵府》虽可作为考试参考书,但由于部头太大,举子们真正使用的却是《佩文诗韵》这样简便易携的册子。正如《应试诗法浅说》所言:“韵书所收字数,详略不同……《佩文诗韵》出,乃集韵学之大成,应举定本,恃此为指南矣,他本未可为据。”[23]因此,若是单从刊刻流传的情况来判断《佩文韵府》的影响,很自然会得出它的影响并不太大这样的结论。不过,通过刊刻流传情况来判断它的影响并不是本文全部目的,本文更想通过这种考察进一步展示官方诗学话语发生影响的积极模式:这种积极模式除了通过将修书、赐书塑造为一种荣誉,藉以达到宣传效果外,还主动将修成的书放进流通领域,让市场的供需来决定它的影响,官方在这里只是扮演一个鼓励者与推广者的角色,接受与否的主动权还是掌握在受众手中。
综上所述,《佩文韵府》的纂修活动在清初兴起的知识的穷尽式集中浪潮下展开,它既是这一浪潮下的产物,又是对这一浪潮的强化,它的问世是清朝官方文化话语全面渗透到文学尤其是诗学领域的有力证明。纂修《佩文韵府》作为一个实践活动,其开展过程也是多重诗学话语的融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虽然行动受限但仍有发挥主体性的空间;而纂成的《佩文韵府》作为一个官方诗学话语载体,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传统个体诗学话语的官方化,此时的官方对传统诗学表达模式有整合、集成之功。纂修《佩文韵府》还是一种官方诗学话语发挥影响的积极模式,纂修活动本身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已经对官方诗学话语产生了很好的宣传贯彻作用,刊刻流传过程也并没有太多官方权力的强制介入,个体仍有选择刊印或不刊印、购买或不购买的主体性。从《佩文韵府》纂修所体现的官方诗学话语建构情形可以看出,官方话语本身也具有积极因素,而个人在多数情形下都有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可能。这样的认识或许不仅可以作为王汎森先生传统文化“无主体性”说的补充[1]430②,甚至也可以视作对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修正,这与后期福柯对“合法—对抗”二元对立模式的自我反思也是一致的。[24]
① 按:《全集》点校者将“王百禄所增《书林事类韵会》”标点作“王百禄所增《书林》《事类》《韵会》”,析一为三,误。
② 王汎森先生认为:“我的观察是国家不干涉你时,或国家不干涉的范域中,人们的文化活动可以非常繁华、非常绚丽,可是当国家要来干涉时,往往变得毫无主体性。”(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从《佩文韵府》纂修人员尤其是查慎行维持主体性的努力与刊刻、销售时书商与购书人选择的自由度来看,即便是在清官方全程“干涉”的官修图籍范域,人们的文化活动仍然可以具有相当程度的主体性。所谓“干涉”,包括消极阻碍与积极干预两种模式,在前一模式下个人仍可尽力坚守自我,而后一模式为文化主体性预留的空间更是可观。
[1]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M]//十通.万有文库本.
[3] 张京华.日知录校释[M].长沙:岳麓书社,2011.
[4] 张玉书,等,撰.佩文韵府[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1.
[5] 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1097.
[6] 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1册[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606.
[7]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15卷第1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470.
[8] 范道济,辑校.新辑查慎行文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
[9]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28.
[10] 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785.
[11] 张玉亮,辜艳红,点校.查慎行集:第5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12] 郑永晓.《佩文韵府》的编纂与康熙朝后期的诗坛取向[J].文学遗产,2017(3).
[13] 蒋寅.陆游诗歌在明末清初的流行[J].中国韵文学刊,2006(1):11.
[14] 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M].扬州:广陵书社,2007.
[15] 素尔讷,等,纂修.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6] 黄丕烈,著.潘祖荫,辑.周少川,点校.士礼居藏书题跋记[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90.
[17] 金武祥,著.谢永芳,校点.粟香随笔[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152.
[18] 史澄,等,撰.广州府志:第3册[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331-332.
[19] 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M].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邱氏粤垣刻本:卷七,3a-3b.
[20]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31.
[21] 张寅彭,主编.清诗话三编:第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39.
[2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22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691.
[23] 叶葆.应试诗法浅说[M].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悔读斋刻本:卷一,2a.
[24] 陈怡含.福柯说权力与话语[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241.
The Compilation of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Dynasty’s Official Poetic Discourse
HUANG Jincan
(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Center,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
The compilation ofprovides a suitable field for contempl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poetic discourse in the Qing Dynasty. It unfolded under the wave of “exhaustive concentration” of knowledge that ro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t serves a product and an intensification of this wave. The unfolding process brought about the fusion of multiple poetic discourses. Among them, the fusion of poetic discourses between Emperor Kangxi and Zha Shenxing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individual cultural activities can still hav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subjectivity even in the realm of official "interference" in the whole process. As a carrier of official poetics discourse,is quite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officialization of individual poetics discourse. Its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process did not involve too much official power, reflecting a positive model in which official poetics discourse exerts influence.
Qing Dynasty, poetics, official discourse,, book compilation
2023-08-30
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中国经学诗学史”(GXXT2021045)。
黄金灿(1988-),男,安徽凤台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韵学与诗学。
I206.2
A
1673-9639 (2023) 06-0017-09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