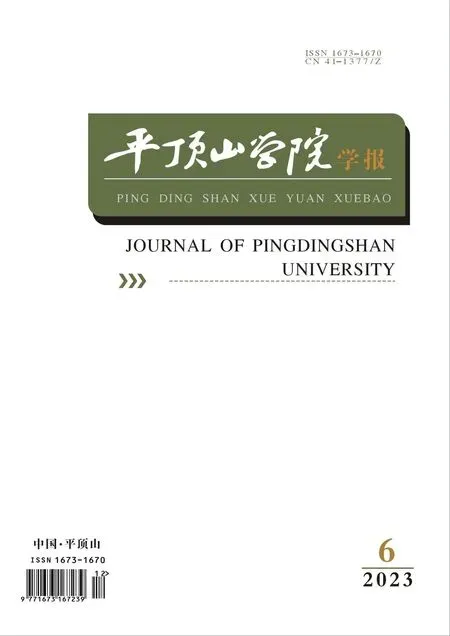苦难的契合与差异
——福贵与冉阿让比较论
2023-02-20陈富志
陈富志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36)
余华的《活着》自问世后很快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为他在国内外赢得巨大的声誉。作品对福贵人生苦难的倾情书写与福贵坦然面对苦难的超然与包容,都是余华用人物的灵魂在说话,用生命在发言。而同样表现冉阿让一生苦难经历的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与余华的《活着》在书写人生苦难方面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从而使福贵和冉阿让这两位中西方文学长廊中不可多得的人物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强的可比性。
一、苦难的契合
福贵和冉阿让作为中西方文学中饱受人间苦难“浸泡”的典型代表,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福贵和冉阿让都置身于社会大变革的话语背景中展开故事。福贵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土改运动以及改革开放前后半个多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但小说故意淡化了社会政治背景,主要是把它当作孕育人生苦难的生存环境,让福贵在这样一个大“炼炉”中命运沉浮,品尽人间苦难和世事沧桑。冉阿让的人生苦难故事背景同样恢宏壮阔。从小说开始提到的卞福汝主教经历的1793年大革命高潮,到卷末没落贵族家庭出身的马吕斯所参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反对七月王朝的起义,将近半个世纪历史过程中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一一呈现出来,揭露了资本家如何奴役人民、如何逼良为娼并制造人间地狱的。无论是《活着》还是《悲惨世界》,都将主人公个人命运的沉浮置于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之下言说,给人以沉重的历史沧桑感、真实感而显得气势磅礴。
其次,福贵和冉阿让都是全身浸透着苦难汁液的受难者形象。福贵的一生与他名字寓意实在是背道而驰。他从大富大贵到不名一文甚至举家无立锥之地,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物质生活变迁使他不得不努力面对残酷的现实和世间的凄风冷雨。诸多的苦难经历将他抛出正常的生活轨道并带来生存的窘迫,更悲惨的是一次又一次目睹妻儿老小六位亲属先他而去。小说文本最后,孤零零的福贵老人不得不和一头名叫“福贵”的老牛相依为命孤苦终老。而《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同样生活在苦难的深渊里。冉阿让作为一个修剪树枝的穷苦工人,仅仅是为了姐姐的孩子不被饿死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刑入狱。因为不满不公平的法律对他的判决,屡次越狱没有成功,反而又被加罚苦役19年。出狱后的冉阿让因为自己曾经是苦役犯而被社会拒纳,走投无路之际在迪涅小镇受到卞福汝主教的点化,燃起了他灵魂向善的明灯。然而,即使他隐姓埋名开办实业、扶弱济贫、一心向善并成为改过自新之人,却一生一直是沙威追缉的犯人。冉阿让在四处逃避追缉的艰难岁月里将珂赛特养大成人,但是却遭到马吕斯和珂赛特的误解。失去珂赛特让冉阿让一夜变老、走向死亡,直到离开人世之际误解才消除。福贵和冉阿让虽然经历的人生苦难形式不同,但都是全身每个细胞都渗透着苦难汁液的受难者形象。
再次,福贵和冉阿让都经历了两次极其相似的关键性人生转折。福贵原来是个家庭富有、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赌博输掉了家产反而因祸得福是其人生的第一次关键转折。如果不是福贵赌光了家产导致其地主和佃户身份阴差阳错地“置换”,土改时被枪毙的就是福贵而不是龙二。龙二因为买了福贵的家产成为“地主”而大祸临头,临死前他不无哀怨地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这无助的埋怨话语背后蕴含着龙二命运的不幸和福贵大难不死的庆幸,揭示出人生命运的变幻莫测和极大的偶然性。福贵人生第二个关键转折点是被国民党拉壮丁后押赴战场打仗。在枪林弹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鲜活生命的骤然消失如晴空霹雳惊醒了浑浑噩噩的福贵,使他第一次真切体悟到“生命”的珍贵,思想上对“生命”的认知发生了质的转变。经过这两次重要人生转折,“旧的”福贵彻底死去,“新的”福贵诞生了。无独有偶,这种人生转折在冉阿让身上同样出现了两次。社会的不公让冉阿让对社会充满仇恨,出狱后准备报复社会的怒火在胸中烈烈燃烧。寄托着雨果人道主义理想的卞福汝主教不仅从警察手中救了冉阿让,还将一对价值二百法郎的银烛台送给了他,从而以上帝的仁爱感化冉阿让,浇灭了他心中隐藏的恶的念头,挽救了在善恶十字路口徘徊的冉阿让,引导他走上一条人心向善的道路。冉阿让人生第二次重要转折点,是在沙威误以为商马第就是多年追缉的凶犯冉阿让。在商马第将被送入监狱之际,经过痛苦思想斗争的冉阿让勇敢站出来,宣布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是冉阿让进而来拯救商马第。他非常清楚承认真实身份的严重后果,但莫里哀主教的“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中,从自暴自弃中拯救了出来,把它交还给上帝”[1]82的教诲使他勇敢地直面苦难。尽管以后逃亡的生涯充满艰辛,但冉阿让的灵魂得以净化和升华。因此,不难看出,龙二和国民党之于福贵,正如同卞福汝主教和商马第之于冉阿让,他们都于无意之中改变了福贵和冉阿让各自的人生命运,使他们对人生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认知,并承载起余华和雨果各自不同的创作主旨和作品中寄寓的人格理想。
最后,福贵和冉阿让都是具有爱心和责任心的苦难抗争者。在经历了家境的变化和两年的兵役磨难之后,福贵对“生命”的认知和“活着”的看法产生了质的改变,担当起一个具有责任心的丈夫、父亲、外公的角色。当他从阔少爷瞬间变成不名一文的佃户时,也想一死了之。正是民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一道德伦理支撑着他活了下来,暗示出福贵潜意识中还是有担当意识和责任心的男人。后来,他竭尽全力地悉心照顾重病的妻子、聋哑的女儿、儿子有庆以及外孙苦根,都是福贵具有爱心和责任心的最好见证。冉阿让作为雨果人道主义理想的荷载者,其仁爱之心和责任感在其开办工厂、扶弱济贫、信守承诺照顾珂赛特甚至以德报怨救了一直追捕他的沙威、冒险救了濒临死亡的马吕斯等行动中,均如狂风暴雨漆黑之夜一道道刺破夜幕的闪电,展示出人道主义的耀眼光芒,均得到雨果浓墨重彩地倾情书写和歌颂。
冉阿让和福贵都是“苦难”的符号化象征,悲惨的不是冉阿让的人生,而是“培育”出悲惨温床的这个世界;苦难的不是福贵的人生,而是符号化背后“福贵”的缩影。福贵和冉阿让这一对中西方文学长廊中的苦难代表,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言说,但两者还有着本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揭示出雨果和余华人物塑造中所采用的不同的叙事伦理。
二、内在的本质差异
福贵和冉阿让在人生苦难诸多方面确实有着惊人的契合。但是,由于雨果和余华在创作时采取迥然不同的叙事伦理,为冉阿让和福贵提供各自不同类型和不同气质的精神资源,直接导致冉阿让和福贵对待苦难的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本质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两者对苦难认知的心灵深度不同。雨果的人道主义叙事伦理,其侧重点就表现在对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黑暗社会的愤怒控诉,将贫苦人民的一切不幸和悲惨遭遇归结为社会对他们的压迫和罪恶。为此,需要冉阿让有一定的心灵深度和理性品格,并积极向着其内心深处掘进,思索苦难的根源和隐藏于苦难表象背后的罪恶黑手。作品中多次出现对冉阿让大段的心理描写,来展示其心灵世界的深度、思索的广度、纷繁的层次性以及鞭辟入里的理性辩证。尤为精彩的是冉阿让在狱中的一段心理活动描写:
走上绝境的,是不是就他一个人有此过失?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想劳动,但没有面包。那首先要问,这能不能不算是件严重的事情呢?后来,有了过失,招认了,而处罚是否过重了?法律在对犯人处罚方面出的错儿,是否比犯人犯的错儿更严重些呢……越狱一次,处罚加重一次,这是不是强者对弱者的谋害?是不是社会在侵犯个人?这种情况逐日加重,持续了19年之久,如何解释?……社会的成员中,分得财富最少的恰恰最需要得到照顾,而社会对于他们却是苛求,这合理吗?……社会必须正视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它自己制造出来的。[1]82
冉阿让承认自己偷一块面包有错,但是法律对他是不公平的,比他偷一块面包罪过更大的是迫使他去偷窃的那个万恶的社会,是那些剥夺他生存权利的统治者,是那些毫无公平可言、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法律!冉阿让自己组织法庭对自己、对社会、对上帝和不公平的法律进行审判,其理性辩证的思索犹如电光石火瞬间照亮了整个黑暗,使人们认识到一切罪恶之源在于社会缺乏公平和正义。冉阿让独有的心灵深度和理性思辨,戳穿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谎言和虚伪面具,揭露出法律的暴虐、残酷和为资本家服务的社会本质,揪出了造成悲惨世界的幕后黑手。恰恰是冉阿让这种使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依旧有些高山仰止的勇气和锋芒,展示出人道主义立场的光辉,使得冉阿让对苦难的认知突破繁杂的表象而上升到社会学范畴,矛头直指造成“悲惨世界”的肯綮所在。
与冉阿让的心灵深度和比较成熟的理性辩证品格相比,福贵如同一个幼稚单纯的孩子,对苦难的心灵认知和思考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对于每一次接踵而至的苦难,福贵从来就不去考虑其根源是什么,对苦难的心灵认知往往停留于极其肤浅的表面,缺乏较深层次的思考,更缺少自我省悟的忏悔精神。即便是苦根儿之死直接和自己的粗心大意密切相关,但福贵也从不考虑苦根儿死于谁之手,他只知道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苦根儿是吃豆子撑死的!他唯一可以做的是面对并接受这个事实。这也恰恰体现了中国民间传统的审美心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当他们受到来自外部世界形成的伤害和苦难时,总能从朴素的民间道德伦理中汲取力量,去努力寻找一种与之和谐相处的途径,将本应爆发的尖锐矛盾一一化解,进而安抚自己内心深处累累的伤痕。因此,面对一切苦难,福贵既没有充满血泪的控诉,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更没半点埋怨之意。面对人生路程上的遍地荆棘,孤苦伶仃的福贵明白命运的不可扭转和小人物的卑微,他所拥有的法宝仅仅有两个字“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这无边无际的“忍耐”而变得沉郁、悲痛和无语。或许这就是余华所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2]中文版自序。在悲苦无依的人生境遇中,福贵别无选择,只有借助余华所赋予的“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叙事伦理观,不得不“淡定”地看待人世间的风起云涌和繁杂多变,并且以极大的耐受力去忍受劈头盖脸降临的苦难和不幸。换言之,对福贵而言,“活着”不只是人生的一个体验过程,而且“活着”就是“王道”,故生命因存在而精彩。或许正是源于此,使得福贵放弃了对苦难做更深层次的灵魂追问和根源性探究。虽然余华极端冷静克制的叙述努力让读者相信福贵是幸福的、超然的,但是其结果却是背道而驰。与之相比,面对苦难的接踵而至,冉阿让更像一个闪烁着雨果人道主义灵光的思想者、批判者、积极的抗争者。
第二,两者对抗苦难的方式不尽相同。不同的心灵深度和苦难认知,使得冉阿让和福贵对抗苦难的行为方式各有差异。冉阿让承载着雨果人道主义理想,使得他对苦难的根源有着深刻的理性认知,确保他具有内心自审和外部理性的行为方式来对抗苦难。因而,冉阿让对抗苦难是完全自发的、主动的、积极的。当他认定法律的不公之际,三番五次越狱,并组织道德法庭对自己、社会、法律和上帝进行逐个审判,将笼罩在道德、社会、法律之外的道貌岸然的华丽外衣毫不犹豫地撕碎;为了信守对芳汀的承诺,他再次越狱并带着珂赛特脱离苦海。在巴黎为了躲避警方和沙威的追捕,他和年幼的珂赛特小心翼翼度日,并充分发挥了他对抗被追缉的积极性,显示出其过人的胆量、高超的技能。一次他带着珂赛特陷入警察的包围而被逼入一个死胡同,犹如一头进入罗网的猛兽,急中生智凭借19年牢狱之中摸索出的技巧,利用灯绳敏捷地翻越高墙躲进修道院;在激烈的街垒战中,冉阿让也勇于投身人民革命起义参加了国民警卫军,用革命行动否定这个万恶的社会。尽管他对革命和理想社会的认识朦胧模糊,但他以斗争的方式去改变社会现状的态度却是主动的、积极的。可见,冉阿让对于每次降临的苦难不是坐以待毙,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与苦难抗争、与命运搏斗。历次的抗争中,他都以理性的思考方式掌握着主动权,解决面临的尖锐矛盾。无论是他人生关键的两次转折,还是他给芳汀许下照顾珂赛特的诺言;无论是他以德报怨放走沙威,还是冒险去救马吕斯等,都是以主动的、积极的姿态来实现“做一个好人”的理想。
与冉阿让对抗苦难的主动、积极相比,福贵对苦难的抗争则是被动的、消极的。他之所以输光了家产没有一死了之,是民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道德伦理观迫使他不得不去还赌债;女儿难产死于医院,他和女婿二喜回家草草将其埋葬并将之归结为宿命。面对降临的苦难,他都以余华所说的“忍耐”来被动接受,缺乏冉阿让那种昂扬的斗志和直面抗击苦难的勇气和骨气,是民间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根深蒂固的理念支撑着他早已是空壳的躯体被动地“忍耐”苦难。在他的人生词典里,似乎就没有“抗争”这个词。被国民党抓走当兵时,他不敢逃跑的原因是怕被打死;正在上学的儿子有庆给春生的老婆献血致死,福贵和春生会面之际,竟然忘记了儿子的死亡和春生聊起了老全,聊到过去吃馒头时居然匪夷所思地“两个人都笑了”,于是儿子有庆的死在与故友的聊天中不了了之。无论是凤霞的死还是苦根的死,对于不公的命运,福贵拥有的盔甲只是默默地忍耐。他以一种平和宁静的心态看待生死,这种“齐生死、等荣辱”的“伪道家”的超然成为他对抗苦难和死亡的“金钟罩铁布衫”,暗示出福贵对苦难的麻木和对一次次噩运的无奈妥协。
第三,主人公面对苦难时的心理流变各有不同。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往往为了表达某种强烈的观念,使笔下的人物直奔作家要传达出的某种哲思,甚至不惜使人物成为自己话语的传声筒。福贵就是余华所需要的这种传达自己声音的人物。为了表达“苦难主题”和“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叙事伦理,余华有纯粹为“苦难”而堆砌“苦难”的嫌疑。他将有可能发生于众多人身上的某一种人生苦难,全部高度集中化后劈头盖脸地砸向福贵,使其整个人生传奇化地跌宕起伏。余华将一系列苦难集中于福贵一个人头上的可能性与艺术的真实性暂且忽略不计,但是,余华忽略了福贵作为一个独立个体,面对苦难降临时所具有的本能的丰富心理流变和情感反应机制,强行剥夺了福贵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使得福贵完全按照余华的意思变换自己的性格特征,从一个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浪荡阔少转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敢于担当并具有责任心的男人。众所周知,人性的转变有一个渐进性和过渡性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外部世界巨大刺激引起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痛苦煎熬和挣扎,在强烈的冲突中,主人公的性格得以重塑,人物形象得以更加丰满和立体化。但是,福贵因缺少大量丰富的心理流变和灵魂博弈的过程铺垫而显得过于陡转急下。作品中更缺少主人公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心灵煎熬,仅仅以“福贵一夜之间瘦了一圈”一句轻描淡写之语一笔带过,使得福贵成为概念化、片面化、受苦受难的符号而已。不单单如此,在《活着》文本中,几乎见不到福贵面临人生大灾大难时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动描写灵魂世界的挣扎与搏击。每次亲人的离去,余华都以简单的几句话就使得福贵以匪夷所思的超然心态接受残酷的事实并无比快乐地“活着”,那种亲人一个个先后离去的撕心裂肺的痛楚和灵魂煎熬都忽略不计。简言之,由于余华惜墨如金,最能表现人物灵魂世界变化的心理流变描写过于缺乏,导致一个极其平面化的灵魂和简单化的福贵形象随之产生,使其缺乏真实感、立体感和生命的质感。
与之相比,雨果在塑造冉阿让人物形象时,除多处采取美丑对比的手法外(比如冉阿让和沙威的对比),更着重于遵循人物内在的心理变化逻辑,把冉阿让内心世界的反复无常、复杂善变描写得充分到位,而不是像福贵一样的简单化、平面化。例如,在拯救商马第之际,冉阿让围绕着“留在天堂做魔鬼,或是回到地狱做天使”这个问题,在自首与缄默的十字路口来回徘徊犹豫不决。尤为精彩的是“脑海中的风暴”这一章节中,雨果更是采取泼墨手法浓墨重彩地描写冉阿让波澜起伏的心理流变和激烈复杂的思想斗争,让我们细致入微地看到冉阿让在是放弃既得的荣誉幸福还是追求崇高正直、是求得灵魂的平静还是含垢偷生这一两难抉择面前的艰难心路历程。不只是在商马第事件上雨果善于运用心理描写,对于每次降临的灾难和人生命运关键转折的事件时,雨果都给予冉阿让大段的心理流变的书写。比如冉阿让受卞福汝主教感化后灵魂善恶归宿的抉择,在狱中对自己、对社会、对法律和上帝的道德审判等,冉阿让都有着丰富而深入的心理流变。恰恰是这些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描写,为冉阿让性格转变和后续行为做足了铺垫,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可感、情感丰富、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物而非概念化、机械化的人物。因而,与福贵相比,冉阿让的每次关键行为都有足够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心理变化过程,进而使人物形象丰满鲜活。
三、迥异的叙事伦理
福贵和冉阿让面对苦难表现出内在的本质差异,其根源在于余华和雨果在创作时采用了迥然不同的叙事伦理。所谓叙事伦理指作家在讲述和虚构故事时,文本中所蕴含的一种伦理后果。这种伦理是作家本人对于笔下人物变幻莫测的命运和生命存在的一种看法,它以对人物生存困窘环境及其根源的探索为基点,将人物和读者的命运紧紧拥抱在一起,唤醒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生命质感,进而上升到对全人类命运深刻思考的高度,其核心价值指向是作家对社会、生命和人性的感悟。因此,作家在创作时,其小说文本中表现出的叙事伦理和价值指向不尽相同。
《悲惨世界》是以人道主义作为其叙事伦理,仁爱和人心向善是其最终价值指向。雨果认为:“世上,只要存在着法律和道德方面的、人为造成的、充斥于我们社会文明的罪恶,存在着由于人类命运不同而呈现出各种性质的人间地狱: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无产使男子堕落,饥饿使妇女失节,黑暗使儿童衰微——不能解决;只要某些地区存在着社会窒息的可能性,或推而广之,只要世间存在着愚昧和苦难,那么,那些与本书同属一个性质的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1]作者序简短有力的序言是《悲惨世界》主旨的最凝练、准确的高度概括,也是作者人道主义理想的宣言。他以犀利之笔通过冉阿让、芳汀、珂赛特、商马第等众多小人物的悲惨遭遇来批判“社会文明的罪恶”,同时也在积极探索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以点燃贫苦人生存下去的希望之光。卞福汝主教身上闪耀的仁爱光芒是雨果人道主义理想最好的诠释。与绝大多数趋炎附势、自私自利的教会人物相比,卞福汝是一个“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好行善事加关心别人的人”。诚如他所言:“我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活着,我是为保护世人的心灵才活着的。”[1]24在那“多少人在挖掘黄金”的罪恶社会里,唯独卞福汝主教怀着一颗菩萨心肠到处给穷人施舍金钱、诊察疾苦、普度芸芸众生。他天使般的圣洁和无比的仁爱之心如温暖的太阳照耀着狄涅城的每位穷人,甚至令人恐惧的强盗克拉华特也特别敬畏他,为他做弥撒送了一份厚礼。诚如雨果所言:“一切受难者在永恒的爱的光辉照耀下,均将得救。”“怜悯可以使一粒石子发出光辉,在爱的指引下,魔鬼终将重归天使的行列。”[3]卞福汝主教用无私的仁爱融化了冉阿让内心的仇恨,无意中选择冉阿让做了仁爱薪火的传递人,并将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传承下去。冉阿让化名“马德兰”在滨海蒙特勒伊城兴办工厂、开办实业,给当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实则是雨果为医治千疮百孔的悲惨世界开出的一剂良药,更是其沙上建塔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幻想。而卞福汝主教送给冉阿让的何止是一对救赎灵魂的银烛台,更是一对闪耀着仁爱之光的接力棒。冉阿让后来的所有善行和重要决定都受其仁爱之光的影响,引导着冉阿让坚定不移地朝着雨果设定的人道主义理想前进。临终之际,冉阿让将银烛台送给了珂赛特,又暗示着雨果人道主义理想的薪火再传和后继有人。因此,从序言到整个小说文本,一直贯穿并高扬着雨果人道主义叙述伦理,并将仁爱和感化作为改造社会的重要途径。在剥削和压迫沉重、暴虐横行的社会,这种充满仁爱之心的人道主义理想蓝图的描绘,犹如黑夜中的一颗启明星,激励着“悲惨世界”的人们为美好理想的实现而积极奋斗。
而余华却认为:“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2]韩文版自序简单明了的话语中渗透出余华超脱世俗的生死、不为物喜不为己悲的恬静与淡定,背后蕴含着“庄子鼓盆歌大道”的大彻大悟,其叙事伦理与道家的“齐生死、等荣辱”超然出世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其价值核心就是“为活着而活着”。因而,在小说文本中福贵因家道中落、赌博输光了家产却反而得以保全性命;龙二在赌场上使福贵破产,却在短暂的享受荣华富贵之时被革命政权枪毙;福贵在陈尸累累的战场上大难不死,却又遭受亲人一个个先后撒手尘寰的致命打击。在客观冷静、通俗易懂的文字中,蕴含着余华对最底层农民生存境遇的关注,表现了作者在特定环境中对命运的变幻莫测、人活着的终极目的予以深刻思考。余华几乎就是用活生生的一个农民半个世纪以来变化起伏的命运轨迹为道家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做经典的注解。但是福贵的精神世界中,绝没有庄子对待万事万物的超然心态和淡定。庄子的超然和大彻大悟与其内在的精神气质相一致,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高度哲理认知作为其精神资源,因而庄子对苦难的淡定和超然是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余华笔下的福贵对待苦难和死亡的态度并非真正道家意义上的超然,仅仅是对接踵而至的苦难麻木忍受。诚如余华所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2]韩文版自序正是这种无边无际的“忍耐”,才使得福贵能够淡然地面对人世间的一切凄风苦雨。
四、结语
无可否认,福贵形象的塑造并非没有优点,其对“活着”的执着、对苦难的“超然”、对未来的微如晨星的期望都让读者看到宇宙之中微小生命的坚韧。余华没有赋予福贵哲人般苦苦思索导致人生苦难根源的精神资源,更刻意回避了创作主体对人生苦难的情感渗透和价值判断,而只是在客观冷静的平面化叙述中纯粹而透明地将苦难一一呈现,使之成为一种超越历史文化、超越社会背景、超越政治话语层面的本原性苦难。因此,福贵仅仅是余华所使用的表现这种“苦难”的符号工具。但将福贵和冉阿让放在一起时,我们会看到福贵身上承载的“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叙事伦理,在冉阿让承载的人道主义理想面前黯然失色,他缺少冉阿让那种恢宏的气势、宽广的胸怀、浩瀚的仁爱之心和直面苦难的勇气和信心。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当然,我们也无法否认雨果在冉阿让身上所寄予的过于理想化的色彩和“神化”了的冉阿让。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都需要冉阿让那种无私的仁爱、积极的抗争、思辨的理性和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