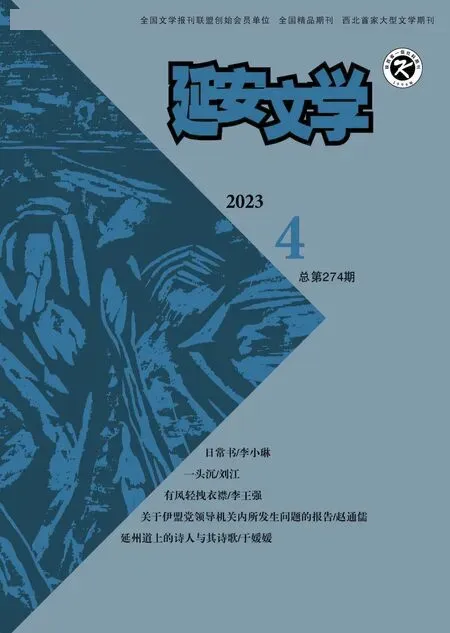凉都二叠
2023-02-19施昱
施 昱
古榕树 尼珠河
南岸育佳木,古榕贺寿龄。虽然古榕沧桑,耸入云天,但是树之茂密与繁衍,却远远不及北岸的千龄古榕。心间突兀一种天然的感慨——北岸之树,绿叶茂密,遮了半边云天,可是南岸壁画下的古榕,却“飘零萧疏”。
古榕下,才真正品读了主动同行的向导,感知了他的智慧涵养。他衣服洗得发白,轻灵地行走,似在轻吻河岸的露水,他的谈吐,让我吃惊:《唐诗》《宋词》《增广贤文》,民间谚语,如在风中,被他信手拈来。有一种真实的美,在谷内晕开;有一种自信,却又谦和。他的素养岂止是一位农民?岂止是一名峡谷里的向导?他俨然就是尼珠河风雨孕育的骄子,行吟考察乡间的文化学者,深入坊间田野,做自己心爱的事。他才是尼珠河峡谷的知音。生活中,俗人往往以貌取人,犯了人生的大忌,这必然产生认识自然的局限。向导和悦的笑声,又传至心里,他的谈笑,和且行且赏之景契合,如神来之笔。
比如他吟诵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他暗指尼珠河两岸的沧桑古榕,尤其是暗合南岸,落叶萧疏的千龄古榕之长势。
西来之尼珠河,难道不是乘风破浪,滚滚而来吗?还有从宣威普利飞来的西瀑布群,从千米之峰巅,刀切斧砍之绝壁,像一帘纯洁的瀑花,清澈了峡谷阴郁的世界。轰然跌入谷底,仍把最后一束花,呈现在七彩的阳光里,让劳顿的行客,倍觉清爽。陡峭跌练之瀑,闪烁爆泉之声,不绝于耳,惊心动魄,难道不也如他的描绘?瀑花之殇,憾而生思:世间的绝美艺术,哪有不是涅槃重生?哪又不是碧血丹心所绘就?否则,哪会有绝世的风景。人生的瑰丽多彩,概莫能外。尼珠河的壁画如此,沧桑千龄古榕亦然。向导清风般的谈吐,倾诉着峡谷世态的风云变幻。风物如此,更何况生命、人类。“冷月照孤单,鸿雁南飞远。翔鸟思家恋港湾,老树春心唤。”从古榕的虬根巢穴,穿行,抚摸,此境,岂止沧桑之态?密密匝匝的树根,无规则地连缀,一拔涌动一拔,大有风起云涌之势,有如尼珠河发情时的澎湃任性。高邈的树身,自然狂野的雄浑态势,拥抱尼珠河的沧海桑田,以及河岸浓荫中的人畜和村庄。树巅与山峰牵连,月儿静挂树冠,峡谷幽居的飞鸟,风尘仆仆地从旷野飞来,几个优美弧形的飘落,归林入巢,用月光洗去羽翅上的风尘。鸟儿清新的歌喉,迎来峡谷之巅透照的第一束朝阳。鸟儿如此眷家,我想,尼珠河外出的游子,一定会在年头岁节,又聚集在苍茫的树冠下,在雌雄偎依的千龄古榕里,一起品尝团圆时母亲的饭香!
南北两岸古榕浓密与萧疏的枝叶,互衬的风采,可谓绝配,成为尼珠河,疏与密、明与暗、粗犷与细腻交织的风景。
河之两岸,自然天成的景致,书写天地间,阳与阴互生,雄与雌和平,南岸与北岸互助,推动物事的发展,衬托了峡谷的千姿百态。尼珠河的千龄古榕,想必也是如此。这种朴素的道理,就是生生不灭的自然哲学。这个亘古不变的良方,隐匿在古老的村子,隐藏在雄奇独特的尼珠河上游、下游的风物中。
尼珠河两岸,人烟的栖息与发展,是否也如此神奇?我自豪地希望。他乡如是,尼珠河更会如此。否则,北雌南雄的千龄榕,怎么繁衍生息,发展绵延?北面雌树,枝叶繁荣,莽莽苍苍,遮天蔽日,青瓦红墙,点缀村庄,掩映其间,恬静而又诗意,淡淡的云烟里,羞涩地时隐时现。穿梭的车辆从繁华的城市,把钢筋混凝土桎梏了思维的人们,引至尼珠河,触摸荒远宁静古榕繁衍的村庄,去追求别样的人生况味。那明亮通向世外的窗口,瓦蓝深邃的天幕,映照着清风、明月、朝阳、飞鸟,还有森林中一树洁白素雅的花朵,以及坦然裸露的心扉。交织着人生的进进出出,品读峡谷内外的世态炎凉。风垭处的赤松,深扎石峰泥土,被清风明月,洗净世俗的铅华。用青亮的身躯,挡住凡尘的风雨,傲然卓立于尼珠河的心岸。总之,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向往大山外的世界,行程里的交流,我感知得到。是的,我们成了矛盾的始作俑者,互羡,隐遁,破坏着,发展着,但不管怎样,大家始终向往未来,而且始终是向上的,正如这处峡谷中的千龄古榕,就算沧桑宿老,树皮粗皴。飞鸟依然筑巢其上,粪便堆积,种子又在其上长出幼苗,树上生树,独木成林。树枝上的寄生树,又焕发出新的枝条,枯涸的荒滩,又被浓密的枯叶,发酵成肥料,衍生一片良田,养育了千余载的人烟,其势蔓延。树圪兜上的根须,又一年的繁茂。根背着根,古榕连着幼苗,幼枝牵着老树,他们互相包容与给养,是岩画的生命,抑或苍老的容颜。一株古老的榕树,窜向熔岩的罅隙,风雨经年,树包着石头,石头上长出绿色的新枝,闪耀着晶亮的花朵。树生动了石头、河滩、峡谷,石峰映衬着古榕树。这是一种生命的延续,树石情深,哪有“水火不容”啊?反之,那只是因为格局太小,小到连自己都难以容纳,怎能容得下世间的苍生?
是啊,难怪尼珠河南岸的几株雄性古榕树,虽然枝柯稀疏,确实比不上北岸的浓密繁昌,但是它却活得执著,活得舒心开怀,活得震撼峡谷的风雨雷电。因为它们心里想着北岸雌林的繁衍生息,它们乐意付出,这就是它们的梦想得以延续的根源,以及获得千年生命强盛的力量源泉。
这种顽强的生命意识,在我们进入尼珠河下游时,得到强烈的印证。
顺河而下,上游宽阔的峡谷,渐渐逼仄起来,慢慢地形成“一线天”峡谷,尼珠河水流湍急,浊浪排空,不敢前视。
远幕苍茫,连接云贵天堑的杭瑞高速公路,亚洲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耸立峡谷之上的云层中,那份高傲,思想一样矗立巅峰,我只能仰视。
在溯下的云雾中,就是尼珠河水电站了。
水电站建设之初,水电没有通达,公路也没有惠及此方偏野,实际上这儿怎能修通来路啊?水电人全凭惊人的毅力,双肩磨出闪亮的泡花,双手飞舞出晶莹的血珠,水电站不负人们的期颐,终于耸立在峡谷的腰肢上,像一幅奋战多年,方能镂刻面世的版画,生动无人问津的峡谷。条件的艰苦,水电人用血肉之躯,背负一篓一篓的泥土,削平一尊尊石头,但是那时思想的封闭和固守,也如一条亘古汤汤的河流,横在大山百姓的心里。
这条汹涌的河流,能被驯服?还能发电?谁又会相信哩。
电流会传输到千家万户,人居然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开出古榕花朵般雪亮的智慧!水电人,以尼珠河岩石般的坚韧,在默然的峡谷中,傲然坚守。这种坚韧,像奔涌向前的浪花,冲过峡谷,切开暗河,他们也有诗和远方。
就算生命湮没在峡谷,也要在峡谷里建成水电站,让光明点亮漆黑千年的峡谷。这是河流生生不息的精神,是尼珠河浪花点燃的光亮,在古榕的花朵上闪烁。
临近傍晚,峡谷中的光线,渐渐暗下来,给这暮色里的风景,笼罩上一层紫蓝的光影。
对岸呼唤回家吃饭的乡音,从河风里传来,带着滋润,主人使劲招手,呼唤回家吃饭的乡音,温暖了峡谷和人心。
告别尼珠河,心生万般遐想。尼珠河的灯光,亚洲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下的水电站,那位谦和送别的妹妹,她风里的招手,像一朵空谷幽兰,疼痛着大家的思绪,渐行渐远。
也许我还会再来,也许选择不会再来,不忍再去触碰那方世界绝美的风景。让这高原峡谷的美好,犹如古榕树上雪白的花朵,永远盛开在心灵的土地,不忍去触碰她。让已迈出的脚步,沁凉甘甜的河流,停栖在树巅的苍鹭,吻伤老树裂口的雾岚,在古榕群落的苍茫里,诗意弥漫。
银杏花开
我是轻轻折进银杏群的,千年银树,好像被惊了一下,当我的手指触摸它的肌肤时,耸入云天的高枝,始终望着蓝天,没有和我亲昵。我不知是欣喜?还是哀伤?
怀着好奇,尊重,拜访了“下马桥”。石桥优雅的弧度,像心卧于溪流之上,连接杏湖,用其温度,贴近水的肌肤,不论春夏秋冬。有水的润泽,尽管石桥沧桑斑驳,却不显老态,相反,在千年绿树的呵护下,显得年轻儒雅。在妥乐绿海的映衬下,它却低过两岸的花草,就连暴突勾连的树根,也在仰望高处树影,没有低头看它。石桥是林中灵性的风景,不管是人或优雅起舞的鹅,或者慢慢地踏过其肌体的动物,它都以低微的身体,承载万物的过往,踏过风雨。
桥下溪水,映照斑斓世界。深蓝天宇下,银杏互映,像童话的世界。此时,一群无视客旅的鹅群,在飞鸟的翼动里,嘎嘎地和鸣,从水中扑腾起来,扇动羽翼,翅膀上的水珠,飞溅滴落,珍珠般的帘,勾人联想。这种自由,可是银杏灵魂在飞舞?平静杏湖,温润裸圆的石头,生命得以滋养,一颗一颗地延宕在银林里,像银杏果实丰硕的思想,长在林中。与畅游者,发出会心的交响,那好像我心跌落溪潭时,生出的心境,我怕如织的游人,攀枝,折桂拍照,银杏原谅了无知的客人,我心却不能宽容自己。遗落人间的佳境,古银杏群落,石桥古井,瓦屋寺院,悠闲耕牛,交媾的白鹅,隐退的田畴,栖息银杏树下的瓦屋,梦里溢出的谷香。
“银杏树王”的青春容颜,早已被风霜剥蚀,但因是“树王”,是林中灵物,无数根祈福的红绸飘带,缠满树身,它可否也如凡人,心被束缚?当你的身心被凡尘干扰,你可还有自由?母树龟裂,那可否是爱得太深的伤口?伫立叶落空阔的千年古银杏树群,林中鸟鸣,和着天籁,苍茫远山,一片绿色铺染,清凉洗身,心自然宽远。一群白鸽,划着优美的弧线,翩然飞舞,隐没林丛树梢。农人仍在地里奔忙,趁着时机,播下种子,将一个美好的梦,种在树群深处,等待花开,希望也如千年的银杏,结出丰硕的果实,不仅是肉眼见到的,还有梦想。独自徜徉,属于自己和银杏的时空隧道,心有归属,在静静的群落里,游至密林深处,我的担心,有些杞人忧天。河溪映林,飞瀑喧泻,白鹭飞舞,飘落芦花深处。这些鸟儿,成了花的精魂。一位晚归的农民朋友,牧鞭啾啾,却未抽打他的耕牛,他疼牛犹如爱自己,我的善意玩笑,让他含羞,回应让人讶然,妥乐林中的牲畜,是银杏的灵物,不可屑之。一千多株银杏,集群生长,相互成就,是感知四季变化的活化石,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皈依。汩汩溪流,从银杏群里溢出,汇聚古井,井泉似清亮的眼睛,晶莹透明,照亮了心仪而来的人心。每一位前来井泉祈福的人,喝一口井水,许下愿望,可否能在银杏林中,也种植一株幼苗,还妥乐一树绿荫,积一瓢泉水,成就更大的幸福?古井无声,争抢木瓢舀水的声响,混杂扰心,令人生厌。一滴一滴的泉水,从瓢中溢出,那可否是井泉的泪?这干净的泉水,自然有古银杏的汁液,怎能白白浪费?望着这杂陈的风景,喜乎?忧乎?一时难以名状。
下马桥,上马桥,分处井泉南北,均是石头筑就,成为连接南北的通衢,尤其是没有公路通达之前,可以想象它的重要。是林中抢眼的风景,不管人,还是物,都以桥为中心,犹如林中永远的等候。比邻石桥的风景,西来寺是不可错过的,寺旁枹桐花开,从北向南铺洒,桐花正炽,如星闪烁。瓦屋掩荫绿树中,静处银杏群,衬托出生命的流动。下马桥的传说极具人文气息,道出人们对生态、银杏、石桥、古井和溪湖的敬畏——尊重自然,福必自来。
西来寺的传说,我们可以不必过多追溯来源,仅从“北有丹霞寺,南有西来寺,香火旺盛齐名”的文字,似乎道出凡尘的奥秘。在这灵性的妥乐树群,他们互不争名,交相辉映。丹霞寺护着千年贝叶经书,护国为民,书写仁爱忠勇;西来寺伴衬千年银杏,生生不息,静衬银杏沧桑变化,以及生命的浪漫,智慧乎?愚钝乎?伫立西来寺“五子登科”银杏树下,仰望细密叶片,枝蔓树梢,它朴素得让人惊讶,不管是高大,或者是形象,都会超出你的想象——它的平凡普通,也许是一千多株千年古银杏中,最不起眼的树了,它静穆生长,花开花落,繁衍生息。同时,它也在衬托世界无出其右的古树群落——世界古银杏之乡。“五子登科”,常年伴寺香火,向善的经文,自然悟出“大道无为”的境界,这样的“无我”,自然让人想到南面树影里的“树王”。沧桑写在它干枯的肌肤,只有用心,才会想象,它无私播撒花粉,把爱的种子,分享给银杏仙子,让她繁衍,开花,结果。连霞彩也恋它的执着,与它燃烧着情爱,哪怕就算一瞬的激情燃烧,就算没有像花仙子和“树王”,千年生生死死的忠贞不渝,它已满足了。可见公树“树王”对仙子的忠贞,就算霞彩之烈焰燃烧的爱,也不移情,也泯灭不了它的忠贞。它播撒爱的雨露,获得爱情的力量,一季季花开,果实累累。我心不忍,轻轻抚摸“树王”的肌肤,怕打扰它的休息,和它传授花粉的春梦,但是它的无私与伟岸,又深深地吸引着我。何况我羡慕的,是树中仙子,是“树王”的忠贞,蛰居千年,子孙满堂。看来,真正的爱情,可以孕育后世的繁昌。花仙子寻得真爱,爱这片森林,这条河流,这片土地的生灵。大爱无言,树活出了一种精神,怎不感染骑马到此的官员、文人墨客呢?怎不下马,凝神静气,轻轻步行,怕惊动仙子呢?看来,忠贞的爱情和无私的奉献,可以涵养风范,生出敬畏。
当我在西来寺,“五子登科”树旁的人家,憩坐品茗,看着姐姐银环般的手指,一颗一颗捡银杏果的声音,像天籁飘入树林,静听姐姐虔诚的故事,再次聆听花仙子的爱情及下马桥的人文历史时,我为没有冒失折枝拍照,漠然树神而暗自庆幸。我早早地下车,一个人,走在一条石头铺就的道路,脚趾吻着清凉光滑的石板,像心捂石头,小心穿行十步梯,一步一步,吻过河桥,怕惊动欢悦爱恋的白鹅,羡慕幽会选在石桥下的智慧。这鹅群欢舞的歌声中,桥上染绿的古藤,静静地护卫着银杏掩隐的石挢。石桥圆润光亮的肌肤,闪烁着树间跌落的阳光,星星点点,闪烁的光,从河心反射到我的双眼。光是亲切柔软的,不太刺眼。桥身的古藤,像绿色的瀑,缓缓延伸到河里,与水亲吻,被鹅交媾欢悦时舞蹈的翅膀掀起,在微风中荡漾,又慢慢地落下。我想,那位下马的官员,也是一位儒雅之人,至少他不官僚,他听得进百姓的劝诫,成人之美。也许他真的被银杏仙子的故事感动,内心希望银杏繁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文不朽,一代代延绵,妥乐人身受养育,人才济济。这难道不是一方世界养育的绝版风景,存放心间?
银杏树林里的人,被故事所感,每一个人,儒雅谦和,微笑从脸上溢出,甚至对绿水青山,油然敬畏。在北山“文笔峰”下的一户农家小院,微风吹拂,花香阵阵,我闻到干净的木香,空气潮润,树林掩映,心自然静泊下来。院旁的枹桐,蓝紫的花,一树树点缀苍茫的银杏群,故意缓解观赏者的视觉疲劳,给朋友留下了创作的欲望。当然,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朝晚,都有其神韵,只是各自的思考不同,心境各异罢了。
大自然很会回报爱护它们的妥乐人,在深绿树群,散落紫花的星星,让绿色不再呆板,由北向南面的山坡,氤氲淡淡岚霭,落日红霞,组成一幅静默的画,留在你的心里。
紫蓝花树散发清香,小河顺势拐了个弯,像一条玉带,在绿树中泛着银白的光,围护着一口古井(又名大富井)。走累了,口渴了,正巧遇见古井,碰到洗浣的妹妹,她脸含微笑,用红色的瓢,舀水递给我,井水缓缓进入口中,甘甜可口。抬头仰望,天空蓝得深邃,映入井泉,在这里栖息停泊。热情的妹妹,在古井与我相遇,热情地叫我带点泉水回家,她细心地把我的瓶子装满,这是一种幸福,就算我们素不相识,但妹妹的情谊,这干净香甜的井泉,正如这处银杏风景,融入心里。
这种纯朴,视他乡之音为乡音,视远客为己出,这是一种包容,这是银杏的种子,一季季花开,一年年收获,她像一枚枚纯洁的银杏果实,孕育的善良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