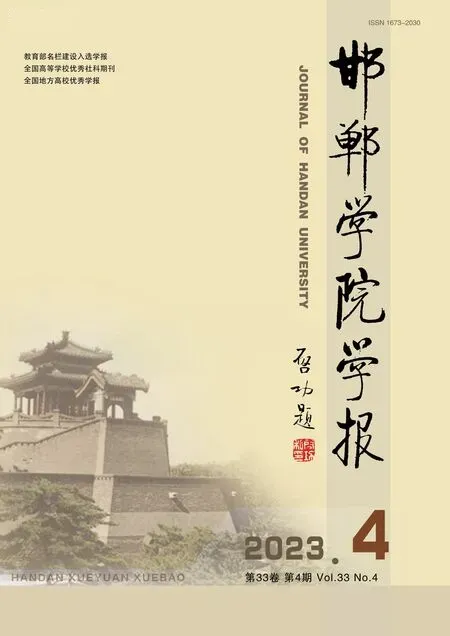“人而不仁,如礼何?”
——简论孔子与荀子说礼的一个差异
2023-02-12陈文洁
陈文洁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城市文化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410)
刘向尝言,惟孟子、荀子为能尊孔子,循孔子之道。[1]559荀子作《非十二子篇》,称孔子为“圣人不得势者”,教人“则法仲尼子弓之义”。荀书自《宥坐篇》以下至《尧问篇》五篇,乃荀子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多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论。《尧问篇》末荀子弟子序荀书,更谓荀子不逊于孔子;该篇为荀书终篇,如《论语》以首句二字名篇,篇名也与《论语》末章《尧曰》相仿,似愈坐实以荀子比之孔子的意图。是虽荀子弟子尊大其师的溢美之辞,亦可见荀门对孔子的推崇。荀子作为“孔氏之支流”①见永瑢等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九。,礼是其承继孔子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荀子关于礼的论说看,他对于如何推行礼有不同于孔子的考虑。这与其说是他与孔子在思想上的差异,不如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所面临的政、教环境的差异。
一、礼以仁为本:治教分离下的孔子之教
礼发端于先民的祭祀习俗:“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敬于鬼神”(《礼记·礼运》)。周公制礼,理旧俗以安民心②见《周礼》卷第十《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郑玄注、贾公彦《周礼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62-263 页。《周礼》卷二:“述大宰之职,亦有礼俗‘以驭其民’之说”。,“监于二代”(《论语·八佾》),“集古圣之成”,[2]121变粗朴的旧俗而成一套纲纪天下、经纬人伦的制度,又立司徒之官、行礼乐政教以为实施保障①见《周礼》卷第九《地官司徒第二》。另,按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卷第十《大司徒》所列礼乐等十二项政教即地官司徒所掌邦教。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23 页。又,《尚书·舜典》云:“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设司徒之官教民,上古已有,只不过舜时仅五教,周则有十二教,范围更广。。故王国维称周公“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3]288-289礼既是政治秩序,又是伦理道德要求,集治、道于一体,非“圣人在天子之位”不能作之②见《礼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1457 页。。周公虽无天子之名,但“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淮南子·要略训》),实则在天子之位;其制礼立官以纲纪教化天下,是一人而兼君师,施教于“敷政出治”之中,[2]131正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③《尚书·泰誓》。孔颖达疏曰:“治民之谓‘君’,教民之谓‘师’,君既治之,师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师’,‘师’谓君与民为师,非谓别置师也。”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73 页。。当此治教合一之时,典章制度皆存于官,官师无二,官之外别无私教,更别无私人著述。
周衰之后,礼崩乐坏,治教分离,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率先在民间普及古代典籍,“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传周公之道,开私人教育之风,“明立教之极”,是以“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公、孔子,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2]122但是,较之周公身兼君师、寓教于政,孔子有德无位,仅凭“好古”的个人信念而承师之一端,聚弟子教诗书礼乐,传周公之道,并无政教之权,且当传统制度失去普遍合法性之际,其说教势必只能诉诸个人的内在认同。所以,孔子以“仁”说礼,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将“仁”视为礼乐的精神内核,为传统制度确立内在的道德根据,由此而树立儒家道德意识,“克己复礼”便也超越了原先治教合一的环境下所认可的不论动机的“表面的善”(合于礼),成为内在之“仁”德。④《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杨伯峻据此认为,“‘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用前人的话赋予新的含义。”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123 页。
但“仁”的说法,孔子之前已有。据学者考证,古“仁”字从“尸”,即祭祀的“尸”;“仁”起源于古代丧祭礼,设尸而祭这种“事死如事生”的尽哀尽敬的礼仪,体现了对祖灵的虔诚、敬拜的自然情感,因此,“仁” 的原始义乃是对先人死者鬼神的哀怜之情。[4]故《左传·成公九年》云“不背本,仁也”。《论语·阳货》中,宰我质疑“三年之丧”,认为“期已久矣”,孔子所以谓之“不仁”,也是基于“‘仁’的本源”“由哀敬父母祖先的心性而立”,“宰我厌服三年之丧”“违背了‘仁’的原始原则”。[4]进一步看,孔子以“心安”说“三年之丧”,更强调了“仁”作为儒家道德本源的内在情感特质。道德即所谓求在己者,“仁”之立与不立,全在一己之心,故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又云“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强调内在之“仁”,则外在之礼仪相对不必隆重。林放问“礼之本”,孔子答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正是就丧礼而言,明“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礼记·檀弓上》)。这一“礼后于仁”的说礼原则不只适用于丧祭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仁之本”固然在“孝弟”(《论语·学而》),但对亲人的这种“仁”的情感可以有等差地推及他人:“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礼记·祭义》)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凡礼所及之人,仁者无不有爱,无不以相应的仁爱之心履行对待之礼。通过孔子的解说,“仁”就扩充而成为礼的普遍的内在道德要求。
章太炎论列诸子得失,特称孔氏“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 之功。[5]174孔子对“仁”的阐发,可以说明他在这两方面的贡献。古人祭祀多有所求。《周礼·春官宗伯·大祝》有六祈之义,《地官司徒·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礼,《仪礼·少牢馈食礼》嘏辞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女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皆是其证。其背后的假设当然是鬼神受祭而能祐助致福于人①并参《礼记·祭义》:“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故季路有“事鬼神”之问,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事人”则修“仁”。通过树立“仁”德,礼就由“事鬼神”的禨祥之事变为君子专以“事人”的安身立命之事。②《论语·尧曰》:“不知礼,无以立也。”这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立场是一致的。既然摒弃了祈福于鬼神的禨祥之事,又当治教分离之际,则孔子就只能以非功利教人。所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教弟子“仁者安仁”(《论语·里仁》)、“仁者不忧”(《论语·子罕》),谓“仁”德本身即是自足的。如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足以显示孔子以“仁”为教之功。
但是,孔门弟子三千,根性各有不同,如颜回者寥寥。颜回死,孔子有“天丧予”之切痛(《论语·先进》),认为弟子之中再未有像颜回一样的好学之人③《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所以孔子在“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的教育中,对于鬼神、超自然之“天”等神秘之物都刻意保持一种既不明其有、亦不谓其无的微妙清明的态度。他教弟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而不务淫祀、“无所事祷”④《论语·述而》:“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参朱熹注“丘之祷久矣”(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7 年)。,又明“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皆是意在维持他们心中对于超凡事物的敬畏。这种敬畏对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堪其忧”(《论语·雍也》)的人来说,尤其是一种勉励和安慰。仁者固然乐其“仁”而无他求,但孔颜之乐并非所有弟子都能领会和悦纳。毕竟孔子“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而“未尝无诲”(《论语·述而》),就意味着要容纳各种不同的天性而因材施教。在此意义上,孔子一再暗示“天”的超自然特征⑤《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除了是他的个人生命感受的自然流露外⑥《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也未尝没有以“知人”之天⑦《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导弟子渐入于礼义之道的考虑。
二、礼法:荀子“治教合一”的论说意图
先秦儒家中,接续孔子“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之业最着力者,莫过于荀子。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与孔子一样,荀子之辟禨祥亦缘自时人沉溺于迷信而不遵行礼义之道。但是,相较于孔子,荀子对迷信的批判更为坚决、彻底,甚至直接消弭了孔子在教育中有意维持的“天”的神秘感。这关系到荀子关于如何推行礼的考虑和论说意图。在治、教分离之时,他试图提供一种弥合治教、重归“治教合一”的方案而使大道遂行。
《荀子·天论篇》开篇即祛“天”之魅,以“天”为自然之天,谓“天行有常”、治乱在人,显明该篇正是针对当时“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於巫祝,信禨祥”而论说。既然治乱在人不在天,则治政之第一要义在“明于天人之分”。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天论篇》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观念“参”:
物双松解“参”为“三”,曰:“其字可见各异其道矣。能知其异,而唯务人道,不干天地,则人道隆盛,可以参天地”①物双松释《荀子·天论篇》“夫是之谓能参”,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680 页。。天、地、人各有其道,各司其职。人以其“治”与天、地配合,此其“所以参”。故人当务于人事,不应“愿其所参”而“与天争职”②钟泰释《荀子·天论篇》“愿其所参”,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680 页。。循此,《天论篇》提出“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按荀子的思路,“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大略篇》),“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王霸篇》),因此,天地、四时、阴阳之类③《荀子·天论篇》:“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治政者皆任命专人司职,自己则谨守人道而已。何为“人道”?《天论篇》有言:“在人者莫明于礼义”,“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道”即礼义之道,人所以能与天、地并立而“参”者,在于能以礼义之道平治天下。从论说角度看,《天论篇》主要是对“君人者”言。该篇以厘清“天”的自然特性开始,继之以辟禨祥而务人事之说,最后得出“治乱在礼”的结论:“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天论篇》以“礼”为其中心论点,辟禨祥正是为了确立礼义作为“人道”与天地之道并立而成“治”的地位。
礼是荀子则法孔子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以“仁”说礼,荀子亦屡言“仁”,如“仁者必敬人”(《臣道篇》),“仁者爱人”(《议兵篇》),“王者先仁而后礼”(《大略篇》),可见他对“仁”的理解与孔子是一致的。然而,荀书中,不仅以“礼”为论说归宿的《天论篇》无一“仁”字,专论礼、乐的《礼论篇》《乐论篇》也不见一“仁”字。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荀子论礼乐何以皆不称“仁”?《礼论篇》云: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所谓“礼起于何也”,并不是一个历史探源的问题,而关乎礼的必要性和作用。荀子的论说思路很清晰:人皆有欲而求其所欲;盲目的欲望驱使人求之无度;人人如此,则必然因物欲之争而陷于混乱匮乏,结果就是大家都不能得其所欲。简言之,没有共同规范的约束,“人天生互为敌人”。[6]296这是一种政治讨论的思路。西人如霍布斯、斯宾诺莎都曾以此构建其政治理论。荀子同样是从政治的角度说明“礼之所起”。他特别指出礼是“先王”为止人之争乱而“明分使群”(《荀子·富国篇》)的政治制作。在此意义上,“先王”可称为“礼之本”。故《礼论篇》云: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礼由人起”(《史记·礼书》),但并非起于人之仁心,而是起于人之争乱①王天海释《荀子·礼论篇》“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参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752 页。。故必待圣人持礼以为人君、为人师而后成治。由圣人身兼君、师来看②梁启雄释《荀子·礼论篇》“君师者,治之本也,”曰:“师,亦君也”,参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759 页。,礼本身就是融政教为一的,其施行有赖于君师合一、治教无二。换言之,如何推行礼是一个治政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这就可以理解何以《礼论篇》无一“仁”字。以“仁”为礼之本,则礼为个人修身明德之事;以君师为礼之本,则礼为君人者治政之事,即《天论篇》所谓“自为守道”。因此,荀书他篇称礼为“法”③《荀子·劝学篇》:“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修身篇》:“非礼,是无法也”;“学也者,礼法也。”。“礼法”并非荀子的创新之辞。在三代时期,“礼实际上便是法”。[7]21虽然荀子志不在澄清礼的历史起源问题,但礼法、君师之说确实显示了他试图重返从前“治教合一”的治政局面的努力。
荀子的礼法、君师之说,表明了他批驳孟子“性善”说的意图所在,从而更突显他在说礼方面与孔子的差异。关于荀子的人性说,或言性恶,或言性朴,颇多争论。二说其实不必互诋。《荀子· 礼论篇》云“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性伪合而天下治”。这与《性恶篇》谓学而积伪则“涂之人可以为禹”,是一致的。《性恶篇》所以特言“性恶”,主要是针对孟子言“性善”而发。从推行礼的角度看,“性善”则劝人修身返性,故孟子讲“尽心知性而知天”(《尽心上》);“性恶”则见礼法、君师之用。因此,《性恶篇》开篇点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后,即论“师法之化”。法出于君、合于礼,“师法之化”即礼法、君师之用。接着《性恶篇》四次针对孟子“性善”说展开论说:
1.2.1 对照组 应用PDCA循环护理模式前,PICC置管护理操作常规开展,措施如下:将PICC置管相关知识详细的说明给患者,包含导管优势、穿刺方法、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等,使患者抵触情绪减少,缓解不良心理,促进生理反应减轻;穿刺当天,适当减少穿刺侧肢体活动,并适当压迫穿刺点;换药间隔时间为3 d;穿刺点情况认真观察并记录;静脉输液后,管道利用生理盐水冲洗,封管液使用低分子肝素生理盐水。
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曰:……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矣。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
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
这四次辩说层层推进。先云“性善”说混淆了“性伪之分”;次驳人性本善、失性而后恶之论,明礼义辞让悖于人的天然性情,顺其性则恶;再论“善”乃“正理平治”,即“合乎礼义法度”④北大组释《荀子·性恶篇》“正理平治”,参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947 页。,显示荀子是从治政的角度说“善”;最后谓“性善”说不具现实可操作性,点明《性恶篇》反对“性善”说的目的在“与圣王、贵礼义”,再申师法合一、治教无二之旨。由此亦可明了,《性恶篇》常以“仁义法正”连说,正是为强调“礼法”⑤杨柳桥释《荀子·性恶篇》“仁义法正,”曰:“法正,犹法政也,法制也”,参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984 页。,而“仁”作为等差之爱⑥《荀子·大略篇》:“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故曰: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也需借外在的礼的秩序规范而体现。相较之下,孟子谓仁、义、礼、智皆发端于心(《公孙丑上》),理、义乃“心之所同然者”(《告子上》),其“性善”说实更近于孔子从“心”上说“仁”。在此意义上,荀子对“性善”说的批驳是意味深长的。
三、一个可能的解释:因势为说
孔子说礼强调“仁”,其所教之礼可略称为“仁礼”;荀子说礼强调(师)法,其所教之礼可略称为“法礼”。虽然荀子的“礼法”“师法”之说有异于孔子以“仁”说礼,他的“治教合一”之论却未必悖于孔子之义。孔门四科,政事居其一,孔门高弟冉有、子路皆长于政事(《论语·先进》)。孔子自己也努力求仕,“志欲行周公之道”①朱熹释《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参见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长沙:岳麓书社,1987 年,第134 页。,想为“东周”(《论语·阳货》),至有“沽之哉”之叹(《《论语·子罕》》)。使孔子得用,想必愿效周公寓教于政而为“东周”。只是孔子遍干不遇②《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以布衣传道,自然只能诉诸个人内在信念和道德情感,发明“仁”说以传授普及传统礼乐制度。
对于孔子的宣道教育之功,荀子亦颇称羡。《荀子·非十二子篇》曰:
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顺,奥窔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孔子作为首先在民间传授古代典籍制度的教育家,弟子众多,英杰辈出,虽教于一室之间,却俨然齐备圣王文章、礼乐制度,成平治之俗。孔子教育影响之大,不仅当时异说不能与之相抗,即便孔子殁后,诸儒仍讲习礼乐于其冢,其道“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史记·孔子世家》)。可谓“明立教之极”。反观荀子自己,“五十始游学于齐”,弟子中虽有李斯、韩非等才智过人者,却对礼义之道并不热心;虽曾“最为老师”,却未得英才而传其教,唯著书万言以明其道而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所谓“遇不遇者,时也”(《荀子·宥坐篇》),荀子所以不能效孔子行教化之功,在其后学看来,是由于时世不同:
孙卿迫于乱世,遒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诸侯大倾。当是时也,知者不得虑,能者不得治,贤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然则孙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谓也。是其所以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也。(《荀子·尧问篇》)
孔子之时,去西周未远,人们对传统制度犹有所敬畏。如顾炎武所论,“春秋时犹尊礼重信”“犹宗周王”“犹严祭祀,重聘享”,至战国时则风气迥异,“文、武之道尽矣”③参见顾炎武著《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故孔子虽不得志,尚有三千弟子愿从学周道,尚能以礼义之道指点当政者(事见《论语·颜渊》“齐景公、季康子之问政”)。当战国时,七雄竞力,士人竞智,“绝不言礼与信矣”③;文、武之道既尽,百家蜂起,诸子纷纷著书,各执一说,“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又常切近功利实用。在此“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之“乱世”,“仁人绌约,敖暴擅强;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荀子·赋篇》),荀子讲说礼义之道,不仅急于事功的“列国之君”“以为迂阔不达时变,终莫之肯用也”(徐干《中论·审大臣》),对一般的功名之士也缺乏吸引力,自然“名声不白,徒与不众”,遑论如孔子一样光辉广布,教于一室而具圣王文章、平治之俗。
因此,荀子说礼传道的方式必然与孔子有所不同。孔子聚徒三千,述而不作,携一“仁”字引领众弟子渐入于礼义之道,其弟子后学又传扬其教,此孔子所以为至圣先师。荀子固孔子后学,但于“师”一端所得甚薄,“徒与不众”,且时移世易,仁义之说、信念之论不足以动人心,故荀子不能效孔子凭私人教育以“仁”弘道,而唯有著书因势为说,以“接人用抴”的“宽容”之术劝人学道守道①参见《荀子·非相篇》。。其说礼所以持“治教合一”之论,当然首先在于当政者是其重要的论说对象。假使当政者能从道守道,寓教于政则礼义行而教化成。但更为现实的一个原因是诸子竞说,荀子谓之“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非十二子篇》)。孔子示教之时,“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荀子说礼则必然首先要面对“十二子”的“欺惑愚众”之说②参见《荀子·非十二子篇》。。为此荀子不仅专作《非十二子篇》,《解蔽篇》《天论篇》《正论篇》《正名篇》《非相篇》《性恶篇》《乐论篇》《礼论篇》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非十二子”的论题。可以说,“非十二子”是荀书的重要内容,也是荀子传道所必须处理的一个极为重要问题。他所提供的“治教合一”的方案本身即包含对诸子异说的排斥:
听其言则辞辩而无统,用其身则多诈而无功,上不足以顺明王,下不足以和齐百姓,然而口舌之均,应唯则节,足以为奇伟偃却之属,夫是之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荀子·非相篇》)
确实,百家争鸣,不过各言其是。荀子著书立说,以一家言恐难以匹敌诸子之异说。何如“圣王起”,执治教之权清理异说?治教合一,则“天下聪明范於一”“人心无越思”;[2]132-133天下既归于礼义一道,岂有诸子异说?孔子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与之一致。这也说明,荀子实“孔氏之支流”,其说礼所以有异于孔子,主要还是由于时世不同,不得不“与时迁徙,与世偃仰”(《荀子·非相》),因势而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