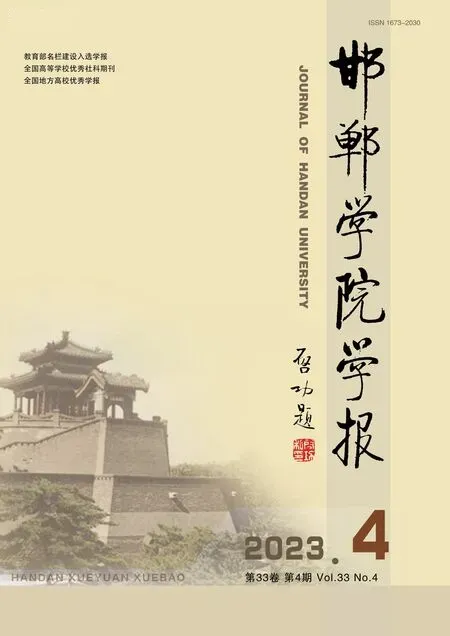《荀子》中“自然状态”与“第一位圣人”难题
2023-02-12路杨
路 杨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礼学”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而荀子是继孔子之后对“礼学”发展贡献巨大的思想家。阐述“礼”的起源时,荀子提出了“圣人制礼”说:“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性恶》)相比于孟子把“辞让之心”视为“礼之端”(《孟子·公孙丑上》)而提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的内在化论证思路有鲜明差异。但是,荀子“圣人”概念的引入又增加了新的问题,如果“礼”是“圣人所生”,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像追问“礼”的起源一样追问“圣人”的起源。
荀子提出,圣人在“生礼义法度”之前,需“积思虑,习伪故”(《性恶》)。也就是说,成为圣人要经历学习、积淀的过程。“伪”成了“圣人”与“礼义”之间的中介。成为圣人需要“习伪故”,而“礼义法度”生于“圣人之伪”。因此,荀学研究中一个著名的难题就产生了,“制作礼义”的“第一位圣人”从何而来?梁涛先生这样阐述这一难题:“一方面礼义是圣人所做,是出于圣人之伪;另一方面圣人又是实践礼义、化性起伪的结果,这样第一个圣人如何制作礼义便成为无解的问题,陷入到底是圣人制作了礼义,还是礼义成就了圣人的循环之中。”[1]16本文将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与“第一位圣人”难题相关的内容加以澄清,试图消除加在荀子思想上的各种误解与成见。事实上,阐明荀子的思想构造中完全没有秩序规则的“自然状态”在历史上是否真正成立,是解决“第一位圣人”难题的关键。
一、圣人制礼的人性起点
《荀子》中“圣人”概念极为重要,是阐述其政治与伦理思想的出发点。荀子的行文叙述中,无论是“化性”“移质”,还是“神明自得”“通于神明”,抑或是“全萃”“全之尽之”“能定能应”等,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圣人形象加以描述。“化性”是从人性角度,言其摆脱了原初的“恶”的状态,“神明”是描述其智慧的神妙莫测,洞彻普通人不能察觉的隐微之处,而“全萃”则是论述圣人人格的完满周全。“起礼义”则是圣人由己达人,造福于人类全体,并进而达成与天地并立,参与完善宇宙秩序的关键一步。因此,荀子提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礼论》)如果没有天地,就不会有万物以及人类的产生,生命的存在与维持当然是达成善治的基础。但是人类产生之后生存状态的优劣,却不是天地所能决定,而是依靠“君师”的治理。为感念天、地、君师为宇宙秩序的完善做出的贡献,祭祀之礼就是以此“三本”为对象。没有作为“君师”的圣人,就没有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则,这也是后人需要祭祀先王的原因之一。
“君师”虽然合成一词,但其意义却各有所指。“君”指的是作为人类共同体“群”的领导者,这是从政治视角对圣人作出的规定。而对于“师”,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儒效》)如果说“君”代表政治统治权力,给人类群体带来压迫性的力量,那么“师”作为统治者就试图达成百姓的心悦诚服,以及道德行动的自觉自愿。①东方朔先生认为:“圣王概念则表现出伦、制两尽,德位一体的人格特征,作为兼具‘圣’与‘王’的人格,‘圣王’表征着道德权威与政治权威(权力)的统一。”参见东方朔《荀子的“圣王”概念》,《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显然,作为“师”的百姓的引导者和教育者更是荀子笔下“圣人”的形象。荀子说:“师者,所以正礼也。”(《修身》)以“师”称呼圣人,着眼于道德教化与秩序完善。因此,在“圣王”统治的理想形态下,君主不仅是政治统治者,也是“礼”的制定者。
不同于其他先秦儒学文献如《系辞》中论述的“圣人观象制器”所建构的“圣人制作”观念,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圣人制礼”说是与其旗帜鲜明的“性恶论”密切关联在一起。②《系辞》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系辞》中的“圣人制作”,着眼于补充人类生活的不足,并没有对人性做出判断。圣人为什么要制定礼义法度,荀子在多处文本中以不同形式进行了阐释说明,其主旨就是针对“人之性恶”: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荣辱》)
执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王制》)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
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乐论》)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执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
虽然只有《性恶》篇明确提及“性恶”,但以上几段材料几乎都包含对“性恶”的诠释,其中一致的论证理路是:人类出于本然的欲望,会对外物产生相应的追求,在自然资源不足的条件下,就会形成相互斗争的情形。这种混乱的状况遭到了圣人的厌恶,因此圣人发挥其聪明才智,为人类制定了规范,使得每个人的欲望都能有限地得到满足,让国家整体有序运行。《乐论》篇中提出,人会因为快乐过度而得意忘形,实际上是从情感角度表达欲望的无限性特点。《王制》篇中“势位齐”而争,只是为了表明在没有等级界限约束的情况下,争斗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无所顾忌。规定等级秩序,是礼义的功能之一,所以“势位齐”也就与“无礼义法度”含义相等同。而《性恶》篇出现类似的内容,则是荀子基于“人之性恶”的立场,论证圣人制礼作乐的目的,就是要对偏颇险恶的人性进行矫正。
如何理解“恶”?从“生之所以然”的角度论,“性”具有“偏险悖乱”的特性。从欲望引发的追求所导致的现实后果言,表现为人类社会的“争”和“穷”。“性”必然会引发“穷”的后果,是荀子将其判断为“恶”的根本原因。荀子说:“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性恶》)这句论述也可以简化表述为:人没有经过师法、礼义的矫正,所以是“偏险悖乱”的。
对“性”做出“恶”的道德评价,仍然要以合乎“礼义法度”的有序状态为判断基础。近年来,荀子研究中存在以“性朴论”概括荀子人性论的观点。当然,人性为“朴”本身不与“恶”相违背,“以朴为恶”在荀子思想中仍可以成立,“朴”与“恶”只是从不同角度出发描述人性。①以“性朴”为“性恶”观点,可参见曾暐杰《“性朴”即是“性恶”——儒家视域下的荀子人性论之衡定与重构》,《邯郸学院学报》2019 年第4 期;吴飞《文质论视野下的荀子人性论——兼评性朴论之争》,《孔子研究》2023 年第2 期;以及李巍《“性朴”即“性恶”——由《庄》观《荀》的新辩护》,《人文杂志》2023 年第8 期。实际上,“性朴”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人性本身是无善无恶的。②这种观点在兒玉六郎的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以“性”为“先天性”事物,如果“不加以修为”则为恶,“加以修为”则为善,善恶皆是“后天性”事物,是对人性的后天引导方向的不同。参见兒玉六郎《荀子の思想——自然・ 主宰の両天道观と性朴说》,东京:风间书房,1992 年。荀子以“无师法”“无礼义”来论证“人之性”,在逻辑层面上,将“性”的概念放在了“礼义”之前,“性”的存在更具有优先性,而善恶则是置之于礼乐的视域中审视而来的结果。在“礼义”之先就已经存在的人性,怎么可以用后起事物作为标准来衡量呢?③举现实中例子而言,自然界中本无所谓害虫、益虫之分别,但以人类经济生产活动为标准,有益于粮食生产的就是益虫,有害于粮食生产的就是害虫。类比这种思考方式,人性即是自然界中的昆虫,本无所谓善恶,而礼义就是人类农业生产的标准,在此标准下,人性被评判为恶。如果承认“性”在“礼义”之先,视之为无善无恶,或超善恶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如此,本文将在后文说明“性”概念在荀子思想中相对于“礼”的优位并不存在,因此以人性为无善无恶也不能够成立。
在荀子的描述中,圣人似乎成为超出人类群体的卓越个体,置身于常人的世界之外,观察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并为之痛心疾首,想做出一些事情改变现状。实际上,荀子有“途之人可以为禹”(《性恶》)以及“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荣辱》)的表述。虽然这些论述更具有劝学导人的意味,但不可否认,荀子也否认了圣人与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可以总结出两条基本结论:其一,仅就人性而言,圣人与常人之间在人性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圣人并非是超世间的存在,而就是在世间之中。从可能性上说,圣人顺其本性,也可作为为了满足欲望而相互争夺的人之一。①梁涛先生将此总结为“人性平等说”,即“圣人与凡人人性是相同的,圣人乃后天努力的结果”。参见梁涛《〈荀子·性恶篇〉“伪”的多重含义及特殊表达——兼论荀子“圣凡差异说”与“人性平等说”的矛盾》,《中国哲学史》2019 年第6 期。其二,成为圣人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圣人也是从“性恶”状态的常人,通过一定的修养工夫“化性”而成圣。
先秦儒学中存在着圣人“生而知之”的观念,在荀子思想中却不能够成立。首先,人性应当视为人所普遍具有的共性,普遍性就意味着即使是圣人也不应当被排除在外。另外,荀子有破除禨祥巫术的思想倾向。《非相》篇中,荀子强调应当是德行而非面相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圣人的依据。这就意味着,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并不是某种前定命运的安排,而是出于自己的德行修养而达成。如果某人注定成为圣人,只能将其解释为来自于“天”或“帝”的意志。这种解读在荀子“天人相分”的世界图景中很难成立。
二、化性成圣的三条道路
(一)尊师法,学礼义
需要意识到,“恶”只是荀子对人性作出的道德判断,是针对谋求欲望的无限度满足的自然倾向而发。但作为“生之所以然者”的“性”之中,却不只包含欲望一项内容,还包括荀子所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王制》)、“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性恶》)等。人先天具有能够把握义理的知的能力,也有能遵从礼义的行的能力。成圣需要能知与能行的先天之“性”的充分发挥。在这一方面,圣人与常人当然也相同。
成为圣人,无论何种途径,都需要一个长时段的为学修身的过程。《荀子》的开篇两章主题即为“劝学”与“修身”,以“终乎为圣人”为目的,足以看出荀子对二者的重视。总结起来有两个方面要点:一为“善假于物”,即选择正确的为学路径;一为“锲而不舍”,即坚持不懈地积累用功。为学修身的正确方法,就是“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劝学》)。荀子强调,相比于六经之文,作为“类之纲纪”的“礼”更为重要。“文”只能停留在语言中,而“礼”可以渗透到人的身体和言行举止。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同上)要使人性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仅要让思想发生转变,也要行之于外。因此,“礼”高于六经不是偶然的。即使如此,荀子还是认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同上)“隆礼”在为学中也并非首要,而遇到合适的老师,得到恰当的指导才是至关重要的途径。礼法本是圣人所制作,与其机械地按照规定去做,不如掌握其中的精义和道理,才能够在各种情况中,尤其是缺乏礼法规定的情境中,都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具有恰当性。圣人的特征之一是“以义变应”(《不苟》),即把握礼义背后最根本的道理,以应对各种现实中复杂的情况。以成圣为目的的为学修身,就是试图做到“以义变应”的过程。
荀子为后学者指引出的成圣路径,无论是学礼还是求师,在礼义法度创制之前都难以成立,由此会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圣人是礼义法度的制作者,而成为圣人却要依据礼义法度。圣人制定礼义是为了矫正人性,而自己本来就是“人之生固小人”(《荣辱》)的一员,谁来矫正自己的人性呢?成为圣人需要先圣的指导,但作为“第一位圣人”却无人可以指导。当然这一悖论对于《劝学》篇而言,并不构成挑战。荀子写作《劝学》篇的目的,就是要让后学者产生向学、向道之心,告诉他们成为圣贤的方法,这是针对当时的后学而发论,不必涉及圣人的起源问题。在荀子的时代,尧舜等先王的存在,礼乐制度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儒家学者的普遍共识。荀子阐明,遵循礼法,遵从师教,都是“善假于物”的捷径,更能够确保效率和可靠性。但是,对荀子思想整体,必须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
(二)习俗化性
“礼义师法”适用于后世服膺儒家思想的学习者的成圣之路,并不意味着成为圣贤只有这一种方法。荀子还提出了“注错习俗”,或“习俗化性”的思想。荀子说:
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荣辱》)
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荣辱》)
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儒效》)
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儒效》)
“俗”,顾名思义即是风俗、习俗,是人所处群体的普遍性的生活方式。“注错”,杨倞注:“谓所注意错履也,亦与措置义同也。”[2]139“注”,是从心而发,把心念集于其上;而“错”,等同于“措”,则是从行而论,指容貌举止皆能够按照习俗去履践实行。“俗”对人的影响,就是身处于其中,按照风俗习惯去思考和行动,久而久之自然使本性产生转变。很明显,习俗不同于礼义法度之处就在于没有固定性的标准与强制性的力量,但同样要求学习者用心专一和历久坚持。
习俗的引入是否可以解释清楚“第一位圣人”的产生?首先,必须认识到“俗”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相比于学礼义、学六经、尊师法,习俗对德性的培养具有不确定性,一旦不幸身处恶劣的风俗中,对人的培养也是负面的。荀子说:“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劝学》)从广义上讲,风俗的影响也是教化的一种形态。在荀子的观念中,蛮夷与华夏之人,从生物学意义来说并无绝对差别,只有风俗习惯的差异。蛮夷之地风俗恶劣,无助于德性的培养与人性的转变。其次,风俗本身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同样也是可以人为加以塑造的,因而不具有确定性。荀子认为音乐有“移风易俗”(《乐论》)的作用。圣王作乐也应当遵循“中平肃庄”的原则,以调节百姓的情感。风俗的不确定性与可塑性表明,要想通过“习俗化性”的方式成为圣贤,需要“居必择乡”(《劝学》),选择良好的风俗环境居处,而良好的风俗也要依靠前代圣贤的塑造。因此,“习俗化性”的思路与尊师法、学礼义的道路并无本质差别,必须依赖于已有的文明成果与道德充盈的社会环境。联系到荀子所讲人类因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引起争斗的情况,即使存在着良好风俗,如果不能努力维持,也很容易遭到破坏。风俗的形成依赖于群体成员的某种共同行为倾向,这比个体的道德意识更难以培养。所以,如果存在着“第一位圣人”,由“习俗化性”产生的可能性较小。
(三)以心化性
当然,荀子思想中还隐含了“以心化性”的成圣之路。实际上,无论是“学礼义,尊师法”,还是“习俗化性”,其根本作用机制,就是使心的方向发生转化,让人性中本有的能知道理与能行道理的能力表现出来。心能够做到“可道”,不会“可欲”,就不会追求欲望的无限制满足。而且以心为路径解释善的来源,也是当代研究者的普遍看法。如梁涛先生提出荀子思想中,心不仅是“认知心”,更是“道德智虑心”。他说:“在荀子那里,最早的礼义或善来自心,是‘圣人积思虑,习伪故’的结果,同时又成为后人学习、认识的对象。”[3]71-80东方朔先生认为,荀子思想中人性的原初结构存在着许多自然情感与道德行为具有关联。而能够完成人性的转化,“其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内在于人性的自然情感为人们最初的道德义务感的养成提供了动机和条件,所谓第一位圣人的产生即是经由这样一种动机机制的逐渐转化的过程,而圣人的产生即意味着人类摆脱‘自然状态’、建立秩序社会成为可能。”[4]99-109与上述两种观点类似的论述颇为常见。
荀子的一段关键的论述为寻找心能够发生转化的可能性提供了根据: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王制》)
这段文字中最重要且最需澄清的就是“义”的含义。在《荀子》中,“义”常常与“礼”连用,作为礼的同义词,并更强调不是具体的条目仪则,而是作为标准准则之意。而作为单独使用的概念,指的也是符合道义的尺度,如“义荣”“义辱”。其次,“义”也代表圣人所掌握的准则规范背后更深层的根本道理。荀子说:“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不苟》)“义”可以引申到“宜”,有“义”才能做到“宜”。当曲则曲,当直则直,从容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适宜,不被表象所局蔽,就在于能够掌握曲直背后的原因。然而,这一段中出现的“义”,与“分”密切相关,“分”既可以理解为分别,也可以理解为名分、职分,可视为人在社会中的分工或等级界限。杨倞注:“义,谓裁断也。”[2]382“义”是“分”能够产生并施行的原因,指称的是人内在具有的能够认识判断并且能够遵从外在的界限秩序的能力。实际上,《荀子》中“义”的意义都是可以互相贯通的,只是有内在具有还是外在,可见还是不可见的区别。“义”在心中即是内在、潜在的能力,表现在外就是现实、可见的规则。
然而,“义”作为判断和遵从界限秩序的能力,无论如何都属于一种使善成为可能的因素。如果每个人都先天具有,那么称“人性有善”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这对“性恶论”构成了某种挑战。何艾克(Eric Hutton)专门对“义”的问题是否与善相关作出了讨论,他反对倪德卫(David Nivison)将其理解为“义务感”,认为这里的“有义”并非意指“先天具有”。甚至“好义”也可以理解为人总是希望别人做符合道义的事情,而使自己获益。[5]220-236本文赞成何艾克对荀子人性论的“一致性”的判断,即“义”并不构成人性中称为善的因素,但并不赞同其“后天性”的解读。首先,“义”虽然属于人的一种先天能力,但并不意味着能够自发地表现出来。①可举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说明。每个人都有学习数学的能力,但如果没有接受过教育,就不可能自发表现出来。在荀子思想中,知善与行善也是在教育的基础上,将潜在能力加以现实化才具有的。在无师法礼乐的情况下,只会呈现相互争斗的情形。因此,即使“义”之能力的先天具有,也无改于人性的原初表现仍然为“偏险悖乱”。其次,“义”的提出是在论述“人禽之辨”的语境。相互争斗的状态中,人类与禽兽无别,但人却有化性成善的可能性,而禽兽不具有转变之可能,这也是“人有义”判断的重要意义。具有成为道德存在的可能性,仍然比不具备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者更为尊贵,即人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禽兽。而尽管人性中“有义”,却不能称为“善”,就在于这种能力无法自发地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义”是人性可以转化为善的条件,却不是善的原因。
“义”作为一种先天能力,其充分发挥表现为“心”对“道”的理解。《解蔽》篇中,荀子提出:“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解蔽》)“心”以解蔽的方式了解“道”,并进一步接受和认可,就是人性转变的途径。“道”在荀子思想中含义深刻并且复杂,浅层而言可以代指方法或礼法制度,深层而言则等同于“以义变应”中的“义”,代指准则规范背后的根本道理,这只有圣人才能够完全掌握。荀子认为,“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解蔽》)万物变化多端不可能穷尽,而“道”可以贯通万物之变。因此,发挥“可以知之性”,达成对“道”的理解与掌握,就是为学的终点。
但是这样一条道路,仍然需要“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解蔽》)“以心可道”的化性之路,也就是“义”之能力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圣王为师,以圣人创立的法度作为标准。与“礼义化性”的道路一样,在这里又陷入了循环。
实际上,无论是从“义”的角度,还是从“心”的角度去讲心灵转化,以至于人性转变,包含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有外在的契机,引导作为行为发动者的“心”发生方向性改变。本然的人性中不包含将“心”引导到正确方向上的内容。因此,仅仅诉诸内在性因素,试图为圣人的产生寻找依据也不能够成立。“礼义”或者“师法”都是让内心走出欲望追求的外在性因素。尽管每个人都具有“义”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认荀子人性论在针对圣人与常人上的一致性,不仅“性恶”一致,“义”的能力不能够自发呈现也应当一致。如果设定圣人出于某种不可知的偶然性,无需学习即能表现出来,实际上与“生而知之”也并无区别,这是荀子思想体系所没有的预设。
综上所述,虽然荀子为后学提供了成为圣人的多种路径,无论是“尊师法,学礼义”“习俗化性”“以心化性”都具有相通性,“礼义”与“习俗”都要作用于人心才能有其效用。总体而言,需要兼具内在能力与外在契机。内在能力每个人都具备,但更需要的是外在契机,即借助前代圣人的留下的思想资源与制度实践。虽然荀子清晰阐明了成圣的路径,却仍然留下了“第一位圣人”究竟如何产生的问题无法解决。
三、作为理论建构的“自然状态”
荀子所阐述的成圣道路,都需要前代圣贤指导,或需借助他们所制作的礼义法度。可见“第一位圣人”如何产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荀子的关注,我们是否应当反思,对于“第一位圣人”的追问是无意义的?是不是我们的思考角度不同于荀子?
“第一位圣人”的追问只能在全无社会规则的情境下才能够成立,也就是荀子的描述中人与人相互斗争的“自然状态”。这个概念格义自西方政治理论中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指还没有产生国家前的状态,这个状态下没有人的法律,但是却有自然法的存在。①关于荀子的“自然状态”思想的研究,可参见孟庆楠《自然与治道——先秦诸子自然状态学说的比较研究》,《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1 期;杨玉婷《荀子的“自然状态”理论》(收入东方朔《荀子与儒家思想——以政治哲学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年);与霍布斯、洛克等西方思想家的“自然状态”学说进行比较的文章也有许多,如陈之斌《霍布斯与荀子关于“自然状态”之比较研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8 期;孙旭鹏、赵文丹《荀子与洛克政治哲学比较》,《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9 年第4 期。显然,在此意义上,显然荀子的思想并不与之相符。如果对荀子思想中的“自然状态”进行界定,应当是“前礼义”的状态,同时也就是无国家、无秩序的状态。
东方朔先生在对荀子论“礼”之起源的解释中,区分了“建构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来自于当代学者提出“礼”起源于原始社会之间的礼尚往来,也就是商品货物交易。而“建构的真实”则是类似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他提出:“荀子试图通过这样一种建构出来的叙述结构将其有关礼义法度的构想和建立一种‘井然有序之社会’的蓝图整合成一种圆满的统一的理论系统。”[6]177东方朔先生的观点极具启发,但只是强调了荀子的礼论中思想建构性的意义,忽略了荀子本人的历史叙事中“礼”与“圣人”之间的互动。“历史”首先不应当是当代学者对历史真实的重构,而是荀子本人对历史发展的观点与态度。
实际上,判断荀子的“圣人制礼”说到底是一种历史叙事,还是一种理论建构,首先应当考察荀子对人与人之间相互争斗的“自然状态”的历史真实性的判定。“自然状态”的历史真实性,决定了思想家对于如何走出“自然状态”的不同选择。②墨子也构想了一个“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的历史时代,而建立秩序的起点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这里“选天下之贤可”的主语应当是“天”,表明在墨子思想中,走出无秩序状态所依据的是作为人格神的“天”的意志。
首先,在论述“圣人生礼义”的相关文字时,荀子都是以推论的语气来论述。如“争则乱,乱则穷”句中,都以“则”为转折,是很明显的推论之辞,而非现实情形的描述。其次,考察荀子的叙述逻辑,无不是强调出于人性会导致“争”,因而产生“乱”,进一步导致破坏“群”。“群”才是荀子关注的重心。荀子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王制》)“群”是人类生存必须的组织形式,如果“群”遭到了破坏,作为个体的人以其有限的身体条件,无法存活于自然环境之中。荀子用“少顷”一词来表达礼义对于维系“群”之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因此,从“群”存在的连续性与必要性来判断,礼义法度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一段时间是不存在的。
如果用逻辑推论的语言加以说明:
1.前提:在且只在“礼义”存在情况下,“群”才能存在。
2.条件:“群”在历史上每个时代都存在。
3.结论:“礼义”在每个时代也都存在。
推论表明,只有“争”与“乱”,而无礼义法度的“自然状态”,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①韩非子对于“圣人制作”的历史观也有自己的看法。《五蠹》篇中,韩非子叙述了一个人口稀少,能够自给自足的时代,但是却因人口的增加而使资源变得不足,引起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很明显,韩非子把荀子作为理论性构造的“自然状态”发挥为一种历史事实的想象,两者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同时也要注意,“争”和“乱”的倾向在任何时代,即使礼法制度很完备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对于某些人而言,即使行为上遵循礼义法度,内心中也有也仍然存在求利的心理倾向,或者道德行为源自于自利的动机。《性恶》中,荀子借尧之口说:“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在更符合自己心理欲求的情况下,即使原来有遵从礼义的道德行为,也会因欲望的满足与再生而有所衰降。这些论述都可以归因于“性恶”的人性状态,即使礼义法度每个历史时代都存在,但人性的现实表现也无不是追求欲望的满足。如果说人性中欲望追求的无限性是导致“争”从而引起“乱”的根本原因,由此导致“群”的破坏,那么礼义法度就是规定合理分配,限制欲望膨胀的因素,是让“群”得以维持的力量。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不断用礼义法度约束人性的历史。在圣王在世的时代,礼义完备,遵从礼法成为习俗,国家运行状态良好。而在桀纣一样的乱世,礼乐废弛,人更多表现为对欲望的追求与满足,因而斗争不断。但荀子的历史叙事中,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也不缺少礼义法度的存在,只是缺少人的遵从。
当然,礼义也要区分像“周礼”一样粲然完备的礼法体系,以及仅仅包含礼义原则的不够周全的制度规则。但是,如果认可每个历史时代都有礼义存在的解释,就会认可“自然状态”是一种并非历史真实的思想假说。“圣人”只能在理论建构中直接设定,不会在历史发展中凭空产生。礼义在每个时代都存在,就会有使个体成为圣人的外在契机。
实际上,从“自然状态”中产生“第一位圣人”的问题实质,是从总体性视角追问“性恶论”的内在矛盾。“自然状态”就是“性恶”的最极端化表现,如果历史上真实存在着这一时代,在人性不包含任何善的因素的前提下,就不可能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但是,把荀子的“自然状态”视为一种纯粹理论建构,无疑有取消“圣人制礼”论断的倾向。如果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礼义法度,圣人何需制礼作乐?“自然状态”可以说是一个构想出来的理论,但礼乐却是现实存在的事物。从先秦儒学思想来看,圣人尤其是周公“制礼作乐”是一个被儒者普遍接受的观念,如果不是历史上的圣人制礼,那么现实中的礼法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因此,仅仅将“圣人制礼”视为理论建构是不完备的。
四、“古今一度”的历史叙事
我们将“自然状态”学说视为荀子的理论建构,圣人作为“制作者”也就无需化性而成。但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无论是夏商周还是上古三代的礼法制度,均出自于尧舜以及周公等圣人的制作,而这些具体的圣人需要经历成圣的过程,需要借助前代留下的制度遗产。①《大略》篇中,荀子说:“故礼之生,为贤人以下至庶民也,非为成圣也;然而亦所以成圣也,不学不成;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圣人制作礼义的目的,是为了矫正百姓的人性,本意并非为指导成圣,但是成为圣人却需要借助礼义。荀子在这段文字中清晰地表达了历史上有制作之功的圣人也需要前人指导的事实。圣人是礼义法度的制作者,不仅是理论建构,也是历史叙事,荀子在论述的时候将其交织在一起,使得后世的理解出现了混淆。
由此,应当对圣人的抽象人格与具体人物作出区分,相应地,礼义也应区分为一般性原则与具体条目。从理论建构上说的圣人,是一个抽象的人格,面对的是人与人相争的“自然状态”,因此其制作的礼义,代表的是一般性的人类社会规范与原则,是约束并引导人性向善的力量。而从历史叙事角度讲的圣人,都是历史有传的某一时代真实存在的人物,如尧舜禹周公等,而他们所制作的礼义法度,也是曾经存在过的具体的礼法条目,如周公所制作的“周礼”。如果涉及起源的追问,只能针对具体的人物与具体的制度。而谈到抽象人格与一般性规则,则不应当存在起源问题。
一般性的圣人人格对应具体性的圣人人物,一般性的社会规则对应具体性的制度条目,两者具有同构关系。圣人能够“以义变应”“宗原应变”(《非十二子》),这就如同“道”一样“体常尽变”(《解蔽》)。恒常不变的根本道理无法以具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能够表现出来的只有在某一具体时代和场景之中的条目,但这些具体性的规则只是“道之一隅”(《解蔽》)。同理,圣人作为抽象人格,也并非某个具体人物所能完全表现。然而,反过来说,“道之一隅”背后也蕴藏着“道之整全”,而具体的圣人所掌握的也就是作为整全者的“道”。
荀子思想中有“古今一度”的思想,可以作为上述阐释的文本依据。战国时代的国家关系与社会状态,是之前任何一个时代从未出现过的。因此,许多思想家认为,面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状况,无法用以往的思想经验来处理,需要创新出新的治理模式来应对。②《韩非子·五蠹》:“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世异则事异”的变化观和进步观在韩非子思想中明显呈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源头就是韩非子。这种观点遭到了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坚决反对。荀子在《非相》篇中写到: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可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圣人何以不可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③王念孙认为,此处应为“古今一也”,以“度”为衍文。参见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实际上,此处“度”音当为duó,以己度彼。此段可说明,前代与后代圣人所思所想皆同,是从对“道”的理解角度发论。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
荀子所谓“妄人”提出世界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的论断,是为提出新的治理原则作出铺垫。在社会形态不变的情况下,儒家的王道理想或许有效,但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也就应当作出相应的调整。荀子不能接受其观点,但却不能否定其前提,即社会和国家的确发生了变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情况。以往任何时代的实际状况,都不能作为普遍一般的社会形态出现,而只能是具体性状态的一种。即使是尧舜之治,也只是适合于当时的最佳治理模式。尧舜之所以为圣人,尧舜统治之时之所以是理想时代,主要原因就在于完成了抽象原则的具体化转变,并且能够用于当世。同理,荀子时代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改变,治理措施也需要相应调整,但不应当在圣人所掌握的根本道理之外。圣人只有时代的不同,他们所理解的道理没有不同,所以荀子讲“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古代与当世之间只有社会形态的变化,却没有治理原则的变化,因此有“古今一度也”的判断。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荀子强调在历史记载缺失的上古时代,并非没有圣贤,他们与后代的圣人掌握根本道理完全一致,只是因为年代久远,文献不足征所以湮没无闻。荀子所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也可以进一步证明,荀子并没有认可一个完全没有规则而只有人与人相争的历史时期,与“自然状态”相关的表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理论建构。荀子的“法后王”思想也与之相应,“先王”与“后王”本无差别,而只有历史时期的远近之别。廖名春先生早已提出:“通过法事迹‘灿然’的后王而去法先王,显然要容易得多,这就是荀子在主张法先王的同时又提倡法后王的原因。”[7]117
从历史叙事的角度讲,五帝之前的社会状况到底如何?荀子因为历史久远没有给出具体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这是一个没有完善的礼乐制度却有一定规则的时代。梁涛先生说:“《王制》称:‘君子者,礼义之始也。’‘始’,开始之意。故礼义最初是由君子参与制作的,而君子之所以为‘礼义之始’,不仅因为其有义,更重要的是能自觉按照义去调节利益冲突,他们是‘伪故’的主要制作者,为圣人、先王进一步制礼作乐奠定了基础。”[8]5-11梁涛先生对于圣人之前的时代“自觉按照义去调节利益冲突”的描述有合理性,但他的论述的前提仍然是“自然状态”的历史真实性,不同于本文的解释思路。①这是梁涛先生基于“性恶—心善”说所进行的描述,作为善之根源的“道德智虑心”可以无需借助外在因素,以“心之为”的方式从完全没有善性的状态中创造出善来。在此基础上,可以承认“自然状态”的历史真实性。而本文并不赞同善性因素的无中生有,认为人性转变必须借助外在契机,因此将荀子的历史观描述为没有“第一位圣人”起源的历史。荀子称五帝之外“非无贤人”,而不是言“非无圣人”,仅有一字之差,说明历史无考的上古时期当然也有圣贤,其德行却不如尧舜周公。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五帝之前的卓越者称为“贤人”更为合适。圣人制礼作乐之前也有善政善法,却不如“周礼”那样周全完备,但应当蕴含着与“礼义”相同的原则。在此意义上,“第一位圣人”也可以存在,但应当指代第一位功业德行最完满的圣人。
社会制度的不完备,可以促使后世的圣人进一步制礼作乐,这就可以说明,即使是历史叙事方面,对“圣人制礼”的强调也是必要的。道德功业完美的圣人,也需要借助以往积累的文明成果,才能够发挥其本有的先天能力而成为圣人。回顾荀子所述的成圣路径,只要外在社会环境中有道义法则存在,对于那些聪明睿智之人就已经足以通过学习实践与积累完成人性转化,将潜存的能知义理与能行义理的能力实现出来。历史上圣人的“制礼作乐”更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根据时代情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将根本的治理原则具体化为适用于当时的制度设施。
余 论
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荀子思想中“第一位圣人”问题并不存在,因为人与人相互斗争的“自然状态”没有历史真实性。“自然状态”只是一种为了说明人性状态的理论构想。或者说,缺乏礼法的制约,是人性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乏产生争斗与走向混乱的倾向。另一方面,从荀子的历史叙事的角度讲,“第一位圣人”却存在,但圣人之前也有不同程度上理解圣人所掌握的根本治理原则的贤人,每个时代也都存在着基本的社会规范。在完全没有礼义法度的世界中人类群体无法存续,只是礼义法度的完备程度与圣人人格有高下之别。即使所处时代的规则秩序不完备,也足以使后起圣人能够理解其中所蕴含的道理。
可以看到,荀子思想中既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能够清楚意识到当时社会形态的变化,并试图寻找合乎时势的治理措施。同时,荀子与儒家其他思想家一样,在对治理国家原则的认知上,缺少历史意识。荀子提出“古今一度”的历史观想要表明,无论社会情形怎样发生变化,治天下的根本原则从来没有变过,尧舜周公等圣人的历史经验仍然可以被后世所用。当然,也不能够原样照搬式地直接运用。孔子有“三代损益”的思想,夏商周三代之间虽在制度上有差异,但却是连续不断的整体。通过夏商周三代相因的例证,也可以类推而知后代的情况。①《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并没有言明历史演进过程中,能够因袭的是哪些方面,能够损益的是哪些方面,荀子的思想无疑是对孔子“三代损益”观的补充和发展。相比于恢复已经被历史淘汰的制度规范的复古思维,荀子的历史意识可以说极具进步性。但是,如果说治理国家的核心原则只有确定性的形式,却没有确定性的内容,更无法诉诸确定性的语言,在现实政治中就更具有灵活解释的空间。正因如此,荀子所构建的能够一贯古今的“道”,也有被其自身内容的空缺性所拆解的危险。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答。既然荀子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理论构想,不是真实的状态,其含义在于礼义法度的缺失。那么,礼义的存在就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而人性中缺少礼义法度的因素,就不能够被认为是自然合理的。人性应当具有善的因素,与人性现实状况缺乏善之间形成鲜明对立,导致荀子对人性的评价是负面的。缺乏礼义法度的“自然状态”的设定不具有历史真实性,把人性视为无善无恶的“性朴论”就不能成立,这是因为,历史上人类就没有脱离礼义规则的时段,作为个体的人自从出生以来,就处于礼义法度的规范之中,也就意味着自始就应当被道德评价的目光所注视。因此可以说,荀子“性恶论”的证成,与“自然状态”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也存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