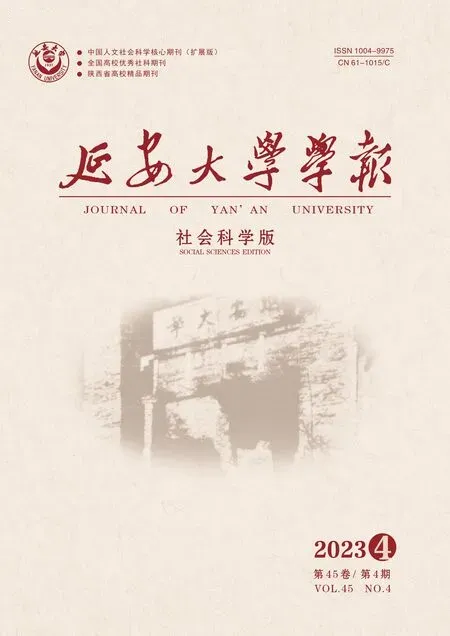论《文心雕龙》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与改造
2023-02-11黑磊磊王小艳
黑磊磊,王小艳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作为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思想宏富的文论专著,《文心雕龙》从其问世之日起就备受关注。刘勰从历史、哲学、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旁稽博考、取精用弘,这种广阔的理论视野让《文心雕龙》的价值超越了文学批评,成为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经典。《文心雕龙》文学批评思想体系背后的理论资源一直是“龙学”研究的热点,从子学视域下考察刘勰文学批评思想的构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路。目前,学界已经就《文心雕龙》与子学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总体而言,刘勰的著述立场是儒家的,在《徵圣》《宗经》等篇中可见,但是通览《文心雕龙》全书,我们也能发现刘勰文学思想的兼容并包之处。道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重新梳理刘勰文学思想与道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让我们看清刘勰文学思想的理论谱系,也能重新认识《文心雕龙》背后的理论渊源。
一、《文心雕龙》论“道”:从宇宙本体向文章本体的演进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奠基者,《道德经》一书被刘勰称为“五千精妙”。老子通过短短五千言的著作,为道家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后世的中国思想史留下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老子思想中只有很少的言论涉及文艺问题,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对于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启发。
(一)自然之道与作文之道的互通
道家思想标榜“自然”,但是这个自然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64意在说明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都是顺应自然的,即天地万物的运动没有任何意志,最终统一于“道”。“道”依照自然规律运行,创化万物,万物亦依照自然规律运动,最终回归“道”。这样的运动周而复始,永不停息,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老子认为,人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只是“道”的自然运行中的一个瞬间而已,所以人应该“知常”,这个“常”就是“不妄作”,就是复归自然。“不妄作”就是庄子所说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2]590不因一己之私欲心生妄念,为外物所役使,从而丧失了其自由自在的本性,成为被指使的工具。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非常重视“道”,开篇即探究了这个问题。《原道》中的“道”很大程度上是对老子“道”的取法,刘勰对于“道法自然”的命题进行了深入地阐释,从而建立了“道”与“文”之间的源流关系。《原道》指出“文”之产生根源于“道”,“天文”“地文”和“人文”都是“道之文”的不同体现形式,都是“自然之道”,即都符合老子对宇宙万物运行生灭的描述。刘勰在“自然”范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本质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3]1这种对“自然”的肯定和重视与老子所谓“道法自然”的观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除了《原道》,刘勰在许多篇章都表现出对“自然”的重视。《明诗》中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65这是用“自然”来说明文章必然具备抒情言志的特征。《体性》谈到艺术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3]505这里则用“自然”说明作家之个性必然表现于文章之中。《定势》中说:“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3]529这是用“自然”说明文章写作必须顺应文体的特点,也就是文章之“势”。《丽辞》谈到对偶的运用而谓:“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3]588这是用“自然”说明文章之有对偶乃是自然形成的,是符合人的思维特点的。《隐秀》中的“秀句”说:“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3]633“自然”强调文章中的“秀句”必须自然形成,而不是刻意雕琢。刘勰的文学本质论认为,文源于“自然”;在文学创作论上,刘勰强调要遵循“自然”,不能生搬硬套,刻意雕琢。
《中国美学史》指出:“老子看到了大自然中一切事物的产生变化都是无意识、无目的的,但其结果却又都是合乎某种目的的。自然并没有有意识地要去追求什么,达到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达到了一切,成就了一切。”[4]87老子的“道”“无为”和“自然”等核心范畴包含了对必然与自由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老子在此基础上而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些命题和思想虽然没有专门讨论文艺美学,但是其中所包含的美学意蕴对于后代理论家和作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从本质上看,老子的“道”乃是必然与自由的统一。“道”是自然运行的,背后没有意志的推动,所以它是自由的;“道”的运行又是周而复始生生不灭的,因此,它是必然的。刘勰的文艺思想延续了老子的这一命题,从“道——天——地——人——文”的演化序列来看,文学的产生是必然的:“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3]2从文学创作论上来说,文学又是自由的,因为它是人的创造力的产物,是人心活动的外化,因此,刘勰文学思想呈现出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特征,也就是一种超越人为和功利的审美境界。
(二)山水之美与文学呈现
老子对“道”的描绘呈现出一种审美境界:“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1]52“道”是恍恍惚惚,难以名状、难以把握的,然而“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1]31“道”是“无中生有”,从无形无象、不可名状中产生出绵绵不绝、气象万千的天地万物,这个过程和艺术创作的过程非常相似。陆机在《文赋》对这个过程有非常生动的描述:“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可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5]89陆机所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就是对文学的创作中“无中生有”的现象的论述,“虚无”“寂寞”是老子对于“道”的描述,这个寂寞虚无的“道”具有源源不断的创化能力,能够孕育万物。文学的创作过程也是对于宇宙本原“道”的追求,用文字来“原道”。老子的思想极大地启发了陆机和刘勰,他们的文学本质论和创作论可以说是对老子智慧的借鉴。
老子重视宇宙的本原与运行过程,因此能够跳出人的狭隘的功利视野,实现对于宇宙万物的整体观照。自然山川、草木虫鱼在道家思想中和人一样,具备了独立的地位和意义,道家思想对于后世山水文学的产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思潮涌动,士人受道家思想熏染,喜欢流连山水,欣赏自然风物之美,促成了山水文学的鼎盛。
《文心雕龙》继承了道家思想中对于自然山川的亲近之感,为后世文艺美学思想奠定了一个基础。《文心雕龙》中有很多对于自然风物的精彩描绘,比如《诠赋》:“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3]134《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3]493《物色》:“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3]693以上都是情景并举,这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也是刘勰的美学追求。《隐秀》中刘勰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美学范畴——“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3]632刘勰认为描绘景物应该做到“物色尽而情有余”,这个说法给后世诗学意境理论的产生以重大启发。“文外之重旨”即是“物色尽而情有余”,都是要求文学在情景交融的描写中要包含深远的意蕴,要有言外之意,韵外之致。
二、《文心雕龙》对道家生命美学的重估
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对道家思想进行了深入地拓展。庄子生活的时代比孔子、老子的时代更加动荡残暴,所以庄子的政治思想相较老子更加激进,他完全抛弃了人的群体生活的意义,认为儒家所崇尚的那套仁义之道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2]350庄子冷眼热肠,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深切而清醒的认识,因此庄子对于儒家的批评也是先秦诸子中最为深刻的。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仁、义、礼、智等是保证社会和谐有序的价值体系,但是庄子却撕下了儒家的仁义的面纱,认为他们所提出的社会理想是迂腐不切实际的。庄子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人们之所以要选择群体生活,遵循儒家的名分之教,其实是自身陷入困顿的结果;如果人能获得想要的自由,那么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庄子既然不关心人类社会的构建,也就不主张复杂的人际关系。
庄子在《齐物论》中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高下贵贱对错美丑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人之所以不自由,原因是“为物所役”,而这里的“物”既指物质,也指观念。一个人被物质世界驱使奴役和被观念世界驱使奴役本质上没什么区别,这样的人最终会在疲于奔命之际变成一具空壳。人类社会之所以陷入一片混乱,原因一方面是统治者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是人们头脑里难以消除的观念斗争,这种斗争集中体现在对于是非的判断中。不同人坚持不同的是非标准,而又试图将这样的标准强加于人,这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混乱与随之而来的斗争。“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2]63人类社会越来越精巧细碎、巧舌如簧的是非争辩,越来越条分缕析、头头是道的善恶说教,使得人们越来越疏离真正的“大道”,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被口舌与唾沫分割的碎片世界,这是庄子认为的导致社会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庄子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人的异化、追求自由。这一核心思想是通过对“道”的论证来展开的,“道”的阐释揭示了人的普遍生存困境。
(一)从宇宙论走向人生论
庄子的道论思想与老子一脉相承,老子只用了“五千精妙”来讨论“道”,庄子则对“道”进行了繁复的描述。《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长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2]231“道”是真实的、终极的存在,未有天地之前“道”已经有了,它在一切之上又在一切之中,这些都是延续了老子的观点。“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2]733庄子思想中的“道”相比老子本质上没有太多的变化,“道”的特征仍然和老子的论述相似,其核心就是“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总根据。庄子强调人要与整个自然、宇宙合而为一,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274其实就是让人回归“道”的状态,从而体会人的自然本质,以此来对抗人类社会由于“名分之争”带来的“异化”。人回归“道”就是回归自然、自由和无限,李泽厚说:“就实质说,庄子哲学即美学。”[6]386也正因如此,庄子的许多命题与文学艺术精神是息息相通的;较之老子,庄子思想对中国文艺理论产生了更为普遍而深远的影响。
庄子的“齐物”思想让他对于天地山川之美非常钟情,他宣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强调人应该去领会自然之美,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2]735庄子的“天地大美”的思想体现在了刘勰的《原道》中,刘勰在探究文章本原的时候说:“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3]2刘勰的原道思想是全书逻辑体系的根基,他认为人文与天文、地文都是本于“道”,这一点刘勰与庄子思想是一致的。
虽然刘勰认为文章写作的目的是对儒家经典思想的阐发,但是在具体的创作中,刘勰更加倾向于庄子的思想,认为文章写作的动机来源于天地万物之美的感发。《神思》中,刘勰指出文章的构思是“心物交融”的过程:“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3]493这里的“珠玉”“风云”等比喻都是在强调万物对人心的感发。在《物色》,刘勰用非常诗意的语言来描述自然之美对文学表达的触动:“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3]693刘勰认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3]693又说:“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3]693所谓“山林皋壤”之说,正来自《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2]729文章的“江山之助”,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
(二)物质嗜欲与创作天机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27深刻认识到了沉迷于感官享受对于人的朴素内心的扰乱。庄子也认为,人为的创造物都是低下的,“有机事者必有机心”,[2]423所谓“机心”就是指人对外物的依赖所产生的机巧之心或者投机之心,人一旦有了“机心”就会“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2]423就是说人的内心的纯朴浑融之心会被破坏,因此人将“心神不定”,就无法“致虚守静”,实现对于“道”的体认与观照。这样的人将成为“无根”的人,成为宇宙间孤零零的碎片。
庄子轻视任何使人内心变得不自由的东西。据载,楚威王听说了庄子的学识与才华,派人用重金请他辅佐自己治国理政,并许以高官厚禄。庄子见到了楚国的使者高傲地说,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灵龟,死了几千年了,现在被绫罗绸缎包裹着供奉在庙堂里,请问这只龟是愿意死了享受如此尊贵的礼遇呢还是愿意活着在稀泥里拖着尾巴爬来爬去呢?使者知趣而退。(1)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03页。庄子在这里想说明的是,生命的价值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人的内心。《逍遥游》中讲到尧想让天下于许由,许由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2]27天下尚且不为所动,何况他物?
庄子在书中讲了很多能工巧匠的故事,比如著名的“庖丁解牛”“梓庆削木为鐻”等等,意在说明,人只有不为毁誉赏罚、功名利禄所动时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虚静,进而获得一种“与道同在”的喜悦,最终通向庄子所向往的自由之路。庄子所说的“嗜欲深者其天机浅”[2]235“外重者内拙”,[2]644都是说明贪恋外物与内心自由之间的冲突。
除了对待外物的态度,庄子对于得失生死问题的看法最能体现其对于人生的态度:“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2]269死是一个人所能面对的最严重的危机,庄子对于死的态度非常达观,这种达观来自庄子对于人的生命意义的独特理解。老子说:“知常曰明。”这里的“常”是指人未降生之前是“无”,死亡之后又重新回归“无”的状态,“无”即是永恒与无限的道,因此人的死亡只不过是“归根复命”,知道这个自然的过程就叫“明”,即智慧。老子死了,庄子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2]136“安时处顺”就是遵循道的运行的自然规律,而“贪生怕死”则是“遁天悖情,忘其所受”,[2]135即不能洞悉生命来去的本质。
刘勰在《养气》与《神思》两篇中发展了庄子的生命哲学,并把庄子的思想融入他的文学创作论。“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3]647这里刘勰引用了庄子“庖丁解牛”的典故,说明文学创作的准备必须做到内心的虚静自然,下笔才能游刃有余。
三、《文心雕龙》对道家哲学的创作论转化
刘勰提出文学创作是感物而发的自然过程,通过创作把“物色”之美转化为“文采”之美。庄子认为,天地之“大美”就是“道”之美,它杜绝了一切的人为造作,纯任自然,因此是一切美的最高境界。庄子提出的“法天贵真”思想就是要人回归“道”的真实与纯朴,反对人为的欲望和矫饰。庄子说:“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2]467“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2]542在庄子的思想中,自然、纯真、朴素既是美的极致,也是个人修养的极致。这种追求真朴的境界体现在刘勰的《情采》中:“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愈殊。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3]537刘勰认为,文学的辞藻是为作者更好表达思想感情服务的,如果没有真实的感情,徒然炫耀华丽的辞藻,这样的辞藻是没有意义的。庄子思想中这种返璞归真的诗化倾向也被刘勰吸收,形成了刘勰独特的美学风格。
(一)诗化哲学与宇宙观照
“道”是自然无为的,因此“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强调的“法天贵真”就是崇尚素朴之美,追求与天地万物同一的终极境界。为了实现这种境界,庄子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身要求。比如,庄子认为人要追求“物化”,方才能领会“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齐物论》中庄子用了一段故事来说明:“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也。此之谓物化。”[2]119庄子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的梦境来说明人与物融为一体的体验,“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此时庄周是真正臻于“物化”之境的。《神思》中刘勰集中论述了自己的艺术构思论:“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494这里提到的“虚静”思想和“意象”理论受到庄子思想的启发。庄子的“物化”说对于人(心)和物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如“乘物以游心”[2]142“游乎天地之一气”[2]233“以游无极之野”[2]381“出入六合,游乎九州”[2]381“游乎万物之所终始”[2]634等等。这些“游”,都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游历观赏之意,而是一种精神观照活动,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刘勰所说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艺术构思活动,与庄子之所谓“游”有内在的相通之处。
庄子的“虚静”是继承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以及“涤除玄览”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庄子认为“虚静”是泯物我、同生死、超利害的具体途径或手段,即只有心灵上达到“虚静”,才能做到物我合一,继而才能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老庄的“虚静”成了古代美学和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虚静”在哲学上是通向领会自然无为之“道”、进入自由和无限的世界的必由之路。在文学构思和创作上又是实现平静专注的创作状态的重要手段。庄子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2]154这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精神修养论,其本质就是不断排除外在的干扰,专念息想,进入一种专注的沉思状态。刘勰在创作论上进一步发展了庄子的“虚静”理论。
(二)言意之辨中的文学
庄子对于言、意关系的探究本意是为了说明“道”的特点:“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2]739庄子明确地讲“道”是“不可言”的,然而他的整个哲学即以“道”为核心,无时无刻不在谈“道”。不仅要“言”,而且要从各个方面把“道”讲清楚,因此,必须面对和解决言、意关系之间的张力和矛盾。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2]569庄子虽然认为言论不能够很好地表达深刻的“道”,但是他并没有否定语言的表达功能,庄子的这一思想经过了王弼的阐释引发了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成了魏晋时期的一个经典命题。
关于“言意之辨”的讨论直接促进了文学写作理论的革新,因为言、意关系始终是文学写作的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陆机在《文赋》中指出,文章写作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5]1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成为历代文论家关注和论述的重点。刘勰在陆机的论述后指出了造成“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3]494的原因,即“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3]494刘勰认为,“言不尽意”的原因在于言实而意虚,以实逐虚便有很大的困难。陆机和刘勰的讨论开启了中国美学史和文论史上经久不衰的讨论,到了唐宋时期,诗话词话大量出现,而其中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依旧是言、意关系,可以说这些都是在庄子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刘勰文学批评体系对道家思想的吸纳与改造是多方面的,正如有学者指出:“魏晋玄学把外在感性、情感性、道德性、知识性等新内涵移注到了道家思想中,实现了一次儒道兼容的理论整合。在这种背景下,道家注重个体自由、注重纯美的出世美学理论资源与儒家注重文明教化、注重道德情感的入世美学理论资源进行了一次大碰撞和大综合。正是在这种儒道融合的大碰撞中,以刘勰为代表的六朝艺术创作“虚静”理论应运而生。”[7]37道家思想是魏晋玄学的理论根基,刘勰身处玄学思潮鼎盛的齐梁时代,不可能不受道家思想的浸染。可贵的是,刘勰并没有陷入玄学思潮的抽象论争漩涡,而是把道家的思想命题融入了自己的文学批评体系,体现出他作为一位理论家的学术驾驭能力。
近年来《文心雕龙》的研究趋于沉寂,如何推进“龙学”的研究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新子学”的提出给我们以新的启发。《文心雕龙》虽然被后世列为集部中的诗文评,但同时也可以算作论文中的子书。在六朝后期,子书与集部交融的现象已经形成。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论之甚详。(2)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页。集部成为取代子部的“一家之言”逐渐走向确立与成熟,子部汉魏之后又呈衰微之势。东汉之后,文人盛行编撰文集,文集遂代子书而兴起,成为著述的新载体。作家开始在文集中投入全副精力,通过“编集”来追求精神的不朽。(3)参见袁济喜,黑磊磊《论〈文心雕龙〉与子学流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76页。虽然子书在六朝人著述思想中的影响力极大,但较新兴的文集还是出现了地位下降的趋势,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从子学与集部的兴衰演变中可以重新审视《文心雕龙》的思想构成与思想意图。刘勰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研究是坚持“折衷”的学术态度,其中就包含了立足儒家,兼采众家之长的意味。他对道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改造拓展了其文学思想的哲学深度。如何打破旧的思路,重新梳理刘勰思想的理论谱系,是“龙学”研究亟待探索的学术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