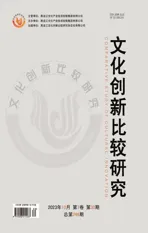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创伤书写
2023-02-09刘颖昕
刘颖昕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 571158)
《长日留痕》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作品于1989年获得布克奖,被誉为英国战后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作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之一,石黑一雄善于将西方元素与日本元素巧妙结合,创作出风格别致的国际化小说。在《长日留痕》中,他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英国的政治和文化及个体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变化,以质朴、细腻且典雅的叙事风格,通过男管家的主观叙事视角,讲述了一段为期6天的旅程,并交叉着他对过往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追忆与思考。在管家史蒂文斯零散且不可靠的回忆叙述中,揭示个人经历对个体的创伤及在大英帝国衰落现实中的集体创伤。
“创伤”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伤口”,后被应用于心理创伤。而弗洛伊德、詹尼特等人对创伤心理机制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创伤记忆作为跨学科研究的焦点,如今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在文学批评中。“笼罩在现代文学中的人物心理的分裂、疏离感、异变和价值观的冲突等,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了创伤记忆的心理阴影。”创伤是石黑一雄作品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美国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经评价:“石黑一雄是我们当中最擅长阐释‘失去’这一主题的诗人。”[1]正如石黑一雄所说“我所写的是关于个体如何面对痛苦的记忆”[2]。《长日留痕》 以日记体的形式展开叙述,“日记的形式具有一个额外的优势,那就是间歇性时间结构。作为分散微小碎片的集合体,日记是一种反映自我意识的断断续续、自相矛盾、支离破碎的理想形式”[3]。石黑一雄以时间顺序建构叙事框架,同时将对过去的回忆和现实并置交叉,逐步完成了对史蒂文斯自我的重识和内心的救赎。对于史蒂文斯而言,对过往经历的回忆,是他慰藉内心的一种方式,但也是他掩盖过去的借口。因为在他闪烁其词的措辞和辩白中,读者能够很快捕捉到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的不可靠性。而这种不可靠的回忆叙述也成为史蒂文斯创伤经历的佐证。
1 史蒂文斯的创伤表征
创伤事件会使人形成创伤记忆,而人对身份的认同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叙述与记忆实现的。作为服务于达林顿府这样显赫门第的管家,史蒂文斯毕生的职业追求就是成为一位“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的管家。而他一味沉浸在对职业信仰的追求,过分压抑和逃避了对亲情与爱情情感的表达,最终导致了个人尊严的消尽和自我身份的缺失。
1.1 来自家庭的原始创伤
史蒂文斯对于自我情感的克制与压抑,与他原生家庭中情感的缺失不无关联。弗洛伊德曾在其心理分析理论中提到,成年之后很多不合乎常理的行为大多是因童年创伤的影响。在没有遭受过一些灾难性事件的前提下,诸如史蒂文斯的这种创伤可以归结为结构性创伤。首先,在史蒂文斯的回忆叙述中,未曾提到过自己的母亲,自童年以来母爱的缺失可能对他的心理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其次,父亲对于史蒂文斯兄长死亡的冷漠,史蒂文斯的兄长死于南非战争,可悲的是这次阵亡源于作战指挥官的严重失职。事件发生的10年之后,同样作为管家的老史蒂文斯竟恪守职责地去侍奉这位前来拜访的指挥官。史蒂文斯更是辩解道,父亲虽然对指挥官将军十分憎恨,但却压抑了自己的情感,表现得过于冷淡和麻木。死亡是最极端的创伤经历,情感的麻木、漠然是受创后的基本表现,受创者表面上平静淡然,实际是一种被动的屈从。而这种冷漠也同样影响着史蒂文斯面对至亲之死创伤时的态度。
相较于母爱的缺失和兄长的死亡,疏离怪诞的父子关系更是加剧了史蒂文斯的创伤。老史蒂文斯曾经也是一位工作卓越的管家,从史蒂文斯小时候开始父亲就详述着其作为管家的经历:一位侍奉主人旅居印度的管家,在注意到餐桌下面蹲着的老虎时,却依旧淡定自若地表现出与身份相称的职业素养与尊严。父亲一直期望用强大的超我无意识甚至牺牲本能与自我,为史蒂文斯树立职业典范,也将自己偏执的观念灌输给他。这直接导致了父子俩除了工作无话可谈,甚至父亲在弥留之际依旧给予管家工作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忽视了自己的生命和父子情。面对难得抽空来探视的史蒂文斯,父亲的谈话内容却是“楼下的一切顺利吗”。当父亲在去世前对儿子表露真心时说道,“我为你感到骄傲。真是个好儿子。但愿我对你曾经是位好父亲。我想我并不是”,而史蒂文斯给出的回应竟是 “抱歉我特别忙,我们可以明日再谈”。可见,父亲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影响到其对工作的执着与忠诚。究其原因,无疑是老史蒂文斯将自己偏执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强加于他的儿子,以父亲为职业标杆和作为“伟大管家的尊严”致使史蒂文斯丧失了主体性,受到来自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成一位符合职业原则的完美管家,就需要无限接近于父亲的理想与标准,放弃对个人意愿的服从与坚守。内化对欲望客体的寻找,并成为欲望的对象。
1.2 盲目追求职业尊严的个体创伤
史蒂文斯面对家庭关爱缺失的麻木及父亲的专制,使其埋下了创伤的种子,也直接导致了他在事业和爱情中留下无法弥补的悲剧。职业尊严是史蒂文斯毕生都在追寻的目标,但他的追求终究是虚妄的,不加辨别地执行达林顿勋爵的各种命令。小说中有一处细节:达林顿勋爵因为担心影响府邸与德国人的外交关系而要求开除两个犹太女仆,史蒂文斯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却依旧被“我对这种情况下应该履行的职责是非常清楚的” 的信念所左右,即使面对肯顿小姐的强烈反对,也未能阻止其开除了她们。他更是在此次事件之后提醒肯顿小姐“我们的工作职责不允许我们只顾及自己的癖好和个人情感,而是要遵从主人的意愿”。史蒂文斯在对自我身份的价值追求中沦为对主人唯命是从的仆人,将完成主人的任务视为对自我肯定的标准。
1923年,达林顿勋爵府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非正式国际会议,史蒂文斯将其视为自己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而就在会议最重要的一个晚上,老史蒂文斯突发疾病与世长辞,闻讯赶来的史蒂文斯并没有为父亲悲伤,而是出奇地将关注的重心聚焦在女厨师莫蒂默太太围裙上散发出的浓重的烤肉气味。父亲的离去没有影响到史蒂文斯对管家职业的坚守,在他眼中注视的是衣冠不整的莫蒂默太太,嗅到的是与死亡气息相悖的“烤肉味”。与此同时对“职业精神” 的过分追求,让史蒂文斯产生了扭曲的价值判断,他曾经认为达林顿勋爵为世界的和平与正义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那么为主人服务的管家也在间接地为整个世界服务。而史蒂文斯对主人和毕生追求事业的所有尊严与幻想都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主人达林顿勋爵被指控犯下了叛国罪郁郁而终后而破灭,酿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对于两性情感的压抑和逃避是史蒂文斯创伤经历的又一表征。肯顿小姐是达林顿府上出色的女管家,她工作认真负责且性格活泼而阳光。肯顿小姐曾多次将自己亲手采摘的鲜花送到史蒂文斯工作居住的配膳室,以表达对他的关心和好感,但却被史蒂文斯无情地拒绝了,他将肯顿小姐的行为视为一种威胁,因为他始终在坚持着作为一名称职管家的原则,杜绝与肯顿小姐产生除工作之外的关联。在屡次向史蒂文斯示爱而无果后,肯顿小姐毅然选择答应他人的求婚,离开了达林顿府。在史蒂文斯回忆的叙述中,曾多次提及数年后肯顿小姐写给他的信,他总是拿出来反复阅读沉湎于往事之中。一直以来他都在隐藏压抑逃避着对肯顿小姐的感情,去维护着他一直坚守的职业尊严。因为男女管家相好在他看来是私通,会被赶出达林顿府,“私通事件对府内井然的秩序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威胁”。在这次为期6 天旅程的最后,史蒂文斯特意去拜访了肯顿小姐,本想邀请其回归达林顿府继续工作,却得知肯顿小姐已然决定回到丈夫和女儿身边继续生活,史蒂文斯发出了“我的心行将破碎”的感叹,这也是他压抑多年首次向肯顿小姐表达爱意,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史蒂文斯为了追求管家的“尊严”,抵制住了两性关系中的情感诱惑。对于童年受创者来说,分裂是人格构成的主要原则,意识的分裂,阻扰了正常的知识、记忆、情感状态与生理经验的统合;自我观感的分裂,阻扰了自我认同的统合。因此,史蒂文斯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与他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4]。爱情带来的创伤是不可见的,但却成为史蒂文斯内心深处无法弥合的伤痕,终生未娶的他放弃了拥有爱情、家庭生活的权利,也为自己书写了痛苦一生的爱情悲剧和创伤记忆。
1.3 历史变迁中的社会性创伤
史蒂文斯回忆里书写的不仅是个人的创伤,也与二战后大英帝国的衰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种历史的创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逐渐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一部分英属殖民地也开始取得属地自由权。昔日的英国贵族走向没落,达林顿府也未能幸免。二战后,达林顿勋爵被定为亲纳粹派,被冠以叛国罪的罪名,臭名昭著,最后郁郁而终。而这一系列的社会历史性事件摧毁了史蒂文斯一直坚守的尊严和精神信仰,曾经的“辉煌成绩”变成了他的耻辱,在人生暮年体验了生存意义的缺失和虚无感。府邸易主后,史蒂文斯被作为“包裹的一部分”被转交给了新主美国人法拉戴先生。法拉戴先生代表着崇尚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美国,期盼弱化与史蒂文斯主仆之间的阶级身份差异,但史蒂文斯一时间无法适应美国文化,加剧了他的失落和痛苦。“他的作用常常是映射一段历史时期、其中的一些人或特定的文化、种族、性别,集体性地经历了巨大的创伤。”[5]史蒂文斯如同一个活化石见证了英国社会历史的巨变,也映射了英国管家阶层的集体创伤。
2 不可靠叙述与创伤
不可靠叙述的概念最早是由叙事理论家韦恩·布斯提出。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韦恩·布斯指出“当叙述者说话或行为符合作品的道德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叙述者是可靠的,反之,即为不可靠”[6]。《长日留痕》以主人公第一视角自传体的叙事展开,史蒂文斯支离破碎、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叙述构成了回忆的不可靠性。而一旦回忆触及痛苦时,史蒂文斯便会选择性地暂停或是回避,一些评论家将其归结为自我否定或自欺欺人。在审视史蒂文斯的叙述行为和道德选择中,必然会发现其在认知上的偏差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他这么做并非出自恶意,也非有意而为之。随着旅游进程的推进,史蒂文斯越发地陷入过去的回忆而不能自拔。作为一生忠诚服务于达林顿勋爵的管家,却可能在过往的工作中间接地成了亲纳粹党的帮凶,复杂的情绪使其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在史蒂文斯极力塑造的绅士风度的外表下,是他对数十年人生过往的悲叹与无奈。
2.1 零散的回忆
围绕回忆的矛盾冲突来展开故事,一直是石黑一雄善用的手法,回忆既是小说的叙述形式,也是他建构情节和主题的方式。他认为“记忆本身就是一个看待事物的透镜”[7]。小说中提及了两次重要的会议,1923年那次恰逢老史蒂文斯病逝,1936年的非官方会议期间肯顿小姐间接地向史蒂文斯表达了爱意,却被冷漠回绝,不久后她便心灰意冷地离开了达林顿府。史蒂文斯一直以来对职业精神的过分追求、对达林顿勋爵的愚忠和对内心情感的压抑,导致了他冷漠和罔顾的性格。可悲的是主人公本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对职业生涯的回忆叙述中,他毫不掩饰地宣称“我主要的满足是源于我在那些岁月里所取得的成功,而且我今天唯一感到骄傲和满足的是我曾被赐予如此的殊荣”。面对自身的人格悲剧,作为叙述者的史蒂文斯浑然不知,而是沉浸在父亲离世和肯顿小姐离开那两晚中其承担管家工作时的优秀表现,并将其视为“油然产生极大成就感”的职业辉煌时刻。史蒂文斯由于自身的认知局限,向读者呈现着现实生活与过往经历间的不可靠叙述。
2.2 错置的回忆
小说中,有一段对于肯顿小姐哭泣场面的叙述,而史蒂文斯却在自己过滤式的回忆中进行了曲解。最初,他将那一晚肯顿小姐的哭泣归因于她姑妈的离世,因为姑妈给予了肯顿小姐母亲般的疼爱。史蒂文斯对于至亲之死的冷漠让他没有对肯顿小姐产生怜惜,反而以更加严苛的标准督促她完成工作。可很快史蒂文斯又否定了自己的回忆,他更加坚信当天肯顿小姐的哭泣是因为她接受了别人求婚。回忆的模糊与不确定性印证了史蒂文斯在面对过往时的矛盾,他深知自己是有意压抑着对肯顿小姐的情感,内心的失落让他刻意选择了逃避历史。史蒂文斯的叙述是带有情感选择性和过滤性的,“夸大或缩小,省略或添加,扭曲或简化,因此历史是被加工过的记忆”[8]。从史蒂文斯被自己改写的记忆中,很容易捕捉到他不愿再现或是看不清的现实。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史蒂文斯对于二战期间和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达林顿府和达林顿勋爵的去世只字未提,我们不禁要反问,他为何刻意地隐瞒了这段历史?毫无疑问,对于他和达林顿勋爵共同经历的这段屈辱的历史,史蒂文斯再次进行了选择性的遗忘。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中阐明了遗忘运作的精神机制,他认为那些人们有意掩盖而想不起来的回忆或是暂时的遗忘症是受压抑驱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林顿勋爵的政治错误被揭示出来,而史蒂文斯毕生对职业的所有尊严和追求也伴随着社会现实被无情地否定和驳斥。如果史蒂文斯在回忆叙述中承认这段历史,就相当于承认了其服侍的主人在“世界事物”中的失败,也同时包含了对自我的否定。弗洛伊德在对梦的解析中提到,人的心灵中存在一些被压抑的愿望,“这些愿望属于原发系统,而它们的满足会遭到继发系统的反对”[9]。所以史蒂文斯采取了错置的回忆来进行自我安慰与麻痹,不去直面历史真相。
2.3 对主仆关系的否定
面对创伤历史,施暴者可能会不自觉地对其进行否定和压抑,或是采取某些必要的防御机制。一直以来,史蒂文斯都在竭尽所能地维护和崇尚着达林顿勋爵的完美贵族形象,认为其在人品和道德方面没有任何瑕疵。即便是在政治错误被曝光之后,史蒂文斯依然辩解道:“达林顿勋爵是位具有伟大思想情操的绅士——这种情操使那些你会碰见地对他大放厥词的人相形见绌。”史蒂文斯一边沉浸在服务于伟大绅士的价值满足中,却又多次在公开场合不承认他与达林顿的主仆关系。旅途中,史蒂文斯被问讯到是否曾服务于达林顿勋爵一事,他却用“啊,不,我现在受雇于约翰·法拉戴先生,这位美国绅士从达林顿家族中买下了那幢房子”的说辞予以遮掩。而面对他人的继续追问,史蒂文斯以着急赶路为由回绝了。另一次是当现在的雇主约翰·法拉戴的朋友韦克菲尔德夫妇来到府邸做客时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史蒂文斯依旧予以否认,他的回答也一度引起法拉戴的不解。史蒂文斯虽然矢口否认他与达林顿勋爵的主仆历史,但越是刻意地回避就越是放大了他的窘迫与惭愧,他终于渐渐意识到自己曾倾其所有附庸于他人的人生价值不过都是自我欺骗的谎言。
3 创伤后的身份重构
史蒂文斯通过回忆的叙述来揭示他曾不自知或是自我隐瞒的伤痛,宣泄了个体创伤。在6 天的旅程中,他找到了重塑自我和重新评价过去的契机。他开始审视自己曾经对新主人作出的解释“尽管并不全是假的,却是那么令人遗憾地不充分”,或许他开始努力正视和重新思考曾经所犯下的错误。旅行的第一天,在一位陌生男子的建议下,史蒂文斯爬上了一座小山,面对“数英里范围内最让人心旷神怡的乡村景色”,他被深深地震撼,“正是从观看风景的那时起,我才相信我第一次开始具有了愉快的心境,这将有利于我以后的旅行”。也正是从这一个经历开始,他逐渐卸下了在达林顿府马不停蹄工作的紧迫感,石黑一雄也希望借助传统英式乡村美景的治愈性,让史蒂文斯渐渐走出创伤的阴霾。一路上,史蒂文斯遇到了很多当地的英国居民,他们热情地招待他或给予他帮助,甚至还邀请他加入村民们畅所欲言的日常交谈中,而这一切都是他在达林顿府不曾拥有过的体验——轻松自如的生活。著名创伤理论专家和治疗专家德瑞·劳和朱迪斯·赫尔曼认为,创伤的修复需要“在关系中”完成。向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倾听者见证或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倾听者可以帮助幸存者将创伤事件重新外化、对创伤经历进行重新评价,帮助幸存者对自己做出公正阐释,重建正面的自我评价[10]。
小说的最后史蒂文斯遇见了一位倾听者,并向他袒露心声,卸下伪装地说道:“在我侍奉他的所有的那些岁月,我坚信我一直在做有价值的事。可我甚至不敢承认我自己曾犯了些错误。真的——人须自省——那样做又有什么尊严可言呢?”史蒂文斯过往的经历凝结了他的人生悲剧,而他对自我的认知和主体性的追求也在愚忠的服侍中消弭。面对史蒂文斯,陌生人劝慰他说:“那你就必须自我解脱。夜晚是一天中最美好的部分。你已干完了白天的工作。现在你能够双腿搁平来休息了,而且要享受人生。”[11]史蒂文斯在静默许久之后终于认同了他人的忠告,决定改变自己,积极地面对易主之后全新的管家生活和余下的人生之途。父亲的骤然离世和肯顿小姐远走他乡在史蒂文斯的心中留下了更多难以磨灭的伤痛,值得庆幸的是在6 天的旅行中,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尊严、克制和冷漠的执迷及它们所造成的人生遗憾。并且在对往事的回忆与反省中,认清了二战后的英国社会现实,重视自我。二战后的国民身份和大英帝国身份重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这场旅行的终点——滨海码头,史蒂文斯幡然醒悟。而滨海码头的隐喻象征着“自我与他者碰撞的阈限空间”[12],史蒂文斯在对自身由“异”趋“同”的过程中突破固有的认知框架,寻找身份认同。
有学者评价史蒂文斯的生活是无趣的、无意义的,因为他“是过去世界的幸存者。他的悲剧性在于他所依附的世界已经消失,给予他生命意义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但他还活着”[13]。史蒂文斯的悲剧性确实受到社会历史变迁的沉重影响,但石黑一雄赋予了其对未来的希冀和新的生命意义。勇于揭开过去的伤口,正视经历与伤痛,并完成自我的心理重建。正如小说《长日留痕》的名字一样,漫漫长日已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但史蒂文斯能做的是对往事回忆的反思、对自我的重构和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卸下伤痛与悔恨,期待来日方长。
4 结束语
《长日留痕》用回忆的方式,对小说主人公所经历的事件进行了碎片化处理和选择性阐述。石黑一雄借用一位“杰出”管家的视角审视着20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探讨了尊严、职业伦理与个人道德判断等一系列具有共同性的人类生存议题。石黑一雄用既幽默却又伤感的笔调,再现了现代社会对个体的压制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也在批判着个人主体身份的缺失、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及战争对平民造成的伤害等诸多现实问题,以独特的创作和批判视角书写着石黑一雄本人对创伤群体的同情与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