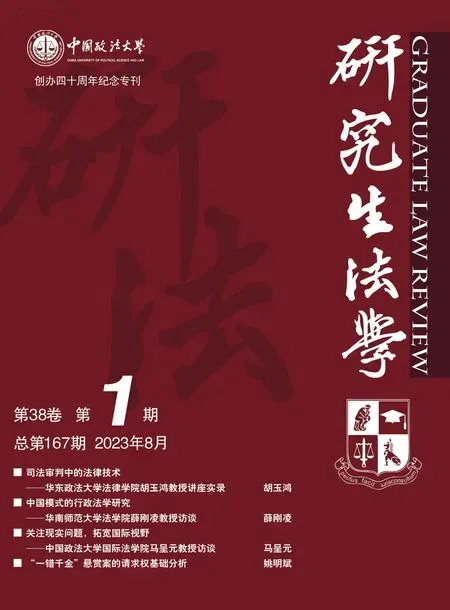廿七年来的回忆:从师问学、比较方法与中国话语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顾元教授访谈
2023-02-08顾元,王世扬,刘效江等
访谈对象:顾元(197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法文化史、外国法律史、比较法律史及中西司法文化比较。曾于《研究生法学》1998 年第1 期发表论文《论香港主权回归后的法源形式》。
访谈者:王世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2023 级博士研究生;刘效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2022 级博士研究生;葛嘉伟,比较法学研究院比较法学专业2022 级硕士研究生。
问:顾老师好,您曾在《研究生法学》1998 年第1 期发表《论香港主权回归后的法源形式》一文。请问您当时缘何选择在《研究生法学》杂志上进行发表呢?
答:这篇论文是我研究生二年级时写就的一篇习作。坦率地讲,习作当时想要发表的话,很难达到正式期刊的用稿要求。所以就想到了《研究生法学》。当年法大的研究生并不是很多,一届大概也就一百多人,博士生更少,《研究生法学》这本刊物在研究生中间还是很有知名度的。而且这本刊物由学生主编,感觉距离上也是我能够接触到的,所以我就投了一下。投完稿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也就出刊发表了。
问:请问当时您为何选择针对香港主权回归后的法源形式作文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是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您的学术路径呢?
答:之所以选择香港的法源形式问题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彼时关于港澳台法制的研究甚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香港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因为它既为英美法系地区,又受到清朝法律传统的影响,清代法在香港当时的法律实践中仍具有一定的地位。后一认识生发的契机源于郑秦[1]郑秦(1943-2000),北京人,1987 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三位法律史学博士之一,导师为张晋藩先生。留校任教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图书馆副馆长、成人教育学院院长、培训中心主任。老师。他在1996年前后给我们上课时提到,香港高等法院(或终审法院)曾请他去做专家证人,负责阐明清朝的法律和习惯。于是我们就了解到一个事实,即清朝的法律,尤其是在土地与婚姻等领域,在香港地区仍有一定的效力,但是需要专家进行证实。我对香港地区这种中西杂糅、现代与传统融合的法律实践样态感到非常好奇。其实,原本构思的是写香港主权回归前的法源形式,在香港主权确定回归后即改为了最终发表的这个题目。香港回归后,在香港适用的法律,除香港本地法、殖民时代形成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传统及清代法律与习惯等之外,还有基本法等全国性法律,几者构成了一个具有相当综合性和特色性的法律适用体系。所以,当时我觉得将香港的法源形式做一个梳理是很有意思的。于是,后来就有了这篇文章。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香港法一直都很感兴趣。包括2002 年留校以后,我还曾与郭成伟[2]郭成伟(1946-2023),1982 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获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制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老师一起讲过几年研究生的“港澳台法制概论”课程,但后来这个课取消了。[3]编辑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现设有“港澳基本法”“港澳台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课程。
问:法律史学的研究是一条少有行人的孤寂之路,在外人看来更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方才可能取得微末成就的学问。请问您当时为何选择了法制史专业;又为何选择了攻读博士学位,且将研究方向从外国法制史逐步转向比较法律制度史和中国法制史呢?
答:总的来说还是主要源于兴趣因素。其实,我在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对法史比较感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主要来自家庭的影响。我父亲大学期间是学中文的,毕业后是中学的语文老师,所以家里历史和文学相关的书籍比较丰富,我从小读过的文史类书籍也就比较多。等到上大学以后,虽然选了法学专业,但我其实对法律并不是很感兴趣,反而觉得有些枯燥,倒是对法制史产生了新的兴趣。大学毕业后,我曾回到老家市政府的法制局工作四年,主要处理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核等一系列工作,所以当时接触的主要是行政法。后来考研时,报考志愿就倾向于个人志趣。其实自己感兴趣应该是宪法(史),所以第一年考研报考的是复旦大学的外法史,因为复旦大学的外法史学科下有外国宪法史方向。当时报考的导师是李昌道[4]李昌道(1931-2021),江苏苏州人,1956 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任教,曾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和法学院首任院长。1987 年至1990 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高级研究员,从事香港基本法制定和研究香港法制;1991 年至1998 年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1998 年至2002 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曾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副主委等职。教授,他当时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也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最后成绩出来以后,他让我去复旦大学读自费研究生,这个当时在经济上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因此我后来就没有去。第二年,我就考了法大的外法史研究生,报考的导师是皮继增[5]皮继增(1938-),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外法史教研室主任。编著有《外国法律简史》(法律出版社1987 年版)《外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999 年版)等。老师,他是当时法大资历最深的外法史导师,也是法制史教研室的主任。
至于研究方向的转变,其实是有一些偶然性的。硕士毕业后,我本想读比较法律史的博士。我考博前的几年,朱勇[6]朱勇(1955-),安徽无为人,1987 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三位法律史学博士之一,导师为张晋藩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所长、中国近代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法律系主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曾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中华司法文明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老师名下曾有比较法律史(或外国法律史)的招生方向,但是我考博的那一年,这个方向没有招生。就报考的导师而言,我当时特别想投入张晋藩[7]张晋藩(1930-),辽宁沈阳人,1950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就读中国法制史研究生,1952 年-1983 年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导、博导,1983 年7 月调至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兼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所长,1983 年5 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导,1987 年被评为中国法制史重点学科带头人,1991 年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2001 年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2012 年被授予首届“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先生门下,所以我记得报名的时候就报了张先生。但又做了一种模糊化的处理,即在报考的导师一栏添加了一个括号,即填上了朱勇教授的名字。后来考完试以后,我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张先生录取,研究方向也随先生基本上转到了做中国法律文化史这一领域。但是,我一直觉得做中法史实际上和外法史并没有很大的分野。因为如果有外法史上对外国法了解的基础的话,对研究中法史可能从视野上、从研究方法上其实还是有很多借鉴和帮助的。所以,我现在经常在上课时跟同学们讲,无论是学中法史还是外法史,都不要简单地将二者隔离起来,那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做法。而且,不但是中外法史的前沿知识,其他的一些交叉学科包括部门法的研究成果,我们都应该去关注。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学校培养研究生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的。我们在学科门庭上不要太狭隘,如果这样的话,最终可能关注的东西太有限,反而对自己的学习研究不太好。
因为就读了中法史方向的博士,所以,除导师研究方向的影响之外,学位论文的选题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研究方向的转变。实际上,我时至今日都对外法史和英美法很感兴趣,但因为教学科研的安排,可能写的相关东西不是很多。而且,我实际上是硕士毕业以后就基本确定留校了,手续都办差不多了,是作为外法史的教员留在法律系外法史教研室。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的系主任朱勇老师还找我谈话,给我布置日后的工作任务。但是,后来因为某些至今也不太清楚的原因没有留校,而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是,我正式留校就延迟至2002 年博士毕业后。那时法学院给我排课排的其实都是外法史,包括到现在,我也给硕士研究生开外法史专题课程。所以说,我的研究方向虽然从外法史转向了中法史,但是对外法史的兴趣和研究是一直没有中断的。
问:您的硕士导师皮继增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张晋藩先生都是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泽被学林的法史大家。请问您的治学路径受到了二位先生的何种影响?在从师问学时,二位先生是否留给您一些深刻的记忆?您指导学生的风格又是否对二位先生有所继承呢?
答:我觉得正常情况下,每一个学生的学术道路肯定会受到自己导师的影响,而且一般来讲,这种影响的程度会很深。因为毕竟跟自己导师联系得多嘛,导师在各个方面对学生的影响都比较大,可能除了学术方面,其他方面也都会有:包括导师的人格力量、为人为师、处事方法,等等,这些对学生都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我的硕士导师皮继增老师,今年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你们可能没有见过,只能在网上找到只言片语的信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学术远不如今天繁荣,学校对老师也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科研考核要求,主要还是以教学为主,老师们的主要精力也都主要投入了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上面,所以大家可能看皮老师的文章和著作并不多。但是,我觉得皮老师人特别好,待人特别真诚、特别热情,对学问也是这样,在人格魅力方面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皮老师没有一点架子,在生活中对我们学生的关心和照顾特别多。老师就住在校园里,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到老师家里吃饭;他也经常会到学生宿舍,来和我们聊天,待人和蔼可亲,极有亲和力。
张先生就更不用说了,我到现在实际上还一直追随着他。因为法律史学研究院的前身就是20 世纪80 年代张先生创建的法律史研究所。我们这个研究院的工作,他也一直非常关注、非常支持。我从1999 年随先生读书,到毕业后留校——也是他把我留下来的。2001 年张先生被聘为法大的终身教授,需要配一个学术助手,所以我就成为了他的第一个学术助手,一直干到我留校以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这24 年没有离开过张先生,一直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去做一些事情,无论是读书写作还是后来的行政工作。2004 年以后到现在将近20 年,我们甚至住在同一个小区,他有事情找我也很方便。先生对我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最大的。这首先得益于对先生学术人生的了解。这么多年来,我对先生做过多次访谈,写过不少文章,[8]我觉得我是和先生联系一直比较密切、对先生了解比较多的一个学生。在与先生交往中,对他不断深入了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潜移默化学习的过程,他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风格,我都比较了解;包括他指导学生的方法与风格,也对我日后对学生的指导影响很大。
问:您是国内较早从事比较法律制度和比较法律史研究的学者。时至今日,比较法相关的研究已然充斥国内各大期刊和各校学生的学位论文,在许多文章中,比较法往往沦于字面,或成为纯粹的“技术”。您认为,正确的比较法研究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对于比较对象的选择,尤其是比较法律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应当遵循何种原则?比较法与比较法史的面相又有何相同与不同呢?
[8] 相关文章可参见顾元:《张晋藩教授: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1 期,第1-6 页;顾元:《法律史学的开拓、发展与中华法系的复兴——张晋藩先生学术访谈录》,载《史学月刊》2006 年第9 期,第98-107 页;顾元:《张晋藩 新中国法律史学开拓人》,载《中国审判》200 8 年第7 期,第32-37 页;顾元:《“不偷懒,不自满”——张晋藩先生的治学与修身之道》,载《北京教育(高教)》2016 年第10 期,第78-80 页;顾元:《张晋藩教授中国宪法史与行政法史研究述略》,载《中国检察官》2020 年第1期,第16-17 页。
答:我其实也谈不上是比较法的专门学者,只是对某些领域的比较法问题比较感兴趣,比如英美法尤其是美国的司法制度和宪法,但实际上也很难说做出了真正深入的研究。在这些领域,部门法学者往往比我们更专业,做的也更好。不过我们法史学者的视角与部门法学者也确实有所不同,我们还是从历史和整体的视角去研究得比较多。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法史学上的比较研究可能还不够深入、不够充分,实际上比较法也包含了将各国之间的法治历史作为一个比较的经典素材。我们国内比较法的发展可能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更多的研究可能还是一些简单化、功能性甚至介绍性的比较,其目的主要在于服务于法律移植。现在一些年轻的比较法新锐做的研究可能更好一点,这些学者经历过国外的法学教育,对外国法律制度和历史、文化了解更加深入,也就更具备研究的优势。而我们90 年代后期读研读博的这批学者,对于比较法或者比较法史的研究,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初始的阶段,写的文章也主要以叙述为主,偏重于法律制度的简单引介和比较。当然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学术发展过程。总的来说,我认为比较法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一个规范制度本身的比较,还要详细考究制度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差异,将几者联系起来,才能做出好的比较法研究,对比较各方都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和把握,才能谈得上所谓的借鉴。
关于比较对象的选择,比较重要的可能是“可比性”的问题。要把两个东西进行比较,首先需要建立起一个问题意识,即搞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做一个比较研究。所谓的可比性并不是表面化的——比如说我有这个制度,你也有这个制度,所以我们就要进行比较——这个就不见得是(唯一)一种可比性。有的时候可能不同的概念、不同的体系之间也会具有局部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也不一定需要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同时期、同政体、同国家结构、同社会形态、同法律部门,实际上都可能构成可比性的来源。而所谓的“可比性”往往也是个性化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当然,这些比较,可能相似性越强,比较借鉴的意义也就越显著。
比较法的落脚点在于我们国家如何对国外的先进法律(制度、思想)进行借鉴,实际上,比较法史在潜意识里应该也有这种关照,可能还暗含着上下优劣的一种比较。比如韦伯,他肯定就认为,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律和社会就是最先进的,你中国没有现代性的法制,所以你就是落后的。不过,比较法史的落脚点可能并不像比较法一样,那么地偏重功能,可能更多的是法律文化差异的比较和借鉴。
问:中国的现代法制多自西法移植而来,实际上与中华法系的传统法制有所脱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应当如何避免落入“法律东方主义”的陷阱呢?
答: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也很复杂,不太好回答。我还是尽量简要地表述一下我的看法,因为我现在不管做比较法也好,还是法制史、法律文化的研究,实际上也会涉及这个问题。所谓法律东方主义,可能主要产生自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而随着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和法律移植,实际上在国人中间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服膺于法律东方主义的倾向。除了文化上、潜意识中的不自信和自我贬低,这种现象也是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的。近代以后,中国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学理论乃至法治实践,都自西方而来,如果不采取这样一种话语体系,实际上很难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实定法层面的有效对话。但是,虽然在法律制度层面,中国的传统时代与近现代存在较大的断裂,但实际上在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层面,仍然还有很多东西是一脉相承的。包括中西方法律建构和发展的目标,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有共通点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法治文明的成果,只不过实现路径可能并不一样,不应对任何一方进行片面的否定。
具体到法律史的研究上,也就是如何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法律的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做法律史研究的一个困惑,或者说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从理论上来讲,研究中国法律知识、解释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法律现象、法律制度,都应该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去展示、去叙述。完全采用现代西方人建构出来的这一套理论体系去解释中国法律史,当然是无法周延的。但是,法律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往往又产生于现代法学的学科体系划分,会不自觉地受到西方法学话语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正常且很难避免的现象。但还是要有贴近中国历史情境去解释法史的意识,即同情之理解。不过,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古代似乎是没有一套区别于日常话语的单独的法学或律学话语体系的,它的特殊性很难被完全发现,这就导致了我们无法完全地融入古人的语境,去对法律史上的问题做出最切合古代的解释。这确实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困境,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是务实的,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那么古人为何会如此立法,是用来调整何种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产生的历史基础又是什么?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它是否实现了古人的预期,实现或没能实现的原因在哪里?这些问题可能是更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问:法律史学本质上是法学和历史的交叉学科。那我们应当如何综合利用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呢?
答:现在有所谓“法学的法制史”和“历史的法制史”的许多争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观点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张先生就认为,法制史首先是法学学科下的法制史,“法”的倾向性应当更加显著,法史学的研究也需要有与法学近似的追求。在具体的研究上,很多历史学出身的法史学者就会对法学出身的法史学者进行批评,认为其存在史料功夫不扎实、材料解读不过关、以论代史等等问题。而很多法学出身的法史学者,又会觉得以史料整理、史实还原为主要目的的纯粹历史方法在法史学科内价值有限。对于我们来说,方法使用的落脚点很大程度还是在于学科门类的划分。对于我们法学一级学科下的法律史而言,纯粹历史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法学的学科体系里面是很难立足的。不过,我们也不应当囿于门户之见,过度限制自己的眼界,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就像上个问题中提到的,我们也要警惕法学的现代性对历史研究的过度侵袭。
问:您认为,古代法制的研究在当今有何意义?我们应当如何使法律史研究经世致用呢?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史鉴价值了。历史当然是有“资治”价值的,自司马迁以来的历代史家都追求“通古今之变”,实际上就是追求历史的史鉴价值。这种追求也就提示着我们,历史研究不能过于虚无缥缈,还是需要关照社会现实,为当下的国家治理出一份力。但是我认为,并不需要在历史研究中明确地条列出所探讨历史问题的史鉴价值。因为如果你切入对某个问题本身的研究,就一定是带着对现实的某种关照,读者也是能够读得出来的,我们研究者本身实际上只需要做到把历史问题研究明白,借此微言大义,研究的史鉴意义也就能够明晰了。现在的许多法律史论文,特别是硕士论文,研究外国法制史,最后就写对中国的启示意义;研究中国法制史,最后就写对现代的借鉴价值。这种新式“八股”,实际上就把历史研究的史鉴价值给庸俗化了,不足为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