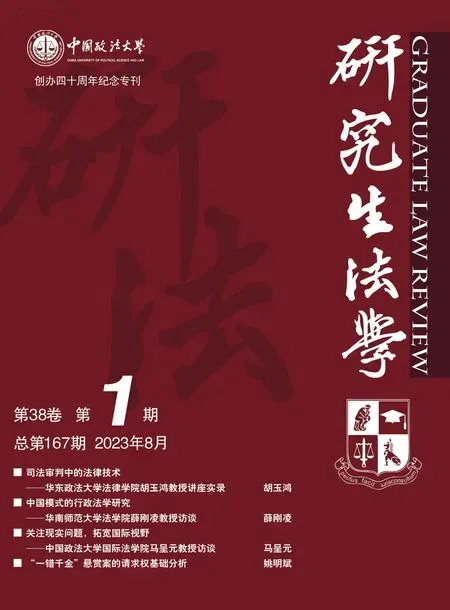法理学研究与学习导引:阅读经典、扎根传统、勤于写作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雷磊教授访谈
2023-02-08雷磊,陈冰倩
访谈对象:雷磊(1982-),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学者”。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中国立法学研究会、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逻辑学会法律逻辑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曾在本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以及译作,分别为刊载在《研究生法学》2005 年第4 期的《法秩序中的探索——〈法学方法论〉与法律解释理论》、《研究生法学》2007 年第6 期的《目的论扩张与法律原则的适用逻辑》、《研究生法学》2011 年第4 期的《如何学习法理学?》,以及《研究生法学》2022 年第2 期翻译汉斯·凯尔森的《论法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的界分》。
访谈者:陈冰倩,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2022 级硕士研究生。
问:作为“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您对我们青年学生有什么阅读建议吗?
答:学术阅读首先当然要阅读经典。当然,可能我们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包括各个导师的学术取向都不太一样。我觉得阅读是有一个从泛读到集中的过程的,我们需要做一个规划。就比如说咱们一年级或者说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可以从法理学的各个领域中都找一本书看看,可以听从一下老师的建议,你都去读一读。读了之后,则需要集中一下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生阶段跟本科生不太一样,本科生看书可以说是越多越好、越杂越好,但是研究生阶段应该往精专的方向去做。通过第一学期试错或者说宽泛阅读,再明确一个感兴趣的领域,然后进行专业化阅读。专业化的阅读要从经典开始,可以选取这个领域的一本经典的书进行精读,在此过程中展开学术化的阅读。我曾在燕大元照微信公众号上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就叫“如何进行研究型阅读”[1]编辑注:原文参见雷磊:《如何进行研究型阅读》,载微信公众号“燕大元照”,2019 年12 月13 日,ht tps://mp.weixin.qq.com/s/NoqiVdecUBM1K9_IxWJYNA。。我们需要以问题为中心去进行立体化的阅读:首先要找到经典的问题意识,围绕问题阅读,找出不懂的地方,然后再去查其他的资料。经典作品之所以为经典作品,要么因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要么是对这个重要的问题的思考往前推进了一步,它必然是在一定的学术脉络和传统中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它的“前后左右”,“前后”是指在同一学术脉络中往前追溯和往后延伸,“左右”就是要了解相近的立场和相反的立场。总而言之,学术研究贵在实践,它不是大工厂规模化生产,而有点像手艺活,需要边学边做。老师跟你讲再多的技巧和方法,你了解的很多但不去做,上手时还是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需要自己反复去实践和体会。
问:在查阅了《研究生法学》的往期目录之后,知道您在求学与任教过程中曾在《研究生法学》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您的整个学术生涯和《研究生法学》有着不浅的交集,可以谈谈您与《研究生法学》相识的渊源吗?是出于何种考虑才将《研究生法学》作为您早期投稿的目标刊物呢?
答:应该这么说,我在读书的时候,从本科阶段到博士阶段,学生办刊属于当时一个比较热的事情。从我本人来说,其实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曾经跟前后级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同学——今天这些研究生同学很大一部分在各个高校,也有在实务部门的——一起自己做过刊物,还是公开出版物。我们得到了一个从法大毕业的师兄的资助,请舒老师(舒国滢教授)起的名字叫《原法》,因为当时有个刊物叫《原道》,当然后来因为大家都各奔东西,所以慢慢地就没有再办了。总的来说,当时是这么个氛围。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本科生办的《学术法大》和研究生办的《研究生法学》当时在同学中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官办或者说学校办的刊物,所以投这个刊物也算是当时的一个尝试。我本科阶段就在《学术法大》发表过两篇文章,包括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发表于此。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我们都知道咱们《研究生法学》历史悠久,从1983 年办刊至今已经40 年了,有很多知名的老师都曾经在《研究生法学》上发过文章。当时我做的是方法论研究,硕士和博士做的都是这一领域,所以有了一些想法以后就投给了《研究生法学》,我学生时代在此发过两篇文章。而且当时我们有同学、后来也有师弟在做编辑、副主编。作为初学者,非常自然地我们会把一些习作投在《研究生法学》上。
当时的环境跟今天还不太一样,今天很多学生尤其是博士,投稿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要投一些核心期刊,因为今天的学术竞争比较激烈,要考虑到以后的就业。我们当时没有,那时博士毕业要求其实蛮低的,只要发表一篇1 万字的论文,随便发表在哪都可以,它没有什么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会考虑这个很贴近学生的刊物。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比我高一级的研究生,他是在《研究生法学》当主编还是副主编我记不起来了,他就说他有一次去开学术会议时看到开会的一些老师、包括知名的教授手里都拿着《研究生法学》。当时的刊物也不像现在这般等级森严,没有非常严格的级别界定,也没有区分C 刊(和普刊)。其实就是那时关注得很少,我们到博士阶段才真正开始关注所谓的刊物级别,我个人是在博士二年级以后才开始关注,因为在以前学校的整体氛围也不一样,重视、强调课题和论文都可能是在最近十几年才开始的。发文基本上对以前的老师们来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上学的那个年代,读书的氛围非常浓,老师们在教学方面投入的精力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后来整个评价标准都变了。
问:那时候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答:当时就是按部就班。我记得舒老师跟我说过,他说可能就那么轮下来,轮到我这到年龄了就是教授了,没有今天这么激烈的竞争。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还有很多所谓的青年导师,就是带着学生读书。比如王涌、龙卫球,当时年龄跟我现在差不多,甚至更年轻一点。当时评价老师的标准和今天不一样。今天老师要争各种资源,评价时要看各种头衔或者别的,当时其实不太关注这些,所以我们属于读书的一个黄金时代。我们研究生班里的同学还会出去读书,一起班里有读书会,我们还跑到清华大学去读书,一起去上高鸿钧老师的课。我们比较活跃,我记得我们承办了一个四校的法理学讨论会,就是北大、人大、我们和北师大,以学生为主讲人;我们还办了硕士和博士之间的法理学专业研讨会;还承办过全国首届的法学方法论研讨会。
问:了解到您博士期间在德国访学,受到了国际知名的法哲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教授的影响。从您既往发表的文章来看,您的法理学研究大多涉及的是欧陆法学方法论,可以结合您的法学教育背景,简单谈谈欧陆法理学对我国当代法理学学术传统的影响吗?
答:影响肯定很深远,我讲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里提到的法学方法论。我个人其实从本科毕业论文开始做的就是法学方法论,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一个关于法律解释的问题;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规范冲突的问题;博士论文写的是类比推理,都是方法论这个领域的。中国的方法论研究兴起于2000 年前后,当然最早的时候,在中国比较成体系性的著作是1995 年梁慧星老师写的《民法解释学》。后来1999 年王利明教授从台湾地区引入了他们的大法官杨仁寿写的《法学方法论》。这些著作主要是日本背景的,梁老师和杨老师都是具有日本学术背景的学者,但是从他们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深受德国影响,毕竟日本的法学方法论也继受自德国,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方法论研究到今天为止大概也就是30 年不到的时间,德国的方法论往远了不说,从近代开始至少可以追溯到萨维尼的法律解释的四因素,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高度发达和体系化的层次。我在2008 年去德国做联合培养博士的时候,是带着我的博士选题过去的。我第一次跟阿列克西教授约谈,他就告诉我在方法论研究上我应该看一些什么书,或者说做一些什么样的研究。他说德国方法论的研究大概有四种进路,向我展示要做类比推理这个主题可能的进路是什么。阿列克西本人是做分析哲学的,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且言简意赅,给我深入这个传统打开了一扇窗户。总的来说,我们的(法学)方法论发展受到了德国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你们都知道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最早是台湾译本,早在我们读博士之前,台译本就以复印本的方式流入了中国大陆,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简体版。因这本书的译者陈爱娥是台湾地区的学者,它对我们前期方法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在2016 年的时候,对欧陆和台湾地区的方法论在大陆的传播做过一个梳理,考察过很多大学的方法论课程体系设计,发现基本上都是以拉伦茨这本书为基础来做的,并区分了这个几个部分:事实的理论、规范的理论、法律解释和法的续造。也就是说,我国的方法论教学其实都是直接以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为基础的,这本书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当然这只是德国对中国法学方法论研究影响的一个代表,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书。德国的整个传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远,最开始(2000 年之后)是一些法理学者在做方法论研究,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部门法学者开始做这个研究,当然他们主要是结合本部门的法教义学展开研究,而这应该是方法论研究的常态,因为方法的生命在于运用。在这个方面,德国给我们积累了大量可以借鉴的理论渊源。
德国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有很多,第二个方面我就说一下法理学教科书。今天我们本科一年级的法理学教科书基本上谈的都是所谓的法学的基本概念。以此为主题的教科书是直接承继自苏联,1950年的时候从苏联传袭过来的。而苏联的这套模式和理论是对德国19 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一般法学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产生的。以前德国的法哲学,像康德和黑格尔,主要谈的是一套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说是法伦理学的东西,实质价值色彩非常浓厚。但是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法哲学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转向,即形式化、结构化的研究,其中一个代表就是一般法学说,即法学的这套基础范畴或者基本概念。我们说的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事件,还有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法律体系、权利义务、责任,就是这样一套基本概念,这是我们本科一年级学的最主要的内容。我们本科一年级学的法理学,其实就是一般法学说。一般法学说起源于19 世纪中叶的德国,由默克尔(Adolf Merkel)创立,后来传播到了欧洲大陆各地,然后传到了沙俄。沙俄时代也有代表作,基本上都是从德国继受的。到苏联时代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又传到中国,所以有很强的这个传续关系。德国对中国法学研究的影响以这两个方面为典型。
问:您在过去十几年间翻译了大量的德国法理学作品,得益于您高质量的翻译,这些域外作品如今大多数都成为了法学院学生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读本,能否举例谈谈您是以何种标准选择域外经典法理学作品作为翻译对象的?
答:迄今为止,包括我独译的、合译的,还有主持翻译的,有18 本译著。这些译著,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涉及到你说的标准选择的问题。任何翻译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译者的前见在里面。我们选择翻译何种作品都会有自己的学术判断。我认为法理学或者法哲学是有自己的问题意识的。你知道,我们法大一直以来秉持的是规范法学的传统,做的是狭义的法理学或者说法哲学。该领域大概就包括三个部分——概念论、认识论或者说方法论和法伦理学。我们早年的时候比较关注概念论和方法论,但是近年来我认为可能要更加关注伦理学的内容,所以我对这三个方面会进行一个有意识的均衡。比如说,概念论或者说法学基本概念、法学方法论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所以我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的“法律科学经典译丛”里面会放这两个领域的书。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般法学说的基本概念及法学方法论领域的书之外,第三个部分就是近年来慢慢出现的法伦理学。我们以前很少关注法伦理学的讨论,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跟法伦理学结合得更紧密。例如最近出现的一些新科技带来的问题,基因编辑还有AI 带来的一些伦理问题等,当下涉及该领域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未来为了知识谱系的完整性,我们可能需要去看看相关领域的一些著作。像我去年翻译的拉伦茨的《正确法》,它的副标题就叫“法伦理学基础”。这是他1979 年出版的一本书,是为数不多的以“法伦理学”为名的书,尤其是在德国。还有一本叫《正确法》的书是施塔姆勒(Rudolph Stammler)写的,那个出版比较早,知名度更大一点。未来的话我可能还会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翻译工作,翻译德国现代以法伦理学为主题的著作。
第二个部分,我还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主持了一套口袋书译丛,这个主要是从受众的角度来考虑的。说实话,就纯粹的学术研究而言,有很多老师都认为没有必要做翻译,就自己的研究来说,看得懂外语就可以直接去研究,所以台湾地区的译作比较少,他们很多学者都持这样的观点。但在我看来,学术还是有一个普及的问题,在受众是学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所以我们是需要做翻译的,说是为了传承学术也好,或者说是普及这套知识也好。当然,这就涉及受众视角的问题。很多老师在做翻译的时候会紧密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这无可厚非,但这里面有对接的问题,可能你自己的研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小领域,那这个东西译出来之后,它的传播度有多大?是不是我们的学生所需求的?因此,我组织翻译了一套口袋书,该译丛现在大概出了8 本书,我预计是要出14 本。之所以做这样的事,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外地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外地的老师跟我聊天时说:“你看你们有很多懂德语的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的或者北京的,但现在市面上译过来的法哲学的德语书又厚又重,学生进入非常困难,他们看不懂。能不能翻译一些适合初学者阅读的书?”后来其他部门法老师也跟我反映过这个问题。我回来之后就跟出版社商量,当然也获得了学校一定的资助,当时就计划选那种10 万字左右小篇幅的书,做成小开本放在口袋书译丛里,这些就是面向学生的书。我个人一开始翻译了4 本,有《法哲学导论》《写给学生的法理论》《法理论有什么用》这样的一些书,在德国属于上架书。德国跟我们不太一样,德国学术书的受众比较小,很多学术书要预定才能买到,不是说只要跑到书店就可以买到那种学术书。就比如说很多博士论文他是一定要出书的,出的书可能会直接给到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或者研究机构,但在书店是没有现货的,你要买就得提前预订。而上架的就是那种比较大众的书,上架就代表它的需求量很大。我在2015、2016 年到海德堡大学旁边的一个雷曼兄弟书店去考察,发现《法哲学导论》这本书摆满了一排书架,第二排就是阿列克西的《法概念与法效力》。
这就是我翻译书时的两部分考虑,一部分面向学生,特别是本科生这个群体,主要考虑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另一个部分当然跟我个人兴趣有关,但是我竭力想要去做一个相对完整的展现,我前面提到的三个领域(法本体论、法学方法论、法伦理学)都应当涵盖。
问:通过阅读您的代表性学术作品,我们也不难发现您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偏好。直至如今,中国法理学学者们仍在研究汉斯·凯尔森、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等上个世纪域外法学家的学说,这些域外法学家的历史文本能够给我们当下法理学的本土研究提供哪些宝贵的研究资源?
答:这个我讲两点。第一,我的一个基本的界定就是,我认为法哲学或者法理论本身是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狭义的法学。我相信很多老师比如范立波老师也会赞同这一点。相信你也听过这句话,“哲学就是哲学史”,黑格尔说的。哲学是没办法以科学知识的那种方式来传承的。你只有深入到哲学史之后,与那些哲学家共思,你才能真正地了解他们如何进行问题的思考。当然还有另外一句话,“哲学史就是问题史”。所以为什么要去研究前辈的法哲学呢?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他们是经典作者,他可能抓住了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些非常核心的问题,而且在这些核心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创见性的思想范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研究法哲学是回避不了他们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法哲学跟自然科学一样,只要有人告诉我答案是什么就可以。法哲学是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的,法哲学它本身就是以“史”的方式来存续和思考。第二,在我看,你的这个问题本身我可能需要稍微地修正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真正的法哲学本身就是普遍性的,法哲学问题本身也是普遍性的。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中国人和德国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路径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些问题肯定是普遍性的。法理学真正的问题,概念论也好、方法论也好,还是价值论或者法伦理学,都是普遍性的问题。对于这些普遍性的问题,思想家们提供的是对我们全人类都有益处的回答。不会因为是一个德国的学者,其提供的这种思考就只适用于德国,就像马克思一样,其思想影响不限于德国。我们研究法哲学其实就是在研究全世界的法哲学,并不是说某个国家的法哲学。法哲学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普遍化的思考,哲学是不分国度的。就像我们中国哲学或者说印度哲学,它对世界哲学也有贡献。当然自然科学就更不用说了,不可能因为是英国的牛顿发现了三大运动规律,就说三大运动规律只适用于英国。
第二,我觉得可能你真正想问的是,有没有一些独属于中国的法理学研究的内容?然后国外的研究会不会提供一些参考?我觉得法理学研究是有属于每个国家的本土特色的,当然我也赞同法理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本土的研究特色指的是一些特定的问题,特定问题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方面它可能是一个隐藏的普遍问题,另一方面它在普遍问题上加了一些特定语境的限制,它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比如我们在讨论一些中国的现实问题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正当性和可行性,正当性本身是一个普遍问题,只是说背后的伦理立场能不能成立、有没有可行性等涉及到现实的一些考量。在正当性基础上,还要考虑在中国的语境中实践这种想法行不行得通。所以特定问题是两部分合在一起的,其中普遍化的部分是可以进行借鉴的。
问:您在法教义学研究领域深耕多年,想必对法理学与法教义学的研究尤为深刻。可以谈一下为什么这种发源于德国文化背景的法学研究方式会在当代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
答: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法教义学这种研究范式肯定是来自于德国,但是这种看似偶然的历史现象背后是有必然的原因存在的,该原因可能不限于德国。
第一,这和近代民族国家的法典化运动有紧密关系。虽然法教义学要早于法典化运动出现,但我们都知道近代以后方法论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民族国家它越来越中心化。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中世纪为止,欧洲大陆长期以来并没有近代的民族国家概念。德国本身四分五裂,当时德国的高校做的基本上就是自然法研究,他们没有自己统一的国家,也没有自己统一的法律,主要研究的是继受自罗马的那套东西。罗马法复兴以后提出了这套所谓的共同法,而他们认为这种共同法就是大写的理性,就是自然法的体现。在咱们看来,这个很显然是国外的东西。但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后,法学研究的重点马上就变了,变成了本国家本民族的法律,尤其是法典化运动之后的法典,一跃成为了法学研究的重心,这也是我们法律人日常打交道最重要的东西。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围绕本国的实证法进行研究,尤其是适用导向的研究,成为了必然趋势。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法典化现象是不限于德国的,我们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专业化的发展要求。以前的法学研究属于一种每个人可能都能说上几句的研究,近代以后它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专业化的趋势。以前可能法学教育的中心不在大学,师傅在实践中带着弟子做就可以了,后来大学越来越成为法学教育的中心,大学教育本身就有一种科学主义的诉求,尤其是要走向专业化。在中国,最早在上世纪80 年代时,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戴逸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戴逸之问”,这对于法学界刺激非常大,他当时对中国的好几个学科逐一进行了点评,提到法学的时候他说中国的法学是幼稚的。这一论断影响非常大,很多学者都受到了刺激。法学学者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法学研究听上去好像充斥着各种大词空话一样。于是当时陈兴良教授就提出要深挖“专业槽”,要停止那些宏大的争议,要让专业本身从本专业的内部去反馈,要发展精准化的法学。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法学一直在走专业化的路,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教义学的发展。德国又是法教义学研究的重镇,自然会受到它的影响。当然,这里要做一个区分,我讲的法教义学指的是它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我认为这是普遍的。我把围绕本国现行实在法进行的解释、概念建构和体系化叫作业方式,即一种working style,这就是专业化进路,所有的法教义学研究都要这么去走。但是存在一种批评,不是针对这种作业方式,而是针对某一些部门法学者直接把德国的学说搬运过来使用的做法。我觉得这种做法的确是有待商榷或者检验的,因为教义学说是具有本土特点的。当然,你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是的确有一些具体的学说内容,可能是在那个特定制度的特定环境中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去检验它有没有可普遍性,至少原则上你不能直接搬过来。作为知识的教义学是有国度的。方法是没有国度的,但是知识是有国度的,我们要学的只是方法而已。真正的中国教义学应该围绕中国的民法典、中国的刑法等在我们的本土适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来展开,你可以借鉴,但是这个借鉴必须谨慎,这是我的观点。
问:早在12 年前,已经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您曾在《研究生法学》2011 年第4 期上发表过题为《如何学习法理学?》的文章,文章提出了青年学生学习法理学应当重视的10 个命题,至今看来仍不过时。在历经十余载的法理学课堂教学之后,您认为在“如何学习法理学”中有哪些命题尤其需要在当代法理学教学过程中被师生们进一步重视或补充?
答:这篇论文当时是一个师妹跟我约的稿,她当时是在《研究生法学》做编辑,相当于给了我一个命题作文吧。当时对法理学的各个方面一共提了10 个命题,今天如果说有什么需要进一步重视和补充的话,我提两点。
第一,当时提出来法理学研究要跟法教义学或者说部门法学相结合,那今天我想重申的是我们整个法理学的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在我读研究生的时代,我们基本上做的都是一般法理学的问题,即法概念或法律的性质问题。当然你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基本就是两大阵营,即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或者说自然法,整个讨论从国际学界到国内学界都是这样,所以大家讨论的着力点都是各种命题,联系命题、分离命题、还原命题等,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是围绕着法的一般性质来展开的一般法理学。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面貌,我们的研究兴趣会更加广泛,然后已经开始涉入一些部门法哲学了,包括国际法学界也是这样的,刑法的、侵权的、契约的等各种各样的主题。这些主题跟我们的部门法教义学之间的关联会更大一些,我认为这些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前段时间有一个博士后翻译了一本书,是刑法哲学的一本译作,他请我写“导读”。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写的,认为刑法哲学是法哲学研究的一块“飞地”,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长久以来,将包括刑法哲学在内的部门法哲学忽略掉了。从学说史的角度来说,欧陆最后一本完整的探讨法哲学的著作是拉德布鲁赫1932 年的《法哲学》。这本书基本上前半部分讲的都是一般法哲学,而后半部分全是部门法哲学。部门法的很多东西,涉及到契约、所有权还有其他很多主题的都属于部门法哲学。这本书之后,出于专业分工的原因,部门法哲学基本上不再出现在体系化的法理学著作中。但以前不是这样的,不用说拉德布鲁赫他们,看看古典法哲学,看看康德、黑格尔他们的法哲学著作,康德就是从私法生出发构筑其法学理论体系的,黑格尔也是。像所有权还有惩罚这些问题他们都讨论过。部门法哲学在未来会是主流,当然法哲学本身的发展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还是得和法教义学、部门法相结合,这样才更有说服力,这样我们法理学理论的对外输出成效可能会更强,因为我们毕竟是法学的一分子。虽然我认为法哲学应该是属于哲学的,但它在今日的学科体系中毕竟属于法学的分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即我们作为共同体的一员,如何与其他的部门法学者对话,让他们感受到法理学是有用的、是美好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可能很多部门法学者都认为法理学讨论那些东西独属于法理学,从抽象的层面上法理学跟他们离得太远了。当然一般抽象讨论也没问题。因为现在法理学内部大概有两拨人,有一些法理学的研究者,他可能在往上走,往上走就直接去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那个部分,我知道我们有一些老师申请的课题都是那个学科的,甚至参加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学术会议,但是还有一拨是往下走的,这也是我所主张的。
第二点,因为法理学的生命就在于不停地建构、反驳和重构论证的过程。所以我今天想补充一个命题,即学习法理学需要学会关注和参与学术争鸣,这是它的常态。法理学永远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甚至它的使命也不在于形成部门法学那样所谓的通说。所以这个方面要重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学术对立立场中汲取养料。你永远不要只关注一种声音,我经常说,如果你只看一本书,你只会觉得很有道理,但从另一个方向来看,会觉得另一本书也很有道理,这样你可能就已经固化了自己的思想,认为某一问题的答案就是这样,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研究生阅读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你读了一本经典之后,你还要看一看有没有等量齐观地去批评它的论述存在。看完批评之后,哪怕你还是支持原来的立场,沿着它的立场往前走,但你会走得更稳。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批驳的,关键是你面对批驳的时候能不能进行强有力的辩护,这种辩护是在交锋中展开的。
问:从您在《研究生法学》发表作品类型来看,从早期学术论文的发表逐步转为向法理学初学者提供入门教程与译文引介,作为法理学教师的您,应该对新一代年轻的法理学读者有很多殷切的学术寄望,可以最后请您给法学研究生在撰写和发表法理学论文上提一些具体建议吗?
答:发表建议的话呢,我当年有一篇网文可以参考:《如何能更好地发表论文?——关于法学博士生论文发表的五点建议》。[2]编辑注:原文参见雷磊:《如何能更好地发表论文?——关于法学博士生论文发表的五点建议》,载微信公众号“蓟门研讯”,2020 年2 月10 日,https://mp.weixin.qq.com/s/D-RK_lQdLmWC2X8sYA3rng?scene=25#wechat_redirect。在撰写法理学论文方面,这个其实我们论文写作课堂上讲得很多且很具体,大概讲这么几点吧。
第一点是问题意识,就是我们写论文为的是解决问题或者说推进对某个问题的思考。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很难,但你得朝那个方向去做,你写不写和你能写成什么样子是两回事,一开始就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做很重要,论文写作一定是围绕问题来展开的。我接触到的写得不好的论文一半以上都是没有问题意识的,可能是资料的堆砌,也可能只是围绕某个主题堆放名人名言、数人头。问题意识来源于文献,要找到文献,首先是要读书。读书、研究和写作是一体,读书首先就是读问题。这也是高中时代做阅读思考题时要做的一个工作,作者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处理的?他在论证中的出发点和推导过程是什么?这个过程有没有问题?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工作,论文写作第一步就是要有问题感,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是来自我们的阅读,阅读经典文献可能就是在思考别人要处理的问题,要把他这个问题重述出来。
第二点是要形成你的论证。有了问题意识之后,要找到你的论证基本结构。简单来说,就是你是怎么推进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论证是要围绕这个来展开的。你在读别人的书的时候,其实重要的不是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人家说了什么,不是记住几句名人名言,知道几句金句;重要的是知道他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什么贡献,他的论证结构是怎么样的,你可以从这个论证结构中获得什么样的收益或者发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写论文的时候也是如此,围绕问题本身形成一个论证结构,可以分成几步走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论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