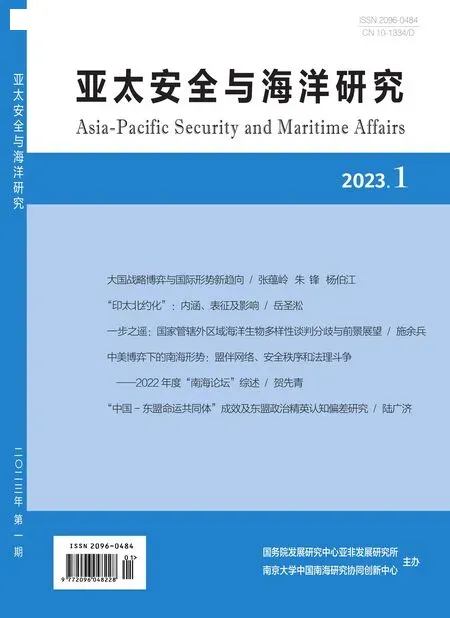“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成效及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研究
2023-02-08陆广济
陆广济
内容提要:2023年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十周年,该倡议在地区层面、次区域层面以及双边层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并不断得到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积极认可,成为双方友好合作的行为指南。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认知偏差,对该倡议采用模糊应对或选择性回应,影响该倡议全面深入的推进。通过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探究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形式,可望助力寻求解决之道,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排除干扰、增加动能。
“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东盟就深化双方友好合作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过中国和东盟双方的共同努力,共同体的内容不断丰富,轮廓更加清晰,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外交一张靓丽的名片。202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峰会上强调:“中国愿同东盟把握大势、排除干扰、同享机遇、共创繁荣,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1)《习近平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1年11月22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11/22/c_1128087275.htm[2022-11-20]。
该倡议提出十年来,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效。但是,在推进过程中,一些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存在疑虑和误解,而决策者的认知偏差直接影响外交政策的走向,导致倡议的落实与推进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因此,本文尝试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去正视和分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进过程中遇到的认知偏差,探寻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以期排除干扰,确保“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向前推进,为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近年来,关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学理研究在国内外兴起,成为当今地区合作和外交研究的显学,也为学术界分析新时期中国-东盟关系打开了新的窗口。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大体掌握目前的研究进度,也可望为后续研究的创新和突破寻找新的着力点。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给予极大关注。通过检索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截至2022年12月16日,共获得国内学者学术论文198篇。国外学者也结合中国对东南亚外交政策,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整体而言,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对地区合作产生的影响、构建路径,以及东盟方面的认知等四个方向展开研究。
1.“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研究。目前,学界对其本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一些学者从经验和理论的层面,将其理解为行为规范、地区秩序、身份认同、合作机制等。例如,陆广济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得出结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既不是政治实体,也不是一套严密完整的制度安排,可以理解为中国与东盟基于共同的前途和命运而构建的一种集体身份。(2)参见陆广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基于“身份政治”理论的分析》,《边界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第106页。翟崑运用国际机制理论,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本质定义为双方制度化合作的延续和升级。(3)参见翟崑:《第三个奇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及展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34页。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政治学教授艾大伟(David Arase)的观点接近结构现实主义,他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形容为中国引领构建的地区新秩序。(4)David Arase, “China’s Two Silk Roads Initiative:What It Means for Southeast Asia,”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5, p.31.比利时学者蓝露洁(Lutgard Lams)选择软实力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中国与东盟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是加强在东南亚的文化软实力,同时也是为了修补与邻国关系。(5)Lutgard Lams,“Examining Strategic Narratives in Chinese Official Discourse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No.3, 2018, p.398.
2.“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对地区合作的影响。随着中国在国际和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国内外学者大都承认该倡议必将对东南亚产生深远的影响。单金环指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凝练了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参照,同时也将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6)参见单金环:《“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思考》,《时代经贸》2022年第1期,第53页。张丽、李瑶更多关注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进程能够提升彼此间相互认同,通过充分的沟通与理解,在基本价值观、发展观等方面达成共识。(7)参见张丽、李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东盟民间外交开展情况分析》,《国际公关》2022年第10期,第41页。菲律宾学者结合南海问题进行研究,预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将为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提供新的思路。(8)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Challenge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Examining the Prospect of a Stable Peace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Vol.7, No.1, 2016, p.28.越南学者考虑到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互利性,希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实施,使得中国对东南亚更加开放,加快双方之间的互联互通,最终实现互利共赢。(9)Do Tien Sam and Ha Thi Hong Van, “ASEAN-China Relations since Building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heir Prospec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 6, No. 2, 2015, p.187.
3.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对于如何建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一些国内外学者提出以加强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政治互信、互联互通等路径来实现。例如,杜兰提出通过加强协调与合作、挖掘合作增长点、共同应对新挑战,从而推动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参见杜兰:《疫情下中国-东盟关系的新进展与未来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第54页。于洪君指出,不断加强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与合作,才能推进命运共同体意识。(11)参见于洪君:《扩大人文交流与合作,强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意识》,《公共外交季刊》 2020年第4期,第3页。马来西亚学者倾向于完善地区合作机制,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助于双方打造共同命运、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通过建立各种合作机制可以实现互利共赢。(12)Lai Yew Meng, “Sea of Cooperation or Sea of Conflict ?: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Context of China-ASEAN Maritim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 8, No. 3, 2017, p.321.新加坡学者则强调加强政治互信,通过打造基于相互信任、合作共赢和共同行动的“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共同挑战,推动地区稳定。(13)Zhexin Zhang,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outheast Asia,”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6, p.62.
4.“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认知研究。一些国内外学者也注意到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进过程中存在的认知偏差。例如,周士新的研究发现,一些东盟国家对中国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相对冷淡,原因是它们对中国倡议认识不够。(14)参见周士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70年:经验、反思及展望》,《南洋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 第8页。李晨阳注意到周边一些国家担心与中国建设命运共同体,会遭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打压。(15)参见李晨阳:《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第73页。邵建平分析了域外国家甚至包括东盟国家的部分学者对中国的东盟政策产生误解,并因此干扰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16)参见邵建平:《中国的东盟政策:误解与正解》,《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第106页。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黄氏霞(Hoang Thi Ha)结合相关报道,发现一些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产生顾虑,未能直面中国的倡议,采取模糊应对的策略。(17)Hoang Thi Ha, “Understanding China’s Proposal for an ASEAN-Chin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nd ASEAN’s Ambivalent Respons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 41, No. 2, 2019, p.223.
(二)相关研究评述
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发现,相关研究大都集中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从权力转移、软实力、国家利益等角度分析问题。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主要采用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关注物质性的现实利益而忽略了认知、观念等非物质性因素的影响。一些观点带有零和博弈的思维,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本质特征视而不见。国内学者的研究侧重于中国-东盟关系以及中国对东南亚外交政策的分析,包括分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建构路径以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积极影响等方面,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对于该倡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涉及不多。特别是对于东盟国家政治精英、普通民众对该倡议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没有专门和细致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十周年为契机,全面分析该倡议推进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和遇到的问题,特别是认知层面存在的偏差和误解,从微观的视角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方式,以寻找合适的解决途径。
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在东南亚的推进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表示愿意在“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关系。(18)参见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十年成效的考察,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既包括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层面的共同体建设,也包括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在次区域层面和双边层面的共同体建设,次区域和双边层面的共同体构建是地区层面“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有效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

图1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关系图
(一)地区层面的推进情况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地区层面的共同体。经过不断探索,中国与东盟以政治安全、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作为合作的三条主线,以促进各领域合作交流全面开展。政治方面,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愿意在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框架内继续深入合作。双方通过加强对话协商、建立信任措施、加强高层交往和政策沟通等方式,增进彼此间的互信与理解。在合作方式上,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双边防务对话交流的同时,加强在多边机制下深化务实合作。合作内容上,双方不但在传统安全领域建立沟通渠道和危机管控机制,而且对恐怖主义、跨境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强地区联防联控机制。在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努力之下,双方的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友好合作意愿更加强烈。2018年,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之际,双方共同制定了对中国-东盟关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2019年,第22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力求实现双方发展战略的对接。202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双方关系进一步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共同制定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2—2025)》,推动“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落实。
经贸方面,2019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全面生效,将双方经贸合作水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未来还将继续研究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可行性。2021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达8782亿美元,同比增长28.1%,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5%。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更加紧密。截至2021年底,中国与东盟累计双向投资总额约3000亿美元。东盟连续两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连续13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19)参见《商务部:我国连续13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商务部公共信息服务网站,2022年3月18日,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e/r/202203/20220303286681.shtml[2022-12-15]。2020年11月15日,中国同东盟十国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1月1日该协议正式生效,将有助于中国与东盟进一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同时也推动双方产业链和价值链延伸与深度融合,带动中国与东盟的产能合作。此外,双方还将加强金融服务行业的合作,发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积极参与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双方互联互通水平和相互依赖程度。未来双方还将加强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海洋经济等新领域合作,持续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
社会文化方面,双方打造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中心、文化论坛、减贫发展论坛、中国-东盟合作基金、菁英奖学金等一系列交流合作平台。2019年双方人员往来已达6500万人次,每周往来航班近4500架次,双方互派留学生超过20万,结成了200多对友好城市。(20)参见陈小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取得重大成果》,中国经济网,2021年11月25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111/25/t20211125_37112862.shtml[2022-12-15]。双方还通过举办各类文化节、展会、学术论坛等方式,促进民间的交流与对话。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交流合作由传统的艺术表演,拓展到影视创作、期刊出版、动漫游戏、文博展览、考古、申遗等多个领域。(21)参见卢羡婷、黄庆刚:《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合作走向纵深》,新华网,2020年11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29/c_1126800231.htm[2022-12-15]。在社会合作方面,双方将加强环保、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合作。包括落实《中国-东盟环境保护战略(2016-2020)》,支持《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25》相关战略措施等;建立中国-东盟环保技术和产业合作交流示范基地;在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等社会治理领域开展合作和经验交流。
(二)次区域层面的推进情况
在次区域合作层面,中国同湄公河沿岸五个东盟国家建立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2016年3月,中国、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六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海南三亚举行了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领导人会议。会议通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打造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22)参见《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全文)》,新华网,2016年3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3/23/c_1118422397.htm[2022-10-21]。,使“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成为首个得到相关国家正式认可并已经进入建设日程的命运共同体。(23)参见卢光盛:《全方面推进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7月9日,http://ex.cssn.cn/gd/gd_rwxn/gd_ktsb_1696/zbmygttjsllysj/202007/t20200709_5153278.shtml[2022-04-16]。同时,这也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次区域层面的具体实践。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发表的《金边宣言》《万象宣言》中,重申了《三亚宣言》提出的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愿景。
“澜湄合作机制”创建以来,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形成“3+5合作框架”,确定了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支柱,以及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合作方向,实施了许多惠及民生的项目,为全面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4)参见《关于“3+5合作框架”》,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网站,2017年12月8日,http://www.lmcchina.org/2017-12/08/content_41448201.htm[2022-12-15]。2017年12月28日“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正式启动,为流域国家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2020年11月30日,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网站开通,澜湄国家将进一步在水资源数据、信息、知识、经验和技术等方面实现共享。在澜湄合作框架下,六国共同发表了深化灾害管理合作、文明交流互鉴、农业合作和保障粮食安全、海关贸易安全和通关便利化合作、地方合作、传统医药合作、可持续发展合作、国家产能合作等领域联合声明,支持澜湄合作与“陆海新通道”建设开展对接,进一步丰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内涵。2021年在新冠疫情的不利条件下,中国同湄公河五国贸易额近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3%,占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近2/3,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复苏和区域繁荣振兴。(25)参见翟崑:《澜湄合作六周年:可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2022年3月30日,http://cn.lmcwater.org.cn/authoritative_opinion/expert_commentary/202203/t20220330_35453.html [2022-12-15]。
(三)双边层面的推进情况
中国分别与老挝、柬埔寨建立了双边层面的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中国与缅甸也就建立“中缅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2019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在北京签署《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并以此为契机共同打造新时代中老关系。(26)参见白洁、王卓伦:《中国老挝签署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开启双边关系新时代》,《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5月1日,第4版。2021年是中老建交60周年,双边贸易额达到43.5亿美元,同比增长21.4%。其中,进口16.7亿美元,增长11.9%,出口26.8亿美元,增长28.2%。(27)参见《老中合作委员会召开会议总结2021年中老双边经贸合作》, 中国驻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网站,2022年2月22日,http://l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202/20220203281634.shtml[2022-12-15]。中国已成为老挝最大出口目的地,第二大贸易伙伴和老挝第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中国还是老挝最主要的援助国之一,通过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无偿捐助、援建项目等方式,帮助老挝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内容涵盖基础设施、卫生医疗、公共服务、农业发展等诸多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开通,北起中国云南昆明,南至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不但极大地缩短旅程时间,还将进一步加快人员和物资流动,实现两国的互联互通。
2019年4月,李克强总理与柬埔寨首相洪森签署了《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作为引领两国关系全方位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将推动双边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28)参见毛鹏飞:《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成果:访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人民日报海外版》2020年5月5日,第10版。2020年10月,中国与柬埔寨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柬埔寨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东盟国家。2021年中柬双边贸易额136.7亿美元,同比增长43.1%。截至2022年3月,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361.9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22.1亿美元。(29)参见《中国同柬埔寨的关系》,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6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72/sbgx_676576/[2022-12-15]。目前,中国已成为柬埔寨最大投资方、贸易伙伴和援助国。诸如,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金边—西哈努克港高速公路、格罗奇马湄公河大桥等一系列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中国的帮助下得以顺利落实和稳步推进。此外,中国还与柬埔寨在农产品出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疫情防控、教育、减贫等领域不断加强合作。
2020年,中国与缅甸领导人在双方建交70周年之际签署联合声明,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承和发扬“胞波”情谊,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30)参见徐惠喜:《携手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经济日报》2020年1月19日,第1版。中国是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以及最大的出口市场。2021年,中缅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83亿美元。(31)参见《中缅经贸合作新动能澎湃》,中国商务新闻网,2022年5月18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3132097555750857&wfr=spider&for=pc[2022-12-15]。早在2017年,中方就曾提议建设“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得到了缅方的积极回应。2020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共同见证了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项目协议交换仪式,标志着中缅经济走廊从概念转入实质规划建设阶段。(32)参见鹿铖:《中缅经济走廊开启实质规划建设》,《光明日报》 2020年1月19日,第12版。近年来,缅甸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困难,而中国发扬“胞波”情谊,在油气管道建设、矿产开发、抗击疫情、农产品出口等领域加强与缅方的合作。中国也成为缅甸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让缅甸政府和民众都感受到中缅命运共同体的实惠。在金融合作领域,2021年12月14日,缅甸中央银行发布第2021/48号公告,准许在缅中两国边境地区直接使用缅币和人民币进行交易。(33)参见中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中缅边境贸易可直接使用人民币与缅币结算》,中国商务部网站,2021年12月3日,http://mm.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112/20211203229067.shtml[2022-12-15]。中国还与缅甸就木姐—曼德勒铁路项目进行研究,如果该项目得到顺利实施,将进一步加强中缅之间的互联互通,提升缅甸在地区合作中的地位。
2022年,双边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又取得新的突破。印尼成为东盟创始国中第一个对双边层面命运共同体表现出初步合作意向的国家。同年7月25日至26日,印尼总统佐科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主席会晤,中印尼两国元首在会晤中明确了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是此访达成的最重要政治成果。(34)参见龚信:《印尼总统佐科访华: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树立发展中大国关系典范》,新华网,2022年7月30日,http://www.news.cn/silkroad/2022-07/30/c_1211672083.htm[2022-10-18]。同年11月19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泰国并与巴育总理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中泰关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宣布构建更为稳定、繁荣和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为双边关系未来发展指明方向。(35)参见《中泰发表联合声明: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中国新闻网,2022年11月19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2/11-19/9898283.shtml[2022-11-26]。中国领导人也曾在多个场合提出与越南共建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例如,2015年11月5日,习近平访问越南时提出,中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36)参见《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新华网,2015年11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5/c_1117055143.htm[2022-04-18]。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表示认同。2017年1月12日,阮富仲访华时,习近平在会见中指出,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并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提出七点建议。(37)参见刘华、郝亚琳:《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国青年报》2017年1月13日,第1版。阮富仲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两党两国关系的建议。尽管目前由于各种原因,中越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推进较为缓慢,但不排除在印尼、泰国合作意愿的带动下,越南方面基于对已有双边命运共同体成果的考量,转而积极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2022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受习近平总书记邀请,阮富仲再度访华,访问期间双方领导人共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将从战略高度引领和指导新时代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38)参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11月2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211/t20221102_10795594.shtml[2022-12-02]。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文莱甚至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在不久的将来也可望同中国建立双边层面的命运共同体。
三、东盟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回应
如上所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但在推进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一些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对该倡议存有疑虑。东盟政治精英是外交政策的决定者,他们对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回应,体现了某种官方层面对于该倡议的接纳程度。通过考察东盟政治精英在多边和双边场合对于该倡议的回应,能够一定程度掌握东盟政治精英对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情况。
(一)多边场合东盟领导人的积极回应
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东盟对于中国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给予积极和正面的回应。从多边场合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发表的一系列声明和公报之中,可以感受到东盟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持肯定态度,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理念,使之成为合作深入开展的政治基础和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理念支撑。
澜湄国家领导人也在澜湄合作框架下对次区域层面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表示肯定和赞许。例如,越南副总理范平明(Pham Binh Minh)表示,越南支持《三亚宣言》中设定的原则与长期合作目标,澜湄合作将加强六国的睦邻友好关系。(39)Deputy PM urges sustainable use of Mekong River, Viet Nam News,2016-03-24, https://vietnamnews.vn/politics-laws/294249/deputy-pm-urges-sustainable-use-of-mekong-river.html[2022-10-18].柬埔寨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巴速坤(PRAK Sokhonn)认为,柬埔寨承诺加强澜湄合作机制,以加深湄公河沿岸各国与中国的友好纽带和相互支持。(40)Voun Dara, Cambodia keen on Mekong diplomacy across entire region, The Phnom Penh Post,2021-03-25, www.phnompenhpost.com/national/cambodia-keen-mekong-diplomacy-across-entire-region[2022-10-18].泰国外长敦·帕马威奈(Don Poramatwinai)表示,泰国决定将与澜湄国家一道努力,在次区域层面推动多维度的互联互通,以建立一个和平、繁荣和稳定的命运共同体。(41)Don commends MLC members on their cooperation, The Nation Thailand, 2019-03-20, https://www.nationthailand.com/international/30366168[2022-10-18].缅甸外长温纳貌伦(Wunna Maung Lwin)表示,澜湄国家只有秉承互信、自信和团结的澜湄大家庭精神,才能战胜当今全球面临的各种挑战。(42)Union Minister U Wunna Maung Lwin attends and co-chairs 6th Mekong- Lancang Cooperatio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yanmar, 2016-06-08,https://www.mofa.gov.mm/union-minister-u-wunna-maung-lwin-attends-and-co-chairs-6th-mekong-lancang-cooperation-foreign-ministers-meeting/[2022-10-18].老挝总理通邢·塔马冯(Thongsing Thammavong)形象比喻称,澜湄合作标志着澜沧江-湄公河是一条造福沿河六国的幸福之河、合作之河。(43)参见储思琮:《澜湄六国领导人共襄“六水合一”》,中国政府网,2016年3月23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3/23/content_5056980.htm[2022-10-16]。

表1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重要政治性文件中的表述
(二)双边场合东盟政治精英的差异回应
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三国政治精英不但在多边场合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表示肯定和支持,在双边场合也给予公开、正面的评价。老挝新闻文化与旅游部部长波万坎·冯达拉(Boviengkham Vongdara)表示:“中国提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一共赢举措,将使东盟各国受益、惠及区域人民。”(44)转引自王伟健:《共商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4日,第3版。缅甸副总统吴敏瑞(Myint Swe)高度评价中国与缅甸的合作项目,认为与《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及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相符合,今后将大力支持。(45)参见《缅甸副总统吴敏瑞:中缅经贸关系紧密对两国发展非常有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网站,2019年9月23日,http://www.cafta.org.cn/show.php?contentid=88092[2022-05-18]。柬埔寨副首相贺南洪(Hor Namhong)说,柬埔寨是首个与中国签署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这是两国命运共同体构建与发展的路线图。(46)参见《专访:构建柬中命运共同体将推动柬埔寨蓬勃发展——访柬埔寨副首相贺南洪》,中国政府网,2020年4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4/28/content_5507158.htm[2022-12-18]。
但有些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在双边场合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谨慎态度,甚至采取模糊应对或选择性回应。例如,2018年4月8日李克强总理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李克强表示愿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盟国家共同建设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李显龙对“命运共同体”并没有做正面回答,强调新方愿加强同中国合作,积极推进新中双边关系以及东盟-中国关系取得新进展。(47)参见崔文毅:《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愿同东盟建设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4月9日,第1版。2017年8月8日,习近平主席就东盟成立50周年向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贺电,提出以2018年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为契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Cayetano)赞赏中国在区域和平稳定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以及双方经贸关系和人员交流的成果,对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没有做出评论。(48)参见《建设更紧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驻菲律宾经商参处网站,2017年8月2日,http://ph.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8/20170802624577.shtml[2022-05-18]。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通讯社对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进行了相关报道,但并没有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进行评价,而是强调双方将在各个领域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49)Panca Hari Prabowo, Indonesia, China agree to promote cooperation fo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Antaranews, 2013-10-02, https://en.antaranews.com/news/90973/indonesia-china-agree-to-promote-cooperation-for-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2022-10-10].印尼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雅加达邮报》刊文指出,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的演讲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并呼吁中国与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尼)乃至整个地区更大的合作,但文中并没有提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50)China president makes historic speech in Indonesia, The Jakarta Post,2013-10-03,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3/10/03/china-president-makes-historic-speech-indonesia.html[2022-10-10].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文莱等国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也鲜有正面回应,而是采取务实和选择性回答,强调继续深化双边关系,加强与中国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性。
(三)对东盟政治精英回应的评价
东盟成立以来不断塑造集体身份,在其产生的重要政治性文件《东盟宪章》中,设想将东盟各国整合为“一个愿景、一个身份、一个互助、共享的共同体”。(51)Chart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The ASEAN Secretariat, 2007-11-20,http://agreement.asean.org/home/index.html [2022-10-09].这在一定程度可以解释东盟国家更愿意在多边场合以集体的方式,表达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的肯定和支持。但是,作为单一个体的东盟成员国,在外交上享有很大程度的独立自主性,对友好合作意愿的肯定并不需要以集体的方式表达。东盟政治精英在双边场合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差异回应,反映出部分东盟政治精英存在认知偏差。特别是一些与美国关系密切、政治上有求于西方的东盟国家,其政治精英对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回应就显得小心谨慎,既害怕得罪美西方,又担心会破坏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因而采取观望或者模糊应对的态度。其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传达的是中国希望加强与东盟友好合作的积极愿望,体现中国“亲、诚、惠、容”的睦邻外交政策,并不涉及非此即彼的战略选择。认知偏差干扰了一些东盟国家政治精英的判断,以至于没有及时认知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构建更为密切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还需要破解认知的局限,消除认知的偏差,打消决策者的疑虑。
四、东盟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偏差
虽然“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地区、次区域和双边层面顺利推进,但是部分东盟国家政治精英认知偏差的存在,阻碍倡议的全面实施。认知偏差从上述一些东盟国家政治精英的回应中可见端倪。下文将通过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分析视角,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认知偏差的表现形式和影响进行剖析。
(一)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心理学是国际关系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微观层面的国际关系理论。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断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引入国际问题研究,用于分析决策者的认知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其中以美国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最为著名,其代表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52)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被认为是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主要探讨了外交决策者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存在的认知局限和偏差,进一步分析了认知偏差形成机制与表现形式,并就如何避免认知偏差提出自己的建议。
认知是指人认识事物与获取知识的过程,而认知偏差是指人们认知事物的过程中由于错误的信息而导致的误判。杰维斯认为,决策者的认知局限不免会出现错误的知觉,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认知偏差。认知偏差对国家行为以及国际冲突与合作会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外交决策是由人做出的,政治精英的认知会影响外交决策,特别是认知偏差会导致形势的误判。诚然,国家是由人构成的政治实体,抽象的国家行为归根结底是决策者意志的具体落实,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不可忽略。美国学者罗丝·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也认为:“个人层面的分析仍然是研究人类决策和行为经验准确性的最佳途径。这一概念对任何有意义的领导力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53)参见罗丝·麦克德莫特:《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李明月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7页。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外交决策者在环境中刺激因素的作用下容易产生误判,夸大对方的敌意甚至误解了对方的善意。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也认为:“决策者往往在面对多种不确定性因素时,会出现不知所措的行为表现,很多时候会更多地受到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从而做出决策,因此也难免产生较大的认知偏差。”(54)参见威廉·冯特:《认知心理学》,王彦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94页。因此,在杰维斯看来,国家决策者的知觉与国家行为存在因果关系,错误知觉导致错误的判断,最终导致国家采取错误的行为。
(二)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的表现形式
杰维斯总结了四种常见的认知偏差,包括统一性知觉、自我中心偏差、愿望思维、认知失调。其中:(1)统一性知觉是指人们将对方视为比自己的行为更统一、预谋性更强的统一体。(2)自我中心偏差是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3)愿望思维则指人们接收信息时往往喜欢接收自己喜欢的而避开自己不喜欢的,从而做出失误判断。(4)认知失调。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于是就出现了认知失调现象。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最早由中国提出,也主要由中国推动,一些东盟国家政治精英对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导致其对该倡议存在疑虑和错误的解读,以至于采取模糊应对和有选择的回应。认知偏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视其为精心策划的战略。少数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误认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一项针对东南亚的战略布局,是中国意识形态在东南亚的扩张。绝对理性思维使得一些政治家用现实主义权力斗争的思想去解读中国的外交行为,无视中国希望与东盟国家全方位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55)Margaryta Rymarenko, “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in regional role location process: ASEAN, China, and great power management in ADMM Plus,”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9, No.2 2022, pp.577-578.
其二,害怕沦为附庸。东盟国家多为中小国家,又与中国相邻。出于被大国控制的恐惧或是意识形态不同的考虑,一些政治家对中国精神层面的倡议和方案存在顾虑,害怕接受之后被中国控制,失去独立性而沦为附庸,威胁现有政权的权威,高估了自身受到外来影响的程度。(56)Mely Caballero-Anthony, “The ASEAN way and the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navigating challenges to informality and central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22, p.4.
其三,政治上不信任。一些东南亚政治精英陷入思维定式,认为大国的崛起势必在国际和地区范围内谋求更大的权力,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和平崛起,即便中国的倡议是和平友善、互利共赢的方案,也会由于“镜像思维”产生敌意。小国对大国政治上的不信任,使得一些东盟国家的政治家更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正确的信息而忽略了事物的本质。(57)Kai He,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 in the Making,”Asia Policy,Vol.13, No.4, 2018, pp.17-18.
其四,担心“选边站队”。美国“印太战略”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在东南亚形成竞争。一些东盟国家在“政治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即便有些东盟领导人想支持中国的倡议,也担心被视为选边站队,影响这些国家与美西方的关系,甚至会造成东盟内部的分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柬埔寨首相洪森、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等东盟领导人,就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出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担忧。(58)Singapore PM offers blunt assessment of US relationship, CNBC News, 2017-02-28, https://www.cnbc.com/2017/02/28/singapore-pm-on-us-china-relationship-we-must-choose-sides.html[2022-12-01]; Duterte to Asean: Don’t choose sides between China and US, elevenmyanmar, 2019-11-03, https://elevenmyanmar.com/news/duterte-to-asean-dont-choose-sides-between-china-and-us[2022-12-29];Cambodia in between China and US, Phnom Penh Post, 2021-08-24, https://www.phnompenhpost.com/opinion/cambodia-between-china-and-us[2022-12-01].
(三)认知偏差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造成的影响
虽然东盟各国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但精英政治仍然在许多东盟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威权主义、精英主义、家族政治等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外交政策走向,也影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在该国的接纳程度。首先,影响该倡议的整体推进。部分国家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产生认知偏差,直接影响该倡议在地区层面、次区域层面和双边层面的整体推进。该倡议虽然是由中国提出,但需要东盟国家的密切配合以及相关国家政治精英的推动才能及时高效发挥作用。否则,再好的倡议也只能停留在观念层面,而在实践层面的推进缺乏执行力。其次,影响集体认同的塑造。中国与东盟山水相依、血脉相亲,是好邻居和好伙伴。集体认同是共同命运的黏合剂,是中国与东盟各领域合作深入开展的情感基础。东盟政治精英正向认知可以带动国家意志的落实,促进中国与东盟集体认同的形成,反之则会动摇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使得倡议推进出现困难。再次,影响双方交往方式。命运共同体要求中国与东盟“以心相交”,将个体利益融合为集体利益。部分政治精英认知偏差的存在,使得双方交往“以利相交”,未能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有的作用,零和博弈取代正和博弈。
五、东盟政治精英认知偏差产生原因及解决思路
东盟国家政治精英的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复杂多样。按照杰维斯的观点,主要由认知相符、诱发定式和历史学习与类比所导致。认知相符导致决策者习惯运用原有的知识结构来判断新生事物,难以发觉“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诱发定式容易造成决策者以自己的思维方式修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本意,违背了该倡议的初衷。而简单机械的历史学习和类比,又使得决策者背上历史包袱,对于接纳“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有所顾忌。破解东盟政治精英的认知偏差,需要通过不同层面的良性互动来改变其认知结构,培养积极正向的认知。
(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
杰维斯认为,错误知觉的产生机制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首先是认知相符现象。“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过程会产生理性认知相符现象,但也会使人们将接收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识框架之中,致使他们所知觉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来预想出现的东西。”(59)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7—148页。决策者在接收新信息之前就保持自己的原有的信息,当新信息与原有信息不一致时,决策者往往会将新信息与原有信息保持一致,甚至曲解误判。其次是诱发定式。“行为体如果错误地认识别人与自己关注的是同样的东西,就很容易被误导。但是即便没有这样的认识,诱发定式也会对知觉产生重要的影响。”(60)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23页。决策者接收信息常以当时关注及考虑的问题为定式,并以此来认识和解读接收的信息。再次是历史学习和类比。“人们很容易把从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汲取的经验应用到类似的情景中去,所以即便是那些认识到这样做会产生误导作用的人也难以避免。”(61)同上书,第243页。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决策者也会从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但如果与现实进行机械性类比,则可能出现严重的误判。
1.认知相符现象导致的误判
在东南亚各国政治精英的认知中,中国是大国,东盟成员国多为中小国家,中国与许多东盟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上存在差异。一些决策者误认为中国提出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中国试图建立地区霸权体系的工具,需要谨慎应对。一些东盟国家的政治精英认为,该倡议旨在为中国的崛起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此同时,中国试图在地区层面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挑战传统的价值观,并建立一套基于中国独有的文化规则、政治价值与核心利益的地区秩序。特别是在美国霸权衰落、国际权力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谋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似乎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主导地位,树立新的国际政治规则,并改变现有的国际机制以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有一些持中立态度的东盟国家政治家认为,现有的国际和地区治理机制存在缺陷和漏洞,未能解决好地区面临的问题。例如,东盟十国努力构建的“东盟共同体”虽然在2015年就宣布正式建成,但是距离真正一体化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否能发挥实际效益还有待观察,因此对中国的倡议缺乏信心。此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倡议,本身具有非物质性的特点,并不像具体的合作机制那样具备很好的操作性,其建成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些对华友好的东盟领导人虽然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抱有好感,但并不完全清楚中国倡议的实质内涵、构成要件和实施路径,行动上感到无所适从。
2.诱发定式导致的误解
随着中国与美国在东南亚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出台“印太战略”并增加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投入,积极拉拢东盟国家。2022年5月12日至13日,美国-东盟特别峰会首次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将在抗击新冠疫情、加强经济纽带和连通性、促进海上合作、增进民间联系、支持次区域发展、技术应用与促进创新、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和平与建立信任八个领域开展密切合作。(62)ASEAN-U.S. Special Summit 2022, Joint Vision Statement, the white house,2022-05-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3/asean-u-s-special-summit-2022-joint-vision-statement/[2022-12-25].同年11月12日,拜登出席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双方宣布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体合作领域包括:美国-东盟电动汽车倡议、美国-东盟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平台、新兴国防领袖计划、粮食安全和清洁用水、弹性健康供应链、东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新发疾病应急处理中心、东盟气候变化中心、残疾人权利、东盟妇女、和平与安全区域行动计划、女性企业家、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标准、东盟中小企业学院2.0、打击非法及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63)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ASEAN Leaders Launch the U.S.-ASEAN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U.S. Embassy and Consulate in Vietnam, 2022-11-17,https://vn.usembassy.gov/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asean-leaders-launch-the-u-s-asean-comprehensive-strategic-partnership/#:~:text=Under%20the%20framework%20of%20our%20newly%20established%20U.S.-ASEAN,region%20that%20is%20connected%2C%20prosperous%2C%20secure%2C%20and%20resilient[2022-12-25].美国还通过其主导的“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倡议”(PGII)、“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新的合作机制,积极邀请东盟国家参与。面对美国的拉拢以及中国提出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一些东盟国家政治精英为了能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避免陷入选边站队的窘境,因而采取模糊应对或有选择回应的方式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误解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所表达的善意。
3.历史学习和类比造成的扭曲
一些东南亚国家历史上曾被纳入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中国封建王朝与东南亚邻国历史上的战争,仍然使一些东南亚国家政治精英心有余悸。冷战时期,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受意识形态影响,双方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虽然冷战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现在的绝大多数东盟领导人都是在冷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冷战思维或多或少地影响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此外,南海问题悬而未决也使得一些与中国存在海洋权益和领土争端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产生心理负担,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难以摆脱历史包袱。为了寻求南海问题妥善解决,中国同相关当事国进行了多次协商和谈判。2002年中国与有关各方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迈出了政治解决南海问题坚实一步。目前,中国与相关当事方正在就最终“南海行为准则”进行磋商,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美国、日本等域外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向东盟国家传达“域外大国干预”的错误信息,同时怂恿一些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渲染“中国威胁论”,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使得南海问题复杂化。对此,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指出:“某些域外国家并不乐见‘准则’达成,也不希望南海风平浪静,因为这将使其失去插手南海、谋取私利的借口。希望东盟各国能够看清这一点,共同抵制来自外部的干扰破坏。”(64)《王毅:中方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前景始终充满信心》,中国外交部网站,2022年3月7日,https://www.mfa.gov.cn/nanhai/chn/wjbxw/202203/t20220307_10648941.htm[2022-12-25]。
(二)避免“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认知偏差的方法
既然认识到决策者的认知偏差对外交行为和国际合作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避免决策者认知偏差的发生也是学者关注的问题。杰维斯建议,决策者要意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在接收信息的时候,特别是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认知相矛盾时,要冷静应对和全面思考。包括:(1)换位思考,决策者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2)多了解对方国内政治和社会进程,避免用本国的习惯和方式去判断对方国家的行为和对策;(3)提倡行为体间加强国际互动,完善相应的信息接收渠道。其中,前两种建议是决策者的主观意识,需要通过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来实现。而加强决策者之间的交流沟通与良性互动,则可以通过客观存在的外交机制实现,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既然国家行为是由决策者做出的,那么决策者应该清晰地对外传达自己的意图,同时也要从对方准确接收信息,因此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必不可少。互动是双方共有观念形成的基础,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决策者之间是没有共有观念可言的。只有在沟通交流顺畅的情况下,通过互应机制加强或减弱一些原有的观念,将己方的一些私有观念传达给对方,在得到对方认可之后上升为共有观念,形成对自我和他者一致的认识,并以此进行新一轮的良性互动。
因此,为了避免东盟国家政治精英和决策者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偏差,需要增强微观层面的政治互信。可以通过加强沟通交流和良性互动,改变决策者原有的认知结构。借助首脑外交、“第二轨道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式,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导人、智囊机构和民众开展广泛的对话和深入的交流,实事求是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争取各方能够理解、赞同和支持中国的倡议。
1.加强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指的是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直接参与的外交活动。国家领导人是外交政策的最终决定者,领导人的认知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交政策走向。中国与东盟国家的领导人可以通过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亚峰会等多边交流合作机制,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双边互访,加强高层沟通与交往,增进彼此之间的友好感情,让东盟各国领导人理解“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次内涵,缓解东盟国家领导人在东亚权力转移过程中对中国的恐惧和不安,让他们进一步体会中国“亲、诚、惠、容”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同时,双方领导人之间还可以建立热线电话联络,就彼此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对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协调,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避免认知偏差扩大。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之间还可以运用首脑外交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并通过这个渠道让东盟国家领导人更多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争取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的理解和支持,进而推动本国的友华政策高效顺畅的落实,特别是推动更多的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双边层面的命运共同体。
2.做好“第二轨道外交”
“第二轨道外交”也称“二轨外交”,指的是各国智库或者政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专家智库是外交决策的间接参与者。国家领导人在做出外交决策之前,往往会征求本国智囊机构的意见和建议,这种资政行为也间接地影响外交决策者的认知。因此,避免决策者的认知偏差,还需要做好“二轨外交”。中国政府支持国内智库、政策研究机构与东盟国家对应的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就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合作进行学术讨论,并在此过程中传播新知识、启迪新思想,将包括“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在内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传递给东盟国家的同行。同时,国内学术界也可以举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研究为主题的国际论坛或会议,邀请东盟国家的专家学者共同进行学理研究,使其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并就如何“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听取东盟国家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3.重视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指的是本国的社会团体对他国民众进行的民间交流活动,以增进彼此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民众是外交决策的背后推动者。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续。随着各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领导人的外交决策越来越顾及民众的感受。如果只依靠官方的推动而民间交流滞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很难形成广泛的民意基础。因此,避免认知偏差还需要重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公共外交,向东盟各国民众讲好中国故事,让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东盟国家民众心中落地生根。中国媒体可以与东盟国家的同行加强合作,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相关的文化宣传片、短视频、公益广告等引入东盟国家,让当地民众认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对推动双方合作共赢、增加友好交往的作用。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可以利用现有的民间交往渠道,加强旅游、文化、科技、体育、青少年等方面交流,让东盟国家民众有机会了解真实的中国,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在社会合作方面,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为引领,加强双方环保、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在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等社会治理领域开展合作和经验交流,将倡议精神落到实处,让普通民众分享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红利。
六、结 语
十年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在地区层面、次区域层面和双边层面不断取得突破。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放弃观望,转而支持中国的倡议。但是,仍然有少数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倡议采取模糊应对和选择性回应的态度,其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对“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认知偏差。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发现,认知偏差产生的原因包括认知相符现象导致的误判、诱发定式导致的误解、历史包袱造成的扭曲。认知偏差导致一些东盟国家政治精英,或采用绝对理性思维看待问题,或高估中国倡议对于本国的外来影响,或陷入强国必霸的思维定式,或出现害怕在中美间选边站队的认知失调。
避免东盟国家政治精英对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产生认知偏差,在于通过加强沟通交流、良性互动,改变其原有的认知结构,培养正向认知。因此,有赖于作为外交直接决策者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通过外交政策间接制定者的智囊机构交流合作,还可以通过增进东盟国家民众的好感“以民促官”,影响领导人的外交决策。
总之,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往更大高度、更广宽度发展,不可忽视微观层面观念性因素的影响。国家是由人构成的整体,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需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特别是关注政治精英的认知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