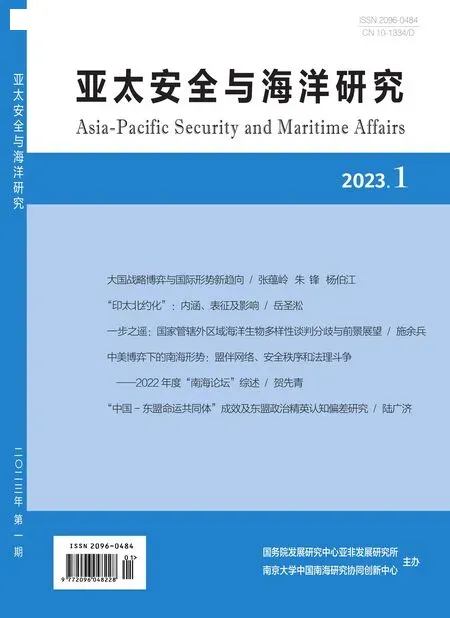“印太北约化”:内涵、表征及影响
2023-04-06岳圣淞
岳圣淞
内容提要:自美国“印太战略”提出以来,学界对“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关注日益增强。既往研究往往强调“印太战略”实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效仿北约的政策倾向,并未触及对这一趋向产生的政策根源的深入探讨。理解“印太北约化”,不能脱离美国对外安全观念变迁的宏观背景,对其内涵的理解也应包含三个方面,即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类比倾向、在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时的“北约化”路径依赖,以及在介入地区事务过程中的“北约化”思维定式。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的内涵、表征与影响,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为未来应对区域秩序动荡和中美关系发展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提供参考和启示。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以来,过去六年间,尽管历经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乌克兰危机加剧、国内政治与社会危机持续等多重复杂因素影响,美国“印太战略”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政策逻辑的延续和实施进程的连贯性,并随着政策议程的不断拓展、资源投入水平与行动策略的不断调整、与政策对象国间交往频次和互动深度的不断提升而对区域乃至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1)参见信强、余璟仪:《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安全竞争》,《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4期,第50页。
尽管美国始终强调“印太战略”旨在维护“自由、开放与繁荣的区域秩序和国际规范”,符合域内国家“广泛而共同的利益”,但事实上美国持续推进“印太战略”的根本意图旨在掌控对区域秩序塑造的主动权。(2)William T. Tow, “Minilateral Security’s Relevance to US Strategy in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 and Prospects,” Pacific Review, 2019, Vol.32, No.2, pp.232-244.面对中美实力对比差距显著缩小的现实,作为霸权国的美国持续受到“对华战略焦虑”的情绪裹挟,因而试图通过“印太战略”的实施作为对华战略围堵与打压、展开“对华影响力竞争”的核心手段。(3)参见孙兴杰:《印太还是亚太?——空间演化、地缘重组与区域秩序未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5期,第22页。但另一方面,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提供方,中国同域内各国间日益深入的合作已事实上成为维护地区和平、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基础。(4)参见余南平:《新冠疫情下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特征与未来挑战》,《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1期,第3页。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印太战略”的深入推进,美国持续升级对华政策攻势,试图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并持续加大对印太地区的资源投入,通过集结域内盟友、升级同域内他国的伙伴关系、巩固在其主导下的现有区域多边机制并不断建立新多边安全架构,以加速在中国周边形成“遏华包围圈”,实现其“形塑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约束中国对外行为”的战略目标。(5)参见汪曙申:《美国介入背景下台湾当局南海政策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3期,第68—69页。与此同时,通过“安全化”政策手段的实施,美国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威胁”、人为夸大区域安全紧张形势、泛化安全政策的指涉范围,并以此为据引入印太地区以外特别是北约同盟体系安全资源,强行将其主观的印太安全关切并入北约的安全政策轨道,造成区域安全秩序与安全形势日益复杂。(6)参见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及政策影响》,《欧洲研究》2022年第5期,第78—79页。在此背景下,“印太北约化”已成为当前美国推进“印太战略”政策实践中日益凸显的政策取向,并由此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文认为,“印太北约化”趋向的加剧,将不可避免地对区域既有秩序形成强烈冲击,其不仅令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更为域内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求对外政策和自身发展目标间平衡的长期努力带来沉重的战略负担和政策压力。对于中国而言,深入理解“印太北约化”趋向的演化特征、内涵、现实表征与影响,有助于在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为未来应对区域秩序动荡和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两洋战略”构想与美国区域安全观的变迁
作为国际体系中长期奉行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霸权国,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演化与实践背后固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物质主义与理性主义行为逻辑,但与此同时,历史经验、决策观念与价值取向等非物质因素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持续性影响同样值得关注。且相较于物质性因素对政策过程的阶段性作用,非物质因素特别是观念性因素对政策的影响往往是连贯而持续的,是政策逻辑完整性和实践过程连续性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7)参见岳圣淞:《政治修辞、安全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第82—83页。正因如此,对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的特定趋势的分析和理解必须基于其相关的政策语境,并对其政策实践的理念脉络展开回溯。对“印太北约化”倾向的分析亦不例外。
需要指出的是,“印太北约化”(the NATO-ization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与“北约印太化”(NATO’s Indo-Pacificization)是在美国大力统筹两洋地带区域政策、推动全球战略资源重组的背景下出现的,是在同一政策过程中的一对相互支撑、互为前提的政策演进趋势。(8)学界对“印太”和“亚太”作为地缘和空间指涉的概念范畴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印太所涵盖的地理范围大于亚太,美国官方政策对印太的解释突出了印太对印度洋地区的囊括,是指“从印度洋西海岸到美国西海岸”之间的区域。总体上,国内政策分析界依旧沿用亚太的概念作为研究地区局势的基础地理单元,仅在探讨美国“印太战略”政策影响时使用印太概念。本文沿用上述做法:在从中国的政策视角进行分析或分析美国在“印太战略”提出之前的区域政策时,使用亚太及其相关概念;在从美国政策视角出发进行分析时,使用印太及其相关概念;在讨论中美在区域内的政策互动或涉及亚太与印太重合的地区时,使用“域内”或“本地区”的提法。有关印太与亚太的概念辨析的代表性研究,参见孙兴杰:《印太还是亚太?——空间演化、地缘重组与区域秩序未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5期,第22—45页;孙茹:《中美全球博弈下的北约亚太化》,《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7期,第51—60页。国内外学界对这一对政策趋势的关注点存在差异。其中,国内学界更加倾向于探究美国“印太战略”对自身所处的地缘政治与安全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因而对“印太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北约化”趋势及其走向予以持续关注。(9)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印太战略”实施进程中出现的“北约化”政策倾向,国内外学界已多有论及,但少有学者明确提出“印太北约化”的相关概念。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可参见胡娟:《“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南亚研究》2022年第3期,第24—41页;巴殿君:《俄乌冲突对全球、印太及东北亚地区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第5—6页;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张景全、罗华婷:《拜登政府对华围堵复合联盟战略及中国应对》,《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6期,第36—53页;葛建华:《欧盟战略自主与欧版“印太战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38—57页;Andrew Erskine, “NATO, AUKUS & The Indo-Pacific: Further Proof of Intra-Alliance Friction,” Nato Association of Canada, December 21, 2021[2022-11-04];Ashley J. Tellis, “Waylaid by Contradicitions: Evaluating Trump’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20, Vol.43, No.4, pp.123-154; Ralph A. Cossa and Brad Glosserman, “Multilateralism (Still) Matters, as New Indo-Pacific Strategy Emerges,” Comparative Connections, 2022, Vol.23, No.3, pp.164-169; Jina Kim, “Ukraine’s Implications for Indo-Pacific Alignmen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22, Vol.45, No.3, pp.47-64; Thomas Wilkins, “A Hub-and-Spokes ‘Plus’ Model of US Alliances in the Indo-Pacific: Towards a New ‘Networked’ Design,” Asian Affairs(London), 2022, Vol.53, No.3, pp.457-480。部分国内学者提出“印太北约化”或相似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21年起国内学界围绕美国试图推动构建“亚太版‘小北约’”而展开的讨论。(10)有关国内学界关于“亚太版‘小北约’”的讨论,代表性的观点参见:林民旺:《“亚洲北约”已具雏形》,《世界知识》2021年第20期,第34—36页;项昊宇:《从四国军演看“印太北约化”》,《环球时报》2021年5月20日;李嘉宝:《“亚太版北约”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5月24日;王键:《俄乌冲突在东亚地区外溢效应论析》,《日本研究》2022年第3期,第25—33页。相比之下,西方学界则更加注重分析“印太战略”推进过程中北约国家的角色作用及其相关安全政策所发挥的“外溢效应”,对北约逐渐加强对印太事务参与的积极性及其影响予以高度关注。(11)Eric Kim et. Al., “NATO’s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Indo-Pacific,” Defence Studies, 2022, Vol.22, No.3, pp.510-515; Thomas Wilkins, “A Hub-and-Spokes ‘Plus’ Model of US Alliances in the Indo-Pacific: Towards a New ‘Networked’ Design,” Asian Affairs (London), 2022, Vol.53, No.3, pp.457-480; François Heisbourg, “Euro-Atlantic Security and the China Nexus,” Survival (London), 2021, Vol.63, No.6, pp.45-62.
回顾学界有关“印太北约化”的研究后可以发现,既往“印太北约化”趋向的相关研究,往往过于关注“印太战略”实践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出现的效仿北约的政策导向,或认为“印太战略”与美国北约政策间之所以出现越发明显的协同关联趋向,主要是由于外部安全局势的剧烈变动触发了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调整机制,其本质还是试图将外部安全局势的急剧变化作为解释美国“印太战略”政策实践转向的核心变量。受此影响,此类研究并未触及对这一趋向产生的政策理念根源的深入探讨,且对其内涵、现实表征和影响的认知存在较大争议。
那么,“印太北约化”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规划出现“北约化”倾向,到底是基于对现实情势急剧变动的反应而产生的阶段性政策调整,还是源于其一贯的政策传统?“印太北约化”的具体表征有哪些,其对地区整体秩序、地区大国产生了何种影响?
本文认为,首先,理解“印太北约化”离不开对美国对外战略特别自“两洋战略”提出以来的历史演进过程的考察。因为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印太北约化”趋向的出现,很大程度可归因于美国一贯对外战略的延续,而非受短期外部安全局势变动影响的结果。(12)He Kai and Li Mingjiang,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of the Indo-Pacific: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Regional Actors,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2020, Vol.96, No.1, pp.1-7.其次,对“印太北约化”内涵的理解应包含三个核心方面,即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认知的“北约化”类比倾向、在发展同印太地区国家间关系时的“北约化”路径依赖,以及在介入并参与地区事务过程中出现的“北约化”思维定式。最后,在持续推动“印太战略”深化的过程中,美国在提升区域网络化关系水平、强化资源整合与投送能力等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逐渐呈现出“北约化”的政策行为特征,并对区域安全、经贸和政治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13)参见金玲:《“全球北约”的亚太转向与前景展望》,《当代世界》2022年第9期,第40—44页。
在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传统观念中,由太平洋与大西洋构成的“两洋板块”始终被视为其对外战略的两大核心支柱。确立以两洋板块及其周边区域为枢纽、统筹资源配置、平衡力量分布,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全球战略布局的“两洋战略”(Strategies on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Atlantic Ocean),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理念的代名词。(14)Lee Willett, “Balancing Act: US Evolves Maritime Strategy to Balance Atlantic and Pacific High-End Threats,” Naval Forces, 2019, Vol.40, No.5, p.S50.事实上,早在冷战结束初期,为巩固在欧亚大陆板块的霸权地位,美国就曾明确提出过“两洋战略”构想,试图通过对两个关键区域政策的协同,以实现遵循自身价值理念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愿景。“两洋战略”的核心内涵是,通过控制太平洋和大西洋,依托北约东扩和美日同盟,从欧亚大陆两端向腹地逐渐渗透,以最终完全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掌握关乎全球地缘、安全、经济、能源等各领域命脉的战略资源支配和秩序主导权。在此过程中,北约与美国自主构建的区域同盟体系,被作为实现两洋战略的关键机制化平台。(15)参见朱听昌、马荣生:《从两洋战略看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的调整》,《国际观察》2003年第2期,第20—26页。
在美方决策者看来,冷战后欧亚大陆的地缘价值并未因苏联解体而降低;相反,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未来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都与它对欧亚大陆的政策紧密相关。(16)参见樊吉社:《从亚太到“印太”:美国地区安全战略的变迁与回归》,《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第33—35页。因此,美国将欧亚大陆视为其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并为其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国别政策,即将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确立为地缘政治的竞争对手;将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确立为具有相对较强地缘影响力的支轴国。若美国期望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游戏中保持长期优势,就必须优先处理好同上述国家间的关系。(17)Stephan Fruhling, “‘Key to the Defense of the Free World’: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levance of NATO for US Allies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ranslantic Studies, 2019, Vol.17, No.2, pp.238-254.
尽管美国重视欧亚大陆整体的地缘战略价值,但对于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关注水平仍有差距。总体来看,在21世纪之前,欧洲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高于亚洲。作为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桥头堡,美国自认为在欧洲有着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大西洋联盟在欧亚大陆上直接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同时也是美国建立“全球民主国家集团”的大本营和对外输送民主价值观的样板与纽带。(18)参见张健:《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9期,第35—43页。相比之下,美国认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一个对自身安全和繁荣越来越重要的地区,但由于亚洲地区国家现实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形势复杂,因此仍需加大资源投入、持续深耕。
在此背景下,1996年6月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发布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指出,美国未来将增强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关注,加大对这一地区的发展投入,致力于激发该地区的经济潜力与整体实力提升,加强美国同地区主要国家间的交往联系。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确保在亚洲不会出现一个敌对的超级大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是美亚太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19)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A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1996, 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files/americas_interests.pdf[2022-11-02].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再次强调,美国必须把广泛地促进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的目标同较为传统的地缘战略利益结合起来,稳定有序地经营欧亚大陆。(20)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May 1, 1997, https://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97[2022-11-02].具体而言,即在欧洲,强调美欧合作,既联欧制俄,又防止欧俄联合,通过推动北约东扩和发动科索沃战争,不断增强对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权,积极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欧洲安全体系;在亚洲,以美日、美中关系为中心,既联日制华,又保持美中关系的总体稳定。
布什政府上台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前任政府欧亚政策的总体走向,不但坚持和强化了克林顿时期的欧洲和亚太战略,还借反恐之名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积极加强对东南亚和南亚的渗透,而且利用中亚国家的选举混乱推动“颜色革命”,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存在和影响。(21)参见潘志平、胡红萍:《中亚将何去何从——“颜色革命”,还是“反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2期,第51—56页。
自奥巴马政府时期起,面对中国实力显著增长的现实,美国对华战略疑虑开始明显上升。基于此,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显著上升的影响力。此后,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自身作为“亚太国家”的身份定位,并持续加大对该地区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明显增强了与域内主要盟国日本、韩国及部分东南亚国家间的互动频次与深度,通过积极参与双多边互动介入亚太事务,意图巩固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22)参见蔡佳禾:《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之遗产——大战略视角的研究》,《南大亚太评论》2017年第1期,第136—189页。尽管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对华威胁感知已经上升至较高水平,但中美关系仍总体保持稳定,这一方面得益于双方均致力于维护双边各层级战略沟通渠道的通畅,有效避免了战略误判的发生,另一方面则由于美国的对外政策依旧遵循了既往的理念路径,即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尽可能地寻求政策平衡,既维护与欧洲盟友间的传统友好与战略协作关系,又寻求在亚洲地区与中国的关系稳定,避免地区局势在任何一方出现急剧转变。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针对欧洲和亚太地区的政策尚存在较为清晰的边界,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国家对亚太事务的介入程度依旧有限,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分歧和矛盾并未因域外国家的过度影响而变得更为复杂。(23)参见岳圣淞:《情境、身份与对外政策:政治修辞理论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1年,第115—158页。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美国新一轮对华政策调整随即展开。在其任内接连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安全战略》《核态势评估》等多份政策报告中,均明确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威胁区域安全与稳定的秩序破坏者”,认为中国正在公开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其目标不仅是改变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秩序现状,“推动其朝着有利于中国的利益和偏好的方向演化”,更是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悖的世界”。(24)Ashley J. Tellis, “Waylaid by Contradictions: Evaluating Trump’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20, Vol.43, No.4, pp.123-154.特朗普政府认为,此前历届政府所推行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应当采取更加强硬的方式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缘战略野心”。基于此,美国提出将以“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取代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对华在更广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展开全面战略竞争——这是美国对外政策历史上首次以“印太”取代长久以来沿用的“亚太”概念来命名相关的区域的战略。(25)Marcin Grabowski, “Joe Biden’s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hange or Continu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olish Political Science, 2021, Vol.50, No.4, pp.95-105.
二、“印太战略”的提出与“印太北约化”趋势的缘起
无论从理论、历史还是现实政策角度看,国际社会对“印太”概念的认知都并非约定俗成且毫无争议。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深化的当下,美国大举推进“印太战略”无疑为“印太”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地缘博弈色彩。“印太”概念的提出,反映了美国对其与亚洲太平洋国家间关系和对整个地区战略布局的新思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一)基于政策成本收益的考量
以“印太”取代“亚太”不仅可以大幅拓展对华竞争的空间指涉,为美国及其盟友深度介入区域事务提供战略层面的合法性依据,还能够实质提升美国全球同盟体系在这一区域内的资源整合与协同能力,吸纳更多域内国家参与美国主导的区域议程,令其以更低的战略成本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成为可能。(26)参见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第14—22页。与此同时,“印太”概念的提出,大幅提升了印度在美国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是对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层级的提升,体现了美国在未来更加倾向于借重印度在该区域发挥地缘影响力,以协助其实现制衡中国的战略企图。(27)Harsh Pant and Abhijnan Raj, “Is India Ready for the Indo-Pacific?”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18, Vol.41, No.2, p.47.
(二)基于维护自身经济与安全优势的考量
根据拜登政府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广义上的印太地区拥有世界近半人口,以及广大东北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国家,还包含了几个全球商贸咽喉要道。(28)The White House,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February 2022,pp.4-6.通过将印度洋区域提升至与太平洋区域同等重要的位置,“印太战略”强化了两洋之间海上通道对促进该地区乃至全球海上贸易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印太”取代“亚太”地区作为美国拓展区域经济合作的纵深地带,其覆盖范围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所在区域实现了高度重合,进一步明确美国未来意图同中国在经济领域争夺影响力、展开“近身博弈”的战略决心。
事实上,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深感自身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经济影响力受到来自中国的严重威胁。在其看来,“一带一路”涵盖范围庞大、涉及国家众多,参与共建的国家普遍具有较强的发展诉求。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为“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资源和实力基础,令其在全球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不仅如此,“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为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提供了契机。通过这一合作机制,中国不仅实现了产能和技术等有形资源的输出,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还间接地向相关国家推广了自身的发展理念和对外政策构想,获得了国际形象与制度话语权的大幅提升。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出的越发自信的姿态,被美国解读为对其全球性主导权力和地位的直接挑战。受此影响,美国试图在其亚太政策中进一步强化对经济因素的重视,并相应地提出旨在对冲“一带一路”影响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展开对华竞争。(29)参见岳圣淞:《政治修辞、安全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7期,第78—103页。
(三)基于地缘战略规划的考量
回顾美国后冷战时期对欧洲和亚洲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历任美方决策者均试图通过某种政策平衡实现对两大区域秩序走向的有效控制,并力求在施加地缘影响力方面做到兼顾。但事实上,直至特朗普政府正式开启“印太战略”的实施进程起,国际社会才真正从制度层面切实感受到了美国试图将“两洋战略”构想“合二为一”的战略决心与意图。(30)参见葛腾飞:《“印太”地区安全秩序纷争与中国的地区秩序愿景》,《外交评论》2021年第3期,第73页。在此之前,美国对欧政策总体上长期遵循了以“价值观导向”为主线、以美国—欧盟经济合作为基础、以北约作为安全保障核心机制的“离岸治理”模式;在亚太地区,由于缺乏类似于北约的高度机制化的安全保障合作平台,美国则更倾向于依赖同日、韩、澳、泰、菲等域内盟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稳定、防范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鉴于亚太地区国家所处发展阶段、践行的社会制度与政治理念的多样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美国无法照搬类似对欧政策的行动框架发展对亚关系,只能采取差异化的经略手段,因而造成与亚太国家关系水平呈现参差不齐的态势的长期持续。(31)参见刘稚、安东程:《东盟国家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国际展望》2020年第3期,第114—120页。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华政策此前始终秉持了以接触为主的战略导向,双边关系的长期总体稳定,令美国并未将双方的价值理念冲突视为“威胁区域秩序走向”的隐患,因而并未采取相应的大规模政策攻势予以应对。
随着对华认知出现结构性转变、中国被视为影响“区域秩序稳定”“挑战国际规范与国际准则”的首要威胁(32)Laura Southgate, “Explain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ailure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2008,” Asia Policy, 2021, Vol.28, No.4, pp.195-215.,美国据此选择将原本限于物质层面的中美双边矛盾推升至多边价值观层面,并号召域内和域外盟友共同应对。在美国的持续渲染和煽动下,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开始转变对华认知,并逐步接受了美方对中国“价值观威胁”的定位,认为中国区域影响力的提升,削弱的不仅仅是美国的霸权地位,更是对西方世界乃至“全球民主阵营”的主导地位带来的整体冲击。(33)参见王鹏权:《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特征分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年第3期,第133—144页。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顺势推动其对欧政策和对亚太政策的一体化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说,“印太战略”的提出,可以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两洋战略”实现高度政策联通与协同的关键步骤。从单纯的地理概念上来看,印度洋地区位处大西洋和太平洋板块之间,战略价值极为重要,但却长期游离于美国“两洋战略”的政策范畴之外,而“印太战略”的提出则可以将印度洋板块正式纳入其原有的亚太战略规划当中,实则是补齐了欧亚大陆上的“最后一块短板”。(34)参见黄郑亮:《印度对“印太”的参与、局限与展望——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南亚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0—132页。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在“印太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总体承袭了前任“大国竞争”的战略导向,继续将印太锚定为开展大国博弈的核心场域,但更注重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和价值观等各领域的政策议题、资源和手段的协同,更倚重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所发挥的“力量倍增器”功能,助力其实现“全方位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35)参见韦宗友:《拜登政府“印太战略”及其对亚太秩序的影响》,《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第44—60页。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在加速推进“印太战略”的具体手段和行动策略上,明显增强了对制度性约束力的重视,认为通过建立起涉及不同领域、不同层级、涵盖不同范围和不同国家的多边机制将更能激发“印太战略”的政策潜力。(36)参见孙兴杰:《印太还是亚太?——空间演化、地缘重组与区域秩序未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5期,第22—26页。但鉴于印太地区现有的合作机制和网络化关系已明显不能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因而拜登政府决意通过借鉴业已成熟的“北约化模式”对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进行重塑——至此“印太北约化”的政策趋势在拜登政府时期开始凸显。
三、“印太北约化”的政策内涵与特点
目前,学界围绕“印太北约化”展开的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而这也大致反映出学界对“印太北约化”趋势的整体认知。
(一)美国对印太地区安全观念的“北约化”倾向
冷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全球霸权地位的排他性和长期性,美国始终坚持将防范任何地区出现可能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区域性霸权界定为其对外战略的核心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对欧战略上始终强调联欧制俄,在对亚太战略上则强调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尽管如此,在“印太战略”正式推行之前,美国对俄和对华政策仍呈现出明显差异,特别是在遏制强度上和对双边冲突容忍度方面,美国对华战略更倾向于在“接触—合作”和“遏制—对抗”之间寻求平衡,但在对俄战略方面则更多突出单向度的以遏制主导的行动取向。(37)参见蔡佳禾:《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政策之遗产——大战略视角的研究》,《南大亚太评论》2017年第1期,第136—189页。
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对中俄之间战略协作水平的不断提升深感忧虑,因而决定将两国共同列为“修正主义大国”,在对外战略层面强调同等程度的遏制,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碍中俄战略合作关系的持续深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两洋战略”视域下,俄罗斯对于欧洲大陆稳定所造成的威胁,同中国崛起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稳定所带来的隐患,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高度同质化的“安全挑战”。(38)Ye Xiaodi, “Explaining China’s Hedg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Review (Hong Kong, China: 1991), 2020, Vol.20, No.3, pp.205-238.也正因如此,美国在处理对俄和对华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决策类比”的认知路径依赖——在将俄罗斯界定为欧洲大陆首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美国不断提升同北约国家的战略协作水平,并试图积极拉拢、影响和策动俄周边国家挑动俄周边安全局势,以期通过间接制衡的方式约束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走向。(39)Anna Kireeva, “Regional Strategies and Military Buildup in East Asia and Indo-Pacific: A Russian Perspective,” Maritime Affairs, 2014, Vol.10, No.2, pp.33-51.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在介入乃至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塑造的过程中,同样期望通过对中国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力,推动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向美国期望的方向演进,以此牵制中国精力、掣肘中国的对外战略布局进程,并最终实现对中国对外战略行为走向的有效约束。
但鉴于亚太地区缺乏类似北约的高度集成化的安全合作机制,美国仍需很大程度上依赖亚太同盟体系发挥其对地区安全秩序的主导作用,并通过对地区既有安全机制的参与和渗透,以及积极筹建新的多边安全机制对亚太版“北约”的缺失作出制度功能性的补充。(40)James Crabtree, “Indo-Pacific Dilemmas: The Like-Minded and the Non-Aligned,” Survival (London), 2022, Vol.64, No.6, pp.23-30.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印太战略”提出伊始,就明确将中国界定为“破坏区域稳定的首要威胁”,渲染中国利用自身经济实力对域内国家实施具有明显强制性和压迫性的对外政策,并暗示中国的区域政策与俄罗斯的欧洲政策存在政策逻辑和战略意图上的高度相似性。(41)参见李岩:《特朗普安全战略的调整与限度》,《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54—72页。基于上述政策背景的铺垫,美国得以在“印太战略”中提出具有鲜明对华指向的政策议程,为其出台效仿北约的行动策略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二)美国发展同印太国家关系的方式呈现“北约化”特点
类似于冷战结束后为填补欧洲地区出现的“权力真空”而推行的“北约东扩”政策,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发展同域内国家间关系的过程中,为应对中国区域影响力不断上升的现实,美国提出将致力于“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以实现对中国的“间接制衡”。(42)Ashok Sharma, “Australia-US Alliance and Strategic Geometr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 Evaluation,” Artha-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7, Vol.16, No.4, pp.39-60.在美国看来,鉴于当前中国的实力崛起进程已突破“质变”阶段,但实现超越美国的“量变”尚需时日,因而只有通过塑造和干预中国密切依赖的外部崛起环境,方能达到迟滞中国崛起进程的目的。(43)参见谢晓光、杜洞光:《美国“印太”联盟体系转型:措施、特征与限度》,《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6期,第54—71页。在此背景下,中国周边国家的立场与态度就变得尤为关键。基于这一战略考量,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加紧了针对中国周边国家的网络化布局,一方面宣布继续加强同域内盟国间的战略合作、推动建立新的“印太伙伴关系”以促进伙伴关系网络扩容,重点争取友华国家和对华经济依赖程度较强国家逐步摆脱中国影响,另一方面则加速推进区域多边关系网络建设升级,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合作机制(AUKUS)、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与“五眼联盟”共同构成螺旋式上升的安全架构,确保“印太战略”的政策实效触及“印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44)参见武香君:《“印太战略”下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国际论坛》2022年第5期,第139—154页。
(三)美国在参与印太事务过程中凸显“北约化”思维定式
“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是冷战后北约在美国操纵下所展开的一系列区域政策实践中所暴露出的、最为国际社会所诟病的两大核心特征。自“印太战略”推行以来,美国参与印太事务、同域内国家在各领域展开的政策互动也越发显现出这种“北约化”思维定式。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各种不负责任的“退群”行动、动辄对域内国家实施制裁与威慑以迫使其屈从于美国的区域政策“一致抗华”,再到拜登政府时期试图组建基于“价值观同盟”的各领域排华圈层、推动区域事务“去中国化”等一系列举动,都凸显出美国单边主义和具有明显霸权倾向的行为特质。从行为逻辑上看,美国在印太地区对华实施战略打压和孤立的种种行为,同其在欧洲地区对俄采取的施压和对抗性战略一脉相承、如出一辙,这也是“印太战略”在实践理念上逐步向美国的北约政策靠拢、进而造成“印太北约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关键表征。可以预见的是,伴随“印太北约化”倾向的日益加剧,集团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将对区域内本已脆弱的互信基础、交往默契、互动模式与政策平衡形成冲击。
四、“印太北约化”的政策表征及对区域秩序的影响
相较于此前历届政府,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推行的“印太战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集结了美国在印太地区既有的同盟体系资源,并通过政策覆盖范围的扩充,将广阔的印度洋地区纳入对华竞争的指涉范围,继续挖掘潜在战略合作伙伴,以共同实现对华战略遏制。在此过程中,美国在提升区域网络化关系水平、强化资源整合与投送能力等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逐渐呈现出“北约化”的路径特征,并对区域安全、经贸和政治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趋势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本地区未来秩序稳定的广泛担忧。
(一)“安全化”与区域安全困境的升级
安全议题始终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2022年发布的新版《美国印太战略》中提出,为防止本地区陷入“混乱和动荡”,美军将视印太为“优先战区”,将加速落实“太平洋威慑倡议”,大力推进“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明确将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和南海局势列为其“首要安全关切”,并通过与域内盟国、伙伴国和北约盟国间开展高频次、多领域军事行动,以不断提升威慑强度,展现维护区域秩序的能力与决心。(45)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2-11-05].
南海问题是“印太战略”框架下安全领域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在安全层面实施对华战略打压的重要抓手。中国同南海有关国家围绕南海海域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久已有之。自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美国就不断强化自身作为“亚太国家”的身份定位、反复重申美国在南海地区“拥有重大核心利益”,意图将自身对亚太地区的政策关注包装成为其为维护自身战略安全利益的合法化举动。(46)参见陈慈航:《美国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政策论析》,《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4期,第68—98页。事实上,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亚太地区域外国家,美国深知自身对南海问题的高调介入本身缺乏说服力,故而试图通过议程扩展和安全化等手段主观建构合法性依据,大肆渲染所谓“南海不安全”和“南海航行自由受阻”的政策论调,企图挑动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关切,为自身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所谓法理依据和正当性逻辑支撑。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的打压态势有增无减。随着中美各领域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华遏制程度日益加深,有关南海主权争端的涉华议题已事实上成为美国对华构建威胁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47)参见张志洲:《南海问题上的话语博弈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第126—134页。
在此背景下,美国将中国归咎为“造成南海紧张局势”“扰乱地区安全”的根源,并以中国同南海有关国家的海洋权益与领土争端为抓手不断进行舆论炒作,导致南海议题在国际舆论界迅速升温。(48)Mikael Weissmann, “Understanding Power Shift in East Asia: The Sino-US Narrative Battle about Leadership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ian Perspective, 2019, Vol.43, No.2, pp.222-248.在此基础上,美国还持续鼓动以菲律宾和越南为代表的南海声索国利用各种国际多边平台和场合主动发声,大肆煽动悲情民族主义以博取国际社会同情,阻止国际社会对南海问题本质、根源及其现状产生客观公正的认知与评判。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纠集其他西方媒体组成针对南海问题的舆论同盟对所谓“受到中国霸凌”的南海主权声索国予以声援、不断壮大舆论声势,凭借西方话语霸权形成的全球传播力和话语影响力展开大规模动员:一方面,依托对国际法有关条款的片面解读,试图从所谓法理上削弱甚至打压中国作为当事国的抗辩权益;(49)参见余敏友:《美国南海政策的新发展及对我国的挑战——评蓬佩奥南海声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第5—19页。另一方面,建构南海声索国的“小国受害者”身份,不断对“中国妥协让步”这一情景展开推演自述,试图刻意避开对事件解决过程中程序合理与合法性的讨论,设置“大国风范”舆论陷阱以达到从道义上绑架中国立场表达的目的。客观来说,西方舆论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是否妥协”同“中国是否遵守国际规范与国际秩序”两个问题相混淆,“中国南海霸凌论”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并持续受到国际关注,令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陷入一定程度的被动。(50)参见杨悦:《大国竞争与特朗普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美国研究》2020年第6期,第89—109页。
南海地区被视为美国开展全面对华竞争的前沿,“航行自由行动”是与之相适应的具体举措,美方在这一行动上表现出了高频率和高压态势,并纠集众多盟友展开联合行动。特朗普政府2017年和2018年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各为6次,2019年和2020年各开展南海“航行自由行动”9次和13次,其任期之内共计34次,为平均每年8—9次的频率。(51)Jeff M. Smith, “Biden Must Keep Challenging China on Freedom of Navigation,” Foreign Policy, Feb.16, 2021, p.5.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的南海政策,其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高于前任,就职一个月不到,美舰就4次进入南海,2021年共计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18次。在独立开展军事活动的同时,美国还同其亚太及欧洲盟友不断展开联合行动,旨在昭示如果中美在南海出现冲突升级的情况,美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调集同盟力量予以驰援。自2021年开始,美国先后同日本、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加拿大、荷兰等国开展了10余次规模不等的联合军演,区域涉及孟加拉湾、菲律宾海和日本周边海域。(52)参见《2021年美军南海军事行动不完全报告》,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2022年3月27日,http://www.scspi.org/zh/yjbg/1648366779[2022-11-02]。
在更为敏感的涉台问题上,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前任政府执政后期的过激言行、屡屡突破美国政府此前长期延续的对台交往限制,更公然将台湾纳入其印太伙伴行列,声称“将同域内外伙伴一道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包括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建设”,不断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53)“Biden Signals Taiwan Defense,” Democrat-Gazette, May 24, 2022, https://www.nwaonline.com/news/2022/may/24/biden-signaling-taiwan-defense/[2022-11-05].2022年8月2日,美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公然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这些踩踏红线的危险做法,凸显出拜登政府意欲将涉台问题纳入“印太战略”行动框架、继续维持两岸分裂、“以台制华”的战略野心。(54)参见信强:《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嬗变与困境》,《台湾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1页。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尽管美方一再声称将致力于维护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打造“更加透明和更具包容性的区域安全架构”(55)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2017, Rand Corporation, 2017,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392.html[2022-11-05].,但不可否认,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开展的一系列政策布局已呈现明显的“北约化”倾向。在美国持续升级的政策攻势下,域内国际关系的分化趋势正逐步显现:部分亚太国家特别是同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国家,由于受到美方怂恿而倾向采取更为冒进的机会主义策略处理对华关系,大大增加了发生双边军事摩擦和意外冲突的风险;对于大多数实力有限的亚太国家而言,来自美方的政策施压令其在处理对美和对华关系时陷入战略被动,因而不得不采取更为保守和谨慎的策略予以应对,而这一趋势的延续也势必将进一步削弱区域安全合作的动力,令本地区原本脆弱的安全治理机制碎片化加剧。(56)参见曹鹏鹏、石斌:《“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0期,第41—54页。
(二)“去中国化”与区域经贸秩序的持续动荡
相较于前任政府,拜登政府充分意识到,单纯强调“印太战略”的安全属性无法形成有效合力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区域影响。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在推动区域经贸合作过程中展现出的越发积极和主动的政策姿态已引发了美国的担忧:2020年11月15日,中、韩、日、澳、新与东盟十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一个覆盖全球23亿人口、GDP总量占比达到30%的全球规模最大自贸区就此诞生;2021年9月16日,中国正式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保存方新西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部长提交申请加入CPTPP的书面信函,标志着作为区域内最大经济体的中国继加入RCEP之后,又正式开启了加入另一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区域多边经贸合作框架的进程。上述政策举措,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贡献一己之力,进一步承诺扩大对外开放,同其他有发展诉求的国家共同分享中国发展成果和市场机遇的良好愿望与责任担当。
尽管中国在区域经贸合作中始终秉持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参与多边经贸合作也完全合情合理,但上述举动客观上加剧了美国对自身在本地区经济影响力被削弱的忧虑。在美国看来,无论是RCEP还是CPTPP,由于美国的缺位,而其他参与国在经济体量上无法同中国相抗衡,因此中国在两大区域贸易机制中将毫无争议地获得领导者地位。一旦中国同时参与这两个自贸协定,将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在亚太地区的生产网络体系和亚太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当中获得更主动的战略地位,对中国未来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经济将带来巨大的提升机遇。
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和政策界人士开始呼吁:“为扭转不利局面、抗衡中国的影响力,美国必须在涉及地区贸易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有效的领导能力。”(57)Senate Finance Committee,“Letter to President Biden,”https://www.sasse.senate.gov/public/_cache/files/c6c90ba8-7be1-4d2c-a257-1bbe46827bfd/11.08.2021-letter-on-digital-trade-fin-committee-final.pdf[2022-11-08].2021年10月底,美国与“印太战略”相配套的经济联盟初露端倪。拜登在同年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宣布,美国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印太经济框架的发展,围绕贸易便利化、数字经济和技术标准、供应链弹性等领域,探索与印太盟友的共同利益与发展目标。2022 年5月23日,拜登访问日本时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斐济等14个国家成为初始成员,致力于在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反腐败四个关键领域加强成员国间的一体化。(58)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o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2022-06-05].但与此同时,为尽快推进印太经济框架进入实施阶段,美方决定暂不考虑将外界最关心但最敏感的对美市场准入和关税减让条款纳入框架范围,这一决定虽然令印太经济框架得以绕开国会的烦琐程序、避免了权力掣肘,但也令那些渴望通过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而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家希望落空。
尽管迄今为止“印太经济框架”仍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机制构想阶段、具体的实施政策举措依旧有限,但从美方公开的框架协议文本内容来看,仍可以较为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框架的提出具有“印太北约化”的集团政治倾向,及明显对冲中国区域经济影响、在多领域开展对华经济竞争的清晰政策逻辑。
第一,“印太经济框架”强调以多种方式加强同盟友的产业分工协作,并凸显出对华“高技术领域竞争”的色彩。美国提出要在芯片等重要产业领域推动供应链的重塑以增强其韧性,并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框架下专门设立了“芯片供应链倡议”, 就关键技术、材料和产品的供应链安全展开合作。(59)Elaine Dezenski and John C.Austin,“Rebuilding America’s Economy and Foreign Policy with ‘Ally-Shoring’,” https: // www.brookings.edu/ blog/the-avenue/2021/06/08/rebuilding-americas-economy-and-foreign-policy-with-ally-shoring/[2022-03-14].上述四国不仅在规划相关供应链安排,还意图借助《技术设计、开发、管理和使用原则》,打造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科技创新的指导原则。除与日韩等芯片强国进行多层面合作外,美国还与印度、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频繁互动,希望将其打造为美国供应链联盟的重要支点国家。同时,美国还希望通过与中国产业链脱钩,既全面打乱中国的产业链正常运作,又压缩其市场空间而减少其规模经济和市场竞争优势,降低中国产业的盈利能力与产业升级可能。(60)参见黄日涵、高恩泽:《“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133—154页。
第二,美国将聚焦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而与更多印太盟友进行协商,以便实现利益与产业发展相互捆绑而挤压中国数字经济的市场空间与竞争力。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问题,将东南亚视为中美竞争需大力拉拢的重要区域。2021年10月,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专门就数字发展问题发表声明,提出将在数字贸易、数字互联互通、数据治理等领域深化合作,并就低碳能源转型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展开协商。(61)The White House,“ASEAN-U.S.Leaders' Statement on Digital Development,” https:// www. Whitehouse. 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 27/ asean-u-s-leaders-statement-on-digital-development /[2022-04-21].
第三,美国在印太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更加注重整合盟友、私营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资源,以构建全面立体的对华打压阵营。“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众多国家的欢迎,也使中国同许多国家在公路、铁路与码头等方面的合作日益增加,影响力持续提升。为制衡“一带一路”,拜登政府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议,并将印太地区作为实施的重点。
对于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大多数域内国家来说,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升民众生活水平仍是当务之急,这一根本诉求在经历疫情冲击后变得更加迫切。基于此,为提升美国对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拜登政府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凸显其相较于“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美国在“印太经济框架”提出之初就为其确立了所谓“高标准”“重规则”“可持续”“强韧性”等属性标签,一方面以此影射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低质低效”,另一方面则标榜自身作为“传统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责任担当”。然而,美国在国际抗疫合作中不负责任的表现令其国际声誉大幅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在上述经济倡议提出后,部分印太国家对美国能否践行承诺也抱有疑虑。
受到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的持续影响,美国现阶段既不能加入或缔结新的多边自由贸易协议,亦无法向亚太地区投入足够的资金以支撑其经济议程的推进。其所谓的“高标准”和“重规则”,实际上并未基于对域内国家发展水平的考量,而是源于对西方发展经验的生搬硬套,与域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严重脱节。而其所谓的“可持续”和“强韧性”,则意在推动“去中国化”的区域产业链加速形成。作为域内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历经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已牢固确立起在区域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执意推动区域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不仅无法实现,还将对域内广大外向型经济国家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受此影响,在后疫情时期亟待通过加强多边合作方能实现的地区整体复苏进程,势将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三)“价值观化”对区域政治秩序的冲击
在不断渲染地缘博弈与硬实力对抗的同时,美国还意图通过“印太战略”强化以“美式价值观”推广为核心的软实力建设——这种强调“价值观导向”的政策手段,同美国对欧洲政策中重视“价值观同盟”的政策路径高度相似,进一步确证了“印太北约化”的政策取向。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印太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更加凸显“价值观导向”,试图将所谓的美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确立为衡量本地区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准绳”和“标杆”,将区域各领域政策议题进行“价值观化”包装,以所谓“推进地区自由民主、反对干涉和胁迫”为幌子,大肆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抹黑中国的对外政策,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交往。
2021年初,在中国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后,美国国务院当即宣布在前任政府通过的所谓《香港自治法案》下做出更新,提出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进一步扩大对华官员制裁名单,继续暂停给予香港特殊关税地位,指责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颁布实施的香港国安法及修订的香港选举制度是所谓对“香港人权和自由的侵犯”,并称美国政府将同盟友及伙伴国加强协调,共同追究“中国政府破坏民主制度的责任”。(62)US Department of State, “Press Statement by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J. Blinken: Hong Kong Autonomy Act Update,” March 17, 2021, https://www.state.gov/hong-kong-autonomy-act-update/[2022-04-01].同年4月8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推出一项长达281页、名为《2021年战略竞争法》的法案。法案呼吁政府加强对“普遍价值”推广的投入,授权一系列“人权和公民社会”措施,在对华政策中加大对香港、新疆等地区事务的“介入程度”,加强同台湾当局所谓“伙伴关系”等。(63)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Chairman Menendez Announces Bipartisan Comprehensive China Legislation,” April 8, 2021,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chair/release/chairman-menendez-announces-bipartisan-comprehensive-china-legislation[2022-04-09].
在持续炒作“香港问题”的同时,美国还伙同加拿大、英国和部分欧盟国家就涉疆问题展开对华“人权危机”的话语攻势:2021年3月22日,欧盟27国、英国和加拿大分别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宣布对有关个人及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同日,美、英、加三国外长发布联合声明,表达“对中国新疆人权问题持续的深切关注”。(64)US Department of State, “Media Note of the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oint Statement on Xinjiang,” March 22, 2021,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n-xinjiang/[2022-04-01].针对美国及西方部分国家假借“人权”之名在国际舆论场中持续推动的对华打压态势,中国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强烈谴责、有力驳斥和坚决反击。(65)“Interview: BCI’s Boycott against Xinjiang Cotton Groundless, Politically Motivated, Says Pakistani Expert,” News from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Daily Bulletin, April 2, 2021.
在对华采取直接“价值观攻势”之外,拜登政府还持续加大对本地区的外交资源投入,不仅频繁与印太盟友、伙伴举行首脑双边或小多边线上线下会议商讨区域议题,其内阁高官也对本地区国家展开高频次访问,不遗余力对域内国家展开价值观输出。在此背景下,中美价值观差异被美方无端夸大为“关乎本地区未来秩序”的“民主与专治之争”。客观而言,受到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多样性等因素的长期影响,价值理念差异在亚太国家间关系的演进中始终存在。但正是由于有关各方始终坚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根本原则,在充分尊重各国价值理念与核心关切的基础上开展务实合作,亚太地区才得以在冷战后迅速摆脱“价值观外交”的桎梏,逐步形成总体稳定的区域交往生态。而历史经验也已充分证明,域外大国无视地区各国发展水平与现实利益诉求,以意识形态划界强行推动地区秩序改造,其结果只能是造成地区分裂态势加剧,动摇区域稳定基础。
五、结 语
2022年初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持续至今。在密切关注俄乌冲突和美俄间战略博弈动向的同时,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战略界和对外政策领域的专家对亚太地区总体局势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也普遍关切,部分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类比于冷战后美国及北约国家对俄政策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国际关系界更应担忧的是美国持续推行的“印太战略”或将造成“印太北约化”趋向加剧,而在此背景下的中美关系是否也将重蹈美俄关系的覆辙?(66)Thomas Wilkins and Jiye Kim, “Adoption, Accomodation or Opposition?Regional Powers Respond to American-led Indo-Pacific Strategy,” Pacific Review, 2022, Vol.35, No.3, pp.415-445.在此背景下,“印太北约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国际关系学界理解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进路径和影响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相较于域内其他国家,中美两国在区域交往互动中的角色至为关键:作为同样具备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两国不仅需要承担相应的区域公共责任,更应妥善地管控分歧,避免双边政策互动的外溢效应对区域整体秩序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这也符合域内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意愿。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发展进程中的身份经历了从参与者到贡献者的转变;相应地,亚太国家也普遍基于这一事实主动调整对华认知与交往模式,并逐步改变在发展对华关系中对自我和双边利益的界定。
在此期间,美国对华认知的转变导致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中国崛起”被美国视为“地缘层面的重大威胁”,两国在本地区展开的战略博弈持续深化,成为影响区域秩序走向的核心动因。应当看到,尽管地区国家对中美战略博弈的看法及其对自身可能带来的影响的评估呈现出明显差异,但多数国家在对中美关系应维持结构性稳定这一问题上总体保持了高度一致,认为任何相关方单方面采取具有明显指涉性的进攻或挑衅行动,都将引发不必要的战略对峙、造成有限区域公共资源的内耗,因此应致力于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确保区域发展始终成为本地区的最优先议程,尽力避免“两强相争”的持续升级直至最终爆发全面冲突。(67)参见赵菩、李巍:《霸权护持:美国“印太”战略的升级》,《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4期,第24—46页。
尽管美方不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和中国作为“区域现行秩序破坏者”的形象,以为“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及放任“印太北约化”趋势的发展提供所谓道义和法理依据,极力拉拢域内国家广泛参与美国主导的区域行动议程,但多数国家对此仍作出了相对审慎甚至略显保守的政策取向——当“印太战略”带来的现实压力正不断压缩着自身本已有限的对外战略选择空间时,“实力和地位有限的理性国家更倾向于选择保存实力而非孤注一掷……但区域秩序的演化不会就此停止,而将在更加封闭和脆弱的环境中走向分裂”。(68)Jung Sung Chul, Lee Jaehyon and Lee Ji-Yong, “The Indo-Paicific Strategy and US Alliance Network Expandability: Asian Middle Powers’ Positions on Sino-U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1, Vol.30, No.127, pp.53-68.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D.Swaine)在其所著《制造不稳定的亚洲:美国“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一文中指出的:“美国为其印太战略冠以‘自由与开放’的标签,其实践效果却与其政策目标背道而驰……印太战略带来的最直接效果不是为地区架构提供积极的制度增量,而是系统性地削弱了本地区既有的战略稳定态势,并很有可能因此触发中国强硬的政策反应,令其他亚洲国家对区域秩序的未来更加警觉而悲观,其结果只能是令地区长期陷入一种高强度紧张的零和博弈,让绝大多数国家被迫卷入美国执意挑起的、毫无意义的对华‘新冷战’中。”(69)Michael D. Swaine,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the U.S.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 2, 2018.
随着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公共生活各领域影响的日渐常态化,作为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增长引擎,亚太地区在后疫情时代被赋予了带领世界尽快开启复苏进程的重要使命,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广大域内国家坚持以地区发展大局为重、摒弃既有成见与争议,全方位、多领域地参与区域治理与合作。在国际局势和区域发展环境持续复杂变动的当下,究竟谁才是“秩序的维护者”,谁又是“秩序的破坏者”?包容开放抑或封闭排他、团结协作抑或集团政治、零和博弈抑或互利共赢,究竟哪种秩序、哪种模式、哪种道路才更符合本地区的共同利益,才能为区域繁荣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相信广大亚太国家都将在参与区域治理的切身经历中得到答案,而历史也终将给予其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