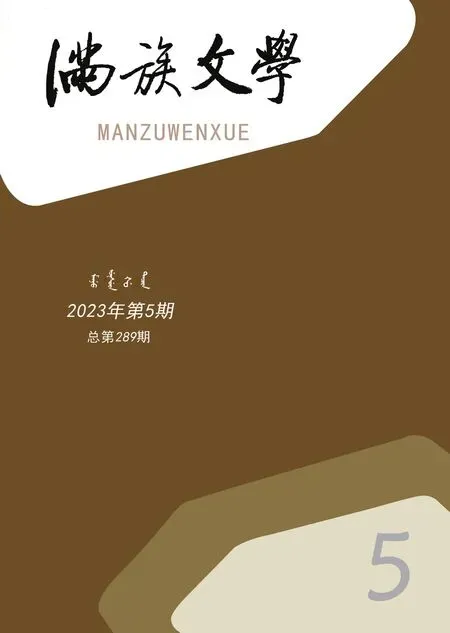离 歌
2023-02-01提云积
提云积
太阳出来了。
潜意识里头脑对光明的感知阻断了我四处溃败的逃亡,梦中没有任何方向,也没有方向感可言。不管面对哪个角度,都是错误的,都不是自己内心想要选定的方向。茫然、忐忑,或许是恐慌更能说明当时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起初是一片陌生的区域,如何进入的已经无关紧要。看不出这个区域有什么特异之处,场景昏暗,是否有雾笼罩也未知,它的昏暗不是太阳落山带来的那种黑,也不是阴天有雨的暗,它的存在给予我无法深究的隐喻。有白色的烟雾从更深的场景里飘摇出来,一束幽暗的光把烟雾牵扯成丝片状,有一些声音就像是雪花落下的那种碎响,从烟雾里挣脱出来,可以渗入到人的魂灵里。
我茫然继续向前走过,目之所及的石人石马对列静立,石人谦恭,双手相交于胸前作揖,面部丰满,嘴唇微翘,似一抹神秘的笑,但有一刻感觉不是,他的异处在眼角,我们常人微笑,嘴唇微翘定会牵动眼角的皱缩,石人只是单纯的翘唇,他谦恭的表情更像是一种偷窥姿态,记不清是不是有长袖宽袍,印象里石人臃肿,只有腰部略躬,与对面的石人打躬作揖。而石马平视,感觉它的目光能掠过对面石马,看向无知的尽处。我也下意识地顺着石马的视线向远处张望,除了昏暗,还是昏暗。
异常给我带来的感觉不仅仅是忐忑,毕竟此处是陌生的区域,清醒的认知还在,有一刻想到这是一处墓地,告诉自己应该赶快离开这个区域。心念刚动,面前的场景急剧变化,昏暗依旧。石人石马还在,但已残缺不全,身首异处,躯体碎落,石人的头颅像是被谁刻意安置地上,保持着端正的姿态,从微翕的眼睛里射出虚无空洞的眼光,好像定定看着在他面前表现犹疑、无所适从的我,嘴角残存的微笑竟显现出丝丝诡异,睡梦中我感到了呼吸急促,还没有来得及从忐忑状态上升到恐惧,荒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出现,它们在瞬间淹没了我面前的一切,代之的是一片光明在我面前漫漶开来。
太阳光来得正是时候。周日的慵懒让我的灵魂出离,好在还有光明在。窗外太阳已经近十点的样子,光线穿越塑钢窗户,从窗纱的缝隙里挤进来,落在我的脸上,刺得双眼紧皱着,应该是在眉心拧起了一个疙瘩。
我不能明确这个梦境会给我怎样的暗示。那片区域多次出现在梦里,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色调,同样的试图逃离的想法。它频频在梦里出现,是我对它怀有眷恋的想法,还是沉溺在它虚构的情节里?我总不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从睡梦中成功脱逃,不知道是庆幸还是一种失落,总之,我在床上怔忪半晌。昨夜瞌睡汹涌来袭时,随手翻看的枕边书《唐诗三百首鉴赏辞典》也没有顾得合上,随手放在了一边。脑子里还是陶公的那句“田园将芜胡不归”。
太阳光不断地晃动着窗纱,我以为是风的小动作,但是,并没有风。处暑刚过几日,溽暑已失,窗外阳光明亮,干松舒朗的空气在阳光底下自由地奔跑,这天地之间是它的祖居地,我们人类客居于此,却俨然一副主人的颜面。
我居住的地方是老城区,起初是这座小城的外围,早年的称呼是北关,此地的原居民说起北关,无一不是向往的神情。北关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还存在的城墙,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拆除干净。现在的北关高楼耸立,现代的街衢分割了新潮与繁华,俨然是中心城区的模样。历史上做为一座以“州府”命名的地域所在,其辉煌的历史行走记录,也只是凭由书籍可考,在现实中无从找寻其丁点儿的原始样貌。
抱着被褥下到底楼,出单元门便是一片空地,起初开发商预留了这方空地是用来做居民活动健身的场所,物业在靠北侧挨着相邻平房的位置竖立了一排晾晒被褥的杆子,方便居民们晾晒衣物被褥。物业的保洁大姐在小区大门外南侧的空地边上摆了一个蔬菜摊。蔬菜摊子不大,花色品种却多,蔬菜都是她男人从乡下一早送到市区的,摊子上还有一把葱,几个青萝卜还带着墨绿的缨子,都是在大田用农家肥喂养出来的,比一般的蔬菜看着圆实,应该是给小区哪家居民留的。保洁大姐的蔬菜是抢手货,有一些是需要提前和她打招呼给预留着,没有的品种由她男人在乡下给帮忙搜罗着。
保洁大姐来此工作时间不久,对小区的居民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完全是一副乡下主妇饭后扎堆聊天的习惯。平时见过几面,都匆匆而过,仅有的几句招呼也只是停留在吃了吗?下班了?今天看到我拿了被褥出来,好像给她提供了一个互相增进了解的机会,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
“啧啧,太阳还真是出来了,大男人晒被褥。啧啧!”
“呵呵,周日没事,找点事情做做,闲着也是闲着。”我生性不会和女人拉呱,勉强和保洁大姐打着哈哈,“菜卖得挺快。”
保洁大姐并不理会我的尴尬,也不顺着我的话题走,只顾按照她的思路,在男人晒被褥的话题上打转。
“在乡下没有男人能帮老婆晒被褥的。”大姐做了一个结论,在乡下,诸如晒被褥此类的家务活只能由女人来做。女人负责家务,主内,男人负责种田、赚钱养家,主外。
“您进城几年了?”大姐像是又想起来什么,没等我回答,继而又问:“在城里住着习惯?”
习惯?我在心里接着大姐的问题询问自己。习惯吗?我的心里是忐忑的。进城居住已经快十年了,我曾经在黑夜睡不着的时候这样反反复复地问过自己,总不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如果是已经习惯市区生活,为什么乡下的生活场景会一次一次地回到自己的梦里。梦境是清晰的,做这样的梦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要回一趟乡下了,只有回一趟乡下,才感觉梦里那些记忆引起我内心的骚动和不适才能得到安稳。
我并没有回答大姐的疑问,自顾把被褥扔到晾晒杆上,扯匀称了。大姐好像非要从我这里问出一些她感兴趣的东西。她并没有注意到,她的问题已经敲痛我的思维神经了。
大姐颇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又问:
“听口音,像是城南片。”
“不是,是城西片的。”
“反正听着不像是城里人的口音,他们这里人的口音都轻,你的音重。”
“嗯,靠着海,咸风吹的。”
“老家没种地?”
“种的,不多。”
“看看你的身板也不像是种地的。你们这些男人早已经被农村淘汰了。”
我不置可否。确切地说,是有一点心惊了。大姐说我是被农村淘汰的男人。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能从农村脱离是一个农人的后生成功与否的标志,可以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像我的父辈、祖辈一样在泥土里刨食。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是一个年代的尾巴,转过年就是七零后。我成长的太多印记都镌刻着七十年代的痕迹,思想、日常行为,等等。我一直对自己的六零后的称谓心怀芥蒂。这样的话题好似有点远了,可终究没有无用的话题。
少时在生产队也参加过农业生产,一般的活路也会一些,及至工作,进城居住就渐渐脱离了乡村。家里的几亩地只是按人均分配的口粮地,我的户口早已经由粮农变为城镇户口。保洁大姐的男人见过几回,像宽厚的土地一样的一个人。朴实、憨厚、大手大脚的一个庄稼汉。大姐的年纪也仅仅是比我大两岁,与她男人同龄,我们都居于六十年代的尾巴。
他们离家来城里工作生活,辨别一个人来自哪里都以口音来做一个区分。城南、城东、城西、城北、老城区。对于口音区分一个人的来历,我已经变得麻木。然而有记忆以来,对于说话发音还是保持着警惕心。时刻警醒自己,环境的改变,生活习惯可以有所入乡随俗,但口音不能改变。它是我的一件隐形外衣,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时时提醒我,这是我独有的,区别于他人的印记,终老都不能改变。
旧年邻居有三个小子,三小子比我大一岁,在一个学校上学,比我高一年级。学校是村小,五个年级,都是一个村子的孩子。我们在一个胡同住着,我家居西,邻西面的大街,他家居东,我们两家共用一堵院墙,一堵山墙。学校在村庄的东南方向,与村庄隔着一公里左右的路程。每日上学都相互招呼一声,或者向西走西面的大街向南,或者是向东,再穿过两条南北胡同,到东面的大街向南。大多时候是向东走。
一日下午放学回家,照例还是结伴一起走。他班级的同学却一直跟随着我们,不断地发着奇怪“wo,wo”声,随之便是哄堂大笑。我不明所以,起初以为只是他们在模仿大人吆喝牲口,以为还是平日大家的嬉笑,没有其他的意思。闹过、玩过之后一切都会归于平常。
第二日,情况照旧。他班级的同学甚至告诉我说,不让我和他一起走,说他不好好说话,他班级把他“晒干(孤立)”起来了。一路无话,快到家的时候,他才红着脸和我说,他们上语文课,老师让他起来读课文,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竟然忘记了用我们本地的口音,第一句话的“我”,他用了生字表上的注音,读了三声。原来这就是昨天“wo,wo”的来历。然而更糟糕的是,他班的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三根毛。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加之看了电影《三毛流浪记》,读音是始作俑者。可怜见,这个绰号竟然要伴其一生了。
进城居住后,第一件麻烦事,我不曾想到会是理发问题。进城之前预想过许许多多的不适,单单把这头上的第一项大事给忽略了。日常生活,关上门,别人看不到,大可以随自己以前的生活方式,无人加以干涉。当然,这头顶之事他人也无有评论。只是自己内心感到了不适。是四十余年的生活习惯,安稳、不惊、不变造成的。第一次在城里理发,找了许多的门店,都悬挂了灯箱广告的门头,各种现代的洗染理发技术纷繁多彩。理发师多年轻,妆扮新潮,男理发师的头型各种样式,染了各色,像一只花公鸡的屁股,色杂,泛光。门前音箱重金属的音乐聒噪不已,未到门前,心里便有了怯意,只能硬着头皮往里闯。态度还好,说了发型,大多不懂,费了许多的口舌,最终却不是自己想要的发型。俗语说“剃头三日丑看”,我准备了几套说辞应付别人的讨问,感觉这是我的过错,与理发师没有丝毫的牵连。以后再理发多刻意回转乡下看望父母时一并了结。
老家的理发屋还是保持着乡土的习惯。一面红幌,书墨色“理发”二字,细竹竿挑了悬挂在门前。迎风招摇几分,也是在我面前的得意之色。理发屋就在进村南门处,居路东,单独一处所在。理发师傅我称为“老老”(爷爷辈,与本家族区分开来),比我大两轮的年纪。进门,说话的口气多了几分客气,不再是在老家居住时的随意。我感到了老老的矜持。屋里没有他人,只有我俩在。待坐到转椅上,围上围巾,老老的话匣子开启。
“进城住着习惯?”
“还好。”
“进城别变修了。”变修是指一个人背离原有大家共同认可的行为方式。这基于在一个村落与大家长久的生活习惯。
“呵呵,哪会?也不敢!”
“这就对了。别像咱村的某某一样。”
某某是我村第一个出远门的人。离家多年后,第一次回乡探亲,年轻人善变,其父见到他的第一眼,儿子的外表变了,衣饰发型与去家之时相去甚远。说话的口音变了,不再是张嘴一口的苞米茬子味,而是我们这里称呼外地人说话口音的“着儿话”(类似于普通话,却又与普通话不同)。出远门前在老家称呼父亲为:爹。现在称呼为爸。左邻右舍的眼神复杂,其父讪讪地照应着。第二日天未亮,其父叫醒他,一起下地做农活。待到自家地头,荞麦已经开花。某某照例还是一口“着儿话”,“爸,青枝绿叶开白花的是啥呀?”其父不做回声,连续的“膈”勾起了怒火,拿起随身携带的小锄,不顾头脸地打了过去。某某受痛吃惊,忘记了“着儿话”怎么呼救,苞米茬子口音吆喝起来,“救命啊!荞麦地里打死人了。”故事的真实性不做辩解,毕竟没有亲见,但关于他的故事,多次听老人们说起过。今天老老又给我讲起,我明白他的想法。
我的堂姐嫁到十余公里地以外的一个村庄,那方区域的口音与南边的青岛地区相差无几,唇齿音居多,不似我们这里的口音清脆。不到一年的时间,堂姐的口音也随着她的婚姻离家甚远了。奶奶说,吃人家的饭,哈(与喝同意)人家的水,说话的调调也是人家的了。现在堂姐已经近七十岁的年纪,春节回娘家过来看望我父,说话口音竟然又发生了改变。我能听得出来,询问她,她就笑,整天哄孙子,学着电视里撇普通话,时间久了怎么就变了。你怎么也能听得出来?
改变的何止是堂姐。每次回乡下老家看望父亲,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都在侍弄第三代,都撇着蹩脚的普通话教着孙子孙女。一个乡村缓慢生长了几百年,甚或是上千年,做为乡土的印记,口音被人为地同化,生生地从乡村的躯体上剥离。在乡间曾围观过屠宰牲畜,屠夫一手攥紧牲畜尚带有毛发的表皮,应该还带有牲畜在这个世界的些许体温,一手执一把尖刀。一刀,一刀,利刃在表皮与血肉之间跳动飞舞,表皮脱离,露出鲜红的肉质,有血水滴沥。今天在想到剥离的时候,这个场景瞬间从记忆深处翻检出来。我们都做了自己的屠夫,把自己从故乡的血肉上,如屠夫一般,一刀,一刀,彻底地剥离开来。因为是自己心甘情愿,我不能想象我们会带着怎样的表情看着自己的身体从故乡的母体上剥离开来,会不会也如早年的屠宰场景一样,露出鲜红的肉质,也有血水滴沥。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它的诱惑力是一剂麻药,起初感觉不到疼痛,等到失却了药效的时候,会痛彻心扉,那种痛是深入骨髓的痛。
村子的后生们纷纷从故乡出走,到我所在的小城定居,有的走得更远,在一些以前只是听说的大城市定居,现在这些大城市因为有他们在,开始变得具体,不再是脑袋里的一个地域符号,也会偶尔的有关于他们在这些大城市的见闻陆续回到故乡人的口口传说里。
我们在小城居住的曾有过一次聚会。由比我年长几岁的同村二哥负责召集,那日晚间偌大的包厢有二十余人到场,有三名女性,已嫁他人妇。年纪大的刚年满六十退休,小的二十岁出头。席间交流,知道至少还有三十余人没有到场。每个人的背后,在故乡就是一个大家庭血脉。能明确的是这些家庭断无再还乡的可能。年纪小的口音已经与故乡发生了错位,在每个人敬酒说一段祝酒词的时候,年轻后生的普通话音色纯正,稍大一点的,三十多岁的口音稍差一点儿,但也已经不是故乡的味道。还好,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尚无明显变化。
由此竟想到,当年嘲笑某某的故事,也是为了维护根土文化的方式,那年孩童们孤立旧年邻居三小子的行为,却是一种对根土文化的保护方式,也是传承维系故土根脉遗传的手段。
然后想到那个多次出现的梦境。石人嘴角的似笑非笑,是不是对我们这些背离故乡人的嘲笑?我们做了故乡的掘墓人,因为我们的决绝离去,故乡的气息益发凋敝。等到老一辈人渐次离去,谁还能给我们看护在祖居地落草时的血脉?梦境中石马眺望的方向,会不会是故乡未知的旅途,它们在歧路口徘徊,无从踏足,也是我们无从选择的旅途。
有一年去一座城市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期间组织者将当地的一项工程项目作为亮点向我们推介。两辆商务面包车载着我们一行数十人在各个社区走访,这些社区多由周边相邻的三个村甚至是四个村庄组成。在一个社区,我突生想法,能否去以前的农家,实地观瞻他们曾经的居住与生活状态。社区的院子里摆放着几块制作精良的彩色刊板,将以前的村庄和现在的楼房做了对比,那些在照片里保持沉默的民居,或高或矮,或阔或窄,都给我传达了一种历史与时光形成的厚重感。作为民居必不可少的门楼,或大或小,或庄重或闲适,它们的朝向不一,保持了这家主人对风水,以及一些传统习俗的认知。照片仅是外观,没有内部的情形。问过社区陪同我们的一位负责人,知道这样的农家已经无存,工程项目的主要任务是让每一个农民家庭都住上楼房,早年的那个村庄已经全部开垦成农田,种植了桃树和庄稼。
在我们坐车离开这个社区,绕上社区东面的公路,前往下一个社区时,随行的接待人员指着车窗外大片的农田告诉我们,这就是以前的村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葱茏的夏日,还有旺长的树木与庄稼。有一堵房屋的残垣尚立于一处果园的外侧,它无声地告诉我们,这里曾有过村庄应该有过的人迹炊烟,鸡鸣犬吠。车辆远行,这一切都从我们的视线里次第消失。现在,它们已经是历史进程上的一个节点,今后会不会一直出现在后人叙述的故事里,是一个无从破解的谜底。。
我们本地有句俗语:五里不同天,十里不同俗。每个村庄传承的习俗不完全一样,现在这样的聚居方式割裂了每个乡村传承了千百年的文化习俗,势必会造成民俗的断代。这不是一个村庄在物质上的消失,而是代表了一个地域特殊传统文化的同化与灭失。
人世间总有一处地域的春天来得比其他地方晚一些。丙申年的春天,严寒辗转离去,春风偶带雨讯,北方的大地开始布满春意。节气顺序有秩,惊蛰几日,春分正在赶往世间的路上,可以听见清明檐角的风铃隐隐作响,万物的萌发已经进入蓬勃期。
这处地域收留了在人世间奔波劳顿的人,他们入此地是后人三拜九叩之后选定的,他们后人的后人也会将他们的后人送至此处,绵延无绝衰。人世间的相遇,此世间的相伴,皆源于血脉相承。
现在,春日萌发的气息好像也不忍心吵醒他们的酣眠,总是晚一些,再晚一些,等到清明时节,后人,及后人的后人来此告知春天已至,可以舒展他们一个冬季蜷曲的筋骨,借助春风的吹拂,到人世间走走看看。此刻,我们共同面对的是一片墓地,这里长眠的是我们本姓本族的先人。最近的一次造访,还是在上年的阴历十月初一为过世的先人送寒衣时来过。一个冬季的严寒侵袭,去年的荒草更加凌乱枯败,坟墓都掩藏在枯草里。
每次回老家,家父总是让我用轮椅推着他到此地转转。其时家父因脑血栓卧床近两年。他总是迫不及待,一个冬季的憋闷于他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他曾经说过,在他逝去后要与他的爷爷奶奶爹娘挨得近一点。在母亲过世时,他亲自来选的墓址,在他祖父墓址的前面。他说,在这一世是一家人,到了那一世还是一家人。他想将这一世的亲情延续到那一世。那一世于他有所期待,并为之自喜。
还不到清明节,我知道墓地应该荒败凄凉,这样的地域本身就带有某种悲意。我总是不允,我害怕家父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更加影响他的情绪不利于病情。但这一次他动了火气,彻底拗不过,只好听从。出乎我的意料,父亲并没有表现出大的悲喜,我看到他在轮椅上努力向上挺了挺身子,深吸了一口气,因血栓造成的脖子歪斜好像也端正了许多。
坟丘分布毫无章法可循,之间根本没有路径,它们勾连相接,挤挤撞撞。我们站在公墓的南侧不再前行,父亲长时间地盯着墓地,我感觉到他的目光在墓地的上方挨个扫过去,最终落在母亲的坟墓所在,那里是他的最终归宿,是他在那一世的家。在我以后,会不会跟进,现在还无法知晓。
清明节再来墓地,已是春天的模样。在这一世的后人来来往往,为先人修葺墓址,这一天,这个世界苏醒过来。就在这个秋天,近秋分,家父离去,其时大地的晨光蒙照了一层厚厚的白露。我与这个世界的纠葛变得空白。是一种整个世界塌陷的空,是无所描摹的白。再回老家已是故乡,这个世界给我撑起一个家的人悉数离去。
多年前听罗大佑的《鹿港小镇》,那时年少,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喜欢,不曾深想歌者给予的深刻含义,更无从将歌词与现实对接的想法。再听此歌,鬓毛已衰。那日偶然于酒楼邂逅,杯酒之后,竟守着一众人潸然泪下。中年人的心里有了些许沧桑,外表安稳的假象下,是汹涌的浪在滔滔而歌。
父母离去后,再回故乡,他们那一代人老弱不堪,所剩无多,每一次回去,几乎都会有老人远离。他们出入的那些门扉,唯有铁锁把持,风雨印痕,锈迹斑斑。在每一个夜晚,无不入梦。黑白的木板,纹理已经沟壑难掩。是岁月的脸,还是故乡的脸?他们是代表了故乡的人,已经把故乡带走。当他们一一从我生命历程中消失的时候,我才发觉,有他们在,便是故乡。我把他们的离去看作是我们这代人与故乡的远离。他们生命中的所有故事与传奇,都构建了故乡的魂魄。他们的离去,把属于故乡的魂魄一一捡拾干净,决绝而去。唯此,我们这一代人,想努力握住岁月给我们最后的时光,在内心唱着怀念的歌谣,然后,频频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