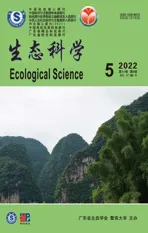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研究进展
2023-01-26王鹤琪范高华黄迎新周道玮
王鹤琪, 范高华, 黄迎新, 周道玮
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研究进展
王鹤琪1,2, 范高华3, 黄迎新1,*, 周道玮1
1.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吉林省草地畜牧重点实验室, 长春 130102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100093
中国的北方草地资源十分丰富, 研究影响草地生产力变化的因素对于合理利用草地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系统综述了环境因素、生物因素以及人为管理因素等对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变化的影响。通过对近年来北方草地生产力变化的分析表明, 环境因素是影响草地生产力变化的主要因素, 生物因素亦会对草地生产力造成影响。放牧、刈割、施肥、草原开垦等人为因素会对草地生产力产生巨大的影响, 并且通过有计划火烧、灌溉、围栏封育及混播等措施能潜在的提高草地生产力。
中国北方草地; 生物量; 增温; 围栏封育; 火烧
0 前言
人类从最初的逐水草而居发展到现代的草地农业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草地生态系统是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重要生态系统之一, 它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更新与维持土壤肥力、促进营养物质循环、固定二氧化碳及释放氧气等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 能为人类生存提供大量的植物性和动物性原材料。据统计, 中国北方草地面积达238万平方公里, 占世界草地总面积的9.92%[2]。且第一次草地普查结果(1996年)表明我国天然草地面积居于世界第2位[3]。目前, 国际上以单位面积产草量、单位面积畜产品产量和载畜量等3个指标作为衡量草地生产力的标准, 而草地净第一性生产力(NPP)作为直接反应草地群落在自然条件下的生产能力是草地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4]。我国北方草地面积广袤, 自然资源丰富, 但自然灾害在某些地区时有发生以及人类活动(如: 开垦、放牧)等的干扰均造成该区草地退化, 草地生产力下降, 阻碍了区域的经济发展[5]。因此本文系统地论述了对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生物因素以及人为管理因素, 并提出提高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的相关措施, 对标草地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草地资源利用上线等3条红线, 加快形成北方草地生产的绿色发展模式, 以期为中国北方草地的生产力恢复和现阶段草地农牧业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1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是影响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变化的主要因素, 其包括气候和土壤因素。
1.1 气候因素
中国北方草地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 且大部分地区降水分布不均匀。气候因素是影响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变化的主要因素。气温与降水往往耦合在一起对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造成影响。
1.1.1 降水的影响
降水对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很大。传统的研究主要关注全年降水量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 近年来, 人们逐渐认识到, 不同时间的降水量对植被生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降水格局发生着显著变化, 进而导致草地生产力显著变化。关于降雨量对草地生产力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年降雨量的影响。例如: 韩芳等[6]根据内蒙古荒漠草1961—2007年年降水量的数据, 分析了不同气候背景下内蒙古荒漠草原的牧草生产力, 结果发现, 年降水量与牧草生产力具有极显著的相关性。多数研究运用模型模拟分析了中国北方草地典型区域的降水与草地生产力的关系, 研究表明降水量的升高能显著提高草地生产力。例如: 杨泽龙等[7]运用模型模拟分析了内蒙古东部地区48个气象站45年的气象数据, 发现在大兴安岭中部地区, 气温与降水有不断增加的潜势, 草地生产力增长趋势明显; 而在大兴安岭南麓与西侧的草地区域, 气候呈暖干化趋势, 草地生产力增长趋势不明显。亦有研究发现松嫩西部草原的净初级生产力随着降水量增加而增加[8]。通过模型模拟的方式不仅可以对近几十年降水对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变化进行分析[9], 还可以进行预测评估[10-11]。例如: 杨凯等[11]通过模型模拟评估未来2071—2100年藏北地区草地生产力的变化, 发现降水量减少的区域中高嵩草型草地地上生物量呈减少的趋势。
在非生长季的降水, 只有部分能够储存在土壤中供植物生长季需要, 并且即使在生长季, 植物在生长的不同阶段对水分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因此, 不同时间的降水对草地生产力影响的差异是显著的。Bai等[12]通过对内蒙古的草地生产力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 1—7月的降雨量是草地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李霞等[13]分析了中国北方温带草原降水年际季节变化, 发现夏季降水量对植被的生长影响最为显著。通过对典型草原生态系统增雨的研究, 发现7— 8月份30%增加降雨会促进草地生产力[14]。
植物在生长的不同阶段对水分的敏感度不同, 相同的降雨量, 随着降水格局的变化对草地生产力产生显著影响[15-16]。Knapp[15]提出Soil water bucket 模型, 该模型对不同的降雨格局的影响进行了总结, 发现在干旱半干旱草地生态系统中, 通过增加降雨强度, 减少降水频率有利于维持土壤含水量, 减少干旱胁迫对植物造成的伤害, 利于草地生产力的提高。张统[16][通过研究前半个生长季(4—6月)和后半个生长季(7—9月)各60%增加和减少平均降雨量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发现, 前期减雨处理降低总生态系统生产力12%, 在后期减雨处理中总生态系统生产力降低32%。增雨对净初级生产力的促进程度大于减雨对净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抑制程度。
茹靖益[17]通过人工控制的方法改变生长季降水分配, 将6月份降水与7月份降水互换以及8月份的降水与9月份降水互换, 分别模拟提前和推迟生长季降雨峰值, 来研究降雨季节分配对半干旱草地总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影响。通过连续四个生长季(2013—2016年)的实验观测发现, 提前降雨峰值对总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影响不显著。在内蒙古草地, 通过模型模拟表明, 重新分配其他季节的降雨到春季及增加较大降雨事件的频度均增加了净生态系统生产, 而重新分配其他季节的降雨到秋季则降低了净生态系统生产力[18]。
1.1.2 气温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温室效应加剧, 使得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这对于中国北方草地植物的生长也造成了影响。有研究表明, 增温能够显著提高草地生产力[19-20]。史瑞琴[19]利用植被气候分类模型和草地气候生产力模型分析得到随着CO2含量升高, 绝大部分草地生产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有些学者提出了气温升高导致生产力下降的观点[21-22]。李镇清等[21]发现, 随着冬季气温的升高, 使得典型草原区春季干旱加剧, 导致草地生产力减少。气温升高有助于一些害虫安全越冬, 这可能对植被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 亦可能造成草地生产力的降低。赵东升[22]等利用模型预测未来几十年NPP总量呈波动下降的趋势, 且下降速度逐步加快。一年当中不同时期的增温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是不同的[23]: 夏季降雨量较高, 增温能够增加植被的光合作用, 从而提高草地生产力; 而冬春季节增温, 会导致土壤水分降低, 加剧干旱, 害虫安全越冬进而导致草地生产力降低。
在全球变化的背景之下, 近年来我国气温不仅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且呈现出不对称增温的特点。不对称增温结果会导致昼夜温差降低, 进而对中国北方草地植被的生长造成影响[24], 不对称增温导致植物发生补偿生长, 从而增加草地生产力。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是国际上公认的能够反映植被变化的参数, 可用来指示北方草地生产力的变化[25], 神祥金等[24-25]利用1982—2006这25年的NDVI以及气象数据分析发现, 这一时期中国草原区植被覆盖度大体呈上升趋势, 但是不同的地区存在季节差异, 春季最低气温的升高是限制植被生产的主要因素; 夏季升温不利于温带荒漠草原植被的生长, 且夏季增温对植被生长产生不对称影响, 即夏季最高温升高抑制植被生长, 夏季最低温升高促进植被生长。
CO2、CH4及N2O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是造成全球变暖加剧的诱因, 对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造成间接影响。研究表明CO2对草地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林舜华等[[26]于1996年研究了两种不同繁殖方式羊草()的生物量对CO2倍增的响应发现, 在CO2倍增条件下, 两种羊草()的株高、地上以及地下生物量明显增加。这与国外关于CO2对草地群落生物量起到促进作用的研究结果相类似[27]。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释放关乎着草地植物生物量的变化。也有研究发现温度会造成草地CO2日排放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草地生产力。董自红等[28]通过对新疆高山草甸草原植物群落夏季CO2排放日变化分析发现, 随着气温以及土壤温度的升高, CO2的排放通量也随之增加; 随着气温以及地温的降低, CO2的排放通量也随之降低。温度升高导致土壤呼吸速率加快, 进而导致大气CO2排放通量增加, 短期来看, 由于大气中CO2含量上升, 增强了植物光合所需固定的CO2浓度, 增强了植物光合作用, 导致草地生产力上升;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由于温度升高会导致土壤中有机质大量分解, 降低土壤呼吸对温度的敏感性, 同时加快土壤氮矿化速率, 因此土壤养分被大量消耗, 抑制草地植被的生长[29]。
1.2 土壤因素
良好的土壤会为草地植物的生长带来益处。而近年来由于气候以及人为活动的影响, 土壤侵蚀以及盐渍化现象不断发生, 使得中国北方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地退化存在以下弊端: 一方面可食性牧草的产量和质量会下降, 另一方面土壤养分含量亦会下降[30]。同时土壤的物理性质以及化学性质均会对草地植物的生长造成影响, 限制草地生产力的提高。例如: 由于不同的土壤质地固定养分与水分的能力存在差异, 在青藏高原草地上, 土壤黏粒含量会显著影响草地净初级生产力[31]。土壤pH亦会影响草地生产力的变化, 相关研究表明, 由于表层土壤退化造成松嫩平原盐渍化现象加剧, 盐渍化草地生长的羊草生物量要显著低于未退化的羊草草地[32]。由此可见, 土壤退化极大限制了草地生产力的提升, 中国北方草地面积广袤, 不同区域的草地土壤的质地, 土壤的含水量, 土壤养分含量, 土壤pH不尽相同, 同样土壤退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 因此各个地方的草原管理部门需要制定合理的措施来防止草地土壤的退化, 减少人为因素对草地的干扰, 如在重度退化的草地上, 禁止放牧和开垦; 在中度退化草地, 可以采取人工补播优质豆科牧草的方式, 增加土壤的固氮能力; 对于轻度退化的草地, 不宜过度放牧, 杜绝人为将草地开垦为农田的现象发生。
2 生物因素
各种各样的草地植物、草原动物以及草地微生物构成了草原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其中存在复杂的种间关系及种内关系[33]。而生物多样性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一直以来是生态学家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 主要分为两个学派: 一方观点认为: 生物多样性对生产力的影响起着重要作用[33-35]; 另一方则质疑前者的观点, 他们认为生物多样性对生产力的影响还需考虑抽样效应, 生态位互补等因素的作用[36]。中国北方不同区域的草地由于存在环境异质性, 生物多样性对生产力变化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例如: 有研究发现青藏高原东部典型高寒草甸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呈对数线性增加的关系[37]。松嫩平原部分地区的草地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呈单峰函数关系[38]。物种多样性对于生产力的影响的机理尚未阐释清楚, 不同的空间尺度, 不同的环境因素以及不同的物种组成都可能对生产力造成影响。普遍认为生态系统结构越复杂, 稳定性越强, 越能抵御外界环境的干扰。因此维持草地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越能保持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对于提高草地的生产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草地植物的生物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应草地生产力水平[33], 同时草地动物以及草地土壤微生物亦是草地生物多样性重要的组成部分[39-41]。草原动物主要包括常见的草食性动物(如牛、马、羊, 草食性昆虫)、啮齿类动物、以草食动物为食的肉食性动物(如狼)以及土壤动物等。草原动物与土壤微生物共同构建起复杂的食物网, 对草地物质循环以及能量流动具有促进作用, 同时对草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表明, 草食性粪尿等方式影响草地植物物种多样性动物可能对草地生产力造成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草食性动物通过不同的采食量、食性选择以及向草地中排放变化所导致的[42]。而肉食性动物通过捕食草食性动物控制草食性动物数量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这有利于防止草地植物被草食性动物大量啃食, 对于维持草地食物链的平衡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肉食动物-草食动物-草地资源”草地生态系统食物链模型发现, 这三者间通过密度调节以及制约机制以达到食物链的平衡, 但是当食物链的平衡被打破后, 肉食性动物的大量灭绝会造成草食动物数量的剧增, 从而造成草地资源被大量消耗, 草地生产力下降, 草地逐渐出现退化现象[43]。同时不能够忽视草地土壤动物以及土壤微生物对于草地食物链的分解作用: 土壤生物不仅能直接影响植物根系, 同时也会对微生物的数量和类别造成影响[44]。国外相关研究表明, 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能够驱动生态系统功能, 例如植物多样性、生产力以及变异性[34]。由于人类放牧强度过大以及草地的集约化管理, 使得草地生长速率低于退化率, 加剧了草畜矛盾, 草地退化现象日益突出, 生物多样性丧失[45]。维持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对草地生产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保护草原动物尤为重要, 同时应将放牧的牲畜数量限制在草地可承载范围之内, 减少人为干扰对草地的影响, 以期保持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
3 管理因素
除了环境因素和生物因素外, 人为管理因素也是影响草地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积极的适应性管理手段, 能够维持草地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 对提高草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具有积极作用[46]。有利于我国草地畜牧业的发展。目前国内主要管理和利用草地的方式有放牧、刈割、灌溉、施肥、火烧、围封、补播和开垦等[47]。这些人为管理的手段均会对北方草地生产力造成影响。
3.1 放牧的影响
放牧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干扰方式, 对草地植被的生长既有促进又有抑制作用[48], 其直接影响植物营养物质的合成与分解过程[49]。过度放牧造成草地土壤含水量的下降的同时降低草地生产力[50]; 适度放牧有助于草地的健康发展且维持较高的草地生产力[51]。例如: 在宁夏盐池县荒漠草原区内, 研究发现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 草地牧草生产力逐渐下降[52]。因此采取合理的放牧制度是提高牧草生产力的关键。目前的放牧制度主要分为自由放牧和划区轮牧两种方式[53]。划区轮牧即有计划地将草地划分成若干个轮牧小区, 使牲畜按照一定顺序逐区采食, 轮回利用。与自由放牧相比, 划区轮牧具有很大的优势, 其一划区轮牧能够降低家畜的采食性行为, 其二能够降低家畜对草地的践踏强度以及频率,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草地恢复生长以及牲畜采食之间的矛盾, 有利于解决自由放牧条件下生产力降低的问题[54]。除了不同的放牧制度以及不同的放牧强度外, 放牧家畜种类也是影响北方草地生产力的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 在中度放牧强度条件下, 混合放牧条件下的生物多样性水平要高于单独放牧下的生物多样性水平[55]。因此在选择有助于提高草地生产力的放牧方式时还要根据具体条件而定, 既需要考虑草地类型、牧草种类、家畜品种、气候等诸多因素影响, 同时也需要建立草地资源分类经营管理的机制[56], 以实现北方草地可持续性发展。
3.2 刈割的影响
刈割是人类利用草地的方式之一[57-59], 过度刈割会改变草地原有群落结构, 造成草地群落物种多样性下降, 草地生产力降低。适当刈割是利用草地的重要原则。由于不同草地植物的生长特性不尽相同, 为提高不同草地植物的产量, 需要确定适宜的刈割频次, 刈割方式和刈割强度。杨恒山等[60]于2002年对内蒙古西辽河平原的健宝进行了刈割实验, 发现随着刈割时间的增加干草产量会有递减的趋势。合理的刈割方式亦能提高草地生产力水平, 比如可以采取不同的留茬高度或者切口方式来影响草地生产力[61-62]。研究表明轻度刈割所累积的生物量要强于无刈割所累积的生物量[62]; 随着留茬高度的降低, 地上和地下生物量有下降的趋势[61]。同样确定合理的刈割时期也尤为重要, 刈割时期按照植物不同的发育阶段分为分枝期、现蕾期、初花期、中花期、盛花期和结实期[63]。不同的草地植物刈割的时间存在差异: 比如豆科牧草最佳刈割期为现蕾期至初花期, 该时期刈割能获取较高产量及品质[63]。因此确定合理的刈割时期、刈割频次、刈割强度和刈割方式对于提高草地生产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3 灌溉的影响
灌溉亦是人类利用草地的方式之一。由于我国自然降水分布不均造成了北方草地某些区域严重缺水, 导致部分区域草地生产力降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仍可以通过人为灌溉等方式来提高部分地区草地生产力。研究表明灌溉促进草地生产力的提高。例如: 通过对希拉穆仁草原的灌溉实验发现, 灌溉可以提高建群种高度、植被盖度以及地上生物量, 从而提高草地植被的生产力[64]。无论是天然草地还是人工草地, 灌溉区产草量均高于不灌溉区产草量近几倍[65]。在灌溉草地的同时需要遵循适时适量的原则, 不应盲目地灌溉, 灌溉过多亦会影响产草量[66]。对于人工草地来讲, 在牧草适宜的生长期进行灌溉既有利于牧草高产又能达到节水的目的, 因此了解牧草的生长周期对于确定合理的灌溉期以及灌溉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相关研究表明, 通过对内蒙古人工草地牧草灌溉实验发现, 在开花期后进行补水能显著提高牧草长期的水分利用效率, 有利于牧草产量的提高[67]。灌溉方式有很多, 比如喷灌、滴灌和沟灌等。不同地区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灌溉方式, 这对于提高草地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意义[68-70]。在灌溉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气候的影响, 研究表明, 降水较多的年份下灌溉对高寒草地影响较小, 而在干旱条件下灌溉对高寒草地的影响十分显著[71]。因此北方草地不同区域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土壤含水量、牧草类型来确定合理的灌溉方式、灌溉时期以及灌溉量, 这样才有利于草地生产力的提升。
3.4 施肥的影响
施肥是提高草地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施肥可以补充草地对植物的营养供应[72], 同时能够促进草地土壤水分的利用效率[73]。许多人工施肥试验表明, 施肥能够提高草地生产力。例如: 顾梦鹤等[74]通过对高寒地区人工草地3年的施肥试验发现, 施肥可以显著提升草地生产力。通过对高寒退化草地的施肥试验发现, 施肥处理的草地与对照组的草地相比, 在平均高度, 盖度以及鲜草产量等方面均明显高于不施肥的草地[75]。对内蒙古多伦退化草地长期控制实验发现, 加氮增加了植物地上净初级生产力, 但降低了植物物种多样性以及群落的稳定性[76]。北方草地面积广袤, 不同地区的土壤, 气候等自然条件不尽相同, 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施肥时间以及施肥比例。施建军等[77]通过对青藏高原退化草地的人工施肥试验发现, 同时施氮磷肥可以提高牧草产量。不同的草地植物对氮磷钾肥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禾本科植物对氮肥的需求较多, 而豆科植物对磷肥的需求较多[78]。因此, 在施肥的同时还要考虑何种元素对哪类草地植物的生长更为有利, 这样更能有效的提高草地生产力。由于草地植物的生长不单单只受施肥条件的影响, 还受温度降水变化的影响, 因此在施肥的同时, 还要考虑使草地植物的生长达到适宜的水热条件, 这对于草地生产力的提高也大有裨益[79]。同时还需要注意施肥虽然能提高草地生产力, 但是过度施肥也会带来群落物种结构改变、草地群落稳定性下降以及土壤酸化等问题[80-81]。
3.5 火烧的影响
火是重要的环境因子, 其对草地植物的生长, 群落的组成以及无机环境等方面均会造成双面影响[82], 一方面火烧有利于草地各个植物种的群落生物量以及数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83]; 另一方面草原火烧后会造成土壤枯落物减少, 土壤温度升高, 加剧土壤水分蒸发, 不利于草地群落生长[84]。周道玮等[85-87]通过对长岭草原区内的草地进行火烧实验发现, 火烧会对群落结构造成影响, 火烧亦有利于叶生物量的增长; 同时在研究不同时间草地火烧后对群落地上生物量的变化时发现, 火烧地各层段叶生物量要高于未烧地; 亦发现早春火烧能够提高羊草()种群地上生产力, 晚春火烧导致羊草()种群地上生产力的下降; 在降水丰年火烧有利于植物群落的生长, 降水欠缺的年份火烧则使产量降低。还需要注意到火烧对不同草地植物的作用是不同的, 火烧可以明显提高羊草比例, 葱属植物的产量基本保持稳定[88], 有利于改善草地群落的物种组成。国外相关研究发现, 火灾频率的变化可能会通过改变土壤碳库和氮对植物生长的限制, 进而改变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和氮循环[89-90], 同时火烧可能与气候、物种以及资源的共同作用进而影响草原的分布[91]。综上, 虽然通过有计划的火烧可以有效地改变草地群落的组成结构, 有利于提高草地生产力, 但是我国草地不像一些外国的草地, 很少存在大量的凋落物, 同时, 受制于我国对预防火灾的管理政策限制, 火烧未能作为我国草地管理的一种常用手段。
3.6 围封的影响
围栏封育是一种常用的管理草原的人为手段[92]。与放牧这种管理措施不同, 这种手段则是通过围栏的方式隔离牲畜防止其对草地进行采食, 使草地达到修养生息的目的。但这种手段也存在两面性, 一方面其有利于退化草地的恢复, 排除放牧对草地干扰等因素, 增加土壤养分含量[93], 便于提高退化草地生产力; 另一方面, 封育会导致大量凋落物的堆积, 影响资源利用效率[94]。有研究表明, 通过对内蒙古锡林郭勒典型草原进行春季休牧实验, 比较休牧区以及非休牧区草地地上生物量发现, 休牧区产草量显著高于连续放牧区产草量, 这可能是由于春季休牧有利于牧草在返青初期积累大量的营养物质, 从而对牧草后期的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 进而提高草地生产力。随着封育年限的不断增加, 草地生产力逐渐增加[95]。然而并非围封的时间越久越好, 国外的相关研究发现, 长期围栏封育并不能显著提高草地生产力。通过对干旱区草场长时间的监测发现, 草地生产力非但没有提高, 还有显著下降趋势[96]。同时不同的封育措施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也存在差异[97]。因此, 确定合理的围封年限对于提高草地生产力来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同的草场围封的年限也是不同的, 例如: 对于宁夏自治区沙化草地来讲, 由于草地沙化现象比较严重, 因此围封的年限需要增加, 研究表明围封8年能够显著提高草地生产力, 但是当围封时间达到19年后会出现植被数量下降的现象, 草地生产力反而下降[98]。因此, 围栏封育对退化草地的恢复起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 并不是围封时间越长越好, 还应根据当地的气候以及植被情况制定合理的围封年限, 才能有效提高草地生产力。同时我们还需注意, 围封打破了草地原有的放牧传统, 虽然能够减轻草地的负荷, 但是也应意识到放牧对维持草地生态系统平衡的作用, 应该将放牧与围封这两种手段相结合, 这样才能够将植物与动物生产相互联系, 进而提高草地生产力。
3.7 混播与补播的影响
近年来, 我国北方草地退化现象严重, 其主要表现在草地生产力的下降, 在对草地进行保护利用的同时, 草地补播亦是提高草地生产力的有效措施之一。草地补播是在基本不破坏草地的基础上, 向草地中种植优质牧草从而达到改善草地群落结构并提高草地产量品质的手段[99], 并改善土壤中的养分含量[100]。多数研究表明, 补播优质牧草的确能增加草地生产潜力[101-102]。例如: 李飞等[101]对补播两年后的草木樨()、黄花苜蓿()等5个群落生产力的调查发现补播显著提高了群落生产力, 补播后草地群落生产力要高于自然演替下草地群落生产力。郑华平[102]在研究补播禾草对玛曲高寒沙化草地植物多样性和生产力的影响时, 发现在该地补播垂穗披碱草()、中华羊茅()和草地早熟禾(), 与对照相比, 补播后草地地上生物量显著增加, 且补播第2年各处理生物量大约是补播第1年生物量的2倍, 这表明补播对草地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需要时间的累积。松嫩平原天然草地的生产力低下, 氮元素缺乏, 而豆科饲草能够通过共生根瘤菌固定大气中的氮素, 通过向该地补播豆科饲草能够解决该地氮素缺乏的问题, 从而提高松嫩平原天然草地生产力[103]。以往混播被视为是一种提高人工草地生产力的措施之一。有研究发现, 混播能够提高草地生产力[104-105]。例如: 宝音[104]关于无芒雀麦()与苜蓿()混播实验研究表明, 内蒙古的无芒雀麦()和草原2号紫花苜蓿()混播地产量显著地高于禾草单播地。通过向天然草地中混播豆科植物和建植禾—豆混播人工草地, 有利于提高土壤碳截获能力, 从而提高草地生产力, 有助于草地可持续利用[106]。综上, 在向草地中补播或混播牧草时, 应考虑适宜品种、时间及方法, 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3.8 开垦草地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 我国已经经历了4次草原大开垦, 开垦近1930多万公顷优质草地[107]。我国于1985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46条规定: 禁止开垦草原。对水土流失严重、有沙化趋势、需要改善生态环境的已垦草原, 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草; 已造成沙化、盐碱化、石漠化的, 应当限期治理。该法明确提出关于天然草地以及人工草地开垦的相关法律规定。开垦会对草地健康状况造成影响, 尤需注意开垦草地对草地碳氮损失的影响, 开垦意味着要将草地通过烧荒的手段转变为农田, 烧荒会导致CO2和N2O等气体排放到空气当中[108], 从而造成土壤养分大量流失, 同时开垦亦会带来草地沙化以及荒漠化[90], 土壤裸露, 水土流失现象加剧, 土壤含水量下降等问题。有研究发现, 栗钙土草地开垦为农田后, 其土壤结构受到破坏, 降低了土壤有机质的稳定性[109]。闫玉春等[110]对内蒙古典型草原区长期开垦35年的草地的研究表明, 长期开垦会降低草地土壤以及根系的固碳能力, 而根系和土壤固碳能力的下降也正是造成土壤养分下降的主要原因, 间接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 通过将长期开垦草地恢复为天然草地, 有利于增加土壤以及植物的固碳能力, 从而有利于草地生产力的恢复。开垦草地对草地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不利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 造成草地资源面积缩小, 极大地限制了草地生产力发展, 但是也应意识到我国传统农耕业并不能完全满足我国人民对食物结构的需求, 发展现代草地农业逐渐成为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主流趋势, 同时也能够获取较高的经济收入, 但易受水热资源的限制以及农作物价格的影响, 经常发生开垦几年后又被撂荒, 重新转化为草地。开垦后撂荒的行为, 导致草原生产力发生剧烈变化, 需要深入理论研究, 从而指导草地资源保护, 以及草地的生产与管理。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梳理草地生产力方面的研究, 本文综合分析了自然因素(温度、降水、土壤)、生物因素以及人为管理因素(放牧、刈割、灌溉、施肥、火烧、围栏封育、补播混播及开垦)对北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降水和温度决定了草地的分布范围, 但是由于我国北方草地分布区之间的温度变化差异不大, 即使模拟全球变化, 增温幅度一般多为2 ℃, 虽然对草地群落的功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由于植物后期的补偿生长等因素, 温度对草地生产力影响较小。而降水是对草地影响的最主要自然因素, 降水的变化对草地生产力影响十分显著。土壤限制了植物养分与水分的运输, 土壤因子也是影响草地生产力的显著环境因子, 并且草地退化多与土壤退化同步进行, 植被的恢复相对较为容易, 土壤的恢复多以十年、百年计, 对草地土壤的保护需要引起重视。自然环境是复杂多变的, 任何一个自然因素的改变都会影响草地生产力的变化, 并且自然因素多是耦合在一起, 一个因子的变化经常会引起其他环境因子的联动, 因此, 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多因子的综合影响, 从而揭示环境因子的综合作用机制。同时也应该注意到, 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剧烈增加, 人类的干扰成为了影响草地生产力的主要因子。尤其是, 放牧与刈割对草地生产力影响极为显著, 需要控制放牧强度, 选择适宜的放牧时间, 从而维持草地可持续利用。理论上, 多次刈割能够获得较高生产力, 但是由于刈割成本以及储藏条件的限制, 中国北方草地的刈割, 多是一次刈割, 因此刈割强度(也就是留茬高度)是维持我国北方草地的重要因子, 需要针对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植被, 提出适宜的刈割强度。灌溉与施肥对草地生产力提高显著, 但是, 由于草地单位面积产出有限, 所以, 灌溉和施肥作为管理大面积草地的方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发展, 但是对于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苜蓿()等草地植物, 其方法还是十分有效的。火烧因子对草地管理还是十分有效的, 但是我国草地不像一些外国的草地, 很少存在大量的凋落物, 同时, 受制于我国对预防火灾的管理政策限制, 火烧未能作为我国草地管理的一种手段。近年来, 围栏封育经常作为我国草地恢复的一种管理措施, 但是围栏封育的效果较为缓慢, 应该结合一些定向、加速等更为积极的方法, 提高草地的恢复速度与质量。混播, 尤其是混播豆科牧草, 能够显著改善土壤营养以及草地植被的蛋白含量, 是国际草地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 值得我国草地管理借鉴。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草地的直接经济收入低于种植业, 经常发生草地被开垦现象, 导致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的丧失,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草地的保护, 划定生态红线, 通过制定合理的草地管理政策及制度并有效施行, 不但可以防止草地退化的现象, 同时也会对草地生产力的提高大有帮助, 达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发展。
[1] 梁艳, 干珠扎布, 张伟娜, 等. 气候变化对中国草原生态系统影响研究综述[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4, 16(2): 1–8.
[2] 贾文晓. 中国北方草地生态系统生产力估算及其不确定性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1–70.
[3] 沈海花, 朱言坤, 赵霞, 等. 中国草地资源的现状分析[J]. 科学通报, 2016, 61(2): 139–154.
[4] 张美玲, 蒋文兰, 陈全功, 等. 草地净第一性生产力估算模型研究进展[J]. 草地学报, 2011, 19(2): 356–366.
[5] YIN Fang, DENG Xiangzheng, JIN Qin, et al.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on grassland productivity in Qinghai Province, China[J]. 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 2014, 8(1): 93–103.
[6] 韩芳, 牛建明, 刘朋涛, 等. 气候变化对内蒙古荒漠草原牧草气候生产力的影响[J]. 中国草地学报, 2010, 32(5): 57–65.
[7] 杨泽龙, 杜文旭, 侯琼, 等. 内蒙古东部气候变化及其草地生产潜力的区域性分析[J]. 中国草地学报, 2008, 30(6): 62–66.
[8] 罗玲, 王宗明, 毛德华, 等. 松嫩平原西部草地净初级生产力对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响应[J]. 生态学杂志, 2012, 31(6): 1533–1540.
[9] GAO Qingzhu, SCHWARTZ M W, ZHU Wenquan, et al. Changes in global grassland productivity during 1982 to 2011 attributable to climatic factors[J]. Remote Sensing, 2016, 8(5): 1–12.
[10] FENG Yunfei, WU Jianshuang, ZHANG Jing, et al. Identifying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climate and grazing to both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alpine grassland productivity dynamics from 1993 to 2011 on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J]. Remote Sensing, 2017, 9(2): 1–14.
[11] 杨凯, 林而达, 高清竹, 等. 气候变化对藏北地区草地生产力的影响模拟[J]. 生态学杂志, 2010, 29(7): 1469– 1476.
[12] BAI Yongfei, HAN Xingguo, WU Jianguo, et al. Ecosystem stability and compensatory effects in the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J]. Nature, 2004, 431(7005): 181–184.
[13] 李霞, 李晓兵, 王宏, 等. 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温带草原植被的影响[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6, 42(6): 618– 623.
[14] NIU Shuli, WU Mingyu, HAN Yi, et al. Water-mediated responses of ecosystem carbon fluxes to climatic change in a temperate steppe[J]. New Phytologist, 2010, 177(1): 209–219.
[15] KNAPP A K, SMITH M D. Variation among biomes in temporal dynamics of aboveground primary production[J]. Science, 2001, 291(5503): 481–484.
[16] 张统. 改变降雨格局对中国北方温带草原生态系统碳通量的影响[D]. 郑州: 河南大学, 2017.
[17] 茹靖益. 降水季节分配变化对中国北方半干旱草地生态系统碳通量的影响[D]. 郑州: 河南大学, 2017.
[18] PENG Shushi, PIAO Shilong, SHEN Zehao, et al. Precipitation amount, seasonality and frequency regulate carbon cycling of a semi-arid grassland ecosystem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A modeling analysis[J]. Agricultural Forest Meteorology, 2013, 178–179: 46–55.
[19] 史瑞琴. 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的影响研究[D]. 南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06: 1–43.
[20] 闫伟兄, 陈素华, 乌兰巴特尔, 等. 内蒙古典型草原区植被NPP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自然资源学报, 2009, 24(9): 1625–1634.
[21] 李镇清, 刘振国, 陈佐忠, 等. 中国典型草原区气候变化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J]. 草业学报, 2003, 12(1): 4–10.
[22] 赵东升, 吴绍洪, 尹云鹤. 气候变化情景下中国自然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分布[J]. 应用生态学报, 2011, 22(4): 897–904.
[23] GUO Liang, CHENG Jimin, LUEDELING E, et al. Critical climate periods for grassland productivity on China's loess plateau[J].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017, 233: 101–109.
[24] 神祥金. 中国温带草原退化草地气温与地温变化及其机理研究[D]. 长春: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16.
[25] 神祥金, 周道玮, 李飞, 等. 中国草原区植被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J]. 地理科学, 2015, 35(5): 622–629.
[26] 林舜华, 高雷明, 黄银晓. 大气CO2倍增对草原羊草的影响[J]. 生态学杂志, 1998, 17(6): 2–7.
[27] LEADLEY P W, NIKLAUS P A, STOCKER R, et al. A field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elevated CO2on plant biomass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a calcareous grassland[J]. Oecologia, 1999, 118(1): 39–49.
[28] 董自红, 蒋平安, 贾宏涛, 等. 新疆高山草甸草原植物群落夏季CO2排放日变化分析[J]. 新疆农业科学, 2007(1): 1–5.
[29] 珊丹. 控制性增温和施氮对荒漠草原植物群落和土壤的影响[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08.
[30] 李博. 中国北方草地退化及其防治对策[J]. 中国农业科学, 1997, 30(6): 2–10.
[31] 何楷迪, 孙建, 陈秋计. 气候要素和土壤质地对青藏高原草地净初级生产力和降水利用率的影响[J]. 草业科学, 2019, 36(4): 1053–1065.
[32] 周道玮, 李强, 宋彦涛, 等. 松嫩平原羊草草地盐碱化过程[J]. 应用生态学报, 2011, 22(6): 1423–1430.
[33] TILMAN D, WEDIN D, KNOPS J. Productiv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fluenced by biodiversity in grasslandecosystems[J]. Nature, 1996, 379(6567): 718–720.
[34] VAN DER HEIJDEN M G A, KLIRONOMOS J N, URSIC M, et al. Mycorrhizal fungal diversity determines plant biodiversity, ecosystem variability and productivity[J]. Nature, 1998, 396(6706): 69–72.
[35] VAN DER HEIJDEN M G A, BARDGETT R D, VAN STRAALEN N M. The unseen majority: Soil microbes as drivers of plant diversity and productivity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J]. Ecology Letters, 2008, 11(3): 296–310.
[36] 邱波, 王刚. 生产力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研究进展[J]. 生态科学, 2003, 22(3): 265–270.
[37] 杜国祯, 覃光莲, 李自珍, 等. 高寒草甸植物群落中物种丰富度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J]. 植物生态学报, 2003, 27(1): 125–132.
[38] 杨利民, 周广胜, 李建东. 松嫩平原草地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关系的研究[J]. 植物生态学报, 2002, 26(5): 589– 593.
[39] WANG Xinyu, Li Frank Yonghong, Tang Kuanyan, et al. Land use alters relationships of grassland productivity with plant and arthropod diversity in inner mongolian grassland[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20, 30(3): 1–13.
[40] ZAK J C, WILLIG M R, MOORHEAD D L, et al. Functional diversity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 a quantitative approach[J].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1994, 26(9): 1101–1108.
[41] OLFF H, Ritchie M E. Effects of herbivores on grassland plant diversity[J].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1998, 13(7): 261–265.
[42] 王德利, 王岭. 草食动物与草地植物多样性的互作关系研究进展[J]. 草地学报, 2011, 4(19): 699–704.
[43] 陈玲玲, 林振山, 梁仁君. 草原生态食物链对人类活动干扰的响应[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4): 117–122.
[44] 博力健, 党德尔, 贾宏涛, 等. 草地生态系统中土壤动物的研究进展[J]. 新疆农业科学, 2006, 43(S1): 49–52.
[45] Gossner M M, Lewinsohn T M, Kahl T, et al. Land-use intensification causes multitrophic homogenization of grassland communities[J]. Nature, 2016, 540(7632): 266– 269.
[46] Folke C, Carpenter S, Walker B, et al. Regime shifts, resilience, and biodiversity in ecosystem management[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s, 2004, 35: 557–581.
[47] HE Nianpeng, ZHANG Yunhai, DAI Jingzhong, et al. Land-use impact on soil carbon and nitrogen sequestration in typical steppe ecosystems, Inner Mongoli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2, 22(5): 859–873.
[48] 陈辰, 王靖, 潘学标, 等. 气候变化对内蒙古草地生产力影响的模拟研究[J]. 草地学报, 2013, 21(5): 850–860.
[49] 张扬建, 朱军涛, 沈若楠, 等. 放牧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进展[J]. 植物生态学报, 2020, 44(5): 553–564.
[50] Gan Lei, Peng Xinhua, Peth S, et al. Effects of grazing intensity on soil water regime and flux in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 China[J]. Pedosphere, 2012, 22(2): 165–177.
[51] 王明君, 韩国栋, 崔国文, 等. 放牧强度对草甸草原生产力和多样性的影响[J]. 生态学杂志, 2010, 29(5): 862– 868.
[52] 张虎, 师尚礼, 王顺霞. 放牧强度对宁夏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结构及草地生产力的影响[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2, 26(9): 73–76.
[53] 成如, 赵楠, 赵青山. 草地放牧利用制度与草地生产力关系[J]. 农村牧区机械化, 2014(3): 29–30.
[54] 彭祺, 王宁. 不同放牧制度对草地植被的影响[J]. 农业科学研究, 2005(1): 27–30.
[55] 王德利, 王岭. 草地管理概念的新释义[J]. 科学通报, 2019, 64(11): 1106–1113.
[56] 刘兴元, 梁天刚, 龙瑞军, 等. 北方牧区草地资源分类经营机制与可持续发展[J]. 生态学报, 2009, 29(11): 5851– 5859.
[57] Bluethgen N, Dormann C F, Prati D, et al. A quantitative index of land-use intensity in grasslands: Integrating mowing, grazing and fertilization[J].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2012, 13(3): 207–220.
[58] Rodriguez D, Van O M, Schapendonk A. Lingra-cc: A sink-source model to simulate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management on grassland productivity[J]. New Phytologist, 1999, 144(2): 359–368.
[59] LU Zedong, DU Rui, DU Pengrui, et al. Effect of mowing on N2O and CH4fluxes emissions from the meadow-steppe grasslands of Inner Mongolia[J]. 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 2015, 9(3): 473–486.
[60] 杨恒山, 曹敏建, 范富, 等. 刈割次数对健宝产草量及品质的影响[J]. 中国草地, 2003(3): 29–32.
[61] 张峰, 陈大岭, 赵萌莉, 等. 刈割留茬高度对大针茅草原群落生物量的影响[J]. 中国草地学报, 2019, 41(5): 73– 79.
[62] 章家恩, 刘文高, 陈景青, 等. 不同刈割强度对牧草地上部和地下部生长性状的影响[J]. 应用生态学报, 2005, 16(9): 1740–1744.
[63] 朱珏, 张彬, 谭支良, 等. 刈割对牧草生物量和品质影响的研究进展[J]. 草业科学, 2009, 26(2): 80–85.
[64] 高天明, 张瑞强, 刘铁军, 等. 不同灌溉量对退化草地的生态恢复作用[J]. 中国水利, 2011(9): 20–23.
[65] 程荣香, 张瑞强. 发展节水灌溉是我国干旱半干旱草原区人工草地建设的必然举措[J]. 草业科学, 2000, 17(2): 53– 56.
[66] 曾光华. 国外草地施肥及灌溉方面的研究概况[J]. 青海畜牧兽医杂志, 1994(3): 31–32.
[67] 王海青, 田育红, 黄薇霖, 等. 不同灌溉量对内蒙古人工草地主要牧草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J]. 生态学报, 2015, 35(10): 3225–3232.
[68] 王琦, 张恩和, 龙瑞军, 等. 不同灌溉方式对紫花苜蓿生长性能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J]. 草业科学, 2006(9): 75–78.
[69] LIU Shuhui, KANG Yaohu, WAN Shuqin, et al. Water and salt regulation and its effects ongrowth under drip irrigation in saline-sodic soils of the Songnen Plain[J].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 2011, 98(9): 1469–1476.
[70] 李和平, 史海滨, 包小庆, 等. 西北牧区灌溉人工草地适宜发展规模分析[J]. 中国草地学报, 2007, 29(4): 104– 109.
[71] 干珠扎布, 段敏杰, 郭亚奇, 等. 喷灌对藏北高寒草地生产力和物种多样性的影响[J]. 生态学报, 2015, 35(22): 7485–7493.
[72] FAY P A, PROBER S M, HARPOLE W S, et al. Grassland productivity limited by multiple nutrients[J]. Nature Plants, 2015, 1(7): 1–5.
[73] 张学梅, 马千虎, 张子龙, 等. 施肥对高寒荒漠草原区混播人工草地产量和水分利用的影响[J]. 中国农业科学, 2019, 52(8): 1368–1379.
[74] 顾梦鹤, 王涛, 杜国祯. 施肥对高寒地区多年生人工草地生产力及稳定性的影响[J]. 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46(6): 59–63.
[75] 魏学红, 杨富裕, 孙磊. 补播和施肥对藏北高寒退化草地的改良效果[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32): 18155– 18156.
[76] 姜勇, 徐柱文, 王汝振, 等. 长期施肥和增水对半干旱草地土壤性质和植物性状的影响[J]. 应用生态学报, 2019, 30(7): 2470–2480.
[77] 施建军, 马玉寿, 董全民, 等. “黑土型”退化草地人工植被施肥试验研究[J]. 草业学报, 2007(2): 25–31.
[78] 陈敏, 宝音陶格涛, 孟慧君, 等. 人工草地施肥试验研究[J]. 中国草地, 2000(1): 21–26.
[79] 程积民, 贾恒义, 彭祥林. 施肥草地群落生物量结构的研究[J]. 草业学报, 1997(2): 23–28.
[80] 李禄军, 于占源, 曾德慧, 等. 施肥对科尔沁沙质草地群落物种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J]. 草业学报, 2010, 19(2): 109–115.
[81] Tian Dashuan, Niu Shuli. A global analysis of soil acidification caused by nitrogen addition[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 2015, 10(2): 1–10.
[82] 周道玮. 火烧对草地的生态影响[J]. 中国草地, 1992(2): 74–77.
[83] 刘昊, 赵宁, 曹喆, 等. 干扰对草地植被与土壤的影响之研究进展[J]. 中国农学通报, 2008(5): 8–16.
[84] 周道玮, 姜世成, 田洪艳, 等. 草原火烧后土壤水分含量的变化[J]. 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1): 102– 107.
[85] 周道玮, 李亚芹, 孙刚. 草原火烧后植物群落生产及其产量空间结构的变化[J]. 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4): 83–90.
[86] 周道玮, 张保田, 李建东. 松嫩羊草草原火烧后地上生产力的变化[J]. 草业学报, 1995(4): 23–28.
[87] 周道玮, 祝玲, 张宝田. 不同时间草地火烧后群落地上生物量结构的变化[J]. 应用生态学报, 1996(3): 280–282.
[88] 李政海, 王炜, 刘钟龄. 火烧对典型草原改良的效果[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1994(4): 51–60.
[89] PELLEGRINI A F A, AHLSTROM A, HOBBIE S E, et al. Fire frequency drives decadal changes in soil carbon and nitrogen and ecosystem productivity[J]. Nature, 2018, 553(7687): 194–198.
[90] REICH P B, PETERSON D W, WEDIN D A, et al. Fire and vegetation effects on productivity and nitrogen cycling across a forest-grassland continuum[J]. Ecology, 2001, 82(6): 1703–1719.
[91] HOFFMANN W A, GEIGER E L, GOTSCH S G, et al. Ecological thresholds at the savanna-forest boundary: How plant traits, resources and fire govern the distribution of tropical biomes[J]. Ecology Letters, 2012, 15(7): 759–768.
[92] 闫玉春, 唐海萍, 辛晓平, 等. 围封对草地的影响研究进展[J]. 生态学报, 2009, 29(9): 5039–5046.
[93] 刘铁军, 杨劼, 郭建英, 等. 围封对荒漠草原植物群落与土壤养分变化的影响[J]. 中国草地学报, 2019, 41(5): 86–93.
[94] ALTESOR A, OESTERHELD M, LEONI E, et al. Effect of grazing on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of a uruguayan grassland [J]. Plant Ecology, 2005, 179(1): 83–91.
[95] 李军保, 马存平, 鲁为华, 等. 围栏封育对昭苏马场春秋草地地上植物量的影响[J]. 草原与草坪, 2009(2): 46–50.
[96] Omar S A S. Dynamics of range plants following 10-years of protection in arid rangelands of kuwait[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1991, 21(1): 99–111.
[97] 杨晓晖, 张克斌, 侯瑞萍. 封育措施对半干旱沙地草场植被群落特征及地上生物量的影响[J]. 生态环境, 2005, 14(5): 730–734.
[98] 刘建, 张克斌, 程中秋, 等. 围栏封育对沙化草地植被及土壤特性的影响[J]. 水土保持通报, 2011, 31(4): 180– 184.
[99] 周冀琼. 补播苜蓿对退化草地生产力和多样性的影响[D].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2017.
[100]刘召刚, 赵明, 张红香. 补播苜蓿对呼伦贝尔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J]. 土壤与作物, 2019, 8(3): 235–241.
[101]李飞, 禹朴家, 神祥金, 等. 退化草地补播草木樨、黄花苜蓿的生产力和土壤碳截获潜力[J]. 草业科学, 2014, 31(3): 361–366.
[102]郑华平, 陈子萱, 牛俊义, 等. 补播禾草对玛曲高寒沙化草地植物多样性和生产力的影响[J]. 草业学报, 2009, 18(3): 28–33.
[103]李玉中, Redmann R E,祝廷成, 等. 羊草草原豆科牧草生物固定量研究[J]. 草地学报, 2002, 10(3): 164–166.
[104]宝音陶格涛. 无芒雀麦与苜蓿混播试验[J]. 草地学报, 2001, 9(1): 73–76.
[105]朱树秀, 李蜀, 杨志忠, 等. 紫花苜蓿和老芒麦混播组合与产草量研究初报[J]. 新疆畜牧业, 1990(1): 27–32.
[106]李强, 周道玮. 草地管理对土壤碳截获的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 2018, 46(23): 1–5.
[107]苏和, 刘桂香, 何涛. 草原开垦及其危害[J]. 中国草地, 2005, 27(6): 63–65.
[108]耿远波, 章申, 董云社, 等. 草原土壤的碳氮含量及其与温室气体通量的相关性[J]. 地理学报, 2001, 56(1): 44–53.
[109]李青春, 李跃进, 王丹斓, 等. 草地与耕地土壤团聚体及有机碳含量对比分析——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例[J]. 水土保持通报, 2019, 39(1): 50–54.
[110]闫玉春, 唐海萍, 常瑞英, 等. 长期开垦与放牧对内蒙古典型草原地下碳截存的影响[J]. 环境科学, 2008, 29(5): 1388–1393.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grassland productivity in Northern China
WANG Heqi1,2, FAN Gaohua1, HUANG Yingxin2,*, ZHOU Daowei1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Jili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Grassland Farming, Changchu 130102,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Institute of Botan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93, China
The grassland resources in Northern China are very rich, and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s of grassland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biological factors and human management factors on the changes of grassland productivity in northern China.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grassland productivity in Northern China in recent years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factors mainly affect the changes of grassland productivity, and biological factors also affect grassland productivity. Human factors such as grazing, mowing, fertilization and grassland reclamation have a great impact on grassland productivity, and the planned measures such as burning, irrigation, fencing and mixed-planting can potentially improve grassland productivity.
grassland in Northern China; biomass; warming; enclosure; fire
王鹤琪, 范高华, 黄迎新, 等. 中国北方草地生产力研究进展[J]. 生态科学, 2022, 41(5): 219–229.
WANG Heqi, FAN Gaohua, HUANG Yingxin, et al.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grassland productivity in Northern China[J]. Ecological Science, 2022, 41(5): 219–229.
10.14108/j.cnki.1008-8873.2022.05.026
S812.8
A
1008-8873(2022)05-219-11
2020-08-28;
2020-10-20
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美丽中国” 项目六课题四“东北农牧交错带生态功能提升与绿色发展示范”(XDA23060405);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工程专项资助(XDA28110201); 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吉林省西部重度盐碱化草地恢复方法研究与示范”(20190303066SF)
王鹤琪(1995—), 男, 吉林长春人, 在读硕士, 主要从事盐碱地恢复草地生态学研究, E-mail: wangheqi@iga.ac.cn
黄迎新, 男, 博士, 研究员, 主要从事草地生态学研究, E-mail: huangyx@iga.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