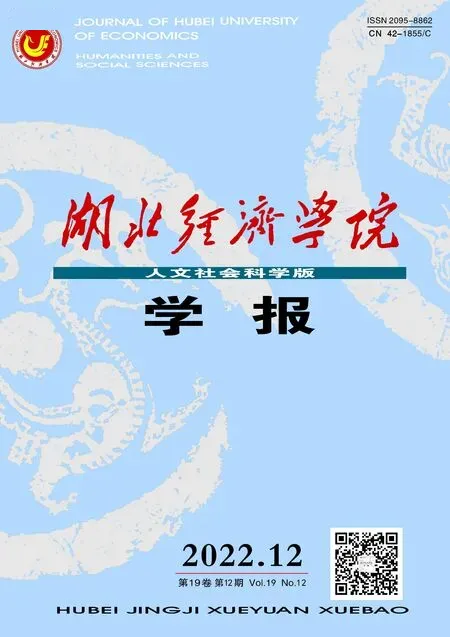梁鸿《神圣家族》中“乡镇”的多重文化表征
2023-01-24张旻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张旻霏(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梁鸿作为一名学者和作家,在《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两部非虚构作品中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剖析的视角揭露了梁庄在城市化进程中留守儿童、农村妇女、生态恶化等多方面的惨痛现实。梁庄不仅成为中国万千农村的缩影,更是梁鸿创作历程中经典的地理形象。大致来说,乡土文学存在三个传统:“从鲁迅到韩少功是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形成的启蒙传统;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是以知识分子立场、人性审美形成的诗化传统;从赵树理、柳青到高晓声、路遥是以农民立场、现实视角形成的“史诗”传统”[1]。显然,梁庄是被置于城市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的、由拥有阐释权的知识分子建构出来的地理形象,这直接继承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对“乡土”的审美认知。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是一个非线性的综合体,而三个写作传统的问题在于都不约而同地将乡土以文学的方式隔离化、陌生化,将其凝缩为单向度的笼统“乡土”。怎样突破以及整合三个写作传统,是当今中国乡村小说所要解决的问题。学界普遍认为《神圣家族》的出现,是梁鸿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转变,梁鸿试图以一种实验性的方法,突破乡土写作的传统,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
“乡土”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学话语,“乡村”和“乡镇”似乎都被囊括进这一概念,而很少有作家单独涉及“乡镇”这一地理空间。《神圣家族》作为梁鸿虚构叙事的首次尝试,小说中出现了“吴镇”这一新的地理形象,与梁庄系列共同形成了“梁庄—吴镇—穰县/北京”的三级地理空间。“乡镇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的落后,但是又保留着一些属于农村的味道;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向城市转变,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城市的水平”[2],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圣家族》中的“吴镇”有着一定的独特性,它不同于以往对于乡土的线性表征,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斯图亚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对表征的定义是:“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它有两个相关的意义,其一是指表征某物即描述或摹状它,通过描绘或想象而在头脑中想起它,在我们头脑和感官中将此物的一个相似物品摆在我们的面前;其二是指象征、代表、做什么的标本或替代。”[3]16表征有着指称和外延两重意义,乡土在指称上首先是一个被划分出的行政地区,而外延则更多地依赖于书写者的想象。关于乡土的表征,则进一步地影响到了文化身份的定位。文化身份是主体的一种认知方式,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至少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被给定的、集体的身份;另一种则认为文化身份“不是本质而是定位”[4]212,即每一个主体都是具有各种不同的、充满矛盾的历史与文化的体验。《神圣家族》以第二种思维方式,在宏伟的叙事结构里,通过十二个短片故事讲述了特殊地理空间中复杂的生命形态与不同的断裂经验,折射了关于“乡镇”的不同文化表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将结合斯图亚特·霍尔的族裔散居文化认同理论重新定位吴镇人的身份,分析梁鸿对于乡土中国未来方向的探索。
一、“穰县/北京”:传统的乡村表征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神圣家族》中具有象征意味,它是一个抽象的地理空间,不仅是农民许家亮扬言要出去打工时的最终目的地,并且还是《到第二条河去游泳》中的“她”在水泥大河中自杀后希望尸体最终漂流到的地方。北京作为一个大城市,是吴镇人希望脱离贫困和追求富裕的地理空间,吴镇的人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都希望能够去到北京。“穰县”在《神圣家族》中虽然不及北京,但仍然是比吴镇高一等级的行政地区,并且还有一个师范学校。在这些从吴镇来的毕业生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留在穰县教书,大部分人只能重新回到了吴镇谋生。从“穰县/北京”来看“吴镇”是典型的后殖民语境中的东方视角,乡镇和乡村共用一个文化身份,吴镇与其他村庄一样,由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区域规划混乱并且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作者在《神圣家族》全篇中继续继承了梁庄系列中对于环境恶化的重视。白天热闹的集市留下来的动物内脏和腐烂的青菜水果,使吴镇空气中一直有着淡淡腐臭气,养育吴镇的湍水也早已经变得破败不堪。《许家亮盖屋》一篇中出现的外地记者正是用这种传统的乡村表征看待吴镇上的人,但在这篇故事中,没有再去将这位记者塑造成曝光农村现状的“正义者”形象,而是着眼于许家亮与记者两种观念的冲突。孤寡老人许家亮的房子已经破旧不堪,所以他开始造起地屋,这个行为在其他的人看来是非常荒谬的,吴镇的人都像看稀奇一样来看许家亮的地洞。作者从内聚焦的视角出发,这样描写许家亮的地屋:“下台阶,到地室里,溜光的青色水泥地面,空间开阔,从地面到顶上三米多高,四周的角落处许家亮都用水泥、砖头加固过,整个空间方方正正,足有一百多平方米。几盏大瓦数的灯泡闪着光,照得这个地屋明亮亮的。”[5]79许家亮对自己的地屋颇为满意,他在挖地洞的过程中似乎找到了自己丧失已久的生命力,但是在记者的眼里,报道却成了:“农民被迫害几近成狂,住地洞如上天堂”[5]83。无论许家亮怎么向记者解释,记者都始终将许家亮看作为麻木的农民,最后因为记者的报道,地屋被填平,许家亮只能站在坡底上,声嘶力竭地怒骂,这是对于启蒙视角的质疑。
当“穰县/北京”存在时,吴镇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表征,但梁鸿没有将重心放在书写对于乡镇(村)愚昧和落后的印象,而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城市主体是如何作用于乡村的动态过程。《圣徒德泉》《那个明亮的雪天下午》《明亮的忧伤》三篇构成了互文性,还原了少女海红的完整形象。在《那个明亮的雪天下午》里,海红计划借看望清飞来与良光的约会,却没有想到在回程中遇到了城市里来的人,在这些人的逼迫下,海红与良光的嘴唇碰到了一起,悄然之间挑起的性欲让海红羞耻地想到了小便,排泄与欲望混杂在一起,反映了海红刚开始对城市的拒绝。在海红和良光纯洁的感情遭到破坏以后,外地打工的清飞开始经常在来信里对海红描述自己的生活,两人之间的距离又悄然拉近。虽然海红清楚地明白与清飞的生活有着一段距离,但她十分享受读清飞寄来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时别人羡慕的眼光。清飞回到吴镇以后,海红对清飞是模糊的态度,任由清飞在她面前脱下长裤又在她的口腔里不断搅动着舌头,但这时的海红却再没有再想起小便。《圣徒德泉》中的德泉视角对这个场景有着更为清晰的描述:“海红眼睛一会儿紧闭,一会儿茫然张开,不知道是在受难殉道,还是在沉醉和享受”[5]41。《明亮的忧伤》里交代了海红最后的归宿,“这一个班,只有海红一个人重又读书,离开乡村,到了大城市”[5]260。作者没有表明态度,也没有融入情感,仅仅叙述了三个看起来不连续的故事,将零碎的海红形象呈现,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行拼凑,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开始就以启蒙视角来塑造海红的写法。
二、“梁庄”:欲望的围城
《神圣家族》中的“梁庄”继续沿袭了《中国在梁庄》中那个贫穷落后的乡村形象,并且在吴镇周围还有很多像梁庄这样的村落,它们都是被压抑的场所。《漂流》一章以轮椅上四处滑动的老太太为叙事视角,勾勒出吴镇在繁忙日子里的角角落落。那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从诊所门口被推到张五家门口,张五家又把她推到兽医家,就这样来来回回,这位痴呆老人最后来到了十字街的正中央,天真而不知所以地看着所发生的一切。屠夫的刀声、货主的叫喊以及将道路堵住的丰田车使吴镇在赶集时热闹非凡,这一天各个村庄的留守妇女都会好好打扮,约上同伴带上孩子早早来到吴镇,逛街游玩一天以后再骑车回家,并且隔天再来。“梁庄”的存在,使吴镇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地理空间。
《美人彩虹》《杨凤喜》中彩虹的老公罗建设和杨凤喜是对于吴镇来说的他者,他们来自吴镇周围的小村庄,这两位原本不属于吴镇的男人都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罗建设的家在吴镇周围一个偏僻的村庄里,但是罗建设来到吴镇后却没有表现出自卑,“罗建设总是付出更多的努力和镇上的人们交际。吃饭、喝酒、泡妞、样样投入,长得也体面,有着吴镇人很少有的温文尔雅和狡黠聪明,是很耍得开的人”[5]115。但是,吴镇人并不喜欢这个努力融入吴镇的人,“他就好像是一个透明的双面人,他一本正经的时候,就是他最假的时候”[5]115。吴镇混杂暧昧的气息对小村庄来说,藏着更大的欲望。罗建设没有珍惜这段与吴镇人的婚姻,他因为偷情而摔断了腿,但他又得继续靠着彩虹的生意享受宽裕的生活,所以即使他厌烦身材早已走样的彩虹,又不得不每次都刻意逢迎彩虹。罗建设的欲望还不止于此,他幻想在彩虹的生意逐渐壮大以后将其占为己有,他想“把那个躺在床上的老女人光裸而丑陋的身体扔出去,带着娇娇和兰兰,骑着马,一路狂奔,跑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5]134。
梁鸿在《神圣家族》中对于杨凤喜的描写,体现的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与乡村知识分子的欲望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杨凤喜来自农民之家,在父亲经常说的“大小是个官儿,强似卖水烟”[5]178的教导下长大,一路读书到穰县的师范学校,最后来到吴镇教书。杨凤喜不同于罗建设天生的社交能力,他有着来自乡村的自卑心理,想要通过当官摆脱掉这种资本,他不惜抛弃了女友张晓霞,与吴镇党委书记的女儿周香兰结婚,最后周香兰的父亲到处奔走打听关系,杨凤喜也还是没能当上官。吴镇对于杨凤喜来说像是一个自设的围城,就连他在网络上的暧昧对象都是来自隔壁药铺家的王秀勤。他坚信自己的才华绝对不止于此,甚至拒绝领那份教师的工资,但是除了这个比小村庄好一些的吴镇,杨凤喜无处可去。
《神圣家族》中大部分的乡村知识分子都是出身于梁庄一样的小村庄,在穰县读完师范学校后被分配去当教师。“他们大多都想办法从村庄调回到镇上,结婚生子过日子。不管在哪个村庄教书,都会努力在镇上买个小房子,每天傍晚下课后,骑着摩托车奔突十来里地,回到镇上。”[5]258吴镇成为这些来自周围村庄的人心里对于尊严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能在吴镇买房,生活就能还算得体面。虽然吴镇比周围的小村庄的条件好一点,但是他们却去不了比吴镇更好的地方。不管是罗建设还是杨凤喜,他们都急于摆脱来自“小村庄”的文化身份,融入吴镇,甚至比吴镇人活得更像吴镇人。吴镇是他们内心欲望的催化剂,但却满足不了他们更多的要求,最后他们只能困在这个小天地里,婚姻与事业都面临失败,这不仅是个人的选择,也是自身的欲望悲剧。
三、“吴镇”:疏离的困境
不同于罗建设和杨凤喜,美人彩虹、圣徒德泉、少年阿清是在吴镇土生土长的人,“乡镇”这一文化表征在他们的故事里又有了不同的意味。美人彩虹将吴镇当作一个封闭生活圈,圣徒德泉是吴镇生活的保卫者,而少年阿清则是眷恋故土美好的人。
彩虹经营着一家名为“彩虹洗化”的店,她年轻的时候有着丰满的身材和傲人的姿色,与来自周围村庄的罗建设结婚,但罗建设一次又一次的出轨,让彩虹最终对这段婚姻彻底失望,彩虹一方面从心里厌恶罗建设,另一方面又把直接罗建设当作自己夫妻生活中的服务者。比起丈夫罗建设,洗化店货架上的货品更能吸引彩虹。力士香皂的腻香、舒肤佳的皂香、薄荷味和绿茶味的牙膏还有蚊香片和不知道哪来的皮革味,“无数的味道,跳跃着,争先恐后地拥抱着彩虹,等待彩虹的鼻子、身体来吸收它们”[5]119,给予彩虹不可代替的安全感。彩虹通过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但是她却哪里也不去,甚至品牌公司邀请彩虹免费旅游,她都不愿意踏出吴镇,每次去外地进货,都是直接到目的地选货,然后掉头返回。这并不是彩虹作为本地人与吴镇产生了亲密的感情,而是因为她更在乎那个只属于自己的四方天地——彩虹洗化店。更确切地来说,彩虹与周围人已经隔绝,从年少时吴镇初中的女神变为成天在日化店坐着,日益圆润的中年女人。吴镇的人一点也不理解她,把她当成一个谜,彩虹也总是放在以旁观者的态度看着店里的客人,不管是顾客还是找她拉家常的人,彩虹对于他们都是不屑的。
美人彩虹是主动疏离吴镇,而德泉则是被吴镇疏离的。德泉认为他是吴镇的守护者,但是在吴镇人的眼里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甚至连精神都有一点问题的人,作者似乎有意地将德泉塑造为一个吴镇的“堂吉诃德”,他总是像骑士一样保卫吴镇的人,却又总是闹笑话。夜晚的吴镇像是德泉手里的棋盘。“他看到吴镇的人摆脱掉白天罩在身上的壳,精神抖擞,竭力去到达白天无法到达的地方,做白天无法做的纯情的人”[5]48,德泉已经像是一个独立于吴镇的人,听着吴镇的声音,洞察着吴镇的一切,德泉发现了吴镇这几年发生的变化,他作为在吴镇生长的人,敏锐地感受到吴镇这几年朝着不好的地方发展,他意识到了这个小镇发生了问题,所以想去保护,但是他作为一个被人当作疯子的流浪汉,这一切又是荒诞的。
少年阿清是长大以后离开吴镇的人。小时候他为了阻止吴保国砍树,他就爬上那颗大槐树,他在树顶上目睹了陌生又充满丑恶的吴镇。他看见李秀娥向路人卖弄姿色,二叔与路寡妇偷情,阿花奶奶的虚伪与丑陋。阿清对他从小就生长的地方感到十分失望,从树上下来以后,阿清变成了认真学习、乖巧懂事的好学生。长大后,阿清去了南方,离开了吴镇,从阿清奶奶口中得知阿清并不经常回来看她,但是去到南方的阿清,也没有栖息之地,他对吴镇感到失望,但他对城市来说又是一个被疏离的异乡人。
四、结语
“地方文化的轮廓,建立在个体释放各种不同层次的原始记忆、情感或依恋的基础上”[6]237,梁鸿在《神圣家族》中为说不尽的“城与乡”题材提供了关照的多元性,赋予“乡土”一个断裂、零碎的文化身份,这也侧面证明了这个古老、悠久的生命共同体正在经历着新生与蜕变的痛苦,即将迎来新文明、新生态的乡土中国。正如斯图亚特·霍尔将族裔内部视为混杂、矛盾和动态的,梁鸿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乡镇的特殊,它的社会生活、情感结构以及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通过表现这一特殊地理空间中不同的生命形态,完成乡镇的多重表征。另外,梁鸿还创新性地使用西方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和文本的互文性,在荒诞和意识的流动中,使读者对吴镇陌生化,在文本的互相补充中,慢慢呈现出不同视角的对话,特别是在不同的故事单元里,从不同的叙事视角出发,形成复调,逐渐充实人物的形象与所处的环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启蒙视角的惯性带入。
诚然,《神圣家族》与梁鸿之前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这些非虚构作品相比,艺术手法还略显生疏,作者本人也未能完全的摆脱传统的视角,彩虹、周香兰作为主要的女性形象,都是丰乳肥臀带有生殖崇拜色彩的女性。《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实际上是中国版《树上的男爵》,但是西方社会那种迷失自我、价值丧失以及荒谬的生存状态却不能完全与中国的乡村背景贴合。文学是语言的载体,而语言又一定会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知识背景紧密相连,因此梁鸿继续延续了对于乡村知识分子的现状的关怀,揭示他们的多余和空虚,但也进一步地在《好人蓝伟》这一篇中给出了与自己和解、与命运和解的解决方案。“吴镇”的出现不是为了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文学地理形象,而是在乡土书写中,已经迫切地需要打破乡土的整体性,摆脱“把一种想象的一致性强加给分散和破碎的经验”[4]210的写作模式。乡土书写方式的现代转换远远没有终止,梁鸿作为一名学者和作家,本着文学对生命真切和细腻感受的原则,反思了写作立场和流行文学话语,为乡土书写提供了新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