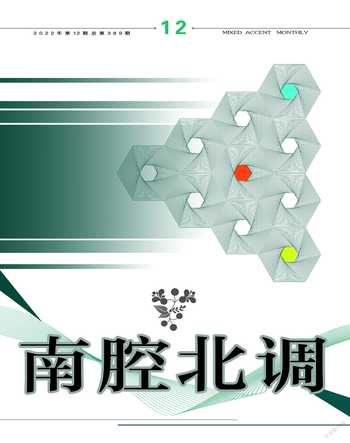葛亮《北鸢》与徐则臣《北上》的历史书写比较
2023-01-11罗欣怡
罗欣怡

摘要:葛亮和徐则臣这两位同年出生的70后作家近年来都在书写历史的道路上作出了许多努力。本文以《北鸢》《北上》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本细读与对比研究的方法,指出《北鸢》《北上》这两部作品的历史书写,不仅均以家族史的叙述方式将目光集中于人的日常生活,而且都采取了他者视角介入、多重空间生产、整体意象塑造的方法来建构历史。结合具体文本及两位作家的成长与创作经历,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二者历史书写的差异、价值与不足,希冀为70后作家的历史书写研究提供更多样的研究角度。
关键词:葛亮;《北鸢》;徐则臣;《北上》;历史书写;70后作家
葛亮的《北鸢》试图在民国历史风云的变幻中探寻一段个人的被藏匿的历史,徐则臣的《北上》则以运河勾连起时间与历史,探求长埋地下被隐藏着的历史。葛亮的《北鸢》被陈思和教授评为一部“民国野史”,徐则臣《北上》的腰封上则写着“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对于这两部作品作出野史或秘史的评价反映了这两部作品中蕴含的特殊历史形态与历史意识,而这种特殊的历史书写既来源于作家的个人经验,反映出各自的创作特色与历史意识,又不约而同地映射出70后作家在認识与书写历史时的某些共性。
一、历史书写的形态与形式
(一)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书写
在葛亮的历史书写中首先呈现出特殊的形态——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书写。其在《北鸢》自序中提道:“这段生活,事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北地礼俗与市井的风貌,大至政经地理、人文节庆,小至民间的穿衣饮食,无不需要落实。”[1]在历史学的视阈下,饮食与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葛亮自称对于饮食的书写是“以食物喻时代,也是由平民立场看历史兴颓,林林总总,万法归宗于民间”[2]。从日常饮食洞见时代背景,这一特点早在葛亮的《朱雀》中就可见一斑。程忆楚的哥哥程国忠用报纸包着她喜爱吃的黄酱卤鸭舌,那“油浸浸的报纸原来是元旦那天的《人民日报》,上面有很大的社论标题,夺目的黑体是赶英超美四个字”[3]。简单的一个细节就将饮食与时代勾连在一起。在另一个情节中,程国忠拿报纸将家里吃剩的汤渣装了准备倒出去,母亲程云和却叫住他,把报纸抖开并把报纸里里外外看了一遍才放他出去,原来是“要查看清楚报纸上有没有印着主席的宝像”[4]。这一与饮食密切相关的细节不仅凸显了程云和谨慎的心理,更重要的是映射出“文革”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时代背景。《北鸢》中对饮食的描写也是延续于此。仁桢替二姐与范逸美运送钱财及药品的地点是在她最常去的老字号点心铺永禄记门口,而承载这些钱财与药物的则是一个点心匣子,结合后文对范逸美身份及其地下活动的揭示,食物与历史又一次巧妙地结合。《北鸢》《朱雀》中的历史大多只是日常生活饮食背后的衬景,无论社会历史如何变化,人的饮食也必须进行,但在饮食的繁简乃至礼节的变化中却也能窥见历史与时代的影响。
徐则臣曾谈及他对历史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看法,认为“即使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即使有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跟我们息息相关,也要通过我们的日常细节和内心反映出来。”[5]在小说《耶路撒冷》的开头,徐则臣就通过书写日常饮食的细节性变化来反映故事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的变化。小说中老何为初平阳熬制了鲜美的鱼汤,他在谈到自己的体会时说:“烧鱼汤关键在火,用柴火,该大时大,该小时小。说了你也不明白。你们这辈人,不会再用柴火煮饭烧汤了。”[6]鱼汤固然可以表现老何内心真诚朴素的情感,但更重要的是,老何提及的青年人不会用柴火煮饭这一细节,既反映了不同代际生活背景上的差异,又表现了某些传统生活方式逐渐被现代社会“淘汰”的现实。徐则臣后来在《北上》中也借人物之口说道:“我不从道理上去理解,而是从故事、细节,从血肉丰沛的运河边的日常生活去理解它。”[7]这进一步显示出作者对宏大历史背景中人的日常饮食生活的关注。小说《北上》中谢平遥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曾为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安危担心,甚至仿佛自己也成为逃犯,“好在造船厂旁边有家面馆,隔三岔五早上去吃碗面,热乎乎地下了肚,这一天才能稍稍踏实一点儿。”[8]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被作者写进一碗面中,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人还是要穿衣吃饭,这一细节恰恰体现了作者的巧思。书中孙宴临给谢望和下厨时也说:“你可以满世界乱窜,但胃是有祖籍的,找对了地方,它就会及时地告诉你。”[9]徐则臣笔下的身体对饮食的诉求不仅表现为一种生理反应,更表达了人的潜意识里对故乡的归依,对自身历史的溯源。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饮食的记述,如谢平遥对小波罗吃面及喝茶的观察,路途中早餐店老板娘的吆喝等。日常生活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词语,除了饮食,它还涵盖了民风民俗、人际交往、生计等方面。除却对饮食的特别关注,这两部作品也多少展示了民情风俗,如《北鸢》中文笙抓周的习俗,《北上》中船民结婚的礼俗等,都是具有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
(二)家族史叙述形式
徐则臣与葛亮都以家族史的脉络与框架进行历史书写,这种将家族与历史缠绕在一起,以家族史的形式书写历史的做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已较为常见。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从母姓“茹”字探寻家族起源,不仅是对个人历史的追溯,也是对中国历史进程中民族与姓氏发展变化的考察。陈忠实的《白鹿原》描写家族之间的斗争,试图构建新的历史讲述方式。郭冰茹认为,“家族史之所以不同于革命史,就在于它通过一个或几个家族中几代成员的命运遭际来书写家族的兴衰,折射历史的变迁。同时,由于借助‘家族这一社会空间,家族/地方的文化心理、风土人情、伦理秩序、道德修养也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因而家族史又往往与地方志相杂糅。”[10]
《北鸢》《北上》的历史书写都采用了家族史叙述的形式,但几乎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北鸢》中的家族故事以作者葛亮自己的家族为参考,其中毛克俞的形象以作者祖父葛康俞为原型创作。小说以昭如、文笙、仁桢的视角书写了家族内部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财权纠葛、情爱轶事等,并主要通过文笙与仁桢的命运沉浮展现了家族的变迁与历史兴衰,同时借助于对襄城、天津、上海等不同空间的书写,展现了民国时期各地独特的文化氛围与风土人情。可以说,《北鸢》的家族史叙述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并没有浓墨重彩地讲述大家族的兴衰起落,而把笔墨花费在描写家族的日常生活之上。正如陈思和评价道:“《北鸢》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民国野史。”[11]《北上》中家族史叙述的特殊性在于其碎片化与断裂化特征。小说选取的是几个家族跨越百年的两个时间点,重点不在于勾勒家族的变迁而是强调家族史的断裂,从而进行家族史的溯源和“生成”。谢望和与邵秉义等人只有通过运河中挖掘出的文物及家中流传的老物件,才得以发现百年之前与谢平遥等人的联系,才能勉强勾勒出各自的家族史。因此,《北上》中的家族史不仅与运河史紧密相连,运河史更是建构家族史的路径,这体现出徐则臣在历史书写上的独特构思。
二、历史书写的多种方法
(一)他者视角介入
“‘他者是群体得以自我界定的必要的衬托体。”[12]20世纪以来的“他者”概念常常与西方的话语霸权相联系,而在《北上》《北鸢》中,“他者”作为一种独特的视角介入小说,丰富与扩大了小说历史书写的视野。《北上》中的“他者”显然指意大利兄弟小波罗与费德尔。义和团成员战斗时手持刀剑仿佛进行舞蹈表演的荒谬,打破了费德尔对中国的浪漫幻想,战争的残酷以及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异化与伤害,也通过费德尔的自述表现出来。小波罗怀着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幻想来到中国,他赞同中国人用筷子进食的方式,喜爱中国美食与茶叶,似乎与谢平遥等人一同融入运河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但小波罗看待中国的方式仍然充斥着浪漫的幻想,其作为西方人的傲慢也时常不自觉地显露出来。当他试图进入马可波罗描述过的府衙时,即便只能看到朱红的高墙,他依然要声称“反正我信了”[13]。当他看到运河上挤满各种船只时,他兴奋地不停拍照、赞叹,甚至像猴子一样缠在船的桅杆上,而谢平遥坐在船头的椅子上却觉得这些船的吵闹声甚至要把运河烧开。小波罗与谢平遥两种不同的视角与感觉,显然丰富了运河的故事。
《北鸢》中“他者”的出现也同样重要,尤其是猶太人叶雅各这一形象的设置寓意独特。“雅各”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他以一碗红豆汤买下了哥哥的长子权并用计谋骗取了父亲对他的祝福。小说中叶雅各刚出场时还是一个勇敢善良的犹太男孩,当他表示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时,他表达的是对这一名字中“欺骗”含义的蔑视。但在故事结尾,长大后的叶雅各却以欺骗的方式卖给永安一批次货,最终导致了永安破产。因此,“叶雅各”这一名字也就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永安面临破产时,文笙曾寻求雅各的帮助,但雅各称自己的行为不过是文笙教他的“顺势而为”的道理。回到小说中文笙教雅各放风筝的情节,文笙提到放风筝要顺势而为,雅各却认为“可你到底还是用条线牵住了它。说顺着它,却又跑不得。”文笙只好轻声辩驳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线就是风筝的规矩。”[14]显然,俩人对“顺势而为”的理解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偏差,文笙所认为的“顺势而为”是有限度、有规矩的,雅各则认为顺势与线的牵制是互相矛盾的,顺势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两种理解的差异其实正代表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
在《北上》《北鸢》中,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的交集既有在战争中的认知,也有日常生活里的来往,西方人的视角与中国人的视角之间所产生的差异,使中国文化展现得更为全面,“他者”视角的介入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入挖掘或反思。《北上》中以费德尔的视角道出了中国人的“本性”,“他们勇猛又怯懦、精明又愚昧、真诚坦荡又虚伪投机、吃苦耐劳又溜奸耍滑、正大庄严又猥琐乖张、秉持公心又贪图私利、热情友爱又冷酷阴险、目力长远又狭隘短视等。这些优劣完全背反的品质,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他们照单全收,却又和谐地熔于一炉,装进同一个身体里。”[15]这一概括不可不说是作者徐则臣借助“他者”视角完成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性情的反思。《北鸢》中雅各与文笙对“顺势而为”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两种选择,雅各以个人利益为先,致使永安破产乃至自杀,文笙则受到内心责任感与情感的驱使,收养了永安的孩子。文笙与雅各,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后者则代表了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文笙的行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对信与义的强调,对情意而非利益的抉择,正如金理所言,“风筝的主心骨正是人们心中‘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守。”[16]葛亮借助雅各这一“他者”形象的介入,表达了对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总之,徐则臣与葛亮在历史书写中都不约而同地引入“他者”视角,试图突破人物思维的局限,以更加理性的角度看待中西文化及思想差异。
(二)多重空间生产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空间是富含着社会性的,它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脉络,同时叠加着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辩证,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被其所生产。”[17]《北上》《北鸢》通过对社会关系与历史背景的书写,促进了文本空间的生产,塑造了各自极为鲜明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前者以北京和运河为代表,后者以襄城和民间为代表。
徐则臣的《北上》通过对运河及沿岸日常生活的书写塑造出了独属于运河的文化空间:小波罗兄弟俩对马可波罗足迹的追寻,谢望和和邵秉义等人的运河生活,运河文物被一一挖掘……《北上》将20世纪初的运河故事与其“前世”和“今生”连接在一起,人物故事以运河为中心延伸开来。因此,运河是复杂的,是跨时代的,具有丰富的历史人文价值和深厚的精神意蕴。徐则臣在《局限与创造》一文中写道:“这些年我用力主要在三块:一是关于北京;二是关于河边的故乡;第三块,基本是天马行空的虚构旅程。”[18]《耶路撒冷》的开头讲述了在北京读书的初平阳回到花街的故事,北京与花街这两个地理空间在该文本中产生交汇,而到了《北上》,连接北京与花街的,正是运河。北京作为谢望和的高祖父谢平遥待过的地方,对谢家人来说代表的是理想之地,因此谢望和的祖父自称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自己的儿子来到了北京。谢望和的堂伯也因为没机会去北京而心存芥蒂,“你以为我不想去北京?你以为这里的人不想去北京?不为要去那里过日子,而是因为生活在河边,从小就知道这条河一直流到北京,那是终点,都想去终点看一看,流过清江浦的水流到那里,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19]运河指示着世界的方向,成为花街人通往世界的指南针,北京作为运河的终点因而成为了理想空间,饱含了人的理想情怀。然而北京也是现实的生活空间,谢望和从北京回到花街后不禁感叹,“北京天天忙得脚不点地,电话、微信、短信、邮件,各种提示铃声,一天到晚就没断过响,好像我是多重要的人,被全世界人紧急地需要着。”[20]因此,北京这一空间既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既代表着可感的繁忙,又蕴含了对理想的憧憬。
《北上》将时间刻意地放置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北鸢》却并非如此。《北鸢》虽然多次提到了战争,但并没有刻意强调时间节点,其主要塑造的是不同地理空间内迥然不同的历史文化气息,并由此反映独特的历史背景。襄城是葛亮所虚构的一个理想之城,这里的人大多重情重义,民风淳朴,俨然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聚集之地,如陈思和所言:“葛亮把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文化精神弥散在整部小说的书写空间之中,传统文化的因子在北中国的普通人家庭均有丰富的蕴藏。”[21]四声坊内扎风筝的龙师傅几代人与文笙的恩遇之情,郁掌柜劝谏文笙时的忠厚善良,文笙动用家产援助永安和收养孤儿的义举,乃至昭德、言秋凰之死的决绝与凛然,这些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品质让人动容。诚信、仁义、忠厚、孝顺这些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维系着文化的传承,由此,小说文本开拓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空间——民间。
空间的塑造显然不只是这两位70后作家的独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王安忆的上海早已有之,空间的塑造几乎已成为作家创作与发展的立足点。单纯的乡村或城市地理空间的生产往往依赖于作家个人的生活经验,而文化空间的塑造则更需要作家的虚构与想象,更考验作家对文化与历史的反思意识,因此多重空间的生产尤其是文化空间的生产几乎成为作家历史书写时不可绕开的路径。
(三)整体意象塑造
有论者在研究曹禺戏剧的意象时提出“整体意象”这一概念,认为“整体意象”是指“在戏剧中起到统摄或者核心作用的意象”[22]。而在《北上》《北鸢》这两部小说中,徐则臣与葛亮则分别塑造了“运河”与“风筝”这两个贯穿全书、具有核心作用的整体意象。
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中说:“审美的意象是指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它能引人们想到很多的东西,却又不可能由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把它表达出来,因此,没有语言能完全适合它,把它变成可理解的……”[23]河流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早已“泛滥”,但将河流作为审美意象进而关注河流的象征含义与文化价值,甚至将河流作为全书整体意象的还并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借着寻根的思潮追逐河流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可以说是对河流、文化、历史的深度挖掘,而徐则臣《北上》的独到之处,在于充分挖掘了运河本身的特殊性与文化价值,使“运河”这一整体意象成为作者历史书写绕不开的坐标。京杭大运河属于人工开凿的运河,它的诞生与人、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关,河流的流动与变化隐喻了时间的流转,见证了历史的兴衰。如今,运河有的河段已成为遗迹,有的河段还在运行,因此它在书写历史变化与展现时代印记上有着天然优势。
“风筝”是《北鸢》中的整体意象。首先,它贯穿了小说全篇,联系着小说人物与故事情节的发展。《楔子》里年迈的文笙到了自己的生日,依然去四声坊买一只虎头风筝,这既是一种习惯,也是与父亲和友人之间深含情感的约定。文笙因放风筝与妻子仁桢结缘,认识了叶雅各,还依靠风筝在战争中解决危机,顺利生还。其次,风筝具有强烈的隐喻性,以其独特的构造隐喻着人的命运。郭敏曾在《瓶湖懋斋记盛》中感叹:“风鸢听命乎百仞之上,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24]《北鸢》特意突出了风筝的隐喻性,风筝在天上的飘摇仿佛是时代中人的漂泊;风筝有着线的牵引,命悬一线或一线生机也成为人乃至国家命运的隐喻。另外,风筝作为一种民间手工艺在社会文化中处在边缘位置,更代表了一种边缘化视角。与此对应,《北鸢》的叙述视角是女性的、少年的而非男性的、成年的,是民间的而非官方的。最后,《北鸢》的名称来源于《南鹞北鸢考工志》,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喻,风筝不仅代表着一件物品,更代表了一种传统技艺以及善的精神。
从整体意象的运用上来看,两位作家都独具匠心,选择了具有丰富内蕴的意象并善于运用其中的隐喻性来进行独特的历史书写,反映个人的历史意识。相比而言,徐则臣《北上》中运河的意象因为饱含时代的变迁更具有历史反思意识,而葛亮《北鸢》中风筝意象的运用则因为站在民间立场上而更凸显传统文化的精神品质。两个整体意象虽然有着不同面向,但都试图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体现出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深度思考。以独特的整体意象的塑造作为观察历史的特殊视角,亦成为这两位作家书写历史的共同方法。
三、历史书写的价值与反思
葛亮与徐则臣小说中历史书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通过对特殊历史形态即日常生活中饮食的书写,表现出了各自独特的历史观念,历史书写成为其创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得其创作展现了更丰富的面貌;其次,二者在历史书写的形式与方法上都提供了较为明显的参照,为整体研究70后作家的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个研究入口;最后,作为当代中国70后作家中的两位代表,他们的小说既表现了独特的童年与成长经验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又体现了来自前辈作家与文学思潮的影响,為研究70后作家写作资源、审美经验、艺术特点等方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葛亮与徐则臣虽然在《北鸢》《北上》的历史书写中都以家族史叙述的形式,注重对民间日常饮食生活的刻画,在书写方法上也都运用了“他者”视角、空间生产和整体意象,但其中所显示出的历史意识却有差异。岳雯曾指出,“倘若葛亮能以小说人物的职业身份为突破,掀起民国时期五金业乃至整个商业的变迁史的一角,由此更进一步,以经济见证时代,想来就令人兴奋。”[25]然而,这一设想不仅只会让《北鸢》可能成为翻版的《子夜》,也不符合葛亮的历史观念。“因为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生活的常态之中,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反高潮的运作。”[26]葛亮的历史观念是有其独特性的,在变革与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他显然更关注历史褶皱间的人与事,书写人的日常生活,强调在变动中恒常的传统文化与民间精神,王德威在台湾版《北鸢》序言中认为其历史情怀表现出的独树一帜大概恰在于此。
相比于《北鸢》,《北上》的历史书写显然更具有史诗性、反思意识与现实意义。船民邵秉义父子生活观念的冲突鲜明地反映出这种反思意识,儿子星池想搬到城市居住,因为当他面对岸上飞速行驶的汽车火车时,他产生了被世界遗弃的感觉,而父亲的观念则是“人还是得用两条腿走路,再慢你也不能把两只脚砍了改装风火轮”[27]。星池被遗弃的感觉以及邵家父子观念的冲突,反映出青年一代面临的历史困境,即坚守过去的传统还是跟随时代的潮流。进一步来看,这种冲突不仅指向个人的前途命运,更指向运河及其历史面对时代变化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孙宴临曾这样反问:“GDP可以让你每天都能看见一条不息的长河在流淌吗?当然,砸出足够的钱,别说一条河,科罗拉多大峡谷也可以挖出来,但你能挖出一条河的历史吗?你能挖出它千百年来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吗?”[28]借人物孙宴临的这番话,徐则臣显示了其个人的历史情怀与责任意识。
曾有学者认为70后是尴尬的一代,甚至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但从《北鸢》《北上》以及两位作家之前的《朱雀》《耶路撒冷》来看,葛亮与徐则臣在经历了早期创作对个体经验的依赖后,也在有意识地书写历史并反映个人独特的历史意识。如果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还是自我书写,是为了展现同代人的精神成长史,那么《北上》则是为故乡边的运河而写,探寻运河被遮蔽的历史。葛亮的《朱雀》以神鸟朱雀为南京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写家乡南京的历史与精神底蕴;《北鸢》则从家族史写起,用意于历史里的个人。徐则臣从花街出发,从河流汲取精神力量,以家族史书写历史;葛亮从南京出发,从民间汲取精神力量,同样也以家族史书写历史。可以发现,故乡空间塑造、个人精神发展与家族史溯源,成为这两位70后作家书写历史时共同走过的道路。以此为历史书写的考察点,其他70后作家的小说如付秀莹的《陌上》、吴文莉的《叶落长安》等也体现了类似的特征。葛亮与徐则臣的历史书写背后,也体现了他们试图还原历史丰富面貌的努力。前者似乎已经找到了自身历史书写的精神来源——民间,并试图写出具有传统文化价值的民间精神的传承与发展,然而其历史书写在宏观上的视野还略显狭窄,人文气息与理想气息过于浓厚,反思意识不足。后者似乎具有更加鲜明的反思意识,在历史书写的技巧上亦显得尤为突出,但作者似乎并没有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找到恒常性的精神传统,仍处于“破而未立”的阶段。
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提出了“作为经验的艺术”,指出了经验对于自我和对象的意义。经验类型及其来源有诸多区分,有与个体感官相关的日常生活直接经验,有与知识教育文化学习相关的间接经验。葛亮与徐则臣的早期创作,鲜明地受到个人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的影响,由于两位作家童年经验与成长经验的不同,他们的创作内容也表现出了明显差异。70后作家的出生地与生长环境已经出现了显著变化,一类是出生于乡村或小镇的,如徐则臣、付秀莹等,由乡村到城市的人生轨迹变化中,必然会带来城乡反差感、不适感、对乡村生活的怀念等体验,这些作家在书写城市时往往是以外来者的视角进行的,徐则臣早期以《跑步穿过中关村》为代表的京漂系列小说就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另一类就是出生与成长于都市的作家,葛亮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出生于南京,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因此其小说的故事题材和人物也大多来源于城市。比如,他的小说《洪才》虽然也涉及乡村,但人物的视角显然来自一个城市孩童。出生并成长于城市的作家或许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城市的发展变化以及城市空间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的《封锁》,写的是现代都市里情感的变异,到了90年代,王安忆的《长恨歌》里王琦瑶那传奇而又平淡的人生不仅是其个人的,也是上海的,看似传奇的经历在现代都市里已成为一个空壳,历史的变迁给城市带来的印记,似乎只有在这个城市长期生活的人才能更鲜明地察觉。葛亮早期短篇小说代表作《谜鸦》《无岸之河》也都是在讲述城市中人的情感变异与日常生活,显然,他受到的始终是城市文化的浸染。
尽管童年与成长过程中不同的生活经验在两位作家的创作中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异,但葛亮与徐则臣的创作也都体现出学院派作家身份的间接经验带来的相似影响,即他们不再单纯依赖自身经历进行写作,而是借助考据、想象、虚构等能力丰富小说的情节结构、文化意蕴、思想内涵。作为70后学院派作家,他们不仅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接受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高等教育,拥有了更加开阔的思想与文化视野,学院派的背景还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诸多理论资源和文本资源,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学院化隐然成为70后作家的某种代际特征。”[2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学院派作家的身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的无疑既有帮助也有限制,他们凭借对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与写作技巧的熟悉,创作时往往能够信手拈来或有意识地运用某种结构或技巧,但由于过分重视技巧的运用,《北鸢》《北上》也都表现出人物形象塑造与情感表达间存在隔阂的问题。
就文学史发展的脉络而言,徐则臣的《北上》与葛亮的《北鸢》显然或多或少受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写实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作品的影响。具体来说,葛亮与徐则臣虽然都注重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与以《烦恼人生》《一地鸡毛》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作品对日常生活的记录有相似之处,但其寄托于情感的态度却与新写实作家有所不同,在其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带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情感寄托。叶兆言、苏童所开创的以民国题材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是以文化中国的立场写作,葛亮的《北鸢》或许也以此为寄托,而徐则臣的《北上》则不局限于民国题材的文化想象,以现代性回溯的方式试图书写文化中国。但与新历史小说不同的是,葛亮与徐则臣他们并没有因否定历史而误入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试图寻觅被遮蔽和未被看见的历史,丰富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结 语
《北鸢》《北上》都表现了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辩证哲学思考,在其“历史”中,两位作家共性地以家族史叙事形式来书写和表现日常生活,利用他者视角、空间生产、整体意象来结构全书。得益于两位作者学院派的知识背景,两部小说在主题与叙事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脉络,其历史书写还承续了新写实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和新历史主义书写历史的形式。但两部作品中人物塑造与情感表达之间的隔膜也成为二者相同的弊端。由于童年与成长经验的不同,葛亮与徐则臣在历史书写的题材内容与历史意识上亦存在差异,葛亮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多方面展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统文化价值与民间精神,语言也更为古典;徐则臣则更擅于在乡村与都市、中国与西方等二元结构中发挥文本张力,显示出反思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魄力。
参考文献:
[1]葛亮.自序 时间煮海[M]//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2]葛亮.由“饮食”而“历史”——从《北鸢》谈起[J].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3][4]葛亮.朱雀[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221,287.
[5]杨庆祥.寻找文学的新可能——联合文学课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2.
[6]徐则臣.耶路撒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11.
[7][8][9][13][15][19][20][27][28]徐则臣.北上[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130,12,181,66,364,174,152,93,170.
[10]郭冰茹.家族史书写中的“历史真实”[J].山花,2018(6).
[11][21]陈思和.序 此情可待成追忆[M]//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12][德]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形象学[J].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2007(3).
[14]葛亮.北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201.
[16]金理.葛亮的风筝——论《北鸢》[J].南方文坛,2017(1).
[17]陈映芳,等.空间生产的政治社会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51.
[18]文艺报社,主编.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325.
[22][23]王俊虎.曹禺戲剧整体意象美学意蕴[J].求索,2006(12).
[24]金鑫.《北鸢》:风筝、命运与隐喻[J].小说评论,2018(1).
[25]岳雯.虚浮的民国——葛亮《北鸢》[J].上海文化,2017(5).
[26]葛亮.谜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223.
[29]孟庆澍.小说、批评与学院经验——论徐则臣兼及“70后”作家的中年转型[J].文学评论,2013(2).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