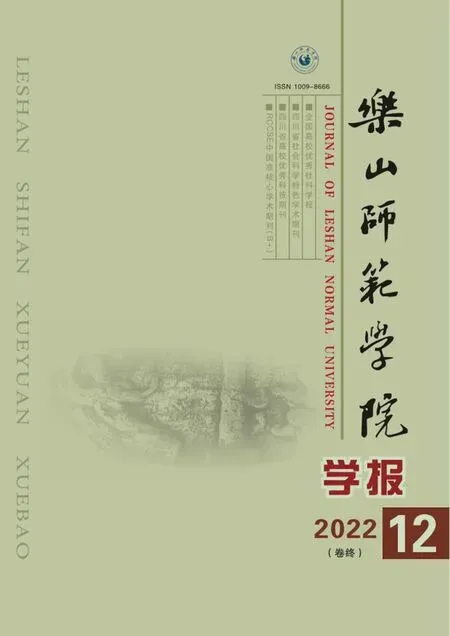论安大简《诗经·秦风》之异文及次序
2023-01-09梁利栋
梁利栋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通过对读《毛诗》与《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①(以下简称“安大简《诗经》”),我们发现:两种《诗》文本存在大量异文。学界对安大简《诗经》的异文研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在宏观上,对安大简《诗经》的异文分类,并简要分析,揭示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多重价值,比如,《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诗序与异文》[1]、《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2]。在微观上,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方法对安大简《诗经》的某一处或某几处异文进行研究,评判《毛诗》和安大简《诗经》在该处的优劣,比如,《从安大简看〈诗经·权舆〉之“於我乎”》[3]、《谈〈诗·秦风·小戎〉“乱我心曲”之“乱”及文字考释的重要性》[4]。值得注意的是,异文的优劣与文本原貌没有必然联系。结合文化语境和文本语境,我们可以比较异文的优劣,但不能就此判定在一组异文中哪一个更接近《诗》的原貌。原因有二:一方面,目前尚不确定《毛诗》和安大简《诗经》所据原本的时间先后;另一方面,亦不知《毛诗》、安大简《诗经》在传播中与原本产生的文本差异。笔者将微观审视和宏观把握相结合,对安大简《诗经·秦风》的异文进行分类研究,力求管窥安大简《诗经》异文的整体情况,进一步了解《诗》在先秦时期传抄过程中的面貌。安大简《诗经·秦风》的异文类型主要包括字句增减、章句异序、异字同义、异字异义(本文不涉及假借字、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等用字现象),笔者将从以上四种异文类型入手,对其逐一分析。
一、字句增减
安大简《诗经》的字数、句数增多或减少,与《毛诗》形成异文。
简本《无衣》存残章——“戟,与子偕作。赠子以组,明月将逝。”从放大图版来看,“逝”字的右下方有一个墨块,下面紧接着《渭阳》中的诗句。因此,该墨块为分篇符号,简本《无衣》的残章属该篇的最后一章。与《毛诗》比照,简本《无衣》的最后一章与《毛诗》第二章局部对应,两个版本都有“(修我矛)戟,与子偕作”两句,但简本多出“赠子以组,明月将逝”两句。
“组”是诗句中的一个核心意象,因而成为理解诗意的突破口。在先秦时期,“组”作为丝织品可拴系、装饰铠甲,兼具实用性和审美性。《管子·五行篇》曰:“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马衍组甲厉兵,合什为伍,以修於四境之内,谀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杀敛也。”注云:“组甲,谓以组贯甲也。”[5]《吕氏春秋·有始览》曰:“为甲以组而便,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也?以组不便,公息忌虽無组亦何益也?”[6]所谓“组甲”“为甲以组”,皆为用组系甲之义。《礼记·少仪》曰:“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幾,甲不组縢,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屦,马不常秣。”注云:“组縢,以组饰之及紟带也。”[7]“以组饰之”即以组饰甲。“赠子以组,明月将逝”这两句诗,融记事、写景、抒情于一体,以景结情,营造了一种静谧的意境,表达了同袍之间的关切之情、勉励之意。简本的两句逸诗与《无衣》的战争语境相合,深化了我们对其思想内容的认识,同时反映了《诗》所达到的高超的艺术水平。综上所述,“赠子以组,明月将逝”在《无衣》中有存在的合理性。
简本《权舆》“始也於我”“於嗟”,《毛诗》作“於,我乎”“於嗟乎”。就简本而言,“始”和“於我”(“於”是介词)都作状语,“也”是句中语气词,表顿宕。全句意为“当初,对于我来说”;“於嗟”是叹词。就《毛诗》而言,“於”是叹词,作独立语。全句意为“唉,我呀”;“於嗟”是叹词,“乎”是句末语气词。简本“始也於我”“於嗟”形成了“二二二”的节奏类型,《毛诗》“於,我乎”“於嗟乎”形成了“一二二一”的节奏类型,产生了不同的听觉效果。
综上所述,简本和《毛诗》所形成的字句增减类异文都符合文本语境,且表意基本相同。
二、章句异序
《诗经》的诗篇以句为基本结构单位,联句成章,联章成篇。安大简《诗经》的部分诗章、诗句顺序与《毛诗》不一致,形成异文。其中,以章序不同为主。
简本《车邻》的第二、三章对应《毛诗》的第三、二章。这两章是重章,《毛诗》第二、三章的最后一句分别是“逝者其耋”“逝者其亡”,表达了抒情主人公对时光流逝和生命逐渐消亡的慨叹。从“耋”(年老)到“亡”(死亡),不仅符合时间顺序,而且强化了感情。因此,《毛诗·车邻》的章次更符合诗意逻辑。
简本《驷驖》的第二、三章对应《毛诗》的第三、二章。这两章不是重章,按畋猎惯例来看,应先狩猎后游乐。西汉司马相如在《天子游猎赋》中所写天子、诸侯畋猎之事可为旁证。徐奋鹏《毛诗捷渡》曰:“首节是往狩时事。二节是行狩时事。末节是毕狩时事。”[8]307《诗经注析》也说:“这首诗三章全用赋体,首章言将狩之时,二章言正狩之时,三章言狩毕之时,脉络很清楚。”[9]360因此,按照时间顺序,《毛诗·驷驖》的章次更符合诗意逻辑。
简本《黄鸟》的第一章对应《毛诗》的第二章,第二章对应《毛诗》的第三章,第三章对应《毛诗》的第一章。该诗本事为“三良”为秦穆公殉葬。《左传·文公六年》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10]597《史记·秦本纪》说:“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11]194“车”与“舆”音近②、义同,故“子车氏”即“子舆氏”。这两处记载均按奄息、仲行、鍼虎的顺序叙述“子车(舆)氏之三子”,且“仲”表明“仲行”排行第二,说明“奄息”“鍼虎”分别排行第一、第三。《黄鸟》三章是重章,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依次表达对奄息、仲行、鍼虎的悲悯之情。姚小鸥认为,“通过《黄鸟》文本自身和相关文献记载所提供的资料,从古代礼制及《诗经》的比兴艺术和叙事规律等方面着眼,总体来看,今本三章的次序更为合理。”[12]因此,《毛诗·黄鸟》的章次更符合诗意逻辑。
简本《小戎》“蒙旆有苑,竹柲绲縢。虎韔豹膺,交韔二弓”,《毛诗》作“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縢”。该组异文虽然句序不同,但都运用赋的表现手法,交代了“竹柲”的用途、弓袋的材质和精美程度、弓的数量和摆放位置,表意基本相同。
综上所述,简本《诗经》的部分章序不合情理。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抄写者眼前有底本的情况下,安大简《诗经》的底本在章序上本身就存在问题,抄写者以讹传讹。第二,在抄写者眼前没有底本的情况下,抄写者默写时因记忆不准确致误。无论哪一种情况,这类异文都反映了《诗》文本(口述文本或书面文本)在传播中的流动性、变异性。杨玲、尚小雨认为,“8 篇异文的产生首先与《诗经》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有关,其次与抄手的疏漏有关,还与人们对诗篇内在逻辑的修正有关。”[13]前两种情况是传播者无意为之,后者则是有意为之,《毛诗》正是在长期的接受史中被不断完善,从而确立其经典的地位。
三、异字同义
安大简《诗经》和《毛诗》在同一诗句的同一位置使用不同的文字,但表达了相同的意义,形成异文。《秦风》中此类异文数量较多。
简本《车邻》“寺人是命”,《毛诗》作“寺人之令”。“是”“之”都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寺人”。《经传释词》说:“‘是’训为‘之’,故‘之’亦训为‘是’。”[14]“是”“之”可互训,是一组同义词。“命”“令”都是动词,义同。“寺人是命”或“寺人之令”都表明寺人听命于国君,起传达作用。“命”和“令”这一组异文的产生,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方面,两字形近,在书面传播中相混;另一方面,两字音近,在口头传播中相混。按王力先生的观点,“命”和“令”在上古同属耕部,故音近。《古文字谱系疏证》进一步说:“令、命本一字,后分化为二字。”“令”为本字,“命”是后起字。[15]
简本《小戎》“在彼板屋”,《毛诗》作“在其板屋”。“彼”“其”都是远指代词,作定语。简本《小戎》“挠我心曲”,《毛诗》作“乱我心曲”。简本用“挠”字,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思妇心情纷乱的样子。徐在国在分析了“挠”的词义和“挠乱”的用例后,总结道:“‘挠我心曲’,即扰乱我内心。形容人心情错综复杂,心神不定。”[4]78简本《小戎》“胡然余念之”,《毛诗》作“胡然我念之”。“余”“我”都是第一人称代词,作主语。“胡然余念之”或“胡然我念之”都运用了直抒胸臆的表现手法和疑问句句型,强烈地表达了思妇对征人的思念之情。
简本《终南》“颜如渥赭”,《毛诗》作“颜如渥丹”。“颜如渥赭”或“颜如渥丹”都是外貌描写,诗人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出秦君面色红润的样子。《诗三家义集疏》曰:“颜如渥丹,其君也哉!注:韩‘丹’作‘沰’,曰:沰,赭也。亦作‘赭’。”[16]451可见,《韩诗》作“沰”或“赭”,与安大简本同。“沰”与“赭”相通,均为“赤”义。“沰”在上古属透母铎部,“赭”属章母鱼部。鱼部、铎部阴入对转可通。
简本《黄鸟》“如可赎也”,《毛诗》作“如可赎兮”。“也”“兮”均为句末语气词,同时,起补足音节的作用。《诗三家义集疏》曰:“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注:鲁‘慄’作‘栗’,‘兮’作‘也’。疏:……‘鲁兮作也’者,蔡邕《陈留太守胡公碑》作‘如可赎也’。《隶续·平舆令薛君碑》:‘如可赎也,人百其身。’与邕引《鲁诗》合,明鲁作‘也’,与毛异。”[16]454可见,《鲁诗》作“也”,与安大简本同。
安大简《诗经》异字同义类的异文,有的与三家《诗》暗合,可以和《毛诗》相互阐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抄写者本人或所在地域的用字习惯。此外,由音近而产生的异文较多,反映了《诗》在口头传播中文本的流动性、变异性。
四、异字异义
安大简《诗经》和《毛诗》在同一诗句的同一位置使用不同的文字,表达了不同的意义,形成异文。《秦风》中此类异文数量亦多。
简本《驷驖》“象车鸾镳”,《毛诗》作“輶车鸾镳”。关于“象车”,安大简整理者认为,“‘象车’,先秦典籍或称‘象路’‘象辂’,以象牙为饰,为帝王所乘。《周礼·春官·巾车》说:‘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17]整理者分析到位,有文献可证。关于“輶车”,毛亨《传》曰:“輶,轻也。”郑玄《笺》曰:“轻车,驱逆之车也。”毛、郑二人均释“輶”为“轻”。孔颖达《疏》曰:“《冬官·考工记》云:‘乘车之轮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车,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鸾于镳,异于乘车,谓异于彼玉、金、象也。”孔氏认为,“鸾镳”与“乘车”无关,即与“玉路”“金路”“象路”无关。[18]413-414“象车”“輶车”各有所据,但联系下文“载猃歇骄”来看,“輶车”轻便,更适合载猎犬而行,故《毛诗》“輶车”优于简本“象车”。
简本《小戎》“虎韔豹膺”,《毛诗》作“虎韔镂膺”。“豹”是名词,“镂”是动词,都作定语。“豹膺”和“镂膺”分别表明弓袋正面的材质和精细程度。“豹”和“镂”这一组异文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二字音近。“豹”在上古属帮母药部,“镂”属来母侯部,药、侯二部旁对转可通,故“豹”“镂”音近可通。
简本《终南》“絅衣绣裳”,《毛诗》作“黻衣绣裳”。“絅衣”,即“褧衣”(罩衫)。“黻衣”,青黑色花纹相间的上衣。联系上文,“黻衣绣裳”与“锦衣狐裘”呼应,均为诸侯之服,象征秦君身份。相比之下,作避尘之用的“絅衣”不符合语境。
简本《权舆》“每食八【五十九】”,《毛诗》作“每食四簋”。(笔者按:【五十九】为安大简《诗经》自带之编号,“八”后脱一“簋”字。)将该诗置于周代礼乐文明的背景下观照,简本“八(簋)”似优于《毛诗》“四簋”。结合语境,该诗的抒情主人公为失意的大夫。按照周代的聘问之礼,上大夫在出使国享受“八簋”的礼遇。《仪礼注疏·公食大夫礼》在解题时说:
公食大夫礼第九【疏】《公食大夫礼》第九。郑《目录》云:“主国君以礼食小聘大夫之礼,于五礼属嘉礼。《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别录》第九。”释曰:郑知是“小聘大夫”者,案下文云宰夫自东方,荐豆六,于酱东,设黍稷六簋,又设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礼。下乃别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又云“上大夫庶羞十六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此篇据小聘大夫也。[19]
推而广之,上大夫在本国的宴饮场合亦使用“八簋”。此外,《诗·小雅·伐木》“陈馈八簋”为此提供了一个内证。程俊英、蒋见元认为,“据《仪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诸侯燕群臣及他国的使臣皆八簋。《毛传》:‘天子八簋。’是周王的宴会也用八簋。”[9]487《毛诗传笺通释》卷十二云:“‘每食四簋’,《传》:‘四簋,黍、稷、稻、粱。’瑞辰按:古者簋盛黍稷,簠盛稻粱。《传》知四簋为黍稷稻粱者,先大夫曰:‘《玉藻》“朔月四簋”亦谓黍稷稻粱’,故知《诗》四簋非专言黍稷耳。谨案《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是四簋为食大夫之礼。《易》言“二簋可用享”者,盖士礼也。簋与簠对文则异,散文则通。《诗》云‘每食四簋’,又曰‘陈馈八簋’,盖皆言簋以该簠。《正义》谓‘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失其义矣。”[20]398-399马瑞辰将“二簋”“四簋”分别与士、大夫对应,忽略了上大夫、下大夫之别;又认为“簋”“簠”散文则通,模糊了“簋”和“簠”的用途和数量。因此,马氏之说不可从。
综上所述,安大简《诗经》和《毛诗》异字异义类的异文互有优劣,体现了安大简《诗经》重要的文献校勘价值。
五、安大简《诗经·秦风》之次序
在传世文献中,十五《国风》的顺序有三种。第一,《毛诗》: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第二,《诗谱》:周南、召南、邶、鄘、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城。第三,《左传》: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安大简《诗经》的《国风》顺序是:周南、召南、秦、某、侯、鄘、魏。在上述文献中,《秦风》的排序分别是第十一、第十一、第十、第三。尽管安大简《诗经》只是楚地的一个《诗》选本,且介于《秦风》和《侯风》之间的“某”风散佚,但《秦风》在其中的重要性通过仅次于“二南”的排序得以显现。《论语·阳货篇》(17·10)说:“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21]《毛诗序》说:“《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18]20自从《诗》在春秋时期再度被编集以来,“二南”在《国风》中一直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杨义在《论语还原》中说:“位置蕴含着意义,居于全书之首,或各类之首的诗,是以篇章秩序的方式确立其特殊的引领意义的。[22]在安大简《诗经》中,“二南”仍具有引领意义,而紧随其后的《秦风》则凸显出重要意义。
“十五国风次序”所依据的标准是多元的,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实力是重要参考。《诗》不是一次成书,其定型至迟可追溯至春秋后期,《左传》所记季札观乐之事即发生于春秋后期。因此,《秦风》排序靠后反映了秦国在春秋中后期综合国力有所下降,这与秦国被中原国家视为“蛮夷”以及秦穆公去世后秦国在较长时期内经历内乱有关。根据安大简整理者的意见,安大简《诗经》是战国早中期文献,所以《秦风》入选楚地《诗》选本并且排序靠前,反映了秦国在战国早中期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
战国初年,秦国的政治、军事实力迅速提升。《史记·秦本纪》说:“(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於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惠文君)二年,天子贺……四年,天子致文武胙”。[11]201-205秦国经过秦献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等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逐渐强大起来,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获胜,赢得周王室的认可和尊重。《毛诗传笺通释·十五国风次序论》说:“其先後次第,非无意义,但不得以一例求之。……於桧、郑、齐、魏、唐、秦,可以乩春秋之国势焉。春秋之初,郑最称强,桧则灭於郑者也,故桧、郑为先。郑衰而齐桓创霸,故齐次之。齐衰而晋文继霸,魏则灭於晋者也,故魏、唐次之。晋霸之后,秦穆继霸,故秦又次之。”[20]9马瑞辰对国风次序的讨论有三点对人颇有启发:其一,承认《国风》排序的多元标准,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其二,将《秦风》排序归结为“国势”(政治、军事实力);其三,关注到秦穆公对《秦风》排序所起的重要作用。
春秋以降,周、秦文化加速融合,秦国的文化实力持续提升。秦仲被封为大夫,继而秦襄公被封为诸侯,秦国自觉接受了周代礼乐文化。毛亨《传》曰:“《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驷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18]408、411韩高年在《〈诗经〉分类辨体》中说:“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随着秦襄公始封为诸侯,加速了周礼西渐的步伐,秦文化逐渐由西戎文化的重实用尚功利转而从制度和观念等方面接受周人礼乐文明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春秋秦文化既刚勇有力又温文尔雅的丰富灿烂景观。”[23]《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之语——“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11]192春秋前中期的秦穆公虽然看到了天下大乱的现实,但仍推崇“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他想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称霸天下,故而更加推崇周代礼乐文化。秦国重视礼乐教化的思想直到战国后期仍有余响。《战国策·秦策》说:“王使子诵,子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王罢之,乃留止。”姚宏本“诵”作“诵经”。[24]所“诵”之“经”包括《诗》。《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杨倞注云:“经,谓《诗》《书》。”[25]《淮南子·说山训》说:“以非义为义,以非礼为礼,譬犹倮走而追狂人,盗财而予乞者,窃简而写法律,蹲踞而诵《诗》《书》。”[26]《汉书·贾谊传》说:“贾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於郡中。”[27]嬴异人归秦后面见安国君,其父当场考察他“诵”的能力,这反映了秦国上层对以《诗》教为重要内容的礼乐教化的重视。《秦风》是周、秦文化融合的结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札对《秦风》的评价,“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10]1285《秦风》体现“夏声”“周之旧”,在乐和义两方面深受周文化浸染。邓翔《诗经绎参》说:“昔季札观乐,称《秦风》曰夏声,谓能夏则大,故袭西周,终代周而有国。”[8]305政治、文化影响文学,秦国对周朝礼乐制度的吸纳使《秦风》带有雅正之声的特征。赵逵夫在《秦人西迁的时间、地点与文化传统的形成》中说:“周人发祥于陇东,周、秦两族很早就有来往。”[28]赵先生着眼于秦的发展史,更将周、秦往来追溯至商末周初。秦文化吸纳周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久而久之,秦国的文化实力必然得到提升。
由于秦国重视礼乐文化,纵观整个战国时期,《诗》在秦国流传广泛。《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李斯“焚书”的主张,“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11]255烧所藏之《诗》、对偶语《诗》者施弃市之刑,人为遏制《诗》的传播,从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诗》在秦国的流行。马银琴在分析了战国时期儒家在秦国的发展情况后,总结道:“尽管儒学自始至终都未能受到秦国统治者的重视,甚至一再受到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家思想的排挤和打压,但儒学在秦地的传播始终未曾断绝。与此相应,《诗》作为儒家学者入门必读的课本,也必然随着不绝如缕的秦国儒学得到传播。”[29]秦国硬实力、软实力的全面提升,决定了《秦风》在战国早中期的《诗》选本中排序靠前。除了秦国的综合国力外,春秋后期秦哀公救楚之事也可能影响到《秦风》在楚地《诗》选本中的排序。《左传·定公五年》记载:“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秋七月,子期、子蒲灭唐。”[10]1729在楚国被吴国攻打、面临亡国危机之时,秦国派子蒲、子虎帅兵救楚,有大恩于楚。因此,战国早中期的楚地《诗》选本不仅选入《秦风》,而且将其排到仅次于“二南”的位置。
安大简《诗经·秦风》的大量异文是《诗》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正常的文本现象。我们通过对异文的分类研究,深化、丰富了对《诗》内容的认识;结合秦国国力的变化,把握了《秦风》排序变化的规律。安大简《诗经》只是新出土的《诗》类文献的一种,将它与《毛诗》以及其他《诗》类文献进行对读,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注 释:
①参看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版。本文凡简本引文,皆引自该书。
②按王力先生的观点,“车”和“舆”同属上古鱼部,故音近。凡涉及上古声韵系统、文字声韵地位,均采纳王力先生的观点,参看郭锡良编著、雷瑭洵校订:《汉字古音表稿》,中华书局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