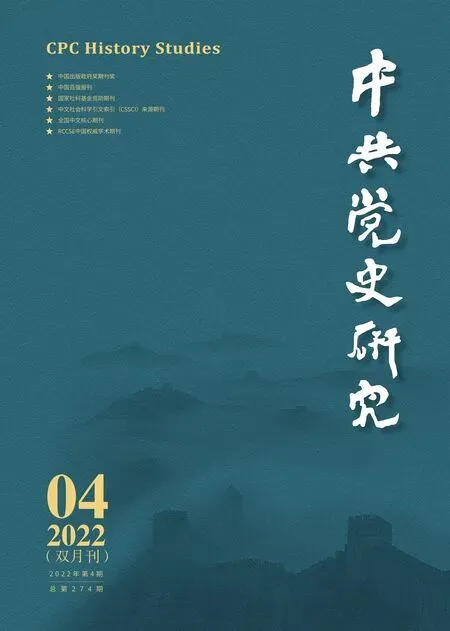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印关系档案评析
2023-01-08陈景彪孟庆龙
陈景彪 孟庆龙
在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外部环境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其中,由于历史、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中印关系曲折前行,友好、合作、分歧、冲突交织并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成本。对现代中印关系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理性、客观地看待其发展前景,因此具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乃至政治意义。而这种研究的基础无疑是搜集、整理、解读和使用中印关系史料。中国和印度的官方档案显然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目前双方核心档案的开放程度都很有限。几个商业化数据库大体上也只收录了反映中印关系和平友好的档案。在这种情况下,就获取路径和使用价值而言,位于伦敦西南部泰晤士河南岸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s,又译“邱园”)附近的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档案文献中心,为各国学者提供了数量庞大、富有特色、价值突出、使用便捷的现代中印关系史档案。
一、重要的现代中印关系史档案文献中心
本文所讲的现代中印关系史,主要指1947年印度独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史,但考虑到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很多时候还要上溯到1913年至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1)后文提到的“西姆拉会议”,均指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殖民者企图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去或制造“事实上的独立”而策划并在印度西姆拉和德里召开的会议。。英国国家档案馆在这方面的馆藏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40多卷。其中纸质版占2/3以上,其目录和档案号可通过互联网远程检索,但正文只能在现场查阅;数字化档案占比较小,可免费下载。
英国国家档案馆拥有便捷高效的查阅系统和舒适良好的阅读环境,除国家法定假日外,一般每周开放六天,可在网上预约要查询的档案并预订阅览室座位,开馆后即可到与座位号相同的档案盒中自取预约的档案。阅览桌上备有供充电的电源、可升降的照相机支架及按压卷宗的镇物。所有档案均可免费拍照,档案馆提供收费的复印和扫描服务。如当天没看完,可通过借阅系统申请暂不归还、次日再看,座位也可保留。档案馆读者众多,好的阅读位置需提前一天预订才有保证。此外,餐饮和休息环境也都十分舒适。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印关系档案来源十分广泛。部门和机构方面,主要有内阁办公室(CO)、殖民部(CO)、自治领事务部(DO)、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CO)、外交部(FO)、首相办公室(PREM)、陆军部(WO)、内阁(CAB)、贸易部(BT)、国防部(DEFE)、空军办(AB)、伦敦事务部(LO)和伦敦档案局(PRO)等。国别方面,除了英国以外,还有来自或复制于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亚(含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加纳等英联邦国家的档案,以及本属于美国、德国(联邦德国)、日本等一些美西方国家的档案。层级方面,涵盖英国内阁、议会、部、司、处、科等级别,以及英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亚等英联邦国家的高级专员公署,驻北京、莫斯科、华盛顿等地的外交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交人员与英国国内的往来电报和信件,因为其中经常附有复制的驻在国文件,有的还附有背景说明和英国官员有关中印关系的官方评估和个人见解。另外还有临时性、专题性研究报告,个人的亲历记、私人来信等,并收藏了一部分朝鲜、北越和南越、泰国、缅甸、日本等亚洲国家对中印关系变化,特别是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官方态度和媒体反应。
二、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现代中印关系史档案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印关系档案内容十分丰富,占绝大部分的是官方(政府机构和官员个人)文件。其中,源自自治领事务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外交部、首相办公室、陆军部及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来往函件又占2/3以上。在这部分档案中,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是以机构名义形成的官方文件,次之是驻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亚、加纳等英联邦国家及驻北京、莫斯科、华盛顿等地外交官与英国国内的往来电报、信函。特别是从印度发回英国的电报和信函,多为英国驻印度官员与尼赫鲁等印度高官晤谈、进餐等之后即时写作的文件,内容包括印度高层对中国的态度、决策考虑、希望和要求等,真实性和客观度较高。另一方面,英国当时是对印度影响最大的国家,印度的许多对外政策决策,尤其是对华态度和决策,往往都要私下里征询英国人的意见。加之当时印度的对华决策基本上由尼赫鲁本人或少数人作出,很少是集体意见,在印方相关核心档案不开放的情况下,上述史料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前述540多卷档案中,数量较多的部门依次是外交部、自治领事务部、首相府、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国防部、陆军部和内阁。从内容来看,直接讲中印关系的有202卷,其他则属于与中印关系有关,包括关于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31卷,关于印度与英国、美国及英联邦国家关系的40卷,关于印度、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的29卷,关于国际上对印度提供经济、技术、医疗和军事援助的75卷,关于中国国内局势、中国西藏政局及其与外部关系和相互影响的136卷,还有一些英美合作、中英关系、英印关系、国际反响等方面的档案。
数量仅次于官方文件的是英国各部门收集的大量报刊纸质版文章剪报、官员个人撰写的报刊文章内容介绍,以及有关国家的小册子和广播稿。这类资料是各国馆藏中印关系档案中独一无二的特色藏品,涵盖英国本土及中国、印度、美国、马来亚、泰国、锡兰、印度尼西亚、缅甸、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南斯拉夫、苏联、朝鲜、蒙古、柬埔寨、法国、瑞士、联邦德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阿联、尼泊尔、加纳、葡萄牙、肯尼亚等近30个国家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内容多半是对中印关系最新事态的即时报道、反应、评论和背景介绍,共计700多篇文章。另有相当数量英国驻外外交人员发回的对驻在国家和地区媒体文章内容的简介和分析评论、《亚洲国家对西藏的反应》等重要的印刷品小册子(有的公开发行,有的则为内部读物),以及印度等国的一些新闻广播稿。这些史料提供了许多细节,特别是人物心理、决策过程、影响决策因素等方面的信息,是对官方文件必不可少的补充,更非后世学者凭个人努力所能集齐。当然,使用时应当注意收集者的立场问题。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印关系档案的第三大类是照片和漫画。这类资料往往能反映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信息和意涵。其中,按事件归宗的系列照片清晰展现了中印关系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两国领导人等重要历史人物之间关系变化的细节。单幅或成册的漫画则形象地显示了不同时期和重要事件发生时印度人对中国的心态、第三方对重大事件的态度。例如,1955年万隆会议的照片及画册展示了尼赫鲁当时在亚非国家领导人中较大的影响力、亚非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亚非国家对中国的不同认知和态度,以及中印关系“蜜月期”达到顶峰的历史场景和精彩瞬间。又如,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印度政府花重金请国内最好的漫画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完成并印制的漫画画册《万隆绅士》(The Bandung Gentleman),深刻、形象地显露了印度无法言表的、极为复杂的对华心态(2)参见Sino-Indian Relations, 1964, DO 196/242。。
整体上看,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印关系档案有以下几大显著特色。一是解密档案数量较多。540多卷中,解密档案有122卷,含绝密29卷、机密27卷、秘密66卷。这在世界各国中是占比较高的。二是很少删减涂改。在所有开放档案中,有删减和涂改的占比不到1‰,而在美国查阅档案时,这一数字是英国的四倍至六倍。即使是那1‰有改动的,一张纸上往往也只涉及几个字、一两行,至多四五行。三是版本保存完整。有的档案经多个层级官员之手,修改多达四五次,而从第一个人准备的初稿开始,每一级官员、每一次修改的痕迹都清晰可见。这在开放档案的各个国家中似乎绝无仅有,也是英国国家档案馆被公认为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使用价值最高的档案馆之一的重要原因。四是源自多个国家。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不光是英国自己的档案,还有大量他国官方文件(但文件题目往往是英国人起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件很可能在当事国反而没有开放或只是有限开放,印度即是如此,其已开放的有关中印关系的档案,绝大多数都是反映两国友好往来和合作的。而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可以查到不少涉及中印矛盾冲突的印度官方档案,如1953年尼赫鲁在印度议会就西藏问题接受质询的记录(3)参见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 1952-1954, DO 35/6709。,1958年8月尼赫鲁和印度议会就《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进行辩论的记录(4)参见Sino-Indian Relations, 1952-1959, DO 35/8817。,1959年3月尼赫鲁就西藏局势在印度议会的发言(5)参见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 1952-1959, DO 35/8980。,1959年4月尼赫鲁就西藏局势在印度议会的陈述和答询(6)参见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 1959, DO 35/8981。,1962年10月中国发起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后尼赫鲁给英国首相的信(7)参见China/India Frontier Dispute, 1962, PREM 11/3838。,1962年11月尼赫鲁给巴基斯坦总统的信(8)参见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 FO 371/164921。,等等。
三、相关档案独特的学术价值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印关系档案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内容的全面性和相对客观性方面。无论是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冲突、缓和、正常化的发展过程,还是友好中夹杂着分歧、矛盾和不友好的复杂情形,英国国家档案馆都提供了丰富、全面的原始档案、一手史料。甚至可以说,要想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源(特别是西姆拉会议和所谓“麦克马洪线”),影响中印边界问题发展的诸因素,中印边界对峙、摩擦、冲突的原因和影响,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对中印关系发展的认知,印度对1962年边界冲突的总结和反思,印度制定对华政策的考量,印度与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英国、苏联(俄罗斯)、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德国)、日本等域外国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英国国家档案馆是必去之地。
中印友好方面,档案数量虽然相对不多,却详细记载和描述了若干重要历史细节,包括领导人的心理活动、英国对印度的影响等。例如,有档案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通过印度以及印度自身向中国提供的援助(9)例如,关于建立新疆供应线、修建印藏公路及盟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档案,参见UK/USA Collaboration Series, 1958-1962, AB 77/12; Allied Supplies Executive China, Tibet and Karakoram Pack Routes, 1942-1945, CAB 111/336; Supplies to China: Sino-Anglo-American Board in India, 1943-1947, CAB 122/774。,1950年印度支持苏联驱逐台湾当局代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议(10)参见Representation of China at UN: Message from Nehru,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Supporting Soviet Opposition to Chinese Nationalist, 1950, PREM 8/1303。,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11)参见Trad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Russia, China and the Satellite Countries, 1952, DO 35/5661.Sino-Indian Relations, 1951, FO 371/92248.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Statements by Mrs.Pandit Nehru about Her Impression of New China; Indian Cultural Mission to China, 1952, FO 371/99270。,中国同意印度驻西藏使团改为总领事馆(12)参见General Correspondence from 1906-1966, Tibetan Defence Measures, 1952, FO 371/99664; 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 1952-1954, DO 35/6709。,1953年至1954年中印通过会谈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13)参见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 1952-1954, DO 35/6709.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India, 1954, FO 371/110647.Participation of China in Talks with India on Tibet, Covering Trade, Culture and Pilgrim Traffic, 1953, FO 371/105627.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Chinese Goodwill Mission to India Planned for December 1953, FO 371/106856.Agreement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on Tibet, 1955, FO 371/115373.Trade and Travel between Tibet and India, 1955, FO 371/115374。,等等。
有关中印友好的档案,最亮眼的是1954年中印领导人互访的内容,其中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由于为印度仗义执言而受到尼赫鲁邀请访印的档案最有价值(14)参见Geneva Conference: UK Foreign Secretary’s Unwilling to Send Further Personal Message to Mr.Nehru, 1954, FO 371/112075; Geneva Conference: Information from Krishna Menon about Talks between Chou En-lai and Mr.Nehru, 1954, FO 371/112076; Geneva Conference: Chou En-lai’s Reply to Mr.Nehru’s Congratulatory Message to Him on Success of the Conference, 1954, FO 371/112084; Statements by Mr.Nehru and Others on Indi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1954, FO 371/112196。。随后的互访过程也留下了一批档案(15)参见Visit by Prime Minister of India, Mr.Nehru, to China and Elsewhere, 1954, FO 371/112221; Note to Prime Minister from J.Nehru on His Visit to China and Indo-China, 1955, PREM 11/916;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CPG and India: Visit of Chou En-lai to New Delhi and of Nehru to Peking, 1954, FO 371/110226;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ibet and India, 1954, FO 371/110647。,详细记录了两国关系步入“蜜月期”的过程,反映了尼赫鲁心态变化的许多细节,对研究此后中印关系变化中的个人作用和心理因素非常重要。此类档案涉及的其他典型友好事例还有:1955年中国在自身煤炭短缺的情况下决定援助印度(16)参见Trad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Russia, China and the Satellite Countries, 1952, DO 35/5661。,1956年2月中国在北京隆重庆祝印度国庆及同年12月周恩来访印(17)参见Sino-Indian Relations, 1952-1959, DO 35/8817。,1957年至1958年印度与中国、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18)参见Soviet Economic Offensive: Reports from India, 1956-1958, DO 35/8644;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Russia, China and the Satellite Countries, 1952, DO 35/5661。。即使在1959年中印关系开始急遽恶化后,也有当年3月尼赫鲁关于应把西藏视为中国内部事务的讲话(19)参见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 1952-1959, DO 35/8980。,当年4月印度钢铁代表团访华(20)参见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1959, FO 371/141285。,1962年边界冲突后中国善待印军俘虏,特别是建议在香港释放印度军官俘虏、为顾全其颜面而有意安排他们乘飞机回国(21)参见Indian Prisoners of War Held in China, 1963, FO 371/170709; 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3, FO 371/170673。等一系列档案。中印关系跌入谷底后,双方仍有一些维系关系、释放善意的举动,如1965年4月印度驻尼泊尔大使出席尼泊尔政府为陈毅举行的欢迎宴会(22)参见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China, 1964-1966, DO 196/260。,同年9月中国根据印度习俗下葬死亡的印度士兵(23)参见Sino-Indian Relations, 1965, DO 196/244。,等等。
中印边界问题方面,首推有关西姆拉会议及所谓“麦克马洪线”的三份原始档案(24)参见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ibet, Simla, July 3,1914, FO 93/105/2; Convention,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ibet, 1914, FO 93/105/2; Draft Convention,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ibet, Apr.27, 1914, FO 93/105/5。。西姆拉会议事关百年来中印边界争端和双边关系发展,其原始档案共有三套,分别存放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拉萨、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和英国的伦敦,目前只有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才可以方便地查阅和复制该档案。通过对这一套被认为事关中印边界问题所谓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档案的精细解读,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中印边界争端是典型的殖民主义产物,是英帝国主义者于20世纪初开始精心谋划、长期准备、狡诈操控和运作的结果。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人明里暗里一手炮制或主导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其中以下三种最为重要:一是英国政府代表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下签署的文件,包括1914年2月,二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非法签署的标有后来被称为“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东北边境,参谋长会议,第1页和第2页,临时发行,1914年2月,比例:1英寸=8英里》地图草稿(25)参见“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 General Staff, Sheet Ⅰ and Ⅱ, Provisional Issue, February 1914, Scale 1 Inch=8 Miles”, Draft Convention,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ibet, Apr.27, 1914, FO 93/105/5。,以及同年3月,二者对此予以确定的换文(26)参见Legality of McMahon Line (Boundary between Tibet and British India Agreed in 1914), 1962, FO 371/164932。。二是4月27日,英国政府特命全权代表麦克马洪(马麦含)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让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及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边觉多吉草签的中、英、藏三方所谓“西姆拉条约”草稿(27)所谓“西姆拉条约”包括一份条约和一张地图。条约的中文名称是“中英藏条约”,英文为“英中藏条约”(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ibet),“中”“英”顺序有别;地图根据条约第九款附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等界线,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档案显示,英国代表签的是英文,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的是藏文,照理说,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应签自己的中文名字,但他签的却是英文,而且名字的拼写与英国人打印的条约正文中的拼写还不一样(条约正文中是Ivan Chen,而陈贻范草签的是Ivan Chin),可见这次草签是多么潦草,并无法律效力。三是7月3日英国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字并盖章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包括所谓“麦克马洪线”的最后文本(28)参见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ibet, Simla, July 3,1914, FO 93/105/2。。在这份档案上,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既没签字也没盖章。三方会议的文件只有两方代表签字,显然是没有任何效力的。除了上述三份档案之外,西藏与印度边境地区的地图也很有价值(29)参见Sketch Maps of the Frontiers of Burma, China, Tibet and North-East India, by Mr.Rose, 1913, FO 925/17136; Maps and Plans, Tibet and Adjacent Countries, 1914, FO 925/17138; Map of Part of Kam, Showing Provisional Frontier Line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Resulting from Tripartite Negotiations of 1918, FO 925/17140; Map Showing India-Tibet Frontier as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the British and Tibetan Plenipotentiaries at Delhi, 24 Mar.1914, Government of India, 1914, FO 925/17162; Boundaries of “Outer” and “Inner” Tibet of the 1914 Convention, 1919, FO 925/17165; “Inner” and “Outer” Tibet of China’s Offer of 30 May 1919, FO 925/17166; Map Showing Frontiers Claimed by China and Tibet, 1913, FO 925/25196; “Sketch Map of Eastern Tibet” Showing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e Old Boundary Recommend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Alternative Boundary, 1911, MPK 1/209/1。,因为它们透露了英国和英印政府对中国边境地区逐渐渗透并加强控制的图谋和行动。
此外,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印关系档案还有利于从一些重要侧面观察中印关系史。例如,英国作为印度的前殖民宗主国,在中印边界争端的根源、1962年边界冲突对中印的利弊得失及西藏问题等议题上,并未给予印度一贯的、大力的支持或同情,有时还很冷淡。对于1914年3月英国代表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下里确定的画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英国政府自知理亏,此后不知什么时候(原始档案里没有标注)往案卷里塞了一张写有三行多字的A4纸,声言“此乃英国代表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双方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私下里非法签署的画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的原始图的影印件”(30)Draft Convention,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ibet, Apr.27, 1914, FO 93/105/5.。此种做法无疑是既想洗刷英国政府在中印边界争端上的罪责,又企图避免公开支持印度。在十分敏感的西藏法律地位及印度与西藏的关系问题上,英国没有明确、公开地完全站在印度一边。1948年7月初,印度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出面,让出版商修改“英国出版的地图上关于印度和西藏边界的标记”,但英国政府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只是淡淡地建议印度政府直接找出版商洽谈解决(31)参见India/Tibet Frontier, 1948, DO 142/468。。即便在中印边界爆发冲突后的1962年11月,英国官员仍然认为“麦克马洪线”只是在地图上标出、并未在地面上划定,因而缺乏准确性(32)参见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 1959, DO 35/8983; Legality of McMahon Line (Boundary between Tibet and British India Agreed in 1914), 1962, FO 371/164932。。相关档案显示,中国方面主动宣布停火、撤军对印度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1962年12月初,英国驻北京使馆官员认为,印度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表现对它不利。有英国官员提出,在1935年甚至20世纪40年代之前,无论是印度与西藏的边界协议,还是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特别是达旺以南的有效控制,证据都对中国有利。英国外交部认为,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印度的主张和提出的证据对它很不利。(33)参见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 FO 371/164921; 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 FO 371/164920; Chinese Military Intensions against India, 1963, DO 196/174; Legality of McMahon Line (Boundary between Tibet and British India Agreed in 1914), 1962, FO 371/164932; 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3, FO 371/170669。边界冲突后,英国不希望中印之间的争端扩大。1962年12月20日,英国外交部官员认为在中印边界争端上替印度辩护不太明智,不愿独自作印度的庇护者,甚至有英国官员认为印度应该让出阿克赛钦七处哨所以解决中印边境争端(34)参见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 FO 371/164924; 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 FO 371/164920; Chinese Military Intensions against India, 1963, DO 196/174; Sino-Indian Relations, 1964, DO 196/242。。
关于1962年边界冲突对中印国际地位的影响,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得更加明白。印度自独立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无论是领导人尼赫鲁还是整个国家,在国际上赢得了众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但是,1962年边界冲突的失败使尼赫鲁的声望和印度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当年11月,印度在边界冲突中败局已定,其外交部列出的“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国家有40个,“同情和关切”印度的国家有5个,“同情”印度的国家有11个,满打满算,站在印度一边的国家共有56个(35)参见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 DO 196/166; 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 DO 196/16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争开始后,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宣布支持中国(只有阿尔巴尼亚不公开地给予支持)。但是,在中国方面于完胜之时主动宣布停火、撤军后短短一周时间里,先后有亚非拉37个国家的政府宣布支持中国的做法,其中有14个是在战争开始后曾宣布支持、同情和关切印度的国家。到了1963年1月,公开亲印的国家只剩下2个。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锡金段军事对峙时,上述曾站在印度一边的56国,绝大多数都没有再对其表示支持和同情,有的还劝说印度正视中国的“最后通牒”,撤走在边界非法建立的军事设施。(36)参见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3, FO 371/170669。
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对于美印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印度态度的转变等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细节。例如,美国原来不重视印度,但1953年10月,美国官员突然称美国对印度的态度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关注点之一(37)参见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USA and India and Pakistan: Visit of Vice President Nixon to India, Dec.1953, FO 371/106857。。1959年9月,印度驻美大使应邀在美国众议院发表题为《印度与共产主义》的讲话,声称印度不怕与中国开战(38)参见Violation of Borders of India by China, 1959, FO 371/141271。。在中印关系尚未公开破裂的情况下,美国此举显然标志着开始改变此前对中印边界问题尽可能不公开表态选边的做法。
相关档案还提供了许多有关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印度的数据和细节。例如,印度和苏联1953年10月签署黄油换小麦协议,12月达成关于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及印苏技术合作协议。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南斯拉夫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印度提供了钢铁、化肥、煤炭、石油及贷款等多种援助。50年代中后期,苏联同意帮助印度勘探铀矿,向印度提供核能和石油援助,准备援建印度核电站和石油设施;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则向印度提供了铁路援助和钢铁援助等。(39)参见Russian Credit for India, 1957-1960, DO 35/8643;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Russia, China and the Satellite Countries, 1952, DO 35/5661; Soviet Economic Offensive: Reports from India, 1956-1958, DO 35/8644。
近年来,国内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印关系档案开展研究的发展势头良好。虽然这些档案绝大多数没有标题,需要专业人士阅读并进行中文标引和分类,费时费力,但已有学者和研究团队深耕十余年,整理并建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数据库,陆续发表了一些高质量学术成果,完成了一些研究报告,举办了一些专题讲座,为我国外交、军事、经贸、文化交流等部门提供了有价值的咨询和参考,同时也促进了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