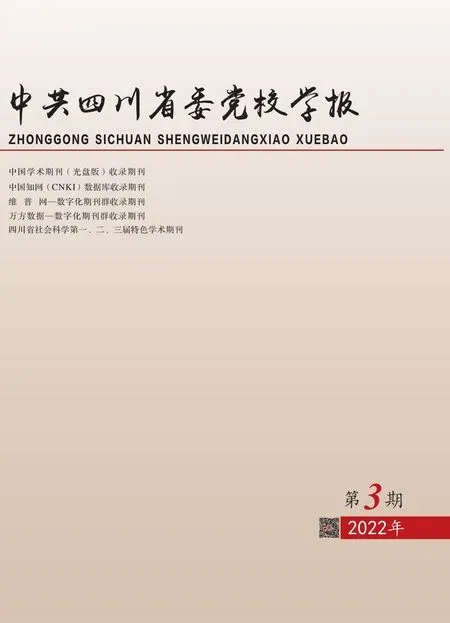居住权制度实施的困境及出路
2023-01-08杜学文
周 坚 杜学文
(1.江苏博爱星律师事务所,江苏常州 213022 2.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太原 030006)
一、引言
此次《民法典》的出台具有很多的创新之处和亮点,也不乏新增的制度,居住权制度的设立就属于其中一个。居住权在我国之前的法律制度中并没有被规定,其起源于罗马法,“制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应反映社会实践需求,对现实需要应及时有效地作出回应。”[1]近年来,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了“炒房 ”问题,大肆抬高房屋价格,使得很多人买不起房子,而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对于离婚、年老体衰而孩子又不履行赡养义务的人来说,连最基本的居住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将居住权纳入《民法典》是基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住房需要,在保障基本人权、注重人文情怀的同时,契合了十九大的指导思想,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将居住权纳入《民法典》的物权编,可以很好地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很大程度上避免弱势群体无所居的问题,使房屋的价值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居住权的设立可以为老人养老、老有所居提供法律保障,有利于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同时居住权的设立也有利于解决离婚案件中无房一方的居住困难,不至于在离婚后出现一方流落街头的尴尬局面,还可以充分发挥房屋的作用和价值,使得物尽其用。
二、居住权制度的内涵及立法沿革
(一)居住权制度的内涵
我国并非开居住权制度的先河,居住权制度并非我国专属和固有的制度。从居住权的概念、功能和性质入手可以很好地分析居住权制度。关于居住权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66条对居住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居住权人有权依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此项规定明确了居住权人对所有权人的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项特殊的用益物权,其并不包括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居住权未经所有权人同意不得出租、转让,不能继承,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权利人对房屋享有的居住权只限于居住,不能带着商业目的等其他非居住目的,否则有滥用居住权之嫌。关于居住权的性质从不同的方面解读则会影响对居住权性质的判断,从基本人权的角度,是国家保障居民有所居的基本住房权利;从身份关系角度,则属于对权利人身份关系性的救济;从财产关系解读,则属于不可转让和继承的财产性利益;从人役权的角度,是权利范围比较狭窄的物权。
(二)居住权制度的立法沿革
居住权制度最早起源于罗马法,这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古老的制度。西方许多国家在民法典中也纷纷规定了居住权,设立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在古罗马,家里的主人公男子去世后,其长子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但为了不让其他家庭成员,如自己的妻子和其他孩子甚至奴隶颠沛流离、无房可住,才诞生了居住权制度。[2]居住权制度在被正式纳入《民法典》之前,在我国就已经存在,只是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对此作出明文规定。居住权的概念首次在我国被提出是在1993年,在最高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提及居住权,2001年居住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同时在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二线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对居住权也作了相关的规定。(1)《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实施若干规定》第六条就规定了,“当事人可以以协议的方式设立居住权”。同年上海市房产局发布的相关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了: “如果 60 岁以上老人未作为产权人登记的,则必须在《协议书》中承诺,保障其居住的权利”。2002-2005年,《物权法(草案)三次征求意见稿》对我国是否要引入居住权制度进行意见征求,但是由于出现了众多反对意见,认为居住权在现实生活中运用得并不广泛,完全可以适用其他的法律规定解决问题,若是涉及房屋租赁关系的居住问题,则可以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若是关于夫妻离婚所涉及的居住问题,则可以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最终还是删除了关于居住权的规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仅仅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较为便宜的房子去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亦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且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无讼”案例库中,有很多涉及居住权的判决,将居住权纳入《民法典》是时代的要求。[3]到了2019 年 12 月,《民法典( 草案) 》终于将居住权编入了《民法典》物权编中。
(三)对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理解
1、当事人应当以合同或遗嘱等书面形式来设立居住权。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通常情况下居住权无偿设立。设立居住权,应当向法定的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2、居住权设立后,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的约定或遗嘱的设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其生活居住的需要。因此,对于设定居住权的房屋,房屋所有权人并不拥有居住的权利,只有等居住权期满或居住权人死亡,房屋所有权人才能拥有居住的权利。
3、对于设定居住权的房屋,居住权人依法只享有居住的权利,不能私自转让也不能继承。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居住权确立后房屋不能用来出租。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我国《民法典》设立居住权是尊重权利人意志的体现,表明了我国法律不仅保障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所有权,还在立法上重视其财产的用益权,以此来满足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房产利用方式的多元化需求。在无需出让房屋所有权的前提下,依法为另一方设立居住权,不仅能有效地保障离婚无房一方、以及未成年人的居住利益,还为老龄化社会下老年人以房养老、拆迁安置住户以及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居住权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将居住权制度纳入《民法典》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同时使得物尽其用,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充分彰显,也是保障人权的需要。然而,刚刚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规定很不完善,仅仅只有6条法律条文是规定居住权的,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不能及时有效地作出回应,相较于其他制度的法律规定,显得过于单薄。
(一)居住权和抵押权存在顺位冲突的问题
居住权和抵押权均属于物权,具体来说,居住权属于用益物权,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它们都是在不转移物的所有权的前提下实现物尽其用,一般情况下二者不会发生冲突。然而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居住权和抵押权也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分为三种,一种是抵押权人与抵押房产受让人同时设立的居住权产生的冲突,一种是设立在前的抵押权与设立在后的居住权之间的冲突,最后一种是设立在前的居住权与设立在后的抵押权之间的冲突。[4]当二者权利存在冲突时需要优先保护谁的权利与利益呢?此时需要《民法典》作出回应。但纵观整个民法典仅仅是对抵押权的实现方式和程序作出了规定,对于该权利冲突却没有提出解决机制。
(二)居住权设立的方式单一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2)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住宅的位置;(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居住权期限;(五)解决争议的方法。和第三百七十一条(3)《民法典》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居住权的设立方式有遗嘱设立和合同设立两种,可见居住权的设立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设立,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自由,但仅仅两种方式太单一且难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要求和出现的新问题。设立居住权主要是保障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需要,然而作为弱势群体的老人、配偶、孩子等往往因为处于弱势地位在签订合同时没有办法很好地保障自己的利益,而这又与立法者的立法初衷相违背。比如现实生活中离婚的夫妻,夫妻一方很可能离婚之后没有可供居住的房子,经济处于困难需要被照顾,此时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应该给予另一方适当的照顾,但具体的照顾和帮助方法需要两人协商,而协商的结果并不排除一方不愿意提供可居住的房屋,此时协商不成则需要法官裁判。可见通过意定的方式去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是远远不够也不足以解决问题的。
(三)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
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等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二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但《民法典》对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只是在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对于住房具有占有、使用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仅限于日常生活需要,对于在居住权存续期间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第一,倘若居住权人在居住期间想要对房屋进行装修和修缮,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那么居住权人是否享有这个权利以及此部分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法律没有明确作出规定。第二,对于居住权人对房屋享有的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该权利包括房屋这个客体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但该权利是否及于一些政策性的权利,比如子女落户、子女入学等,法律也没有作出明文规定。第三,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居住权人的义务。居住权人在居住权存续期间如果房屋这个最重要的客体灭失,或者房屋由于自然灾害、老化等非人为的原因遭到破坏,该责任应由居住权人承担还是所有权人承担,法律亦没有作出明文规定。
(四)缺乏权利救济措施
任何权利的存在都有可能出现被人为滥用的可能性,居住权也不例外。设立居住权是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需要,但社会生活和人的个性是纷繁复杂的,一方面居住权人可能会侵犯、滥用该权利,主要表现在居住权人在居住权享有期间作出的行为超出了日常生活和居住的需要,比如居住权人未经所有权人同意而私自将房屋进行出租、转让,甚至将居住权进行抵押,或者改变居住权的用途而对外开展营利性质的商业活动,或者无正当理由故意破坏房屋所有权甚至侵害房屋所有权人的人身权利,这都严重侵犯了所有权人的所有权。另一方面房屋所有权人可能会滥用该权利侵犯居住权人甚至无辜第三人的权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房屋所有权人在存在大量债务无法偿还的情况下,为了逃避债务很有可能会在房屋上设定居住权,以至于法院无法强制执行,这就属于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二是如果房屋所有权人将房屋无正当理由地予以收回,导致居住权人无房可住,或者居住权的设立违背公序良俗、侵犯第三人的权利等现象出现。发生这些情况应如何进行救济,法律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司法解释作出说明。
四、对居住权制度的完善措施
针对居住权制度在司法适用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逐一地采用不同的措施和方法进行完善,以更好地解决居住权制度在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保障好权利人应享有的权利,实现交易秩序的安全,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一)按照物权登记的时间顺序解决权利冲突
在房屋上并存居住权与抵押权时,法律对该冲突又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法官应在均衡抵押权人与居住权人利益的基础上,在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和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为了保障司法公正,可以按照二者的登记时间顺序解决冲突。抵押权与居住权均采用法定的登记公示手段,都要将居住权合同和抵押权合同拿到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即是以合同登记为生效要件,二者的公示效力相同,都会产生让社会相信的法律后果。对于均办理了登记的抵押权和居住权,可以参照《民法典》第四百零五条关于租赁权与居住权的冲突解决规则适用,(4)《民法典》第四百零五条 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即在设立抵押权之前,房屋已经设立了居住权并且已经转移占有的,该居住权不受抵押权的影响,后成立的抵押权不能对抗先成立的居住权。反之,如果抵押权登记在先,则抵押权可以对抗后成立的居住权,以此保障抵押权人的权利。总之,对于房屋上并存抵押权和居住权的情形,可以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顺序决定具体保障何方的权利。
(二)增加法定居住权
我国《民法典》没有明文规定法定居住权,法定居住权的设立在我国可通过法院裁判的方式为特定主体设立居住权,以符合设立居住权的立法目的,契合法律精神。一是可以基于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设定法定居住权,这是对子女对父母应尽赡养义务的延伸和扩展,但该种法定居住权是附条件的,仅仅是在父母无房的情况下,对于父母有房的,则不需要强制要求子女为其提供房屋,否则子女背负的义务太重了,不利于父母与子女良好关系的建立。二是可以规定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相互具有法定居住权,这样可以保障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行使监护权,促进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三是基于夫妻关系产生的法定居住权。对于离婚后无房且经济困难的夫妻一方,如果只是暂时性的生活困难,法律可以规定在短期内为其提供住房;如果已经年老体衰再也没有劳动能力,根本不可能改善其生活条件,购买房子已经遥遥无望的,法律可以为其设立永久性房屋居住权。对于丧偶夫妻一方,无论对其房屋是否享有继承权,法律都应当为其设定居住权,这既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赡养义务的体现,同时也是法律对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的精神体现。
(三)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居住权人在居住权存续期间,很难避免因房屋的维修和修缮在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之间产生一系列的债权债务关系。为了减少因此种情况产生的冲突,法律可以明确规定,在当事人签订合同时设定必备条款,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在合同中应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居住权人不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否则会侵害所有权人的利益。[5]关于权利可以明确规定居住权人享有的权利不仅包括对房屋和附属设施具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还应包括落户和子女入学的权利。在我国很多城市子女是否能落户和入学往往是和房屋所有权挂钩的,对于离婚的夫妇且孩子判给没有房屋的一方,如果只是让其占有、使用房子,孩子的义务教育很可能就会得不到保障。此外,还可以明确居住权人对房屋应尽的合理使用义务,以及因自己的原因造成房屋损害时的修缮义务。因为如果不明确规定修缮义务,就会很容易导致居住权人和所有权人不屑于也不愿意管的问题,那么房屋的经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严重影响所有权人对房屋的经济利益。但这种修缮义务只限于单纯的维护修缮,如果超过单纯的维护修缮,比如对房屋进行大范围整改则应该由房屋所有权人承担。[6]这是出于保护弱势群体和符合立法目的的需要,一方面居住权人对于房屋只是占有、使用,而没有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另一方面居住权人往往都是无房的弱势群体,此时再由他们承担超过单纯的修缮范围的负担并不符合情理。
(四)明确权利救济措施
法律不能只简单地规定一项权利,而疏漏了该权利受到侵犯或被滥用的问题,对此应当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权利救济措施,建立一整套健全的救济机制。可以赋予居住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对居住权的撤销权,当权利遭到侵犯时,可以启用这套解决机制,同时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和结果发生的原因分担其责任,居住权人权利受到损害时,可以基于物权法的规定,向第三人主张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灭危险等权利性救济。如果不明确规定权利救济措施,则不利于保护弱势一方的居住权,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与设立居住权的立法目的也不相符合,甚至会严重影响房产市场的交易秩序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稳定发展。
五、结语
《民法典》中新增的居住权制度,是对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关于保障弱势群体“住有所居”的落实,同时填补了我国关于居住权的立法空白,丰富了物权编的内容,推动了我国法律的快速发展。(5)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对当前市场经济中频出的“炒房”问题以及夫妻双方离婚但不离家等社会热点问题,居住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指导作用,有效地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而且有助于解决涉及居住权的房产纠纷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7]但一项制度刚出台肯定是不完善的,居住权制度亦是如此,其在与抵押权的顺位、权利义务规定、设立方式及权利救济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缺陷,必须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完善自身体系,以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满足弱势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