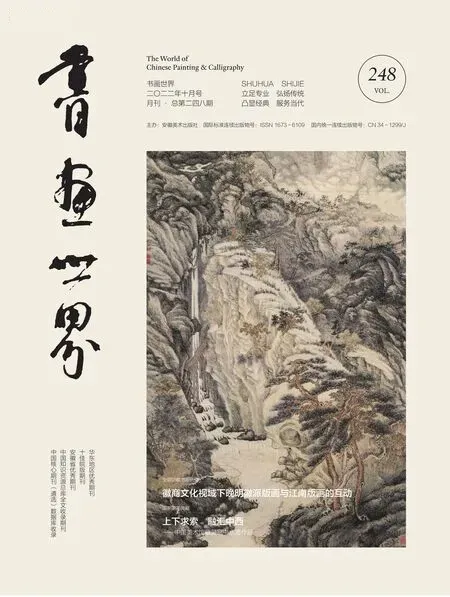罗聘《鬼趣图》中形神的隐喻研究
2023-01-06刘雪
文_刘雪
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画系2020级研究生
内容提要:《鬼趣图》是清代画家罗聘的画鬼佳作。本文通过分析画中的情节内容与鬼怪形象,结合当时社会现象、世人需求及时代背景,并根据对后世题跋的研究,梳理出画中形与神背后的审美趣味;以霍宝才收藏的《鬼趣图》画面内容为主要参考,探索《鬼趣图》背后隐含的时代内涵。

清 罗聘 鬼趣图尺寸不详1771 霍宝才藏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画家罗聘曾自云:“凡有人处皆有鬼,鬼所聚集,常在人烟密簇处,僻地旷野,所见殊稀。”其思想与画作结合促成了《鬼趣图》的出世,罗聘对鬼怪们的形神谙熟于心,以写实与夸张相结合的手法塑造出生动鲜明的鬼怪形象。清乾隆时期,社会上流行鬼事怪谈。罗聘上京城后,受时风影响,便开始创作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的鬼怪题材作品,形象怪异别致、个性突出。他借鬼怪形象描绘人间百态,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在中国人物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罗聘与《鬼趣图》
罗聘,字遯夫,号两峰,祖籍安徽,出生在扬州,年轻时得到金农的赏识,拜金农为师。他擅长画人物、山水、花卉,在“扬州八怪”中被称作是“五分人才,五分鬼才”的画家。传说中他有着绿色眼眸,他诡称自己可白日见鬼物。罗聘创作出多本《鬼趣图》,轰动南北画坛。其中,流传至今的《鬼趣图》有三个版本,分别是藏于香港艺术馆的手卷本、方闻旧藏的折扇及霍宝才私人收藏的段本[1]。其中霍氏收藏的图卷是罗聘三上京城随身携带的版本,本文将根据此版本进行探析。
乾隆时期,社会繁荣,市民消费文化的需求体现在绘画上,就是画家群体追求标新立异,寻求突破传统,注重表达天性和创作的意趣。当时“文字狱”兴起,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画家的创作倾向,也影响到扬州画坛。1771年罗聘初上京城,尔后结交许多学者高官,并因当时王椷的《秋灯丛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乐钧的《耳食录》等鬼怪题材文学的流行影响,开始创作一系列的《鬼趣图》,因此名噪京师,并得多位名流题跋;1779年罗聘二上京城,但停留十分短暂,当时其妻已病重,待其归时,早已天人相隔;1790年罗聘再次前往京城,当时他在扬州已颇有盛名,他穿梭于达官贵胄之间,《鬼趣图》第二次成功吸引诸多名流题跋,但他依旧并不宽裕。法式善曾在诗中描述罗聘在京城的生活,“灶炊茶烟断,墙出石墨干。雪中蕉叶好,画向低头难”[2]。罗聘鬼怪题材的创作,是时代与文化观念的产物。
霍氏收藏的罗聘《鬼趣图》共八幅,共描绘了十九个造型各异的鬼怪形象,每幅少则由一个、多则由四个鬼怪形象组成,内容互不重复,经装裱后以手卷册页的形式存在。画中的鬼怪形象形态各异,造型经过变形,夸张而传神,凸显出笔墨在视觉上的情绪感,使得画面表现出戏剧化的暗讽效果。烟雾缭绕的环境中每个鬼怪面目离奇,似真似幻中显露惊恐、谄媚的神情。这些鬼怪有的呈静止低声细语的状态,有的前后奔走,尽显鬼魅之感。鬼怪的手和脚的描绘也各不相同,在五官、神态、衣着、头发等细节的刻画上极富变化,每幅中的鬼怪之间都有交流。画面虽简省了背景的刻画,却清晰地交代出了内容,引人遐想。
二、“形”的符号化
符号化在这里指艺术家将思维赋予描绘对象以形式,并运用艺术手段提炼出能够表现情感的艺术造型,使描绘的对象更容易被受众认识。符号化有着可识别和不可复制的特征,艺术家创作中的个人风格特征可以理解为艺术家自身独具特色的符号,将来自生活中的素材和概念通过美学的形式,形成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且不可复制的个人符号。在绘画中,符号化体现在画家创作的个性化表达手法带给受众视觉感受上的独特性。当然,绘画作品的符号化不仅仅是带给人们视觉上的震撼,它更多的是画家对客观现实的本质认识及内心情感提炼后的符号化。个人主观思想意识的不同,是每个画家创作出个人风格绘画作品的重要因素。
“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3]因为鬼怪没有具体的形态,画家可以把他们画成任意形态。在追求形似的绘画风气下,很多画家将人形赋予鬼怪,画中的鬼怪形象便有了世人的影子。不同时期鬼怪题材的创作都有着各自的时代特色与符号。唐朝吴道子《天王送子图》中鬼神的形态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演变的结果;南宋李嵩《骷髅幻戏图》中儿童与骷髅的互动描绘,展现出生与死的对峙;元代龚开《中山出游图》中的鬼怪以人的形态存在,充满荒诞、诙谐的趣味,但其中又饱含着无奈,表达出了对当时社会的憎恶嘲讽;明代戴进《钟馗雨夜出行图》中鬼怪簇拥下的钟馗,威严凶狠,凸显出畸形的人格、心理;清代金农、罗聘、黄慎等画家均有鬼怪题材创作,其中罗聘的《鬼趣图》尤其突出,其笔下的鬼怪多一分无形,少一分无意。《鬼趣图》中形的符号化延伸了画面内容的图像多样性,主要表现在造型方面。画中的鬼怪“角色”形体胖瘦不一,他们的互动之态引人遐想。他们的形态夸张,有拄拐的矮鬼、四肢修长的绿发鬼、头大身小的大头鬼、以伞为中心游戏的鬼。画家通过变形夸张的姿态表现出每个鬼怪的独特之处,形成丰富多彩的鬼怪世界。但纵观整体,我们可以发现画中无论什么形态的鬼怪都带着凄凉之感,也许只有生活在黑暗之处的画家才能创作出有悲凉氛围的画作;也可以看出罗聘对社会百态细致入微的观察。他将人生经历和对社会现实的情感态度融入《鬼趣图》的创作语言中,使作品具有了特殊情感。鬼怪“形”的符号化特征也表现在技法、线条、笔墨等绘画语言中。技法上,充分运用水墨的晕染效果,先润湿纸张,在纸面未干时细笔施墨勾画鬼魅的形态,画面鬼怪形象与背景晕染形成实与虚的对立关系,晕痕自然形成神秘的氛围,自饶别趣;线条上,取法陈洪绶白描人物画的高古意蕴,在浓雾渲染中简练勾勒,使得相互渗透,鬼怪形象似取自市井人物,身形简单仅勾轮廓以成,造型简练,线条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现出鬼魅来回穿梭的灵趣与鬼怪身影婆娑的疏离感;笔墨上,墨色因湿润而晕开,墨气的渲染增加了恐怖的意境。《鬼趣图》画面简洁直白,鬼的姿态和表情刻画精细到位,让人遐想;衣纹流畅,湿纸墨线勾勒,拟人的创作手法,独具一格;鬼怪之间的关系,引人想象,有画家自我的符号化语言。这种形态上的夸张,是画家臆想的客观表现,耐人寻味。
三、“神”的趣味性
《历代名画记》中记载:“至于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魏晋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以形写神”,强调绘画作品要注重传神,画面才能生动有趣。“神”是画作融入内涵与画家灵魂的表达,这使得“神”有了更多的内涵。《鬼趣图》中“神”的趣味性,不仅从画面中笔墨的变化、造型的抽象表达得以显现,而且延伸到了作画者对社会现实的暗讽。首先,鬼怪的五官神态表达出不同的故事情节。如画中有两鬼窃窃私语;旁边另一鬼在偷听,手中拿着的花朵,仿佛表达鬼怪之间的爱情。神态是个体内在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早期鬼怪题材的创作,多表现简单,是为宣传宗教或政权服务的表达方式。在后期的发展中,鬼怪题材的创作逐渐转向神态多样、趣味浓重。其次,《鬼趣图》中“神”的趣味性可以体现在形象刻画的夸张表现上。罗聘根据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夸张变形,用线勾勒得极为简练,同时又描绘得极具故事性。画家对故事的阐释是其主观情感的表达,让画面的趣味性再次提升。罗聘通过对社会时事隐喻暗讽的创作方式,让鬼怪的形象更丰满,神态更生动。传说是一位张姓的姑娘被衙役调戏后,罗聘上前帮助反被痛打,心中愤怒,便作多幅鬼怪画张贴于官府门前,画中女鬼张牙舞爪,使得县官衙役们都很恐惧。
在清政府统治下的汉人多受压制,罗聘创作的画中鬼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正如大多数人的处境,因此反映“人趣”的《鬼趣图》被世人接受。所谓“鬼趣”重在游戏人间“趣”的表达,将鬼怪人格化,鬼怪的神态中都透着人情味。鬼怪题材的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诸多佳作。早期的鬼怪题材作品多是围绕外在形体来描绘,缺乏内容与内涵,多是单纯为宗教或政权服务;宋末元初,鬼怪题材画作才慢慢表现出现实意义。罗聘的鬼怪题材作品表达的现实情趣更加深切浓烈,形象更加人性化,作品的“神”也更有趣味性。《鬼趣图》中题跋众多,题跋存在的趣味性表现在诗与画的相得益彰。每个题跋都是题写者对画面故事情节与情境的聊表自得,如吴楷所题“幽人具冥怀,涉笔便成趣”。鬼怪题材的作品是画家主观想象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表现画家的个人趣味。
四、图像背后的时代隐喻
关于鬼怪的图像发展,远古时代人们认为鬼神皆是来自大自然中未知领域的存在,并在民间口口相传至今。《礼记·祭义》中记载“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说鬼是人死后的灵魂;儒家则“事鬼敬神而远之”,认为鬼神超脱于骨肉形骸,隐于世人之间,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存在;道教认为鬼怪是民间巫术,修道可由鬼变仙;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认为鬼是对人死后依生前牵引至六道轮回之中,善恶在六道的流转中得到相应的因果报应。中国历来有着丧葬文化,很大程度促进了鬼怪文化的发展[4]。在朝代更迭中,统治者将鬼神之说作为政权统治的手段,以此巩固正统。因此,在不同朝代的社会环境影响下,鬼怪的内容与形式便不尽相同。随着文人画的发展,画家将个人情感融入画面中,把自我个性通过画面展现,鬼怪题材的创作背后所蕴含的内容也随之丰富。鬼怪文化在士大夫群体中流行,他们认为鬼怪是人间的镜子,反映的是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活动。画家们借助“鬼”的形象和故事警醒和教化世人。当今社会也有人认为鬼怪是受尽永恒折磨的存在,以此寓意来震慑人心、激发世人对恶畏惧、积极从善。
《鬼趣图》上的大量题跋揭示出当时社会借鬼怪形象讽刺社会的潮流,所谓的隐喻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时事的暗讽。如张曾题“天生屈子多离忧,国殇山鬼愁复愁”,将屈原的诗歌与罗聘的鬼怪画作相比较,认为屈原的骚体中引用美人香草和神话传说来比喻胸中情怀,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畅想将来的美好,同时又以鬼怪来暗示现实的残酷;蒋士铨题“侏儒饱死肥而俗,身是行尸魂走肉”,以矮胖鬼暗讽贪婪享乐、趋炎附势的小人;张问陶题“对面不知人是骨,到死方信鬼无皮”,将画中骷髅暗讽为丧失骨气之人。《鬼趣图》中所绘众鬼各有凄惨之状,例如鬼怪形象胖瘦之间的对比,是对社会贫富差距的批判,这与当时社会的官僚风气有很大联系,是对官场的暗讽,对污浊丑相的揭露;画面中的鬼越来越多,鬼气凛人、夸张嗔怪、阴森缥缈,表现出了社会的阴暗。形态各异的鬼怪形象皆是画家隐晦的表达,对鬼怪世界的刻画喻示着画家所处的世间之景。画家通过作品直抒胸臆,不仅表露了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在暗讽中带着些许期许之意。
结语
随着科学的发展,从现代的视角看,鬼神只是虚构的存在,是人们特殊的情感寄托。对于鬼怪,罗聘将他“看”见的鬼怪描绘出,让大家心中有了具象的形象,写实与抽象结合,形与神贯穿。在对鬼怪的时代审美风尚中,他赋予了《鬼趣图》更多隐秘的意味。在鬼怪形象创作的历史变迁中,通过对罗聘《鬼趣图》的研读,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形与神在创作中的作用,形象固然是夸张与变形的,但万法自然,都是画世人、画自我,都是画家表达个人思想的手段。罗聘的《鬼趣图》在很大程度上也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价值,拓宽了艺术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