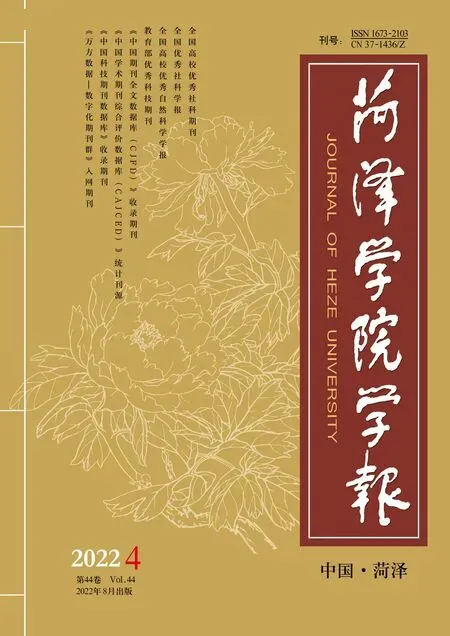中西喜剧观之比较*
2023-01-06陈海燕
陈海燕
(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菏泽 274015)
喜剧和喜剧精神是不同的概念,但二者之间也有交叉联系。喜剧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或戏剧类型,是一种戏剧文体,是源于人类或人的喜剧精神的。寻求快乐是人的生命本能之一。喜剧的产生,是与人的生命需要相系的。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三个结构: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遵循的是唯乐原则。而喜剧或者游戏精神是人类或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需要。自人类产生一直到今天,喜剧精神一直伴随着人类。可以说,喜剧是人类的一种生命体验和需要,也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中西(笼统地说)两大文化谱系关于喜剧的理解和观念既具有人类普泛意义上的共性,也有各自文化孕育的独特个性。本文从中西喜剧产生、表现、及造成其不同的原因等方面作一探析。
一、中西喜剧之产生
中国喜剧艺术导源于古代优人的活动。大约在公元前5至6世纪,宫廷就曾出现了一批专供天子王公贵族取乐的俳优。他们大都是侏儒、畸形的人。《国语·郑语》:“侏儒、戚施,实御在侧,近顽童也”[1]。这些俳优的见识和口才,高出很多宫廷贵族之上,他们有时通过滑稽嬉笑来讽刺那些宫廷贵族的愚蠢。秦汉时期,俳优之风更盛。据说西汉东方朔曾以滑稽闻名。《汉书·朔传》:“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儿童牧竖,莫不眩耀,……”[2]从南北朝至唐代的“参军戏”,也吸收了宫廷中俳优、侏儒的讽刺手法。参军角色的呆头呆脑,苍鹘角色的机智活泼,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参军在奴仆的对比下,出尽洋相,演绎出一场场引人嬉笑的短剧。到宋代的杂剧、金元的院本,受群众喜爱的讽刺性剧目就更多了。总的来看,中国喜剧一开始就受到宫廷的欢迎,后来才在民间广泛流行。
西方喜剧从字源上考证的话,《牛津大字典》中的喜剧一词源于Comaedia,具有“欢乐”意思。早期古希腊喜剧由酒神祭祀中群众游行的狂欢歌舞脱胎而来。这是一种戏谑表演,生殖崇拜和与性有关的粗鲁玩笑是其主要内容,后来喜剧逐渐脱离了性内容的原始表现,“讽刺”成为喜剧的一个重要因素。喜剧这一艺术形式随着社会不断变化,以及所反映的内容与题材的不同,又产生了不同变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传奇喜剧(又称浪漫喜剧)、即兴喜剧、宫廷喜剧、情景喜剧、风俗喜剧等。
西方戏剧文学形式成熟非常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表现出其成熟与完整的风貌。但是,西方喜剧一开始就受到排斥,被视为滑稽可笑、低级、粗俗。从亚里士多德到别林斯基的西方喜剧观念实际上指讽刺喜剧,是与悲剧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是“卑贱人物”的写照。尽管西方悲剧观念与悲剧创作构成西方文学的主流,但西方喜剧观念和喜剧创作也在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本·琼生、莫里哀、伏尔泰、狄德罗等一直到荒诞派戏剧,从《巨人传》《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到《尤利西斯》,黑色幽默派作品等都延续和发展了西方喜剧精神。
二、中西喜剧观念及其表现
从亚里士多德到别林斯基,西方的喜剧与悲剧一直是二分对立的。喜剧描写和讽刺的对象多是“坏人”“卑贱的人”“平民”和“野人”等。它的作用是抨击恶习,匡正时弊,惩恶扬善;它的戏剧冲突的本质是表现“自身的矛盾”。
中国传统喜剧描写和讽刺的主要对象是统治阶层,而不是平民野夫。它的讽刺是婉转的,语言技巧高明;歌颂英雄人物,常描写美丽、勇敢、智慧和善良的妇女形象,歌颂淳朴、善良的劳动阶层。它没有悲喜优劣之分,唯有悲喜相间之长。中国每个优秀的古典戏曲都必然穿插精彩的喜剧情节;而结尾是“大团圆”的。
西方喜剧在人物刻画上,注重人性的挖掘与揭示,探求人性当中的善恶、美丑在言行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与错位,揭示人性的复杂性内涵。西方戏剧从古希腊戏剧开始就比较重视对人性的揭示,比如《阿伽门农》《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等都揭示出了人性的复杂。这种创作倾向一直延续下来。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们儿》《暴风雨》《第十二夜》等,都不是简单地写人物和反映人物性格。他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以复杂而生动的剧情和鲜活的人物去传达自己的人生体验。莎士比亚的剧作常常是将“崇高与卑贱、恐怖与滑稽、豪迈与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3]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大师莫里哀的《愤世者》《悭吝人》《伪君子》等一系列喜剧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和“他的同时代悲剧作家高乃依的荣耀相竞争。特别是他的喜剧的社会严肃性与复杂性可以同高乃依、拉辛的悲剧洞析力相媲美。”[4]西方戏剧和喜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人性的关注与揭示,这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戏剧和喜剧的地方之一。
中国传统戏剧对人物的刻画,往往基于社会背景、道德伦理影响下的性格差异的揭示上,注重表象差异所造成的不谐调的喜剧性效果,从道德一维的角度去评判人物,偏重于道德倾向。社会道德批判和讽刺远远超过对人性的揭示,比如《救风尘》《望江亭》等中写一个弱女子或一个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妓女,敢于面对恃官仗势的花花公子或权豪势要的迫害,满怀信心地同他们周旋,最后取得胜利。作品不是深入且广泛地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揭示,矛盾冲突往往是在相对简单而单薄的人物斗争中得以顺利解决的。《西厢记》对正面人物红娘的刻画流于表层,专写她的善良、美丽、勇敢、机智的一面。相国夫人呢?则是从她作为封建礼教代表,在道德层面上批评她是正当爱情的破坏者,而没有从人性层面进一步深入开掘。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是各种力量相互调和的结果。中国传统喜剧,无论是剧情的设置还是人物关系的安排以及矛盾冲突的形成与解决,都服从于和受控于一个预设的“和”的理念,剧情最后往往是大团圆的、人物关系往往斗而不破且握手言和的,最后的矛盾冲突是缓和与调和的。
三、悲喜相分与悲喜相间
西方古典戏剧理论主张悲喜二分,反对悲喜杂混。他们一般认为悲剧是崇高、神圣和严肃的;而喜剧则是滑稽、低级和粗俗的。悲剧意在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喜剧则使人感到可笑和愉快。他们认为将喜剧掺进悲剧,会冲击悲剧。中国传统戏曲一贯重视悲剧的喜剧因素和演出的喜剧效果,充分利用喜剧手法,所谓悲欢离合,实乃人之常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悲喜浑然一体,因此,中国戏曲所引起的情感反应是混合式的、复杂的。
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神话与悲剧,就已表达了强烈的命运观念和主题。也许是西方人通过借饰演悲、喜两类戏剧,表达人与命运的复杂关系,既有对人的伟大的肯定,也有人被捉弄的滑稽可笑,从而进一步引发人们或壮美崇高或欢欣解颐的情感。中国传统戏曲则是以人之“有情”为基点,以人的希望、向往、欲念之类为目的,把人的社会性、伦理性作为戏剧与叙事故事的出发点,来表达“历尽劫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悲喜交加的心理感受。中国传统思想主张“怨而不怒”“发乎情止乎礼”,认为“物极必反”“喜极而悲”等。这样就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不要大喜大悲,而要在悲与喜两种情感之间寻求某种调和。德国美学家、文学家席勒在谈及悲剧与喜剧的差异时说:“悲剧诗人总是实际地处理自己的题材,喜剧作家总是理论地处理自己的题材。”[5]喜剧作家实质上是“预设”地编排故事结构和情节,故事往往是封闭的和理想化的。这种结尾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倾向与愿望。这和西方以否定姿态为基本特征的喜剧性质,是不相同的。中国式的喜剧,热衷于那种如愿以偿的目的实现之“乐”,而并非如西方那种在结尾处使人恍然大悟地感叹“原来如此”似的讽刺喜剧。西方的这种“求真”的思想观念,具有一种探求宇宙真相、世界本体的极端精神。中国“调和”的思想观念,积极的意义在于能使人少些冷酷与恶毒的阴暗情绪和眼光,表现出一种宽容与大度的文化处世方式。但消极的一面在于,人性的恶却隐蔽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我们对社会和人生的悲苦根源的探究不够或浅尝辄止,不对根源进行刨根问底式地发问与追索,本来可以令人深思的地方,人们也敷衍了事,一笑了之。
在欧洲古典美学中,“喜剧”所嘲讽的东西,在意义上是负的,没有价值可言,更多地属于人们主观情感愿望与需要。他们更多地认为人在命运、灾难、世界、宇宙等面前的孤独、痛苦、恐惧才是人之本相,因此,他们热衷于悲剧而视喜剧为附赘,把它看作人类在悲剧的体验中解颐的插曲而非人生主流。另外,在文学作品的审美倾向上也体现出了西方异于中国的地方。美国作家海明威就认为,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只要写到黑奴吉姆被骗子卖掉,故事便应该结束,后边的喜剧全是骗人。在中国往往有一种“圆满”情结,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无一不体现这一情结。
在启蒙主义文学时期,产生了一种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悲喜剧——正剧。它打破了旧有悲剧和喜剧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界限。其基本特征是将悲剧和喜剧两种审美感情糅合在一起,既不使听众陷入悲伤,又不使听众过于轻浮。这样的戏剧形式颇似中国的戏剧风格。
西方由悲、喜两分到悲喜混杂相间的发展变化,是否意味着与中国传统悲喜剧风格实现了历史的呼应呢?分析中西戏剧,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国“悲喜剧”,从本质上来讲,喜是其旨归,是核心,是内在要求。写悲归宿在喜,写悲非仅为悲而写悲。而西方“悲喜剧”,悲是旨归,喜是手段,是方式,是悲的调和剂,写喜而意在凸现悲。在西方文学传统上出现的一系列审美效果:“含泪的笑”“绞刑架下的微笑”“荒诞境遇下的无可奈何的笑”“绝望的笑”等。这些都有着深沉的悲剧意识。西方戏剧由对立的悲、喜两分,到相互结合而形成悲喜剧或者悲喜的混杂性,勾勒了一条西方文化心态、审美心理的变迁轨迹。中国传统戏剧悲喜兼容的特点,似乎没有大的变化,只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我们文学中出现了接受西方悲剧与喜剧相分影响的情形以及在悲剧与喜剧精神方面的变化。中国传统戏剧悲喜兼容的特点,体现了我们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
四、中西喜剧差异之原因
中西何以有如此不同的喜剧观念呢?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西不同的文化以及所形成的异样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伦为核心形成了伦理化的哲学观念。在伦理哲学支配下,民族心理更多关注的是现实生活,或者由阴差阳错等造成的人生起伏跌宕与不幸命运。而对是否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情“命运”,却并不在意,更不要说深追细究了。中国一直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等人世和历史循环的宿命观。因此,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在现实中的痛苦和遭遇。人们在现实中的肉体之悲,常会在精神上找到补偿。也就是鲁迅先生所揭示的国民性——阿Q精神胜利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虽然认为“天意”难违,但是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认为“上帝”意志具有某种绝对性。在我们民间信仰中,有些主宰者的面目是威严不足而慈悲有余的。他们外表威严,可每当人们遭难之际,又多少都会施些或神或魔之法,以助人舒难,救人于水火。可以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人间之“悲”可得“天道”之“慈”作为调和剂。于是,“悲”的浓烈程度得以减轻和稀释,甚至化悲为喜。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倾情于清官戏、大团圆之类的戏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泛滥于当今中国影视屏幕上的电影、电视剧都不约而同地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了。
另外,中国人的“急切实用心理”和“大同”的“调和”心态以及与这种世界观相对应的互补的辩证法,也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观念,即我们“不太介意事物必须经过必要的过程,才能达到最终结果的道理,而热衷于自己的预定意愿,最好转瞬就能实现与成功。”[6]它关注的不是对立双方的对抗与挣扎,而是双方的调合,对事物的认识和期待都是模糊的、含混的。以一种主观的期望来看待当下问题,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不管是在天人关系、人际关系,还是身心关系上,都立足于“和”,把“和”看作目的、终极价值和标准,而不纠缠于对立双方“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7],对达到终极目标的艰难过程也重视不够,而对结果、目标的期待远大于对过程的关注。
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人与世界的对立对抗。西方哲学有尊重人的个体自由、张扬个性的传统,有探求真理、为真理而不惜生命的传统,也有像西绪福斯式的独立承担反抗虚无的精神传统。他们在一次次对世界本体、宇宙真相的探求中和一次次的自我蜕变中体验到世界的无限与不可知,体验到人作为人的自由意志、独立和尊严。他们不问结果如何,重要的是在于追求和奋斗的过程,相信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于当下的奋斗,他们不寄希望于未来的幻想。正像存在主义者所主张的:存在先于本质;世界和人生皆为虚无;人可以自由选择;人生的价值在行动中完成。因此,了解到世界真相后所作出的行动选择,才是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
通过上述一番比较,我们可以对中西喜剧以及喜剧所反映出的精神有了大体上的了解,但其中更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怎么样在中西两种存在很大差异的文化之间实现交流和对话。当前是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多元化意识正在深入人心,戏剧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一个多元并存、空间自由的生态环境,固守一种标准和人为限制都不利于中国戏剧艺术的独立发展。在继承优秀传统戏曲戏剧文化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传统的传承,还要努力实现传统的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只有创新,才有生命力。在当下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在中西两种存在根本差异的文明中,要实现双向互动交流与平等对话,我们应坚持“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精神,着眼于文化发展的问题,着力从人类文明中汲取智慧与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