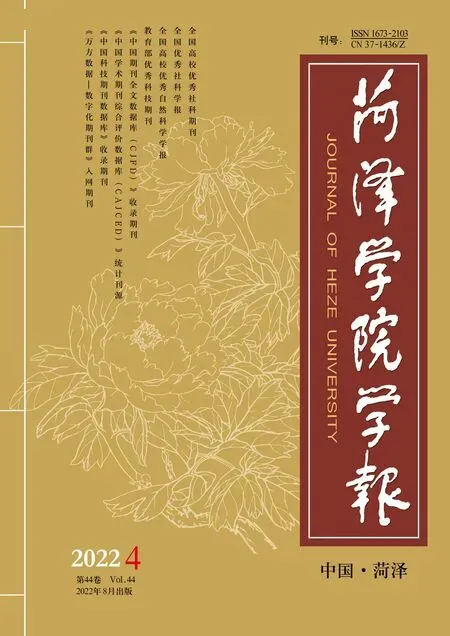反叛与创造
——电影《暖》对小说《白狗秋千架》的改写研究*
2023-01-06李惠马腾飞
李惠,马腾飞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改写理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作为一种创作实践,改写有着悠久的历史,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家在继承前人理论经验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改写进行界定和修改,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改写现象最初表现为对莎剧的改写,大量西方戏剧家如布莱希特、邦德等首当其冲,成为莎剧改写的先锋。此后经过数十年的质疑与停滞,到20世纪90年代,改写理论正式形成且被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中,主要观点有:瑞奇从女性作家的角度出发,认为改写是对文本的“修正”;布鲁姆则在对改写理论的解释中提到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斯科特、泰勒等人通过对莎剧改写研究,强烈意识到互文性对改写理论的影响,到21世纪,随着费什林、福杰等人的深入研究,改写理论最终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时至今日,改写理论被大量应用于翻译研究、影视改写研究等跨理论研究,本文以电影《暖》对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改写为例,探究改编影视作品与原文学作品之间的反叛与创造。
影视艺术自兴起以来便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纵观影视发展史,无数电影导演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促成文学与电影一次次巧妙的结合。近五十年来,电视艺术应运而生,不可避免地向文学寻求帮助,各位导演也不再局限于经典文学作品而是将改写的范围不断扩大,改写的实践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模仿,开始进行“二度创作”。2003年,由霍建起执导的电影《暖》上映,在收获一众好评之后,其原著小说《白狗秋千架》也被更多人熟知,二者的共性与差异也成为讨论研究的焦点。电影在情节与主人公设置等方面遵守了影视改写的“忠实度”原则,没有做大幅度的改变,但在意象、典型人物形象、审美感受等方面适当做出调整,体现了文学文本与电影艺术多元化的审美转向。
一、意象:“白狗”意象的建构与消亡
从小说到电影,意象间的改写差异主要体现在“白狗”上,小说建构了白狗这一意象,并对其赋予深刻内涵,而电影中这一意象则随着情节与人物形象的改变而消亡。
(一)小说中“白狗”意象的建构
白狗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它不仅见证了井河与暖少时朦胧的爱恋,参与了他们生命中的重大转折事件,更是在井河离开后一直陪伴着暖,并在十年后引导井河与暖再次相见。此外,小说情节的每一次转变都因白狗的存在而更具合理性,使读者在作者所设计的跳脱情节中依旧能够有迹可循,而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更是赋予了它非动物性与神秘性。
首先,白狗充当了暖的陪伴者,它跟随着暖,见证了暖整个跌宕起伏的人生。白狗原是井河的白狗,自他离开家乡以后,白狗便一直跟随暖。遭受不幸的暖选择嫁给哑巴,组建了一个更加不幸的家庭。哑巴粗暴低俗,对暖拳脚相加,生下的三个孩子全部有先天缺陷,如此境遇下的暖是孤独的,此时的白狗才是暖真正的陪伴者。此后暖的每一次出现,都有白狗的跟随,对于暖来说,白狗代表了井河,也代表了哑巴,在漫无边际的寂寞生活中,它才是暖真正的陪伴者、倾听者。在文章结尾,暖更是将最为重要而神圣的事情交给白狗,她在高粱地中对白狗说:“狗呀,狗,你要是懂我的心,就去桥头上给我领来他,他要是能来就是我们的缘分未断。”[1]由此可以看出,在长时间的陪伴中,暖早已对白狗有了极大的信任,白狗成为她漫无边际的苦难生活中的一丝慰藉,也是她对不幸生活倾诉的对象。
其次,白狗是井河情感的承载者。井河在十年后再次见到白狗时,他感受到白狗深深的敌意,即便已经认出了井河,它还是冷冷地瞅了他一眼,再也没有了少时的亲热,甚至有了些许敌意。井河深知白狗见证了他与暖的一切,参与了暖起起伏伏的人生,由此才生出了对自己的怨怪,然而这一切,都不是一只无法言语的狗所能表达出来的,不管是它淡漠的眼神,还是井河所感受到的敌意,都是井河自我心理的映射,他将十年未归乡的愧疚以及对暖的忏悔,转移到了白狗身上,此时的白狗身上饱含着浓浓的乡情、恋情,也承载着厚重的文化符号,拷问着离乡游子井河的灵魂。
最后,白狗是暖的表现者。白狗在高密东北乡是非常受欢迎的品种,在它来到井河家时,纯种白狗已经近乎绝迹,就连像白狗这样有些缺陷的,也已很难求,父亲把它抱来时,更是引起众人称羡。而这时候的暖,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比起大演员也毫不逊色,如果不是破了相,她会如阳光一般,始终闪闪发光。在井河离乡归来之后,见到了十年未见的白狗和暖姑,此时的白狗眼中已经有了浑浊,也不再像其它壮年狗见到生人那样露出一副凶相,而是慵懒的趴在自己的干草窝里,时不时的叫一两声,从形态到动作都流露出了岁月的痕迹。此时只有29岁的暖,也与白狗一样,呈现出与年龄不匹配的样貌与形态。井河再次见到暖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皮肤黝黑且行动粗俗的女人,俨然没有了当年清秀的模样和气质。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文中对白狗的描写,实则是他从男性角度对暖的一种审视,同时加强了白狗这一意象的非动物性。
小说作者莫言对白狗这一意象的设置是非常高明的,文中的白狗,既充当了暖的陪伴对象,也承载了井河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同时也是暖的表现者,作者用隐喻的手法为白狗这一意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给予读者更强的审美体验。
(二)电影中“白狗”意象的消亡
霍建起导演曾说起:“暖是原文的女主人公。另外,在原著中白狗也是一个角色,而在我的电影里被去掉了,如果沿用原来作品的名字,感觉就不合适了。用《暖》作片名,一方面是由于影片是围绕着这个女孩儿的命运写的,同时也是在表达片中男孩儿对女孩儿‘暖’的一种称呼和呼唤。再有,这个故事虽然有些伤感但还是挺温暖的。”[2]可见,在电影中白狗这一意象被去掉的原因有三:一是电影名称的改变;二是电影中的暖更加具有的女性意识;三是小说中白狗所依存的环境氛围在电影中不复存在。
首先,原著小说以白狗与秋千架命名,同时围绕这两大意象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了暖、哑巴等典型人物形象,其中白狗作为重要的线索几乎贯穿了整篇文章,使小说在情节转换时显得更加柔和而不生硬。在电影中,导演将影片的名称进行调整,用女主人公暖来命名,突出了电影围绕人物进行叙事的特征。同时,电影在进行情节转换时主要依赖于镜头的转换与拼接,这意味着电影不需要白狗这一线索进行叙事线的引领,因此在电影中不再出现白狗这一意象。
其次,与原著小说相较,影片中的暖更具有女性意识。在原著小说中,作者通过井河这一男性视角对暖进行人物刻画,十年前的暖光彩夺目,十年后的她粗俗丑陋。不仅如此,从暖自身出发进行审视也不难看出,遭受不幸之后的暖逐渐臣服于生活,她嫁给哑巴,生下三个有缺陷的孩子,生活的摧残使她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能力与勇气,变得冷漠而自怨自艾。在这样的人物形象之下,作者建构了白狗这一动物形象,表面看是对小说的内容进行丰富与充实,实则是为了衬托出暖这一人物的悲剧性,从而展现了农村机械、痛苦的劳作压抑、湮没了一个纯情少女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进而膨胀了她内心的恨意与绝望。可以说,小说中白狗的存在使女主人公暖的悲剧性上升到顶峰。而电影《暖》对女主人公暖的性格特征进行了调整,井河十年后再次见到暖时,她虽然早已不复当年的光芒,也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但她并未就此自怨自艾怀抱遗憾度过一生。影片中的一个情节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井河曾经在去城里以后给暖寄过一双皮鞋,这不仅代表了井河始终牢记对暖的承诺,同样预示着暖还有能够去城里的希望。但是暖并未抱着这不切实际而又渺茫的希望生活,而是选择认清现实,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十年后井河去暖家中探望她时,暖特意穿上了从前井河寄给她的皮鞋,保存完好锃亮的皮鞋与暖的装扮十分不配,但是她姣好的面容依然留有往昔的光彩,能够与美丽的皮鞋相搭。在暖的心中,即便已经清楚再也配不上井河,却也不愿把自己的落魄展现在他的面前。在吃饭过程中,暖自豪的告诉井河,她将与丈夫一起攒钱为女儿买一台电视机,这样的暖,虽也历经风雨,却依然保有自己的女性意识,她独立自主,内心强大,并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自然也不需要白狗的陪伴与衬托。
最后,白狗的产地是高密东北乡,小说开篇便在白狗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地域烙印,这与文中男主人公的思乡情绪相吻合,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浓郁的恋乡情结。而影片《暖》则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改为了江南水乡,这种变化与影片想要营造的温情、柔婉的情感氛围相匹配。虽然江南也产狗,但已无法重现小说中所要表达的狗身上那种高贵血统和神性,影片中白狗的缺失合乎内在逻辑,所以导演索性去掉了这一意象,反而更加契合整个影片的情感基调。
二、人物:典型人物形象的美化
小说在构造情节时创造了男女主人公,但实际上作者是以男主人公的视角为焦点,并以他为叙述者来看待整个故事的发展与演变。而在影片中,导演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的视角,带领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情节的跌宕起伏。这样的改写使得两部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在性格方面出现了互文性差异,其中以暖和哑巴这两个人物最为突出。
(一)暖
小说中的暖是典型的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作者以男主人公井河的眼睛为叙述焦点,对女主人公前后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十年前的暖是光彩夺目的,她美丽、清秀,自信而清高,不仅得到了仪表堂堂的蔡队长的青睐,也使井河着迷。而作者对十年后的暖更是进行浓墨重彩的描写,她变得丑陋、粗鄙,“右边没有眼,也没有恨,深深凹进去的眼眶里,载着一排乱纷纷的黑睫毛。”同时她怨恨、偏激,在井河问她几个孩子了,她形容生孩子像下狗一样,“一胎生了三个,吐噜吐噜的,像下狗一样”,问到孩子的性别,她答道:“全是公的。”在说到白狗时,她说到:“活不了几天啦,再一晃儿就该死啦。”[3]作者运用一系列语言、动作以及细节描写,将事故发生前后的暖进行细致的刻画,使读者感受到前后期人物性格、命运的变化,表现了在遭遇不幸后暖的悲剧性,给读者展示了一个痛苦的灵魂。
影片《暖》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对暖的形象塑造进行了调整,同样遭遇了生活的不幸,同样嫁给了看起来更相配的哑巴,同样受尽了生活的折磨,影片中的暖却被极大的美化。首先,导演将暖由瞎子变为了瘸子。原文中秋千架的事故使暖的面容被毁坏,一只眼睛被槐针扎瞎,永远的变成了独眼,对于任何一位女性来说,容貌都是及其重要而神圣的,这样的事故无疑将她彻底毁灭,也确实改变了她的整个命运,不论是对爱情的绝望,还是嫁给丝毫没有感情的哑巴,抑或是接受生命的摧残,都与她脸上的残缺息息相关。而在电影中,霍建起导演保留了暖姣好的面容,将她的残缺转移到了并不十分重要的脚上,这虽然不影响整个故事的情节,却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暖的命运。导演选取柔美而又刚毅的李佳来饰演暖这一角色,她在演绎暖走路的一瘸一拐时,不但没有引起观众的反感,甚至会增添一份对女主角的怜悯之情,从而使得整部影片充满温情。其次,影片中加入了很多小说没有的镜头,使得暖的形象更加立体鲜明。比如在事故发生前,暖与舞蹈队的姐妹们一起在谷堆旁练舞,嬉笑打闹的氛围展现了暖的活泼与俏皮。在井河去暖家探望时,暖没有像小说中一样局促不安,反而十分淡然且彬彬有礼,她从容地张罗着饭菜,怜爱地看着自己女儿,幸福地望向自己的丈夫,显然十分满足于当下的生活。
可以说,暖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在小说与电影中有着较大的差别,小说中的暖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丑陋不堪、尖酸刻薄,却又因渴望依靠男人改变生活而令人唏嘘叹息。与此相比,电影中的暖是一个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却依旧热爱生活的人,她独立而满足,温和而从容,给予荧幕前的观众精神层面的鼓舞与力量。
(二)哑巴
小说中对哑巴描写的篇幅很少,虽然是女主人公暖的丈夫,但作者并没有对哑巴进行过多的介绍,所有的描写几乎都集中在一处,就是井河再次登门拜访暖的时候。作者通过井河的视角,对哑巴进行了这样的描写:“出来迎接我的却是一个满腮黄胡子两只黄眼珠的彪悍男子,他用土黄色的眼珠子恶狠狠地打量着我,在我那条牛仔裤上停住目光,嘴巴歪歪地撇起,脸上显出疯狂的表情。他向前跨一步——我慌忙退一步——,翘起右手的小拇指头,在我眼前急遽地晃动着,口里发出一大串断断续续的音节。”[4]短短的两句话便将哑巴这一人物的主要特征崭露无遗,即彪悍、粗俗、凶神恶煞,同时也为后文描写哑巴与暖之间的交流做下铺垫。
在小说中,暖与哑巴结婚前并无任何感情基础,二人的结合是“独眼嫁哑巴,弯刀对着瓢切菜,并不委屈着哪一个”。哑巴的霸道与蛮横,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里,与暖之间更是毫无爱意与温暖可言。见到暖昔日的情人,哑巴丝毫没有考虑过暖的感受,在他所有的动作中,透露出来的都只有强迫和占有。正如作者所描写的,“哑巴猛地把她拽开,怒气冲冲的样子,眼睛里像要出电。”“哑巴愤怒地吼叫着,左手揪住暖的头发,往后扯着,使她的脸仰起来,右手把那块糖送到自己嘴边,用牙齿撕掉糖纸,两个手指捏着那块沾着他黏黏的口涎的糖,硬塞进她的嘴里去。”文章通过对哑巴一系列的动作描写,充分展现了哑巴的粗俗与暴虐。除此之外,暖与哑巴一起孕育了三个孩子,也全是哑巴,看似有一个美满的大家庭,暖却始终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也从未得到过来自丈夫的温暖和尊重。可以说,与哑巴的结合并未给暖带来任何来自于家庭的幸福与安定,反而增强了她的悲剧性。同时,对哑巴的形象塑造也间接体现了小说结尾的合理性,正是由于与哑巴感情的淡漠,才令暖更加留恋与昔日青梅竹马之间的感情,她在无望的生活中力求一丝温暖,即便违背伦理道德也在所不惜。
与小说不同的是,影片中哑巴的镜头明显增多,甚至比男主角井河还要多,这足以看出在电影中哑巴具有重要的话语作用。同时,影片中的哑巴少了戾气,多了善良,少了粗暴,多了温柔。哑巴和暖在少时便相识,还是少年的哑巴便对暖怀有情义,但那时候的暖能歌善舞,拥有脱俗的容貌和完美的身材,哑巴自知两人的差距,选择默默守护,在井河离开之后,哑巴没有强迫暖,依然选择无声的守候。情节的转折出现在井河第二次给暖来信的时候,哑巴看到暖将信撕碎扔进了水里,他明白了暖内心的抉择,适时的出现在她身边,最后与她结为夫妻。与哑巴的结合不是暖因生理上的残疾而做出的无奈之举,而是遵循她内心的想法,与善良的哑巴真心相守。当井河归来时,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他感叹命运的无常,对暖感到愧疚与惋惜。可当暖与井河再次四目相对的时候,她对他说,我挺好的,这并不是暖为了在昔日恋人面前保持自尊而强颜欢笑,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慨。影片中的结尾是情节的高潮环节,也是人物形象发展到顶峰的部分。哑巴以看似粗暴的方式将暖母女推向井河,也正是这一举动将人物的无私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与小说的结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审美感受:残酷到温情的转变
通过上文分析意象与人物性格方面的差异不难看出,作者在原著小说中运用苦难叙事,描写了一个充满悲剧情怀的爱情故事,其中的女主人公暖穷其一生也未寻找到自己想要的依靠,小说结尾的借子更是将人物的悲剧性上升到顶峰。电影将名字由《白狗秋千架》改写为《暖》,其中的人物性格特征被美化,情节设计更注重苦难中孕育真情,甚至于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也由荒凉苍茫的高密东北乡改为了江西婺源一处风景秀美的小镇,一系列改写十分明确地说明电影试图为观众营造与小说不同的审美性感受,正如霍建起导演所说:“我希望在悲之中有美好的温暖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只看到恶的东西,就会太绝望了,无论在何种环境下,能客观地看世界,客观地去理解这个世界,并化解你所遇到的不如意,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你会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寻到一种快乐,我不否认美化的倾向。”[5]霍建起导演一直善于用景致来表达人物情绪,亲情与爱情,希望与失望,挣扎与痛苦,如小桥流水般缓缓划过荧幕,不论是《那人·那山·那狗》,还是本文所研讨的《暖》,都延续了导演一贯的风格:柔和,温情,反映人与人之间的至情至爱,给予观众不同于小说的审美感受。究其原因,不但是因为影视改写理论的发展,也与影视媒介的特征以及影视改编的市场性有关。
(一)影视改写理论的叛逆
自影视改写出现以来,“忠实论”一直被电影导演频频引用,法国导演罗贝尔·布莱松在《非纯电影辩——为改编辩护》一文中,以作家内尔纳诺斯的《乡村牧师日记》的改编为例,提出只有像它这样原封不动地转现原著在银幕上的改编才是最高级的改编[6]。德国电影理论家奇·克拉考尔继承并发展了巴赞的改编理论,认为电影必须记录物质世界,应当追求形象的真实,而一切抽象的真实,包括内心生活、思想艺术和心灵问题,都是非电影的[7]。随着时代和文化语境的改变,“大话”“戏说”等与“忠实原著”完全不同的改编方式兴起,一元论的价值观念开始遭受质疑,在导演和改编者眼中,原著不再是“神圣”的,而是可以进行解构和加工的素材。霍建起导演在对原著进行改写时,既没有完全忠实于小说,又保留了其中的核心部分,更倾向于借用的改写方式,正如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所说:“改编就是把原著当成未经加工的素材,可以按照电影自己的艺术要求进行创作,不必注意素材所已具有的形式。”[8]
(二)影视传播方式更具共情性
与小说文本相比,电影的大荧幕展现形式更能引起观众的共情意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无法带给读者情感共鸣,而是与电影对比时,小说文本用文字形式叙述出当时的人或事,有自身的虚构性,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始终保有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情感判断。而电影艺术运用光影技术将人物与故事情节以更直观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视觉的直接冲击更能带给观众强烈的快感,使得他们更加身临其境,因此,电影中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人生遭遇更能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同时,约翰·费斯克谈到观众对电影文本的接受时指出:“电影观众对于文本的接受方式较为单一,因为电影只提供了一种观看方式,所以不需要争夺观众的注意力,观众自然而然的投入到电影内容中。电影观众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力”的,他们只能服从电影的话语环境。”[9]因此,小说从开头到结尾始终弥漫着令人绝望而窒息的悲剧气息,这种绝望悲凉之感不仅会给篇幅不长的文字赋予一种沧桑感,吸引读者为人物的命运与遭遇唏嘘不已,而且会对读者产生情感上的冲击。电影却在悲情的基调中加入了温暖的元素,以江西婺源为景,更为电影增添了一丝唯美与诗意,导演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改变,一方面是为了让人们在观看悲剧时会对主人公产生怜悯之情,意识到自己是善良的,从而产生愉悦的快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观众在观看影片时不会过度绝望,只有在绝望中孕育着希望,才能够使观众在绝望中看到希望,从而得到精神与心灵的净化与升华。
(三)市场经济的影响
电影的商业性使得影视化形式更受市场经济影响。随着影视技术不断发展完善,电影行业的竞争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势头,各种类型的影片用尽十八般武艺在节假日蜂拥而至,贺岁档、暑期档、国庆档,电影行业逐渐由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导演们也在符合大时代主题的前提下,越来越注重大众的审美需求。在这样的市场影响下,我国电影的发展在主题方面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其中一种便是温情化电影的泛滥。不管是本文所谈论的《暖》,还是与疾病和健康相关的《肿瘤君》系列电影,甚至在《集结号》《红海行动》等战争性电影的拍摄中,也不可避免的以温情式结局作为结尾,这已然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普遍现象。《暖》作为一部会上映的市场电影,不可避免要符合市场化的需求,因此,霍建起导演在对《白狗秋千架》进行改写时,不仅需要考虑对原著的忠实度问题,还需要考虑观众的审美需求。所以,他将影片中过于残酷的部分进行了修改,避免给观众带来情感上的不适,进而取得可观的票房收入。
综上所述,霍建起导演在对《白狗秋千架》改写时,既遵循原著,也注入了二次创作的元素,同时考虑到影视发展的市场因素。总体来说,小说《白狗秋千架》与电影《暖》是文学作品两种不同的展现形式,它们在各自所属的传播媒介形式下散发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在传媒飞速发展的今天,影视对文学文本的改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能够使文学审视自身的缺陷与短板,同时也能避免影视文化走向追求平面、低俗、消遣的纯娱乐效用的境况,是一种双向获利的发展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