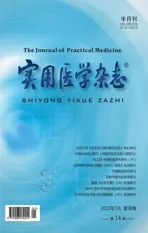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治疗的血流动力学研究进展
2023-01-05唐前辉陈靖杨晗覃晓
唐前辉 陈靖 杨晗 覃晓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南宁 530021)
主动脉夹层(aortic dissection,AD)是指主动脉内膜破裂,血液在压力作用下经内膜破口进入血管壁中层,导致主动脉壁纵向分离,形成真假两腔[1],其发病率为2.9~4/10 万[2]。该病起病急,病死率高,院前病死率高达17.6%,发病后24 h 内死亡占21.4%[3]。自1999年首例Stanford B 型夹层应用腔内修复技术(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EVAR)治疗以来,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已广泛用于Stanford B 型夹层的治疗。腔内修复术改变了既往开胸、开腹等大创伤性治疗主动脉疾病的现状,且疗效确切,创伤小,大大降低了患者长期死亡率[4]。腔内修复术通过置入覆膜支架,将动脉内膜破裂口隔绝,从而阻止血液经破裂口进入假腔,达到治疗目的。施行腔内修复术时,要求近心端至少有1.5 cm 的正常血管作为支架的锚定区[1]。因此,对于累及重要分支动脉开口的复杂型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术的使用受到限制。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之后,杂交手术、烟囱技术、开窗技术及分支支架技术现已应用于该类复杂主动脉夹层腔内的治疗。考虑目前主动脉夹层的治疗方式多样,结合各治疗措施的优势及缺陷,现就主动脉夹层及各治疗方式的血流动力学特点作一综述,为复杂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提供参考。
1 主动脉夹层的血流动力学特征
主动脉形态、主动脉壁弹性和血流动力学均可影响主动脉夹层的重塑和转归。主动脉整体呈“问号”状,主动脉“问号”形状的大小可影响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后假腔血栓化的程度,“问号”的程度越高,假腔形成完整血栓的可能性越小[5]。而破口的数量影响主动脉直径变化,与主动脉直径稳定的患者相比,主动脉进行性扩张的患者破口数量更少[6]。主动脉壁弹性下降可导致假腔中部和远端的直径增加[7]。同时,假腔内的射血分数也是主动脉扩张的独立预测因子[8]。血流在第一破口分裂,分别进入真腔和假腔,真腔具有更高的血流速度,以及更低的逆流指数,而假腔中的血流呈涡流[9]。基于真腔与假腔内不同的血流动力学,在两者之间存在压力差,该压力差沿主动脉从正到负分布,在夹层的某个位置,存在一个压力差等于0 的平衡位置。支架置入后,促使这个平衡位置向远端移动。若术后平衡位置移出夹层区域,该部分患者预后明显改善,而平衡位置转移到腹主动脉区域的患者,预后较差。支架置入后3个月平衡位置向远端移动的幅度与随后的真腔扩张和假腔血栓化相关[10]。综上所述,主动脉夹层的发生、发展受多个因素的影响,而血流动力学因素在其中充当了很重要的作用。
2 杂交手术
杂交手术并不是完全的腔内治疗方式,而是将传统开放手术与腔内修复术结合,其优势在于减少了传统开放手术的创伤,降低了手术并发症。针对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张勇等[11]提出了将无冠窦补片应用于Standford A 型夹层根部成形手术中,效果显著。针对Stanford B 型夹层,其原理主要是通过腔内修复技术处理主动脉病变,再通过开放手术的方式重建重要的分支血管,该手术方法一方面延长了腔内修复术的锚定区,为支架处理夹层病变提供空间,一方面又保证了重要器官的血供。杂交手术相对于完全开放全弓置换手术,早期并发症和早期死亡率均较低,分别为9.2%和15.6%,而完全开放手术早期并发症和早期死亡率分别为17.4%和25.7%,并且杂交手术组的1、3、5年生存率均优于完全开放手术组[12]。对于行主动脉腔内修复术,联合右腋动脉-左颈总动脉-左锁骨下动脉转流的患者,虽然手术后改变了弓上分支血流的原有形态,但是并未影响颈动脉的血流动力学,因此未见有脑梗死、昏迷等严重神经系统并发症[13]。但是因为术中需阻断部分颅脑的血供,因此术中需严密监测,预防颅内缺血的发生,目前结合4D-CTA 技术,可切实监测头颈的血液循环,量化动脉、静脉的血运时间[14]。
血流动力学研究表明,杂交手术后一年,假腔较前明显缩小,主动脉弓曲率也有所减小,真腔的压力随时间延长,最终会接近假腔的压力。然而,杂交手术后主动脉弓部变长,远端腹主动脉直径较术前扩大[15]。因此,杂交手术虽然可恢复真腔中的血流并促进主动脉的正向重塑,但是需要严格监测主动脉弓及远端腹主动脉的变化。虽然杂交手术较完全开放手术缩短了手术时间,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但是与全腔内手术相比,操作仍较繁琐,手术时间长。因此杂交手术的开展需选择合适的患者,进行充分的术前评估,从而提高手术成功率,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3 烟囱支架
烟囱技术指行主动脉腔内修复术的同时,在分支动脉内置入小型支架,且近心端伸入主动脉内,从而保留被主动脉支架覆盖的重要分支血管,该技术最早于2003年由GREENBERG 等[16]提出。该技术有效解决了支架近端锚定区不足的问题,拓展了腔内修复术在Stanford B 型夹层的应用,避免了开放重建重要分支血管的杂交手术风险。但是烟囱技术对支架要求较高,若支架不合适,有Ⅰ型内漏及支架闭塞风险。据报道,对于保留左锁骨下动脉的烟囱支架,Ia 型内漏发生率可高达19%,支架闭塞发生率为2.5%[17]。内漏的发生与烟囱的类型及近端撕裂口的位置相关,三烟囱技术比单烟囱技术和双烟囱技术具有更高的即时内漏发生率,且近端破口位于0 区的夹层即时内漏发生率也更高。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内漏都需要积极手术干预,随访发现约36.0%的内漏可自行消失[18]。
针对烟囱支架的闭塞,术后烟囱支架内管腔的减小以及流速的增加导致支架内复杂的血流动力学和高的壁剪切应力,当管腔面积<14 mm2,收缩压梯度>25 Pa/mm,收缩时血管壁剪切应力>45 Pa 时,将有可能导致烟囱支架的闭塞[19]。KOENRADES 等[20]发现在整个心动周期中,支架末端角度平均变化为(1.7± 0.8)°。虽然烟囱支架有限的偏转角度降低了支架疲劳弯曲的风险,但烟囱支架末端的角度变化可能会引起晚期支架的闭塞或狭窄。一项针对烟囱支架置入前后肾动脉压力梯度的研究表明,烟囱支架置入后的肾动脉压力较置入前无明显下降[21]。然而,在血流量方面,烟囱支架和开窗支架均可导致目标脏器的血流下降,但烟囱支架下降更明显。烟囱支架可导致血流量减少43%~53%。而开窗支架的血流灌注减少15%。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烟囱支架的长度及扭曲导致的[22]。与原位开窗组相比,烟囱组的手术和透视时间更短,失血量更少,使用的造影剂量也更少[23]。烟囱技术有效保持了主动脉大支架的完整性,避免了对主体支架的人为改装,并且有效缩短手术时间,但是由于在有限的空间内重建分支血管,需要各支架之间具有很好的相容性,避免内漏的发生,同时选择合适的支架长度,避免支架扭曲,减少支架闭塞等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4 开窗技术
主动脉支架开窗技术目前包括体外预开窗及原位开窗两类。体外预开窗是指在影像学精确测量的基础上,在支架主体植入体内之前对预计覆盖分支血管开口的位置上提前将覆膜部分修剪掉,从而保障血液能经修剪的破口,流入分支血管内。原位开窗技术包括激光、穿刺针、射频等技术在置入体内的主体支架上开窗,随后经分支血管置入分支支架。原位开窗需要术者术中精准的定位与操作。为了提高开窗的精确度,3D 打印技术已应用于辅助开窗。与针刺开窗相比,使用射频或激光开窗技术在窗口的最大面积、形状方面无明显差异,但是射频或激光可产生移植物碎片及有毒物质,需进一步关注[24]。激光开窗的体外研究表明,分别使用6 mm 和8 mm 直径的球囊扩张窗孔可提供最小的撕裂和精确的窗孔。直径大于10 mm 的球囊增加了对覆膜支架的撕裂和破坏。另外体外试验还发现在过滤的盐水溶液中观察到熔化的纤维残余物[25],这些纤维残余物在体内是否会造成进一步的影响尚未见相关报道。
PIAZZA等[26]通过体外实验表明,波长为810 nm的激光用于血管内移植物织物的开窗安全、有效。为了更精确的开窗,CONDINO 等[27]开发了新型电磁可跟踪仪器,为术中开窗装置提供精确、有效的导航,并增加开窗操作的稳定性。虽然原位开窗的手术成功率高达96.9%,且长期通畅率可达97%[28],但是依旧存在内漏及支架闭塞的风险。对106 例接受开窗技术的患者进行随访,发现Ia型内漏发生率为1%[29],但开窗治疗的患者,有6%的患者发生卒中[30]。开窗技术面临的内漏问题,主要来源于开窗后窗孔边缘不整齐、松散,在心动周期中压力的变化引起移植物的疲劳,从而影响支架的稳定性。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体化织物覆膜梯度化结构的设计理念被提出[31]。因此,为了降低内漏的发生率,提高开窗的精确度,需要在覆膜支架的材料和辅助开窗技术上,不断探索,结合最新的人工智能手段,开发新的技术途径。
研究其血流动力学因素,发现开窗支架对主动脉血流动力学有明显影响。分别在左颈总动脉和左锁骨下动脉行开窗并置入支架后,左颈总动脉和左锁骨下动脉的管壁压力较前下降,并在左锁骨下动脉支架内外壁之间出现压力差。血液流经开窗支架周围时会发生加速,并且在左锁骨下动脉支架后方的主动脉弓处减速,这一改变导致该区域成为血栓形成的高发区域。因此,需要对接受开窗支架治疗的患者密切随访[32]。开窗支架对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大小与开窗支架进入主体支架的长度相关。三种体外模型中模拟分析不同的原位开窗策略,在开窗支架的突出长度为23.2 mm的模型中,在开窗支架表面发现压力差,并观察到支架周围的血液加速现象。只有2.36%的血流分配给左锁骨下动脉。开窗支架的突出长度减半的模型中,分配至左锁骨下动脉的血供升高至4.01%。对于去除开窗支架的突出部分的模型,血供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达到了6.14%[33]。原位开窗技术的难点在于穿刺破膜,而体外开窗技术的难点在于支架定位,因此,开窗技术要求操作者有熟练的手术技巧,且选择适当的支架类型及材料,适合有经验的大中心开展。
5 多层裸支架
为了弥补上述技术的不足,降低手术风险,提高手术治愈率。临床需要更方便、更安全的操作系统。多层裸支架的概念最早于2000年报道,BENNDORF 等[34]应用2 个裸支架重叠治疗颈动脉夹层,术后造影提示假腔流速显著减少,随访发现假腔消失,真腔血流不受影响。多层裸支架是有孔的支架系统,相对于覆膜支架机械性的完全隔绝血流不同,多层裸支架用于治疗动脉瘤、动脉夹层的机制是改变瘤腔或假腔内血流动力学,诱导血栓形成,同时不影响重要分支血管的血流[35]。
在主动夹层的治疗方面,2011年CHOCRON等[36]首次应用多层裸支架治疗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术后3 个月随访发现假腔消失。同时他们指出多层裸支架置入后,支架外的血流速度较前下降90%,为假腔内血栓形成提供了血流动力学基础。SULTAN 等[37]报道应用多层裸支架治疗主动脉夹层的手术成功率为97.4%,未见因手术失败或动脉破裂致死亡患者,且无术后并发内脏缺血或重要分支血管血栓形成患者。STEFANOV 等[38]分析接受多层裸支架治疗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及分支血管情况,发现真腔体积由(175.74 ± 98.83)cm3增加到(209.87 ± 128.79)cm3,假腔体积由(135.2 ±92.03)cm3下降到(123.19 ± 110.11)cm3,假腔压力分别下降(6.23 ± 4.81)%和(3.84 ± 2.59)%,且颈动脉、肾上腺及肾脏的供血均较前增加,随访期间未见有夹层破裂、截瘫等并发症。但是在该报道中,并未见假腔完全闭塞的病例。COSTACHE等[39]通过计算流体力学分析了多层裸支架置入后真假腔的形态变化,发现术后真腔体积增大和假腔体积减小。在血流动力学方面,多层裸支架置入1年后,真腔的血流变为层流,同时伴随真腔压力的下降,这为真腔的重塑提供了有力条件[40]。基于上述研究数据,目前认为,多层裸支架在治疗主动脉夹层方面,短期疗效确切。但上述研究纳入样本量小,随访时间短,其在临床广泛、大量应用的证据仍不足。
因为多层裸支架在隔绝动脉瘤、夹层血流的同时,不影响重要分支血管的血流,有效解决了主动脉疾病在行腔内修复术时,近端锚定区不足或累及重要分支血管的问题。但是多层裸支架置入后,诱导瘤腔内血栓形成,并非机械性隔绝血流,因此,在多层裸支架置入术后的一段时间,仍有血流经过支架间孔隙进入瘤腔导致动脉瘤破裂的风险。不仅SALVATI 等[41]报道多层裸支架置入后,动脉瘤体积进一步扩大并接受进一步治疗的病例,而且KANKILIÇ 等[42]亦报道了1 例胸腹主动脉瘤患者,术后3年出现动脉瘤扩大,肾动脉闭塞。KE 等[43]提示,应用多层裸支架治疗主动脉瘤,有12.6%的患者动脉瘤可持续增大,内漏发生率为1.9%,分支血管的通畅率为98.4%。对于主动脉夹层,多层裸支架置入后,是否仍有血流经过支架的空隙进入假腔,影响夹层的重塑,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6 分支支架
左锁骨下动脉作为左侧椎动脉和左上肢重要的供血血管,若左锁骨下动脉被覆膜支架覆盖,30 d 卒中发生率为8.2%,显著高于左锁骨下动脉血运重建的患者(0%),并且左锁骨下动脉覆盖后有11.5%的患者发生左上肢缺血[44]。因此保留左锁骨下动脉显得尤为重要。分支支架作为新型的支架材料用于治疗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其手术成功率为97%,内漏发生率为5%,分支部分的支架闭塞是导致手术失败的主要原因。分支支架置入后随访一年内病死率为5%,六年内病死率为7%。并且在随访过程中,在支架的近端和远端分别发现了新发的破口,并且术后分支支架闭塞的情况也存在[45]。对比烟囱技术,分支支架的分支闭塞及内漏发生率更低,且更有利于胸主动脉夹层假腔的血栓化[46]。应用内嵌式模块化设计的WeFlow 分支支架是可用于重建弓上分支的另一款支架,该支架可能拓展腔内治疗的适应证,包括可能应用于Stanford A 型主动脉夹层。目前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相对于烟囱技术、开窗技术的操作难度,分支支架优于是成熟的支架系统,操作更方便,操作流程也更规范化,同时对支架本身的改变也更低。同时,由于因分支支架的设计更贴近于临床,符合主动脉及分支血管的血流动力学特点,因此有望成为未来复杂主动脉夹层有效治疗手段。
7 总结
综上所述,复杂Stanford B 型主动脉夹层的全腔内治疗方式主要包括烟囱技术、开窗技术、多层裸支架技术及分支支架技术,各项技术在使用及患者选择方面各有优缺点,在临床工作中可参考主动脉夹层及相关治疗方式的血流动力学特征,结合患者的病情及医疗条件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同时,深入研究主动脉夹层的血流动力学特征,积极的将人工智能与临床科研相结合,研发新型支架及材料,将有利于未来全腔内治疗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