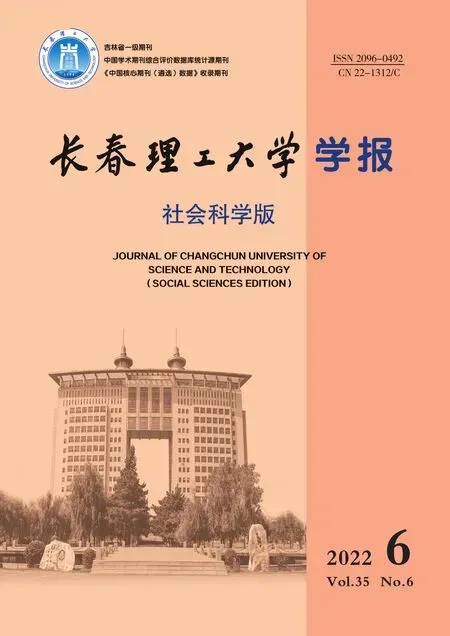张翎小说《阵痛》中的“城与人”
2023-01-05付兰梅周施祥
付兰梅,周施祥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2)
温州籍新移民女作家张翎①1957年出生于杭州,祖籍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5岁时回到温州市区县前头生活,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目前,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市。是当下炙手可热的新移民作家之一,她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创作。近年,张翎创作的有关温州的代表性小说有《阵痛》(2014)、《流年物语》(2016)、《劳燕》(2017)、《廊桥夜话》(2019)等。
张翎的长篇小说《阵痛》,以时间为线分四部分描写上官吟春(后改名为勤奋)、孙小桃(后改名为孙小陶)、宋武生、杜路得四代女性的生活,将上官吟春、孙小桃、宋武生祖孙三代温州女性独自生产的痛楚放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以母亲的坚忍象征民族的生命力。
关于张翎小说中的“温州”的研究成果共计约15篇,主要集中在温州文化、温州形象、温州情怀等方面②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司方维的《论张翎小说中的温州书写》阐述了温州是故事的背景,更代表了梦想和生命力;汪雪莲的《移民的况味故乡的回望》描述了张翎用温情、平淡的笔调将普通小人物的生活故事与历史变迁悄无声息地糅合在了温州;章怡虹、周春英的《精神原乡与基因来源——论温州文化对张翎小说的影响》通过张翎作品中的温州元素,探究其浸透着温州文化的内在意蕴及温州文化对张翎小说创作品格的影响。。关于张翎小说中的“温州人”的研究成果共计约70篇,多集中在女性形象研究、移民形象研究等方面③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周春英的《她们的背影中有“温州”二字——张翎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共性》阐明了张翎笔下的这些女性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具有坚韧精明、敢于闯荡、自强自立的文化共性;郭坤英的《论张翎小说中的女性书写》重在写历史潮流之下或婚恋家庭中小女人的命运,她笔下的女性大多善良、敢冒敢闯,彰显着温州人精神;葛倩倩的《所有的写作都要落到土地上》中的女性、气血和精神家园是张翎书写温州人形象的关键词。。可见,学者对张翎小说中的“温州”与“温州人”早已有了深刻的关注,但对温州的“城与人”呈现给读者的表象特征和深层结构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目前,张翎小说中的“城与人”的问题的研究暂未见及相关学术成果。相较于张翎前期创作的怀旧类小说,《阵痛》对“温州”和“温州人”有着更为丰富的论述,尤其是对温州人的研究。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对这篇小说中“温州”和“温州人”关系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拟从“温州”与“温州人”、“城”与“人”的关系、“城与人”折射出的温州文化三个方面对《阵痛》中“城与人”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挖掘出“城与人”的深层次关系及其赋予的特殊情感,同时展现小说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温州文化。
一、《阵痛》中的“温州”与“温州人”
张翎在《阵痛》中通过对温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描绘,展现古朴清新的温州形象,并通过其塑造的各类温州人物形象,彰显温州人的坚忍勇敢。
(一)古旧清新与包容开放的温州形象
温州是张翎生活和成长的地方,基于个人成长经历和对故乡的关注,张翎的小说大都围绕温州展开,温州是张翎的精神家园。《阵痛》主要从温州老城区的街巷与景致对古旧清新的温州形象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同时,张翎还向读者展现了温州包容开放的形象以及历史人文的演变,抒发自己对温州的深厚情感与眷恋,并对温州景象进行细节化描写,直接或间接地叙述着温州故事。
张翎在《阵痛》中将温州这座城市的整体布局平铺在读者面前,通过描绘温州老城区的市井街巷,展现温州的古旧形象。“谢池是一条巷的名字……从巷口看到巷尾没有一座楼,都是矮秃秃的平房。那平房见过了太多的朝代的太多的烂事,那砖那瓦那门那窗都是一脸的愁苦相。”[1]71谢池巷虽说年代久远又有些破旧,却坐落在温州的中心,拐过小巷边上就挨着百货公司、中山公园、华盖山等。勤奋嫂的老虎灶就开在谢池巷口,“两眼大灶,两个风箱,两个大木桶”[1]72就是全部家当。老虎灶虽听着有些吓人,却不过是一个卖热水的小铺子,一分钱可以灌一个热水瓶。老虎灶飘散着的煤饼在炉膛里烤出的硫磺味以及木桶浸泡在开水中的腐烂味,使得整条老街终日飘散着古旧的味道。此外,温州的闭塞也体现了城市的古旧,瓯江这条水路是温州通往外界的唯一路径,也是小城与世界勾连的唯一方式。温州的清新则主要集中在对自然景物尤其是九山湖的描写上。孙小桃在放学后会到九山湖坐上一会,“她喜欢下午的日头把湖水渐渐变得浓稠起来的感觉,也喜欢风穿过水面和青草的清凉气息”[1]100。湖边人迹稀少,她喜欢靠在大槐树下,感受午后日头的热烈、青草地的清新、湖水的荡漾,将脑海里的东西搬上速写册,但有时也只是静静地发呆,“听着头顶上鸟儿唧唧啾啾地叫着,懒懒地看着远处水变成了天的地方”[1]101。
温州始终以敞开的胸襟欢迎外来者,呈现城市包容的形象。温州接纳了因时代变迁而从藻溪背井离乡到这里打拼的勤奋嫂、二姨娘(月桂婶)和孙小桃。南下干部子女坚持和抗战从不穿城市孩子穿的衬衫和裙子,一年四季只穿从他们父亲身上脱下来的旧军装改造过来的军绿或灰蓝的衣裳。可是,逢年过节依旧有同学带来粽子、年糕塞在他们的课桌里,就连新发的课本也有同学帮忙包好书皮再送还给他们,甚至因为他们的到来,老师开始使用蹩脚的普通话授课。而温州的开放体现为对时新事物的接受与认可。赵老板开着江南最大的绸缎庄,还将生意做到了南洋,因而他的女儿赵梦痕的衣着行头都是从上海采购来的洋货,一天一个样式,连颜色都很少雷同,这不禁引得同学们的称赞与探讨。她家中的八音盒和唱片机也打破了城市古旧的氛围,为其注入了罕见的时髦。对于新鲜的事物,温州保持着好奇与开放的心态接纳和吸收。
古朴清新的温州不仅是故乡的地理坐标,更蕴含着张翎对包容开放的温州的深切怀念,也展现着温州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
(二)坚忍勇敢的温州人
张翎在《阵痛》中塑造了许多坚忍勇敢的温州人,特别是温州女性形象。
坚忍刚强、勇敢追寻是温州女性最好的代名词。上官吟春去看望父亲的途中遭日本兵侮辱,后发现怀孕,得知真相的大先生陶之性陷入挣扎并表现出冷漠和憎恶之情。流产未成的吟春只能在惶恐中隐忍等待,即将临盆时因害怕将“贼种”生在大先生面前而独自跑到山洞里生产。后惊喜地发现女儿是大先生的亲生骨肉,急忙赶回家时才发现婆婆与大先生已离开人世。此刻,她明白陶家的天已经塌了,往后只能靠自己扛着。一切变故都来得太过突然,19岁的上官吟春硬是坚强地撑起了陶家,撑起了女儿小桃的天。上官吟春坚忍刚强的性格也贯穿了她的一生。随后,为逃避土改,吟春隐姓埋名带着女儿小桃和远房表亲月桂婶搬到谢池巷开老虎灶。她靠着一瓶瓶开水、一卷卷纸烟,艰难地维持着整个家。她一刻都闲不住,忙前忙后,就连中午吃口饭的时间都不得安生。“从小到大,母亲像男人一样挣着她碗里的每一粒饭。”[1]176这让孙小桃觉得她的妈有点像别人家的爸,撑起了家里的天。
一直被同学嘲笑为“老虎灶西施”的孙小桃幸运地考上了大学,在上海求学追梦时不顾一切与越南留学生黄文灿相爱。但很快黄文灿不得不因国内战争而撤离回国,可是此时的小陶已怀孕,还坚决地要留下孩子,不得已和一直关注与照顾自己的班主任宋志仓促成婚。未婚先孕的她,没有因为要独自抚养孩子而心生畏惧,甚至勇敢地选择回到温州待产。她家族的女人的血脉里似乎永远流淌着一股勇敢与追寻的精神。小陶生产时正赶上武斗最激烈的时候,没有接生婆也没有麻药,可她竟没吭一声,咬着下唇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连母亲勤奋嫂都忍不住感叹,“我的闺女,身上到底有我的秉性,她真能忍”[1]240。
孙小陶的女儿宋武生在多年后独自远赴异国留学,追逐梦想。“武生从她上大学开始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羽翼,而且一天比一天刚硬,现在她要用它去丈量另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天空。”[1]272这是她养父宋志成在她出国前发出的感叹。当然,武生也没有停止过对爱情的追寻,后嫁给杜克。但杜克却在“9·11”事件中丧命,快要临盆的武生在得知真相后昏倒在地,清醒后忍着阵痛在法国深夜的街头拦出租车,最后勇敢地生下了女儿路得。
不只是女性,乱世中的温州男性也诠释着他们的坚忍刚强,在时代的夹缝中艰难前行。供销员仇阿宝明白自己是个浑身毛病的土佬,得不到勤奋嫂的欢心,但还是始终帮她抵挡苦难。他将积攒的劳保手套送给勤奋嫂,饥荒时又让出农垦米的份额,还省吃俭用给小桃寄高额生活费,甚至在武斗最激烈时冒着枪林弹雨给即将临盆的小陶找谷医生接生时被流弹射死在街头。仇阿宝将世道的艰难险阻都挡在自己的身后,但却在勤奋嫂面前展现着温州男性的刚强。谷开煦本是温州最大医院的内科医生,却在“反右运动”中被下放到偏远乡村朱家岭,艰苦的卫生条件与匮乏的医疗设备让他苦不堪言,甚至想到寻死。可是,恶劣的生活环境却让谷医生的医术突飞猛进,还学会了给牲畜看病。压在枕头底下的普希金诗集和勤奋嫂邮寄的一封封信内化为他强大的精神支撑,让他以坚强之姿迎击生活的艰难。摘帽回到温州的他学会了隐忍,默默救治病人做好本职工作。
《阵痛》中的上官吟春、女儿孙小陶和外孙女宋武生祖孙三人的生育经历都极其相似,没有丈夫的陪伴,勇敢而坚强。她们体现了温州人坚忍刚强、敢于追寻的性格共性,更代表了不同时代下坚强勇敢的温州女性群像。而仇阿宝、谷医生在乱世中也并未退缩,展现着温州男性的坚忍与刚强。温州人永远有着一股向前的韧劲,从不低头,也不服输,镌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坚忍刚强与勇敢追寻完美地诠释了温州人的形象特点。
二、《阵痛》中“城与人”的关系
张翎写温州故事,都与她的成长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温州这座城市始终贯穿着她的文学创作,城与人的交融使得不同的故事在这里不停地上演。她漂泊海外多年,以远距离的姿态审视温州,从而对“城与人”的相互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
(一)“城”对“人”的陶染
温州的许多人情风物都不自觉地感染着张翎的认知与感受,进而对其小说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阵痛》中的“温州”以其独特的魅力及强大的包容性陶染着“温州人”,造就了他们勇敢追寻、坚忍刚强的性格。“城”对“人”的陶染在小说中温州人的身上得到鲜明地体现。
古旧的温州见证着城市的风起云涌和人物的命运沉浮,破旧的街巷和低矮的平房默默吞下这些陈年烂事从不多言。温州磨砺了温州人,让他们在贫瘠的土地和困苦的环境中喷发出强大的坚忍之力。政治风云席卷温州,勤奋嫂一家在温州隐姓埋名,谷医生被下放到偏远山村,孙小陶找不到接生婆,还直接导致为其寻医的仇阿宝丧命街头。可他们始终相信只要咬紧牙关就可以熬过苦难,勤奋嫂辛苦经营老虎灶,谷医生在艰苦条件下增进医术,孙小陶在没有麻药且难产的情况下生下女儿武生。温州人迎难而上,在历史的夹缝中繁衍生存,以匍匐的姿态回击现实的残酷。其实这也是温州城市精神的一种直观表现,在苦难面前他们坚强隐忍。作为温州人的他们,代表着温州在发声。
温州的清新让孙小桃在糟糕的生活环境中迸发出坚忍的力量。例行的家访使得小桃努力隐瞒的老虎灶被全班同学知晓,由于同学们看不起开老虎灶卖草纸为生的女人以及她的女儿,因而被摒弃与孤立在学校群体的边缘地带,还有了“老虎灶西施”的绰号。可是小桃没有抱怨更没有自我放弃,她在清新的自然山水的陶染下重拾生活的勇气,蜕变得格外坚强。放学后的她会到九山湖坐上一会,并将这里的花鸟景致、山水楼阁都一一搬上仇阿宝送的速写册。柔和的微风吹过湖面与青草地,扑面而来的清新让她丢掉疲惫和烦恼,每当这种时候她就觉得“脑子被水洗过了一遭”[1]101,也多了一股坚强隐忍的力量。即使条件艰苦得买不起绘画本、画儿书,班级里没有可以说话的同学,成日浸泡在老虎灶的硫磺味和腐烂味里,但温州的清新一直陶染着小桃,在洗涤心灵的同时还不停地给予她力量,让她始终坚持绘画、坚持完成学业并积极面对生活,最终考取上海的纺织服装学院。
温州的包容首先给外来者提供了生存空间。勤奋嫂带着小桃和月桂婶一起逃到温州,以寡妇的身份在城中开着一家小小的老虎灶维持生活;谷医生是杭州人,在温州最大的医院做内科医生,摘帽归来的他也被城市欣然接受;抗战和坚持是南下干部的子女,到温州读书并得到老师同学的关照,这代表着温州对温州人的包容与肯定。温州通往外界的唯一的路径是水路,而这条水路上漂泊的轮船载着勇敢追梦的温州人闯荡世界,孙小桃带着全家的希望前往上海读书。温州的开放也内化为她的勇敢,给予她追逐服装梦想,给予她与黄灿文大胆恋爱的勇气。
此外,“城”对“人”的陶染已内化为心灵最深处的情感,会在自己受到伤害或是最无助之时被唤起。在异国他乡的深夜里武生即将临盆,忍着疼痛着急又无力地拦着路过的出租车,却在司机摇下车窗的那一刻嚷出了一句温州话“我要生了,求求你”。原来在镇静破裂之时,迸发出的是埋藏心底的故乡情愫。可见,温州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武生,可以说,温州早已镌刻在她心底最深处,因而她才能在异国他乡充斥着法语的城市里,在最为无助之时不由自主地喊出温州方言。
(二)“人”对“城”的逃离与归依
首先,《阵痛》中“人”对“城”的影响体现为“人”对“城”的逃离。所谓逃离,是指《阵痛》中的温州人试图通过逃离城市的苦难而找寻真实的自我,抑或是追梦。老虎灶的炉膛里飘出的硫磺味以及木桶中散发的腐烂味一直浸泡着孙小桃的鼻子,那时的她讨厌家亦如她讨厌这座城。她从小就跟着母亲在这座古旧得一成不变的小城里生活,在她放假归来时,温州的街巷甚至家门口旧年的年画都一点儿没变。同时,她也讨厌“老虎灶西施”的绰号。所以,孙小桃在考上上海的服装学院时,急切地渴望逃离这座古旧且印证自己不愉快的人生经历的城市,她的“眼神里已经明显带有小城的天空所不能覆盖的丰富的内涵”[1]156。她乘船离开这条叫作瓯江的河流,驶向东海,驶向大都市。除了小桃的主动逃离外,其实谷医生和勤奋嫂也在逃离温州,只不过他们是从城市逃到乡下。谷医生被下放到朱家岭,摘帽回到温州后的他发现自己愈发喜欢和享受乡下的生活,与城里的古旧传统相比,朱家岭条件较差的卫生所是他大展身手的地方,在乡下他能获得乡亲的尊重与信任,并且自在随性。谷医生带着勤奋嫂和孙小桃逃到朱家岭避难,这里惬意的生活让勤奋嫂也不禁发出“别说你,连我都不想回到城里去”[1]250的感叹。其实勤奋嫂也在逃离温州,对她而言,她即使住在温州,叫得出谢池巷的每一人每一条狗的名字,但还是觉得日子像浮萍,没根没底。温州发生了太多的事,也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她在温州艰难谋生,经历了温州改头换面的半个多世纪,在经过生活与苦难的磨砺后每隔两三年都会回藻溪看看,藻溪能在一定程度宽慰她的心灵。孙小桃、谷医生和勤奋嫂都渴望逃离这座城市,因为温州积压他们太多的情绪与苦难,只有逃离这里才有可能找寻真正的自我。
其次,这种影响还包含“人”对“城”的皈依。所谓归依,是指《阵痛》中的温州人对温州这座城在情感上有依赖,温州是给予他们安慰与疗救的港湾,让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这种归依主要体现在孙小陶和勤奋嫂身上。城市的清新从小就净化着孙小桃的心灵,即使被同学孤立、被嘲笑为“老虎灶西施”,她也能在九山湖找寻到慰藉。多年后,早已远去上海读书的小桃在校园里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情,未婚先孕的她却在第一时间选择回到温州待产生育,她知道这座城市虽然古旧,但是却能包容和接纳此刻的她。恰如当年那样的清新也从未改变,依旧宽慰与温暖着她。勤奋嫂对温州的皈依表现为一直隐姓埋名的她在其地主婆身份被揭发后,并没有直接回到藻溪,而是继续留在温州经营老虎灶。她知道这座城市的宽容,在这里她可以依靠自己的开水铺养家糊口,撑起她和小陶的家。孙小陶和勤奋嫂以各自的方式依赖着温州城。
张翎在描绘温州的城中人时,通过理性的思维方式呈现了“人”对“城”的逃离以及“人”对“城”的皈依,两者看似矛盾,但实则是“城与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所必经的磨合。温州为温州人提供了居所,而温州人则为温州注入了活力,传播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及精神。
三、《阵痛》中“城”与“人”折射的温州文化
《阵痛》中的温州文化,包含了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和移民文化[2],小说中的“城与人”折射出温州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中可以体会到温州这座城市对文化的强大包容力以及温州人敢于闯荡的精神。
九山湖秀丽的山水让孙小桃、抗战及赵梦痕等人置身其中,尽情享受自然的风光。这里的一花一草都深深地印刻在孙小桃的脑海中,成为其源源不断的绘画素材。自然山水在为温州人提供物质资源的同时,还为其洗涤心灵。九山湖不论何时都始终以清新的姿态和安静的氛围宽慰着被同学孤立与生活贫苦的小桃,为她提供可以放松且自由的秘密基地,还给予她面对挫折时咬牙坚持的刚强力量。孙小桃在山水的陶染下不仅获得了慰藉还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依赖。温州依山傍水,山水自然成为温州人的依靠,他们从这里获取安慰,得到放松,同时也在山水的感染下学会坚忍与刚强。由此可见温州与山水文化天然地契合。
温州包容开放的形象和温州人坚忍勇敢的性格与频繁的海内外交流密不可分。温州闭塞古旧,瓯江是小城与世界勾连的唯一路径。仇阿宝出差带回的速写册和赵老板从南洋等地带回的亮丽绸缎、唱片机等众多的时髦物品随着生产和交易进入温州,多元文化和海洋文明为温州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频繁的贸易往来一方面让温州不断地保持着包容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外来者和吸收时新,另一方面却是在文化的碰撞冲突下,温州人展露出勇敢闯荡且坚忍刚强的性格特征。例如,勤奋嫂、谷医生等温州人在乱世中不断克服艰难险阻,展现了逆流而上的坚强勇敢,也在逃离的过程中又选择归依温州。温州因海而兴,作为典型的沿海城市,在商品交换与海上运输中形成多元开放的格局[2],温州人也由此衍生出迎难而上的韧劲。所以说,海洋文化已深刻在温州人的骨子里。
此外,温州还因其清新的地理环境与包容开放的城市形象不断吸引外来者来此繁衍生息。勤奋嫂和二姨娘带着孙小桃从藻溪到温州定居,杭州人谷医生来此工作生活等。当然,也有相当多的温州人迫于生活或是为了追求发展而外出经商、求学以及定居。怀揣着服装梦并勇敢追寻的孙小桃闯出了温州,到上海求学,最终成为颇有名气的面料设计师。其女儿宋武生更是留学海外,为了理想走向陌生的大洋彼岸。温州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不管是迁入还是迁出,富于冒险精神的温州人有勇气和决心勇敢地闯荡。可见,移民文化早已深入到温州精神中。
总而言之,山水文化、海洋文化、移民文化等各类文化内涵丰富且相互交融。温州这座城市始终秉持着开放、勇敢的心态,以包容的姿态接收多元的文化。
张翎对“温州”与“温州人”的认知与把握十分深刻,她从本质出发对“城与人”进行剖析,通过《阵痛》向读者展现蕴含在“城与人”之间的深层意蕴,“城”对“人”的陶染,“人”对“城”的逃离与归依,在小说中汇集成对温州的深切眷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张翎的小说以独特的视角与丰厚的意蕴扩展了当代温州地域文学,对温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