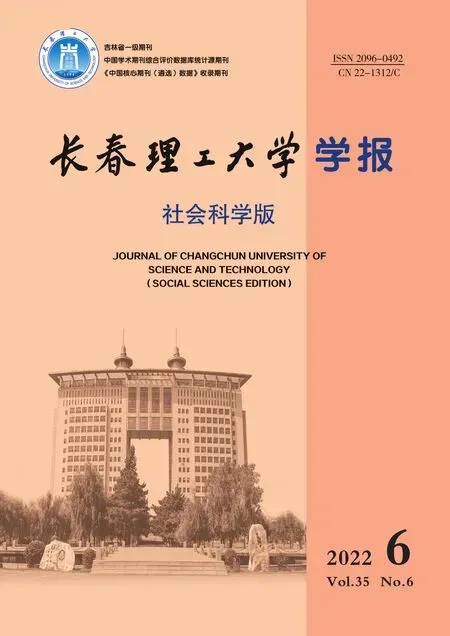“典型”的退场
——路内小说中工人形象的个性化重塑
2023-01-05尹晓琳亓梦蝶
尹晓琳,亓梦蝶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翁”,受到各个领域的关注,成为作家书写和学界热议的对象,以工人形象为中心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呈现出“井喷式”增长趋势,工人形象书写也呈现出与时代发展同质的走向和作家表述异质的特征。无论是“十七年”文学中“高大全”的工人英雄形象、“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式工人干部形象,还是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分享艰难”的工人形象,抑或是新世纪以来以“打工者”为主体的“新工人”形象,都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内涵。
英国史学家华顿曾声称文学“具有忠实的记录各个时代的特色和保留最生动的、含意深远的世态人情的特殊优越性”[1],工人是现代社会的建设者,是工业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亦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文学形象,“十七年”文学以来的“高大全”式工人常常被视为具体、独特、感人的“典型”工人形象,集中展现了新时期以来工人们开展工业化建设的风采,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这是文学对工人形象的真实记录,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文艺政策影响,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推波助澜。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下,在消费市场的刺激下,工业小说的外延不断扩展,工人作为被表现的主体,理应在展现真实、表现典型的基础上寻求新的改变。而路内笔下的工人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20世纪90年代工厂工人形象的新诠释。
路内是新世纪积极践行“泛工业小说”书写的作家,他以回望姿态,以亲历者的身份,在作品中表现90年代“下岗潮”,书写世纪末的“工厂挽歌”,透视感知那一时代所经历的“阵痛”。如何塑造独特又真实的工人形象?路内从亲身体验和理性思考双维角度出发,去关注工人的生存境遇,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甚至暴露剖析他们的人性弱点,从“高大全”形象的颠覆式书写、理想品格的消解和迷茫精神困境下的“出走”三方面,用现代的笔触描绘出历史转折时期的工人形象,丰富新时期以来的工人形象图库。
一、“高大全”形象的颠覆
人物塑造是小说创作的核心,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评判标准之一在于是否塑造了“情状逼真,笑语若活”的人物形象,人物外在形象的塑造通常给读者以最直观的感受,读者也能从其外在形象的细微之处来了解人物所处的生存环境及其性格特点。原本概念化的“高大全”式的工人外在形象随时代发展变得不再被读者和大众全盘接受,新的时代语境、文艺市场需求和读者期待召唤着工人形象的多元化呈现,期盼工人形象以一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的面貌回归。路内从自身经验出发,以一种写实的姿态,从外在相貌和言行两方面向我们展示了戴城化工厂一群“不完美”的工人。
自“十七年”文学以来,文学创作中对工人外形的描述总是围绕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等积极词汇展开的,这无疑是对工人外在形象进行一种“固化”书写,使其难有突破。在《乔厂长上任记》中,蒋子龙通过机电局长的所见向我们展示乔光朴的直观外在形象:“这是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恶虎般深藏的双睛,颧骨略高的双颊,肌肉厚重的润脸,这一切简直是力量的化身。”[2]将一个在改革中锐意进取的工厂厂长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期待通过对其形象的正面描述来表达对于改革的积极态度。
路内在描述工人外在相貌时,放弃了全面正面的表述方式,工人外在形象与之前的“高大全”形象相差甚远。《天使坠落在哪里》中的包部长,长着“倒鸭梨”样的脑袋,大嘴巴、短下巴,双目分开足足有五公分宽,还是倒八眉,着实“天赋异禀”。在《少年巴比伦》中,化工厂里的工人的形象更是滑稽可笑,电工们穿着条纹枪驳领西装和太子裤,上身笔挺修长,下身却短人一截。老一辈的工人师傅都有着粗俗的绰号,这些绰号或是指涉其身体缺陷或仅为粗俗的表达,但工人对此类粗俗且颇有歧视性的绰号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甚至以此为傲的。而在展现工人的言行时,小说又体现出了独有的“工厂特色”,粗俗的脏话、调侃的笑话随意地夹杂在人物的日常对话之中。
但仅单纯地将路内笔下工人们这种粗鄙的言行归结为工人群体的素质低下是失之偏颇的。他们的工作是单调乏味、日复一日的车间劳动,化工原料损害着他们的健康,改制的工厂既不能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也不能成为他们的精神依托,这种“油滑”的语言和“粗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工人们面对无力的现实,调剂困苦人生的一种方式。“美”代表着美好品质,传递出的是一种秩序化、规训化的原则,通过变形的“丑”来反抗主流的“高大全”话语,以短暂忘却人们习以为常的“完美”工人,展现人在现实境遇中的悲剧命运。
路内带我们来到了一个真实的工人世界,不再向工人阶级“示好”,工人形象也变得真实可感,工人们的外貌着装、身体缺陷和语言行为等都成为打破工人固有印象的利器,无论是滑稽还是正经,工人的形象已然跌出“高大全”模式,抹去了光环。“这种人每天拿着老虎钳跑来跑去,身短脖子粗,胡子拉碴一身油污。这当然是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是最先进的形象,可惜九十年代这种形象已经分文不值了。”[3]这种对典型的破坏和对伟大的遮蔽,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多元共存的驳杂之感,消解了工人外在高大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的“真实感”,让工人形象从“完美”变得“有瑕”,展现出一种在90年代工人本应拥有却被遮蔽了的“丑态”和“窘态”,塑造出一批极具时代特色的工人形象,其创造的文学世界也变得现实而立体。
二、理想品格的消解
路内小说中工人形象的重塑还体现在工人们“理想品格”的消解上。在当代工业小说作品中,我们可以轻松罗列出一批埋头苦干、锐意进取、敬业爱岗的工人形象,他们身上体现出作为工人所应具备的“理想品格”,常被称为“理想工人”。《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为炼钢铁不顾手被烧伤;《沉重的翅膀》中,郑子云为工厂改革日益操劳,最终积劳成疾;《卖厂》中,宋师傅为了穷途末路的工厂甚至要去卖掉自己的肾来维持工厂运转。在不同年代的工业小说中都有着大量的“理想工人”们的身影,他们鞠躬尽瘁,爱厂如家,有着集体主义精神和甘于奉献的人格光辉,在自己处于艰难境地时,心中所想的仍然是工厂的利益,这些“理想品格”与“十七年”时期工人形象一脉相承。工人们为了维护工厂的利益不惜牺牲健康与生命的态度,可视为作家们对“理想工人”的追溯和讴歌。
但这种“理想工人”的形象在路内的作品中是欠缺的,文本对工人推三阻四、敷衍消极的工作态度展现无疑是对工人“理想品格”的消解。路内以亲历者的身份,观察着处于时代列席中的工人们,以冷静客观的笔触书写着在时代变化冲击下隐藏起美好品质的工人们。
在《少年巴比伦》中,糖精厂钳工班的工人们会在下班前擦自行车,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工作也会因为工人的“磨洋工”而耗费半天。“我们换灯泡的时候,除了爬梯子以外,还揣着几颗大白兔奶糖,遇到有小姑娘,就把奶糖掏出来给人家吃,然后就坐在桌子上与人聊天,这么一圈搞下来,换一个灯泡得半天时间——不是虚指的半天,而是实打实的半天,整整四个工时。”[3]老工人自恃经历老,上班的时间更是散漫无比,与工厂干部斗智斗勇,把所有的活儿都推给人善可欺的年轻工人。在《少年巴比伦》中,路小路问师傅什么时候教他修水泵,但是师傅却反问“你修好了水泵又怎么样呢?会给你加奖金吗?”[3]“那你修不好水泵又怎么样呢?会把你辞退吗?”[3]在得到路小路“不会”的回答后,师傅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你还是去帮我看自行车摊吧。”[3]
工人们对工作的态度是消极的,对工厂的情感是淡化的。锐意进取、爱岗敬业成为一句空谈,老工人们“混日子”的工作态度不能为刚进入工厂的“路小路们”起到价值表率的作用,于是一批批年轻的工人们学不到技术,看不到未来,心灰意冷,在工厂中惹是生非,更枉谈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理想工人”在时代语境中逐步成为一种典型“符号”,同时这一代表性“符号”也在文学中不断地体现与传承。但是当作者在新语境下试图在文本中召唤这一形象时,却陷入了怀疑的危机,使之难有体认之感。这固然有作者实际经验的影响,而更多地来自于产生“理想工人”的时代环境的大变动及消费主义冲击下的精神认同危机。而通过对工人们“理想品格”的消极书写自然就对传统工人形象进行了消解,也防止了“理想工人”在文本中的滥觞。
“理想工人”为何在小说中难以再现?从工厂本身出发我们可以寻到原因,八九十年代的粗放型化工厂的工作是一种单一的极度消耗体力的劳作方式,并且工厂的恶劣环境无法保证工人们的安全和健康,苯酚车间刺鼻的味道刺激着工人的鼻黏膜,使他们不断地流鼻涕,工人患病的概率极大。但即便是在如此高强度、损害着健康的工厂拼命地工作着,也无法为家庭的物质生存提供保障,在《慈悲》中,工人们要靠“捐会”这种自救方式来救急,为了能拿到15元的补助给妻子看病,水生的师傅不得不向他最讨厌的车间主任下跪,而身为工程师的陈水生,最后也不得不为了生病的妻子放下尊严去申请补助。
此外,工厂属于一种封闭式“规训空间”,它也是权力运作的场所,在特殊的年代,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则更为明显,“监视”成为权力得以实现的基本方式之一,所以我们能在文本中看到记录工友不当言行并谄媚上报的朱建华,因脚踢阀门而被送入劳改场的孟根生,抓到工人迟到罚他们在工厂门口举牌子的安全科科长等一系列热衷于发挥“监视”权力的工人。当然,在强权高压之下,也会出现大闹会场的路小路、一身反骨的孟根生等工人的反抗。工人在冷漠的工厂内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算计争利,充满着不信任与伤害。
而至国营工厂改革时期,工厂属于私人所有后,对工人的盘剥压迫更甚,老实人无法保全身家,精明者却升官发财,在令人窒息的压迫环境中,工人们“理想品格”自然被消解,“理想工人”也难以再出现。
但“理想工人”并未从路内小说中完全销声匿迹,在《慈悲》中,厂里退休的老书记,为了举报新厂长宿小东侵吞国有资产,70多岁孤身去省城举证上告。“我虽然老,但必须出头,厂就像我的儿子,我不能够给它伸冤,就没天理了。”[4]在老厂长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路内对距今还不算遥远的“工厂时代”的怀念与致敬。
三、迷茫精神下的“出走”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化”的外沿不断拓宽,内涵不断深化,传统国企制度与工业现代化要求无法适配,国企工厂改革势在必行。于是,在此种社会语境下,在工厂改革、生活捉襟见肘、面临下岗等重重威胁之下,90年代不再是高喊“我们工人有力量”的年代,工人阶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难,工人阶级脱离了“领导”行列,变成了“社会底层”,难以养家糊口。路内敏锐地捕捉到此种状态,去书写精神失落、信仰迷失、失去对工厂和工人阶级忠诚的工人,展现工人们在不知未来出路何在这一精神困境下的“出走”。
在《十七岁的轻骑兵》中,路内以“三部曲前传”的形式让读者们看到了“路小路们”的过去并从过去透视未来,他们注定属于糖精厂、化工厂、农药厂、苯酚厂,等待着他们的是辛苦的“上三班”,然后庸碌多年,最后下岗失业,被时代抛弃。在集体主义大厦将倾的年代,浑噩迷茫是青年工人们的精神主调,“这种青春既不残酷也不威风,它完全可以被忽略掉,完全不需要存在”[3]。
在路内的“追随三部曲”中,主人公都是从化工技校毕业,或进入工厂,或失业游荡的路小路,三部作品的故事独立完整又相互补充,完整展现了“路小路们”的青春之路。作为刚入厂的青年工人,他们的青春与冰冷的工厂捆绑在一起,被桎梏在日复一日的“倒三班”中,心有不甘,但却逃之无路。“九三年是个无处可去的年份,在工厂里上班,外面的世界变得很快。”[3]青年工人在厂子里跟着老工人学不到任何技术,耗费着青春,想要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又被工厂的制度缚住了手脚。
青年工人长脚曾对路小路描述过一个美好的计划“考上夜大,读一个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以后通过送礼走后门,做一个技术员,然后调到科室里,然后做科长”[3],但是管工师傅们却依赖长脚修管道,在发现长脚偷偷学习准备考试离开钳工班后,竟然去“围捕”长脚,把他的学习资料都给烧掉来阻止他学习。在工厂只要是做有违工人“本分”的事就会被嘲笑、被阻止。“路小路们”走出工厂,却又没有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相适应的能力,注定被社会淘汰,青春本应拥有的另一个面貌——“奋进、专著、忐忑不安、百战不殆”[5],都已在工厂里消磨殆尽。
但是路内也未曾将前路堵死,青年工人们仍然是不断冲撞着、寻找着未来的出路,工厂容不下他们的梦想,理解不了他们的情怀,在工厂下岗威胁的助推和消费社会吸引的双重影响下,他们思考着去路。看不到未来的年轻工人们开始计划着离开工厂,白蓝不断学习,考研成功去了上海,走向更广大之地;小噘嘴和李光南双双离开工厂,投奔姑妈,去往新兴的“淘金之地”深圳,小苏也随着研究生女友去了北京发展;路小路的表姐,在路小路和悉志常的“护送”下奔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只有路小路,还在原地逡巡着,没有找到突围的出口,但最终他也以一种荒诞的形式离开了禁锢自己的工厂,路在何方,无人可知,但总会有路的。
如果说青年工人是为了追寻更好的未来从工厂“出走”,那么,在工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人则是被迫无奈地失去他们对工厂的忠诚。在90年代改制、下岗的浪潮波及下,有一部分为工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人被工厂无情抛弃,他们失去了终身制的工人身份,成为工厂的过客,过去近半个世纪作为工厂“主人翁”的优越感不复存在,身份的强烈落差带来心理上的失衡,而物质上的匮乏让他们不得不在体制外谋生,甚至转头成为工厂的“对头”。工厂从刚开始的“非常权威、非常友好而且正经,像一个微笑的老大哥”[5]摇身变成“敌人”,并且不断压榨工人的生存空间,于是工人开始绝地反击。在《慈悲》中,水生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苯酚厂改制,他的对头宿小东成了厂长,作为工程师的水生重新下操作车间,被逼无路的水生与邓思贤合伙帮助其他企业家建苯酚厂来对付宿小东,在亲手建盖起的苯酚厂里,他们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个老工人的尊严,最终也搞垮了老厂。
八九十年代,改革文学盛行,出现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一系列工业题材作品,小说中的工厂也是面临着各种困境,这一时期国企工人身上建国初期时的奋斗豪情已然难觅,但他们的心仍与工厂连在一起,愿意同工厂共渡难关。在谈歌的《大厂》中,劳动模范章荣在生命垂危之际仍然心念大厂,担心工厂前途,袁家杰放弃别家企业的高薪聘请,选择留下与工厂共渡难关。苦难时期仍不乏一批充满正义感与道德感,有理想有志气的工人,“分享艰难”构成了工人这一时期的精神品格。路内作品中的工人,同样是面临改革,却没有了视厂如家的精神,但也正是通过对工人们的“出走”,作品才实现了对改革时期的矛盾问题进行不同以往角度的真实反映,对现实生活中面临下岗工人们的悲痛与无奈进行真实刻画。
个体生命的发展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之中,我们发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变成某种无法体认的存在。这种以“国营化工厂”为发展主力的“前工业社会”已成过往,改革固然推动了工业进步和城市发展,但却忽略了对社会的主体——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人的精神如何自处却无人回答。来自工厂内部的变革和来自外部时代变化的冲击使得工人们惶惑地想去寻找一个出口,然而旧的时代已将这些工人们抛弃,新的时代却未曾向他们敞开怀抱,路内小说中所展现的工人的“出走”正是这种时代夹缝中无可避免的精神困境。
四、记录与反思:重新挖掘工人形象书写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梁鸿曾在访谈中说:“当一个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动,把一整拨人都挤压到外面的时候,这本身就是特别值得书写的一个东西。”[6]纵览新时期后的工人形象,这一群体不论是生存状态还是精神状态甚至是对自我身份的体认上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们从享受工厂企业的各种令人艳羡的福利到难以养家糊口的生存窘境,为公无私的昂扬精神也变为迷茫、痛苦与无措,“主人翁”与“工人阶级”的光荣称号与他们日趋渐远,他们逐渐沉入“社会底层”,失去了往日的话语权,就像一位在舞台上曾大放异彩的舞者无声退场至幕后的边缘角落。引人深思的是,在不同年代刻画工人形象时,既有文艺政策、文化市场、读者期待这样的外部推力,同时也有作家自身的创作姿态、写作理念与审美探索的内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共同促成了工人形象的不断解构与重塑,因此对于工人形象的变化进行持续的关注与研究是极具价值与意义的。
长期以来,在主流文学中人物塑造往往被异化理解为对“典型人物”的强调,这导致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过于单一和虚假,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创作则以“生活化”和“凡俗化”的特征来反抗崇高与典型,力图抹去“典型人物”的固化痕迹,但是由于文学上的历史遗留问题,人物形象总是难以突破,批评界也鲜少有人讨论关注人物形象问题,更多地将批评的中心放置在叙事、思想主题等批评热点上。路内在新世纪对工人形象的塑造,让我们看到了工人形象脱离典型的可能,有着强烈的作家特色。对工人形象的解构书写也继承了先锋文学消解宏大叙事的传统,他以青年工人“路小路”的视角看待工厂众工,塑造了多个“丑角式”的工人形象,不再停留在集体式书写,而是将工人作为个体从集体中凸显出来,从外在形象到内在精神,塑造一个个活生生的工人,而不是以集体为先的理想工人,将工人阶级的宏大书写降低到了以工厂琐事来展现人物,探究工人们的内心精神世界。
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工人一词有更为复杂的身份构成,路内与前辈作家对工人形象书写的巨大差别,一方面是作家自身的工人经历使然,路内在70后作家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在发表小说之前做过多种职业,而工人的经历带给路内深刻的体验,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主要素材。作品中为我们呈现出来的工人形象,一定程度上则是作家所闻所见在文学上的真实反映,另一方面则是作家深入现实的重要体现,虽然书中那段艰难的时代“阵痛”已成为过去,“苦难”成为日常,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却促使着他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曾承担起变革巨大代价的工人群体,让读者在看到承载呐喊之声的文字后依然可以跨越时空感到直击灵魂的“苦”与“痛”。同时,路内有意识地对工人群体进行重构,把工人群体放置在历史发展的宏伟脉络里,考察其失去原有号召力和推动力的原因,并借“路小路们”失去了工人曾经的“符号化”身份后,或以探寻或以对抗的姿态试图重新激发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以证明工人文化仍然有着影响甚至形塑现实的可能性。
新世纪工人文化在自身机制变化和消费社会发展双重影响下不可避免地有世俗化倾向,身处后工业社会文化语境,工人形象的书写既不能走怀旧式书写为工人“立传”以期待工人文化觉醒,又不能做全然否定式失之偏颇的书写,工人形象书写如何在困境中突围,如何使退出言说中心的工人再度活跃,如何发现和重构工人在新时代的主体性,这是亟待讨论与实践的。
文学是反映时代的镜子,工人形象也是扼住时代脉搏的关键,这一群体有着曲折多变的命运,在书写上有着极为丰富的价值和内涵宽广的言说空间,不仅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现实主义创作与悲剧主题,以虚构却又真实的文学形象展现生命的苦涩与艰辛,同时也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融入新的反思内涵与特质,增强了小说的言说力量。虽然工人形象在创作中存有不足,但我们仍对其未来形象的不断更新重构抱以期许,越来越多的作家也摒弃了单向度的创作,为我们展现出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和社会图景,带来心灵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