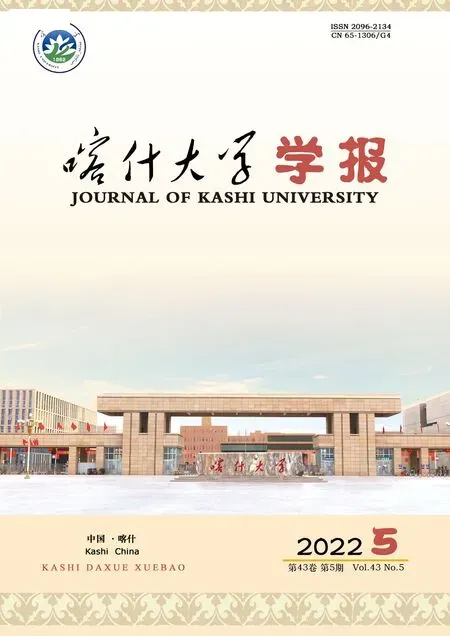王安忆女性成长小说探究
——以中长篇小说为例
2023-01-05司双鹂
司双鹂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成长,是作为人存在而无法回避的问题,个人的成长之路促进了人类的反思、进步与发展。成长这一话题进入到文学范畴后,便产生了一种文学作品题材——成长小说,例如拉伯雷的《巨人传》、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等。女性在历史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所以以往成长小说的概念范畴只涵盖男性主人公作为成长主体的小说。当叙述女性成长的小说出现后,相对应的女性成长小说概念逐渐产生。当代文学作品中,王安忆的多数作品表现了女性的成长历程,因而以王安忆笔下的中长篇女性成长小说为探讨核心,是研究王安忆作品的应有视角,亦有助于丰富女性成长小说研究。
一、成长小说与女性成长小说概念
(一)成长小说概念
成长小说起始于18 世纪的德国,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被认为是这一类型小说的原始模型。巴赫金把成长小说定义为:“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变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名誉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1]225他强调了成长中的主人公具有动态性,这是对成长的一种本质把握。狄尔泰认为成长小说“是以一个敏感的青年人或年轻人为主人公,叙述他试图了解世界本质、发掘现实意义、得到生命哲学和生存艺术启示过程的小说”[2]。将视线集中于人与外部,忽视了人与自我之间的成长。成长是一种螺旋上升性的机制,人认识外部从而得到经验,经验反作用于内部,促进内部成长,进而形成相互影响的螺旋式,因而成长本质就是动态的。莫迪凯·马科斯把成长小说阐释为:“一类把成长描绘成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另一类把成长解释为认知自我身份与价值,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3]5
古代或现代都对成年的年龄进行了规定。《礼记·曲礼上》认为“二十曰弱,冠。”[4]古代认为男子在二十岁即已成年,在中国现代法律、社会学中,规定一个人满18岁即是成年人。因而从襁褓之时到18 岁都可以作为成长的过程。实际上,将时间度量扩大到从出生到死亡,这一阶段都算作是人的成长过程,然而这只是在外在的、时间顺序意义下的历时性内涵。因此,成长不是指某一个时间节点,其本身是一个行动驱动器,驱动人不断朝向民族、文化长久发展以来所共同认同的成熟状态。在此层面上,我们无法单一地用年龄、时间来规定成长内涵,关注的核心部分也并非是在哪个具体的年龄阶段发生了成长变化,而是要从内在、心理角度辨析成长,这正如马科斯所述,“悲剧”成长,即未能成功调解自我与社会关系,成长后的绝望、受到的刺激大过想要继续活下去的愿望,最后以精神状态失常、结束性命等悲剧作为人生的结果。此类成长也是具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暂不纳入此文讨论范围。因而,本文女性成长小说的概念是在积极的成长概念下去探讨的。
(二)女性成长小说概念
首先,女性成长小说概念同样具有成长小说概念的基本内涵,向内看,女性人物心理层面达到成熟状态,向外看,自我与社会调解后达成的平衡状态。其次,女性成长小说还有成长小说概念外的含义。社会由母系社会更替为父系社会后,男性的权力不断加强,女性地位逐渐边缘化,因而成长小说概念具有男性色彩,缺乏女性色彩。中国五四运动之后,女性作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逐渐增多,女性文学展现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艰难成长,显示了女性对社会几千年来潜移默化形成的男性特权的挑战与反抗。女性人物成长的研究进入人们视野。现有的成长小说概念已经不足以支撑研究女性成长小说,因而女性成长小说概念出现了:“女性成长小说是以生理上或精神上未成熟的女性为成长主人公,表现了处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从或抵制父权制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艰难建构性别自我的成长历程,其价值内涵指向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即成长为一个经济与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5]
中国当代文学中,王安忆在一定程度上讲述了女性的成长历程,其作品里的女性形象占有重要地位。将王安忆的一些作品划分到女性成长小说中,是试图通过探讨作品中女性的成长历程来更好地观察女性形象、地位、处境等。因而对王安忆作品的探析可以作为支撑探讨女性成长小说的基础。本文主要是从女性成长的文本呈现、女性作为成长主体的真实处境与叙述策略两方面进行探析。
二、王安忆笔下女性成长的文本呈现
王安忆在表现女性的成长时,不仅体现在文本结构设计上,还体现在人物的语言、形象和故事情节等方面。我们可以从人物的流动性和深化性来分析王安忆是如何呈现女性人物成长轨迹的。
(一)人物的流动性——对世界的逐步认知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人物的成长总要经历一个逐步认知过程,在这过程中形成对自身和外部的探索、认识与觉醒。因而我们可以发现人物的生活、形象和状态都是具有流动性的,并非是一成不变,等同于巴赫金所说的“动态性”。
人物在某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是稳定的,然而具有动态性就必然要依托时间进行。巴赫金在谈到成长小说时认为“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1]227由此可见时间在成长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使小说获得了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中通过人的持续性的日常生活描写人的个性的特征,同时也蕴含着作者的情感和态度。”[6]75
时间是人物成长的最好见证者,作品中的时间是如何显示人物成长历程的?《长恨歌》的目录有三部分,将王琦瑶一生的时间划分成了三个阶段,让人物生活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之中。第一部分是王琦瑶成长为上海“三小姐”,委身于李主任,而后李主任坠机;第二部分是王琦瑶寻找生存空间,在弄堂里依靠打针赚钱,结识新的朋友;第三部分是王琦瑶生下女儿薇薇后,与女儿共享时代的生活。这三个阶段的切分向我们展示了王琦瑶的成长过程,以及对外部世界的逐步认识。王琦瑶在成长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年龄的增长接触到了不同的事情,从而形成了对自己的认知和对世界的看法。王琦瑶本身不知道自己的美丽,正是有了吴佩珍的丑、旁人的赞美、社会上对美的界定,让她认识到了自己是美丽的。王琦瑶本身并不知道权力的作用,看到了他人对李主任的卑躬屈膝,才知道权力的威力。人正是在成长中才形成了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世界的认知。
类似划分方式还出现在了《桃之夭夭》中:一至五章的标题用了五句词曲:“梨花一枝春带雨”“新剥珍珠豆蔻仁”“千朵万朵压枝低”“豆棚篱落野花妖”“插髻烨烨牵牛花”。第一章主要是写了郁晓秋的母亲笑明明的年轻时代,并交代了郁晓秋的出生。第二章题目指代的就是郁晓秋,她正处在少女的豆蔻年华,就像刚剥出来的豆蔻仁一样新鲜、有活力。第三章“千朵万朵压枝低”本是写黄四娘家的花朵很香,这里用来暗指郁晓秋已经初长成,像花儿一样到了盛放的季节,吸引了蝴蝶和蜜蜂。第四章写郁晓秋下乡,但是在艰苦环境下依然呈现出与他人不同的乐天派心理。最后一章标题出自陆游的《浣花女》,联系前面的一句“青裙竹笥何所嗟”,展现了一个农村妇女出嫁时没有多少彩礼和嫁妆,夫妻双方清贫,但生活幸福美满,头上仅插着一朵牵牛花也挡不住其对生活、婚姻的喜悦。标题与文本内容交相呼应,并且暗示了郁晓秋的彻底成长,她已经大不相同,“现在,她可真是绚丽啊!”[7]这五个章节的标题借用不同词曲的内涵指代与概括了人物在不同阶段中的重要特征与发生的事件,以此一步步写出了人物在时间、空间变化下的成长。
在创作成长小说过程中,成长小说的典型情节模式是“对人类共同的成长经历的摹仿”[3]84,有着自己的走向:诱惑—出走—考验—迷惘—顿悟—失去天真—认识人生和自我。如果用上述情节模式观照王安忆的《长恨歌》,可以用几句话概括王琦瑶的人生成长历程:少年时代王琦瑶参观了电影拍摄现场,虽然与朋友相处时体现出小心机,但仍是纯真的。在世俗的诱惑下参加了“选美大赛”并认识了李主任,成了李主任身边的一只金丝雀。李主任消失后,王琦瑶内心开始迷茫,去乡下外婆家散心。她在邬桥找回了自我,回到上海成了一名打针医生,然而遇人不淑,意外怀孕,独自生育与抚养女儿薇薇,在新时代的成长中走向了成熟。这是经典的成长小说路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王琦瑶的人生中出现了一个有意味可循的人生转折点:为王琦瑶抚慰伤痛的邬桥。王安忆在第二部分中用一章节写邬桥和阿二,邬桥是一个最自然不过、最抚人心的地方,阿二是讨人心的女性化男性。阿二自称自己是一个没有影子的人,偶然间见到王琦瑶后,却忽然有相同之感,心里想:“这才是我的影子呢!”[8]158阿二是邬桥世界里的王琦瑶,王琦瑶是上海繁华世界里的阿二。两个人互为里外,正是阿二的勇敢与“鲁莽”滋养了王琦瑶,王琦瑶有了足够的能量重新返回上海。阿二勇敢地拼向上海,表征着王琦瑶已经真正找到了方向。回上海的路途明亮而宽广,表征着王琦瑶被治愈,千疮百孔的心已经足够积极与坚强,由一个依靠着男人的小女人,成长为一个“双性同体”的人,阿二已内化为王琦瑶精神的一部分。回到上海依靠自力在弄堂活出一番天地的她,不再毫无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成为一名经济独立与思想独立的女性。
《富萍》中的富萍与李天华有婚约之后,被奶奶叫到上海生活一阵,但内心并不同意这场婚姻,偶然去舅舅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再见到李天华时,提出出来单过的要求,没有得到同意后,逃离了这场婚姻。之后认识了一个残疾青年,在两人相处中认定了自己想要的婚姻。富萍的成长轨迹也是成长小说典型情节模式的变形。其人生轨迹中出现的转折点便是在舅舅家这段时间。小君是富萍的唯一的伙伴,在小君影响下,寄人篱下不敢反抗的富萍释放自己的天性,敢于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因而对李天华说“我们分出来单过”[9],这是她主体意识的一种宣示,也是对与李天华之间关系的一种宣告。富萍与王琦瑶一样,都有一个“离去—归来”的历程,“离去”的是人物所处的想要逃离的处境,“归来”之后到达的是人物最终的精神归宿之地,在“离去”与“归来”之间有一个“某地”,作为她们暂时的“世外桃源”,为其提供精神滋养,帮助成长,最终“归来”到人物心仪的世界。王琦瑶离开了爱丽丝公寓,到了邬桥这个“世外桃源”,又回到了自己的归属地——上海弄堂,成为一名独立女性;富萍离开了步步紧逼的奶奶,在舅舅家寻找自我,最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她是顶梁柱,是一个拥有话语权的“人”。
以上是对成长典型情节的分析。但在典型情节被概括之前,成长小说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成长主体的,因而典型情节也带有一定的男性主体倾向。目前对女性成长小说的典型情节没有一个学术界定论,但是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女性的成长路径一定需要一个寻找到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契机,它可以是一个地方,抑或是点醒人物的话语,最终目的所指都是女性找寻到了自我主体意识,摆脱他人的束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二)人物的深化性——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调整
“在成长之路上,有一次次偶然和必然的机缘,年轻的主人公在经历身心的震撼和磨砺的同时,也探索怎样穿越幽暗的命运通道以达到真正的和谐与圆满,寻求自我在社会中的定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10]在成长过程中,主体认识社会、世界的同时,因主体的发展无法完全逃离社会,所以会被社会塑造、改变自我价值观,两者互相交织,最后达成主体所认同的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一过程,也是主体完成成长的重要一环。
王琦瑶和李主任交往后,李主任提出给她租一套公寓。王琦瑶内心明白自己已经面临着要被有权有势的李主任包养的现实,哭过之后,“神情反是轻松些,也坚决些,好像完成了一个告别的仪式,从此就开始新的阶段,轻装上阵了。”[8]108这是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来看王琦瑶,也写出了王琦瑶的内心。王德威曾评价王安忆的作品人物:“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是辗转于上海无限的虚荣与骚动间,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协现实的艰难。”[11]上海的“女郎还是乐意嫁首长,首长年纪却必然相当大,而且有了人。”[12]265这是无可奈何的社会生存,是跨越人生层级的最佳通道。结识李主任、感受李主任的权力、爱上李主任,一系列的过程都让王琦瑶认清了权力至上的现实,投身到权力之下成为一只笼子里的金丝雀,寻找到了自己与社会的最好的相处模式,接受了这一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享受着这一结果给自己带来的益处,达成了自我与社会的和解。李主任的消失使王琦瑶的人生重新进入了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是自我选择与现实变故之后带来的,经过外界与自我调节之后,她重新找到了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并不需要依附于男人生活,并且在弄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王琦瑶无法脱离上海的生活,在自我审视、认识之后,从邬桥回到上海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她经历内心劫难之后与自我、生活和社会的一种和解。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一直依靠公婆过着富太太的生活,公公家被抄后,她没有坐以待毙,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积极寻找着赚钱养家的方法——去典当物品,替别人看护孩子,到工厂日复一日地做着重复、枯燥的工作。端丽由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太太变成了凌晨起床排队买菜的妇女,狼狈而艰难地支撑了下来。虽然所作的一切与端丽以往的身份有些不符,但现实让她找到了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与眼前的生活达成了共处。十年里,家里的一切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她成了家庭里的主心骨,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文革”后,公公的东西被送了回来,端丽家又回到了以前的优渥生活,然而只有端丽知道,时间“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13]。十年的苦日子,使端丽不仅仅获得了更为丰厚的社会认知和洞察人性的能力,还得到了宝贵的心理成长和精神成长。虽然是文光说这人生的真谛实质是自食其力,但实际上作者是借他们之口替端丽表达心声:这个家庭没有谁能比端丽更懂得自食其力带来的满足与快乐。端丽正是通过逆境中的社会磨练,找到了人生的立足点。
作品中女性人物经历挫折之后,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会遭受到“活”的挑战,然而都拒绝接受苦难下的逃离路径,转而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与自我和社会现实达成更好的和谐相处状态。
三、女性作为成长主体的真实处境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成长主体的成长面临着许多与男性成长不同的环境与状况。王安忆作品中叙述的女性成长经历可见一斑。
父系社会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长久地运用强者话语权,使男性女性的思维、社会生长环境成为定式,这就造成了女性成长中的困境。这种困境既有长久束缚下社会、他人对女性造成的,也有女性在突围困境时自己成造的。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女性逐渐动摇着父系社会的地基,然而在父系社会的长久浸染下,女性依旧会在自觉与非自觉中陷入困境,同时,这种困境继续影响着人物的成长。
女性成长的困境首先来自社会意识。波伏娃曾说:“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14]男性与女性在出生之时,除去生理特征,其作为人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然而正是长久父系社会的统治,使得在男人、女人生存于不同的成长期待、成长态度和成长环境之中。失去了爹娘而跟着叔叔婶婶生活的富萍十分看重自己的婚姻大事,但是富萍的成长空间不允许她自己做决定去找自由恋爱的对象,只能通过传统说媒的方式,与李天华说了亲。到了上海,富萍脱离了乡下的束缚,有机会寻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因而努力挣脱家庭、乡下给自己造成的成长困境,做出了一个主体性选择——组建一个自己的家庭。在《桃之夭夭》中,郁晓秋只是因为自身发育与身边女生的节奏不同,有着好看的“S”曲线,就被其他人冠上带有恶意的称呼,甚至成了母亲笑明明随时打个巴掌的理由。女性身体在青春期发育时,是美好的时期,有着青春的活力,有着抽枝发芽的舒展。身体的生理发育是人类成长的必经之路,然而却成为了女性自身的过错,这是父系社会遮蔽女性身体的一种手段,也是女性意识被父权文化长久规约后对女性同类无意识的束缚。
女性受制约于男性话语权下几千年,生存与成长环境早已被父权思想浸染。父权统治者为了更好地把握自己的话语权,为女性设置了重重限制,让女性伏身于自己的身旁,最终形成了女性依附男性的传统与思想。王琦瑶依靠李主任的施舍拥有后半辈子吃喝不愁的金条;严家师母依靠自己的丈夫每天无所事事不愁生活;欧阳端丽依靠丈夫父亲的积蓄过着富家太太的生活。男性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和经济权,这些女性依附于男人,她们的“世界非常小”,是“女人的世界”,被大世界主宰着,大世界是基础,是立足之本,是男性权力的化身。她们“来去都不由己,只由他的”[8]105。作品中的女性本可以通过学识或能力等多种途径,摆脱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的命运,但自己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最传统的路径——依附男人。“爱丽丝”公寓的众多与常见,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普遍性。但依赖男人并不是什么都不用做,需要女人放弃自己主体的话语言说,全部顺从男性,因而加重了社会对女性进行压迫、轻视而造成的困境,女性更加轻易地被男性当作掌中之物。除了有来自社会为女性制造的困境,还有传统女性文化对女性的规约制造的困境。这就使得传统女性文化、女性、女性思想之间形成了完全的闭环结构,传统文化的教育环境导致女性成长为具有符合传统文化思想的女性,遵守女性传统思想又进而增强了传统文化的统辖力。一代代女性便在这样循环往复的结构中成长起来。
四、王安忆女性成长小说的叙事策略
在长久的社会意识与传统女性文化的规约下,女性成长遭遇着独属女性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下,女性依旧在不断努力寻找出路,王安忆对女性成长中所面临的困境有着自己的方式与策略:以身体为载体的女性主体思想的被遮蔽与突围及自我掌控。
除去生理特征的差异,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没有差别,但是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女性身体在父系社会中总是被男性话语所言说、统治,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导权,甚至到了市场经济时,女性的身体明目张胆地被物化、客体化。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由共同意识和被塑造的个人意识共同促成的。女性在这种意识环境下的成长过程中无法掌控的不仅仅是肉体层面的,更是以身体作为符号载体的女性意识和话语权。王安忆在作品中,多是将人物放置进成长的曲折进程内,让她们在男性话语权的笼罩下由无意识的堕落转向有意识的自我突围与掌控。
在王安忆的作品中,许多女性人物都经历过男性话语权下的无可奈何。王琦瑶认为选举上海小姐是为女性谋得社会地位,实际上上海小姐比赛并非是对女性的一种认同,只是掌握着权力与话语权的人将美丽的年轻女性作为一种物化的客体进行展示,用男性的标准进行审视与评价,而王琦瑶正是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走进了男性把控的世界。在上海这个城市,王琦瑶的美造成了她成长中的挫折,也是她得心应手的工具。“惯在上海生活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这种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这种光荣所含的危险。”[15]王琦瑶与李主任在一起后住进了爱丽丝公寓,虽然上海局势紧张,但是她没有受到影响,不需要为生计发愁,不需要为明天做筹划,只是一心一意地“等”,仿佛如此就可以和李主任在这乱世之中达到永恒,继续做美丽无忧的“三小姐”。通过用身体交换的方式拴住了男人,找到了一时的归宿。一切都处于被动之中,任由摆弄,失去作为女性的主动权与主体性,只是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可以随时被舍弃的情人。
苏提如何能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发展呢?她明白自己以学历、才识是无法立足于大城市中的,只能通过利用青春、美貌、身体才能实现在上海大城市中的阶层转变,这是最适合她的途径,也是最快的方法。苏提们在城市中的成长打拼里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身体的权力,享受利用身体为自身带来的便利,这是社会促成的结果,也是自主意识被男性话语权遮蔽的女性为自己找到的最佳路径。女性对身体的轻视与无谓的同时,将身体工具化,加剧了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客体化。当意识到这些时,女性早已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肉体和主体意识一同失去了。
王琦瑶选择了李主任,就选择了身份的缺失,这便是丧失女性主体性思想与失去反思意识的开始。在遇见李主任之前,程先生便喜欢着王琦瑶,但是王琦瑶“志不在此”,程先生只是再无选择后的选择。上海这个地方,“闻竞争生活,竞争婚姻、出路,都无形而相当激烈。”[12]265她宁愿做李主任的“妾”也不愿做程先生的“妻”,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王琦瑶家里也并不阻拦,因着“李主任的汽车牌号在上海滩都是有名的”[8]106,开明地默认了女儿的选择。为了更好地迎合社会男性的认同,王琦瑶在成年男性的指导之下,找到了适合自己且能更好地满足男性审美的搭配,这都是迎合男权社会的行为,这也是女性成长进程中步入无意识堕落的开始。
在女性成长过程中,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遮蔽,还有外来文化对女性意识觉醒的遮蔽。《我爱比尔》的阿三是一个师范大学艺术系女生,正是在尚未形成整体性价值观的人生阶段,通过画廊汲取到了新鲜的见识,接触到了西方文化下成长的外国人,对她的思想有了冲击。而上海又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人文环境的城市,“多元文化的环境对于环境主体的价值观念形成又着不可低估的影响。”[6]29阿三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下充满了困惑与迷茫,误入了歧途。她来不及看清,“一个女孩子在身体和精神都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毁灭,自毁。”[16]
女性身体与女性主体思想被遮蔽,作品中的女性逐渐走上了“堕落”之路,然而王安忆并非任其任意放纵。王琦瑶踏入男性为女性制造的圈套之前,作者为王琦瑶设置了一位引路人——导演,暗示王琦瑶所选择的是一条歧路,试图引导王琦瑶走上正途,“上海小姐”这顶桂冠“它迷住你的眼,可等你睁开眼睛,却什么都没有”,到头来,“要多虚无有多虚无”[8]68-69。王琦瑶跟随了李主任之后,王安忆为她制造了挫折,经历了绝望与打击的王琦瑶,在邬桥洗礼过自我精神之后,重新找到了生活的路径与方向。虽然早年走了些弯路,但成长后的王琦瑶总算处在了掌控自我话语权的人生状态中,即使自身发生了重大变故——意外怀孕,也坚持生下了薇薇,独自抚养,逐步成了新时代中的一位独立女性。阿三也并非彻底沦陷,虽中途迷失在与外国人的周旋中,但是王安忆设计了一场“劳改所之旅”,使得阿三进劳改所之后有所触动与转变,在出逃劳改所的路途中看见了一枚小母鸡藏起来的处女蛋,回想到了自己也是如此藏起自己的“处女蛋”,阿三对这颗蛋的珍视亦是对自己的爱怜。
由此看来,王安忆的叙事策略是:一是对真实现实的颠覆与突围。年轻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为了生存或找寻到更好的生活而用身体来交换,身体与主体意识都被遮蔽在男性话语权之下,而生活却并非得偿所愿,经过事件后开始清醒与反思,进行对男性话语权的突围与自我解救,追寻新的自我。这种叙述策略不仅为女性的思想及行为转变找到合理的支撑点,更是通过人物经历来证明女性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女性在遮蔽下的突围的意义。如果女性在成长过程中,缺乏自己的主体意识、反思意识,那么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重新陷入主体困境之中,被笼罩在男性话语权制造的黑暗地界内,失去女性的话语,一步一步走入无止境的恶性循环。因而,王安忆在作品的落脚点是其一直关注着女性最后是否找回了女性主体性意识和话语权。
二是对精神出路的叙事建构。在这些作品之后,王安忆开始思考找回女性主体性意识和话语权的女性该如何选择、走向何方,因而在富萍、笑明明身上出现了探索的苗头,此时王安忆的叙事策略发生了转变,对于女性的生存,不再是只给予依赖男性这一条出路,而是依靠自力;对于女性的思想,让她们摆脱了与男性过多的儿女私情的纠缠,而是转向关注自身,追求更好的人生。
王安忆的作品体现了其对女性问题连续不断地思考,在文学实践中积极找寻适合女性的生存路径及两性相处方式,并非仅站在女性本位角度思考女性问题、两性问题,而是立足于更广阔的人性、两性和谐立场之上叙述女性的生命与成长历程,这也是值得继续探索的。
五、结语
如果单纯从时间、年龄的角度来考虑成长,就会使人物的成长具有单一性、局限性,甚至在部分程度上会失去社会性、文学性、文化性,正如我们一开始定义的成长小说一样,要分别向内、向外探讨,向内是探讨成长与认知,向外是探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何种程度,这两种都是不可缺少的。樊国宾在著作中阐述:“所谓小说的‘成长’主题,也就是通过叙事来建立主人公在经历‘时间’之后终于形成了自足的人格精神结构——即‘主体’(生成)过程的话语设置。”[17]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女性主人公在成长中对话语权以及主体意识的争夺。但需要注意是,话语权与主体意识一定是以女性自我为核心,如果是围绕着男性思维,那么就会重新落入死胡同中。此外,反思意识同样不可缺少,女性自足的人格精神仍旧需要不断回视、反思,从而使自己立足于日新月异的世界之中,更好地增进两性的和谐相处。同时,在分析女性成长小说时,也不能局限于小说文本本身的探讨,而要站在更广阔的角度去分析女性成长小说及其发展脉络。女性成长小说还可以是创作主体意识和作品人物的形象系列随着时代或社会、思想(作者的创作思想、女性思想等)的变革而产生的变化、发展(包括正面的进步,反面的退步)的女性成长发展史的集合体,这些也是不能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