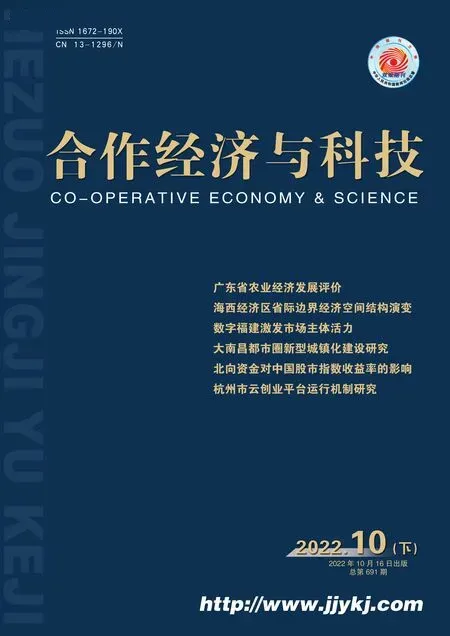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机制研究
2023-01-05潘晓宇
□文/潘晓宇
(1.广西大学经济学院;2.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院 广西·南宁)
[提要]本研究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直接减缓相对贫困,以及通过促进居民就业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互联网保险、储蓄效应等间接减缓相对贫困。
2020年,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战圆满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贫困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全会首次提及“相对贫困”,这表示相对贫困会成为未来扶贫工作的重要核心内容,等待着我们的是更严峻的相对贫困问题。此后,中国正式进入“后脱贫时代”。这也意味着现实的情况对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往学术界已经对如何解决绝对贫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对于如何深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却少之又少。在解决绝对贫困的攻坚战中,金融扶贫强调的是精准;在解决相对贫困的持久战中,金融扶贫需要注重普惠。
金融科技发展快速,其在普惠金融中的应用也不断加深,令真正全面发展普惠金融成为了可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缓解信贷约束,其包容性让众多本不能接触到金融服务的人以低成本获得贷款,减轻了人们对于传统金融物理网点的依赖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于是,在相对贫困概念的提出以及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如今,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分析,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减缓相对贫困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贫困减缓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自从金融抑制现象提出,许多国外学者便开始从金融的视角来研究贫困,试图找到通过金融的方法解决贫困问题。之后,随着普惠金融这个概念首次被联合国提出,这给国内外学者研究减贫机制与减贫效应提供了新的方向。经过研究,众多学者认为普惠金融的普惠与便捷让许多贫困人群以较低的成本接触到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进而增收减贫。比如,Park通过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分析了普惠金融对这些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减贫效应,得出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减缓贫困的结论。同时,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研究。例如,马彧菲、杜朝运通过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与居民消费水平的关系,通过居民消费水平进而反映收入差距,以此来衡量贫困减缓的效果;卢盼盼、张长全创新地采用GMM法分析贫困发生率,进而折射出贫困减缓的效果。总结来说,国内外对于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研究中,大多采用基尼系数的变化、收入差距的缩小来衡量。
自普惠金融概念提出后,我国于2016年8月率先提出数字普惠金融概念,自此贫困减缓的研究正式转入通过数字金融来实现。起初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研究依然类似于传统的普惠金融方面的研究,比如宋晓玲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间要素的耦合作用与门槛效应进行研究分析,得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城乡间收入差距,进而减缓贫困;黄益平和陶坤玉也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通过数字技术有效打破了贫困人口金融服务获得难的壁垒,便捷交易,共享信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传统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束缚,促进了社会平等,有效减缓贫困。并且随着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编制,对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入。黄倩等通过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进而反映其减贫效果卓著,尤其是对于贫困人口更为显著。龚沁宜和成学真通过面板平滑转换回归,分别对经济状况各不相同的各个省份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分析得出,不论是经济发展缓慢还是经济发展快速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相对贫困,对于经济发展缓慢的省份则是更加有效果。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只有满足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才能有效减贫。杨艳琳和付晨玉在文章中提出,虽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从而增收减缓贫困,但这一情况仅对贫困强度稍轻的农户有效,而对于贫困程度较重的农户则不能有效减贫。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涓滴效应,虽然数字普惠金融帮助了一些轻微贫困农户销售了商品、获得了贷款,从而增加了收入、减缓了贫困,但是对于那些贫困情况较为严重的农户,他们接触不到互联网技术,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的涓滴效应就不能覆盖到其家中,便不能获得低成本贷款,进而失去了创业就业的机会,而导致双方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了所谓的数字鸿沟。此外,依旧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抑制贫困的减缓。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绝对贫困已经不再存在。然而,对于相对贫困,学术界的研究依然较少,并且对于相对贫困的定义也并没有一个共识。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研究依然处于缺失的状态,于是本文将对当前学术界对于相对贫困的概念进行整理,并分析几种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
二、相关概念
(一)相对贫困。绝对贫困关注的是基本物质需求,是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的贫困,可以被理解为物质上的匮乏,然而相对贫困是一种主观判断,是相比较而言的贫困,是由社会做出的,关注的是相对差距水平,它实际上是社会上多数人对较低生活水平的一定确认,相对剥夺和相对排斥是其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相对贫困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依靠个人或家庭的劳动力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虽能维持基本生活保障,但无法满足在当地条件下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其他生活需求状态。这就导致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地区的相对贫困标准并不相同,其衡量标准往往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力、人口质量等密切相关。这就给我国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出了难点,一是如何划定相对贫困标准;二是如何在基于当地特定条件下解决相对贫困。因为从一个县来看存在相对贫困人口;从一个市来看存在相对贫困县;从一个省来看存在相对贫困市;从全国来看,存在相对贫困省份,这就导致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相对贫困标准的划定与相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案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需要全国上下各地齐头并进,共同努力。但不变的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完成各个阶段的任务。将人民需要的各个方面划入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中,所以仅仅依靠收入水平衡量是远远不够的,相对贫困应该是一个用多维因素衡量的指标,根据对现有文献的阅读总结,结合全国各地的试点经验,我国相对贫困的衡量应该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融入、收入水平等方面入手。接着通过各类统计方法,比如变异系数法等方式为各维度各指标赋权,以便更准确地衡量相对贫困。
目前,对于相对贫困指标的衡量有如下几种常见的情况:一是依旧是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标准,选取当地居民收入中位数或平均数的40%~60%,或者是当地人口的一定比例作为标准,比如广东省便是采用这类方法;二是选用基尼系数作为重要指标来衡量相对贫困,但这种方法存在缺陷,其本意是通过基尼系数计算收入差距,进而衡量相对贫困,但这种计算本来就存在问题,何况用收入衡量相对贫困太过单一;三是采用多维贫困指数,典型的方法是A-F法,其理论基础是相对剥夺,从各个维度选取指标,若是某人或某家庭该指标数额低于当地的剥夺线(约平均水平的50%),则视为该指标被剥夺,再通过各类指标权重计算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这种方法是如今的主流方法。
(二)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金融”,是众多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可以与供给、需求、市场等经济术语并列。亦或说,金融是一个行业,与建筑、教育等并列,这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起点。第二层含义是“普惠”。“普惠+金融”的社会意义,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希望能够为农民、老人、学生、小微企业等金融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服务,使其能够利用金融服务获得更好的经济改善和生活便利。在这个意义上,普惠金融的重点对象是弱势群体,重点目标是帮助弱势群体获得融资,摆脱贫困。第三层含义是“数字”,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普惠金融。如今,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已经深刻影响到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和数字叠加,是普惠金融如何和时代特征结合的问题。目前,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学界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按照综合性、均衡性、可比性、连续性和可行性等原则,从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三个维度出发,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三个维度总共包含9个二级维度、24个具体指标,可以全方面、综合性地对数字普惠金融进行衡量,反映其实际发展状况。
三、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机制理论分析
根据作用途径和效果的不同,本文将从直接与间接维度来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一是直接角度,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和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从而直接提高贫困者所能拥有的物质资本,进而减缓相对贫困;二是间接角度,即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居民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互联网保险、储蓄等方面来提高贫困者拥有的人力、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居民增收和贫困减缓。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直接作用。传统金融往往具有“嫌贫爱富”的特点,即市场中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往往会向优质的客户靠拢,而资本量较低的长尾人群往往只能通过高成本来获得金融服务,甚至根本得不到金融服务,这部分长尾人群似乎被市场忽视了。然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很好地缓解了这方面的问题,其通过创新金融产品,优化储蓄、信贷服务流程,简化支付手段等方式,很好地将数字科技手段与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解决了传统金融服务成本高、速度慢、覆盖面少的缺点,提高了长尾人群对金融服务资源的可得性,同时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减少了金融机构的成本,从而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总而言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使长尾贫困人群更易接触到金融服务,从而充分获得数字红利,直接减缓相对贫困。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间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居民创业就业从而缓解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让贫困群体更容易接触到金融服务,从而获得创业资金,同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催生出一些新兴产业或者传统产业的新模式。另外,随着移动支付的全面覆盖,商户与商户、用户与用户、用户与商户之间的交易越发便捷,大多数信息全面共享,能够快速把握市场风口。贫困居民能够获得资金、能够获得信息、能够获得技术,其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进而增加居民收入,缓解相对贫困。
传统信贷服务中,人们需要通过担保、抵押或者高信用来获得贷款,这是因为传统金融机构获取人们信用记录的方式太过困难,从而导致获取信息的成本较高,因而对于普通民众借贷的需求,审核较为严格,人们借贷成本较高。但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相关技术手段,对过往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存储加工,从而形成用户个人的信用记录,能够减少金融机构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因此,金融机构放松了对居民获取贷款所需的抵押担保品,令居民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借贷需求不再受到抵押品价值和担保方式的制约,从而有效缓解信贷约束,提高居民收入,进而减缓相对贫困。
增大相对贫困差距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因意外致贫或因疾病致贫。过去人们对于保险的意识缺乏,而如今数字普惠金融方便人们通过互联网购买保险,同时通过大数据将各种市面上所能接触的保险产品聚集,给人们提供了更容易接触除社保以外的其他保险形式的通道,提高了人们面对意外、疾病时的抵抗能力。而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增加优质保险产品的覆盖以提高居民在遇到意外或是重大疾病时的风险抵御能力,从而降低财产方面的损失,进而减缓相对贫困。
综上,随着诸如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发展,极大促进了人们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快捷性,大大冲击了传统金融的发展模式,人们对于传统物理网点的依赖性逐渐减少,依托于区块链、大数据的帮助,传统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得到了新的机会。但是,当前的研究大多基于传统的普惠金融亦或者是基于对绝对贫困的减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研究较为空缺,尤其是其减缓相对贫困的途径。
本文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从直接减贫效应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直接减缓相对贫困;(2)从间接减贫效应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居民就业、缓解信贷约束、互联网保险、储蓄效应等间接减缓相对贫困。
根据如上结论,在这里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与想法:一是丰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产品品种,增加贫困人群充分接触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可能性。如前文所述的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减缓贫困的过程中,存在涓滴效应与数字鸿沟问题,那么在减缓相对贫困的情况下,是否依旧可能存在严重的涓滴效应与数字鸿沟问题。即由于人力以及资本的匮乏,相应的低收入贫困群体或许无法有效地接触到新兴数字技术,从而无法有效获得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好处。所以,丰富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以及容易获得的服务,是社会上大多阶层,尤其是相对的低收入群体所需要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提供多层次、全方面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建立独特有效的产品供给系统,是必不可少的,如此让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接触到数字普惠金融。二是要重视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不仅要包括银行服务,还要包括投资、保险、货币基金、征信等服务的创新。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互联网技术,促使金融产品的数字化,争取创新出低门槛、低风险的金融产品,真正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大众化。三是相应机构需要精准锚定目标群体,解决“灌溉式扶贫”问题,缓解精准性不足的问题,并且提倡政府利用好数字技术优势,做好相应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大众的数字金融应用水平且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切实保护公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