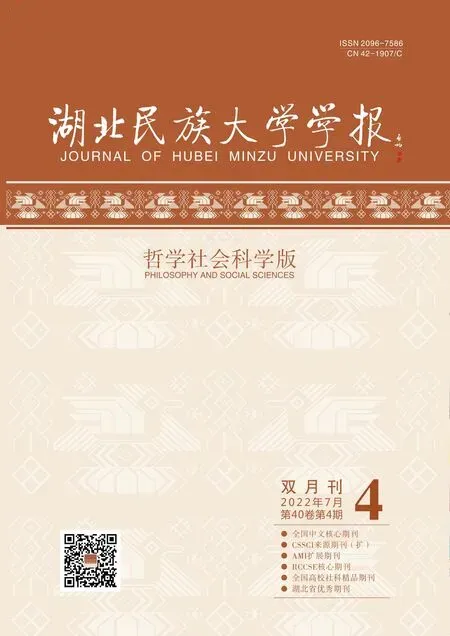卫所移民、社会流动与民族互嵌
——以湖广施州卫为考察中心
2023-01-04陈文元
陈文元
学界对卫所制度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诸多前辈时贤进行了旨趣各异的研讨,深入推动了卫所制度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一些学者从王朝开拓、历史移民、边疆治理、民族融合等层面的专论中,讨论了卫所移民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影响。(1)参见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杨洪林:《历史移民与武陵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等等。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区域或个案,从民族互动、地区开发、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等角度关注了卫所移民的融入与发展。(2)参见史继忠:《明代卫所与清镇开发》,《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1期;郭红:《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期;邹立波:《明代川西北的卫所、边政与边地社会》,《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肖晴:《明代的边疆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记忆》,《中州学刊》2018年第8期;龙圣:《明代五开卫“华款”初探——兼论明代汉侗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王泽琪:《卫所移民与边地社会:明代岷州卫的实践》,《社会科学论坛》2020年第6期;等等。具体到施州卫,范植清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施州卫的建置、屯戍与民族融合。(3)范植清:《施州卫建置屯戍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范植清:《明代施州卫的设立与汉族、土家族的融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这些成果或多或少涉及“卫所移民与民族互嵌”议题,但并无系统专论与微观考察。
“民族互嵌”看似是一个现代概念,却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互嵌”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从明代实施并延续至清前期的卫所制度,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重要力量。不同于以往的军事屯垦移民,明代大量卫所汉族移民的永久迁入与融入,“他乡”变“故乡”,连接起“内地”与“边疆”,整合“主流”与“边缘”,对各民族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笔者粗略认为,明代数百万卫所汉族移民进入南方山地社会,形成了初步的“民族互嵌”格局。(4)陈文元:《关于明清卫所制度研究的新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6期。笔者曾撰文简略讨论了“卫所移民与民族互嵌”的表现形式(5)陈文元:《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互嵌》,《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但并未基于个案的深入探讨和分析。鉴于此,笔者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以施州卫为例,窥探明清时期卫所制度三百余年的历史脉络,阐发卫所移民的社会流动与融入情形,分析卫所制度与民族互嵌的形成过程、结构类型与文化内涵,以期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地方经验和历史智慧。
一、施州卫建制与移民构成
明朝建立后,组建军户征调大量男丁充实军伍,从沿海到内地,从腹地到边疆,均以卫所镇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6)张廷玉:《明史》卷89《兵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75页。伴随着明初开国军事建制深入地方与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设置施州卫,并不断完善建制。大量的施州卫移民于鄂西万山中驻扎生根,成为一个影响区域社会结构的文化群体。
(一)军政建制
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平定明夏政权正式接管湖广西部,但当时仅立施州,卫所系统尚未建立。为管控鄂西土司,经略边地,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廷设立“施州卫指挥使司”,属湖广都指挥使司,时施州卫与施州尚同城而治。此后土司时而“作乱”,为稳定地方,建立统治秩序,明廷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省州入卫”。“本朝洪武四年仍置施州,领建始一县,属四川夔州府。十四年置施州卫指挥使司,属湖广都指挥使司。二十三年割建始县隶夔,省州入卫,改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属湖广布政司。领千户所三,军民千户所一,宣抚司三,安抚司八,长官司三,编户三里。”(7)薛纲修,吴廷举续编:《湖广图经志书》卷20《施州卫》,嘉靖元年(1522年)刻本。经过此番调整,施州卫成为既统辖土司又兼理民政的军民卫所。
施州卫建立后,建制略有变动,据《清史稿》所载:施州卫“辖三里、五所、三十一土司:市郭里、都亭里、崇宁里;附郭左、右、中三所,大田军民千户所,支罗镇守百户所”(8)赵尔巽:《清史稿》卷512《土司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209-14210页。。施州卫所辖“三里”乃明初合并施州而来。相比一般卫所的五所建制,施州卫内统仅三所,“有左、中、右三千户所,有军兵四千六百七十九人”(9)张家檙修、朱寅赞纂:《恩施县志》卷2《军置》,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卫所建制与军队人数略低于常制。不过,洪武末年建立大田所,嘉靖年间又立支罗所,皆为施州卫外领。
大田军民千户所建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编户一里,初戍额1620名,其中调酉阳、平茶土兵1110名、施州卫左所汉军510名。“就留酉阳、平茶等司随征将卒一千一百一十名把隘守卫。土司乱发不常,复调本卫左所汉官兵五百十名兼同协卫”(10)张梓修、张光杰纂:《咸丰县志》卷19《艺文志》,同治四年(1865年)刻本。,不过,万历年间已增至3127人(11)徐学谟:《湖广总志》卷29《兵防一》,万历十九年(1591年)刻本。,可能是防止鄂西土司“作乱”,增兵以扼其势。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又增设支罗百户所,“四十五年题准支罗新旧二寨改为守御百户所,官军就于施州卫三千户所摘拨屯种,以便弹压”(12)李东阳:《大明会典》卷131《镇戍六》,正德四年(1509年)刻本。,官兵从施州卫原额中调拨。
卫所制度是明廷设置于地方的军事建制。即便是军民卫,其立卫之本依然是军事镇戍与屯田。施州卫武备设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总旗、小旗,以及大量旗官(军士)。卫指挥以下军官多世袭;文秩设抚夷同知、儒学教授、训导、卫经历。道光《施南府志》载明代施州卫抚夷同知有28人,儒学教授43人,训导27人,经历33人。(13)罗德昆:《施南府志》卷19《官师志》,道光十七年(1837年)刻本。不过此为流官性质,与施州卫官、军士的永久性移民不同。
(二)移民构成
施州卫“惟屯籍系明初调拨京省等地的军队”(14)张家檙修、朱寅赞纂:《恩施县志》卷4《风俗》,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亦即军士多为外地汉族迁入。嘉庆《恩施县志》记载有13家世袭卫官:其中,7家来自南直隶(童、唐、周、陶、冯、马、石),3家来自北直隶(李、孙、杜),2家籍贯湖广(赵、邓),1家籍贯河南(孙)。如童氏,入卫始祖“童辅,合肥人,永乐四年调施州卫指挥,世袭佥事,辅传锺,锺传璋,璋传昶,昶传希卨,希卨传养廉,养廉传天宠,天宠传复元,传八世”(15)张家檙修、朱寅赞纂:《恩施县志》卷3《人物》,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嘉庆《恩施县志》前载“童昶”条亦有言及:“童昶,字明甫,本合肥人,其先人辅永乐四年调施州指挥世袭佥事,遂为恩施人。”(16)张家檙修、朱寅赞纂:《恩施县志》卷3《人物》,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又如孙氏,入卫始祖“孙演,无锡人,洪武十七年调,传斌、启军、端、輗、竭、辅、继芳、光裕九世”;周氏入卫始祖“周斌,怀远人,洪武三十年调,传正、溥、椿、鹏、继志、一元、经、历久、历远十世”。(17)张家檙修、朱寅赞纂:《恩施县志》卷3《人物》,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
大田所见志共有15家世袭官员:11家汉官中有6家来自南直隶(杨、蒋、徐、丁、梅、邢),3家来自湖广(舒、蒋、张),1家籍贯河南(耿),1家籍贯四川(田)。3家土官(冉、许、杨),均来自川南酉阳、平茶等地。另有1家籍贯不详(张)。如杨氏入所始祖,“杨公保,原籍江南淮安府山阴人,洪武二十三年调湖广施州卫大田所”;又如徐氏入所始祖,“徐腾达,原籍江南凤阳府人……随蓝玉征散毛诸峒。洪武二十三年官大田千户”(18)陈侃:《咸丰县志》卷11《氏族志》,民国三年(1914年)刻本。;再如耿氏入所始祖,“耿全,汝阳人,大田千户,传正、辉、忠、焘、杰、维城、良将八世”(19)张家檙修、朱寅赞纂:《恩施县志》卷3《人物》,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土官冉氏,“冉应义,原籍四川酉阳司宣慰使如彪之子,明洪武二十三年与弟应礼、应信随其叔如豹隶蓝玉军,征散毛峒有功,后如豹授施州卫指挥二十年,应义、应信俱授大田千百户等职”(20)陈侃:《咸丰县志》卷11《氏族志》,民国三年(1914年)刻本。。
从以上内容可知,施州卫移民多来自长江中下游一带,除大田所有一部分军士是土家族外,其余均为汉族。虽说卫官籍贯与卫所军士不尽相同,有“袭职”与“充役”之分,但结合明代军伍属性,或有出入,大致如此。(21)如利川朱砂屯《朱氏族谱》称:“洪武十三年,弟史致仕携家,由荆州石马头笤箕坳起岸,屯军于施州卫。”又,利川吴氏宗祠碑《原建宗祠记》记载:“吾吴氏派衍南京,族起句容……诸季仍居原郡,惟我恒祖,生应芳公,自明洪武十六年迁居湖广施州卫。”虽不能一一考证施州卫普通军士的具体来源地,但大抵“皆迁诸内地”无疑。明廷规定,卫所军士应娶妻生子,且需军余在营生理。以施州卫正军、军余、余丁及所属军眷五口计,则明初鄂西迁入有近3万汉族移民(第一代)。卫所军士隶军户,子孙需世代从军,因而卫所移民的人口是较为稳定和长期的。由明迄清,施州卫移民在鄂西万山间世代生息繁衍,久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族移民群体。
二、移民社会流动与互嵌类型
明廷在土司地区增设卫所,移民屯戍,可谓向这些地区“直接治理”的方向又迈了一步。(22)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从明初至清初,施州卫存续三百余年。(23)清朝建立后,施州卫依存南明政权以图存。1662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清廷消灭鄂西“夔东十三家”势力,于康熙三年(1664年)才正式接管鄂西。之后,废除施州卫的卫官、军户世袭制度,改设流官性质的守备、千总驻防,但保留施州卫建置,缓至雍正六年(1728年)裁撤。在这一长久历史过程中,施州卫汉族移民与鄂西土家族开展了官方/民间、主动/被动、直接/间接等形式多样的互动互融,构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民族互嵌。
(一)治理结构
鄂西“外蔽夔峡,内绕溪山,道至险阻,蛮僚错杂”(24)罗德昆:《施南府志》卷2《疆域志》,道光十七年(1837年)刻本。,处在川、鄂、黔交界处,族群关系复杂,地方势力交织,是较难治理之地。明朝建立后,明廷“以原官授之”,安置鄂西大小土酋,设置了众多土司。洪武十四年(1381年),照宋元旧制设立施州,“复置夔州府施州,以建始县隶之”(25)《明太祖实录》卷137,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月辛卯条。,施州属四川夔州府领县之散州,又置施州卫指挥使司,控蛮戍边。但随着土司反叛和施州几任知州被害(26)设立施州的当年,“洞酋覃芳诸破州城,公(施州知州李才)与州同知孙明用、州判王杰、吏目李毓秀皆死”,又“胡士能知州,洪武二十年,安福蛮夏得忠引诸蛮攻城见害”。参见张家檙等:《恩施县志》卷3《名宦》,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为加强治理,整饬防卫,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割建始县隶夔,省州入卫,改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27)薛纲修,吴廷举续编:《湖广图经志书》卷20《施州卫》,嘉靖元年(1522年)刻本。,施州卫成为既管军事又兼理民政的军民卫。州县、卫所、土司对应的是经制社会、屯堡社会、溪峒社会。此时的鄂西,腹心以施州卫镇戍,旁之有巴东县、建始县,清江以南诸土司分布,鄂西地域大致形成了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的卫所、州县、土司互嵌式的治理格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鄂西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土司“叛乱”。明廷遣凉国公蓝玉攻克,增置大田军民千户所,属施州卫。“先是凉国公蓝玉奏:散毛、镇南、大旺、施南等洞蛮人叛服不常,黔江、施州虽有卫兵,相去悬远,缓急卒难应援。今散毛地方大水田与诸蛮洞相连,宜立置千户所守御。”(28)《明太祖实录》卷201,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闰四月丙寅条。与施州卫治不同,大田所“于八面环夷腹心之中,紧扼诸司之口”(29)张梓修、张光杰纂:《咸丰县志》卷19《艺文志》,同治四年(1865年)刻本。,植入土司治理核心地带。“施州卫是明朝控驭鄂西的实力中心,大田所是施州卫最重要的辅助力量。”(30)范植清:《明前期对鄂西民族地区的治理》,《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施州卫与大田所一北一南,屯田相交,防卫呼应,进一步控扼土司势力。
嘉靖年间,龙潭土司黄俊、黄中父子作乱。明廷平定后,黄中复叛。“(嘉靖)四十四年,诏川湖会兵夹攻,川兵进攻牛栏坪,湖兵自施州卫进,中由思南逃去,为楚军所获,川军捣其巢穴,支罗平。”(3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3《四川八》,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451-3452页。后增设支罗百户所。“中既平,割半置所立屯,以百户二镇之,为支罗镇守百户所。”(32)黄世崇:《利川县志》卷1《沿革表》,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支罗百户所以二百户分别驻守,分为上、下支罗所。明中期以后,卫所军政废弛,屯政破败,施州卫自不例外。不过,支罗百户所的设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施州卫西面的防卫,使其治理触角更深嵌入土司地区。
不仅治理结构相互钳制,在土司社会治理结构中,映衬着州县、卫所管理系统。土司行政架构中有中央王朝委派具有流官性质的经历、知事、吏目等。“置湖广容美、忠建、施南、散毛四宣抚经历、知事各一员。”(33)《明太宗实录》卷55,永乐四年六月癸亥条,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2年,第814页。土司还效仿州县管理形式,在辖区设立土州、土巡检。鄂西容美土司就设置有芙蓉、大里和龙家坝三个土知州。土家族土司实行“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以“旗”为单位来组织、管理土兵和征战,很可能是摹仿卫所制度军队建置。(34)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09页。在与卫所的交流中,土司的基层建制与军事制度深受卫所制度的影响。
(二)政治身份
施州卫与土司是两个不同的政治群体,彼此的政治身份各不相同。卫所是中央王朝派驻地方的军事机构,卫所移民属王朝户籍管理中的“军户”,久之形成“屯籍”;土司是“朝廷命官”,但土司所辖土地不纳入“版图”,所属土民更不“编户齐民”,属于王朝统治界定中的“化外自治”。简言之,卫所与土司,军户与土民,两者之间的政治身份泾渭分明。
前文已述及,施州卫移民群体多来自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汉族,他们所携带的文化、技艺、“奉旨镇守”的“皇命”荣耀与汉人身份,对王朝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了一种政治资源与政治身份。在古代封建社会,“汉人”“汉文化”的主流身份与主流地位相对于“蛮夷”而言是一种吸引。土司家族“造谱”现象可视为改变政治身份的表现。譬如鄂西田氏土司,“土司若忠峒、忠孝等宣抚司,多田姓,故田亦巨族,然皆土人。惟君(容美土司田舜年)先世系中朝流寓,不与诸田合族”(35)顾彩:《容美纪游》,《容美纪游》整理小组:《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页。。容美田氏土司乃鄂西土酋,但自明代起田氏积极学习汉文化,家族先后出现了9位文人,并逐步将先系追溯为朝廷派驻地方、奉命平叛的镇守将军(36)参见雷翔:《土家田氏考略──兼评“造谱”现象》,《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第3期;吴柏森:《容美田氏世系事迹述略》,《湖北三峡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葛政委:《祖先再造与国家认同——容美土司〈田氏族谱〉和〈蹇氏族谱〉的人类学解读》,《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3年第6期。,其目的自然是有着强烈的“脱蛮入儒”的文化理想和摆脱“蛮夷”、塑造“汉人”身份的政治愿望。
相比于土司的积极靠拢,卫所移民则多半是被迫嵌入。明代中后期,卫所屯政破败,卫官大肆侵占屯地,军士成为世奴,军屯上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封建的奴役关系。(37)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7页。频繁的军事征调、繁重的差役与卫官腐化,而土司地区较低的赋税、差役,致使卫所军士弃耕逃亡“夷地”。施州卫西面、南面与土司地区广为接壤,常常成为军士潜逃之区。“施州卫延袤颇广,物产最饶,卫官朘削,致民逃夷地为乱。”(38)张廷玉:《明史》卷310《湖广土司》,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496页。卫所军士逃往“化外”的土司地区,成为“脱籍”“无籍”之人,其政治身份无疑发生改变。土司家族攀附历史名贤的“汉化”与卫所移民进入土司地区的“夷化”,是政治身份转换与互嵌的表现。
(三)民族关系
明廷在鄂西设置施州卫,其重要作用是监控和钳制土司势力,卫所与土司是对立的关系。施州卫在与土司交界险要之域设置关隘,共计十四处关口(39)所设十四关分别是:五峰关、东门山关、石乳山关、梅子关、铜锣关、老鹰关、深溪关、散毛关、土地关、野猫关、胜水关、虎城关、野熊关、野牛关等。参见徐学谟:《湖广总志》卷29《兵防二》,万历十九年(1591年)刻本。,从军事上掌控与管束鄂西土司。军事上的对抗影响民族关系发展,明初施州卫世袭指挥佥事童昶即称:“国朝设立关隘,把截甚严,至今尚传蛮不出境,汉不入峒之语。”(40)李勖:《来凤县志》卷17《武备志》,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不仅如此,为防止“汉、土”纠纷,施州卫还设立“汉土疆界碑”。“万历四十一年,忠路土司覃寅化霸占民田相仇杀,抚夷同知章守愚檄指挥唐符戡治寅化伏辜,立土汉界碑。”(41)黄世崇:《利川县志》卷10《武备志》,光绪二十年(1894年)刻本。以此观之,除了官方性和军事上的交流与互动,卫所“汉地”与土司“蛮境”人群并无过多交往。
不过,自明代中期起,卫所武备废弛,军士大量逃亡,边界模糊,防卫松散,“汉、土”互动日渐增多。而且,卫所军事职能退化,土司是卫所的重要倚赖对象,迫于战事压力,不得不征调土兵。“按明祖以土司滋扰,设卫广屯,欲使官省馈运,而人自为战也。其后兵不能卫民,反借民以卫兵,又借客兵以卫卫,则见于邹维琏之《志序》,是有卫而无兵矣!”(42)罗德昆:《施南府志》卷16《武备》,道光十七年(1837年)刻本。更甚者,卫官与土司交往形成利益关系,卫所与土司相互制衡的机制已遭到破坏,甚至土司外出劫掠,分赃卫官以求包庇:
先年卫官犹畏国法,遵例钤制夷汉,不许出入,地方得宁。自正德年间蓝、鄢叛乱,调取土兵征剿,因而习知蜀道险易,熟谙州县村落,致惹后来不时出没为害,流劫地方,杀掳人财,奸人妻女,遂将所劫子女财帛,分送施州卫官,遂与土官习为表里,违制结姻,深为缔好,故纵劫掠,事无惮忌。名虽本管,实同窝主,乃至事发,上司委官提戡,该卫所员非惟占护不发,且又力为党蔽,捏文回护。昔年唐崖长官覃万金舍等夷,出劫黔江等七州县,众议调官军将首恶擒获,监卫辄又受财,朦胧卖放。近日散毛假土官副使黄廷表等,统领千人,劫杀掳掠,至今未擒拿,该卫仍复窝隐,不肯解发。(43)刘大谟:《四川总志》卷16《经略志》,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刻本。
明廷禁止卫官与土司联合,但土司的利益输送与卫官自身腐化,使禁令似一纸空文,根本无法制止二者的勾结。卫官与土司“媾和”表明,相比明初施州卫对鄂西诸土司的防范与监控,此时双方已为政治同盟,结为姻亲,互相馈赠,形同一体。
不过,卫官与土司结交,只能表明卫所官员阶层与土司阶层对立关系发生改变。卫所军士与土民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在民间,卫所军士与土民的交融无时无刻地发生着。卫官的压榨、兵燹、生存空间狭小等使得卫所军士纷纷逃离卫所,去往他处谋生。而就在近处地广人稀、赋税、差役较轻的土司地区是他们重要的潜逃区域。这一情形在民间文献中颇有反映,施州卫军屯后裔的《焦氏族谱》有载:“……于明太祖洪武辛酉年拨湖广施州卫镇守,地名磨子岩,借住三载,四处访查落业之所,得南乡安乐屯焦八斗,甲子秋遂搬此处,携家小一齐共坐。待至万历年间数载二百零有七,不幸于九君年间被残兵扰乱,庶民不安,喜得与唐涯司(唐崖土司)侯姓开亲结义,方得趋吉避凶,又有数十载矣。”(44)焦羽平:《焦氏族谱(修订本)》原谱序,1999年。鄂西一些卫所移民遁入土司地区繁衍生息,后逐渐融入土家族。
(四)经济方式
土家族长期以来采取的是游耕经济(45)雷翔:《游耕制度:土家族古代的生产方式》,《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兼及渔猎采集。施州卫汉族移民群体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的迁入为鄂西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与耕作方式。卫官带领军士在鄂西山地开荒、屯田、兴修水利,在清江沿线及其支流的河谷平坝地区开辟了大片良田,推动了当地的农业技术革新与农业发展。不过,鄂西复杂的山地环境并不适宜广泛开展农耕。如九溪卫麻寮土千户所山羊隘“军丁专以刀耕火种,所植惟秋粟龙爪谷而已……春来采茶,夏则砍畲,秋时取岩蜂黄蜡,冬则入山寻黄连剥棕。常时以采蕨挖葛为食,饲蜂为业……”(46)甄氏族谱:《山羊隘沿革纪略》,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等编:《容美土司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84年,第490页。可以显见,施州卫移民迁入鄂西万山,大力发展农耕技术的同时,囿于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适时采用土家族的生产方式是一个比较可取的选择,土家族原有的游耕经济依然长时间得以保存。
明代中后期,卫所军事职能退化,屯田时被土司侵占。施州卫所隶属的大田所,周边土司环绕,屯田侵占最为严重。“边境田地为施南、唐崖、散毛、木册、腊壁各土司占去不下百十余处。”(47)陈侃:《咸丰县志》卷10《土司志》,民国三年(1914年)刻本。土司侵占卫所屯田后,募民继续耕种,原来无地的卫所汉族军士成为招佃对象。相应地,土民也习得了卫所汉族移民的生产理念与土地开发技术,推动了土司社会发展。根据杨洪林的研究统计,改土归流时,咸丰县官府勘出龙潭河北岸土司地区的水旱田竟比大田所屯田超过20%之多。(48)杨洪林:《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但龙潭河之北境大部分是高山、二高山地带,平地极少,开垦难度更大,表明至少在明末清初时,土民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
土民积极吸取汉族农耕技术的同时,并不完全改变自身的耕种方式。譬如农作物种植,土民虽受汉族影响,将稻谷纳入主粮范畴,但原有的饮食体系与主粮结构依然长时间保持,并适时遵循地域环境种植农作物。“其田任自开垦,官给牛具,不收租税。民皆兵也,战则自持粮糗,无事则轮番赴司听役,每季役只一旬,亦自持粮,不给工食。在役者免出战,故人人便之。其粮,以葛粉、蕨粉和以盐豆,贮袋中,水溲食之;或苦荞、大豆;虽有大米,留以待客,不敢食也。”(49)顾彩:《容美纪游》,《容美纪游》整理小组,高润身主笔:《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5页。可见,土民的主粮除了稻谷,还有葛粉、蕨粉、盐豆、苦荞、大豆等,这与卫所移民稻作农耕的粮食结构略有不同。总之,从经济方式与生产关系来看,基于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在改土归流以前,施州卫汉族移民与鄂西土民在经济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互构互嵌的发展态势。
(五)文化习俗
卫所汉族移民在与土民的长期接触中,汉族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相互影响,出现了“汉夷互融”的现象。“卫所与土司并存,实际上是同一个区域内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两种文化共存于同一个区域内,必然会发生对流和互动。”(50)段超:《元至清初汉族与土家族文化互动探析》,《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施州卫驻地有三个千户所,还有原施州的三里编户,建有卫学、商贸集市,汉族移民居住地相对较为集中,加之汉文化的主流地位和向心力作用,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对周边土司地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廷又规定:“以后土官应袭子弟,悉领入学,渐染华风,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51)张廷玉:《明史》卷310《湖广土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98页。朝廷明令促使鄂西土司阶层学汉文、习汉俗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古代土家族人名命名经历了有名无姓—汉姓土名—汉姓汉名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52)陈廷亮、叶德书:《土家族土司人名训释》,《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鄂西土司从明初“汉姓土名”到明末“汉姓汉名”的转变,体现了汉文化的渐进影响。
但鄂西在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文化并非处于弱势地位,汉文化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卫所驻地区域,深入土司地区,其影响力则较为有限。诚如明末邹维琏在《重修〈卫志〉序》中所言:“去城(卫城)不数里,民则处于不华不夷之间。”(53)罗德昆:《施南府志》,重修《卫志》序,道光十七年(1837年)刻本。与施州卫驻地不同,大田所地处鄂西土司腹地,受土家族文化影响更为直接。前文已经述及,大田所官兵是汉、土军结合,汉、土军比例大致为1∶2。汉军人数偏少,又深处“夷地”,故而万历《湖广总志》在叙述大田所风俗时,即称:“其风朴野,俗尚耕稼,土旷民稀,獠蛮杂处”(54)徐学谟:《湖广总志》卷35《风俗》,万历十九年(1591年)刻本。,“其风朴野”似乎表明原先汉军已经被“土家化”了。“文化互嵌主要表现为族际的共同性文化要素增多。”(55)杨洪林:《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以明清时期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自明代中期以后,“汉、土”交流日渐频繁,卫所移民与土民在语言、习俗、宗教信仰、饮食、节日等方面呈现出“互相类似”的文化现象,形成文化互嵌。
三、卫所移民与民族互嵌意义审思
施州卫建立之初旨在“控蛮戍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构建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凝聚核心,不同类型的互动形成了民族交融基础,治理与融入促进了民族社会整合。由明迄清,卫所移民与土民相互融入、彼此互嵌,渐成一体。
(一)构建民族凝聚核心
自秦汉以来,汉族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凝聚核心。(56)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从明至清,卫所汉族移民在长久的岁月中成为推进传统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无形遗产”。“在增强我国各民族凝聚力的过程中,明代实行的卫所制度曾经起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57)顾诚:《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91页。一方面,明廷建立施州卫,修筑卫城,兴办卫学,拓展驿道,开辟屯田,进一步确立了它作为鄂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地位。大田所的驻地成为清代以及今天咸丰县的县城,同样构成了区域副核心。甚至诸多施州卫、大田所曰屯、曰堡的屯戍地,由于交通、地理与人口聚集,经过长久发展,形成商贸集市,今天这些地方多已发展为当地重要的乡镇。核心地位与资源优势使卫所汉族移民与汉文化成为边缘互动的凝聚群体与媒介。另一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军事屯垦移民,卫所移民是“大范围、广纵深且长时段”(58)陈文元:《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互嵌》,《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6期。,程度远超前代。迁入鄂西的施州卫汉族移民选择交通要道、河谷、平坝、台地等地方驻防、屯垦,以“城”“屯”“堡”“寨”的形式围绕屯田分散聚居,于万山中呈点、线般辐射穿插,或“民逃夷地”循入土司地区,与土民村寨犬牙交错,形成社区“聚点”。这些“聚点”起着凝聚和联系的网络作用,使卫所汉族移民与土民逐渐形成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二)形成民族交融基础
创造民族互动的地域环境与空间结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和基础。“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可以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结构性保障。”(59)郝亚明:《民族互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逻辑》,《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第一,施州卫汉族移民迁入,使得原先鄂西由“土民”“土蛮”为主要构成的民族结构发生改变,近3万第一代卫所汉族移民及其后代生息繁衍,是互嵌交融的人口基础,鄂西地域由“夷多汉少”变为“夷汉相间”。汉族移民与土家族组建成新的民族大家庭,彼此交互,改变了鄂西民族交往形态。
第二,施州卫汉族移民在山川林立、溪流纵横、地形崎岖的鄂西驻扎生根,以先进的文化与技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社会环境,基于权力结构变化、空间拓展情形与经济文化类型,影响着族际互动的频度与深度。“施州卫介荆梁之会……溪洞军民错居。”(60)徐学谟:《湖广总志》卷30《兵防志中·险要》,万历十九年(1591年)刻本。经过300余年的磨合,卫所与土司结为一体,移民与土民不断融合,削弱了各民族的离心倾向,为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交融创造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第三,明代施州卫汉族移民的迁入与融入过程,产生了施州卫城、大田所城以及众多屯、堡等,伴随的城镇的兴起、聚落的形成,是市场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无疑给鄂西各民族营造了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基础。
(三)促进民族社会整合
建卫之初,州、卫同城而治,施州卫是比较纯粹的军事机构。但施州负责民政,辖建始县,所属编户为“里籍”,属四川布政司;施州卫负责军政,监管土司,所属军户为“屯籍”,属湖广都司。土民不编户,直属土司。而旁之巴东县属湖广布政司,整体行政区划与隶属关系较为混乱。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廷平定鄂西大规模土司反叛后,省州入卫,施州卫与巴东县同属湖广布政司,建始县划归四川夔州府。至此,施州卫成为军民卫,统领原施州民政与鄂西土司,结束了施州、施州卫二元治理模式,大体上实现了鄂西一元化治理,这一治理架构运行300余年,推动了多民族社会整合。
施州卫辖有“市郭里、都亭里、崇宁里”三里。村寨具体情形,按嘉庆《恩施县志》所载:“西南曰‘市郭里’,村镇八:南屯堡、朱砂溪、芭蕉村、落坡村、军寨村、龙马村、屯堡、金子坝。北曰‘都亭里’,村镇六:水田坝、三会驿、落业坝、马者村、木贡村、木抚村。东曰‘崇宁里’,村镇十二:河水屯、三里坝、蒋家坝、滚龙坝、七渡溪、人山岭、花被村、落渡村、石板场、董家坝、马尾沟、杉木寮。”(61)张家檙修、朱寅赞纂:《恩施县志》卷1《建置》,嘉庆十三年(1808年)刻本。其中,西南市郭里、北边都亭里与土民村寨都是深度接壤,形成交错杂居。与此同时,施州卫还辖有“左、中、右”三所,经过300余年的发展,此处“三里”已是原施州卫内属三所屯堡军户和三里民户混合以后的乡村建制。并且改土归流后,都亭里及其屯堡大都并入利川县(今利川市),形成混合聚居态势。大田所紧邻土司地区,军户屯堡与土民村寨更是犬牙交错。从聚居、杂居到共居,社区结构进一步整合。
施州卫汉族移民多是来自长江中下游一带,特别擅长山间沼泽地的开发和围湖造田技术,他们所拥有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与农业耕作技术推动了当地的农业革新,使原先遍布的渔猎采集、刀耕火种等经济方式一定程度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汉地农耕技术,经济生活更趋于主流。
卫所移民不远万里世代驻守,繁衍生息,久之“他乡”变“故乡”。一方面施州卫基于自身的军政职能,积极开展社会治理与地域社会构建。明代中后期,随着卫所军户“民化”与“在地化”,这一过程是施州卫汉族移民的不断融入;另一方面,从明初的对立到明末的融合,既有卫官与土司结交、军事联合,也有经济方式与生产技术借取,更有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这一过程是土著社会的接纳。卫所移民与土民相互依存、相互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发展格局。
四、结语
明代的卫所制度,是从国家层面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汉族移民运动。但卫所制度所承载的不仅是军事移民,更不仅仅只是一项普通的军事制度。伴随着卫所制度,还有人口体系、驻防屯垦、经济开发、社会治理、城市建设、文化交流、社区互动、民族关系等,对各地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这些影响,无一不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的历史原动力。
施州卫的案例显示,卫所与土司介于不同情形、不同时期的交流与互动之中,在治理结构、政治身份、民族关系、经济方式、文化习俗等层面表现出卫所移民与土民形式多样的互动互融互嵌。施州卫只是明廷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众多卫所之一,毗邻周边还有常德、永定、九溪、辰州、黔江等卫所。放眼整个南方,每省设卫不等,少则二十余卫,多则三十余卫(行都司),这些成百上千的卫所与数百万汉族移民汇聚,巩固了统治、稳定了地方,促进了民族融合,在长久的历史岁月中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进程的重要“无形遗产”。
明代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广设卫所,迁入卫所的汉族移民进一步地将南方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轨道。数百万卫所汉族移民渗入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自明初至清初犹如点、线般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辐射穿插,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形成了初步的民族互嵌格局与民族交融基础,奠定了多民族联合而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即便清朝康熙至雍正年间大范围裁撤了包括施州卫在内的众多卫所,但经过几百余年的历史积淀,因卫所制度而产生的人口结构、汉族凝聚核心作用、多民族文化交流形态、各民族互动交融模式却不会泯灭。这些影响构成了重要的历史前奏和缓冲,为清代雍正朝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做了铺垫,更使得改土归流“政治一体化”进程发挥了更大的社会效应,深入推动了南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