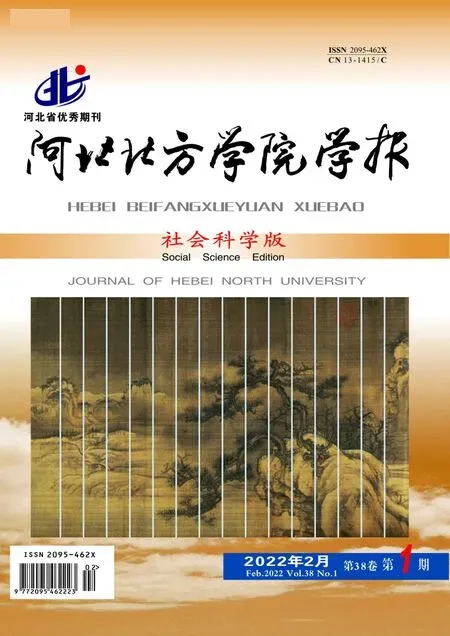《长门赋》中的“君臣”对话与性别转换
2023-01-04王丹阳
王 丹 阳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司马相如所作《长门赋》开赋家后妃宫怨题材之先河。有关此赋的作年与作赋目的历来众说纷纭,结合司马相如生平看,此赋更像是他被贬为孝文园令后以“后妃”身份对常居长门宫的武帝抒发“思君”之情所作,其主旨既是“思君”,也是被贬逐后怨闷惆怅的抒发。《长门赋》暗含着一位渴望“君臣遇合”的臣子被压制与被放逐的愁闷悲思,其与文人“悲士不遇”的哀叹相比更加隐微,但展现出来的赋家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却愈加尖锐和深刻。
一、对楚辞“神女论述”传统的继承
《长门赋》继承了屈骚“神女论述”的传统,将“家之弃妇”与“国之逐臣”的身份相糅合。赋中“男女君臣之喻”与“奇花异草之喻”的结合也是司马相如效法屈原,以女性弱势身份唤起男性君主同情模式的再创造。通篇看似是为人作赋,实质上却是向君主“叹不遇”与“表忠心”。
(一)“神女论述”的延续
自屈原以来,以追寻“神女”为主题的辞赋层出不穷,连同赋中的相关作品形成了中国辞赋史中的“神女论述”传统[1]2。而这些“神女”都是男性作家笔下的产物,她们不单被寄予了美好寓意,更被附加上政治的色彩。例如,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提到:“《离骚》以灵修、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2]3此后也多有文人论述《长门赋》对屈原“神女论述”传统的继承,如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评论道:“《长门赋》出于《山鬼》”[3];《艺苑卮言》卷二也有云:“《长门》从《骚》来,毋论胜屈,故高于宋也”[4];《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更是直接将《长门赋》归入屈原赋类。可见,司马相如在创作《长门赋》时深受楚辞的影响。如“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5]130,就引用了《楚辞·九辩》“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车既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倚结軨兮长太息,涕潺湲兮下沾轼”[2]184-185,表达思君却无法相见、一腔忠诚却无法诉说的苦闷。又如“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5]131,也是继承了《楚辞·远游》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煢煢而至曙”[2]163之意,生动地呈现出陈皇后在漫漫长夜中的孤独与落寞。
在《离骚》《高唐赋》及《神女赋》中,“神女”这个意符“以自美自恋的弱势景观,博取君王的同情赏爱,进而构筑同性结盟的政治理想国”[1]3。如屈原以香草或美人比德,佩戴香草以示高洁,展现的都是他遗世独立的自美与自恋;司马相如在《长门赋》中着意刻画的形容枯槁与愁闷悲思的陈皇后也是以弱势的地位乞求获取“同情与赏爱”。可见,女性地位在男女情爱中无限低下。此外,“神女”意符也籍以“揭露赋家所谓‘失志不遇’的悲哀,这其实是缘由君王视臣属如女色的性别扭曲,以致在自我认知上无法解脱‘封建阉割’的迫害阴影”[1]3。屈原不为楚王重用,无奈之际只能以女性的弱势身份唤起男性君主的同情与亲睐。司马相如在《长门赋》中明显延续了屈原以男女之事言说君臣之事的传统,表面看是替陈皇后作赋复宠,实则是将自己转换成女性,以哀叹夫妻离心暗指君臣失和,从而借后妃对君主的日夜思念传递自己的思君之感。
(二)“男女君臣之喻”与“奇花异草之喻”的比兴手法
自《离骚》起,“家之弃妇”与“国之逐臣”的结合由隐微转向明朗,具有典型范式的意义。夫妇与君臣以及妇道与臣道之间是一种异体同构的关系,所以借男女以喻君臣,借弃妇以喻弃臣[6]。“神女论述”正是涉及双方的男女角色扮演,尤其是张设在君臣关系之上的性别迷藏[1]7。《离骚》全篇贯穿了“男女君臣之喻”——前半部分把楚王比作“美人”,自己比作女子;后半部分把楚王比作神女,自己比作男子。洪兴祖补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句云:“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2]6《离骚》中直接以男女和夫妇关系象喻君臣关系,将君王对大臣的信任喻为夫妇好合之初的“成言”,将君臣间的聚合离弃喻为“黄昏以曰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以男子违背双方约定喻怀王猜忌贤臣[6]。屈原以“求女”喻“求君”,“求女”不得正对应着君臣失和以及贤臣被黜的无奈与苦闷。
承接“男女君臣”之喻的还有“奇花异草”之喻。在屈原作品中,“秋兰”“辟芷”“申椒”和“菌桂”等香木香料香草皆“以象比德”,是高洁、正直及不与众同流合污的象征。司马相如在《长门赋》中多处引用香草作比,向武帝展示陈皇后之德行高洁。当然,这其中自喻成分更多。如在描写陈皇后一夜空庭思念君王无果后无奈“颓思就床”时,就以“抟芳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茝香”[1]131象征她高洁的品性与美好的品格。王逸注《离骚》中“芳”指代“群贤”,“茝”为香草,皆是喻贤者[2]7,即以香草自证德行兼备;“荃”作香草“以喻君也”[2]9;五臣注“兰”曰:“兰蕙喻行,言我虽被斥逐,修行彌多。”[2]10王逸注“纫秋兰以为佩”句云:“兰,香草也,秋而芳……故行清洁者配芳……言己修身清洁。”[2]5司马相如“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愍其志焉”[2]3,可见他同屈原一样虽被君主弃而不用,却没有放逐自我,始终保守一颗忠贞之心,以期再次被委以重任。
二、从思欲抒写到政治隐喻的继承
司马相如以“佳人”自喻,抒发自己“贬谪思君”的情怀。将“佳人”的女性身份与赋家的臣属身份等同,借“佳人”思君不得抒发赋家“悲士不遇”的失意怨闷。司马相在《长门赋》中通过对环境景物的细致刻画,既表达了被遗弃宫妃的愁闷孤寂,也隐藏着一位得志文人被贬逐后的孤寂落寞。通篇没有声嘶力竭的哭诉与不满,却饱含失意难耐的怨闷之情。
(一)遗弃宫妃的“愁闷悲思”
后世对汉武帝与陈阿娇的了解更多地是源于“金屋藏娇”的典故。陈皇后是馆陶公主的女儿,因馆陶公主曾力荐汉武帝为太子,汉武帝即位后便立阿娇为后。虽然后人无法确证汉武帝与陈皇后之间有无深挚的爱情,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武帝与陈阿娇的结合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意愿”[7]74。“先秦到魏晋涉及情色议题的辞赋,仿佛可以说是在君权掌控中或世俗伦常下,被默许去渲染或反而被迫朦胧了情欲本质……于是,要不是迫不及待的耽溺欢爱,就是漫漫无尽的相思等待”[1]36,被遗弃的陈皇后在富丽堂皇的长门宫中能做的就只有无尽的相思等待。然而,在通篇的“愁闷悲思”中却只有自悲而不见怨愤之词。
司马相如在《长门赋》中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陈皇后的“愁闷悲思”。其一,环境的动态变化。司马相如在写到陈皇后神色枯槁登台远望时,没有专注于其面部情绪的描写,而是从外部环境的动荡表现她思绪烦乱和愁苦难耐。如陈皇后将阵阵雷声幻听成君驾,独上兰台看到的却只有空荡深宫中风吹帷幔,桂树摇荡,玄猿长啸的萧条孤寂。短短数语就展现出强烈的画面感,以天气转换的变化不定和突如其来衬托主人公的心绪不定,幻听雷音似君音更让人感觉悲苦不已。司马相如用写景来配合抒情,景愈悲而情愈深。其二,宫室的富丽华贵。汉武帝曾许陈皇后以“金屋藏娇”,如今虽恩宠不复,却依旧可见长门宫之富丽:以木兰为榱、以文杏为梁、以瑰木为欂栌、以错石为瓴甓、以羅猗为幔帷及以楚组为连纲,但如此华美的宫室如今却徒有萧瑟空堂与秋风落叶。司马相如在此用“金屋”装饰的华美反衬主人公内心的孤寂,以宫室华丽依旧却苍凉不已直指陈皇后失去君心后的孤寂冷落。其三,时事的凝聚包容。整篇赋没有像汉代骋词大赋那般铺张扬厉与汪洋恣肆,从各个角度刻画陈皇后对君王的思念,而是将所有思念凝聚在一个点去表达充沛的感情,如全赋时间只停留在一个普通的夜晚,事件也不过是由后妃登台思念转入深宫思念,看似结构简单,却使读者透过这一寻常夜晚看到了寂寞宫妃空房独守的无数日夜。
尽管后世已无法像恩格斯评价处于文明时代的女性“实处于无限低下的社会地位”那样来评价汉代一位身份显赫的皇后,但“外表上受尊敬,对于一切实际劳动完全隔离”确是实际存在的[7]47。后宫以恩宠影响人际尊卑,后妃乃至外戚如此看重是否受君王宠幸,这表面上是对君王情爱欲念的争夺,实则是“君王透过对锁情思欲念所达成的权力宰制”[1]25。恩宠对应着权势,被遗弃则代表着权力的消失。
(二)受宰制臣属的政治诉求
武帝时代倡导文治与辞赋隆兴,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称“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8]。但即使在武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也有“贤者失志”的无奈。“‘任贤与能’也是谈不上的,有才能的人受到朝廷重用总是凤毛麟角;根据裙带关系、门第观念的标准是少不了的。”[9]403龚克昌在《汉赋研究》中指出,汉代赋家往往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因写赋而遭到轻视;二是政治上不得志[9]403。这两个问题在司马相如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陈子良撰《祭司马相如文》云:“弹琴而感文君,诵赋而惊汉主。金门待制,深嗟武骑之轻;长门赐金,方验雕龙之重。”[10]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经久流传,他的赋作也曾“三惊汉主”,但即便如此,他也只是“金门待制”与“长门赐金”的弄臣身份——原本要扬名立万,“竟止于文学侍从之列,以顺谏谲讽略收德音”[11]47。
据龚克昌在《汉赋研究》中记载的司马相如生平看,他的几次为官经历都十分短暂,且与他所期望的政治权利及地位相差甚远。司马相如20岁时做景帝武骑常侍,仅两年就辞官到梁孝王门下做游士。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因作《天子游猎赋》为武帝所惊叹,任武帝侍从官(郎)这一闲职。据瞿蜕园《历代官制概述》中记述,“郎”是汉代一种无职务、无官署与无员额的官名,与皇帝亲近,其任务是陪在君王身侧,随时供其差遣,可见武帝从一开始便没打算启用司马相如。元朔元年(前128年),被控出使西南夷受金,遭免官,闲居茂陵县。45岁又“召为郎”。47岁改拜孝文园令,至此政治生涯结束[9]147-149。《长门赋》便作于此时,故此赋不过是借陈皇后荣宠一时却被弃的典故抒发自己从天子近臣到被贬黜放逐后的惆怅之情。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提到:“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12]司马相如数次为官却数次未能被重用,只能作一个位卑禄薄的小官,这也证明汉武帝根本无意让他参与军国大事。武帝需要的只是一个能随时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满足帝王的耳目之欲,只供君主精神愉悦,夸饰证明君主文治武功”的“俳优”,这明显与司马相如“傲诞”的性格与远大的理想抱负相违背。可见,“在封建剥削的任何时代,即使是再圣明的君主也总是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也总是要压抑、打击和陷害大量的人才,剥削阶级的自私、残暴与人才的发掘是格格不入的”[9]264。或者说,不止司马相如,身处汉代中央专制主义集权制度之下的汉代文人依附于王权,君主对臣子绝对的控制使得文士只能够通过迎合君主的喜好来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君对臣“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5]181,这与战国时期游走于各国的谋臣策士可谓是差之千里,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使汉代“悲士不遇”题材的文学作品兴盛不绝。
三、“视臣属如女色”下的性别阉割
“盛世”与“不遇”是汉代辞赋抒写的两条平行脉络。就“士不遇”这一主题而论,汉赋大家基本延续了屈骚讽刺的两大核心:一是直刺昏君不辨忠奸,时势难容;二是怨愤志士沉于下僚,难展其才。究其根本则是自屈原起,君主“视臣属如女色”的权力剥夺。司马相如追求实现政治理想抱负与汉代专制主义社会压抑束缚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传递出的正是无数汉代士人追求“君臣遇合”却不得的怨闷与无奈。
(一)臣属身份的重叠
《长门赋》中,陈皇后的妻子身份同司马相如的臣属身份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封建时代是重叠的。游国恩认为,中国自古以来“臣子的地位与妻妾相同。……妻道也,臣道也”,臣与妻均属同类[13]。在一个以男性为本位的时代里,“臣属被刻意矮化为女性”[1]5,君王对后妃与君王对臣属皆是单方面的统治和压制。君对夫与臣对妻的模式也会导致男性创作主体借异性关系来表达个人在政治际遇上与另一同性间的问题[11]563。文人多将君臣比男女,如屈原的《离骚》通篇贯穿了“男女君臣之喻”,“女人”是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论述材料,而“女人”正是象征他自己[2]192。如王逸在注“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一句时指出:“众女,谓众臣。女,阴也,无专擅之义,犹君动而臣随也,故以喻臣”[2]14,意思是为臣为女要听命于为君为夫之人,不能有“专擅之义”。又如王逸注“谣诼谓余以善淫”句为:“众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僭而毁之,谓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犹众臣嫉妒忠正,言己淫邪不可也。”[2]15可见,在文学作品中,君王“视臣属如女色,比君臣如男女”[1]23这一传统由来已久。
《长门赋》中,司马相如借陈皇后独守空房与自己“自媚君上”的共同遭遇召唤同情共感,以求重获帝王的青睐。首句“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娱”至“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5]130,以零聚焦视角看谪居冷宫陈皇后的孤寂凄凉,之后转入陈皇后视角自叙,从被抛弃到日夜等待君王,先写周围华丽冷清的景物,后写自己凄凉空虚的处境,足见失魂丧魂与忧郁惆怅,即使长夜难眠、形神枯槁也丝毫不敢忘记君王。“佳人”和“妾人”所指代的被遗弃的宫妃与受宰制的臣属都是受控制与被压抑束缚的“臣”,武帝“透过禁欲所展示的控制权”[1]24正是君权的力量。换言之,武帝以对陈皇后情爱的钳制与权力地位的掌控来强调自己统治地位的至高无上。“帝王以钳抑情欲、剥夺男权(为夫、为父之权),来保证统治的优势,而臣属则在性与权力上完全牺牲奉献于道德的荣光。”[1]22汉武帝统治下的前朝与后庭是一个完全以男性为主导的天地,在这一方天地间,生理上为女性的后妃与政治地位上如女性一般的臣属是很难参与进来的。君王将道德与情欲相关联,对臣属的“阉割去势”[1]19更体现在长臣子面对情色爱欲是否痴迷的考验中,在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和司马相如《美人赋》中,面对楚王与武帝的质问,两人完全不动心,义正严词地证明自己不好色。在他们看来,越是证明自己“不好色”,就越能展示自己道德品质的坚贞,只有这样才是诚心效忠君主。
赋家有举国经业的政治理想抱负,同时他们又是文学侍从,是被视为仅供愉悦耳目的倡优,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必然导致内心的痛苦。汉武帝把赋家看成倡优一类,只供满足君主的精神享乐与耳目之欲,却始终没有在政治上对他们加以重用。赋家固然艳羡叱咤于政治舞台中心的士子,但苦于身份所限没有机会“大展拳脚”,只能委曲求全充当弄臣,凭借过往所学侍奉王侯,寄望能一朝出头。在这些士子看来,弄臣身份只是一条助他们直通政权中心的捷径,却不曾想弄假成真[11]6,成为了弄臣。
(二)“同志共为治”的政治理想
“同志”二字在现代社会中特指同性身份,在古时却指有相同理想抱负的人。“同志”一词最早在王逸注《离骚》中出现,如注“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句云:“言自当勉强,上求明君,下索贤臣,与己合法度者,因与同志共为治也”[2]37;又如注“路不周以左转兮,指四海以为期”句云:“过不周者,言道不合于世也。左转者,言君行左乖,不与己同志也”[2]46;再如注“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句云:“执守忠贞,以自娱乐,且徐徐浮游,以求同志也”[2]42,以上几处出现的“同志”一词都指有相同理想抱负的“同道中人”,而非相同性别。周华山在《同志论》中指出:“同志不是由性行为对象的性别来界定的,它是个人(性)身份的政治选择。”[14]在他看来,“同志”是指同性之间志气相投与肝胆相照的盟友。“同志不必然是由性行为(对象性别)来决定,而可以是一种‘非生物化’政治身份。”[1]53对汉赋大家而言,他们终其一生追求的正是成为“君主奋发驱驰的盟友同志”[1]14。
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司马相如追求“君莫胜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15]2665这种和谐共进的君臣关系,但自“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15]2655,他寻求政治无望,只能退求文章不朽。《史记》与《汉书》中都有司马相如作《封禅书》的记载,明凌约言云:“相如《封禅书》,议者谓其至死献谀,然予观太史公《自序传》,其父谈曰:‘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是知当时以登封为盛,有事为荣,盖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当代,见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兴乐章,度其必封禅以夸耀后世。当其时,谓可秉笔托附不磨,由是草书,将以上劝,而不幸病以死,则初意不获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于是属其妻身后上之。”[16]司马相如虽在文中讽谏武帝不要封禅,但言辞却迎合着武帝‘好大喜功’的内心欲求,可见他其实预见到了武帝会有封禅之举,所谓的劝诫不过是如《大人赋》般‘飘然有凌云之志’的翻版。因此,《封禅书》其实也是司马相如最后推动且‘参与’武帝旷世伟业的一种政治行为。事实上,赋家用事无功,那些华丽的文辞亦不过是司马相如“讽谏”的载体。无论是“赋诗言志”与“讽颂得失”,亦或是“抒下情以托讽喻”和“宣上德而尽忠孝”[5]464,其根本目的是上达天听,虽“《长门》与《哀二世》二篇为有讽谏之意”的赋作,但赋家所谓的“讽谏传统”却也只是“王政之下”的讽谏。赋家“对国君的忠往往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达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手段”[9]379。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相如作传记之由“《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讽谏,归于无为”[15]2873。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本意是劝诫武帝不要沉迷仙术,最后反倒让武帝“飘飘然有凌云之志”[15]2663;《子虚》和《上林》中闳侈钜衍的丽靡之辞实与讽劝之义相悖,洋洋洒洒的辞赋反到成了臣子“宣誓效忠的去势戒律”[1]23。
身处汉武“盛世”却仍感生不逢无疑是对“盛世”的莫大讽刺。司马相如不满于弄臣身份,常称病不去武帝面前献殷勤,虽处盛世但这盛世“只讲穷达,不管是非;只讲成败,不分善恶;赏罚不明,贤愚莫辨;压抑人才,埋没人才”[9]404。吴质在《答魏太子谏》中提及,司马相如后期“称疾避世,以著书为务”,空有兼济天下之心却再无上升路径,没有了《离骚》主人公面对理想与现实相违时的誓死决裂与殉道精神,只有沉没在封建统治的漩涡之中,一切归于对现实的无奈与妥协。
综上所言,尽管司马相如为汉王朝歌功颂德,润饰鸿业,却有一颗不甘为弄臣的心。君臣本是同性却无法以同性身份直接对话,只能借助女性身份作为君臣交涉的媒介。君主“视臣属如女色”[1]23正是为臣者在汉代专制主义统治之下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政治迫害。赋家身处集权统治之下,得失都系于君主一人之手却还妄图成为君主“奋发驱驰的盟友同志”[1]14,“未摆脱时代的羁绊”[9]143却还有着“名挂史笔”与“事列朝策”的政治幻想,最后只能“趋于世俗之途”[9]143,一身才学化为满腔怨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