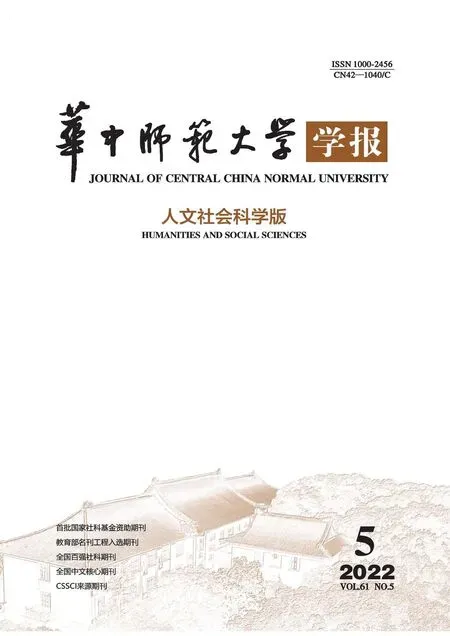邓之诚日记中的吴兴华
——兼及作家传记文献的拓展与限度
2023-01-04易彬
易 彬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一、引论:燕京大学→邓之诚→日记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家,基于历史原因,生前名声不显,日后在重新发掘过程中,往往会面临相关传记文献比较单薄的问题,吴兴华(1921-1966)即是一例。人们往往乐于视吴兴华为一个传奇式人物,友人宋淇(1919-1996)较早时候就有“陈寅恪、钱钟书、吴兴华代表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的说法,文学史家夏志清1976年的一篇关于钱钟书的文章中采信了其观点,对此也有推波助澜的效果(1)夏志清当时因误听钱钟书逝世的消息而作《追念钱锺书先生——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解志熙称,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之交读到此文,对所引宋淇说法“甚为吃惊”,此后才开始关注吴兴华,见《吴兴华佚文八篇(附:辑校札记)》,《新诗评论》2007年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0页。;日后吴兴华著作出版时,多袭用类似说法,如《吴兴华诗文集》(2005)、《吴兴华全集》(2017)的封底或腰封处,除了引述宋淇观点外,还有“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钟书式的人物”(王世襄)一类推荐语。但正如“如果”这一假设句式所示,其“传奇性”属未完成时,尚不能就此指认吴兴华的全部历史形象。如何更广泛地搜罗各类文献,构建一个更丰富的吴兴华传记形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这正是难题之所在!吴兴华早年遭逢战乱和贫困之境,后又经历了多次运动,于1966年过早离世,从搜罗文献最为齐全的《吴兴华全集》来看,自传类文献的保存度很有限,未见自述类文字,未见日记,书信虽单列一卷,但实际上仅收录1940-1952年间致宋淇的60余封信,这意味着其他书信或已不存于世。宋淇原名宋奇,又名宋悌芬,笔名林以亮,1935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全面抗战爆发后,曾在武汉大学、光华大学等校借读,1939年重回燕京并结识吴兴华,毕业后留校任教。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锁,宋淇移居上海,1949年移居香港,吴兴华书信得以保存,即与此有关。至于相关他传类文献,有家属和友人的一些回忆文,但总量比较有限,且一些回忆内容有待订误(2)参见解志熙:《艺文有奇传,只怕想当然——〈宋淇传奇〉吴兴华章订误》,《东吴学术》2017年第2期。。由此,循着相关线索深入发掘,以获取更宽泛的传记知识背景,尤有其必要性。在吴兴华的人生图景之中,“燕京大学”即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3)参见易彬、谢龙:《全集、作家形象与文献阀域——关于吴兴华文献整理的学术考察》,《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邓之诚日记即由此进入视野(4)参见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
邓之诚(字文如,1887-1960)为著名史学家,长期任教于燕京大学。吴兴华与其交往应是始于燕京大学时期,1937年,年仅16岁的吴兴华考入燕京,其时邓之诚为史学系教授。吴兴华后留校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邓、吴二人均进入北京大学,仍为同事。邓氏日记始于1933年5月1日,止于1960年1月1日,可说是横贯了吴兴华进入燕京大学之后的二十多年,仅其生命末期无从照拂。
《燕京大学人物志》有吴兴华“从张孟劬学《公羊传》、《谷梁传》,又从邓之诚学历史”(5)北京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的记载。1942年4月8日,吴兴华跟宋淇谈到自己正“大念中国历史,为彻底重念从古至今的中国诗的准备”(6)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页。。此处即或与张尔田(字孟劬,1874-1945)、邓之诚有关。1944年6月10日,吴兴华跟宋淇谈起“去看了几次张尔田,其学问甚博,with views so reactionary that they almost seemed radical——去请教一些公羊春秋的问题。”(7)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150页。在同辈人面前,吴兴华用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说法——小段英文翻译过来大致即是,“观点如此保守,以至于看起来几乎是激进的”。1945年张尔田逝世,吴兴华写过一则悼念短文(8)吴兴华:《张尔田先生》,《燕大双周刊》第2期,1945年12月8日。。关于邓之诚,吴兴华未专门谈及,其1951年9月10日致宋淇信中有“邓老”字眼,表示也许要搬家,“可以距芝联、邓老等都近些”(9)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24页。。不熟悉情况的读者,当不知“邓老”为何人。
邓之诚日记关于吴兴华的记载始于1946年初,即吴兴华重返燕京不久,止于1959年10月,近70条,基本上以“吴兴华”称之,有几处记为“吴馨华”“吴”,根据前后语境,也可确定之。看起来,最初的记载比较稀疏,交往或不多,1950-1953年间较为频密,1954-1958年间较为稀疏,1959年又有增多之势,但随着1960年1月初邓之诚逝世,记载即戛然而止。
邓之诚日记之于吴兴华传记文献而言,是一次比较明显的拓展。观诸文献效应,吴兴华致宋淇信作为自传类文献,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详细,书信计有十多万字,吴兴华的日常生活、诗学观念、写作与翻译以及相关人事、时代因素均有较多展现;一是连贯,尽管部分年份偏少甚至空缺(1946年、1948年各两封,1945年、1949年各1封,1950年空缺),但1940-1952年间的吴兴华形象仍不失其连贯性。因此,在吴兴华研究之中,这些书信值得充分重视。相较而言,邓之诚日记属非直接性的他传类文献,相关信息往往比较简略,近70条记载,有近30条为“吴兴华来”这类最简单的信息,但时间跨度近十四年,也有持续的、连贯的效果,且其时段与吴兴华信有重合,相关信息可对读之,以获取更多元的信息,激活更多的话题。
二、时代气息、校园氛围与个人遭遇
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吴兴华致宋淇信明显不足,信息阙如,而邓之诚日记对于时代多有记载,无论是否涉及吴兴华,作为一种宽泛的传记背景当无疑义。
比如1945年,正值抗战胜利、燕京大学复校的时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查封后,吴兴华经历了几年异常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返燕京。但该年书信仅1月25日一封,且几无现实层面的内容,而是表示“来日太阳一出爝火全熄定有一个与政治复兴相当的学术方面的振起,这个责任我们若不担负,还要推给谁呢?”(10)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162页。即便在艰难岁月里,吴兴华仍将“学术方面的振起”视作个人之责任,这是其传记形象非常重要的一面,而现实层面的因素则有待其他文献的补充。
邓之诚1945年日记中多有关于燕京大学人物事迹和复校事宜的记载,如“诣洪煨莲,告我以十月十日复校,旧教职员曾在伪组织、学校、研究所及机关任要职者,不再邀请;已有职任,一时不能脱离者,亦不邀请”(9月1日);“为燕大作募捐启,煨莲昨所嘱也”(10月1日);“往燕京观开学礼”,“今日此间行受降礼”(10月10日),等等(11)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302-303、303、304页。。这些即吴兴华重返燕京前后的总体背景。
再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刻。本年吴兴华信也仅3月23日一封,为平津通邮之后所写,称“北大、清华、燕京都已照常上课,学术研究,也极自由”,“开始温习那些英国文学的书籍”,“此地新书甚不易来,故只有钻故纸了”(12)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00-201页。。语气与1945年信相若,看不出多少时代紧张感。查邓氏日记,1949年3月2日有“本校正式上课”的内容;10月1日有“校中师生皆入城,庆祝新中国之诞生,新政府之成立”的记载(13)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470、484页。。
再则就是1951-1952年间,燕京大学先改公立、后遭撤销的时刻。改为公立是在1951年2月,陆志韦被任命为校长,吴兴华多次跟宋淇提及相关事宜,如4月1日写道:“学校自改为公立以来,本年就此拖下去,作一些准备工作,以后‘坚决而稳步’的要进行课程改革。各方面问题甚多,皆待商讨。政府态度很虚心”(14)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09页。。
邓之诚此时在叙及燕京事时,吴兴华的名字多次出现,如1951年2月12日:“下午,高名凯来,言:今晨接收演说……派陆志韦为校长,皆好听之话。傍晚,陆志韦欢欣跳跃而来,言大功已成。夜间,校中火炬游行,有焰火。”3月8日又有:“陆志韦、高名凯、吴兴华来,陆面邀明晚到彼家开文、哲、史三系研究会议。”(15)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558、561页,按,本文引文中的“……”均非原文所有,而是笔者因省略部分原文所加。对照之,陆志韦携吴兴华等人前来当与校务有关。1949年10月5日,吴兴华当选为校教务委员会委员(16)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主编:《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366页。;1951年1月22日向宋淇表示:因为燕京大学的“外国人都已逐渐离去”,自己“在系里地位‘日益重要’”(17)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03页。。以此观之,其重要性不仅仅在教学方面,在人事、校务、教务等方面也有体现。
关于燕京大学末期的校园氛围、学校被接收的情形,1952年的邓氏日记也多有记载:
(1月24日)下午一时,校中开反浪费控诉大会。本定晨九时开会,以昨夕会至深夜,故改下午。首由陆志韦检讨,众嫌太泛,令其下期再说。……明日上午,各系继续开会。下午,开展览会,反动国旗及贪污浪费证件均须陈列。今日之会,陆公受窘可谓至矣!
(6月12日)晚,蒋南翔在校讲学校以学习为要,政治系为学习服务,能为人民服务者,即不当目之为个人主义、单纯业务观点。
(10月4日)今日北京大学行开学典礼。从此,燕京成为历史名词矣……晚有捷克歌舞。(18)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628、654、675页。
现实远比邓之诚所记更为严峻!这些或紧张或热闹的情境之中都没有出现吴兴华的名字,但发言控诉或游行庆祝的队伍之中是有其身影的,“陆公受窘”事即一例。陆志韦是燕京大学的老校长,学生吴兴华被认为是其“最为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19)巫宁坤:《一滴泪》,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第19页。。但陆、吴之间有一桩“公案”,即在1952年春全校师生员工揭批、控诉陆志韦的大会上,吴兴华以及林焘、高名凯、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等人登台。其批判文稿刊载于4月14日燕京大学校报《新燕京》(20)参见巫宁坤:《一滴泪》,第18-19页;林焘:《浮生散忆》,见《南大语言学》编委会编:《南大语言学》(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11-312页;方继孝:《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03-105页。。邓氏日记所载“陆公受窘可谓至矣”之事发生在1月24日,其中未列出吴兴华等人登台控诉一类细节,是否更早时候的一次亦不可知——邓氏日记对当时燕京校园内的人与事多有记载,不知何以更紧张、也更窘迫的情形未予记载。
但邓之诚记载的吴兴华个人事宜也别有意味,比如,1952年7月3日有“吴兴华来,言彼星期日结婚,不敢惊动我,当于婚后,同来拜见。”随后7月6日(即星期日)又有记载:
下午六时一刻,大雨历半小时而止。……全校教师冒雨入城至教育部听钱俊瑞三校合并第二次报告。吴兴华结婚行礼毕,亦逐队而往,盖教师学习结合三校调整,不可缺课也。予老病不能往,殊为阙事。(21)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658页。
7月19日,吴兴华跟宋淇谈到结婚之事,不过没有提及“逐队而往”的情形:“我们结婚很有意思,一切全由系里其他先生代办,我根本没有参加意见,也没有出多少钱。现在的仪式全是这样,很简单。”(22)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37页。若此,个人生活既可以由组织“代办”,婚礼、大雨与集体学习叠合在一起,也就不足称奇了。
及至形势日益紧张的1957年,邓之诚9月8日又有记载:“今日校中东操场有杂技,家人往观。见吴兴华妇子嘻嘻,亦在场中,批评斗争若无其事然。”(23)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1039页。据吴兴华妻子回忆,当时“由于对苏联专家的教学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打入‘地狱’。不仅撤去职务,降了级,还剥夺了教书、写作的权利。”(24)谢蔚英:《忆兴华》,见吴兴华:《森林的沉默:诗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页。对于此番境遇,吴兴华却作“若无其事然”——如此坦然或许会让人吃惊,但在20世纪40年代那些“身逢乱世,生活朝不保夕”的时刻,吴兴华亦泰然处之,比如,“日本人来了,一家九口挤在会馆”,“依然若无其事”地跟宋淇“讨论梅花诗”(25)宋以朗:《宋淇与吴兴华》,见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59页。。1957年对于个人处境的这种反应,也属其一贯的处世方式。
随后的记载也继续显示了吴兴华处境的恶化,1958年邓氏日记没有吴兴华到来的信息,仅2月17日记载了高名凯传递“吴兴华撤职,另予较低职务”(26)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1069页。的信息。1959年的5则记载,有3则出现了“久坐而去”(6月28日)、“久谈”(7月26日、10月10日)一类字眼,其时邓之诚身体状况已欠佳,吴兴华仍“久坐”“久谈”,当是“满腔心事和盘托出矣”(27)借用邓之诚1952年12月9日日记中的语句,见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691页。。
1959年9月5日,邓之诚写道:“吴兴华来,与谈及报载:赫鲁晓夫前日在作家萧洛霍夫家作客事。吴言:列宁尝致书党部,谓爱惜名士,当如保护名花也。”(28)邓之城著、邓瑞整理:《邓之城文史札(修订本)》(下),第1181页。援引领袖“爱惜名士”的言论,其中无疑包含了吴兴华个人的切身感受与生命诉求。
三、吴兴华的阅读小史
邓之诚是一位治学、藏书兼备的史学家。书籍、阅读是邓氏日记的重点所在,其中多有吴兴华借书、还书、赠书以及相关书籍的信息,略加规整,可以发现某种内在的线索。
吴兴华为好读书之人,常手不释卷,但时乖命蹇,上大学时,父母即相继病逝,他作为“家中主要的生产者之一”,“家累甚重”——始终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20世纪40年代曾陷入个人生活朝不保夕的境地,自己被家传的肺结核病所苦,两个妹妹更是因生病、无钱医治而先后死去。新中国成立之初,情形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诸如“要养病,经济情形奇窘”;“这些年来一直是我一人担负弟妹教育,劳累困难,也是病总不好的缘故之一”(29)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02、208页。。以此来看,吴兴华似无力进行充裕的购书和收藏,或者说,相较于其超乎常人的阅读量,个人藏书乃至校内图书馆的藏书均难以满足其需要(30)谢蔚英回忆称,因“没地方放”“加上经济困难”,1971年从干校回来后,将《四部丛刊》及经史子集等共12箱卖与他人,若此,吴兴华实际藏书量也不小。见吴丹:《吴兴华:“失踪”半个世纪的天才诗人》,《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3月3日,第A11版。,向藏书丰厚的人士借书自然是其获取阅读资源的重要途径。
最早的记载是1948年4月19日,“吴兴华来借《赖古堂集》、《居业堂集》、《读史亭诗集》。”(31)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449页。此后所借之书有《通鉴注商》《思适斋集》《王西斋集》《顾亭林诗笺注》《南宋杂事诗》《阎古古集》《鲒埼亭集》《鲒埼亭外集》《湘绮楼未刊文》《旅堂诗文集》等。
也有吴兴华携来重要书籍、钞本或传递相关信息,如1951年8月17日记载:“吴兴华来,以《愚谷诗稿》见示,盖张芝联自上海借来者,读之如获重宝,当托人传钞一本。”9月20日又有:“吴兴华来,言:王沄《辋川诗钞》六卷在《艺海珠尘》竹集,《云间第宅志》一卷在上集。当借阅之。”(32)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582、587页。钞书是邓之诚搜书的主要途径之一,“遇到重要书籍,而又无法购买时,多托人抄录副本”(33)王献松:《邓之诚藏书聚散考略》,《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7期。,故“托人传钞”“当借阅之”一类语句,均显示了邓之诚对于吴兴华所示或所论版本的激赏。1957年1月13日、1959年6月28日,又有吴兴华来告知“北大买得钞本《肇域志》”“校中善本图书室买得吴农祥钞本《骈文留铅集》二册”的记载(34)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988、1166页。。
赠书的记载有两次。前一次颇显情义,发生在1948年10月,先是4日,“吴兴华来,送美国纸烟一条,厚礼也。”14日,“招吴兴华来,以《西昆酬唱集》注、《淮海同声集》赠之,报馈纸烟之惠也。”(35)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460页。后一次则是1955年8月31日,“晨,吴兴华来,久不来矣!”“坐久始去,以《琐记》一本赠之。”(36)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888-889页。《琐记》即《骨董琐记全编》,堪称邓之诚的代表作,前一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对于吴兴华的读书情况,邓之诚的激赏之情也有流露。如1951年10月11日,由吴兴华“自孙星衍《松江府志》钞得李逢中事实”,引发了欲求证究竟是“李逢申”还是“李逢甲”的想法(37)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589页。;1953年11月25日则作赞词:“吴兴华来,久谈,言:李善注,误南齐刘整为梁刘整,可谓读书心细。”(38)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761页。
邓之诚日记有一些对于当时书籍和人物的激烈品评,有两次吴兴华在场。1953年9月5日论及杨树达《〈淮南子〉证问》,认为“穿凿支蔓,时杂谩骂,甚欲取胜前人……然非杨树达可得而望也。妄至于此,妄由于自矜,自矜由于不悦学,为之一叹!适吴兴华来,遂举以予之。”1959年8月11日则有:“吴兴华来,言:有钱钟书者作《宋诗选注》,自谓过厉樊榭远甚。举世皆狂人,当食无肉,天所以罚之,我辈受其拖累耳!……此人亦颇自豪,大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概,是不只风狂,直是妖孽矣!我辈乃与之共一世界,岂非命乎!”(39)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741、1174页。此类认为时人著作颇狂妄的记载,满纸都是厚古薄今的气息,大抵即是邓之诚身上的老派学人或古名士气使然。
关于吴兴华的写作也有一处记载,为1950年3月14日:“吴兴华以所撰《读〈通鉴〉札记》求正。”(40)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508页。此文后载《燕京学报》第39期。观其内容,不少即涉及所借之书,除了明确引述赵绍祖的《通鉴注商》外,还引述了全祖望(《鲒埼亭集》《鲒埼亭外集》的作者)的著作,并多次提及顾亭林(炎武)著作,由此可见所借阅图书之于写作的效应。
上述关于阅读、写作及相关话题的记载,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乎古籍,作者则多是明末清初以来的人物。这是邓之诚治学与藏书最专深的领域,也是吴兴华一段时间之内的寄怀所在,个中情形,如1951年9月10日吴兴华与宋淇所谈:
我最近中国书大都念的是明清时代的史籍诗文集。特别是明末清初的人物与文学,钻研得相当透彻,环顾四周,也可以说:“不如我者多,似我者少”了。明末志士遗民的著作,具有百折不回的坚韧性,尤可令人奋发,时时翻读甚为有益。(41)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24页。
更早的时候,1945年1月25日,吴兴华曾表示“近来读书以史籍居多,尤其对古今兴亡治乱割据盈缩之迹再三致意”。1951年2月20日,也曾引王荆公《凤凰山》中的诗句,“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以为“整个旧诗领域内很难找到如此悲哀的句子”(42)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161、206页。按:所记与王安石《凤凰山》原诗有出入。。以此来看,在历史转折之际,吴兴华于史籍之中寄寓了很深的感慨,而那种“令人奋发”的、“百折不回的坚韧性”,当是他历经磨难而仍埋头研读的动力之所在。
四、相关人物与交游
邓之诚日记之中曾与吴兴华同时出现的人物计有:高名凯、陆志韦、张芝联、聂崇岐、徐献瑜(以上有多次记载)、许大龄、张伯驹、孙铮、张东荪、王钟翰、翁独健、余敏、林元汉、徐苹芳(以上有两次记载)、陈淑华、乔维雄、周桓,林树惠、王兆荣、宋毓珂、余逊、杜洽、哲学王、阎简弼、王之均、汪镳夫妇、李文瑾、陈街坊、缪四爷、陈述(以上为1次记载),等等。
陈街坊、缪四爷等人应该是街坊邻居,此处不议。其他的主要是燕京、北大的师生,其中,仅张芝联(1918-2008)、陆志韦(1894-1970)等较早即在吴兴华人物关系研究视域之内,一些老师辈的人物如张东荪(1886-1973)、聂崇岐(1903-1962)、高名凯(1911-1965)、翁独健(1906-1986)等,在相关文献中偶有提及。多数人物则是首次见闻于邓之诚日记。这在一定程度上透现并拓展了吴兴华的人物关系圈,可以此为线索,作进一步的梳理。
比如张芝联,1935年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37年因战争原因转入光华大学,1941年重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后辗转中法大学等校,又在耶鲁、牛津等校有过一年多的留学经历,1951年从光华大学北上燕京大学任教,随后转入北京大学,其所作《我认识的才子吴兴华》为2005年版《吴兴华诗文集》的“代序”,其夫人郭心晖(郭蕊,1937年毕业于心理学系)、宋淇之子宋以朗也有相关文字。
邓之诚1951年上半年日记多有吴兴华传递张芝联“即将来校任教”信息或“同张芝联来”的内容,之后也多记及张芝联,如1953年3月15日有:“张芝联来,言彼家藏书善本万余册,寻常本二万册,悉数捐与本校文学研究所。存我处二种(《愚谷诗稿》徐开任、《洵美堂集》杨文骢),即以见赠。”(43)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704页。
张芝联日后在世界史特别是法国史方面造诣深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回顾个人学术道路时,曾谈到洪业(洪煨莲)教授建议其“以明末清初历史作为专攻范围”,“明末清初是中国和西方文明初次接触的时期,这段历史西方学者虽作过不少研究,但他们没有掌握中国资料;中国学者也有志于此,但缺乏西方语文的训练,无法利用外国材料”;同时,“明清史专家邓文如教授和瑞士教授王克思有能力来指导”(44)张芝联:《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6-7页。。邓文如即邓之诚,王克思即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1888-1956),任教燕京大学二十多年,主要教授西洋史、基督教史等方面的课程。此回忆一方面勾描了其治学理路,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吴兴华—张芝联—邓之诚”之间具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观诸相关写作,张芝联在张尔田、聂崇岐的指导下写过论文《〈资治通鉴〉纂修始末》(载1944年《汉学》创刊号),而吴兴华从小即熟读《资治通鉴》,日后作《读〈通鉴〉札记》,其间应是有着学术关联。再者,吴兴华20世纪50年代所作《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载《文学遗产》,1998年第4期),论及清代常州作家骈文,其论证“骈文有近乎诗的属性”一节,既引述刘勰《文心雕龙》等大量古代文献,又频频引述亚里士多德、柯勒立治以及现代批评家赫伯特·黎德等不同时代的西人观点,这种广博的中西诗学对照视野,很符合洪业教授的期待——抑或说,很符合燕京大学的总体氛围。可见,吴兴华虽在西语系,但密友之间的学术动向及学校氛围,也构成了其学术生长的内在理路。
哲学系教授张东荪(万田)为张尔田的胞弟,1941年七八月间,张东荪曾找吴兴华处理宋淇的中译英稿件(45)参见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4-8页。。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张、吴仍为北京大学同事,不过未见两人交往的信息。语言学家、翻译家高名凯的名字在邓氏日记中出现频次很高,曾与吴兴华同来,也传递了不少信息,可见作为燕京、北大同事,实际交道不少。聂崇岐为宋史研究专家、目录学家,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与吴兴华的名字暂只见于燕京大学的一般性描述之中。20世纪50年代,聂崇岐点校《资治通鉴》,并展开研究,不知两人是否有过交集。史学家翁独健曾任燕京大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其任教务长期间,吴兴华为教务委员会委员,更多情况则无从获知。
张伯驹(1898-1982)也是老师辈人物,目前未见张、吴二人交往的直接线索,倒是从一篇关于周汝昌的回忆中获知,1939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的他当时也是一位诗人,曾“与张伯驹、吴兴华等先生唱和”(46)吴小如:《诗人周汝昌》,见周伦玲编:《似曾相识周汝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6页。。周汝昌的名字曾出现在邓之诚日记之中,周汝昌也自陈其红学研究得益于邓之诚的指点(47)参见周汝昌:《史学大师邓之诚先生》,见《师友襟期》,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23-27页。。《燕京大学史稿》则有吴兴华所承担的翻译课“曾因病由周汝昌代课一个学期”的内容;许大龄、阎简弼以及聂崇岐等人,在燕京大学1951年5月公布校公共课教研组负责人名单中,与吴兴华并列其中(48)参见张玮瑛、王百强、钱辛波主编:《燕京大学史稿》,第86、1374页。。至于徐献瑜、王钟翰、宋毓珂、徐苹芳等人,目前未见相关线索。
最后要说的是吴兴华与日记作者邓之诚的交谊。吴兴华在西语系,邓之诚治中国史。吴兴华意欲综合中西诗学(这在致宋淇信中多有展现),有此自觉意识,故“从邓之诚学历史”。现在可待归结的是,这种交往何以能持续十数年?
纵观邓之诚日记,有的人物交往一度非常频密,后来又因为某些原因少有出现,比如陆志韦,1945年燕京大学复校之后数年内,他可能是邓氏日记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人物。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陆志韦调至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邓氏日记慢慢地就没有他的身影。吴兴华不然,一则他们始终是同事,在同一个校园,行走间即可能遇到(日记中多次记载),来往颇便利;二则,邓之诚丰富的藏书、对于版本的激赏、在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方面深厚的学识,都吸引着吴兴华不断前来。吴兴华对于张尔田的评价,“学问甚博”“观点如此保守,以至于看起来几乎是激进的”,放在邓之诚这里大抵也是合适的。再则,如前所述,尽管邓氏日记的相关言辞很简略,但从“久不来矣”一类感慨以及“坐久始去”“久坐而去”“久谈”一类记载还是可以见出其中所跃动的精神涵蕴,吴兴华于史籍独有寄怀,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50年代,邓之诚已然成为那种既能满足其精深而僻冷的阅读需求,又能给予某种精神慰藉的人物。这当是促进两人交谊不断延续更为内在的动因。
五、余论:文献之限度
日记之于作者本人自是最恰切的自传类文献,对于所记载人物的形象呈现、线索发掘等方面,往往会有特别的效应,但也必然有其限度。这些方面的情形,可从未记和实际记载的角度略作说明。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记录视角与实际内容。邓之诚是一名老派史学家,其为人为学均有古名士之风,这一身份与视野也贯穿于日记。其所记录的吴兴华,倾向性其实非常明显:吴兴华作为一位好学、熟读乃至精通中国史籍的学者形象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而其他方面少有记载,相关形象也就无从展现。
吴兴华作为新诗人的形象从未被记载,恰如内容非常翔实的吴宓日记,关于“查良铮”有十余次记载,却从未涉及“穆旦”及其作为“新诗人”的一面(49)参见易彬:《〈吴宓日记〉中关于穆旦(查良铮)的记载》,《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2期。。关于“新诗”,邓之诚或许只有一条记载,即1950年7月6日,“汪玉岑自沪来见,新诗之人也。”(50)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523页。吴兴华此前多次与宋淇提及这位燕京诗人,但两人当时是否有过会面,则不得而知。
吴兴华一直对外国文学多有阅读,非常熟稔。1951年5月13日,他跟宋淇谈道:因为“代教十八世纪文学”的缘故,“大看”斯威夫特等人作品;1952年7月19日更是表示“已经把兴趣完全放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上”,也引申着钻研“十七和十九世纪英国和欧洲,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学”(51)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13、237页。。这类外文教学与读书方面的信息不见闻于邓氏日记。
吴兴华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与翻译者的形象,有一条记载,即1953年12月20日,“吴兴华来,久坐,言中印友好团。丁西林此次往印度,所备演讲稿由彼翻成英文,稿中称引司马迁《史记》,推服备至。”(52)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下),第769页。其实,吴兴华当时的翻译工作很不少,包括国家翻译(如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翻译工作、中共八大文件的翻译等)、文学翻译(如《亨利四世》等)以及自认是“为了生活”(53)吴兴华:《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第221页。而作的翻译(如萧乾的一篇小说、萧三的《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等)。这些行为亦不见闻于邓氏日记。
私人日记贯穿着作者的内在视角,由此导致某些在旁人看来可能重要但未记或仅简单记载的情形并不稀见。比如,燕京大学国文系容庚教授1938-1944年间的日记约有7次提及邓之诚,有的内容看起来比较重要,如“访邓之诚,假得沈复《山水》轴”(1938年1月9日)、“至邓之诚家开历史研究会”(1940年11月20日)之类,但对照之,邓氏日记多缺记,仅1943年2月27日同有记载,内容方面又有差异(54)参见容庚著、夏和顺整理:《容庚北平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518、635、680页;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修订本)》(上),第186页。。由此推想之,邓氏日记关于吴兴华唯一的一次翻译记载,很可能是因为涉及古代典籍《史记》而得到特别看待。若是,则新诗、外国文学、翻译等方面信息未被记载,也未必是不曾谈及,而是最终未进入其日记视野,而代之以“吴兴华来”“吴兴华又来”“久谈”“久坐而去”等笼统性的用语。
就实际记载本身而言,内容的详略程度也是必须面对的事实。邓氏日记对书籍往往详加记载,对于众多往来人物则多简笔勾勒,而且,吴兴华在西语系,邓氏日记人物多是其同事、学生,多与中国史学相关,其间存在不够对等的状况,这意味着相关线索能否成型,还需要更多文献的支撑。至少在目前,部分人物关系即便有线索提示,能搜寻到的确切文献仍相当有限,发掘通道多被阻断,而少量的相关回忆往往也没有旁证,如吴兴华与张伯驹、周汝昌的交往是否确切,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订。
总的来看,尽管与致宋淇书信这一自传类文献不可同日而语,但在目前所见吴兴华同时代文献之中,邓之诚日记是时间跨度最长、记载最为频密、同时也独具精神涵蕴的一类记载。故本文以此为中心,详加剥索,以图发掘时代与个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类线索,为原本单薄的吴兴华传记图景增添较多新因素、新线索。也因为如此左右腾挪,清晰地碰触到文献的限度,深感缺少线索或有线索而无从继续追索的困局。吴兴华近年来被“打捞”出来,其传记形象一时之间难以全面树立,文献始终是症结所在。
由此而言,吴兴华传记的难度,亦在于其知识的广博——尽管就实际成就而言,吴兴华的才华未得充分施展,难符“兼通中西的大儒”之名,但无疑地,唯有相当的知识素养,方能给出更全面的研究成果,获得更丰满的传记形象。